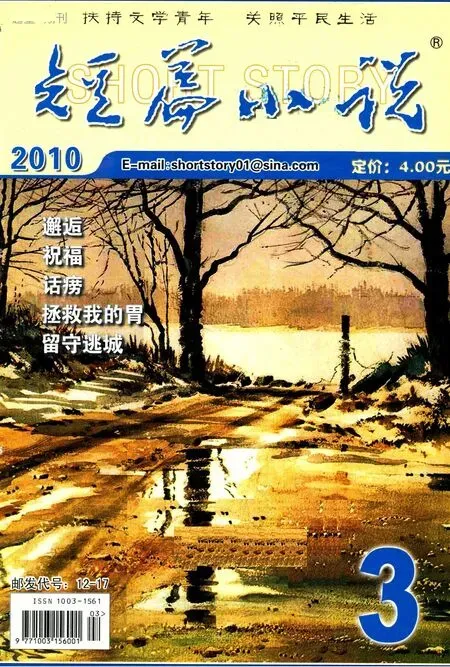边界
◎王晓静
边界
◎王晓静

这是一个漂亮的女人,从她腰肢款摆坐上车,庄成明的眼睛就像长了翅膀似的一直围着她转,女人穿着一条极短的裙子,那其实根本不能算作是裙子,直白点说,更像是一片薄薄的玫红色的布。这布紧紧地包住了女人呼之欲出的臀部,但好像也没遮掩住啥,女人轻轻翘起腿,薄布与大腿根处便出现了一小片魅惑的阴影,这阴影像一只柔若无骨的手,一点一点撩拨着庄成明,让他忽然觉得口干舌燥。
女人纤巧的手指拈了根烟,吸了一口,硬邦邦地吐出三个字:三里河。庄成明从眼前的香艳里重重地跌回现实中来,他的大脑飞速地盘算一番,报出了车价,话刚出口他的悔意便幽幽地从心底爬了出来,这价定得有些低了。为什么?是因为这个女人吗?也许吧,他承认被这个女人吸引住了,潜意识里他想做这笔生意。
有没有搞错啊,你打劫啊,这么贵!女人的脾气跟她的外表成反比,语气夸张而急躁。但在美女面前,男人们的脾气往往都像烧了半天的灯芯,蔫蔫地弯了。才二十出头的庄成明也不例外,他耐心地说,大姐,你问问别的司机,这价钱会不会拉你,我说的价钱真不高。女人猛地扭头,凌厉的眼风像把刀子一样掷过来,你叫我啥?你有病吧?睁大你的眼瞧瞧,我有那么老吗,还叫我姐,别恶心我了!这把刀子显然刺到了庄成明,一阵尖锐的疼痛像水波一样蔓延开,那些恶意的话语一个字一个字地刮着庄成明的神经,轻易地把他深藏的暴戾勾了出来,他死死地盯住了女人不停翕动的红嘴唇说,操,我不拉了,你下车!
你牛啥呢?我就不下!今晚我坐定你的车了!女人甩出几张钞票,气定神闲地把长腿搁在驾驶台上,那么完美修长的双腿,带着一种肉感的荤腥,像一片白瓷一样在如墨的夜色里泼剌剌地跳入庄成明眼里,扰得他一阵迷乱,他又开始觉得嘴唇发干,舌头发硬。
操,他在心里暗骂。车刷地像一尾鱼一样倏忽游入无边的黑暗里,荡起一路烟尘。女人扯着喉咙大声嚷嚷着,喂,你抢死啊,开那么快!庄成明狰狞着脸,扭过来说,再叫就下车!女人撇撇嘴,噤了声。但就在这一瞥间,庄成明愣住了,他忽然发现这个女人的面容似曾相识,这种感觉就像经常在梦里路过一条街道,当有一天这条街道真实出现在面前时,那种虚幻和现实的重叠覆盖让人深深地陷入一种怅惘感。庄成明努力从这种怅惘感里挣脱出来,又偷偷瞥一眼女人,开始在心里默默地将她洗去厚厚的粉底,擦掉重重的唇彩,拭净浓浓的眼影。再扳着她的脸看,他被一种深深的恐惧砸得头晕目眩,难道是她?怎么可能?他想起总是梦到的那片辽阔的水域,他被四面八方的水包围着,而水的深处有个面孔,被气泡和飘舞的头发掩映,模糊虚幻,但又仿佛近得伸手就可以摸到……
庄成明迟疑了一会儿问,你看着有点面熟,老家哪儿的?话一出口,他就发现自己的声音细弱无力,充满了犹疑和一丝丝胆怯,像一缕烟雾一样很快消失在夜风中,恐惧又像只猫一样悄悄盘踞在他心头,他怕那个答案被女人艳红的嘴唇轻巧吐出,是的,他怕女人就是她。正神思恍惚间,庄成明忽觉脸侧一阵香风袭来,女人凑近他的脸,伏在他耳边温柔地低语,你喜欢上我了是吗?想勾搭我是吗?找这样的话搭讪多俗啊。女人吐气如兰,庄成明的耳边像有无数细毛在轻抚他的耳垂,痒痒的,酥酥的,一股电流刷地击中了他,有种力量像匹野马一样在他的全身左冲右突,女人身上的幽香像一堵厚重的墙砸过来,将他砸得晕头转向。可这种令人窒息的甜蜜转瞬即逝,女人一扭腰,坐直了身子,从鼻腔深处发出一声冷笑,这冷笑饱含着轻蔑和不屑,像支箭一样刺中了庄成明。哼,一个开黑车的,还想惦记着天鹅肉。冷笑后的话杀伤力更大,庄成明心中狂奔的猛兽咚地撞到了坚硬的墙上,皮开肉绽。痛彻心扉过后便是怒火灼灼燃烧,烧红了他的眼。这女人鄙视的语气跟菁菁一模一样。
菁菁是庄成明的小女友,两人都是没上完学,很早便辍学回家了。他学了开车,买个二手车跑黑车,而菁菁在这个城市的国茂大酒店当服务员,两个人还算情投意合,晚上总是一起去吃个大排档或看场电影,沉浸在小儿女甜蜜的情思里。但随着时间的流逝,菁菁的心就像一块干净的白布慢慢被世俗染上斑驳的颜色,这颜色里有虚荣有攀比有欲望,她开始抱怨,不停地抱怨,抱怨庄成明挣钱少,没本事。这抱怨像秋天的落叶一样无休无尽,拂了一身还满。庄成明开始还能忍耐,慢慢便忍受不了了,都是二十出头的年纪,谁又能窝下去火呢。于是,争吵在所难免,两人经常三天一大吵,两天一小吵,不吵的时候只能是在床上了。有次两个人吵凶了打起来,瘦小的菁菁抡着一瓶矿泉水,清秀的五官因为愤怒皱到了一块,庄成明看着她那凶神恶煞的样子愣住了,他清清楚楚地发现她的眼底没有了往日的单纯清澈,而是变得复杂难懂了,他不相信,那里面竟掺杂了一些市侩、狡黠和凶狠,她再也不是当初那个为一对廉价耳环就能笑逐颜开的女孩了。
庄成明早就预感到像她这样心高气傲的女孩不会跟他太久。果然,一次吵架后,她爽快利落地收拾干净自己的东西,从他们租的小屋搬走了,他去酒店找她,她就躲着不见。过了一个月,庄成明在酒店门口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搂着菁菁上了车,那么粗壮的胳膊紧紧圈着瘦弱的菁菁,就像挟着一只小羊,只不过这羊是心甘情愿地送入虎口的,而庄成明只能呆呆地站着,看着她往虎口里跳,却无能为力,他感觉有种东西正从他的身子抽离出去,逐渐远离。
这是什么?是爱情吗?可他能怎么样呢,没有钱就失去了挽救爱情的资本。这几年来,庄成明的生意越来越不好干,跑黑车的人鱼龙混杂又缺乏管理,出过很多次事,搞得很多人宁愿在路边苦等出租车,也不愿坐 “黑的士”。其次是政府查得很严,很多同行都不干了,但庄成明还一直坚持着。这种坚持是绝境里的无可奈何,庄成明上学时成绩差,高中没念完就出来闯荡社会,没有一技之长,做生意又没有本钱,只好这样靠开黑车混口饭吃。庄成明忽然想起,有次吵架菁菁说,跟着你我看不到希望。庄成明愤愤地想,妈的!你找希望,也找个像样的啊,那么丑的老男人搂着也不嫌恶心!
女人忽然轻轻地哼起了歌,歌声像一把剪刀不动声色地剪断庄成明跟回忆黏连在一起的思绪。庄成明定下神,用余光偷偷打量女人的腿,那两条白花花的腿,闪着肉欲的光泽,庄成明强按下心头蠢蠢欲动的欲念,打开车上的广播,电台里正放着一首歌,音乐在车里流转,令人窒息的空气被轻轻搅动开来,打破了浓稠的尴尬。女人不耐烦的声音随着音乐骤然响起,你车有毛病吗?怎么开这么慢啊?要不是我今晚有急事,才不会坐这种破车。庄成明像是有了免疫力,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女人微微侧过脸看着他,忽然,她的眉眼一弯,脸上露出一种熟能生巧的妩媚,这妩媚里又含了一丝邪气。她轻笑一声问,你这么帅,有女朋友吗?庄成明心头的几簇怒火被这娇柔入骨的声音安抚了下去,但落寞仍然掩饰不住地从眼底露出,他没好气地说,分手了。女人脸上显出一种满意的神情,轻笑一声说,那肯定是嫌你没钱吧?庄成明有些不悦,你知道我没钱吗?女人撇撇嘴,尖着喉咙说,你一个开黑车的能有什么钱?一辈子也就这样了。原先心头那几簇零星的火焰马上像被泼上一勺油,刷地在庄成明心中燃成燎原之势,他叫道,嘿,你凭啥这么小看人?!女人满脸不屑的神情堆都堆不下,简直要淌下来,哼,开出租的就是没钱嘛,还非逼我说出来。如果我是你女朋友,也绝对跟你分手!庄成明气急了反而说不出话来,只能听到自己的鼻息声,这鼻息声在热烘烘的大脑里像用喇叭扩音了,沉重而急促。
正在这时女人的手机响了,她掏出来,捂着嘴对着手机小声说起话来,那紧张神秘的表情像是长出了无数触角,轻轻地挠着庄成明,挠得他心痒难耐。他恨不得将耳朵瞬间拉长成电视剧里的招风耳,在空气中努力捕捉女人细微的声音,放心吧!钱我拿到手了,是五万。现在就在我包里躺着,先不说了,我挂了。女人挂断手机,脸上立马挂上一层寒冷而坚硬的冰霜,她一脸戒备地看了庄成明一眼,两条胳膊紧紧地把包箍在怀里,那层冰霜好像瞬间冻结了她的全身,让她固若金汤,坚不可摧。庄成明赶紧将微微倾斜的身子坐正,装作专心致志地开车,但眼睛却被心中的鬼驱使着,偷偷地往女人怀里瞄一眼,再瞄一眼,那个鼓鼓囊囊的红色小包里可是有五万块钱啊!庄成明的心再也无法像刚开始一样正常跳动了,完全乱了节奏,像被一个五音不晓的人拿着鼓槌咚咚咚地一阵乱敲。五万块!是拉多少趟黑车才能挣够的呀!如果有这五万块……呵呵,庄成明想,一定要狠狠的摔到女朋友,哦,不,是前女友菁菁的脸上。到时候她会不会抱着自己,娇嗔着不让自己离开呀!庄成明踩着自己用想象一手打造出来的云彩,晕晕乎乎地横冲直撞。
可这团看似软绵绵的没有土壤的虚幻云朵里,却渐渐显现出一个清晰的核心,这核心的轮廓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在庄成明眼底,逼着他正视自己的所思所想:这钱不能让它从眼前飞了。庄成明忽然想起以前一块儿开黑车的朋友黑子,黑子在一次醉酒后曾亲口告诉过庄成明,有年夏天黑子拉过一个中年女人,那女人喝了很多酒,上车时还有意识,一会就人事不省了。到地方的时候,黑子迅速地拽下女人的金耳坠,捋下了她的金手镯,还拿走了她的钱包,一把把她推下车。干这行有个好处就是:只要司机不想出现,乘客们压根就没法找到。总共有五千多呢!黑子晃着酒瓶兴奋地对着庄成明吼。庄成明沉浸在回忆的河流中,一种异样的隐隐的骚动像条冬眠的蛇一样慢慢醒来。
突然,女人的声音在耳边像晴天里的滚雷一样炸开,你傻愣着干嘛呀?车开得像蜗牛一样,今晚咋遇到你这么个司机,真倒霉!庄成明心中游丝一样飘曳不定的迟疑马上被愤怒代替,那条苏醒的蛇刷地张开了血盆大口,庄成明忽然想起说书节目里常听的一句话: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原来这恶跟怒是同体相生,同体而存,牵动一个,便会扯出另一个的魂魄,如同一根腐木上长着的两朵毒蘑菇。庄成明知道,残存的善念已被这个脾气暴躁且说话刻薄的女人消磨得一丝不剩,在他心中已反复燃烧几次的燎原大火一直没被扑灭,那些愤怒的火焰上蹿下跳急需找个出口。庄成明开始慢慢地把车偏离了轨道,开向了一条比较偏僻的公路,路上偶尔有车往来,但几乎没有行人。他心中那团模糊的骚动渐渐长出轮廓,露出清晰而狰狞的面孔。
树木在夜色中像半蹲的黑黢黢的怪兽,夜风清冷,路两边是大片大片泼墨般的浓黑。女人看着窗外,平静的神色慢慢起了变化,惊慌的表情在脸上闪过。她问,喂,你这是要去哪儿?!庄成明缓缓地说,去你要去的地方呀。他阴沉的声音虽然不大,但却像块铁块一样尖锐冷硬。女人失控地叫了起来,这不是我要走的那条路!你啥意思?!庄成明此时满眼都是那红得耀眼的包在飞速地旋转,女人的声音虽然尖细高昂,但在他耳朵里仿佛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抵达到他心里时只剩下一丝微弱的余音,仿佛是被宰割的羔羊临死前的哀鸣,而作为决心杀它的猎人根本无心顾及。
庄成明颤抖着手把车缓缓靠到路边,女人的叫声里饱含着恐惧,你要干什么?你有病啊?庄成明趁她情绪激动的时候,快速而有力地一把拽过她怀里的包说,我最近缺钱用,下车!那个包带着女人微热的体温被紧紧裹在庄成明怀里,凭手感都能摸出那鼓鼓囊囊的就是人民币,粉红粉红的人民币,无所不能的人民币!女人惊呆了,摆出一副不要命的架势扑上来抢包,嘴里的污言秽语像打翻的水一样汩汩不断地流泻出来。
庄成明生气了,使劲推她,骂她,把她往车外蹬,可她像只顽固的粘虫一样死死地粘在车门上,她一边用手抠着车门一边大声喊,救命啊,救命啊!抢钱啦!旁边的马路上遥遥地可以看见几星灯光,那是远方驶过来的汽车,庄成明害怕起来,怕被过路的车辆听到。就一把把她拽上车,心里想道,妈的,就不信收拾不了一个女人!他使出蛮力把她压倒在车厢里,又从车座下翻出一根绳子和一团破抹布,没费多大劲儿便把女人的双手捆起来,把她咒骂不休的嘴塞上。女人睁大眼睛,愤怒地瞪着他,嘴里还含糊不清地呜呜着。
庄成明的回忆忽然像被剪开了一个小口,不小心洒落出来一些往日的光影。多年前鬼影般的树林、昏黄的月光、暗褐色的血都如暗夜里的幽灵缓缓浮现,仔细看又面目不清,遥遥地向他招手。这些往事的片段让他有一瞬间的犹疑,但拉开包,看着那粉红诱人的人民币活泼泼地跳入眼帘,他的心又坚定下来,定若磐石。他忽然理解了那些杀人越货的强盗。在诱惑面前,人的意志力太脆弱了,脆弱得就像冬日的窗花,薄薄一层,呵气即化。动物本能无法战胜人类的意念,所以会犯罪。在欲望上,每个人其实都一样,这条界线是如此轻易便能越过。
庄成明为自己的良心找好了说辞后又开始发愁,怎么处置这女人呢?把她扔到路边?这荒郊野外的,万一她出了什么事,警察顺藤摸瓜地找到自己咋办?把她带到人多的闹市区?那不是给自己挖坑吗,人多眼杂的,看到一个被绑架的姑娘,人们还不马上报警。那把她带回家?庄成明瞥了她一眼,不由地喉头发紧,这样漂亮的女人哪敢放在家呢,他真怕自己会把持不住。
庄成明把嘴里的烟头摁灭,把她搬到了后备箱,女人蜷着修长的双腿,他不敢看她的眼,刻意回避着,但仍能感觉到她冰冷的眼神像蛛丝一样粘在他脸上。折腾了半天之后,他就着车里昏暗的灯光数了数包里的钱,果然有五万。他慢慢地开着车,一边开一边想,把女人放在哪呢?有好几次,庄成明都想把女人扔在路边,但说不清是什么原因,他最终没有这样做。
夜色像一块巨大的黑幕披头罩了下来,掩盖了大地上发生的一切罪恶、秘密和躁动。忽然,砰地一声,车被重重地撞了一下。庄成明从后视镜一看,原来是追尾了。真他妈倒霉,他骂了一声,心也像被撞了一下疼得要命。这些年,钱几乎都花在菁菁身上了,他手头没一点积蓄,只剩下这辆车了,对这唯一的家当他可是爱如珍宝,精心地保养、护理,一有空就仔仔细细地擦得一尘不染。
但只是一瞬间庄成明又想到了女人,刚才撞的力度不轻,不知道她怎么样了。这时,车窗上响起了笃笃笃的敲击声,像一只啄木鸟带了几分试探啄着树干。寂静的夜里忽然响起这声音,把庄成明吓了一跳,一扭头,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正在窗外敲着玻璃,从他比划的手势可以看出,他就是肇事的车主。庄成明拉开车门,噌地跳下去怒道,你咋开车啊!老头谦卑地弯着腰,一个劲儿地道歉,兄弟,对不住啊,我是新手。你看看该赔多少就赔多少,我绝不耍赖!庄成明拉着脸走到车后,仔细查看着被撞的那块车皮,一面揣摩着女人是否会受伤,一面按压着心中那几欲窜出的担心和焦虑。就在这时,他眼角的余光隐隐捕捉到一小片黑影,像鬼魅一样缓缓地漂移。只是瞬间,他便意识到,这是一群人!后面的车上走下来了好几个人,悄无声息地向他围拢过来。不祥的预感像粒火星一样在心中亮了一下便彻底熄灭了,因为他刚想转身,便觉脑袋剧烈地一痛,眼前一片漆黑。
等庄成明再睁开眼的时候,发现在自己的车里躺着,头像是被砸碎了又黏上,满是钝钝的疼,空气中有一缕阴凉的血腥气像小蛇一样爬过他的鼻翼,一定是脑袋后面被打出血了。庄成明定定神,努力让意识彻底醒过来,他的手上捆着绳子,嘴上贴着胶布,周围坐着两个人,都用黑布蒙着脸。一个在开车,另外一个坐在庄成明旁边,鹰一样阴鸷的眼神死死地盯在庄成明的脸上,阴恻恻地说,他醒了。开车那人说,看好他,老大说了这条路上车来车往的,换个地方解决他。另一个人又说,看他开车那么慢,本来以为是个女的开的,妈的,竟然是男的。
庄成明的心骤然跳得失去了节拍,只差一点便要从喉咙里跳出来,糟糕,遇上劫匪了,而且是要置他于死地的劫匪。他暗自使出全身的力气想挣脱手上的绳子,恨不得立马学会武侠片里的缩骨术,可无奈绳子捆得死死的,根本无法挣脱。盯着他的那个人感觉到了他的动作,一脚把他从座位上踹了下来,你小子给我老实点!庄成明痛得蜷成一粒虾米,一动也不敢动。他心里暗想,报应这么快就来了?还想抢人钱呢,没想到还有黄雀在后。一时间哭笑不得,如灼铁一样烫手的欲望早被泼上一盆冷水,冷却下来之后便凝铸成了坚硬的后悔,他想起小时候常听的那些故事,愚蠢和贪心的人往往没好报,像那个渔夫的老婆。唉,一声叹息从心底像缕烟一样地飘逸出来。
忽然,庄成明想到了那个女人,如果自己死了,还有谁知道她还在后备箱里呢!也许她会因缺氧和饥饿死在那里!庄成明心里开始升起一股巨大的焦灼,紧接着他又为自己的焦灼而感到可笑,已经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了,还想着那女人,不会是喜欢上她了吧?
车窗玻璃在黑色的背景下变成了一面镜子,映出了庄成明的脸,他和“镜中”的自己默默地两两相望,车窗里的他眉毛像两条藤一样纠结地拧在一块,挂满了忧愁,嘴角却有一丝似有若无的微笑,给这苦哈哈的脸孔添了一抹怪异和滑稽。
车外一直是浓稠厚重的黑暗,这符合夜的本质,但也让人觉得惶恐不安,不知道这黑暗会延续多远。车终于停了下来,庄成明被两双有力的手揪出来,他的眼睛早已在黑暗中游刃有余,毫不费力便看清了周围的环境,这是一座破败的废桥。现在已经是午夜了,周围没有一个人,只能听到虫声密集如雨,庄成明忽然觉得心里悲凉,也许今夜的这些虫就是目睹他被害的证人,那么它们现在弹唱的,就是哀乐了吧。他抬头看着那月光,从来没觉得月光竟像冰一样寒凉入骨。这些细小的冰棱刺穿他的身体,让他冷得弯下腰去。
后面跟上来一辆车,下来两个人,脸上都蒙着黑布,其中一个顶着满头白发。庄成明想,今晚是满月,如果他们不蒙着脸,还真是能清楚地看到他们的长相。满月的晚上……庄成明的心忽然颤了一颤,一股神秘的宿命感瞬间击中了他,像一支锃亮的箭镞一样穿过他的身体,他忽然觉得像被抽去了筋骨,绵软无力地瘫在地上。
那个白发老头拎着一团东西走过来,他浑身散发出一种慑人的气场,残忍、暴戾、阴沉。他问道,说,这是从哪来的?肯定不是你的!庄成明在黑暗中努力睁大眼睛,女人红色的包像团火一样灼疼了他的眼睛,庄成明努力放稳语调说,我老婆的。老头沉默,即使蒙着脸,庄成明也能感觉出他眼睛里深深的怀疑。但老头没再多说,只是拎着包转身走开,随口对旁边一个人说,把他扔河里吧。庄成明的思绪一下子被抽空了,像是曝晒在日光灯下,脑子里一片无垠的茫茫亮白,什么想法都没有,什么念头都消失,只是本能地从嘴里发出呜呜的求救的声音。
以前失恋的时候,庄成明每天躺在床上,感觉生不如死,甚至想过自己的很多种死法,研究每种死法的优劣,但从来没有想过是这种。第一次离死亡这么近,他感觉到那穿黑袍的死神就站在不远处,傲然看着他,浑身散发着腐朽糜烂的气息,这气息呛得他几欲落泪。正在这时,一个男人忽然喊,“老爷子,我听着车厢里有动静。”男人们迅疾地悄声围拢过去,一人惊叫起来:“有个妞!”女人被拖了出来,她显然搞不清眼前的状况,剧烈地咳嗽着,一双大眼睛惊恐地转来转去。一个男的上前刷地撕掉庄成明嘴上的胶布,恶狠狠地问:“说!这女的是谁,怎么放在后备箱里?”
庄成明耷拉着头,躲避着女人惊恐的眼睛,低声说,她是我老婆,吵架闹别扭了我就把她扔那儿了。男人们把女人围在中间,就像一群鹰围着一只战战兢兢的兔子,庄成明心里隐隐的担心像雾一样越来越浓,很快,这担心就变成了现实。
一个男的上前拽出女人嘴里塞的布,问:“你是他老婆?”女人的目光直直地盯着庄成明点了点头,目光变得像一面湖水一样深不可测,庄成明好像被吸进了这面湖水里,深深地沉溺下去,她为什么点头,她在想什么,他的头脑变得混沌,完全不懂湖水深处隐藏着什么。男人上前开始脱女人衣服,老头笑骂了他几句,其他几个都嘻嘻哈哈地笑起来。女人像条鱼一样扭动着身子拼命挣扎。她的衣服被撕破了,前胸一颗豆大的黑痣露了出来。庄成明的脑袋轰地炸开了,像有一万架飞机在嗡嗡乱飞,他努力站起身来,虽然双手被捆绑着,但仍然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用身子撞开男人,男人显然愣住了,趔趄了一下。庄成明用身子护住女人,急声说:“别动我老婆,她,她,她怀孕了!”周围死一般寂静,几个男人都阴沉沉地盯着庄成明,这种无声无形的威慑在空中迅速铺展开来,向庄成明压了过来,他为自己忽然涌出的胆量而震惊,女人在他身下扑闪闪地眨着眼睛,清亮的眼睛里蕴藏着极其复杂的内容。庄成明的心忽然一震,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愫在心里慢慢弥散开来。
男人们一把将庄成明拽过来,摔在地上,拳打脚踢。他像块破布一样被踩来踢去,意识在疼痛中一会儿清楚一会儿模糊,他想,打吧,反正横竖是个死,只要他们别害了女人。仿佛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女人的声音,放了他!也放了我吧!我们结婚好几年才怀上孩子的。庄成明头上的血流下来迷住了眼睛,他透过一片红色震惊地望着她,庄成明没想到,她会为自己求情。男人们打累了,又扑向女人,庄成明强忍着疼痛,努力爬向女人,用身子盖着她,不顾男人们雨点一样的拳头落在他身上头上,他痛苦地呻吟着,眼睛被血糊得睁不开,嘴里流出的血、身上流的血染透了女人薄薄的裙子。庄成明的心里此刻只有一个念头,我一定不能让她受到伤害!十年了,那颗痣一直像根刺一样扎在他心头,他不能拔,一拔就是伤筋动骨的疼痛,每次做噩梦,都会梦到那颗痣,那样清晰,那样痛楚,那样不堪的往事都跟着那颗痣在回忆里复活。
老头忽然说:“弄死孕妇子嗣是伤阴骘的事,要倒大霉,阿强,这女的就算了。她没见过我们的脸,男的扔了。”老头的声音不大但暗含了一种无法抗拒的威严。其余几人都垂头丧气,一副悻悻的不情愿的样子,庄成明看着女人,心里的石头骤然被摔了下来,如释重负的感觉后就是虚脱般的疲惫,紧接着,他的心又骤然缩成一团,看来今晚难逃一死了。想逃跑,可浑身疼得一点劲儿也没有。两个男人抬起庄成明,往桥边走去,抬走时,庄成明瞥见了女人,她反绑着双手坐在那儿,直直地盯着他,眼角正有一滴清泪缓缓流下。从桥上下坠的时候,庄成明这短暂的一生仿佛又如过电影般从眼前浮现。水面溅出巨大的水花,扑通一下便马上恢复平静,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男人们满意地拍了拍手离去。
庄成明感觉到水从四面八方涌过来,灌进耳朵里,眼睛里,鼻孔里,将他变成一块浸透了水的海绵,河底好像有无形的吸力,吸着他迅速下坠、下坠,最后关头,他脑海中浮现的不是母亲、不是前女友、不是最好的朋友,竟然是一张模糊而痛楚的脸,这脸缓缓向他移动过来,这就是经常出现在他梦中的那张脸,这脸越来越清晰,是她!十年前那张脸和现在她的脸渐渐重合交叠在一起。接着,庄成明便失去了知觉。
朦胧中,他感到有人在扇自己耳光,啪啪啪,耳光甩得很响。睁开眼,竟然是女人。庄成明一侧身,哇地吐出一口水,周围树影模糊,圆月当空,女人面朝河水拧着自己的头发,脸上的表情像这月光一样寒凉如冰。庄成明的惊诧迅速地发酵,散发出强烈质疑的气息,女人淡漠地说,多亏你绑我的手不够紧,一路上我早把绳子磨松了,他们一走我就挣开了。庄成明沉默了半晌说,为什么要救我?难道不怕我再害你吗?女人望着远方天空渐渐浮现的鱼肚白,冷冷地说,从你护着我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
庄成明苦涩地一笑,心中五味杂陈,他张了张嘴,最终说了句,我们真有缘分啊。女人说,是啊,我给你讲个故事吧。很多年前,我只有二十岁,在一个不出名的卫校上学,那时我在学校谈了个男朋友,对我很好,我们经常出去约会、逛街、看电影。我和很多年轻女孩一样,爱笑爱撒娇,心中充满了爱情的甜蜜和对未来的憧憬。可一切很快被打碎了。那天夜晚,我们看了电影,我怕宿舍大门上锁,催着让男友送我回去,可是他非要去山顶公园转转,那晚的夜色很黑,已经是深夜了,我本来不想去,可架不住男友的软磨硬泡,便去了。我们走到一片荒僻的草坡处时,迎面碰到一个满身酒气的男人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就在他们擦肩而过时,那个男人突然一把拉住我的胳膊,色眯眯地说:“这妞真漂亮。”我男朋友很慌张地说:“你干啥啊?”然后就赶紧拉着我想要走开,那个脸上有刀疤的男人把手里的啤酒瓶摔破,指着我男朋友说:“这妞留下,你滚。”当时的我很害怕很害怕,连一声救命都喊不出来,只会紧紧抓着男朋友的手,可让我的心像掉进冰窟的是男朋友竟然甩下我就跑,我也想跑,却被那个刀疤脸用力拉住。他的手像铁箍一样,我根本无力挣脱。恐惧再加上伤心,我根本连路都走不成了,刀疤脸把我拖到了草坡上的小树林里,当时的我还来着例假啊,我就使劲哭喊着,挣扎着。另外那个十岁左右的小男孩也吓傻了,结结巴巴地劝着:“哥,别这样了。”刀疤脸冲他骂着吼着,让他到一边去,我觉得我的灵魂像是脱离了身体,浮在半空中,眼睁睁看着我的肉身在遭受劫难,却无能为力。我只记得那晚的月亮就像今晚这样,是血红色的,就像我一直流淌的鲜血。后来,当他们走的时候,我听到他们的交谈,才知道他们住在秋北巷。因为我一夜未归,被查宿舍的老师发现,让我写检讨,结果全班都知道了我夜不归宿这事。我恨男朋友,就打他电话,可他不接我电话,不回我短信,一见我就躲瘟神似的赶紧跑。有次,我气不过,硬拉着他质问他那晚的懦弱,他只是说:“我对不起你,不过你也别缠我了,我不能接受一个被糟蹋过的女朋友。”我好恨,恨自己看错了人,我气得失去了理智,上前抓烂了他的脸,对着他破口大骂。结果他和我反目成仇,把我的遭遇宣扬得全校皆知,我每天都活在别人的白眼里。可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更可怕的是,我所在的卫校组织献血,我被查出来携带有艾滋病毒,男友也献了血,他没事,我知道,肯定是那个刀疤男,也只有他!我毕业了但无心找工作,一直在秋北巷打听那个男人是谁,通过好心人的帮助,我终于查清了,可已经晚了,他早跑到外地打工了,我又托人辗转打听他的下落。这样一找,不知不觉已过了很多年,这么多年来,我的父母为了我的病跑过很多地方,试过很多偏方,慢慢地无奈地接受了噩梦般的事实,他们的头发全白了,是愁白了。多年来,仇恨已经在我心里生根发芽,由一棵树长成了一片茂密的森林,我不能拔,拔一棵便是牵筋动骨的痛。多年来,我没有认认真真找过一份工作,一直在四处打工寻找刀疤脸。多年来,我没有谈过一次恋爱,每个追求我的男孩知道我的绝症后都果断离开。
最终,我找到了,那个刀疤脸叫庄成辉,一年前已经在狱中被人打死了。家中父母已病死,他还有个弟弟,就是你,在这个城市开黑出租。哥哥死了,报应就应该落在弟弟身上。因为仇恨太深了,总得找个口去宣泄,否则会憋出病的。
“所以,你找到了我,一切都在你的计划中,是吗?”庄成明哑着喉咙问。这个夜晚所发生的事情从前往后,一桩桩一件件被他捋顺了,理出头绪,拢在一起。言语尖刻难听是故意的,车上的露财炫富是故意的,风骚入骨的勾引是故意的,如果得了艾滋病再住进监狱,那人生等于堕入深坑,永远都是望不到头的黑暗。他想着,禁不住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女人一旦狠毒起来还真是让人防不胜防啊。
女人像是看穿了他的心思,冷笑一声说,知道事情在哪里发生转折了吗,在我看到你拼命护着我的时候,这让我想起曾经那个落荒而逃的男友,这辈子我没遇到过像你这样能拼死护着我的男人,我承认,我是被你感动了,也许心里冰冻太久荒芜太久,照过来一丝阳光我都贪婪地想攫住,更何况一整片温暖的火焰呢,我不舍得亲眼看着这火焰熄灭,所以,我救了你。善恶只是一刹那,不是吗?放过别人,也就跨过那条善与恶的边界了。十年了,已经十年了,也许一切都该放下了。
女人站起来漠然地望着远方,拍拍身上的土,往不远处的公路走去,走之前她回头深深地望了庄成明一眼,他愣愣地看着她,嘴张了张,最终什么也没有说出来。他已经被汹涌而来的往事淹没了。
十年前的庄成明才12岁,是个单纯的初中生,他的成绩不好,但老师们都不约而同地放弃了他,因为谁都知道,他有个怎样的家庭。庄成明的父母是有名的“赌博迷”,整日沉溺于赌场,从来不管两个儿子。哥哥庄成辉是当地的地痞流氓,不学无术,整天干些欺善凌弱的事。这样的环境成长出来的孩子,能不跟着打架斗殴已经不错了,老师们就没敢再期望他门门及格了。那晚庄成辉带着弟弟和朋友们在山顶公园玩,喝了很多酒,后来朋友们都陆续走了,就在他们也要离开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女孩和她男友……很多年了,庄成明不敢去回忆,拼命使自己忘记,那是他心里最深处一块结了痂的伤口,轻轻一撕,便鲜血直流。那个月光明亮的夜晚,那个女孩身下流出的血,极度的惶恐使庄成明忘了女孩的面容,但这些却深深刻在记忆深处,尤其是女孩前胸的一颗痣,那么触目惊心,像个烙印一样深深烙在他记忆的底版上,使劲擦也擦不掉,久了便成了心头挥之不去的一团阴翳。庄成明无法忘记那肮脏罪恶的一幕,这么多年,他常常梦到一个模糊而痛苦的脸在流着泪喊:“为什么不救我,为什么?”那颗痣也像噩梦一样缠绕着他。这种压力使他根本无心学习,初中没上完就辍学回家了,而且每谈一场恋爱,他都会想到那个女孩,他不由自主地对女友们有求必应,甚至当她们欺辱他时,他竟有种莫名的轻松和愉悦感,以致所有的女友都在分手时说:“你不像个男人,跟你在一起真没劲。”“你脾气太好了,豆腐一样没意思……”他每谈一场恋爱都是以失败告终。三年前,他遇到了菁菁,他是真的爱上了这个开朗泼辣的姑娘,她像一道明亮夺目的阳光劈开了他人生的黑暗,可依然是以分手为结局。那么多暗夜里,辗转反侧的他常想,也许有天自己也会像哥哥一样变成个坏人,压抑、苦闷在心里憋得太久太久了,他快要爆发了。庄成明还经常想,如果有天能找到这个女孩,他一定要诉说这么多年的愧疚,替哥哥,也替他自己。
可是现在庄成明觉得没有必要说了,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了。他眼睁睁地看着女人孤凄而寥落的背影,慢慢化作一个小小的红点,像一簇跳动的火苗,消失在视线尽头灰蒙蒙的边界……
责任编辑/乙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