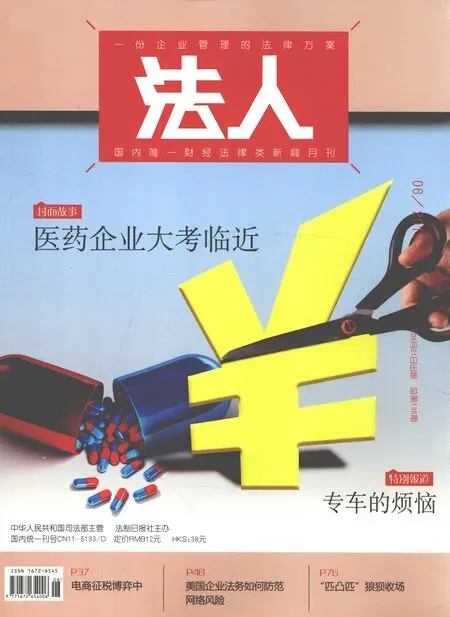十二公民:12种愤怒中的正义
◎ 文 武杰
十二公民:12种愤怒中的正义
◎ 文 武杰

《十二公民》剧照
青年导演徐昂将影史经典之作《十二怒汉》改编为中国版的《十二公民》,自5月15日上映以来票房一路走高,并保持惊人的票房增加。同时,该片更是引发了全民热议。
该片让12个来自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普通人坐在一个充满实验意味的虚拟法庭上,“好好说话”。而这部涉及“存疑不起诉”“陪审团制度”等概念的影片,在今年《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实施之后,也希望能与国人做一场理智的对话,并为司法系统与普通民众找到一扇沟通的大门,传达出公平与正义的法治理念。
寻找每个偏见背后的原因和共识
《十二公民》的主创们则想尝试用类似的形式和方法,谈论一下在经济高速发展下的中国,人们面对贫富差距问题时的误解及公平。
“十二公民”的身份各不相同,有出租车司机、房地产商、数学教授、河南小保安、北京土著、小商贩、保险推销员等,他们代表的是12类各个阶层的人,也代表着他们的愤怒、不甘、委屈和彷徨。
在当下,标签化了的“富二代”代表着目无法纪、张扬跋扈,陪审团最初给出的答案,在这种偏见之下也简单粗暴:一个平时就不懂礼貌、不思进取的富二代“当然”是杀人犯。12个没有名字只有代号的陪审员刚一坐下,便迅速给出了结果,11比1,11人认为有罪,1人认为无罪。
只有何冰扮演的8号陪审员认为,“咱们应该讨论讨论”。无论是半个世纪以前还是现在,《十二怒汉》的多个版本都
保留了单一的场景、证据的漏洞甚至争论的节奏,但是每个版本描述的又是当下本国面临的现实问题。
1957年美国版的《十二怒汉》,主人公是贫民窟长大的少年,种族歧视正是他们当时关注的问题;1991年日本的《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主人公是一个因受不了前夫纠缠而杀夫的弱女子,也是唯一一部设置女性陪审员的改编,日本探讨的女性权益的保护问题,也将日本人拉帮结派的个性在陪审团的争论中展示了出来;2007年俄罗斯版《十二怒汉》讲的是车臣男孩被指控谋杀自己俄罗斯军官的继父,车臣一直是俄罗斯一根敏感的神经。
中国版的“12公民”,他们分别是儿子出走老婆离家的出租车司机、与大学生真爱的房地产老板、蒙冤入狱的纹身男、儿子要补考的医生老爸、校园外小卖部老板、被打成右派的老人、不想让儿子当民工的城乡结合部房东、想考政法大学的河南小保安,在他们每次争论的背后,都有对他人的偏见和对自己的怜悯。12个不同阶层的陪审员,徐昂试图寻找每个偏见背后的原因和共识。
徐昂说,这部电影最有趣之处在于,它虽是一部法律题材电影,但你不必非得把它拍出教育意味。恰恰相反,这部电影的结论并非是歌颂法律公正而在于揭示偏见。

获奖照片-徐昂导演在罗马国际电影节上。Photo Leonardo Paniccia
探讨一个奔向正确的方式
影片《十二公民》中,经过一轮的讨论,再次匿名投票,坚持无罪的8号陪审员同意,如果其他人都选有罪,他就放弃。
9号陪审员最先改变了立场。这位曾经的“富二代”,1957年时成为“右派”,他带着沉重的铁牌子接受批斗的时候,一个看起来很凶的女人偷偷把挂在他脖子上的铁丝提了起来。而他也希望,“如果这个‘富二代’真的没罪,要是能有个人站出来说上一句……”
同时也是他提出,楼下老人不严谨的证词是因为想得到重视。他紧紧地攥着手里的帽子说:“接受采访的时候,老人紧紧地夹着胳膊,不希望人们看到他破了的衣服,努力的不让人看出他残疾的腿,多少年没有人愿意听他说话,这次不仅有人专门听他说话,还会印在报纸上。”
而其他人无法理解,一个老人说谎仅仅是因为重视。也许只有这个同龄的“右派”才能明白这沉重的孤单和并非恶意的自我催眠。
随着一次次的讨论,争论甚至冲突,证词一次次被推翻,比如同样的刀子不止一把;楼下老人不可能在列车噪音中听到“富二代”的喊叫;老弱残疾的他也不可能在15秒内赶到门口看到“富二代”逃走;声称看见杀人的妇女鼻子两边有凹痕,证明她长期戴眼镜,而晚上她不可能戴着眼镜睡觉,所以她在床上看到杀人的证词不可靠……
投票也由10比2变成8比4;6比6;3比9;1比11,时间从傍晚到深夜又到凌晨,夕阳落下,哗哗啦啦的雨声成为背景,唯有出租车司机还坚持着“有罪”的看法。
演员何冰说,我们的谈论就是这么困难,想谈到一个统一的结果更是无比艰难。人们不是纯理性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绪,这部电影表面看是1个人赢了11个人,但其实是大家克服了自我的成见,真理就在那摆着,“通过辩论、聊天,其实是些微的、临时的擦去了心理的成见,也许明天还是从前的样子。只是希望这个电影能够探讨一个奔向正确的方式”。
3号出租车司机嚷嚷着:“哪怕是吵架的时候动了他爸一根儿手指头,也是有罪的!你别让我看见他!我要是见着他,我亲手给他毙喽!”处处挑刺,又油嘴滑舌、市侩的3号突然严肃起来,他有个可爱的儿子,但是一次争吵动手之后,儿子已经6年没有回家,跟老婆也离了婚,天天跑车、挣钱却不知道是为了谁。与儿子的矛盾变成他对“富二代”杀父的偏执,一颗受伤和敏感的心,唯有尖酸刻薄的语言掩盖。
经过一番自我剖析,3号哭着将头埋在桌子上,高高的举起了右手,这一票“无罪”,是对自己的,对儿子的原谅和救赎。
而8号也在影片的最后亮出了自己的身份——人民检察官。



访谈韩景龙:少有的社会主义法制理念好故事
《法人》:《十二公民》被评价为中国改编最成功的电影,为什么会去改编《十二怒汉》这部电影?你当初选择这个题材的奇迹、初衷是什么?
韩景龙:先得说这个剧本从开始策划到最终完稿,都不是一个人的独立创作。每个阶段都是大家群策群力的结果。从最开始我和制片人王鲁娜就不想为了完全迎合市场去追求大投资、大制作,或者是过份趋同的爱情或者喜剧类型片。
我们想做一些更有意义的电影,所以确定要做一个现实题材电影,锁定法律题材,也是它最具时代性与社会性的,却恰恰是时下电影市场最缺少的。为此还找过不少导演,直到最后遇到导演徐昂。
徐昂提出想改编经典法律电影《十二怒汉》,与我们的想法不谋而合;并且通过话剧《喜剧的优伤》,我们也很相信徐昂导演的能力。所以,我们一拍即合,事实证明我们当初的选择是对的。
《法人》:在改编时,这部戏做了哪些本土化的设定?
韩景龙:《十二公民》本土化的最大改编还是在人物上。从真实的陪审团改编到虚拟陪审团,我们电影的主题已经有了很大转变。《十二公民》讨论的更多是时下中国人与人之间的理性沟通。所以对于每个人物的改编是我们下了非常大的功夫。不仅在最初的剧本,包括开拍前我们还和十二个优秀的演员就剧本进行了16天的排练,在这个过程中,再针对每个演员的特点,重新修改台词和人物细节。
《法人》:为什么会用《十二公民》的名字,你想表达什么?
韩景龙:我们的剧本最初在审批立项时,有三个名字备选。延续原版的《十二怒汉》和《十二个中国人》以及现在的《十二公民》,这三个名字各有利弊,我们自己也很难目前抉择。
最后是负责审批的老师帮我们分析:从我们的剧本来看,已经完全脱离了原版,所以叫原版《十二怒汉》并不合适;《十二个中国人》又太有针对性,容易就“中国”产生不必要歧义;而从剧本讨论的内容和剧本中传达的有关法律的观念与意识,《十二公民》是合适的。
《法人》:故事是关于陪审团制度的,属于法律专业问题,创作、拍摄过程中是否有专业的法律人提供意见和建议?创作前期需要哪些相关的调研和准备?
韩景龙:编剧中除了我与导演徐昂,还有一名编剧——李玉娇,她是辽宁省检察院的高级检察官,她为我们的剧本提供了专业的意见与建议。我们在创作前期主要是针对媒体、网络上的热点讨论案件展开大量调研。这些都让我们的剧本不仅在广电局与最高人民检察院的审批中一路畅通无阻,还得到了专业的好评,认为我们的剧本是近年来少有能真正体现法律精神与当下社会主义法制理念的好故事。
《法人》:有评论说,12个中国人实际上是12个中国故事,对于陪审员的性格,职业是如何选择的?
韩景龙:在长达两三个月的策划讨论中,12个人物一直是我们讨论的热点。每一次我们的讨论会都会有十几个人参加,每次就人物所产生的地域、财富等问题,我们都会展开激烈的讨论,不亚于电影里展现的过程。最终能就这12个陪审员的性格、职业还有其它达成一致都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要做一个好电影。
《法人》:许多人了解陪审团制度,就是通过《十二怒汉》,很多观众也从《十二公民》中感受到了现实意义的体现。这是你的初衷吗?你觉得这部电影的热映反映了当下人们怎样的?
韩景龙:当然。就像我开始说的,这是我们所有主创人员想要达到的效果。也正如我在前面所说,我们并不是去真正讨论一个人的生死,或者参与到真正的法律审判,而是用电影向大家展示一种沟通方式的可能,希望观众在观影过程中或多或少地看到自己的一些影子,从而能产生一些思考。这也是我在创作这个剧本中得到最大的收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