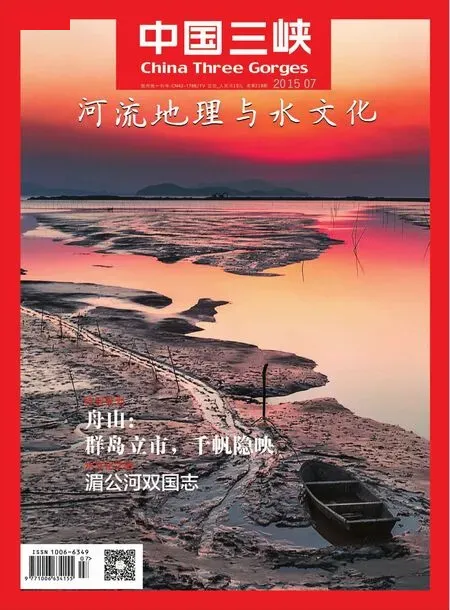莱蒙湖的启示
文、图/大 河 编辑/罗婧奇
莱蒙湖的启示
文、图/大河编辑/罗婧奇

莱蒙湖像一弯新月静卧在阿尔卑斯山的怀抱里,湖光山色无以伦比。
从阿尔卑斯罗讷大冰川发源的罗讷河沿着横贯瑞士南部的瓦莱大山谷一路奔流而下,汇入了一个方圆八千平方公里的大湖。在湖里沉淀下一路上裹携的冰川泥沙后,湖水变得清澈碧蓝。在湖西南角的日内瓦,罗讷河走了出去,继续纵穿法国,最后在法国南部进入地中海。因为世界名城日内瓦位于湖的一角,这个大湖有一个为中国人熟知的名字——日内瓦湖。可是对于生活在湖的南北两岸的法国和瑞士人来说,他们愿意用一个更美的名字称呼这个大湖——莱蒙湖。
莱蒙湖像一弯新月静卧在阿尔卑斯山的怀抱里,湖光山色无以伦比。第一次见到它时给我的震撼至今仍难以忘怀。
那是我第一次去瑞士。在苏黎世下了飞机后乘火车去洛桑。乘了一夜的飞机,疲劳让我在火车上昏昏欲睡,一路上强睁着眼睛观赏瑞士中部美丽的田园风光。快到洛桑时火车钻进了一个山洞,正当黑暗带来的困意就要把我征服的时候,火车呼地钻出了隧道。眼前一亮,莱蒙湖像从天而降的仙境出现在眼前。
车窗外,火车正沿着一个碧蓝清澈的大湖飞驰。明媚的阳光下,蓝色锦缎般的水面上白帆点点。远处阿尔卑斯山的雪峰在闪闪发光。路基下郁郁葱葱的葡萄梯田铺满山坡,一直铺到湖边上。葡萄园里散落着黄墙红顶的小村庄和小教堂。从飞驰的列车车窗望出去,就像穿行在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山水画里。
漫步莱蒙湖畔,清澈透明、瑰丽沉静的湖水更是一种巨大的诱惑。湖畔草坪上,休闲的人们悠然地享受着阳光,湖面上白帆点点,不时有滑水爱好者从湖面掠过,岸边甬路上鲜花盛开,绿树婆娑。宁静、安逸、清新,莱蒙湖畔的生活展现出它最美的一面,无不让慕名而来到此一游的旅游者发出由衷的赞叹。
然而,他们是否会想到,眼前这清澈美丽的湖水在三十年前曾经在死亡的边缘挣扎呼号呢?
如今年纪并不很老的湖畔居民都还清楚地记得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那场令人惊恐的湖水污染危机。
莱蒙湖方圆近八千平方公里,是中欧第二大淡水湖。法国和瑞士两国隔湖相望,莱蒙湖区是两国人口稠密、经济发达的地区之一。其南岸有法国名牌矿泉水“依云”的产地埃维昂,北岸有著名的奥林匹克之都——瑞士的洛桑市和号称“瑞士的里埃维拉”的旅游胜地蒙特勒。
从来源上看,莱蒙湖是一个冰川湖泊。在二十世纪初以前它一直保持着冰川湖湖水的特点:洁净,低氧,低微生物。1894年,日内瓦市政府曾委托当时著名的卫生学家马索勒博士负责检测莱蒙湖湖水的水质,他对湖水做了严格的检测后得出结论:“日内瓦市民拥有得天独厚的良好生活条件。他们所饮用的湖水是最洁净最优质的水。”1904年现代湖沼学之父、著名的科学家F-A.弗莱勒博士也曾这样评价过莱蒙湖的湖水:“莱蒙湖为人们提供的饮用水的水质相当于、甚至优于矿泉水。从卫生学角度评价,这一湖水的水质十分值得称道。”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欧洲工业化、现代化的飞速发展,莱蒙湖地区的人口激增,从二十世纪初的不到十万人增长到了四十多万。现代化、工业化为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繁荣和富裕,同时也激发了人们无止境的欲望。对财富和享受的追求让人们无节制地向大自然索取,似乎一切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没有人去顾及大自然正在悄悄发生的变化,一场灾难正在莱蒙湖畔酝酿。

从飞驰的列车车窗望出去,就像穿行在一幅美不胜收的巨大山水画里。
对人们来说,灾难似乎是在一夜之间突然降临的。说不清是哪一天,人们惊愕地发现,美丽清澈的莱蒙湖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昔日里荡漾的碧波如今整个被黄绿色的水草和藻类所覆盖,水波疲惫不堪地托举着一层厚重的水藻晃荡着,发出阵阵腥臭。湖畔的居民一直习惯趟入清澈的湖水中享受那份沁人心脾的清凉,如今他们涉入的竟是一片暗绿色令人恶心的“浓汤”。湖畔精心栽种着花木的漫步小径上经常见到腐烂的水草和死鱼,微风吹过就像下水道一样发出恶臭。
我们的莱蒙湖怎么了?惊慌的人们忙去向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寻问究竟。而他们也正在这前所未有的可怕现象面前一筹莫展,暂时无法从他们熟悉的理论和公式中找到答案。
是大自然的生命循环遇到了危机。更令人困扰的是,引起这一危机的并不是生命的衰亡,正好相反,源于生命的暴发!一个人们以前很少听到过的新名词——“水质富养化”被不断地灌进人们的耳中。
“富含营养”曾经是在贫困饥饿中挣扎过的人渴望和追求的美好字眼,如今竟变成了造成湖水危机的元凶。原因很简单,接收营养的不是饥饿的穷人,而是湖水的公害——水藻。这一营养源就是植物肥料的基本成分——磷盐。莱蒙湖湖水含有过剩的磷盐,以其为营养的水藻如获至宝,疯狂地繁殖生长起来。在阳光和氧气充足的湖水表层大量繁殖的水藻很快便侵占了大片大片的水面,而它们的生命循环结束后剩下的腐败物则沉入水底有待分解。分解过程需要消耗水中溶解的大量氧气,水中正常溶解的氧气已无法满足如此大量的腐败植物的分解需要,带来了湖水缺氧的恶性循环。
于是在富养化条件下疯狂生长的藻类早已打破了湖水的生态平衡,富养导致缺氧,以至无氧。缺氧造成湖水中大量正常生物的死亡,生命的消失意味着湖泊的死亡。
莱蒙湖水藻的暴发就像掀起了一场风暴,人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污染”这个当时人们尚不熟悉的字眼成了议论的中心。甚至考古学家们也追忆起他们在那些已经消亡的古代城市的湖泊中曾经闻到过的类似的腐败气息。这一切让沉溺于繁荣富裕的物质生活中的人们清楚地看到了愤怒的大自然派来的死神的黑影,人们惊恐并不得不开始行动。
蔓延湖中的水藻终于被打捞干净,人们又见到了一个绿波荡漾的大湖。然而那湖水中已经没有了生命,曾经让莱蒙湖渔民骄傲的美味鳜鱼早已不见了踪影,曾经在湖水中自由嬉戏的居民也不敢冒然在污染的水中游泳了。湖水死寂一片,水质堪比矿泉的美丽的莱蒙湖正在走向死亡。
生命是脆弱的,恢复它要比扼杀它艰难得多。科学家找到了湖水死亡元凶磷盐的主要来源。除了工业污染源以外,另一个主要来源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每天都在制造的东西——生活污水。
生活污水中除了众所周知的污物、细菌和油脂等污染物以外,还有大量日常生活所必需的洗衣粉、洗碗液等清洁洗涤用品中所含的磷盐。这些化学成分不知不觉之中源源不断地被排入湖水中,使莱蒙湖的含磷量在十年里翻了一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每升湖水的含磷量达到了92微克的历史最高浓度,从而造成了水藻大暴发。从这个意义上讲,湖区的每一个居民都对湖水污染有着一份责任。

莱蒙湖湖水瑰丽沉静,湖面上白帆点点,一派悠闲模样。
为了挽救莱蒙湖,整个湖区行动起来。除了建立起完善的工业污染控制监测体系外,莱蒙湖两岸的瑞士、法国成立了国际湖水保护组织,联手治理污染的湖水。到2005年为止,沿湖共修建起二百二十一座生活污水处理厂,应用物理、化学和生物方法多级多层次地将整个流入湖区的生活污水在排放到湖中之前全部进行去污净化处理,并且需要通过严格的质量检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两国政府先后出台了禁止生产含磷洗衣用剂的法规,在日常污染源的层面严格限制和减少磷盐向湖水中的排放。
另一方面,在普通居民当中大力推广环境保护的教育和宣传,让每个人都建立起环保意识和相应的公共道德,承担起自己的一份责任。在当地的生活,可以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中感受到人们的环保意识和良知。当地居民已经不再把家庭的下水道当作排放生活垃圾的管道,随便将丢弃物从下水道冲走了。他们在将生活污物倾倒进下水道之前,先将油脂和有害的化学污物分别收集起来,送到专门的地方进行处理。油漆、溶剂、杀虫剂、显影剂等有毒物也避免倒入下水道,因为这些物质会杀死在污水处理厂充当生物净水重任的微生物。在商场购物时人们有意选择无磷洗涤剂,并尽可能减少和节省化学洗涤剂的使用。在室外,人们避免在市政下水道口附近冲洗车辆或做有可能污染下水道的浇灌、清洗工作,因为他们知道市政下水道的污水是不经污水处理直接排入湖中的。这些保护措施与其他的垃圾分类、处理和节约能源的方法经过几十年的培养,目前已经成为了莱蒙湖区和瑞士全体公民的自觉。
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终于获得了令人欣喜的结果。据2006年的莱蒙湖湖水检测报告,莱蒙湖水中的硝酸盐含量很低且稳定,含磷量已从三十年前的每升92微克下降到27微克。莱蒙湖的贵族鱼类鳜鱼又回来了,百分之八十的湖畔沙滩水中的细菌含量达到了非常清洁的水平,人们又可以放心地在清澈的湖水中畅游了。
目前莱蒙湖区正为实现将湖水的含磷量降到每升20微克以下而努力。只有达到了这个标准,才可以说莱蒙湖真正恢复了它的生态平衡。随着目标的接近,任务变得更加艰巨起来。一代人几十年的努力才将被自己污染的大自然重新复生,也许还需要另一个几十年的努力才能让它恢复真正的生态平衡。这沉重的代价也应该引起世界上所有人的深思。湖水之美丑,清也在人,污也在人。望世人真正吸取莱蒙湖污染与复生的历史教训。

路基下郁郁葱葱的葡萄梯田铺满山坡,一直铺到湖边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