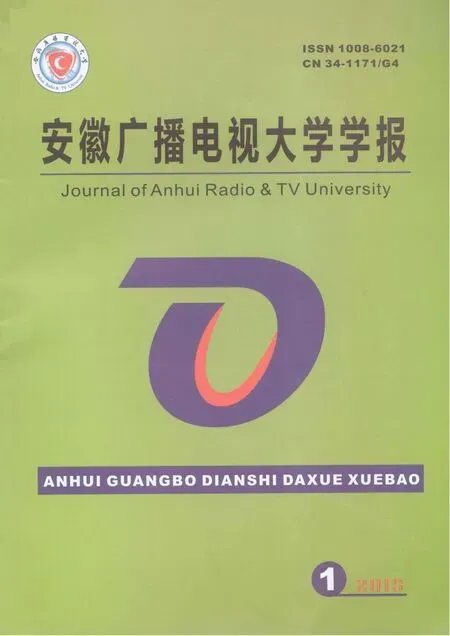当浪漫与革命相遇
——论蒋光慈对拜伦的接受
倪正芳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中文系,湖南 娄底 417000)
当浪漫与革命相遇
——论蒋光慈对拜伦的接受
倪正芳
(湖南人文科技学院 中文系,湖南 娄底417000)
摘要:蒋光慈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影响和独特价值的作家,他的创作在内容和风格上都受到了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的深刻影响。不仅如此,由于个性的因素和时代的需要,蒋光慈所理解和重构的是一个既有侠义色彩又具革命精神的蒋式拜伦形象,这也使他的“革命文学”创作表现出独特的气质。
关键词:蒋光慈;拜伦;革命文学;侠义
中国近现代时期的苏曼殊和蒋光慈都曾自比为拜伦。如果说清末民初时期的苏曼殊主要是因为个性情感与人生遭际的相类而将拜伦引为同调,成为第一个自比为拜伦的中国人,那么蒋光慈则是在寻求民族前途的时代旋律里和革命文学的开拓探索中发现了拜伦的价值,从而立志成为另一个中国的拜伦。蒋光慈与他所理解和重构的拜伦相遇,使他的“革命文学”创作表现出独特的气质。
一
拜伦虽然出身贵族,但他的许多社会政治活动却表现出强烈的叛逆性、斗争性和民主性,他在议会上公开支持爱尔兰人民为争取民族权利所作的努力,为工人阶级反对资本家而采取的捣毁机器的斗争辩护,至于他亲自投身意大利民族解放斗争和希腊独立革命运动乃至英勇献身的事迹,更充满了传奇般的革命色彩。而熟悉拜伦的创作的人还知道,他的大量作品也充分地反映了上述内容,表现出同样的思想倾向和情感。
蒋光慈一些言论和创作表明,他非常了解拜伦的这些事迹和传奇经历并深深为之感动,因此他对这位异国诗人充满仰慕之情并毫无保留地献上自己的怀念和赞美。
《怀拜伦》[1]是蒋光慈在“拜伦殁后百年纪念日”(1924年4月19日)所作,较早也较为集中地体现了诗人对拜伦争取自由、反对阶级压迫、同情被奴役民族和人民的精神的激赏:“拜伦啊!/你是黑暗的反抗者,/你是上帝的不肖子,/你是自由的歌者,/你是强暴的劲敌。/飘零啊,毁谤啊……/这是你的命运罢,/抑是社会对于天才的敬礼?”“黑暗的反抗者”“上帝的不肖子”“自由的歌者”“强暴的劲敌”,这就是作为普罗文学的代表、中国现代作家中最早的自觉以文学形式反映工人革命运动的蒋光慈对这位去世已百年的英国诗人的“价值判断”,实际上也道出了作为一位异族的古典诗人的拜伦为什么还能赢得文化背景极为不同的现代东方民族人民怀念和敬意的原因。我们注意到,在1925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少年飘泊者》篇首,作者又将这一节诗摘录为序,这表明他对《怀拜伦》一诗所概括出的拜伦的精神特征仍然是认可和满意的。
在《怀拜伦》中,蒋光慈接着还将自己对拜伦的认识和之所以将其引为同道的理由具体化。他写道:“我们同为被压迫者的朋友,/我们同为爱公道正谊的人们:/当年在尊严的贵族院中,/你挺身保障捣毁机器的工人;/今日在红色的劳农国里,/我高歌全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
经历了苏联火热的斗争生活,革命激情高涨的蒋光慈,是站在中国20世纪20年代工人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潮头,表达对这位贵族叛逆诗人的高度认同和赞许的。蒋光慈进而将自己视作拜伦精神和事业的继承者:“拜伦啊!/十九世纪的你,/二十世纪的我;/际此诗人殁后百年的纪念,/我真说不尽我的感想之如何!”
他就是这样以一种责任在肩、舍我其谁的气概,自比为20世纪的拜伦,宣示了自己对民族社会历史责任的一种大义凛然、毫无保留的承担。
蒋光慈与女友宋若瑜的通信,也表明他们对拜伦及其作品的共同关注和喜好。宋若瑜在给蒋光慈的信里几次提到阅读拜伦的作品并谈论起对拜伦事迹的感受。如1925年11月13日,宋若瑜致信蒋光慈说:“苏曼殊著的《英汉三昧集》你看见过吗?……《拜伦诗选》一小本很好,也是曼殊译,有原文及中文。”[1]149-150在另一封信(1925年12月16日)中她又写道:“读拜伦的《去国行》:Come hither,hither,my little page!/why dost thou weep and wail?……当拜伦去国的时候,他是何等的悲壮!”[1]157-158这些通信内容无疑也能反映和折射蒋光慈的阅读兴趣和思考焦点。
蒋光慈还曾借小说人物之口表达自己对拜伦高尚品质的赞赏。在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中,他有这样的描写:“曼英还记得,在未上床之前,那位可怜的诗人(周诗逸)是怎样地向她哀求,怎样地在她的面前跪下来……她开始嘲弄他,教训他。她说,他自命为诗人,其实他的诗比屁还臭;他自做风雅,其实他俗恶得令人难以下饭。她说,目下的诗人太多了,你也是诗人,我也是诗人,其实他们都是在放屁,或者可以说比放屁还不如……只有那反抗社会的拜伦和海涅才是诗人,才是真正的天才,只有那浪漫的李白才可以说是风雅……喂!目下的诗人只可以为他们舐屁股,或者为他们舐屁股都没有资格!”[2]不仅如此,蒋光慈认为,相比拜伦,甚至历史上一些地位颇高的诗人也不过如此了,他在《新梦·自序》中就明白表达过自己鄙视吟风弄月歌颂醇酒美人的苏东坡、袁子才,而要以拜伦等诗人作为自己仿效对象去做一个伟大的革命性诗人的决心:“我以为诗人之伟大与否,以其如何表现人生及对于人类的同情心之如何而定。我们读歌德、拜伦、海涅、惠德曼诸诗人的作品,总觉得他们有无限的伟大;但是一读苏东坡、袁子才诸诗人的作品,则除去吟风弄月和醇酒妇人而外,便没有什么伟大的感觉了。”“我生适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力为东亚革命的歌者……用你的全身,全心,全意识——高歌革命啊!”[1]256
蒋光慈是从内心里将拜伦视为自己为人为文及从事革命事业的楷模的。特别是拜伦为希腊独立而献身的事迹,成为鼓舞他为改变中国的衰弱命运和混乱时代而奋斗的强大动力。当然,我们下面将要谈到,蒋光慈受拜伦的影响以及他要做中国拜伦的决心主要落实在创作上。
二
蒋光慈虽然鼓吹和向往革命,但对当时的许多实际革命活动蒋氏往往并没有积极参加。蒋夫人吴似鸿回忆,蒋光慈曾对她说:“党组织说我写作不算工作,要我到南京路上去暴动才算工作,其实我的工作就是写作。”[3]蒋光慈对当时的一些革命活动有自己的看法,不过他在自认为最适合自己的、同样属于革命工作的文学创作中,却始终是在积极表现革命、讴歌革命的。而这些创作特别是他的诗歌中,很多都体现着拜伦式的风格,有些作品甚至可以明显看到拜伦创作的直接影响。
如他的《写给母亲》有这样的诗句:“我几次想投笔从军,将笔杆换为枪杆,/祖国已经要沦亡了,我还写什么无用的诗篇?/而今的诗人是废物了,强者应握有枪杆,/我应该勇敢地荷着武器与敌人相见于阵前……”[1]459。这种在民族生死危亡关头挺身而出与敌人决战到底的决心与勇气,包括显示这种精神的心理活动过程,都与拜伦《凯法利尼亚岛上的日记》何其相似:“死者们全都惊醒了——我还能睡眠?/全世界都抗击暴君——我怎能退缩?/丰熟的庄稼该收了——我还不开镰?/枕席上布满了荆棘——我岂能安卧!/进军的号角天天鸣响在耳边,/我心底发出回声,同他应和……”[4]。
蒋光慈1925年10月创作的《海上秋风歌》与拜伦的《去国行》在情感表达上的共同之处也很多。这两首诗都是诉说主人公面对浩瀚无涯的大海、抒发沉痛悠长的故国之思,主人公郁积于心的那种连绵的哀怨与惆怅都是那样的深沉和真挚。“海上秋风起了,/吹薄了游子之衣”[1]385,中国的游子蒋光慈感到了一股寂冷萧瑟之气;“一身孤孤单单,/在茫茫大海漂流”[4]137-141,英国的游子拜伦也是满怀孤寂和凄清。蒋光慈“哀祖国之飘零”,不知“向何方归去”;拜伦痛感于“没有任何人为我嗟叹”,于是赌气式的叮嘱船儿“任凭你送我到天南地北,/只莫回我的故乡。”实际上两者都表达了天涯孤客渴望寄托和归宿的沉痛心情。当然,在拜伦的背后,毕竟还有一个强大的帝国;而对蒋光慈而言,祖国积贫积弱、多灾多难,即使个人寓居海外,也只是个遭人白眼的弱国子民。这一差异,后来蒋光慈在东京养病时写的日记中曾明白地作了比较:“唉,我是中国人,一个不幸的中国人!就是旅居在异国里,也没有什么自由的可言。这较之当年羁留在巴黎的海涅,流浪在意大利的拜轮如何?他们虽然是愤慨,他们虽然是不见容于祖国,然而他们在异国里究竟是自由的人啊!……”[2]431。这就是作为身处异国的落后民族国民的痛苦悲哀和无奈,这些情绪,跟拜伦、海涅的遭遇比较,当然还是有区别的。
拜伦生前非常关心希腊的民族独立和复兴事业,他曾通过《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告诫尚处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奴役之下的希腊人民,不要指望别人会无私地使自己摆脱别人的压迫:“他们巴望着外国的军器和救助,/却不敢独自去反抗异族的欺凌,/或者摆脱可悲可耻的做奴隶的痛苦处境。”[5]他大声疾呼:“世世代代做奴隶的人!你们知否,/谁要获得解放,就必须自己起来抗争;/胜利的取得,必须依靠自己的手?/高卢人或莫斯科人岂会拯救你们?”[5]108蒋光慈的《太平洋中的恶象》同样旨在既向同胞们揭露侵略者的狰狞与凶残,也警示人们小心帝国主义的伪善面孔,鼓励大家要争得民族解放还得靠自己的行动:“隐隐跃现着的,那不是/美利坚假人道的旗帜的招展,/英吉利资本主义战舰的往来,/日本帝国主义魔王的狂荡?/…… 远东被压迫的人们起来吧,/我们拯救自己命运的悲哀,/快啊,快啊!……革命!”[1]273-274
拜伦有一首《致苏里人之歌》:“苏里的儿郎!起来,上战场!/时机已到,把重任承当!/那边有城墙,那边有城壕,/冲啊!冲啊!苏里的英豪!”[4]125这是他在奔赴希腊前线途中所写,既是对战士们的动员,也是对自己的激励,读来感觉像冲锋的号角般铿锵有力,令人大长士气。而鼓励民众奋起反抗,将自己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军阀的蹂躏中解脱出来,正是蒋光慈诗歌中反复回荡着的主题,他的《中国劳动歌》更是与《致苏里人之歌》一样有着鼓点般的节奏,传递着诗人急切的催促和呼喊:“起来吧,中国劳苦的同胞啊!/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到了极度;/倘若我们再不起来反抗,/我们将永远堕于黑暗的深窟。/打倒帝国主义的压迫,/恢复中华民族的自主;/这是我们自身的事情,/快啊,快啊,快动手!”[1]323
最能让我们看出蒋光慈诗歌受拜伦影响之直接程度的,无疑体现在他的《哀中国》与拜伦的《哀希腊》所具有的鲜明的可比性上。
中国与希腊都曾创造过辉煌的历史文明,又都经历过遭遇异族奴役的苦难。因而,拜伦的《哀希腊》所表达的“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绪很能激起中国人的共鸣,本诗仅在中国近代时期就有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等人的翻译,可以说是当时最有影响和最具社会意义的外国诗歌。蒋光慈无疑对这首诗是非常喜爱的。不然他不会将自己赴苏回国后在“黑暗萃聚的上海”写成的诗集命名为《哀中国》。而其中的“主打诗”《哀中国》[1]391-393,可以说从标题到内容,从内在情感到言说方式,都可看出借鉴《哀希腊》的痕迹。
《哀希腊》[4]147-153首先回顾该民族的光荣历史和昌盛的文明,然后与其被奴役的可悲现实对照:“希腊群岛呵,希腊群岛!/你有过萨福歌唱爱情,/你有过隆盛的武功文教,/太阳神从你的提洛岛诞生!/长夏的阳光还灿烂如金——除了太阳,一切都沉沦!”同样,《哀中国》一开头也历数祖国山河美好,紧接着也揭示出其惨遭蹂躏的现实:“你怀有无限美丽的天然,/你的形象如何浩大而磅礴!/你身上排列着许多蜿蜒的江河,/你身上耸峙着许多郁秀的山岳。”但现在,“满国中外邦的旗帜乱飞扬,/满国中外人的气焰好猖狂!”
命运的今非昔比,两个民族固然都有相似之处,民众的精神状态似乎也一样令人痛心。拜伦在《哀希腊》中曾回顾希腊往昔的武功,痛惜今天的人民甘为“顺民”奴隶:“置身于披枷带锁的民族,/与荣誉无缘,也心甘情愿。”蒋光慈也看到中国的老百姓无声无息,甘受奴役:“回思往古不少轰烈事,/中华民族原有反抗力。/却不料而今全国无声息,/大家熙熙然甘愿为奴隶!”拜伦的《哀希腊》流露出羞愤与自责:“歌唱的时候,我羞惭满面;/诗人在这里有什么作用?/为祖国落泪,为同胞脸红!”蒋光慈的《哀中国》也表现出愧疚和怆然:“我今枉为一诗人,/不能报国当愧死!/拜轮(伦)曾为希腊羞,/我今更为中国泣。”
尽管如此,两人都意识到不能因此委顿下去,诗人有责任激励民众奋起斗争,把握自己的命运,做振兴国家民族的战士。在《哀希腊》结尾,拜伦慷慨激昂地鼓励民众振作起来:“亡国奴的乡土不是我邦家——/把萨摩斯酒盏摔碎在脚下!”蒋光慈的《哀中国》最终也对灾难深重的民族寄予了信心和期望:“哎哟!我的悲哀的中国啊!/我不相信你永沉沦于浩劫,/我不相信你永无重兴之一日。”?
三
从以上蒋光慈的议论和创作中流露出来的倾向看,他所接受和构建的拜伦是一个有着鲜明的侠义气质和革命色彩的独特诗人形象。
蒋式拜伦最大的特点是“侠气”。创作于苏联时期的《我的心灵》(1923年1月24日)一诗中,蒋光慈将拜伦、海涅等一批有着强烈的现实主义情怀的浪漫主义诗人作为自己追慕的对象,他认为拜伦就是为自由的希腊而献身的“侠”:“多情的拜伦啊!/我听见你的歌声了,/自由的希腊——/永留着你千古的侠魂!”[1]309确实,身为英格兰贵族的拜伦却去声援爱尔兰民族独立运动和工人阶级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特别是还冒着生命危险直接投身意大利和希腊的民族解放事业,与中国传统文化中仗义执言、打抱不平的侠客形象颇有相似之处。
就蒋光慈个人性情而言,他是一个豪爽任性的人,可以说义侠之气正对他的胃口。因为尚侠,蒋光慈早年曾改名“侠僧”,在与宋若瑜的通信中还自称“侠生”。在《〈鸭绿江上〉自序诗》中,蒋光慈也表白,对侠的向往是他从小就有的情愫:“我曾忆起幼时爱读游侠的事迹,/那时我的小心灵中早种下不平的种子……”[1]429所以,蒋光慈把拜伦的义举跟“侠”联系起来,也是很自然的事。
同时,把拜伦永留希腊的英灵比作“侠魂”,还带有浓厚的民族文化意味。联系此前中国知识分子对拜伦的介绍,我们已经可以窥见人们塑造拜伦形象的民族化过程中尚侠倾向之一斑,实际上,人们是把这种侠气跟当时的民族革命精神等同视之的。自近代拜伦进入中国以来,知识分子将拜伦视作民族复兴与革命大业一面旗帜的“侠”而加称颂的非蒋光慈始。早在1902年11月15日,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在《新小说》第2期上刊出了拜伦和雨果的照片并作简短文字介绍,文中称:“拜伦又不特文家也,实为一大豪侠者。当希腊独立军之起,慨然投身以助之。卒于军,年仅三十七。”此评语表明梁氏看中的就是拜伦的乐于帮助弱小民族的、他概括为“大豪杰”的“侠义”的精神,而“私人”的拜伦遭到了放逐。
无独有偶,当时的马君武也持相同的拜伦观。他在《十九世纪二大文豪》一文中,也称拜伦是在参加希腊独立战争中病死的义侠作家。他在比较歌德、席勒、丁尼生、卡莱尔、拜伦和雨果后得出结论说,“(拜伦)英仑之大文豪也,而实大侠士也,大军人也,哲学家也,慷慨家也”,“闻希腊独立军起,慨然仗剑从之,谋所以助希腊者无所不至,竭力为希腊募巨资以充军实,大功未就,罹病遂死。”[6]
梁、马二人认识和观察的出发点是为半殖民地中国寻找出路,因而拜伦的“豪侠”行为是他们所渴盼和歌颂的。因此他们才撇开了拜伦一生活动中实际比重极大的情感游戏和个人冒险,只将拜伦一生的事迹归结成诗歌创作与政治革命行动两种并“绝对地注目于后者”[7]。谢天振、查明建等学者据此也认为,自梁启超开始,拜伦是以“大文家”“大豪侠”的形象进入中国,而“后者的形象要重于前者,或者说中国的知识界更看重的是拜伦作为崇尚自由、敢于反抗的‘豪侠’的一面。”[8]
由此可见,蒋光慈的拜伦形象,同清末民初时期谋求民族复兴大业的前辈所选择性接受并塑造出来的拜伦形象有相当程度的一致之处。大革命时期的阶级斗争和清末民初时期的民族革命,都需要那种为了多数的弱势人群的利益能够挺身而出、勇于抗争的具有号召力的英雄,从而导致了身处不同时代的知识界精英们不约而同地看中了拜伦的这种“侠”之形象。他们对拜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可能并非不清楚,但出于政治与革命斗争实际的需要,他们没有进行学术研究意义上的全面了解和深入研究,这样他们表现或塑造出的拜伦便是这种功利性十足的梁式、马式、蒋式等等中国式拜伦。
不过,与此前及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多数忽视甚至轻视拜伦诗学方面的成就不同,蒋光慈还对拜伦的浪漫主义特质给予了相当程度的关注并展开了创作上的仿效。他通过创作体现出了对拜伦及其创作的个性化理解,在当时来说,这一点是非常独特而宝贵的。
比如说,蒋光慈的浪漫主义创作风格的形成就与拜伦有着直接的联系。蒋氏浪漫主义固然是五四运动那个狂飙时代的历史产物,是诗人革命斗争生涯以及在苏联这个“新造之邦”特殊经历的反映,是诗人豪迈不羁的性格气质以及美学理想的自然表现,但是,世界文学中浪漫主义的文学传统,特别是作为浪漫主义代表性诗人的拜伦对他的深远影响,是怎样也不能低估的。
从《怀拜伦》《哀希腊》等诗即可见拜伦的浪漫主义精神和创作风格对蒋光慈的影响之深,特别是对蒋光慈革命浪漫主义诗歌的催生作用。而在所谓“革命加恋爱”的“革命浪漫蒂克文学”的蒋光慈小说创作中,也可以见出时代思潮与拜伦创作的复合影响。罗成琰在《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中谈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革命浪漫蒂克文学”时指出:“它摈斥了‘五四’浪漫文学思潮的个性意识,强化了阶级意识与群体意识,作品表现出一种社会化、群体化的情绪。……在它所推崇的群体意识中,又分明流露出许多知识分子的个人情趣和个人意志;在它所塑造的革命浪漫主义英雄形象身上,也分明可以看到拜伦式人物的影子。”[9]可以说蒋光慈小说创作尤其是其中的人物塑造正是这段论述的典型体现。如他的《少年漂泊者》,首先是选择了书信体这种浪漫主义的典型体裁,其次是通过主人公汪中“漂泊之旅”的浪漫叙事,塑造了一个命运坎坷却顽强不屈,虽然浪迹江湖却不惜与命运抗争直至最后毁灭(牺牲)的“拜伦式英雄”。但是,正如“革命加恋爱”的模式无法适应表现残酷的革命现实的需要一样,“拜伦式英雄”也不是中国社会革命所真正需要的依靠对象。蒋光慈的绝笔之作《咆哮了的土地》等表明,对社会斗争复杂性和艰巨性的认识日益加深,对革命文学的本质把握越来越成熟老练的蒋光慈,已经逐渐疏远了这位昔日的偶像,而将希望更多地寄托在拥有深厚民族根基又接受了革命新思想的本土英雄如张进德、李杰等底层觉悟者或阶级叛逆者身上了。
参考文献:
[1]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3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361-363.
[2]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2册[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431.
[3]吴似鸿. 我与蒋光慈[M]. 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68.
[4]〔英〕拜伦.拜伦抒情诗七十首[M].杨德豫,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124.
[5]〔英〕拜伦.恰尔德·哈洛尔德游记[M].杨熙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0:108.
[6]莫世祥.马君武集(1900-1919)[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26.
[7]〔日〕藤井省三.鲁迅比较研究[M].陈福康,编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3.
[8]谢天振,查明建.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288.
[9]罗成琰. 现代中国的浪漫文学思潮[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17.
[责任编辑陈希红]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021(2015)01-0095-05
收稿日期:2014-09-27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YBA173);湖南省教育厅重点科研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4A077)。
作者简介:倪正芳(1966-),男,湖南安乡人,教授,文学博士。研究方向:比较文学与外国文学。
When Romance Met Revolution
——On Jiang Guang-ci's Appreciation of Byron
NI Zheng-fang
(Chinese Department, Hu'nan Institute of Humanities,Science and Technology, Loudi Hu'nan 417000, China)
Abstract:Jiang Guang-ci is an important and special writer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His writings have been deeply influenced by romantic poet Byron both in content and style. Furthermore, because of his character and the needs of times, Jiang Guang-ci has constructed a unique image of Byron who possesses chivalrous quality and revolutionary spirit. Jiang's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creation therefore expresses some distinctive features.
Key words:Jiang Guang-ci; Byron;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chival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