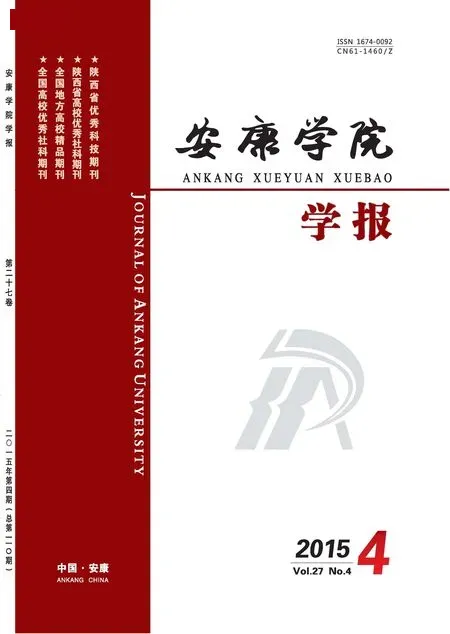论莫言小说《蛙》中姑姑的人格结构
张 玲
(安庆师范学院 文学院, 安徽 安庆 246133)
2009年12 月,莫言创作了长篇小说《蛙》,该作品在2011年8月一举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自此以后,学术界对《蛙》这部小说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论争方向主要有:书信体的叙述角度,人性忏悔与救赎,以及解放初期的社会现实等等。一部作品一经完成,便成为一个客观存在物,读者从不同的角度出发,便会获得不同的意义。艾布拉姆斯在其著作《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了著名的文学四要素观点,他认为文学是一种活动,由作家、世界、读者、作品组成[1]。其中读者对作品的阅读其实也是读者对作品的再创造。作为莫言无数读者中的一员,笔者认为除去小说特别的叙述手法,深刻的社会现实意义,《蛙》这部小说最扣人心弦的还有其主人公——姑姑的心理世界。虽然目前也有部分评论家从精神分析学的角度来论述《蛙》,但笔者认为还不充分,故在此从人格结构角度对姑姑进行精神分析。
一、家族纽带
从时间的维度看姑姑的成长历程,不难发现,在其生命过程中最早对她产生深刻影响的是家族环境。姑姑的父亲是八路军,抗战的时候师从白求恩,后来光荣牺牲。姑姑从小便成了革命烈士的后代,也正因为这一身份,她在解放初期受到国家政治上的优待,给她安排了光鲜体面的工作。姑姑风风光光地投入工作后,万家上上下下也因为姑姑吃“皇粮”而与有荣焉,对姑姑倍加尊敬。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家族荣誉感在姑姑这一代人心中是多么重要,个人依附于家族的纽带关系从而获得自身的价值认同感。
《蛙》中描写的这种家族荣誉感的心理模式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了原型。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学术概论》中讲到:“邃初之民,必笃于教……稍进,则为崇拜祖先。盖古代社会,抟结之范围甚隘。生活所资,惟是一族之人,互相依赖。立身之道,以及智识技艺,亦惟侍族中长老,以为牖启。故与并世之人,关系多疏,而报本追远之情转切。一切丰功伟绩,皆以传诸本族先世之酋豪。”[2]古代中国,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人们的生活模式: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从事固定的劳作,以氏族为生产生活单位。人们赖以生存的一切,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上的,都依靠祖先积累并从其继承而来。在中国文化中,祖先崇拜、家族荣誉源远流长。
中国传统文化两千多年,深深地影响着世世代代的中国人,在解放初期,中国人的经济模式和生活方式与传统的小农经济相去并不远(1956年中国才初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受这一经济基础的影响,祖先崇拜、家族荣誉感还深深地扎根于解放初期的中国人心中,而这也是滋生姑姑对自己根正苗红的家族历史无限崇拜的土壤。
弗罗姆在《逃避自由》中说到:“人对某一既定社会的特定生存方式的动态适应会把人的精力塑造成那种特殊的性格形式。”[3]188也就是说因为急切的自我保存需求迫使人接受他生存的环境,这种环境中的生活模式又决定了人的性格结构,而“性格反过来又决定着个人的思想、感觉和行动”[3]188。姑姑在中国传统生存模式影响下,形成了一种特有的性格,而这种性格又必然会决定着她的思想和与之相应的行为。在这样一种生活模式和文化氛围中,个人对命运是很少进行自我思考的,因为个人消解在整个家族之中,他要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承袭。这一背景下的中国人,在心理上有一种类似于婴孩与母体之间由脐带连接的关系。封建的伦理道德和小农的经济方式把人束缚在一个固定不变的位子,它限制了人的自由,但同时又给人带来一种莫大的安全感、归属感。所以,家族荣誉感往往淹没了人的自我意识。姑姑年轻时那种饱满的工作热情和充满优越感的生活,都来源于她光荣的家族背景。但是她却不知道,这种价值的体现是靠一种家族纽带的关系来维系的。后来,由于飞行员男友的叛变,差点毁了姑姑光辉的红色背景。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姑姑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竟然割腕自杀。根据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人最基本的两种需求,是人实现其他任何一种需求的基础。而生命作为承载这一切需求的载体更是最最重要的[4]378,那么,在姑姑的内心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念超越了对生命本能的珍视呢?姑姑的这一行为让我们联想到弗洛伊德关于人格构造中“超我”的论述。
弗洛伊德提出人格结构由“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构成。“本我”是指原始的自己,包含生存所需的基本欲望、冲动和生命力,它按快乐原则行事,不理会社会道德、外在的行为规范,它唯一的要求是获得快乐,它是无意识的,不被个体所觉察。“自我”介于“本我”与外部世界之间,是人格的心理面。“自我”的作用是一方面能使个体意识到其认识能力;另一方面使个体为了适应现实而对“本我”加以约束和压抑[5]126。“超我”是指“能进行自我批判和道德控制的理想化的‘自我’,它的职责是指导‘自我’以道德良心自居,去限制、压抑‘本我’的冲动,去按至善的原则去行动”[5]129。
弗洛伊德这一概念的基础主要基于以下观点:“坚持既严格又极高的道德目标;他们生命中的动力不是获得幸福的愿望,而是追求正确与完美的强烈冲动;他们受到一系列的‘应该’和‘必须’的支配。‘超我’的主要功能是用良心和自豪感等去指导自我,限制‘本我’的冲动。”[6]137如果说人的“本我”里都有一种惧死向生的愿望,那么姑姑的行为则可以解释为是她的“超我”迫使她这么做。家族的荣誉和清白是外在于她的期望和准则,是她认为最正确,最必须履行的职责。在她内心,这种牺牲得到了一种更大的补偿,即继续感受到自己的力量与价值。维持自己根正苗红的家族纽带关系,从而依附于这种关系得到对自己价值的肯定已成为她“超我”的心理部分,压抑着她内心“本我”(对生命的热爱本能)的冲动。因为深受这种传统的家族荣誉思想的影响,在姑姑的内心,她根正苗红,是革命烈士之女,也是万家下一辈效仿的楷模,她所有的荣誉感、自我价值感都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所以姑姑无法面对一个独立的自己,渺小、又无力,她必须使自己屈从于一个外在的关系即家族,使自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从而感觉到力量和价值。姑姑风风火火的青年时代,正是套着家族荣誉的这层光环而大放异彩。
二、国家纽带
在文革期间受到批斗后,姑姑像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她比以前更疯狂地投入到工作。为了响应党的号召,严格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她甚至不惜伤害孕妇的生命,其中已有三名孕妇(耿秀莲、王仁美、王胆)惨死在她手下,2800多个婴孩被她剥夺了来到世上的权利(而年轻的时候,姑姑接生过无数婴儿,是村里的“送子观音”)。凡是符合计划生育政策的,姑姑焚香沐浴地为她接生,凡是超计划生育的,绝不手下留情。这时候的姑姑已经不是一个具有热爱生命本性的人了,她成了国家政治机器的一个齿轮,她已经把抽象的国家要求内化为自己具体的行为,自己的愿望和目标与国家融为一体,即在国家面前没有个人。在这里,我们看到,姑姑又抓住了她生命中的第二根纽带——国家。她如此强烈地屈从于这一外在的权威,是因为这一外在的权威已内化为她“超我”的部分。姑姑执行计划生育政策的顽固心理正是这一强迫性的内在权威使然。她使自己完全隶属于党这一伟大组织,服从它的任何要求,因为只有当其作为党组织中的一份子,她才能感觉到自己的存在与力量。即使偶尔有良心的挣扎,姑姑还是能坚持党的政策到底,她对任何事物的价值判断,已经完全从自我这一主体转移到党这一权威。她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她为自己坚定不移的意志和对党的忠诚而骄傲。她把党的准则当作自己的准则,做一切党要求做的事。也正因为这样,她在残害上千名婴儿的情况下,还能在内心使自己免于良心的责备,因为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她的行为是为了服从国家的要求,她愿意为这一神圣的事业而奉献牺牲,而姑姑也能够从坚持这一权威的准则——严格执行计划生育中获得优越感、价值感。姑姑是小说中人物的典型,除她之外,小说中的其他人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性格特征,文革期间的人斗人,更是把这种个人完全丧失自我,成为国家机器的奴隶、利益斗争的奴隶,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里让我们联想到古代希腊的民主自由政治,斯巴达人全民集体参与政治,直接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但同时他们又必须对集体的权威完全服从。虽然人民获得了政治权利,但是“社会的权威机构干预那些在我们看来最为有益的领域,阻碍个人意志”[7]47。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是西方民主的滥觞,但是在贡斯当的《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这本书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古希腊这种表面上民主自由的政治实际上暗含了对个体人性的忽视。在斯巴达,个人完全没有自由的概念,人仅仅是机器,它的齿轮和转动装置由法律来规定,个人以某种方式被国家所吞没。尽管公民个体对国家的大小事务都有直接的管理、干涉权,但是贡斯当最后说到:“我们已经不再欣赏古代人的自由了,那种自由表现为积极持续地参与集体权利。我们的自由必须是和平的享受与私人独立构成的。”[7]48
在《蛙》这部小说里,国家机器与个人自由独立性之间的冲突比比皆是,而姑姑更是这一冲突的典型。她完全成为国家机器的奴隶,并使其上升为她人格结构中的“超我”,她隶属于国家机器,完全丧失自己,在她的人格里没有任何私人独立的空间。但是在小说中,我们同样也可以看到对这种国家侵害私人独立性的反抗。当偷偷怀孕这件事东窗事发,要被抓取堕胎,否则小跑的公家饭碗不保,王仁美毫不犹豫地说自己要生孩子,回家种地又有什么关系。小跑开始还犹豫,最后也决定要放弃军衔,保住老婆孩子。从这一切,我们不难看出个体对生命的本能热爱、希望按照自己自由意志生活的愿望超越了对国家机器的服从。在这里,莫言和贡斯当是有共鸣的:人,必须首先是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必须充分享受自由与和平,在此前提下,国家才是有意义的。小说中,像姑姑那样的一代人对国家的集体政治充满热血的激情,因为她自身的价值实现和自我认可都融入到了这一集体事业之中。但同时作为自己的主人,作为一个具有生命意识的主人,他们是忽视的,甚至是没有意识到的。
从两千多年来的小农经济社会中,中国人知道需要形成一种社会纽带关系,个人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中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归属感,他的人生目的不是他通过自己探索知道的,而是被他的社会身份告知的。人们漠视生命的独立性得到的补偿就是不用独自面对这个不可知的世界,面对生命中的不确定。使自己隶属于一个家庭、一个团体、一个社会,以该社会组织的价值为自我的价值,以这种理想化的“自我”即“超我”来指导自己的现实行为,完全忽视“本我”,这是小说中姑姑典型的人格结构特征。
三、“本我”的释放
“如果一个人将一生的安全感建立在不是真实自我的基础上,那么当他发现外表的背后还有人时就会大吃一惊。”[6]121经过岁月的洗礼,可以说姑姑晚年回到了她一直逃避的自己,但她的反应不仅是吃惊,更是深深的痛苦。姑姑以前是发自内心地热爱妇产科事业,孩子来到世界上来的第一声啼哭是她认为最美的声音。她的工作合乎她的“本我”的一种内在诉求,所以她由衷地热爱妇产科事业。但在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时,姑姑从送子娘娘变成了刽子手,她认为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人口不控制,国家就完了,排除万难,也要毫不留情地执行这一国策。在姑姑的意识里,她因为一种外在权威的庇护而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正当且高尚的,她也因此获得一种正义感和安全感,但实际上她内心的“本我”却是抵触这一做法的(尽管不为她的意识所知)。弗洛伊德在论述意识的不同含义时说到:“潜意识一方面包含着种种因潜伏而不为意识所察觉,其余一切都与意识相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包含着种种被压抑的活动,这些活动如要变成意识活动,它们肯定与意识中其他种种活动形成极鲜明的对照。”[8]所以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到了晚年,姑姑终于不堪重负、崩溃了。因为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残害婴儿这一做法与她的“本我”相抵触,当这种抵触从潜意识上升到意识的时候,她原来的意识领域顿时混乱了。那个雨夜的蛙声,可以说是2800多个冤魂的哀鸣,更可以说是姑姑内心的“本我”与被“超我”异化后的“自我”相互征战的声音,“本我”极力渴望被释放。
自由、信念是一个人发自内心地认为对他有价值和必须履行的情感或行为准则。它不是人格结构扭曲的结果,而是“自我同一性”(自我同一性是指一种熟悉自身的感觉,包括社会与个人的统合、个人的主体方面与客体方面的统合、自己的历史任务的认识与个人愿望的统合,等等)[4]143的表现,当一个人用外在的纽带、权威异化自己,从而获得安全感、价值感的时候,他获得的一切都只是表面。一个人的行为只有在摆脱“超我”的强迫,合乎自己自然本心即“本我”的时候,他才不会有心灵的负担。任何过度压抑的“本我”,终有一天,都将被释放。
[1]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5.
[2]吕思勉.先秦学术概论[M].湖南:岳麓出版社,2010:5.
[3]埃里希.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0.
[4]黄希庭.人格心理[M].浙江:浙江教育出版社,2005.
[5]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M].吉林:长春出版社,2004.
[6]卡伦·霍尔奈.精神分析新法[M].潘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7]邦雅曼·贡斯当.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M].阎克文,刘满贵,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8]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导论[M].吉林:长春出版社,2004:3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