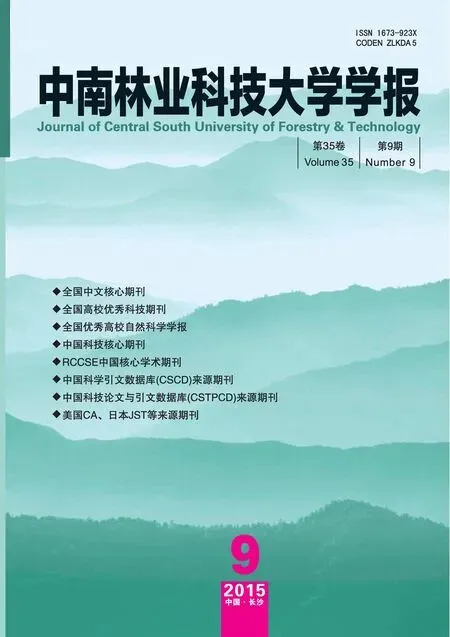南岭自然保护区各功能区景观格局研究
廖芳均,陈志明,刘宗君 ,谢 勇
(1.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2.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广东 韶关 512727)
南岭自然保护区各功能区景观格局研究
廖芳均1,陈志明2,刘宗君2,谢 勇2
(1.中山大学 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广东 广州 510275;2.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广东 韶关 512727)
以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资源小班数据以及1988、1999和2009年3期遥感影像为基础数据,基于eCogntion、ArcGIS 和IDRISI 软件,对保护区各功能区20年间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各功能区景观以森林为主,其中实验区针叶林和常绿阔叶林约为77%,缓冲区常绿阔叶林约为56%,核心区则以常绿阔叶林为主,约为78%;2)各功能区景观类型斑块面积呈波动趋势,斑块数量、边缘密度和斑块密度增加,景观破碎化程度随时间的推移呈上升趋势;3)各功能区森林景观类型之间转化频繁,非森林景观类型建设用地和水域面积变化明显增加;4)各功能区景观类型最大斑块指数呈波动趋势,景观结构随时间变化更加丰富和复杂;5)研究期间各功能区景观连通性增强,景观多样性基本维持稳定水平,有效维护了生态系统的稳定性。
自然保护区;景观格局;景观指数;功能区;广东南岭
景观格局是指大小和形状各异的景观要素的空间分布与组合特征[1],景观格局及其变化是自然、社会和生物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2],景观格局分析可以量化地分析景观要素的结构特征及其相互之间的空间分布关系,在看似简单无序的斑块镶嵌景观上,发现潜在的、有意义的规律性及其形成机制,从而成为进一步研究景观功能和动态的基础[3-4]。近年来,国内许多学者对流域景观[5-6]、湿地景观[7-8]、城乡景观[9-10]、山地景观[11-13]等的景观格局及其动态进行了研究报道,对景观生态学的理论研究和景观生态学在实践应用上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14]。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森林景观格局及其变化不仅对森林生态系统内的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产生影响,制约生态过程,进而影响森林的演替,如斑块的大小和形状会影响种群的生存能力和抗干扰能力[15-16],还会对全球生态系统平衡起着直接作用。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是人为划分的物种保护中心,随着人类对环境保护意识的逐步增加,对此类景观的研究也日渐深入,但目前的景观研究大多从整个保护区的角度来进行的[17-19],对各功能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的分区景观结构研究较少。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位于南岭山脉中段南麓,其森林景观既有亚热带特色,又显露出热带的某些特点,具有明显的过渡性,是生物基因交流的纽带[20],南岭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在生物进化史中具有特殊的地位[21]。而其植被类型的多样性和动植物种类的丰富性反映了其区系成分的复杂性和过渡性的特点,是其所属生物地理区的最好代表。本研究基于景观生态学原理,以RS和GIS为技术支持,以森林资源小班数据(2007年)和3期遥感影像为基础,对近20年保护区内各功能区森林景观动态变化进行分析,以期对南岭自然保护区景观规划和管理、 生物多样性保育及森林资源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参考。
1 材料和方法
1.1 研究区概况
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地处广东省北部,南岭山脉中段南麓。地理坐标为东经112°30′~113°04′,北纬 24°37′~ 24°57′,面积为 58 368.5 hm2。南岭自然保护区所处的南岭山地是我国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的中心地带,植被分布从下至上依次为:沟谷常绿季雨林或丘陵、低山常绿阔叶林→中山常绿阔叶林或中山常绿落叶阔叶混交林→中山常绿针阔叶混交林或中山常绿针叶林→山顶(常绿阔叶)苔藓矮林→山顶灌丛草坡。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为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原生的亚热带中山常绿阔叶林、原生的亚热带山地常绿阔叶矮林、保存较好的次生亚热带中山常绿阔叶林),珍稀、濒危的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环境,主要功能是保护南岭独特的自然资源和自然环境,使之免遭人为干扰和破坏;采取各种措施拯救濒危物种,保持生物物种的多样性;保护和扩大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和现存的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的种群数量;建立科研、科普教育基地,珍稀野生动植物拯救中心。研究区位置见图1。

图1 研究区位置Fig.1 Location of Nanli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1.2 数据来源及处理
1)本研究中的基础数据主要有1∶10 000地形图,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2007),1988、1999和2009年Landsat5 30 m分辨率的3期遥感影像。对地形图进行数字化,运用遥感图像处理软件ENVI 4.5对3期TM影像进行纠正、增强以及裁剪处理。根据森林资源二类调查数据,结合研究区遥感影像特点,并参照全国土地利用分类系统标准[22-23]进行分类,获取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阔叶混交林、灌木林、其它林地、耕地、其它土地、建设用地和水域10类景观类型,在eCogntion面向对象软件下进行人工目视解译。
2)根据我国自然保护区功能区划采用的模式[24],突出对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及珍稀濒危动植物的保护与研究,确保亚热带森林植物群落的生物多样性和珍稀动植物的安全和生态环境,综合研究区的自然生态条件、生物群落特征,从整体性和适宜性将南岭保护区划分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3个功能区,根据广东省林业规划体勘察设计院(1999)设计,具体分布见图2。

图2 研究区功能分区Fig.2 Functional zone division of Nanli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3)景观格局指数是景观生态学广泛使用的定量研究方法,高度浓缩了景观格局和景观动态信息,能够很好地了解景观格局的组成成分、空间配置和动态变化过程。本研究在进行景观格局分析时,选取生态学意义明确且公式计算简单的指数:类型面积(CA)、斑块个数(NP)、斑块密度(PD)、边缘密度(ED)、香农多样性指数(SHDI)、Simpson指 数(SIDI), 通 过 FRAGSTATS3.4和EXCEL软件包分析统计,从不同角度对森林景观进行定量分析。具体计算公式和计算方法都采用FRAGSTATS景观格局计算分析软件的表达方式[25]。
2 结果与分析
2.1 各功能区景观格局
广东南岭国家自然保护区所处位置为粤北山区,其内部社区和周边社区主要为国有林场职工及瑶族居民,长期的人为与自然相互作用,使得保护区内景观斑块呈现诸多差异,不同时期各功能区景观格局分布见图3。实验区分布在人口分布相对密集的区域以及周边零散地带,区内景观类型以针叶林为主,约为46%;常绿阔叶林也占一定比例,约为23%,而人为活动痕迹如建设用地和耕地也大部分分布在此功能区;缓冲区分布在保护区周边及实验区的周围,景观类型除了常绿阔叶林占据大比例外,约为56%,其它各景观类型都分散分布在此区域;核心区在缓冲区的内部,保护区中间地带,北边与湖南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相连,区内景观以常绿阔叶林为主,约为78%,针叶林和针阔混交林呈小片分布,而人类活动强烈的耕地在此功能区没有分布,其它景观类型如其它土地、其它林地、灌木林和水域在此功能区域呈零散分布。

图3 1988~2009年各功能区景观类型分布Fig.3 Landscape type distribution in each functional zone from 1988 to 2009
2.2 各功能区景观类型变化
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社会的发展,各功能区所受干扰强度不同,各景观类型斑块面积变化呈波动趋势(见图4),其中实验区针叶林、灌木林面积持续减小,常绿阔叶林面积先减小后增大,阔叶混交林、耕地、其它土地、建设用地和水域面积持续增大,变化最大的为其它林地,在研究后期增长迅速;缓冲区主要景观类型为常绿阔叶林,其它森林景观类型占一定比例,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和水域面积呈下降趋势,其它景观类型面积则持续增加,增长最快的为其它林地;核心区常绿阔叶林面积占绝对优势,研究期间除其它林地面积呈下降再上升趋势外,其他景观类型面积变化不大,较为稳定。
从斑块数量(见图5)看,在各功能区面积不变的情况下,实验区除阔叶混交林数量减少外,其它景观类型斑块数量均增加;缓冲区除水域外,其它景观类型斑块数量均增加;核心区则常绿阔叶林和阔叶混交林斑块数量减少,其它景观类型均增加。从整体景观上来看,各功能区的斑块数量变化呈现一定规律,在研究前期斑块数量减少,而到了后期则增加显著,其中增长最快为实验区,其次为核心区,这也表明景观受到外界干扰程度增强,破碎化程度增加,景观格局明显趋于复杂。

图4 1988~2009年各功能区不同景观类型斑块面积变化Fig.4 Area changes of different landscape patterns in each functional zone from 1988 to 2009

图5 1988~2009年各功能区不同景观类型斑块数变化Fig.5 Number changes of different landscape patterns in each functional zone from 1988 to 2009
2.3 各功能区景观异质性变化
研究期间,实验区各景观类型斑块密度除阔叶混交林和耕地减小外,其它均呈增大趋势,其中针叶林、针阔混交林、常绿阔叶林和灌木林等森林景观类型呈现波动现象,为先减小后增大,而其它土地、建设用地和水域等非森林景观则持续增大;缓冲区在研究后期没有水域,总体上斑块密度呈现一定的规律性,为增大趋势,稍有不同的为耕地,为先增大后稍微减小,其它景观类型则为先减小,后期增长迅速;核心区整个研究期间没有耕地,其它各景观类型最终都呈上升趋势。边缘密度指数则为,实验区除灌木林,缓冲区除建设用地,核心区除其它林地外减小,各功能区景观类型均增大。
从各功能区的整体上来看,斑块密度指数呈波动现象,具体表现为先减后增,最终为增加,实验区各年份斑块密度指数分别为5.09、4.24、6.52;缓冲区各年份斑块密度指数分别为5.34、4.18、6.59;核心区各年份斑块密度指数分别为4.05、2.73、4.46,反映了景观结构随时间变化更加丰富和复杂。总体上破碎化程度增大,表明景观的抗干扰力增强,这主要是由于前期一直进行的生态公益林保护工作,以及后期的人工造林面积增大的原因。
2.4 各功能区景观类型矩阵转移
表2~表7为1988年至2009年各功能区景观类型转移矩阵,反映景观类型之间相互转移情况,研究前期(1988~1999年),实验区耕地、建设用地、阔叶混交林和针阔混交林面积增加,并主要有常绿阔叶林和灌木林转化而来,其它景观类型面积变化不大,均稍有减少,表明在此期间,该区域受到强烈的外界干扰;缓冲区针叶林面积大量减少,主要转化为常绿阔叶林和灌木林,其它林地和耕地内部相互转化,建设用地转化频繁,水域和其它土地面积变化不大,表明该区域受自然和人为影响相互作用,人为活动基本在森林周边;常绿阔叶林与其它景观类型转化频繁,最终面积增加,且主要由阔叶混交林、针阔混交林和针叶林转化而来,其它林地减少的面积也大部分转化为常绿阔叶林。整体上核心区符合自然演替规律,实验区人为活动急剧增加。

表1 1988~2009年各功能区各景观类型斑块密度和边缘密度变化Table 1 Changes of PD and ED of each function zone in studying area from 1988 to 2009

图6 1988~2009年各功能区景观斑块密度和边缘密度指数变化Fig.6 Changes of ED and PD of each function zone in study area from 1988 to 2009

表2 1988~1999年实验区景观类型转移矩阵Table 2 Transition matrix of landscape types of experimental zone in 1988~1999 hm2

表3 1988~1999缓冲区景观类型转移矩阵Table 3 Transition matrix of landscape pattern of buffer zone in 1988~1999 hm2

表4 1988~1999年核心区景观类型转移矩阵Table 4 Transition matrix of landscape pattern of core zone in 1988~1999 hm2
研究后期(1999~2009年)实验区常绿阔叶林、阔叶混交林、针阔常绿混交林、其它林地和针叶林之间相互转化,水域面积明显增加,主要由针叶林、其它林地和常绿阔叶林转化而来,耕地面积稍有减少,大多转化其它林地,建设用地面积则持续增加,主要由针叶林转化而来;缓冲区常绿阔叶林、灌木林、其它林地和针叶林之间转化频繁,建设用地和水域面积增加,主要由常绿阔叶林转化而来,其它土地转入转出频繁,面积增加,总体林地面积减少,这与正常演替规律相反,表明在此期间外界干扰增强;核心区森林景观类型内部转化频繁,常绿阔叶林面积减少,转化为建设用地和水域面积明显增加,灌木林转化频繁,最终面积稍有增加。
整体上,整个研究区域以森林景观类型为主体,研究期间面积波动不大,景观类型之间相互转化频繁,非森林景观类型(耕地、其它土地、建设用地和水域)面积在实验区从急剧增加到稍有增加,表明研究期间该区域受外界干扰强度逐渐变轻,在缓冲区从稍有减少到大量增加,表明外界干扰明显增强,在核心区没有耕地,其它非森林景观类型面积很小,所占比例也极小,但面积呈上升趋势。其中,整个研究区域,水域和建设用地大量增加,表明人为活动强烈。

表5 1999~2009年实验区景观类型转移矩阵Table 5 Transition matrix of landscape pattern o experimental zone in 1999~2009 hm2

表6 1999~2009年缓冲区景观类型转移矩阵Table 6 Transition matrix of landscape pattern of buffer zone in 1999~2009 hm2

表7 1999~2009年核心区景观类型转移矩阵Table 7 Transition matrix of landscape pattern o core zone in 1988~1999 hm2
2.5 各功能区景观多样性分析
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水平的香农多样性指数在研究时期实验区分别为1.31、1.32、1.38,缓冲区分别为1.27、1.27、1.33,核心区分别为0.92、0.83、0.87,表明实验区斑块丰富,景观破碎化程度最高,而核心区斑块则相对较为单一化,景观连通性最强;各功能区的变化除核心区呈波动趋势外,实验区和缓冲区景观破碎化程度均为增大。

图7 1988~2009年各功能区景观香农多样性和Simpson指数变化Fig.7 Changes of SHDI and SIDI of each function zone in studying area from 1988 to 2009
Simpson指数在研究时期实验区分别为0.66、0.62、0.42,缓冲区分别为 0.66、0.61、0.40,核心区分别为0.68、0.63、0.40,表明实验区斑块优势度最为明显,而核心区斑块则相对较为均匀;各功能区景观连通性增强。整体上,研究期间景观类型多样性维持基本稳定水平,破碎化程度较小,能够有效地维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保护生物多样性免受降低。
3 讨 论
(1)各功能区景观以森林为主导景观,其它景观类型镶嵌在森林景观中。各功能区景观类型具体表现为实验区以人为干扰强烈的针叶林为主,缓冲区常绿阔叶林占据大比例,而核心区则以常绿阔叶林为主, 这主要是由于保护区实验区大部分在原国有林场辖区,而占主体部分的常绿阔叶林为保护对象。
(2)各功能区景观类型斑块面积呈波动趋势,针叶林面积变小与保护区成立后采取的封山育林等保护措施有关,而其它林地面积增长迅速是由于2008年雨雪冰雪灾害后其它森林景观类型转化而来,作为主要保护对象的常绿阔叶林在整个景观类型中占绝对优势,并且面积稳定。
(3)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各功能森林景观类型之间转化频繁,非森林景观类型面积稍有增加,其中建设用地和水域变化明显,受外界干扰强烈。
(4)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各功能区间以实验区斑块数和斑块密度最大,缓冲区次之,核心区最小,表明实验区景观破碎化程度最大,斑块形状更为复杂。平均斑块面积则以核心区最大,缓冲区次之,实验区最小,表明核心区景观类型连通性好,破碎化程度低。
(5)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各景观指数随时间的变化呈波动趋势,形状指数在研究时段持续增大,说明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斑块的镶嵌具有较强的不规则趋势,斑块形状趋于复杂。景观多样性更加丰富,景观多样性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实验区,这也反映了人为干扰程度所造成的景观异质性差异。
[1] 邬建国.景观生态学: 格局, 过程, 尺度与等级[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0.
[2] 白军红, 欧阳华, 崔保山, 等.近40 年来若尔盖高原高寒湿地景观格局变化[J].生态学报, 2008,28(5):2245-2252.
[3] 傅伯杰, 陈利顶, 马克明.景观生态学原理及应用[M].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1.
[4] Musacchio L, Ozdenerol E, Bryant M,et al.Changing landscapes,changing disciplines: seeking to understand interdisciplinarity in landscape ecological change research[J].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2005,73 (4): 326-338.
[5] 古丽克孜·吐拉克,李新国, 刘 彬, 等.开都河流域下游绿洲景观格局变化分析[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4,28(3):174-180.
[6] 伍 星, 沈珍瑶.长江上游地区土地利用/覆被和景观格局变化分析[J].农业工程学报, 2007,23(10):86-93.
[7] 袁晓红, 李际平, 赵春燕.西洞庭湖区森林景观格局斑块对构建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2014,34(7):36-40.
[8] 王永丽, 于君宝, 董洪芳, 等.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的景观格局空间演变分析[J].地理科学, 2012,32(6):717-724.
[9] 彭保发, 陈端吕, 李文军, 等.土地利用景观格局的稳定性研究——以常德市为例[J].地理科学, 2013,33(12):1484-1488.
[10] Y Xin Q, Z Rui C.A land use change model: Integrating landscape pattern indexes and Markov-CA[J].Ecological Modelling, 2014,283:1-7.
[11] 岳 刚, 杨 华, 亢新刚, 等.长白山天然林景观地形分异格局的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 2012,32(9):114-118.
[12] 张秋玲,马金辉,赵传燕.兴隆山地区景观格局变化及驱动因子[J].生态学报, 2007,27(8):3206-3214.
[13] Paula K L, Leandro R T, Robert M E.Land-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in Alantic Forest landscapes[J].Forest Ecology and Management, 2012,278:80-89.
[14] 胡海胜, 魏美才, 唐继刚,等.庐山风景名胜区景观格局动态及其模拟[J].生态学报, 2007,27(11):4696-4706.
[15] Fahrig L, Merriam G .Habitat Patch Connectivity and Population Survival[J].Ecolog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85,66(6):1762-1768.
[16] Kratz T K, Benson B J, Blood E R.The influence of landscape position on temporal variability in four North American ecosystems[J].The American Naturalist, 1991,138(2):355-378.
[17] 施清华.茫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格局研究[J].安徽农学通报, 2014,20(14):83-85.
[18] 陈 寅, 李阳兵, 谭 秋.茂兰自然保护区景观格局空间变化研究[J].地球与环境, 2014,42(2):179-186.
[19] 王艳芳, 沈永明.盐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景观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力[J].生态学报, 2012,32(15):4844-4851.
[20] 庞雄飞.广东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研究[M].广州: 广东科技出版社, 2003.
[21] 徐燕千.建立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重大意义[J].生态学报, 1993,13(1):14-20.
[22] 陈百明, 周小萍.《土地利用现状分类》国家标准的解读[J].自然资源学报, 2007,22(6):994-1003.
[23] 刘茂松,张明娟.景观生态学原理与方法[M].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4.
[24] Diamond J M .The island dilemma: lessons of modern biogeographic studies for the design of natural reserves[J].Biological Conservation, 1975,7: 129-146.
[25] 郑新奇,付梅臣.景观格局空间分析技术及其应用[M].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
Study on landscape patterns changes of each functional zone in Nanli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in Guangdong province
LIAO Fang-jun1, CHEN Zhi-ming2, LIU Zong-jun2, XIE Yong2
(1.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 and Planning,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Guangdong, China; 2.Nanling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Administration, Shaoguan 512727, Guangdong, China)
With 1∶10 000 topogaphic maps, updated Forest Resource Inventory Data in 1988, 1999 and 2009, based on the GIS platform and eCogntion, ArcGIS and IDRISI softwares, the dynamic changes of landscape patterns of natural-level nature reserve functional zones during the 20 years period in Nanling National Reserve in Guangdong province were quantificationally analyzed.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landscape zone patterns mainly were the forests, of them, the coniferous and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occupied large proportion (77%) in the experimental zone, the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occupied 56% in the buffer zone and the evergreen broad-leaved forest occupied 78% in the core zone; (2) the numbers of patch, patch density and marginal density all increased,the areas of landscape type plaque fluctuated, the degree of landscape fragmentation raised with time passed in each functional zone; (3)the forest landscape types conversed frequently in each functional zone, the non-forest landscapes such as construction land and water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4) Maximum plaque indexes of each landscape type showed fluctuation trends, the landscape structure changed more rich and complex with time went on; (5) Landscape connection enhanced in each functional zone during the studying period, and landscape diversity almost kept the maintenance level, which effectively maintained the stability of ecosystem in the studied region.
natural-level nature reserve; landscape pattern; landscape index; functional zone; Nanling reg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
S759.92
A
1673-923X(2015)09-0113-08
10.14067/j.cnki.1673-923x.2015.09.020
2015-01-23
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数字化监测与管护平台项目(GDHS13SGHG05025);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珍稀植物的种质资源收集、保护和利用”(2010B060200038);广东省林业科技创新专项资金项目“南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健康评与可持续经营关键技术研究”(2011KJCX020)
廖芳均,高级工程师;E-mail:blithe_fang@163.com
廖芳均,陈志明,刘宗君,等.南岭自然保护区各功能区景观格局研究[J].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报,2015, 35(9):113-120,138.
[本文编校:谢荣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