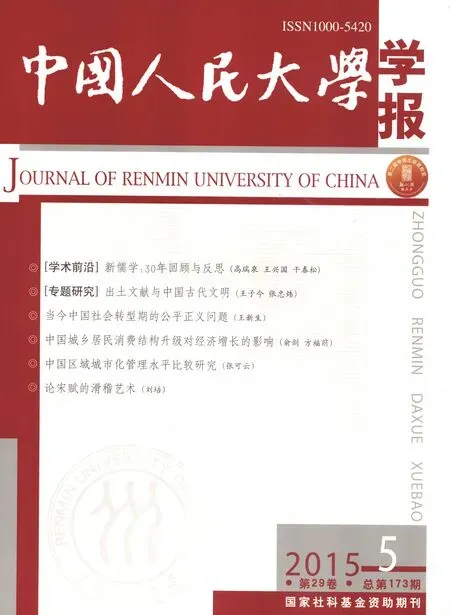汉代河西市场的织品
——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相结合的丝绸之路考察*
王子今
汉代河西市场的织品
——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相结合的丝绸之路考察*
王子今
汉武帝时代占有河西、列置四郡、打通西域道路之后,丝绸之路的历史文化意义更为显著。对于汉代丝路贸易实际情形的考察,限于资料的缺乏,推进颇有难度。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了解河西地区民间市场的中原织品,可以增进对当时丝绸之路经济与文化功能的认识。士卒贳卖衣财物,是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出土汉简简文与汉代遗址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可以证实相关现象。河西“市”的繁荣为织品贸易提供了便利。活跃的西域“贾胡”可能亦对这些商品继续向西转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河西毛织品的发现,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丝绸之路贸易的认识。
丝绸之路;河西;织品;民间市场;汉简;发掘资料
在张骞“凿空”之前,丝绸之路已经发挥着联系中原与中亚、西亚地方经济往来与文化交流的作用。[1][2]汉武帝时代占有河西、列置四郡、打通西域道路之后,这条东西通路的历史意义更为显著。正如俄罗斯汉学家比楚林(Бичурин)评价西域丝绸之路开通的意义时指出的,这一历史进步“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3](P224)。对于汉代丝路贸易实际情形的考察,限于资料的缺乏,推进颇有难度。结合出土汉简资料与遗址发掘收获了解河西地区民间市场的中原织品,可以增进对当时丝绸之路经济与文化功能的认识。
士卒贳卖衣财物,是中原织品流向河西的特殊形式。出土汉简简文与汉代遗址发掘获得的实物资料可以证实相关现象。活跃的西域“贾胡”可能亦对这些商品继续向西转运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河西毛织品的发现,也可以增进我们对丝绸之路贸易的认识。
一、“戍卒贳卖衣财物”与“吏民”“贳卖”现象
“戍卒贳卖衣财物”是河西汉简社会生活史料和社会经济史料中常见的现象。居延汉简可见如下题名的简册:“●第廿三部甘露二年卒行道贳卖衣物名籍”(E.P.T56:265),“甘露三年戍卒行道贳卖衣财物名籍□□”(E.P.T53:218),“●不侵候长尊部甘露三年戍卒行道贳卖衣财物名籍”(E.P.T56:253),“甘露三年二月卒贳卖名籍” (E.P.T56:263),“第十七部甘露四年卒行道贳卖名籍”(E.P.T3:2),“□年戍卒贳卖衣财物名籍”(E.P.T59:47)[4]等。另外简文可见“戍卒贳卖衣财物爰书名籍一编”(10.34A)[5],“戍卒自言贳卖财物吏民所定一编”(E.P.T53:25)[6]。
我们还看到有《亭卒不贳买名籍》。例如:“元康二年三月乘胡隧长张常业亭卒不贳买名籍”(564.25)[7]。
有简文说明,这类“贳卖”行为是受到禁止的:“案戍田卒受官袍衣物贪利贵贾贳予贫困民吏不禁止浸益多”(4.1)[8]。按照官方文书的说法,戍田卒“贳卖衣财物”的出发点似乎主要是“贪利”。然而,简文则又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句:“辞贫急毋余财独有私故练袭”(180.23)[9]。所陈说的似乎是因“贳卖衣财物”受到责罚者的辩解之词,自称其动机只是“贫急毋余财”,不得不变卖所“独有”的“私故练袭”。
居延汉简简文又可见参与类似“贳卖”“贳买”行为的主体是一般“吏民”的情形,如:“□行禁吏民毋贳卖”(239.115),“□平吏民毋贳买” (255.26)[10]。似乎“吏民”“贳卖”“贳买”也是常见的经济交易现象。“禁吏民毋贳卖”简文,体现这一情形也受到禁止。[11]有学者曾经指出“买卖双方均非军职人员”的情形,以为“以往说边塞衣服的买卖均在军事系统吏卒之间进行,这种说法值得商榷”[12]。然而所举简例“元康二年十一月丙申朔壬寅居延临仁里耐长卿贳买上党潞县直里常寿字长孙青复绔一两直五百五十约至春钱毕姚子方”(E.P.T57:72)[13],并不能确证“买卖双方均非军职人员”。
几则简文说到“平”的情形引起学者关注。如“第五隧卒马赦贳卖□□袍县絮装直千二百五十第六隧长王常利所,今比平予赦钱六百”(E.P.T56:17)[14],有的学者认为:“这里‘比平’即平抑物价。”论者分析这则简文以为:“士卒一件装了丝絮的冬袍原值一千二百五十钱,结果被砍价一半多,物主最后只得到六百钱。”[15]今按:“物主最后只得到六百钱”的解说或可商榷,“今比平予赦钱六百”也许是说王常利又补付马赦“钱六百”。简文“平”的具体含义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是这种形式限制“贳卖衣财物”的意义却是大体明确的。
“吏”予以“禁止”的,首先是“戍田卒受官袍衣物贪利贵贾贳予贫困民”现象。这些简文,似乎原本属于所谓《卒居署贳卖官物簿》(271.15A)[16]等文书。有学者认为,“居署贳卖”与“行道贳卖”形成对应关系:“戍卒的贳卖(买)活动或发生在‘居署’,或发生于‘行道’,‘居署’与‘行道’相对而言。”[17](P138)认识“贳卖官物”情形,可以参考《汉书》卷六一《张骞传》有关汉使团西行的记载:“妄言无行之徒皆争相效。其使皆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18]颜师古注:“言所赍官物,窃自用之,同于私有。”“所市之物,得利多者,不尽入官也。”[19](P2695-2696)以“官物”“贱市以私其利”,虽然为法令和军纪禁止,但仍然是普遍的情形。
我们又看到戍卒私人衣物即所谓“卒所赍衣物”(56.16)[20]以“贳卖”方式进入市场的普遍情形。邵台新曾经指出,这些简例反映的“都是布匹、衣物的买卖,价值不高,在买卖的过程中还有证人,买卖完成要以沽酒酬劳证人”[21](P208)。
“戍卒贳卖衣财物”是丝绸之路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据简牍文字提供的信息,除成衣之外,邵台新所谓“布匹”实即作为衣料的成匹的织物也成为买卖对象。
二、简牍记录:织品的“卖”和“转”
在相关交易与债务记录中,可以看到买卖对象并非成衣的情形。衣料的“贳卖”“贳买”在简文中有所反映。例如:“收虏卒丁守责故隧长石钦粟桼斗皁布亖尺”(E.P.T59:114),“白素五尺□□,白素五尺十七”(E.P.T65:524)[22],“吞远隧卒夏收自言责代胡隧长张赦之赦之买收缣一丈直钱三百六十” (217.15,217.19)[23]。这种交易,已经并非“衣物”。贳卖成匹的织品,在简牍资料中也可以看到“贳卖”织品数量可观的记录。如:“毋尊布一匹”(E.P.T51:329),“元赤缣一□”(E.P.T51:338)[24],“皁练一匹直千二百”(35.6),“八稯布一匹直二百九十”(287.13)[25],“布一匹直四百”(E.P.T59:657),“缣一匹直六百”(E.P.F31:34),以及诸多“帛一匹”的简例(E.P.T65:63)、(E.P.T65:65)、(E.P.T65:107)、(E.P.F22:293)、(E.P.T65:160)[26]。多数以“一匹”为计的织物交易均为士兵个人私物买卖。典型例证有额济纳简:“第九隧卒史义角布一匹贾钱五百约至八月钱必已钱即不必”(2000ES9SF4:22)[27]。此简例织物“一匹”已经完成交易过程。简文有“贾钱”记录,并说明“约至八月钱必已”。这是典型的“贳卖”形式。

简文还可以看到织品数额更大的情形:“始元三年三月丙申朔丁巳北乡啬夫定世敢言之,□□二百卌七匹八尺直廿九万八千一百”(47.3)[38],“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直六十万八千四百,率匹二百一十七钱五分”(73EJT26:23)[39]。前一例据价格“直廿九万八千一百……”,可知“□□二百卌七匹”应为“一千二百卌七匹”。后一例“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这样的数量,当然有满足部队被服制作需求的可能。我们看到有涉及“袭”的数量的简例,如甲渠候官简:“受正月余袭二百卌二领,其二领物故,今余二百卌领”(E.P.T51:192)[40]。“袭”显然是部队军装。“二百卌二领”仅仅只是“余袭”,可知军需数量确实是可观的。我们还可以分析以下简例:“最凡吏九十七人,其十四人已前出,定受奉八十三人,用绛一匹,用布十八匹,用羊韦八十三件,交钱五万九百八钱”(E.P.T40:6B)[41]。现在不能确定“用绛一匹”、“用布十八匹”这两项织品消费的具体用途,但推想可能是“吏”“定受奉八十三人”制衣所用。汉代尺度规格,每匹四丈。《说文·匚部》:“匹,四丈也。八揲一匹。”段玉裁注:“按‘四丈’之上当有‘布帛’二字。《杂记》曰:纳币一束,束五两,两五寻。郑曰:纳币谓昏礼纳征也。十个为束,贵成数,两两合其卷,是谓五两。八尺曰寻。五两,两五寻,谓每两五寻则每卷二丈也。合之则四十尺。今谓之匹。犹匹偶之云与。”[42](P635)今按:居延汉简(168.10)“三楪□长三丈三尺以直钱三百五十”[43],“楪”似应即《说文》“八揲一匹”的“揲”。《急就篇》卷二:“贳贷卖买贩肆便。资货市赢匹幅全。”颜师古注:“四丈为匹,两边具曰幅。”[44](P107-108)《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载:“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45](P1149)参考前引简文“八十三人,用绛一匹,用布十八匹”,合计十九匹,平均每人0.228 9匹。那么,前引简文“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按照这一比例,可以满足“吏”12 220.36人“用绛”“用布”数量需求。
简文“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直六十万八千四百”,有总价值数字,“率匹二百一十七钱五分”,每匹的价格也是明确的。如果推测这批“七稯布”之“入”与河西织物市场直接相关,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敦煌汉简中有关于“出牛车转绢如牒毋失期”(1383)的记录[47],可知河西地方织品供应成为重要运输内容。“毋失期”,说明“转绢”运输任务有严格的绩效规定和时限要求。
以上所举简例,大致织物“一匹”者,很可能由戍卒自家乡携带至边地。如肩水金关简所见情形:“广野隧卒勤忘贳卖缥一匹隧长屋兰富昌里尹野所” (73EJT23:965)[48],可能具有典型性。

三、边塞织品文物遗存
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七记载了“天都”地方汉章帝章和时代(87—88年)“木简札”的发现:“崇宁初,经略天都,开地得瓦器,实以木简札,上广下狭,长尺许,书为章草,或参以朱字,表物数,曰:‘缣几匹,绵几屯,钱米若干’。皆‘章和’年号。松为之,如新成者,字遒古若飞动,非今所畜书帖中比也。其出于书吏之手尚如此。正古谓之‘札书’,见《汉武纪》、《郊祀志》,乃简书之小者耳。张浮休《跋王君求家章草月仪》云尔。”[53](P213)《宋史》卷八七《地理志三》:“天都砦。元符二年,洒水平新砦赐名天都,东至临羌砦二十里,西至西安州二十六里,南至天都山一十里,北至绥戎堡六十五里。”[54](P2161)“天都”在宋与西夏战争前线,据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地在今宁夏海原。[55](P20-21)[56](P307)也应相当汉代北边。看来,“缣几匹,绵几屯”简文传递的信息在宋代已经为学者关注。
甘肃考古学者在总结敦煌西部汉代长城烽燧遗址出土实物时,列言“生产工具、兵器、丝绸……”[57],丝绸位居第三。
据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流域的考察,许多汉代烽燧遗址发现织品遗存。如烽燧A6与汉代封泥、木简同出有“敞开的、织造精美的覆盖有黑色胶质的丝织品残片;丝质纤维填料;细股的红麻线”等文物。通称“破城子”的城障A8与诸多汉代文物同出“天然丝,丝绸纤维填料”,“植物纤维织物”,“天然褐色和其他颜色的丝绸残片”,“不同颜色的丝织物、丝绸填料、植物纤维材料残片”。烽燧P1发现“黄色天然丝绸的小块残片和羊毛纱线”,烽燧A9发现“一块红丝绸”。障亭A10发现包括“褐色、红色、绿色和蓝色”的“不同颜色的丝绸残片”。台地地区“地点1”标号为P.398的遗存,发现“(天然)褐色、黄色、深红色、深蓝色、浅蓝色、深绿色、浅绿色”的“小块丝绸残片”。“地点7”标号为P.443的遗存也发现丝织物,“色泽有褐色(天然)、黄褐色、浅绿色、深绿色、蓝绿色、和深蓝色”。金关遗址A32“地点A”发现“有朱红色阴影的鲜红丝绸残片”,“地点B”发现“玫瑰红、天然褐色丝绸和丝绸填料残片”,“地点C”发现“天然褐色、褐色和酒红色丝绸残片”,“地点E”发现“丝质服装、丝绸填料和纤维织物残片”,“部分缝补过的丝绸为天然褐色、绿色、蓝绿色、蓝色和红色”。地湾遗址A33“地点4”发现的丝绸残片,色彩包括“褐色、浅红色、深红色、绿黄棕色、黄绿色和黄色”,又据记述,“色度为:接近白色、褐色、红色、绿色、普鲁士蓝”。大湾遗址A35地点1、地点2、地点5、地点12发现“丝绸残片”,地点4、地点6、地点7、地点8、地点9、地点10发现“纺织物残片”。“地点1”标号为P.66的遗存,发现“各种颜色(浅黄色、灰色、褐色、绿色和玫瑰红色)的丝绸残片”。[58](P34-35、60、86、94、284、288、333-334、339、350、376-377)
有的丝绸残片是在鼠洞里发现的。[59](P275)额济纳河流域汉代遗址的丝绸遗存普遍经过鼠害破坏,因此每多残碎。但是台地地区“地点7”标号为P.402的发现,据记录:“黄色(天然)丝绸残片,其中一块的整体宽51.5~51.7厘米。”[60](P288)地湾遗址A33“地点6”发现的丝绸残片中,“第2件和第19件保留了完整的宽度,其宽分别为45厘米和40厘米”[61](P359)。
对照前引《汉书》卷二四下《食货志下》关于“布帛广二尺二寸为幅,长四丈为匹”的规格,“广二尺二寸为幅”以西汉尺度通常23.1厘米计,应为50.82厘米,“整体宽51.5~51.7厘米”的形制与此接近。而以东汉尺单位量值23.5厘米计*据计量史学者考论:“西汉和新莽每尺平均长23.2和23.09厘米,二者相差甚微,考虑到数据的一惯性,故厘定为23.1厘米。而东汉尺的实际长度略有增长,平均每尺长23.5厘米”。为了尊重实测数据,故东汉尺单位量值暂定为23.5厘米。参见丘光明编著:《中国历代度量衡考》,55页,北京,科学出版社,1992。,“广二尺二寸为幅”恰好为51.7厘米。
以51.7厘米为幅宽,前引记载织品数量最多的简文“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总面积达13 594平方米。
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纺织品140件,其中丝织品114件。“品种有锦、罗、纱、绢等”。所谓“绿地云气菱纹锦”,“以绿色作地,黄色为花,蓝色勾递,基本纹样为云气和菱形几何图案”,“织锦的工艺技术要求是相当高的”。“马圈湾出土的四经绞罗,是一个不多见的品种,其经纬纤度极细”,“轻薄柔美,是少见的精品。”“黄色实地花纱”1件,“是目前我国所见最早的实地花纱,在丝绸纺织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绢92件,研究者分析了其中61件标本,“其特点是经纬一般均不加拈,织物平挺、紧密,色彩丰富、绚丽”。“颜色有:红、黄、绿、蓝、青、乌黑、紫、本色、青绿、草绿、墨绿、深绿、朱红、桔红、暗红、褪红、深红、绯红、妃色、褐黄、土黄、红褐、藕褐、蓝青、湖蓝等二十五种”[62](P54-55)。
贝格曼考察额济纳河流域多处遗址发现的织品均颜色鲜丽,特别引人注目。瓦因托尼一线的“障亭10”试掘出土“各种颜色的丝绸”制作的“丝质缝缀物”,“9块丝绸衬里的颜色为:深酒红色、绿色、浅灰绿、深蓝、蓝绿色;3块丝绸面子的颜色为:深红色(主要的两部分)、深天蓝色(三角形的角)”[63](P93-94)。鲜艳华美的织品竟然在以“寒苦”为生活基调,甚至往往“至冬寒衣履敝毋以买”(E.P.T59:60)[64]的边塞军人身边发现[65][66],使得我们不得不注意导致这种异常现象发生的特殊的织物市场背景。
汉代制度礼俗,色彩的使用依身份尊卑有所不同。如《续汉书·舆服志下》:“公主、贵人、妃以上,嫁娶得服锦绮罗縠缯,采十二色,重缘袍。特进、列侯以上锦缯,采十二色。六百石以上重练,采九色,禁丹紫绀。三百石以上五色采,青绛黄红绿。二百石以上四采,青黄红绿。贾人,缃缥而已。”自“采十二色”、“采九色”、“五色采”、“四采”至所谓“缃缥”,形成了等级差别。“缃缥”是极普通的单一之色。刘昭注补:“《博物记》曰:‘交州南有虫,长减一寸,形似白英,不知其名,视之无色,在阴地多缃色,则赤黄之色也。’”[67](P3677)这种“贾人”服用的所谓“缃缥”,在有的条件下显示“赤黄之色”,通常则“视之无色”。很有可能就是不加漂染的原色织品,即前引文字所谓“黄色(天然)”、“褐色(天然)”。有学者注意到:汉代墓葬发掘资料中织品衣物色彩品种的多少,也依地位高下有所不同。[68]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河西边塞遗址发现的织品之色彩纷杂绚丽,如果以为普通军人自身所服用,也是不好理解的。
考古学者发现,边塞遗址发现的织物质量,竟然可以看到对可能用以满足远销需要的设计美学品级追求。前说“障亭10”发现的丝绸残件中,可见这样的作品,“华丽的复合经线棱纹丝绸残片,底色为苔藓黄,简单的斜纹菱形图案的交叉处有蓝绿色和浅绿色条纹,缝缀在一块普通的灰绿色丝绸上”。又如,“2块华丽的复合经线棱纹丝绸残片,有蓝色、绿色、灰白色,其中一块缝缀在另一块上面”。有学者认为,“其制作水平从技术和艺术两个方面来讲都很高。图案属于很特别的类型,堪与欧亚地区流行的动物风格相媲美。”[69](P96)
有经济史研究者注意到:“至今仍不时在沿丝路沙漠中发现成捆的汉代丝织品。”当时丝路交通形势十分复杂:“所谓通西域的丝路,实际上是在亭障遍地、烽墩林立和烟火相接的严密保护下才畅通无阻的。”[70](P440、439)而河西烽燧遗址发现的大量的“汉代丝织品”,也成为丝绸之路贸易史的生动见证。
四、“禄帛”“禄布”“禄絮”
汉武帝控制河西,“移民开发河西”,“变河西游牧之区为农业定居之区”,对于丝绸之路交通有重要意义。[71](P307)不过,河西地区距中原经济重心地区路途遥远,正如有的学者所分析的,“一些财政收入缺乏的地区,要仰赖中央或其他地方发来钱币,有时便不能如期发放俸钱”。于是,“汉简中常有官吏数月未能领取俸钱的记录,甚至以实物计价发给官吏替代俸钱”。例如:“始元三年九月四日以从受物给长中帛若干匹直若干以给始元三年正月尽八月积八月奉”(509.19),“出河内廿两帛八匹一丈三尺四寸大半寸直二千九百七十八给佐史一人元凤三年正月尽九月积八月少半日奉”(303.5),“入布一匹直四百,絓絮二斤八两直四百,凡直八百,给始元四年三月四月奉,始元四”(308.7)[72][73](P47-48)。简文涉及作为“奉”的“替代”的实物,有“帛”“布”“絮”。
居延汉简中又多见政府用中原织品支付军人俸饷,即应用所谓“奉帛”(89.12),“禄帛”(39.30,95.7,266.9,394.1[74],E.P.T65:79[75]等),“禄用帛”(210.27,266.15,480.11)[76],“禄布”(E.P.T59.297),“禄县絮”(E.P.T6:81)[77]的情形。边地军队指挥部门和地方行政机构可以提供充分的织品,提示我们关于这种特殊物资供应体系之工作效能的信息。
“帛”“布”“絮”作为“禄”的形式为军队官兵所接收,也反映了当地市场交易条件以及以此为基础形成的对于相关商品的社会感觉和价值知识。内地出产的织物成为交换各种商品的等价物,对于河西地方市场的丝绸流通无疑也会产生重要的影响。
《汉书》卷九九中《王莽传中》载:“(天凤三年)五月,莽下吏禄制度,曰:‘予遭阳九之阨,百六之会,国用不足,民人骚动,自公卿以下,一月之禄十繌布二匹,或帛一匹。予每念之,未尝不戚焉。今阨会已度,府帑虽未能充,略颇稍给,其以六月朔庚寅始,赋吏禄皆如制度。’”[78](P4142)有学者指出:“现知居延简中以布帛充奉的只有始元三年、四年以及元凤三年等年号”以及“新莽时以布帛充奉”现象,论者特别指出:“凡以布帛充奉各简,并无赋奉未到的记载”。[79](P7-8)由此似可反映河西地方“府帑”储备中“布帛”比较充足的情形。
五、河西的“市”与织品贸易
上文所说戍卒与吏民之间的私人“贳卖衣财物”形式,属于民间交易。而“赵丹所买帛六匹”(168.13)[80]则可能通过市场。又前引“今余广汉八稯布卌九匹直万一千一百廿七钱九分”,“□□二百卌七匹八尺直廿九万八千一百”,“入七稯布二千七百九十七匹九尺六寸五分直六十万八千四百,率匹二百一十七钱五分”数例可以称作大宗的买卖,大概也应如此。
我们看到,也有“贩卖衣物于都市”的情形:“甲渠言部吏毋铸作钱发冢贩卖衣物于都市者”(E.P.F22.37)[81]。
有学者根据出土简牍资料分析“投入居延市场的货物”中,有“衣服类”和“布帛类”:
衣服类,计有:
皂布衣、韦绔、皂袭、皮绔、皂襜褕、布复襦、绛单襦、皂练复袍、布复袍、皂襦、缥复袍、白紬襦、袭布绔、皂复绔、单衣、缣长袍、皂绔、裘、绉复襦等。
布帛类,计有:
七稯布、八稯布、九稯布、练、缣、皂练、白素、皂布、布、絣、鹑缕、廿两帛、白缣、絮巾、缇绩、系絮、丝等。[82]
“衣服类”中“韦绔”、“皮绔”、“裘”等大致不属于我们讨论的对象。“布帛类”中可能“絮巾”不宜列入。“系絮”应为“糸絮”之误。由于新出土简牍资料的陆续发表,现今我们看到的“衣服类”和“布帛类”的品种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当时的统计。
《汉书》卷二八下《地理志下》说河西四郡风俗:“其俗风雨时节,谷籴常贱,少盗贼,有和气之应,贤于内郡。”[83](P1645)“谷籴常贱”,已经言及这一地区的市场形势。《后汉书》卷三一《孔奋传》记述:“时天下扰乱,唯河西独安,而姑臧称为富邑,通货羌胡,市日四合,每居县者,不盈数月辄致丰积。”调任的“河西守令”,往往“财货连毂,弥竟川泽”。对于所谓“市日四合”,李贤注:“古者为市,一日三合。《周礼》曰:‘大市日侧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今既人货殷繁,故一日四合也。”[84](P1098)河西地方的富足和市场的繁荣,得到史籍的明确记录。有学者指出:“居延地区靠近汉代中西交通大道,有条件发展转运贸易,这也是居延的商业市场具有一定水平和商业得以发展的有利条件。”[85]这样的判断是有根据的。正是在“市日四合”,“人货殷繁”的情况下,织品实现了“通货羌胡”的贸易程序。
居延汉简可见“为官市”简文(456.2)。[86]又有“居延市吏”称谓(E.P.T59:645),这一职任似乎亦参与织品交易的管理。
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禽寇燧卒冯时贳卖衣物契约券”,亦出“所买布疏”:“所买布踈:大□郭成买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斗,始乐尹虎买布三尺五寸直一石四斗,万贳范融买布一丈二尺直四石二斗,长生赵伯二石,凡九斛前付卿已入,索卿”(77.J.H.S:17A.B)。[87]“布”的“直”以谷物计,或许体现了河西市场在特殊情况下特殊的交换方式。
六、河西军人消费生活中的毛织品
马圈湾烽燧遗址发掘出土毛织品13件,“品种有罽、褐、缂毛带、毡垫、毡靴等”。有“图案非常精美”的“方格罽”1件。又有“晕繝罽”1件,“花部依次由黄向蓝变化,呈晕色效果。这是目前我国发现最早的一件晕繝毛织物,它对唐代晕繝锦的产生,无疑起过重大影响”。又有“红罽”2件,“深红罽”2件,“莲紫罽”1件,“黄罽”1件,“青褐斑罽”1件。[88](P55-56)
贝格曼考古报告中也有许多关于毛织品发现的记录。
河西出土麻织品可能多来自中原地区,而毛织品,特别是质量较高的毛织品不能排除来自西域地方的可能。河西汉塞的毛织品遗存可能经由匈奴传入*有学者指出:“僮仆都尉驻准噶尔盆地直通塔里木盆地的天山南麓焉耆、危须、尉犁三个小国之间,征发三十六国亘于农、牧、工、矿各方面的产品,以及草原大道之外的沃洲大道上商业利润,构成匈奴经济面不可缺的一环节。” 姚大中:《古代北西中国》,76页,台北,三民书局,1981。,活跃的西域商人或许也曾经直接促成了这种商品在丝绸之路沿途市场的流通。
西域商人曾经有非常活跃的历史表演。如《后汉书》卷八九《南匈奴传》记载:“(建武)二十八年,北匈奴复遣使诣阙,贡马及裘,更乞和亲,并请音乐,又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89](P2946)*《太平广记》卷四○二《鬻饼胡》:“但知市肆之间,有西国胡客至者,即以问之,当大得价。生许之……将出市,无人问者。已经三岁,忽闻新有胡客到城,因以珠市之……”可知“胡客”多是“贾胡”。参见李昉等编:《太平广记》,3244页,北京,中华书局,1961。“西域诸国胡客”和匈奴使团同行“与俱献见”,值得我们注意。班彪为汉光武帝刘秀起草的“报答之辞”将“求率西域诸国胡客与俱献见”写作“欲率西域诸国俱来献见”[90](P2946-2947)。“胡客”的身份被隐去,似乎“西域诸国胡客”可以看做“西域诸国”的代表。此外,又有《后汉书》卷四七《班超传》的说法:“超遂发龟兹、鄯善等八国兵合七万人,及吏士贾客千四百人讨焉耆。”[91](P1581)可知西域“贾客”亦参与战争。有学者以“游牧民族商业化的倾向,也就愈益显著”的说法概括匈奴对“贸易权益”的追求。[92](P111)其实西域诸国可能更突出地体现出“商业化的倾向”。
《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写道:“后复征拜谒者,使持节领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所谓“贾胡数遗”“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应是一种贿赂行为。也许这种行为曲折体现了匈奴占领时期特殊经济形式的历史惯性。其中“罽”正是西域特产。“贾胡”身份,应是西域商人。李贤注:“贾胡,胡之商贾也。”[93](P1683-1684)西汉中期,即有西域商人活跃于北边的史实记录。如陈连庆所说:“在中西交通开通之后,西域贾胡迅即登场。”[94]以敦煌汉简为例,所见乌孙人(88,90,1906),车师人(88),“知何国胡”(698)[95](P9,202,71)等等,未可排除来自西域的商人的可能。《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篇末有以“论曰”形式发表的对于西域问题的总结性文字,其中说到“商胡贩客”:“论曰:西域风土之载,前古未闻也。汉世张骞怀致远之略,班超奋封侯之志,终能立功西遐,羁服外域。自兵威之所肃服,财赂之所怀诱,莫不献方奇,纳爱质,露顶肘行,东向而朝天子。故设戊己之官,分任其事;建都护之帅,总领其权。先驯则赏籝金而赐龟绶,后服则系头颡而衅北阙。立屯田于膏腴之野,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96](P2931)因军事控制实现贸易的繁荣,其中“商胡贩客”的积极表现引人注目。
据斯坦因的考察记录,在敦煌地方的烽燧遗址中,“得到半段木简,上书古撒马尔干同布哈拉通行的古窣利语;这半段显然是作为符节之用。”“在这一段长城一座烽燧尘封堆积的室中发简历八封干干净净用古窣利文字体写在纸上的书函……其中有些找到时外面用绢包裹,有些只用绳缠住。这种字体因为过于弯曲以及其他缘故,极难认识,现在知道这是中亚一带商人到中国以后发回的私人通讯。他们显然很喜欢用新发明的纸作书写材料,而不喜用中国人所墨守着的木简。”经造纸史权威学者考察,“证明这些书函的材料是现在所知道的最古的纸”[97](P128、133)。邵台新据此认为,河西“有胡商居住且与中国商贾贸易是不容置疑的”[98](P212)。如果这一发现正确不误,这些书信遗存应当反映了“中亚一带商人”在河西活动,而他们的书信也通过汉王朝驿传邮置向远方转递的事实。斯坦因河西汉代烽燧考察记录中写道:“所得诸有趣的遗物中有一件是古代的绢,头上书汉字同婆罗谜文,这是古代绢缯贸易的孑遗。绢头上面备记产地,以及一疋的大小重量等项。这块即是从那疋上割下来的。”[99](P134)这当然是丝绸之路上“绢缯贸易”正确无疑的文物实证。而烽燧戍卒也参与了“胡商”积极从事的这种贸易,值得我们关注。
据《后汉书》卷二四《马援传》记载,对于马援南征进击迟缓以致“失利”,有“类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的指责。李贤解释说:“言似商胡,所至之处辄停留。”[100](P844)《马援传》说“西域贾胡”,李贤注称“言似商胡”,可知“商胡”和“贾胡”称谓大致指代相同的身份。可能正是由于“商胡”“贾胡”的活跃,促成了“罽”等毛织品流入内地,进入了河西军人的消费生活。这种商品继续向东转输,应当是丝绸之路贸易活动中很自然的情形。

《盐铁论·力耕》载“文学”曰:“今骡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鼲貂旃罽,不益锦绨之实。”[111](P28-29)“西胡”之“骡驴”与中土之“牛马”,“西胡”之“鼲貂旃罽”与中土之“锦绨”,彼此形成对照。而很可能在丝绸之路上,正是“锦绨”与“旃罽”作为产地各在东西,品质亦显著不同的商品,经历辗转历程实现了交换。在当时特殊的商运程序中,河西地方似乎发挥了重要的中转作用。而汉简文字与烽燧遗存提供的信息,反映来自内地的戍防军人也在一定意义上曾经积极参与了这种文化交流,这是值得我们特别注意的。
[1] 王子今:《穆天子神话和早期中西交通》,载《学习时报》,2001-6-11。
[2] 王子今:《前张骞的丝绸之路与西域史的匈奴时代》,载《甘肃社会科学》,2015(2)。
[3] В.Н.狄雅可夫、Н.М.尼科尔斯基编:《古代世界史》,北京,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教材编审处,1954。
[4] [6][13][14][22][24][26][28][30][40][41][50][64][75][77][81]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文化部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居延新简:甲渠候官与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
[5][7][8][9][10][16][20][23][25][29][31][38][43][46][72][74][76][80][86] 谢桂华、李均明、朱国炤:《居延汉简释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11] 王子今:《汉代丝路贸易的一种特殊形式:论“戍卒行道贳卖衣财物”》,载《简帛研究汇刊》第1辑“第一届简帛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历史系、简帛学文教基金会筹备处,2003。
[12][82][85] 徐乐尧:《居延汉简所见的市》,载《秦汉简牍论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
[15] 龚留柱:《中国古代军市初探》,载《史学月刊》,1994(3)。
[17] 李天虹:《居延汉简簿籍分类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18] 张德芳:《汉帝国在政治军事上对丝绸之路交通体系的支撑》,载《甘肃社会科学》,2015(2)。
[19][45][78][83][102][103] 班固撰:《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21][98] 邵台新:《汉代河西四郡的拓展》,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
[27] 魏坚主编:《额济纳汉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32][35][48]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肩水金关汉简(贰)》,上海,中西书局,2012。
[33][36][39] 甘肃简牍博物馆、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肩水金关汉简(叁)》,上海,中西书局,2013。
[34][37] 甘肃简牍保护研究中心、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古文献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肩水金关汉简(壹)》,上海,中西书局,2011。
[42][104]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据经韵楼臧版影印,1981。
[44] 管振邦译注,宙浩审校:《颜注急就篇译释》,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7][95] 吴礽骧、李永良、马建华释校:《敦煌汉简释文》,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
[49] 大庭脩:《再论“检”》,载《简帛研究》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
[51] 沈刚:《居延汉简语词汇释》,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
[52] 萧璠:《关于额济纳河流域发现的八点二号汉代封检》,载刑义田、萧璠、刘增贵、林素清合编:《居延汉简补编》,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九十九,1998。
[53] 邵博撰,刘德权、李剑雄点校:《邵氏闻见后录》,北京,中华书局,1983。
[54] 脱脱等撰:《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
[55]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2。
[56] 史为乐主编:《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57] 岳邦湖:《丝绸之路与汉塞烽燧》,载关西大学东西学术研究所编:《东西学术研究所纪要》第25辑,1992;《简帛研究》第1辑,北京,法律出版社,1993。
[58][59][60][61][63][69] 弗克·贝格曼考察,博·索马斯特勒姆整理:《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斯文·赫定博士率领的中瑞联合科学考察团中国西北诸省科学考察报告考古类第8和第9》,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
[62][88]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马圈湾汉代烽燧遗址发掘报告》,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敦煌汉简》,北京,中华书局,1991。
[65] 王子今:《汉代西北边塞吏卒的“寒苦”体验》,载《简帛研究二○一○》,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66] 王子今:《居延汉简“寒吏”称谓解读》,载《居延敦煌汉简出土遗址实地考察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67][84][89][90][91][93][96][100] 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
[68] 杨继承:《白衣再考——汉代的服色、等级与符命》,待刊稿。
[70] 傅筑夫:《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史》,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
[71] 梁加农:《早期丝路研究》,载朱新予主编:《中国丝绸史》,北京,中国纺织工业出版社,1997。
[73] 何德章:《两汉俸禄制度》,载黄惠贤、陈锋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79] 薛英群、何双全、李永良注:《居延新简释粹》,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
[87] 嘉峪关市文物保管所:《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调查报告》,载甘肃省文物工作队编:《汉简研究文集》,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
[92] 殷晴:《丝绸之路与西域经济——十二世纪前新疆开发史稿》,北京,中华书局,2007。
[94] 陈连庆:《汉唐之际的西域贾胡》,《中国古代史研究:陈连庆教授学术论文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1。
[97][99] 斯坦因:《斯坦因西域考古记》,上海,中华书局,1936。
[101] 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
[105][107][110] 李昉等:《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用上海涵芬楼影印宋本复制重印,1960。
[106][108] 张溥编:《汉魏六朝百三家集》卷一一《汉班固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09] 曹植著,赵幼文校注:《曹植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11] 王利器校注:《盐铁论校注》(定本),北京,中华书局,1992。
(责任编辑 张 静)
Fabric in Hexi Market of the Han Dynasty:The Silk Road Study of Combining Han Bamboo Slips Unearthed with Excavated Materials
WANG Zi-jin
(The School of Chinese Classic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Beijing 100872)
The Silk Road became historically and culturally more significant following the occupation of Hexi by the Han Empire,which successively set up four commanderies,and opened up the road to the Western Region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Wudi.However,owing to the lack of data,advance in the exploration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Han Silk Road trade is rather difficult.Combining Han bamboo slips unearthed with the excavated Zhongyuan( Central China )fabric in folk market of Hexi area can help promot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economic and cultural functions of the Silk Road at the time.The soldiers selling clothes and other belongings on credit was a special form that Zhongyuan fabric flew to Hexi.The Han bamboo slips unearthed and the physical materials excavated from the Han sites can verify the related phenomena.The prosperity of the Hexi “market” facilitated the fabric trade.The active western “Gu Hu”probably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ransporting these goods to the west.The discovery of the Hexi wool can also enhance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Silk Road trade.
Silk Road;Hexi;fabric;folk market;Han bamboo slips;excavated materials
王子今: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出土文献与中国古代文明研究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 100872)
*本文写作得到杨继承、李兰芳、杜晓的帮助,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