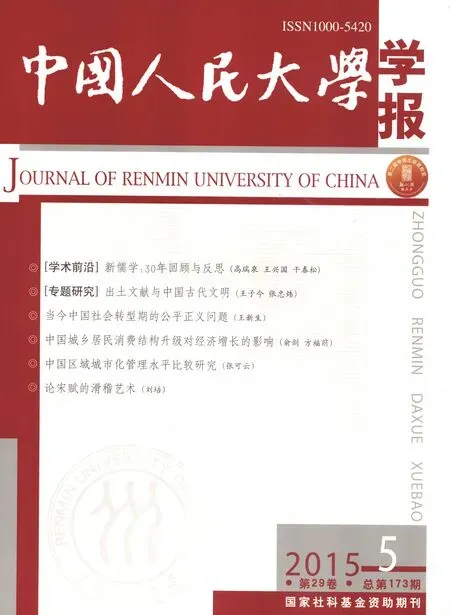论宋赋的滑稽艺术
刘 培
论宋赋的滑稽艺术
刘 培
辞赋创作自娱娱人的内在冲动相当明显,宋赋对滑稽描写相当重视。宋代文化重视学殖深淳、理趣盎然和道德情怀,这三者构成了宋赋滑稽艺术的基本要素。宋代文人大多兼具学者与作家身份,其诗文创作相当重视彰显学术,因而从互文性的角度来观照宋赋的滑稽艺术,是非常有必要、有意义的。对于滑稽的世俗特色,宋人在辞赋创作中以提升的态度来面对,而非拒斥。游走于雅与俗之间的宋赋,在庄严与轻佻、高雅与平庸的巨大反差中凸显着滑稽艺术的幽默诙谐的特色。宋赋能够在俳谐描写中以情观物、以理释情、融情入理、情理相谐,实现超越物象噱笑层次的幽默效果和情理感悟,让人在解颐之余产生感触与遐想。宋代文人对现实政治具有批判精神,也具有整饬世道人心的道德自觉。宋赋继承了滑稽艺术的这种淑世情怀,并将其发扬光大。
宋代;辞赋;滑稽;互文性;雅俗;理趣;道德情怀
辞赋创作自娱娱人的内在冲动相当明显,和其他文体相比,辞赋从它形成之时就和娱乐性结下不解之缘。汉赋的一个重要源头是古优的优语、俳词。《史记》中将古优列入《滑稽列传》,以表彰其“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1](P3191)的政治价值。以“滑稽”代称这类人,是因为优人的俳语既具出口成章、词不穷竭、能言善辩、言辞流利的节奏美感,又具内容上的诙谐谑噱性质。①前人对 《史记》的《滑稽列传》和《樗里子甘茂列传》以及《楚辞章句》的有关注释,皆把滑稽训释为酒器,似没有充分的证据,但训释为“圜转纵舍无穷之状”、“出口成章,词不竭穷”,则相当准确地概括了俳优艺术的喜剧性特色。滑稽表演的俳词,妙思迭出,滔滔不绝,既具有语言的节奏美感又具有内容上的诙谐谑噱性质。至于汉语流畅整齐的语言,尤其是韵语,对营造喜剧效果、烘托喜剧气氛的作用,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深思的问题。
本文所谓的滑稽,就是针对辞赋创作中内容和语言上的这些特点而言的。谑戏文章在六朝时期成为俳谐文一体,专以调笑诙谐为目的的辞赋也被称为俳谐赋。不过,辞赋与生俱来的滑稽基因在几乎一切赋体中皆有显现的可能,它并不会因为体式的分工而增强或减弱,而且它重视行文流畅整齐,铺排协韵,其语言的节奏美感,较之俳谐文更能体现文学的娱乐精神。宋赋直承汉魏六朝传统,相当关注传统辞赋中引人入胜的滑稽描写,并且将之发扬光大。宋代文化重视学殖深淳、理趣盎然和道德情怀,这三者构成了宋赋滑稽艺术的基本要素。
从整体创作来看,宋赋的滑稽色彩是相当浓厚的,本文就其滑稽艺术有别于前代的突出特征作一探讨,以就教于大方之家。
一、立足于融会贯通的互文性观照
宋代是一个文化昌明的时代,文人大多兼具学者与作家身份,其诗文创作相当重视彰显学术,他们崇尚的创作状态是融会众学、以才运学,通过对既有知识和历史经验的把握来提升识见,展示文华风采和胸襟学力。基于这样的创作倾向,那些优秀的诗文,往往广泛涉及前人书写中关于这方面问题的种种思考与探索,他们善于揣摩、体会前人的心理、境界,并通过创作来融会、超越之。因此,从互文性的角度来观照宋人的创作是非常有意义的,对于宋赋的滑稽艺术,这种探索也同样有价值。
宋代辞赋的滑稽成分,有许多是对具体源文本的转相祖述。扬雄的《逐贫赋》和韩愈的《送穷文》是将“贫”“穷”拟人化以自嘲的俳谐佳作,而且二者之间也存在着互文关系。*黄庭坚《跋韩退之送穷文》曰:“《送穷文》盖出于扬子云《逐贫赋》,制度始终极相似。而《逐贫赋》文类俳,至退之亦谐戏,而语稍庄,文采过《逐贫》矣。”参见黄庭坚:《山谷全书·别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宋人创作中以此二赋为蓝本的作品,或铺采摛文,踵事增华;或反其道而行,翻新出奇。赵湘的赋体文《迎富文》*对赋体的认定不能完全依赖于名称中是否有“赋”字,而应该根据其内容和形式上的体式特征和继承性来鉴别,在崇尚破体为文的宋代,这一点相当重要。本文所引辞赋赋题中无“赋”者,皆为赋,下文不再一一说明。顺二文之势,在送穷、逐贫之外,以迎富构思,同一机杼,各写两边,旨趣所趋相同。赋中铺排仁富、义富、信赋、孝富,意在说明若仁义信孝,即使贫穷,人格上也是富有的,人生也是充实的,读之令人会心一笑。王之望的《留穷文》基本上是对韩愈《送穷文》的模仿,其中描写个人际遇一段,完全脱胎于韩文,只是描写更为具体,语言更为整丽流畅。通过这种对原作毫不避讳的有意“冒犯”来与之争衡,是宋人惯常的做法,意在显示自己的才华不输前人。而且,这种模仿不是偷偷摸摸的,作者故意强调了作品与韩文的联系:“吾读韩子,久闻尔名,谓子有知,庶几神灵。子则不然,憎贫弃旧,我不尔驱,尔顾我咎。凡人之生,各有定分,贵贱穷达,造物所命。天生我穷,令与子俦,命实为之,汝安归尤?物极必反,否泰相缪,吾穷久矣,庶其有瘳。”*本文所引辞赋,均出自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上海、合肥,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并参校文渊阁本《四库全书》,为了行文方便,除特殊情况外不再胪列出处。这是在说此作是受到韩文的启发,意在和韩愈较艺,二文之高下留待读者评说。作者想在辞章和义理方面和韩愈争雄。如果对韩文不了解,此赋的意蕴可能难以理解透彻。崔敦礼的《留穷文》则反扬雄、韩愈之义,铺写五穷,即仁穷、义穷、礼穷、智穷、信穷,暗扣赵湘《迎富文》主旨,意在强调人有此五德,何穷之有!将二文之义又转深一层。区仕衡的《送穷文》之于扬雄《逐贫赋》,与王之望《留穷文》之于韩愈《送穷文》一样,都是通过故意模仿来和古人比试文华风采和胸襟见识。赋作对贫苦之状的模仿极其精彩,铺排更为具体深入,语势更为流畅自然,富于气势,节奏更为顿挫,内容上也更具生活感。如果是与作者境遇相仿,或者是同时代的人阅读此篇,较之韩文,感染力和现实感更为强烈。与此相类似的俞得邻的《斥穷赋》则是责问人世的不公道,这就使扬雄、韩愈二文讨论的问题转向人生困惑的角度。
可见,宋赋的滑稽描写在转相祖述的过程中,源文本的语词、主题、结构等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充实和发展,辞章方面也不断得到提升,内蕴得到充分挖掘,宋人往往强调“无一字无来处”,对宋赋滑稽艺术的理解,若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很难理解其中之况味。
宋赋滑稽描写的互文性流变,是一个不断增饰、变形的过程,有时候其对源文本的扩大、升华,呈现出意义上的“增值”特点。
苏轼的《后杞菊赋》仿陆龟蒙的《杞菊赋》,二赋均表现贫而餐菊的洒脱人生,苏轼将此境界表达得相当传神:“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为贫,何者为富?何者为美?何者为陋?……吾方以杞为粮,以菊为糗。春食苗,夏食叶,秋食花而冬食根,庶几乎西河南阳之寿。”几个问句咄咄逼人,引发读者对齐物达观的深入思考,暗示膏粱肥腴与糙粝藿食没有本质区别,然后以轻快的语调写出餐杞菊不仅可以果腹,而且可以助寿。其中流露的自解自嘲情绪令人发噱,这比源文本只是阐述杞菊助寿要深刻得多。如果再联系苏赋的上文,其调侃用意便豁然开朗:“吁嗟先生,谁使汝坐堂上称大守?前宾客之造请,后椽属之趋走。朝衙迭午,夕坐过酋。曾杯酒之不设,揽草木以诳口。对案颦蹙,举箸噎呕。昔阴将军设麦饭与葱叶,井丹推去而不嗅。怪先生之眷眷,岂故山之无有?”身为太守而食藿充饥,未免太夸张了,其实,这是在拿新党执政减少官员薪俸的举措来调侃。作者想说的是,王安石是要让官员们都成餐菊延寿的世外高人!张耒的《杞菊赋》大肆美化苏轼的餐菊之举,借此彰显自己作为新法对立面的政治身份,作者在赋中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新法的反对者,都是像苏轼这样的君子,都具有像屈原那样的餐菊饮露的高洁品格。思想意蕴比苏轼更进一层。张栻的《后杞菊赋》则是借苏轼餐菊的形象来表现物我相得的自适心态,其思想深度超过前两篇,文章把苏轼的自解自嘲提升到一个哲理的高度,这只有在阅读前两篇的基础上才能够体会出来。应该说,滑稽的“增值”现象在宋赋中是相当普遍的,这正是其文学追求“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创作倾向在辞赋中的表现之一。
宋赋滑稽描写的互文性有时不仅立足于某一篇或几篇源文本,而是对于各种文学作品共同表现的某类意象的融会贯通与铺张排比。它的互文是针对某类内容或某类思想的。
薛季宣的《七届》铺写七种人生追求,第一部分放笔铺排饮食和美女的诱惑性。女色描写在楚辞《招魂》中就已露端倪,继宋玉《登徒子好色赋》后,这类描写在舞蹈、音乐、神女等辞赋中逐渐泛滥,甚至像张衡的《南都赋》等都邑大赋也时或有之。对饮食的描写,枚乘《七发》较早涉足,以后在都邑赋和“七”等辞赋中几成俗套。枚乘的《七发》集食色描写之大成,指出沉溺于美食和美色的享乐生活是“甘餐毒药、戏猛兽之爪牙”,薛季宣的描写要比枚乘详细得多,他显然不是单单对《七发》的模仿,而是针对前代一系列关于饮食男女的作品的,在几成俗套的滑稽描写中,作者希望自己的文笔更具辞章方面的审美性,更具哲理的深度,更吸引人。赋中点题道:“瞽哉!燕安枕藉,吾知其斧斤酖毒也,不知其它。”这和《七发》的“伐性之斧”之说遥相呼应,但是它又不单单是绍续枚乘之说,女色伤身是古人共识,《庄子·达生》曰:“人之所畏者,袵席之上,饮食之间,而不知为戒者,祸也。”[2](P117)汉严遵《座右铭》:“淫戏者,殚家之堑。”[3](P360)嵇康的《养生论》曰:“唯五谷是见,声色是耽,目惑玄黄,耳务淫哇,滋味煎其府脏,醴醪鬻其肠胃,香芳腐其骨髓,喜怒悖其正气,思虑销其精神,哀乐殃其平粹。”[4](P151)乃至于孟郊的《偶作》还说:“利剑不可近,美人不可亲。 利剑近伤手,美人近伤身。 道险不在广,十步能摧轮。情爱不在多,一夕能伤神。”显然,薛季宣的描写以及观点是对一系列作品和见解的总括。范成大的《问天医赋》对于这一话语表述,其互文性的表达更具概括性:“人之多疾,自取自探。不一其凡,大略有三。其一者心根泄机,命门丧阻。明消精散,形弊神苦。掷温玉以畀火,奉甘餐而戏虎。阴惑阳而化蜮,风落山而成蛊。若是者得于晦淫,命曰伐性之斧。”*“风落山”,《周易·蛊卦》象曰:“山下有风,蛊。”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 3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左传·昭公元年》云:“女惑男,风落山,谓之蛊。”载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 201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作者之所以没有详细阐述食色害人,是基于对前代类似文本的互文性概括,暗示读者去联想类似的作品。林半千的《遣惰文》沿着薛季宣的路子,融饮食与美色于一体,他将之概括为人的惰性,该赋模仿屈原《招魂》的结构,把灵魂的流荡忘返置换为心志的懈怠低迷,内容上则是如薛季宣赋那样,立足于对饮食男女的描写。

二、游走于雅俗之间的诙谐幽默
关于宋代文学的雅俗之辩,古今论述汗牛充栋,由于雅与俗是一对具有感性色彩的伸缩性很强的概念,要犁然分明并非易事。宋代士大夫是一个享有政治特权的文化精英阶层,他们对自己的身份和文化具有高度自觉的认同意识。这种身份认同不仅表现在他们具有较之前代任何时期的文人更为强烈的政治抱负和使命感,更表现在他们对低俗、庸俗情调的警惕、抵制与排斥。他们希望通过超越性的思维和心境来理解人生,感受生活,拒绝平庸浅薄的趣味,他们追求不累于俗、不受制于外物束缚的精神愉悦和贯通历史与知识的远见卓识,以达观超然的态度和深刻的哲思来化解生活中的不快、不幸,在自嘲自讽中获得精神的升华。他们眼中的“俗”,不仅包括平庸的情调,也包括作为这种情调的载体、形式,以及庸常生活中不具有高雅气质的琐细微末之物态。他们对于无处不在、触目可及的“俗”,大多采取以俗为雅、化俗趋雅的“提升”的态度。
滑稽艺术从一开始就与世俗有着亲缘关系,低俗、浅俗、媚俗甚至是滑稽的重要构成元素。对于滑稽的世俗特色,宋人在辞赋创作中同样以提升的态度来面对,而非拒斥。游走于雅与俗之间的宋赋,在庄严与轻佻、高雅与平庸的巨大反差中凸显着滑稽艺术的幽默诙谐特色。
生活中的琐细之物、庸常之事,是咏物赋的表现内容之一,其潜在的滑稽因素颇为赋家看重。宋人用流畅优美的文辞来铺写这些俗物俗事,使其脱离鄙俚浅陋气息,以文雅写庸俗,同时,这类作品惯常的粗俗噱笑被提升为超越凡俗的高雅趣味和高妙道理,以雅趣化俗情,使其与士大夫阶层的思想境界和审美好尚相契合。
例如,蛙的可憎面目和其鸣叫的聒噪吵闹使它成为俳谐文学热衷表现的对象。张耒的《鸣蛙赋》紧扣悲和乐,组织一连串的比喻,描摹蛙鸣执著、持久、放肆、呕哑嘲哳的特点,作者在结尾加了这样的一段:“尔其困于泥潦,失其所处而悲;又若夫旱暵既久,得其所处而乐也。”蛙的絮聒不已,是缘于得时跋扈抑或失时焦灼呢?还是缘于得意忘形而炫耀抑或穷困潦倒而呼天抢地呢?这就在蛙鸣与文人对人生的思考之间建立起若隐若现的联系,得势者的炫耀鸣唱不就像蛙鸣那样惹人讨嫌吗?困厄者的悲叹号呼不就像蛙鸣那样焦灼悲酸吗?顺着这个角度去体会,作者对蛙鸣的描写不仅仅是引人发噱,更有关注人生、默然心会的苦涩一笑。结句的一点,使具有世俗色彩的滑稽描写具有了一种符合士大夫雅趣的深远韵味。李新的《蛙赋》显然受到张耒的启发,赋以与蛙的对话结构全文,对于自己的呼号不已,作为居士的蛙是这样回答的:“兴《考槃》之歌,赋《衡门》之诗,引《泽畔》之吟,咏《北门》之薇。士不得志,故嗟叹之。鸟鸣常山,孤雉朝飞;杜宇亡国,秋猿号儿。物不得平,哀也无期。”蛙的鸣叫与有志不得伸的屈原等贤人同调,蛙鸣与贤人失志的高雅主题联系在了一起。南宋理学家杨简的《蛙乐赋》循着这一思路,以相当优美的比拟来描摹蛙鸣的悦耳动听,说蛙鸣如黄钟大吕振奋人心,那声音的特点是:“其莹然之鉴,澄然之渊。至动矣而静,至繁矣而不喧。是音也可闻而不可听,可以默识而不可口宣。”单调的聒噪居然有如此悠远的美韵,给人些许难以理解之感。作者解释道:“孔圣遇之而忘齐国之肉味,黄帝得之而大张于洞庭之原。胡为乎独不见省于横目之士,至憎而为烦?甚以为冤。冤矣乎,冤矣乎!”原来蛙鸣是天地之间天理或道统流传之一个环节*杨简此赋中蛙之鸣,与道学家鸣道之鸣同类。如真德秀的这段话可以作为此赋的一个注脚:“汉西都文章最盛,至有唐为尤盛,然其发挥理义、有补世教者,董仲舒氏、韩愈氏而止尔。国朝文治猬兴,欧、王、曾、苏以大手笔追还古作,高处不减二子;至濂洛诸先生出,虽非有意为文,而片言只辞,贯综至理。若《太极》、《西铭》等作,直与六经相出入,又非董、韩之可匹矣。然则文章在汉唐未足言盛,至我朝乃为盛尔。忠肃彭公以濂洛为师者也,故见诸著述,大抵鸣道之文,而非复文人之文。”参见真德秀:《跋彭忠肃文集》,载《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三十六,上海,上海书店,1989。,大乐与天地同和,只要人们进入仁者境界,难听的蛙鸣可以成为天下最动听的音乐。蛙鸣之为凡俗讨厌,与当时道学家的“鸣道”所遭受的世人非议极其相似,这种巧妙的构思和深邃的思致是非寻常人能够行之笔端的。刘克庄的一篇描写蛙鸣的“失题”之作可能是出于对杨简等以蛙鸣写鸣道的不满,赋中对蛙鸣近乎谩骂式的宣泄,其背后隐含的士大夫文人思想争锋的意气用事,合而读之,令人发噱。
可见,宋代的赋家立足于自己审美立场来感受、体会琐细之物,在俗之物象和雅之情趣之间,巧妙地建立起联系。李刚的《药杵赋》和刘子翚的《闻药杵赋》能把捣药的单调声响描绘得如音乐般动听,苏轼的《菜羮赋》、陈与义的《玉延赋》能把野菜、山药描写成天下致味,等等,都是通过俗物俗事来感发文人士大夫雅怀的佳作。
宋人还喜欢用戏仿来展现辞赋的滑稽特色,他们对传统成规存心犯其窠臼,以游戏心态出其窠臼,用惯常的辞赋中雅文学的表现手段来写琐细之物事,雅俗的反差产生诙谐效果。
例如,高似孙的两篇描写水仙花的赋表现的是面对水仙花产生的求女幻觉。从楚辞以来文人雅士每每以铺写求女来寄托人生追求、政治抱负,高似孙则把这一传统题材用来写水仙花,他的《水仙花前赋》仿《九歌》,《水仙花后赋》仿曹植《洛神赋》,其感情之一往情深与文辞之飘逸清倩,深得骚人之旨。如果我们意识到这是作者表达对水仙花近乎痴迷的由爱恋入玄想,由玄想入幻境,是否会忍俊不禁?赋中有问难一体,主要通过责难和应答来表现文人们对各种人生道路的思考与探索。这种赋体与辞赋中抒发政治命运的“士不遇”赋同一机杼。洪咨夔的《老圃赋》以老农与小儿的对话结构全文,暗示了其与问难体的联系,不过,全文探讨的是“汝亦知夫世有遇不遇之蔬乎”,以此领起全篇,对各种蔬菜命运的铺写用了近六百字的篇幅,一气流贯,节奏顿挫,类似说唱艺术的“贯口”,读来令人解颐。喻良能的《古甕赋》模仿《天问》结构模式对着耕田所得之古甕,也像《天问》那般困惑发问:“噫嘻悲夫!岂秋草朔风,闺人愁心,思寄征衣,欲捣寒碪,藉尔清响,振其远音,岁久俱废,塊然独瘖者欤?岂天高气清,落月横生,幽人妙兴,将调素琴,假尔逸韵,相其悲吟。人琴云亡,草蔓见侵者欤?又其白刃纵横,窜付长林,埋金韬玉,规人莫寻,至宝忽逝,独留丝深者欤?抑或却立炼形,鹤驾鸾骖,窖其丹砂,灵泥是缄,五色羽化,此焉墆淫者欤?”作者设想了古甕的四种来历:或助闺人捣衣振响,或助幽人弹琴扬声;或战乱以藏宝,或方士以窖丹。面对古甕的这段精神游历,亦庄亦谐,引发读者对人生的种种思索。
宋赋滑稽艺术的戏仿,其原结构模式所暗示的思想内容在拟作中仍然在起作用,这就使得滑稽铺写具有了契合文人趣味的意蕴。
拟体俳谐文是滑稽文学的大宗之一,通过对严肃文体,比如公文、祈祷文、吊问文等的戏仿,营造出消解庄严的戏谑效果。这类调笑文字有时虽不以“赋”命篇,其实有的形制就是赋体,属于杂赋类。宋赋中这类文体创作不在少数,而且多能在传统戏谑的基础上展现雅致情怀,这是宋人超越前代俳谐文的可贵之处。表文是陈述性的上行文章,陈造的《表盗文》是写给光顾自己家的蟊贼的。之所以以“表”的形式向盗陈述,可能是由于家贫,向空手而归的盗贼聊表歉意吧。赋以惊魂甫定的妻子之絮叨开篇,尽管家人受到了惊吓,可是由于一贫如洗,盗贼多次光顾都无功而返。在此滑稽场景的基础上作者大发感慨:不仅慢藏诲盗,高墉大屋也是累人之外物,欲望越多,痛苦也越多,对利禄无止境的贪欲只能换来无尽的烦恼。这种达观齐物的论调,出自作者这样的面对蟊贼都赧颜的贫困者之口,是有感而发呢,还是自我安慰、自我调侃呢,诙谐的笑谈中包含着深沉的苦涩。谕文,是告晓类文书,一般用于上对下。戴埴的《谕鹤文》这样晓谕与鸡争食而受伤的鹤:“饥不啄腐鼠,谓在田也;渴不饮盗泉,谓在野也。翮短尾雕,混迹鸡群,郁郁豢养,壮志未伸,又非颉颃烟霞、轩翥林汀也。”短短几句,哀其不争的感怀跃然纸上。姚镕的《谕白蚁文》写白蚁“性具五常”,以人间生活来比附白蚁的穴居,暗讽人间生活如白蚁一样蝇营狗苟。作品通过与白蚁的对比,把人类生活的一切价值观念都祛魅了,使神圣庄严回归平凡庸常,喜剧意味蕴含其中,也符合士大夫阶层普遍的对历史发展的超越性认识。 其他如陈淳的《谕蚁文》也是类似的作品。移文是官府间交往的平行文体。黄庭坚的《跛奚移文》仿王褒的《僮约》而踵事增华,并依照孟子不能与不为之辨立论,阐述量才而用的道理,赋中铺排种种奴仆庶务,流畅而整齐的韵语加强了诙谐效果。林希逸的《金天移文》也是一篇滑稽佳作。赋中写一位友人丧偶后自号“在家僧”,却写了好多淫词艳曲,因而招来了佛国的移文谴责。赋作铺排了朋友丧偶后的寂寞和难以自持、心念佳人的躁动。让人大噱的是,这位朋友在寂寞难耐之际,情不自禁把内心的冲动寄之于翰墨,作下了绮语恶业。这篇赋在立意和手法上基本上承袭了徐陵的《答周处士书》。徐陵在答复周弘让书中说:“承归来天目,得肆闲居。差有弄玉之俱仙,非无孟光之同隐。优游俯仰,极素女之经文;升降盈虚,尽轩皇之图艺。虽复考盘在阿,不为独宿。讵劳金液,唯饮玉泉。比夫煮石纷纭,终年不烂,烧丹辛苦,至老方成。及其得道冥真,何劳逸之相悬也!”[5](P3450)字面上写周处士修行得法,劳逸相悬,实际暗指处士的修行其实是打着房中修炼的幌子在行纵欲之实。此赋把这种欲望与掩饰的窘态描绘得更为具体、传神。如果此赋的内涵仅止于此,那也不过是一篇一般意义上的谑噱之作,其令人深思的是,西天(金天)那个极乐世界面对人们正常的情爱要求,竟然如此不堪一击,可见,正常的情爱才是真正的极乐世界!其他如宋白的《三山移文》、杨杰的《南山移文》、冉木的《古富乐山移文》等,也是引人入胜的佳作。
宋赋中,祭吊祈祷之文也被拿来戏谑、调侃。晁说之的《祭麴神文》敬告麴神自己将断酒,原因是贫病无以自养,作者描绘贫病偃蹇、妻侮女嗔的窘象如闻其声、如睹其形、如味其神,在自嘲中寄寓着世态炎凉。告文是祭文的一种。周紫芝的《告巨木文》是为移去宅前巨木而敬告巨木之灵,希望取得谅解,文章列举巨木给自己和家人的生活造成的种种不便,令人忍俊不禁。其实,作者想表达的是,自己不得不在巨木笼罩下的弊庐安身,是由于家贫,没有其他安身之所,在作者张皇其事、大动干戈的伐树描写中,生活的酸楚流注其中。其他如周邦彦的《祷神文》、谢逸的《吊槁杉文》、薛季宣的《吊遗骴文》、张榘的《吊丛塚文》、周文璞的《吊清溪姑词》等,多寄寓着深沉的人生感慨,诙谐色彩相对淡薄。
三、意在言外、含蓄不尽的韵味
宋代文学的一个显著特征是追求情理相得的理趣。文学创作中理趣的获得,缘于对具体物象的哲理关照与情感体验之相谐相融,这需要作者具有丰富的知识储备、深厚的胸襟学力和敏锐的感知能力。宋代文人兼具学者的特殊身份为此准备了必要的条件。铺采摛文是辞赋的重要文体特征,这就使得辞赋表达容易言谈务尽,难以做到像诗词那样的韵味无穷。不过,宋代一些文人却能够很好地使骋辞炫学与含蓄不尽取得一致,创作出隽永优美的辞赋佳作。幽默是滑稽的重要组成要素,建立在含蓄、机智、风趣、顿悟等基础上的幽默,与理趣有非常大的一致性。宋赋创作对理趣的追求,有时候会演化为幽默,成为其滑稽艺术的重要内容。一些宋赋能够在俳谐描写中以情观物,以理释情,融情入理,情理相谐,实现超越物象噱笑层次的幽默效果和情理感悟,让人在解颐之余产生感触与遐想。
宋赋中的滑稽,多能从小事小物中引申、暗示深刻的哲理和丰富的人生况味。苏轼的《老饕赋》以优美的辞藻描绘食物之精美与女色之动人,似乎落入辞赋滑稽描写之俗套,结尾处笔锋陡转:“美人告去,已而云散,先生方兀然而禅逃。响松风于蟹眼,浮雪花于兔毫。先生一笑而起,渺海阔而天高。”原来这场食色盛宴是黄粱一梦!此赋创作于苏轼落魄黄州之时,当时的苏轼生活困顿,蔬粝充腹,作这样的美梦也在情理之中,将之写入赋中,展现自己之馋痨,已经令人发噱,而由此生发出超越食色的理念,更令人绝倒。作者郑重其事地告诉人们,人世间的蝇营狗苟、荣华富贵何尝离得了食色二字,不也是大梦一场吗!杜甫《八仙歌》诗:“苏晋长斋绣佛前,醉中往往爱逃禅。”苏轼梦中一醉亦能逃禅彻悟。引人深思的是,作者是真的逃禅了呢,还是贫困生活中的自我排遣呢,实在是难以言表,任由读者思量。姚勉的《战蚁赋》写的是大雨将至,蚁群为争夺高地厮杀的场面,属于俳谐文学当中的寓言类。作者以人间争斗的视角来审视蚁群的厮杀,甚至还有献俘斩馘告于成功的典礼,亦庄亦谐,引人深思。结尾处,作者点睛道:“一寓目而观戏,三重为之太息。天下之区区,何以异于蚁穴之微;人心之好竞,何以异于众蚁之智!……驱万姓于锋镝,争一战之雌雄。竭民膏于中国,要边功于外夷。”这“三重太息”是:感叹人间的蜗角之争;感叹蚁群竟然如人类这样残酷,从人到微虫,无不做着毫无意义的争斗,其根源就是“好竞”,就是争名夺利的欲望使然;感叹边将邀功,轻启边衅,置黎民于锋刃之端,这与蚁群争斗何异!其他如苏轼的《黠鼠赋》、宋庠的《蚕说》、宋祁的《感虭蟧赋》、毛滂的《送鹤文》、陈与义的《放鱼赋》、陈藻的《桔槔赋》都是类似的优秀作品。


四、深挚而强烈的现实关怀
司马迁写《滑稽列传》的着眼点是因为其“谈言微中,亦可以解纷”,也就是说,滑稽之言具有一定的政治价值。之后,滑稽艺术忧时讽世、伤时骂世的特色得到充分发展。宋代文人士大夫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他们的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非常浓厚,普遍具有深挚而强烈的现实关怀。这种现实关怀,既表现在对现实政治的批判精神,也表现在整饬世道人心的道德自觉。宋赋继承滑稽艺术的这种淑世情怀,并将其发扬光大。
宋代台谏制度发达,士大夫阶层普遍热衷于议论政治,一些政治举措往往引起朝野上下群议纷然。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因修建景灵西宫,徽宗命人采太湖石纲运京师。程俱的《采石赋》就此事而发。赋中以三老与吏争辩朝廷采石伤民结构全文。赋中欲扬先抑,首先强调当今皇上非古代那些大兴土木、穷奢极欲的败德之君,明扬暗贬,欲盖弥彰。吏从五个方面为朝廷辩解,其一曰:“西有未夷之羌,北有久骄之虏,顾蹀血之未艾,乍游魂而送死。方将不顿一戈,不驰一羽,殄丑类于烟埃,瞰幽荒于掌股,庶黄石之斯在,傥素书之可遇。”吏的狡辩偷换了概念,他把授兵书的黄石公和皇家采石故意混淆了。他指出,当今北有契丹,西有党项,天下不靖,若能得黄石公之奇书,若当年辅佐汉高祖的张良那样,岂不免黎庶于锋镝,静边尘于须臾。其二指出皇上采石是为了铸斩佞之剑,既斩边廷怀逆之酋,也斩朝中邪佞之臣,如此,则天地清明,盛世指日可待。为了增强说服力,他还引经据典,指出采石是当今天子在效仿周穆王采石铸剑的圣举,而非步武魏明帝之修景福殿的败度也。其三写帝王采石是在鞭石求雨,以泽惠天下。其四写皇帝采石是为了施行嘉石列坐的古制,严明法制。其五指出采石是为了效仿大禹之巡行天下,以广视听,体察民情。全赋强调夺理,引申归谬,正话反说,尽显采石的荒谬。作品对今上徽宗穷奢极欲、不恤国事的讽刺力度是空前的,赋的结尾,三老的一句:“圣治盖至此乎!”更是充满了挖苦之意。

较之苍蝇,蚊虫利觜害人,是恶人之类。虞允文的《诛蚊赋》把官场比作是群蚊乱飞的蚊阵:“爰有黍民,出于庐霍。呼朋引俦,讶雷车之殷殷;填空蔽野,疑云阵之漠漠。利觜逾麦芒之纤,狭翅过春冰之薄。其赋形而至眇,其为害而甚博。”苍蝇只是令人可厌,而蚊虫,则是让人可怕。南宋初期,尤其是秦桧专权的时候,文丐奔竞,恶人充斥朝堂,动辄兴起事端,遥诼忠良,朝野上下人人自危,这与蚊阵何其相似乃尔。攀附权贵,攻击善类是当时官场的风气,和之前的士大夫相比,高宗朝的士人更没有操守,人格更为低劣猥琐。虞允文此赋,是一篇声讨当时官场的檄文。之后,王迈的《蚊赋》、姚勉的《嫉蚊赋》等都是按着这个思路来声讨恶人的作品。
南宋官场上因循苟且之风盛行,中期以后,王朝更是如燕巢危幕般迁延度日,当时辞赋有感而发,出现了几篇描写猫的滑稽之作。李纲的《蓄猫说》借猫喻人,希望朝臣尽职尽责、戮力王室。洪适从李纲赋的反面立意,作《弃猫文》,以讥刺庸官。作者感慨道:“汝岂不见国家之设官乎?宠以高位,畀以厚禄,相图治于朝端,将折击于边服……凡厥庶僚,各厥其局。一有旷瘝,旋跬屏逐。人尚如此,况于微畜。”两赋相反相成,对官员的尸位素餐深感忧虑。刘克庄的《诘猫赋》与上两赋相类而更有故事性。赋写因鼠害而储猫,结果又遭来猫灾。文中写猫在捕了几只鼠后就依功自恃,贪图享受:“俄伤饱而恋暖兮,复嗜寝而达晨。信半质之难矫兮,况驴技之已陈。彼瞷尔兮柔且仁,汝视彼兮狎不嗔。”赋作对猫鼠狎昵的描写绘声绘色,暗示邪臣嬖女的祸国行径。
当然,宋赋的滑稽描写对现实的关注是多方面的,虞允文的《信乌赋》鞭挞世俗的浅陋见识,曾丰的《蠹书鱼赋》、刘克庄的《谴蠹鱼赋》对道学人士假托圣人、破碎经籍的行径表示了忧虑和愤慨,胡次焱的《嗟乎赋》对汲汲于科名的世风强烈谴责,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宋赋的诙谐中还有一些这样的作品,以道德卫士自居的赋家,从恪守道德戒律出发,激于义愤,言论偏执,对不入眼的物事横加指责,以迂腐冬烘消解风趣幽默,给人焚琴煮鹤、点金成铁之感,作品不期然而至的喜剧感来源于作者自身。
竹夫人又叫青奴,是一种柱形的竹制品。宋人喜竹席卧身,拥之以消暑。辞赋中喜以“夫人”“奴”戏称之,以取得媟亵噱笑的效果,如谢薖的《竹夫人赋》、洪适的《竹奴文》,就是这种幽默风趣的作品。其中谢薖的《竹夫人赋》于低俗中寓清新,尤为动人。但是金盈之的《竹奴文》则是另一幅面孔:“非有《鹊巢》之德,《采苹》之职,曷为而受夫人之呼?人之称汝,既以重诬,汝辄披襟,于汝安乎?夫金炯有清明之鉴,而袭彻侯之爵;毛颖以翰墨之勋,而掇中书之除。汝非有功有德,可与二君子为徒。今黜汝之僭号,而谓汝为竹奴。盍安名而谨分,顺主人之所驱。无沮怍以觖望,遂衔冤归憾于吾。”作者对小小的竹夫人也要辨名分,别尊卑,示等威,如果这也是幽默,那么这种幽默实在是太沉重笨拙了。赋中折射出的卫道热情和浩然正气,使得这一题材蕴含的谐趣荡然无存。目前所见的宋代近二十余篇关于梅花的赋,大多把梅花与神女、美女相比附,以摹状其高洁俊逸之姿。唯独姚勉的《梅花赋》把梅花写成君子,写成一位男性,一位恪守道德的男性:“桃李华而近浮,松柏质而少文。未若斯梅之为物,类于君子之为人。今夫异离木而独秀,冠群芳而首春,是即君子之材。拔众萃而莫伦,立清标而可即,正玉色以无媚,是即君子之容。羌既温而且厉,寒风怒声,悄无落英,严霜积雪,敢与争洁,君子之节也。瑶阶玉堂,不增其芳,竹篱茅舍,不减其香,君子之常也。在物为梅花,在人为君子。皎茵璧之连接,莹壸冰其表里。既物我之通称,又焉得舍此而取彼。”从为人、禀赋、仪容、节操、坚守等几个方面把梅花和君子道德相比附,梅花在文学创作中凝固而成的摇曳多姿的美丽形象顿时消失。当然,君子也可以是女性,但是在文学世界里,君子的男性品格是早已定型了的。姚勉此赋显然不是以调笑诙谐为目的,但是其不期然而至的喜剧性令人绝倒。
宋赋的滑稽艺术,是建立在融会贯通前人作品和历史经验基础上的以才运学,它立足诙谐幽默而契合士大夫阶层的审美好尚,它追求情理相谐的理趣而具有摇曳生姿之美韵,它包含着深沉的淑世精神,忧时讽世。这些特点是宋赋对滑稽艺术的一次品质提升,使它远离俗文学窠臼而登堂入室,与士大夫阶层的“雅”文学靠拢、融合,这是宋赋的滑稽艺术在辞赋发展史上最显著的表征。
[1] 司马迁:《史记·滑稽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王先谦:《庄子集解》(《诸子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59。
[3] 严可均辑:《全汉文》,卷四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58。
[4] 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5] 严可均辑:《全陈文》卷九,北京,中华书局,1958。
(责任编辑 张 静)
On Comical Literary Technique of Song Fu
LIU Pei
(The Editorial Department ofLiterature,HistoryandPhilosophy,Shandong University,Jinan,Shandong 250100)
It is rather obvious that there is some inner impulse to entertain the author himself and other people in Cifu creation.Song Fu also attached much importance to comical description.The culture of the Song Dynasty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deep cultivation,rational interest and noble moral.These three constitute the basic elements of the comical creation of Song Fu.Most scholar-bureaucrats in the Song Dynasty were both scholars and literati,and therefore their works always revealed their academic skills.It is highly desirable when we study Song Fu’s comical cre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textuality.Scholar-bureaucrats in the Song Dynasty also adopted positive attitude rather than repulsion to mundane trait.Wandering between elegance and vulgarity,Song Fu made humorous feature of comical literary technique prominent with enormous contrasts between solemnity and frivolity,elegant and mediocrity.Song Fu could observe objects through feelings,interpret feelings through reason,merge feelings and reason together and balance them well,thus transcending the comicality of objects,arousing imagination and striking a chord in the hearts of the readers after a relaxation from reading Song Fu.Scholar-bureaucrats in Song Dynasty had critical spirits of real politik and conscientious moralities to the manners and morals of the times.Song Fu inherited the emotion of saving society from comical literary technique,and carried it forward.
Song Dynasty;Cifu;comical;intertextuality;elegance and vulgarity;philosophic flavor;morality and feelings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宋代辞赋的社会文化学研究”(12BZW037);山东大学自主创新基金重点项目“宋赋整理及其文史哲学的交叉研究”(12110070612064)
刘培:山东大学《文史哲》编辑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 济南 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