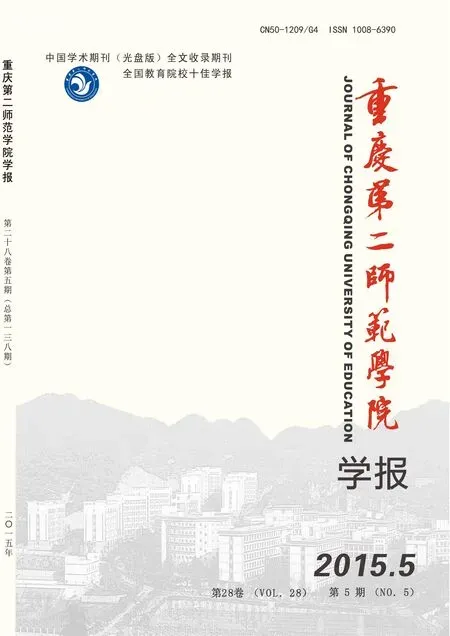试论碑刻文献整理中的文本问题——以《北岳安天王庙碑》校理为例
试论碑刻文献整理中的文本问题——以《北岳安天王庙碑》校理为例
何山
(西南大学 汉语言文献研究所、出土文献综合研究中心,重庆 400715)
摘要:全面调查统计和对比分析《北岳安天王庙碑》四种碑文文本得出,摹录本较可靠,撰作本中的刻本和排印本次之,两者均可选作校勘底本。重刻本、转录本除转录时的笔误、主观臆断等人为造成的问题外,录文依据多为二次文献,真实性较差,应当谨慎对待和使用这类文本,在有其他文本的情况下,一般不宜选为底本,可重点发挥其在碑刻文献整理校勘中的参考作用。
关键词:碑刻文献校理;文本选择;北岳安天王庙碑
收稿日期:2015-04-13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2YBWX088);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1YJC870007);中央高校基本科研项目(SWU1309208)
作者简介:何山(1973-),男,四川仪陇人,助理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碑刻文献整理与研究。
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5)05-0033-04
碑刻文献作为出土文献的重要类别,对于传承悠久的华夏文明、保存优秀的民族遗产、存储厚重的精神财富意义非凡,对于认识和研究古代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民族宗教、科技教育、民风民俗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自宋代以来,整理、纂录历代碑刻文献的著作陆续出现。纵观包括碑刻在内的各种诗文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同著作中同一篇碑文的释录依据往往各不相同,或自碑拓摹录,或转录他文。辑录方式有排印,也有抄录。核之碑刻原石或拓片,同一碑铭的不同文本常常存在或多或少的文字差异,部分录文特别是辗转传抄的录文,其文字的阙脱、讹误等还相当严重,极大地影响到材料的有效利用。这充分说明录文质量与碑刻文本的选择密切相关。开展碑刻文献研究,科学整理研究材料是基础和前提,而选择可靠而精善的碑铭文本作底本,是确保校勘整理工作取得实效的关键。历代碑刻成果存在哪些类型的著录文本,怎样确定基本可靠的校勘底本,成为碑刻材料整理面临的关键问题。下面以《北岳安天王庙碑》释文校理为例,具体探讨碑刻文献校理中的文本选择问题,祈请方家指正。
曲阳北岳庙始建于北魏,千余年来因各种原因屡毁屡建。较近的一次发生在北宋时期,因辽宋战争该庙被契丹人纵火焚毁,再次遭受劫难。宋淳化二年(公元991年)朝廷重新修缮,并命左司谏、知制诰王禹偁撰写《大宋重修北岳安天王庙碑铭并序》。碑系奉敕而建,现立于河北省曲阳县北岳庙内,通高5.12米,宽1.70米,厚0.45米。碑文行书,两千余字,书法潇洒俊拔。河北省古代建筑保护研究所藏有碑石整拓,《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下简称《北图汇编》)[1]37册P197著录该碑拓本,题名为《北岳安天王庙碑》(以下简称《庙碑》)。碑文记述北岳庙的兴衰,重修后的庄严雄伟,百姓祭祀,焕然神功,人神共志等,其内容对研究北岳庙历史和宋代宗教文化等有重要价值。由于北岳庙不平凡的经历,撰文者王禹偁又是北宋重臣、著名文学家,因此清代以来的重要著录书多收录该碑文。根据各著录书文字迻录方式及其与拓本内容的吻合程度,其著录文本可大致分为四类:摹写(刻)本、重刻本、转录本和撰作本,四种文本各具特点,而文字各有差异,有的是几种文本共同的问题,有的则是一种文本独立的判断。现以拓本为依据,从文献学、碑刻学和语言文字学等角度分类简析诸本文字差异并择要校勘,从而还原碑文真实面貌,澄清北岳庙重建史实,深入理解文本内涵,全面评估各文本的价值和不足,为文献材料的有效利用、碑刻著录整理中文本的科学选择、北岳庙及曲阳地区相关文史研究等提供参考和借鉴。
一、摹录本
据拓本文字原样摹录,有的写,有的刻,基本保持碑面文字原貌,由此产生的著录文本称为摹录本,具体可分为摹写本和摹刻本两类。前者如宋洪适《隶释》,每篇碑文依隶字构形以楷书笔画转写而成;后者如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下简称《八琼室》)、王昶《金石萃编》、陆耀遹《金石续编》等。摹写(刻)被学者们称为碑刻文献最佳著录方式之一,其文本优势在于最大限度地保持文献真实性,除重点反映文字原样外,拓本空格、行款等也尽量呈现,有的甚至摹写(刻)碑头、画像等。尽管如此,《八琼室》[2]卷86、《金石续编》[3] 3285卷13摹录《庙碑》碑文时仍存有少许问题,具体包括:
(一)7处未按拓本文字原形摹刻,而录作相应的异体字。如:拓本“汙”《八琼室》卷86录作“污”、“佇”录作“伫”等。
(二)1处脱漏。即文句“定州诸军事”中,《金石续编》卷13漏录其“事”字。
(三)两处误录。即“雕题儋耳,骈罗入正会之图;僸佅兜离,沸渭杂宫悬之曲”文句中,拓本“入”《八琼室》卷86误作“人”,“离”误作“罗”。从句式看,“入”与下句“杂”相对,皆为动词;从文义看,僸佅、兜离均为我国古代少数民族音乐名称,与其后“宫悬之曲”意思对应,如作“兜罗”,则与句意不吻合。故《八琼室》录文误。
摹录者书刻过程中伴有随意改写、疏忽大意等情形,加上字形变异和行草书字用笔的放纵牵连,增加了准确辨识文字的难度,转录错误难以避免,给摹录文本留下些许遗憾。
二、重刻本
以隶楷书字(多为通行繁体字)重新编辑刊刻碑文内容,体现新的字体风格和时代特征,这种经人为另行编排刊印的碑刻文本称为重刻本。其录文依据未严格限定,或为碑拓,或为其他著录文本。如《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山川典》[4]18册P22292(下简称《集成》)所录碑文就属重刻本,是书卷42著录《庙碑》碑文,经与碑拓比勘,有32处与拓本不合,说明重刻文本与原碑文字有一定差异。
(一)误录或改录拓本文字,共13处。如:“臣闻元气肧浑”句中,拓本“浑”《集成》卷42录作“胎”。碑文“肧”同“胚”,胚浑为混沌之义,而胚胎比喻事物的开始或起源,比较而言,碑拓“胚浑”更切合下句“结而为山岳”所表文义,《集成》改录非。又如“黄门贵人,鸠工而蒇事”一句,意指黄门贵人聚集工匠完成北岳庙的重建,与下文“门阙有翼,阶陛斯隆”一脉相承。碑拓“蒇”《集成》录作“董”,则有违碑文所表之意,《集成》改录不妥。其他如“冻”误作“扺”、“穹”误作“空”、“拳”误作“卷”、“侍”误作“祠”、“匈奴”改作“天骄”等。其根源乃误认形近字、误解文义等所致。
(二)录作碑拓异文,包括使用通假字、异体字等,共17处。如:“当暑操扇,则轸下狱之非辜”,拓本“操”《集成》刻作“掺”。“掺”为“操”之异体,汉碑即有出现,《隶释·汉议郎元宾碑》:“君生也,即有殊摻。”“掺”同“操”,操守。再如:“何以赠之兮赤绋斯皇,何以处之兮峻宇雕墙。”拓本“绋”《集成》录作“芾”,两字应为通假关系。
(三)文字误衍,共1处。如:“于是戒尸祝”,《集成》录文“于是”后衍“乎”字。
(四)文句严重不合,共1处。即拓本“革彼豺狼之心,或鼓以雷霆,剿其犬羊之类”一句,《集成》录作“革其邪心,或声以雷霆,剿彼丑类”,文句表述有较大出入。根据碑拓、摹录本以及下文论及的撰作排印本所述内容、文字吻合情况可知,王禹偁写定碑文后,没有进行过修改或润饰。则此处文句差异当源自《集成》所据文本或系编者臆改,应以拓本为是。
本研究所参《集成》版本,为在迄今最通行、最精善的1934年版《集成》基础上重新影印而成的,其所录重修北岳庙的碑文却出现较多偏误,应归结于重刻时碑铭底本选择不够科学、文字识认不够准确、校勘不精等原因。
三、转录本
以通行简体或繁体楷书转录其他著录书中的碑文,一般还加上现代标点,原书所存问题一概如故,特别是与碑拓原文的差异传抄中亦因其旧,不作改动,这样的文本称为转录本。如《恒山志》[5]207《全宋文》[6] 8册P119等。标点本《恒山志》前言《标点说明》称:“这个标点本《恒山志》所依据的底本,是原浑源州州署藏版、乾隆癸未(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重镌本。”《全宋文》卷159收录《庙碑》碑文,文尾列出的校录依据包括《小畜集》卷16、《恒山志》利集、《古今图书集成·山川典》卷42、《金石续编》卷13,均为收录《庙碑》碑文的著录书,未见碑拓依据。将所转录的碑文与拓本文字比对,均存在较大差异,甚至出现明显失误。其中《恒山志》有38处与拓本不合,表现在:
(一)拓本文字录入错误,共18处。如:“潜”误作“攒”、“祅”误作“袄”、“諴”误作“诚”、“大定”误作“以安”、“迩”误作“建”、“韫”误作“袭”、“柟”误作“楠”、“渭”误作“谓”、“乌”误作“鸟”、“槛”误作“楹”、“忿”误作“志”、“巡”误作“临”等。
(二)文句不统一,共2处。即碑拓“置侍祝者九十人”句《恒山志》录作“置祷祝者九千人”;拓本“来诣祠宇”句《恒山志》录作“未诣祀宇”。
(三)文字误倒,共1处。即碑拓“至若掖廷椒房,俭约中度”中的“掖廷”,《恒山志》录作“廷掖”。
(四)以通假字、异体字等转录碑文,共17处。如“祇”作“祗”、“冱”作“沍”、“元元”作“原原”、“蒐”作“搜”、“徼”作“邀”等。
再稽核《全宋文》所录碑文,有28处与拓本不合,有的是与《恒山志》相同的问题,如“冱”作“沍”、“柟”误作“楠”等。有的则是新出错误,如拓本“叶”《全宋文》误作“系”、“国”误作“侯”、“亶”误作“禀”、“代”误作“燕”、“曲”误作“典”、“非”误作“罹”、“旰”误作“盰”、“咎”误作“启”、“楣”误作“楯”、“互”误作“玄”、“巚”误作“岳”等。也有相同碑拓文字而两书录文完全不同的情况,如:“原享惟馨之奠,永安不测之灵”一句中,拓本“原享”《恒山志》录作“愿飨”,《全宋文》录作“厚厚”。前者只是改变了词义的记录符号,仍可从字际字词关系的角度进行分析,“原”与“愿”、“享”与“飨”均可通假;后者则纯属误录。
《全宋文》著录碑文时将诸文本对校,如遇诸家意见不一,则通过理校做出判断和取舍。一部分结论于碑有征,另一些文字参以己意,取舍合理,值得肯定,因而其录文与碑拓文字的差异比《恒山志》明显减少。如“足冻长城之窟”中的“冻”,文后注一云“‘冻’吴本作‘踏’”,其录文未取吴本而作“冻”,与拓本合;“诞符至諴”中的“諴”,注二云“‘諴’原作‘诚’,据吴本改”,所改与碑拓合,识断完全正确;“僸佅兜离”中的“僸”,文后注四云“‘僸’原作‘傑’,据吴本、傅本改”,《全宋文》纠正了拓本之误刻(见前述),十分可取。但有的结论与拓本不合,仅为一家之言,不足采信。如“影达大漠之墟”一句,注云“‘达’库本及《金石续编》作‘连’”,碑拓亦作“连”,录文未取库本等的“连”,不知据何本而作“达”,不可信。再如,注三云“‘王’原作‘正’,据傅本改”,而拓本作“正”,《全宋文》录作“王”属妄改。
转录本直接转自他书,未参照碑拓之类原始而又可靠的第一手文献材料,存在一误再误的危险。有的在文本整理中虽经理校而作出选择,但仍不能脱离主观判断的藩篱,错误在所难免。
四、撰作本

此外,我们还调查了上海涵芬楼影印本《小畜集》[9],该书系钞本,扉页题《王黄州小畜集》,四部丛刊集部。核之碑拓,其卷16所录碑文有39处与之不合,主要包括:
(一)文字误录,共31处。如:碑拓“固阴冱寒,万物之所藏伏”句中的“藏”误作“载”,“帝尧开唐国之封”的“国”误作“封”,还有“止”误作“士”、“祀”误作“祝”、“民”误作“氏”、“沉”误作“况”、“畤”误作“畴”、“先”误作“光”、“蒇”误作“藏”、“阙”误作“闢”、“将”误作“长”、“溜”误作“海”、“杳”误作“查”、“坤”误作“神”等。
(二)文字误脱,共3处。如:“每战战兢兢”句漏录一“战”字,“何往不利,何谋不臧”句漏录“臧”字,“臣沐浴皇泽,优游紫垣”句漏录“游”字。
(三)文字误衍,共2处。如:“铸农器而毁戈鋋”句录文“铸”后衍一“铁”字,“契天地以为心”句录文“契”后衍一“而”字。
(四)文字误倒,共3处。如:拓本“天神地祇”录文作“天地神祗”,碑拓“岂比夫禋于六宗”句中的“比夫”录文作“夫比”,碑拓“更鉴王悝之策”句中的“王悝”录文误倒而作“悝王”。
上述材料表明,尽管同为撰作本,但钞本录文的准确度远低于刻本和排印本。真正的宋刻本现已十分稀少,难得一见。后起刻本、排印本等大多经翻刻产生,文献真实性远不及宋刻本。而钞本多经过转相传钞,文字的误、倒、脱、衍不可避免,文献的真实性更受到严重影响。
碑刻文献中,碑原石易风化损毁,且不便使用,但可通过捶拓产生的拓本客观反映石刻的真实面貌。拓本便于保存、翻检,信息相对准确,于是成为特殊、原始而又可资直接利用的石刻文献形式。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很多石刻材料没有留存下来,相当数量的碑文已见不到碑石或拓本,因此科学选择参照文本是碑志文校理时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前述四类文本是碑刻整理中经常碰到的文献源,通过《庙碑》录文的调查统计和对比分析不难发现,各文本录文质量有优劣之分①,怎样确定好的工作底本,如何依据拓本或相关文本校订文字异同,成为决定校勘工作成败的关键因素。相对而言,摹录本录文是较可靠的,虽个别字形的隶定略有偏差,但总体上能反映拓本文字的原始状貌。不过,将摹录文本转换为通行汉字文本时,对异体俗字的辨识又是必须克服的另一道障碍,其中有很多工作要做。撰作本碑文出自撰者之手,有的甚至载于撰者自编文集,本可作为较好的校勘底本,惜其古本多散佚,原始文本不存,靠钞本和翻刻本流传于世,而抄录、刻写中个别字词会有笔误,加上录文时文字的误、倒、脱、衍等问题,大大降低了撰作本应有的文本、文献和使用价值,其中刻本的情况相对要好一些,而钞本错误较多,不可信赖。重刻本、转录本除转录时的笔误、主观臆断等人为造成的问题外,录文依据多为二次文献,真实性较差,应当谨慎对待和使用这类文本,在有其他文本的情况下,一般不宜选为底本。总之,碑石和相应拓本一般未经人为改动,是最理想的校勘底本;就文本而言,当首选摹刻本,其次是撰作本中的刻本和排印本,在没有其他文本的情况下,才考虑选择钞本、重刻本或转录本,且应持慎重态度,重点发挥其在碑刻文献整理校勘中的参考作用。
注释:
①从碑拓本与摹录本、排印本《小畜集》所录《庙碑》碑文内容及文字差异看,文章上石后王禹偁未对碑文进行过修改或润饰,因此以碑拓作底本校勘其他文本的思路可行,也就是说本研究文本比较的标准是统一和科学的,保证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
参考文献:
[1]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
[2]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3]陆耀遹.金石续编[M]//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5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
[4]陈梦雷,蒋廷锡.古今图书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成都:巴蜀书社,1984.
[5]宋金龙.恒山志[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6]曾枣庄,刘琳.全宋文[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7]王禹偁.小畜集[M].王云五,主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8]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M]//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石刻史料新编:第1辑第25册.台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79.
[9]王禹偁.小畜集[M].上海:上海涵芬楼借江南图书馆藏经鉏堂钞本影印,1930.
[责任编辑文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