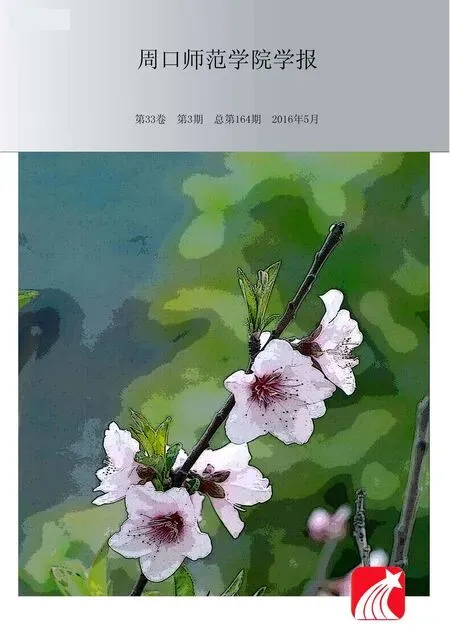精神·人物·语言
——论刘庆邦长篇小说《黑白男女》
王 越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精神·人物·语言
——论刘庆邦长篇小说《黑白男女》
王越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刘庆邦是活跃于当代文坛的重要作家,也是具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作家。他的长篇小说力作《黑白男女》,以现实主义手法书写了矿难之后矿工家属的悲欢离合。透过小说的精神、人物以及语言等,可以体察出作者的人生理想和审美追求。
关键词:刘庆邦;《黑白男女》;精神;人物;语言
一、悲悯的精神内涵与温情的人文关怀
刘庆邦的矿区题材小说相对于他的农村题材小说是清醒、理智、冷静的,表现方式是呈现性的,但始终因着对小人物生存的深切关怀,自有刘庆邦式的独特温情在其中。也因着这温情,刘庆邦的小说很少直接描写矿难本身,而是着重写矿难带给亲人物质与精神上的双重打击。有论者说:“任何一个真正关注人类命运的作家都不会回避对死亡的理性思考并以严肃的社会责任感在自己的作品中艺术地描写死亡。”[2]刘庆邦强烈的生命意识和人文关怀同样在《黑白男女》这部小说中有着深刻的体现。
小说以一次重大的矿难开篇,整部小说弥漫着的悲情色彩压得人几乎喘不过气,而老矿工周天杰强烈的生命意识,则是这阴郁色调中透露出的一抹亮色。周天杰是一个退休老矿工,一家和睦,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儿孙绕膝,老伴儿贤惠持家,生活一切如意。但是儿子周启帆的突然罹难“使这个原本平静的家庭顿时失去了平衡,变得风雨飘摇危机四伏”[3]12。老人在遭此大难后并没有倒下,他还有孙子,孙子小来是他的精神支柱和生活动力,是他生命价值的体现,因此必须留住孙子。要留住孙子就要留住儿媳郑宝兰,在儿子亡故后他和老伴儿加倍地对儿媳好,一日三餐做好,表面上也并不干涉儿媳的自由。儿媳还不到30岁,留她在家是一种自私,可是周天杰没更好的办法。他强撑着精神,拖着年迈的身躯苦苦支撑着因儿子离去而支离破碎的家,每天在菜园忙活着种菜,带孙子玩耍。家中气氛压抑,他努力调节情绪强颜欢笑。“他像是在独奏、独唱,又像是在跳个人舞,在演独角戏。没人配合他,没人为他喝彩,甚至连喝倒彩的都没有,只有他一个人唱来唱去,跳来跳去。”[3]61老年失独,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但周天杰毅然顽强地支撑着整个家庭,让读者会不由得震撼于人的生命力可以如此强悍,历经风雨而不倒,这才是人最高贵的生命姿态。
死亡的突然降临带给家庭的是断裂性的灾难,而生存的艰难则是家庭持续性的负担。煤矿工作的高度危险性不只是威胁矿工们的生命,也时刻威胁着他们的健康。作为老矿工的周天杰虽然一辈子没有遭受过重大事故,但是多年来的采煤生涯也给他留下深刻的烙印——脸上的煤瘢和黝黑的煤肺。煤瘢在脸上在身上是外在的显而易见的,煤肺在身体里是不显见的,他们吐的痰都是黑色的,可见采煤工作对矿工健康的戕害。比起矿难夺去生命,拥有煤瘢煤肺已是万幸,人生的两难选择可见一斑。矿难带给矿工的危害又岂止是夺去生命,更是对整个家族造成的灾难性的摧毁和打击。遇难矿工家属之一的卫君梅在生活艰辛、备受弟弟和弟媳排挤的时候,也曾抱怨丈夫陈龙民,“你这一走,你倒是省心了,你哪里知道人家是怎样欺负我们,你哪里知道,我们孤儿寡母遭的是什么样的罪!”[3]52足见矿难带来的痛苦是广泛的、深远的、永久的,卫君梅是心酸无奈的,无数个失去顶梁柱的矿工家庭是悲痛哀伤的。“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生命都不是孤立的,与其他生命有着共生的关系。特别是和亲人之间,骨肉相连,血脉相连,心心相连,是互相依存的关系,谁都离不开谁。”[3]77正是这一悲痛之源的最好注解。
二、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
女性在刘庆邦心中是真实美丽善良的形象。作家在小说中塑造了两个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蒋妈妈和卫君梅。
(一)胸怀博爱的母亲——蒋妈妈
蒋妈妈同刘庆邦以前多篇小说中塑造的母亲形象一样,以“妈妈”的称谓出现,没有名字,甚至连姓氏都是亦步亦趋地跟随着丈夫和儿子。她没有自我独立的空间与意识,是女性丧失主体本真的一种表现。她心底里的自我认同身份是一个母亲,想做的事情就是趁年纪身体还行可以抱上孙子,分担儿子和儿媳的困难,这样才算对得起去世的丈夫和蒋家的先人,也对得起自己,一生的使命才算完成。这是她在传统思想熏陶下最大的心愿,体现了母爱和母性的深重。蒋妈妈这一称呼作为“夫之妻、儿之母”形象出现,虽然抹杀了她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但并不妨碍人物形象闪耀着金子般的光芒。
蒋妈妈也是遇难矿工家属,不过她的丈夫是在之前的一次冒顶事故中亡故的。蒋妈妈忍住悲痛,带着正在读高中的儿子蒋志方来到矿上接替丈夫的工作。来到矿上,蒋妈妈没有工作却做着更有意义的事情。她先是受女工部韩部长的邀请在矿工大会上以切身感受讲述矿难带给家庭和亲人的巨大伤害,提醒矿工们要记住血和泪的教训,注意在矿下的生产劳动安全。后又帮助遇难矿工的家属们积极面对生活困难,家属们心有郁结需要发泄时都去蒋妈妈的家里寻求精神慰藉,仿佛这里是自发成立的精神抚慰中心。蒋妈妈对在这次矿难中失去丈夫的王俊鸟更是给予无微不至的照顾。王俊鸟因为小时候得过病导致心智不健全,在失去家庭支柱后被别人欺负,蒋妈妈就给她洗澡洗衣服,做她的坚强后盾。蒋妈妈对王俊鸟是母亲般的最宽厚无私不求回报的真情,虽然王俊鸟并不懂得太多人情,但是这大爱温暖滋润着她干涸的心灵。
蒋妈妈对待生命和生活的态度展现了人性最美好、本真、醇厚的一面,也让读者对人性重新充满希望。她饱经苦难依旧顽强不屈,经受挫折依旧微笑面对生活,她急人所难、侠义助人、乐善好施,拥有博大宽厚的胸怀,散发着人性的光辉,张扬着自然健康、原始纯真的母性意识和母爱情怀。她是天下所有伟大母亲的形象代言人。
(二)坚强独立的新女性——卫君梅
卫君梅的丈夫陈龙民在矿难中离世,家庭的稳固和谐瞬间被打破,然而她并没有被生活的困境吓倒,而是坚强地支撑残缺的家庭。她一边种地一边在矿里的食堂工作,还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一日三餐从不落下,女儿的功课也亲自辅导,可以想象她是承受了多么沉重的生活和精神压力。
面对同样是矿工遇难家属的好姐妹郑宝兰,她施以援手给予精神慰藉,用自己并不宽阔的肩膀为好姐妹撑起一片心灵避难的空间,引导郑宝兰积极面对生存困境。在郑宝兰眼里,“君梅姐是一个心劲儿很大的人,也是一个很有志气的人。人说船的劲在帆上,人的劲在心上。君梅姐的劲果然在心上。人又说人凭志气虎凭威。君梅姐的确有着非同寻常的志气”。“郑宝兰有时还觉得,君梅姐对她的关爱像是一种母爱。母爱是一种感情,也是一种智慧,一种能力。……而君梅姐像是代替着母亲,源源不断地给予她一种新的母爱。”[3]255-256
对于和郑宝兰相同遭遇的秦风玲,她更是倾力相助,解决生活中的实际困难。秦风玲失去丈夫后想重新寻找依靠,经小卖店的老板介绍和单身矿工尤四品认识,卫君梅作为姐妹也帮助相看,并语重心长地嘱咐他下矿要注意安全,这正是有切身之痛的人才会有的关怀之言。秦风玲的儿子陶小刚因抢劫进派出所时,她四处奔波请求相助。在陶小刚放弃学业回到家中与尤四品发生冲突时,她又出谋划策帮忙解决纷争。在一定意义上,卫君梅也是秦风玲的“母亲”,是她人生的精神导师。
其实,卫君梅最艰难的生存处境不在于生活的忙碌艰辛,而是在陈龙民去世之后她和两个孩子如何重建精神家园。丈夫在时,一家人和睦团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妯娌之间亲如姐妹,婆媳关系也甚是和谐。丈夫的突然离去使公爹和婆婆身心受到重创而一病不起,弟弟和弟媳则因老宅未来的归属而处处排挤卫君梅和孩子们,妄图让卫君梅改嫁,而把他们从老宅驱逐出门。还有蒋妈妈的独子蒋志方对卫君梅的猛烈追求,这些都带给她极大的困扰。但她仍坚守自己的处事准则和行为方式,对蒋志方说,“我跟你说过了,我不需要你帮,也不需要别的任何男人帮我。我就是要试一试,靠我自己的力量,能不能继续活下去,能不能把两个孩子养大”[3]41。在周天杰老人看来,“卫君梅简直是梅花的姿态,她要傲霜斗雪,独立于世”[3]131。卫君梅果然人如其名,捍卫自己君子如玉般的品质,秉承梅花傲立于霜雪的高洁,展现了自尊自立自爱自强的现代女性观念,凸显她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独立,增加了沉闷话语下一抹亮丽的生命底色。
三、诗情哲思的语言风格
(一)语言节奏诗情舒缓
莫言认为,“小说一是要有故事,二是要有语言。一个作家写作久了,总会想到要寻找自己的语言”[4]。语言本身就是一个调子,《黑白男女》开篇的灰色基调就铺垫了小说叙事节奏的舒缓。第一章以周天杰老人在菜园里拔辣椒棵子开头,描写缓慢细致层层展开。作者的笔触就像摄像机一样捕捉到辣椒细微的根须甚至被拔掉叶子上的青虫,从臆想中青虫呼天抢地的呐喊推进到辣椒的辣味、土地的包容性和各味俱陈,进而写到人生的苦难与挣扎,从室外的景象书写到室内人们的生活。这样层层推进并不激烈的叙事语言是刻意减缓的速度,作者试图把生活经验的细节注入文字中传递给读者,给人一种不做作不突兀的语言美感,带给我们阅读的审美享受,也让我们在舒缓的叙事节奏中领悟作者心底的温情和人文关怀。
刘庆邦在讲述故事时经常会斜笔逸出另一生活片断。这边写周天杰在菜园忙活,那边斜笔写到鸡窝写到孙子小来拔鸡毛甚至写到了公鸡被拔毛的心理细节,小来拔鸡毛做毽子这一情节反映北方孩童幼时的娱乐活动,显示了独特的地方风俗。这种旁逸斜出的写作笔法,拖缓了叙事节奏,使小说显得有缓有急,泰然自若。整部小说都没有过于激烈的叙事冲突,都是在缓慢叙事中呈现叙述,体现出作者的独特诗意匠心、脉脉温情及对笔下人物的深切关爱。
(二)语言特质温情哲思
《黑白男女》中,刘庆邦一直采用旁观式的叙述策略,看似冷静客观实则充满感情与关怀。“爸爸是罩在孩子头上的一把伞,伞没有了,雨点迟早会落到孩子头上,没有大雨点,也有小雨点儿。我们想为孩子遮风挡雨,但终究不能代替他们的爸爸。……当孩子知道爸爸不在的时候,他们跟别的孩子就不一样了,离他们长大就不远了。”[3]29这是卫君梅和郑宝兰讨论丈夫离世要不要告诉年幼的孩子时,卫君梅的回答。可以期待的是卫君梅的孩子一定会如她一样坚强乐观、坚定地面对生活。这是卫君梅在丈夫陈龙民的世界坍塌之后重新构建孩子们精神世界的第一步,首先就要正视生活中的困难与挫折,并且把陈龙民的照片放大放在家里正屋上。“我与你的看法相反。他们的爸爸走了,这事掖不得,藏不得。我就是要把照片放在醒目的位置,不断提醒他们,让他们学会正视现实,面对现实。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爸爸这棵大树不在了,不能依靠爸爸了,要坚强起来,把自己变成树,自己依靠自己。”[3]99这或许是作者对所有失怙少男少女想说的话,其中包含太多的深层精神体验与情感期待,充满着普世情怀与温情的注视,这文字背后留下了意味深长的回味与喟叹空间。
人生活在世界上是孤独的,始终要依靠自己的双手创造心中的世界。人生或许是无意义的繁杂的,但并不妨碍我们积极进取、开拓世界的决心。语言带给我们的感动如一袭清泉温暖滋润着人心,也同样让我们看到来自作者心灵世界的认知,蕴含着作者对人生命运的终极思索,引导着我们思考人生。
参考文献:
[1]莫言.文学创作的民间资源:在苏州大学“小说家讲坛”上的讲演[J].当代作家评论,2002(1):5.
[2]王颖卓,梦红.论《红楼梦》死亡描写的艺术表现手法[J].红楼梦学刊,2008(3):158.
[3]刘庆邦.黑白男女[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
[4]杨扬.莫言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3.
莫言把民间文学的写作分为两种:一种是“为老百姓的写作”,另一种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1]。刘庆邦最新长篇小说力作《黑白男女》继承了他一贯书写题材的传统,描写了一个叫龙陌的大型煤矿遭遇瓦斯爆炸,炸死138名矿工,矿工们的遇难导致原本稳定的家庭结构迅速解体,他们身后的孤儿寡母面临的是生活和情感的重新建构。本文通过对小说的精神脉络、人物形象及语言书写的分析,进入作者为我们提供的艺术境地,从而探究作者追求的精神世界和审美理想。
DOI:10.13450/j.cnki.jzknu.2016.03.005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9476(2016)03-0024-03
作者简介:王越(1991—),女,河南周口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2015-1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