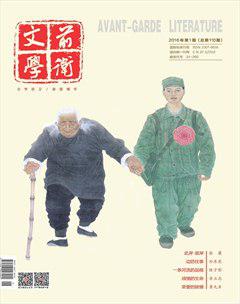彼岸有多远?
西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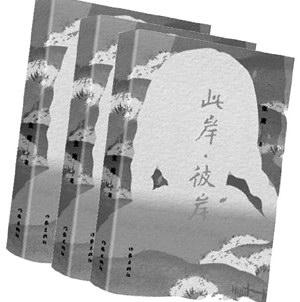
长篇小说《此岸·彼岸》是一部与众不同的作品。有关革命历史回忆的小说似乎色调都比较单一,要么赤烈火热,要么沉重晦暗。这样的结果,是作者的精神向度所致,对历史有什么样的期待,作品就会呈现什么样的美学结果。而《此岸·彼岸》不同,轻灵、单纯、洁净,具有童话般的美感,又不失锋利、厚重,因为掩卷之后,你会突然发现小说的意图是在革命历史背景下,拷问一个直指人性深邃处的问题,这是有关信仰、感情、忠贞等等基本价值的艰难对话。这就使得小说陡然间增加了重量,令人不得不直面,不得不思考。我相信这部作品不会淹没在文学历史的长河中,反而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加让人念念不忘,时时怀念。
一
小说的故事内核似乎并不复杂,少女小碗(秦诗伊)与强哥是红军长征途中的小伙伴,有着生死相依的真挚感情。但出于革命需要,小碗嫁给了受伤并残疾了的首长(孟寒朴)。小碗对孟寒朴的感情也从不情愿到敬仰,最后生出很复杂的爱意。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孟寒朴与小碗双双被国民党逮捕,进入牢狱。孟寒朴出于对小碗的情爱,在小碗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按照国民党的意图写了自白书,而其他一同被捕的同志拒绝投降,走向刑场,英勇牺牲。
不久,孟寒朴与小碗阴差阳错地被解放军解救,保住了性命。但因为孟寒朴有变节行为,进了监狱,出狱后被安置在县城。而小碗也与孟寒朴离婚,回了农村老家。之后几十年,两人共同开始了漫长的心灵拷问之路。孟寒朴放弃了县城的清闲工作,以残疾之身过最艰苦的生活,最后在悔恨中死去。而小碗及后辈也度过了充满艰辛的历程,受歧视,失去得到更好生活的机会,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小碗家的第三代人成长起来,才开始新的生活。
虽然小说整体的叙事线索基本是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展开,但阅读过程中却总是让人感到一种不断的倒叙。这种倒叙的感觉特别强烈,它逼着读者回到历史之中某个原点之处。这个原点在最后才交待出来,它是一把钥匙,也是一切矛盾交织的节点。但读者随着叙述最终走到这个交汇点之后,猛然发现,自己此时此刻站在了庞大历史的隐晦之处。平时晦暗不清的疑问此时有了思考的基础,有了开始的起点。
那么,《此岸·彼岸》是如何做到的呢?小说用的是追忆。几乎所有人都在追忆,小碗和强哥在追忆长征途中的情境,小碗的女儿休休(孟休)在追忆自己不明所以,却充满艰辛的生活,而第三代人少女盈盈则干脆考入历史系,从历史文献中追索那个历史节点的真实情况。小说貌似在按历史线索交代着什么,但同时在隐藏着一些至关重要的东西,因为力量还积蓄得不够,问题的视野还未全部交代出来。每个人的追忆就像一股十分强劲有力的洪流,涌向那个隐秘的历史节点,无限接近真相,并且在真相显现的一刻,显现出巨大的悲剧力量。这是小说《此岸·彼岸》叙事上的秘密所在。
二
张鹰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获文学博士学位,从事过相当长一段时期文学批评,写下很多有质量的评论文章,并于新世纪初出版一本军旅文学研究专著《反思当代中国军事小说》。这本专著在世纪初很具有标志性,提出的很多理论命题被后来批评者所延续。也就是说,在觉察问题的敏锐性和看待问题的深刻性方面,张鹰的学术研究是很见功力的。
十年前,张鹰就在写长篇小说。写了整整十年,这是一般作家不敢想象的事情。此前,我也从未读过张鹰的虚构类文字,比如小说。所以,我也从未想象过,她的小说会是个什么样子。我是晚辈,在诚惶诚恐地与她打交道的过程中,会感到她的严厉、不通融,也会隐隐感到她的傲气和倔强。她是一个敢于和时间豪赌的人,而我们都不是。我们总是给自己规定每天写下多少字,每年要写多少个中篇、短篇小说,一年或两年要完成一部长篇小说,生怕被历史潮流落下,生怕错过站在潮头的机会。我们这样的作家是注定拿不出具有革命性意义的作品的。但是,一个敢于和时间豪赌的人不是这样。他们的赌注特别巨大,也就意味着,他们知道豪赌之后会有一个更加巨大的结果,他们有这样的自信。当明了这些之后,我觉得我读到的《此岸·彼岸》似乎正在情理之中。
不知张鹰过去写没写过中短篇小说,至少我没读过。中短篇小说似乎是向长篇小说过渡的必由之路。通过中短篇小说的磨炼,作家起码会掌握两门手艺,一个是惊艳的语言,另一个是机智的叙事。这两种手艺会吸引读者读下去,即便读到后来大失所望,或什么都没记住,但至少是把一整本小说消费掉了。《此岸·彼岸》的语言说不上惊艳,叙事称不上机智,但会给人另外一个层面的感受。叙事的秘密前面已经谈过,不是小机智,而是大格局,这里且谈一谈语言。
《此岸·彼岸》的语言可称得上洁净、洗练、温情。其中大部分追忆叙事都是通过少男少女,或年轻男女来表达出来的,具有一种类似于童话般纯粹、明净、天真的色调。无论是绝境中的情愫,苦难中的挣扎,似乎都保持着一种孩子般明媚。这种语言是一种刻意的追求,也是一种心境的传达,似乎更像一种沧桑过后的恬淡,绝望过后的留恋。虽然没有青春写作的魅惑、冲动、无畏,却有洗去铅华之后的本真。
当然,《此岸·彼岸》的语言与叙事都不是与时间豪赌之后的那个结果。那个结果在于小说所最终迫使读者去思考的悲剧内核。
三
小说里使用的悲剧并不是指通俗意义上的悲伤的、错误的、不应发生的事情,而是指源于古希腊悲剧意义上的悲剧。实际上,这个概念在张鹰自己的研究专著《反思中国当代军事小说》中就经常使用。我猜想,这也是张鹰有意为之的艺术追求。
当我追随着《此岸·彼岸》多条叙事的洪流来到那个讳莫如深的历史节点之上时,我们发现,我们正站在历史的现场中,也站在那个悲剧舞台上。那么,舞台上演出了什么呢?此时,正是孟寒朴写下自白书的那一刻。孟寒朴是一个资深的革命者,照常人的理解,本不应该投降,而是和当时其他革命者一样,英勇地走上刑场,以就义的方式完结自己的一生。而小说中设计的情势也似乎并没有太多的余地,写下自白书就意味着生存,反之,就意味着死亡。孟寒朴选择生存,并不是害怕死亡,而是出于另一个原因——他爱小碗,舍不得与她诀别。为此,他不惜退出革命,从此不再是革命的同路人。
无论如何,在孟寒朴写下自白书的那一刻,一切都改变了。革命与情爱,在某一刻必须做出选择,二者必居其一。虽然两人后来都活了下来,但他们终生都处在痛苦的忏悔之中。孟寒朴有意让自己过上苦难的生活,其情形和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相类似,并最终在饥寒中死去。而小碗一家因为与叛徒有关,几十年过着受歧视的生活,儿子无法上大学,女儿不能与心爱的人结婚,结局都很悲惨。小碗知道孟寒朴写下自白书是因为对自己的爱,可是她久久不能原谅孟寒朴,因为他背叛了革命。小碗与孟寒朴都参加过长征,知道多少人为了革命而牺牲。
几十年的苦难生活救赎了孟寒朴和小碗,以及他们的后人了吗?他们为那一刻的选择所付出的代价足够了吗?似乎没有。小碗爱着孟寒朴,一直保留着他送来的红围巾,但她不能原谅他,无论他的自我惩罚多么重,而孟寒朴至死都怀着强烈的罪恶感、负罪感。如果所有人都回到那一刻,一切又该如何选择呢?如果再选择一次,结果又是怎样的呢?
悲剧是一种宿命,一种矛盾,一种无法选择。大多数人可能终生无法遭遇悲剧,可能并无多大困难地做出了选择,甚至两者很幸运地结合在一起。可是悲剧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必须站在某一个节点,直面某一个问题,然后深入地思考,可能有答案,也可能没有答案。任何一种选择都是沉重的,而不是轻飘飘的。
《此岸·彼岸》试图给出一种解释,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张力。革命者的使命固然是义无反顾地走到彼岸,但他们可能终其一生也无法走到那里。一代人、几代人都将生活在此岸,过着凡人的生活;彼岸很遥远,但那里闪烁着理想的光芒,照耀着我们,给我们以希望。
《此岸·彼岸》从始至终都处在一种巨大的悲剧矛盾之中,与其说是一种对革命历史的反思,不如说是对当下社会的诘问。因为,在距离革命已经很遥远的今天,人们似乎很容易做出选择,对任何超越性的东西都失去了热情。这与其说是一种自由,倒不如说是一种奴役。
走进小说所提供的悲剧现场,我们得到的恐怕不是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一次精神的折磨,一次自我的教育,一次深刻的反省。但这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