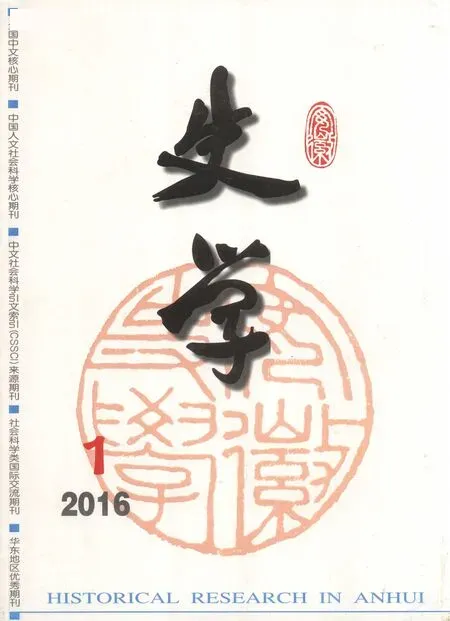变抑不变: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之考察
李国芳
(中共中央党校 党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变抑不变: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之考察
李国芳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北京100091)
摘要:国民党一大召开前后,面对苏联、共产国际对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和革命方法灌输,孙中山为争取苏联援助,虽然有选择地“师法”其革命方法和政党组织、训练方法,但他并不准备,最终也基本没有接受苏联、共产国际建议的民族主义政策。孙中山所恪守的仍然是其自五四运动以来新发展的“积极底民族主义”政策,其通过“修约”反帝的策略也与苏联、中共所倡导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模式大相径庭。
关键词:孙中山;民族主义;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共产国际;苏联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师法苏俄”,进行改组,通过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以下简称《国民党一大宣言》)。传统的说法是,孙中山在该《宣言》中基本上“采纳”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共产国际决议》)的主要内容*如黄修荣:《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介绍共产国际1923年11月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学习与思考》1982年第1期;[德]郭恒钰:《俄共中国革命秘档(一九二○——一九二五)》,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6年版,第97页;欧阳军喜:《苏俄及共产国际对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清华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等等。,对三民主义“作了适合时势要求的新解释”,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反帝反封建的、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经过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在基本原则上同中国共产党的民主主义纲领一致,符合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要求”*尚明轩:《孙中山传》,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第124—126页。持大致相似观点的还有:张克林:《孙中山与列宁》,拔提书店1934年版,第34—36页;崔书琴:《三民主义新论》,商务印书馆1946年版,第1页;张磊:《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北京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3页;郭世佑、邓文初:《民族主义的裂变——以孙中山与苏俄关系为中心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5年第2期;张磊、张苹:《孙中山传》,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22页,等等。。台湾的学者虽然不同意“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的提法,但也承认在1924年前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的确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尤其是反帝部分,更“是他的民族主义最后的,同时也是最高的形式”*朱浤源:《再论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总第22期(上册),1993年,第344—355页。。与这种传统说法相反,日本学者松本真澄等认为,孙中山在有选择地认可或接受共产国际关于民族自决观点的基础上,仍然坚持了“一贯同化说”*[日]松本真澄著、鲁忠慧译:《中国民族政策之研究——以清末至1945年的“民族论”为中心》,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第99—123页;陆文学:《变中的不变:论孙中山的民族同化思想》,《民族研究》2009年第3期。。
上述两种说法的问题在于,他们都或多或少地拘泥于《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就事论事”,而没有把这些解释与《共产国际决议》的相关文本逐条进行对照,考察他们之间是否存在差异;没有注意或不愿意注意到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起草《宣言》过程中与共产国际、苏联代表鲍罗廷等人之间的根本分歧,以及这种分歧背后隐藏着的异质的革命意识形态;也没有把孙中山视为一位正在寻求苏联援助的政治家,把《宣言》与他在此前后的一系列相关言说结合起来,剖析《宣言》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哪些属于“言为心声”,而哪些又是“言不由衷”的。
因此,本文拟既围绕《国民党一大宣言》的文本进行对比分析,又跳出文本,将其置入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加以考察,仔细辨别国民党一大前后孙中山民族主义学说的主体思路是否发生了变化;如果发生了变化,是在何种程度上、在什么层面的变化。其中,核心问题是孙中山是否接受了《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民族主义的重新解释。
一、国民党一大召开之前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的界说
“民族”、“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思潮,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被引入中国的。引入的目的,就是以此取代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华夷”观,救亡图存。但是,中国传统的“华夷”族类划分如何与源自于西欧历史经验的“民族”概念对接起来呢?中国未来应走一种什么样的建国路线图呢?
当时的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对“民族”概念的理解并没有什么差异。他们判定,“民族”的划分标准主要是“血统”、“语言文字”、“宗教”、“习惯”、“地域”等,民族就是“具有同一之言语、同一之习惯,而以特殊之性质区别于殊种别姓”的“人类之集合”*《民族主义之教育——此篇据日本高村世雄所论而增益之》(1903年),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三联书店1960年版,第405页。。拿这种从日本转口舶来的理论分析中国,他们认为,清朝疆域内的汉、满、蒙、回、藏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族类,就等同于“民族”。中国未来须“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余一:《民族主义论》(1903年),《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1卷,第486页。。
但与此同时,他们对于未来中国的建国路线图又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孙中山等反满革命者更多地汲取中国传统的华夷观念,一再把“满洲人”与“中国人”区别对待,认为“中国人”或“汉人”受到“满清”的屠杀、压迫,国家政权被“满人”所夺,汉人成为“亡国之民”。因此,革命须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为口号和目标*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向美国人民的呼吁》(1904年8月31日)、《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秋冬间)、《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9—252、296—297、324—325页。。换言之,在他们看来,按照当时“一个民族建立一个国家”的民族理论,未来的民族国家仅包括汉族居住的内地18行省地域,满、蒙、回、藏等非华夏族类地区是被排除在外的。与上述建国路线图不同,梁启超反对“排满”,主张引入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民族学说,希望将来中国须“取帝国政略”,以汉人为“中心点”,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再建立“大民族”的国家*梁启超:《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1903年),《梁启超全集》第2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1070页。。
20世纪前10年,这两种民族国家构建路线图互相激荡、互相渗透,到辛亥革命后在知识界、政治界——无论其为何族——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他们大多认为,中华民国须继承清帝国的版图。在此版图之内,虽然存在“五族”,但“五族”必须“同化”为一个民族。即“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完成“民族之统一”*《临时大总统宣言书》(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页;另参见黄兴涛:《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兼论辛亥革命与中华民族认同之关系》,《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等到清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认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以后“所当致力的”仅余民生主义一项任务*《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的演说》(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19页。。
但是,孙中山很快发现,北京民国政府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其共和理想,因而数度起事,继续革命,结果屡遭挫败。到1920年前后,孙中山痛定思痛,认为中国之所以专制制度仍存、外国强权依在、国土四分五裂,根本原因在于辛亥革命后错误地采纳了“五族共和之说”,致使中国各民族仍不能团为一体。孙指出,“汉族光复,满清倾覆”仅仅是达到了民族主义的“消极目的”。当前须改弦易辙,“努力猛进,以达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孙中山解释说,“民族主义之积极目的”,就是在继承清帝国版图的基础上继续沿着“一民族一国家”的路径,建立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汉族当牺牲其血统、历史与夫自尊自大之名称,而与满、蒙、回、藏之人民相见于诚,合为一炉而冶之,以成一中华民族之新主义,如美利坚之合黑白数十种之人民,而冶成一世界之冠之美利坚民族主义”*《三民主义》(1919年),《孙中山全集》第5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87—188页。。随后,孙中山进一步把这种否定其他民族存在,主张以汉族为中心来同化其他各族、增强国家向心力的做法,称为“积极底民族主义”*《在中国国民党本部特设驻粤办事处的演说》(1921年3月6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473—475页。。
与此同时,巴黎和会对中国权益的侵害以及由此激发起来的“五四”运动,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又增添了外向的目标,即“外抗强权”。在这股历史洪流中,孙中山作为中国革命的政治领袖,自不能置身事外。他开始注意到,“现在清室虽不能压制我们,但各国还是要压制的,所以我们还要积极的抵制。”*《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的演说》(1920年11月4日),《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394页。至于如何“抵制”,仍想求助于外国的孙中山尚没有考虑清楚。
到1922年中,孙中山求助于西方各国、或联合国内地方军事势力反对北京政府的努力陷入困境。是年6月,陈炯明围攻“总统府”,与孙中山彻底决裂,迫使孙逃出其根据地广东。孙中山遭遇到了其革命生涯中最惨痛的一次挫折。正当孙中山孤立无援之际,苏俄正在东方寻找合适的盟友。经过初步沟通,孙中山决定汲取俄国革命经验,“容纳”中国共产党,着手“改进”国民党党务。
因为急于得到苏俄的军事援助,这次“改进”工作又吸收了中共党人李大钊、陈独秀等和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等人参与,孙中山在坚持“积极底民族主义”的同时,开始引入苏联的某些民族政策。1923年元旦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规定:民族主义“消极的为除去民族间之不平等”,“积极的为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而实现民族主义的主要途径包括,对内“励〔厉〕行教育普及,增进全国民族之文化”;对外“力图改正条约,恢复我国国际上自由平等之地位”*《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3页。。对民族主义的这种解释虽然较以前增加了消除民族间不平等及“改正条约”等“反帝”的新内容,但与苏俄、中共将民族问题置于阶级革命之下、以暴力手段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相比,仍属殊途。
孙中山此时之所以主张有选择地去吸取苏联的民族政策,原因可能在于他依然热衷于美国“民族同化”式的建国路径,而对苏俄可能向中国灌输其世界革命、阶级革命等意识形态十分警觉。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曾特地向苏联外交代表越飞说明,“中国并无使此项共产制度或苏维埃制度可以成功之情况”,因此“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并得到越飞“完全同意”。孙中山还着重强调,“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1—52页。
二、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对民族主义解释的分歧
1923年初启动的“改进”国民党的希望再次落空后,经苏联和中共一再做工作,孙中山最终决定“师法苏俄”,进一步“改组”国民党。
1923年8月,蒋介石率代表团往访苏联,考察军事,顺便向共产国际介绍国民党的状况。其中,民族主义作为孙中山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肯定要讲的。这时,代表团对孙中山的民族学说与苏联的民族理论之间的差异很可能是了解的,因此在这种外交性的场合,对民族主义的解释便非常含糊。他们在向苏联人提交的书面报告中指出:“民族主义意味着所有民族一律平等,一方面,我们应该为捍卫我们的独立而同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帮助弱小民族发展他们的经济和文化。”*《国民党代表团关于中国国民运动和党内状况的书面报告》(1923年10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301页。
同时,代表团又重申了孙中山对越飞谈话的精神,再次向共产国际表明,国民党并不打算采用苏联的意识形态。11月26日,国民党代表团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举行会谈。蒋介石在演讲时开门见山地讲道:中国目前不能开始无产阶级革命,不能使用共产主义口号。相反,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会有诸多便利之处,三民主义“应当成为中国革命的政治口号”*③《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31—332、335—336页。。
代表团所解释的民族主义与苏联、共产国际的要求相比,显然相距甚远。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力图向国民党施加影响,规劝国民党进一步向共产国际和中共的政治纲领靠拢。他明确表示,国民党的三民主义口号“不是共产主义的口号”,但应当规定得“更具体、更明确”些。季诺维也夫建议,民族主义应该“不为新的资本家阶级、新的资产阶级在中国的兴起提供可能”,“不应用中国资本家阶级的统治去取代外国帝国主义的统治”,也“不应该导致建立中国一部分居民对另一部分居民的霸权地位”,即“无论如何不应该导致对生活在中国境内的各民族的压迫”③。
共产国际既是施援方,又自认为手握先进革命理论,向国民党推介阶级革命、民族革命的劲道自然强势得多。上述会谈两天后,即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正式发布了《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该《决议》首先批评国民党过去长期革命之所以未能成功,主要是因为“没有吸收城乡广大劳动群众参加斗争”,而把希望寄托在“国内反动势力上”。接着便建议国民党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以表明其是“一个符合时代精神的民族政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42—343页。。
与此同时,在广州,共产国际派给孙中山的顾问、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鲍罗廷也在不断地向国民党人推介苏俄的阶级革命经验*[苏]亚·伊·切列潘诺夫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3、45—46页。。问题是,《共产国际决议》也好,鲍罗廷的介绍也罢,其主旨都是共产国际《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参见《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35页;《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1920年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翻译室编译:《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919—1928)》第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0—46页。。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与中共的相关民族纲领是不相上下的;相反,与国民党长期坚守的革命理念却有着相当的距离。正因为如此,廖仲恺专门向广州的国民党区党部委员解释拟议中的土地法令等并不代表国民党已经“苏维埃化”*⑧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734、1740页。;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在党纲中特地加写了一段话:“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倡之吾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故其内容解释,当以孙中山先生之说为断。”⑧正因为如此,蒋介石当天读罢《共产国际决议》,心中并不以为然,感觉其“普〔浮〕泛不实,其自居为世界革命之中心,骄傲虚浮”*《蒋介石日记》(手稿本),1923年11月28日。转引自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上册,山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20页。。即使在起草、通过《国民党一大宣言》的过程中,围绕民族主义的解释也曾多次发生或明或暗的争论。但是,作为一位政治家,孙中山心里非常清楚,为了争取苏俄援助、师法苏俄改组国民党组织体制、达到革命目的,自己必须在某些方面做出让步。那么,从文本上看,《国民党一大宣言》与《共产国际决议》围绕民族主义的解释,存在哪些相同与不同之处呢?
首先,关于民族自决问题(见下页表1第1项)。民族自决,意即全世界各民族,不论大小,均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命运和政治归属。它是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夺权时期所采用的策略之一,后经美国总统威尔逊推动,而成为一种世界潮流。但是,苏俄的实践与威尔逊的提法并不完全相同,即布尔什维克在立国掌权后一方面并不否认俄国境内各民族拥有自决权力,另方面又要求这些民族联合成为一个联邦国家。
孙中山决定改组国民党后,苏俄即开始向国民党灌输其俄式民族自决理论。
1923年10月上旬,鲍罗廷甫抵广州,就给孙中山等国民党人吹风,“慢条斯理地、羞羞答答而拐弯抹角地”
介绍民族自决权问题*《鲍罗廷给维经斯基的信》(1924年1月4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95页。,说苏联已经实现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35页。。换言之,在鲍罗廷看来,孙中山应该以苏联为榜样,来解释其民族主义。《共产国际决议》则直截了当地建议,“国民党应公开提出国内各民族自决的原则,以便在反对外国帝国主义、本国封建主义和军阀制度的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以后,这个原则能体现在由以前的中华帝国各民族组成的自由的中华联邦共和国上。”*《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43页。
但是,如前所述,自辛亥革命后,尤其是自“五四”运动后,孙中山等革命者实际上已经开始接受“同化”中国国内各民族为中华民族这种美式做法,而不再把非汉民族区域排除在“中国”之外了。1923年元旦发表的《中国国民党宣言》就曾声明,“盖以言民族,有史以来,其始以一民族成一国家,其继乃与他民族糅合搏聚以成一大民族。民族之种类愈多,国家之版图亦随之愈广。”*《中国国民党宣言》(1923年1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1页。在这种情况下,要国民党人承认中国国内各少数民族的自决权并在此基础上实行联邦制度,自然会困难重重。
最终,在共产国际有软有硬的灌输下,国民党做出让步,在其一大《宣言》草案中写进了这个名词。但与此同时,该《宣言》又把民族自决权严格限定在“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版图之内,以示与苏联联邦制的区别*《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19页。。而这种表述,等于无形中取消了少数民族的自决权。面对这种自相矛盾的解释,鲍罗廷认为自己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在当下折衷处理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相信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自己会明白这里有矛盾”。鲍还建议,“共产党人应该揭示这个矛盾,争取在国民党的下一次代表大会上采用另一个提法”。毛泽东也洞察到了这种解释的牵强之处,指出:《国民党一大宣言》不能把少数民族自决权“置于这些民族属于,中国的这样一个老的概念之中”它需要明确国民党赋予了少数民族哪些权力*《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66、469页。。

表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与
资料来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42—345页;《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8—119页。
说明:下划线为引者所加。
其次,与民族自决相关的、隐隐约约的外蒙古问题(详见表1第1项)。从清末开始,随着中央政府控制力日弱,加以俄国挑动,外蒙古地区的离心力渐盛。辛亥革命后,外蒙古宣布“自治”。布尔什维克立国后,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声称:“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定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薛衔天等编:《中苏国家关系史资料汇编(1917—192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7页。但是,到1921年,苏俄国际环境转好后,便推翻上述承诺,出兵外蒙古,帮助其再次宣布独立。
苏联既不准备放弃对外蒙古的控制权,又肯定不愿意为此给日益接近的苏、孙联盟造成麻烦。《共产国际决议》便暗示说,由于“中国官方的多年压迫”,中国国内的少数民族“甚至对国民党的宣言也持怀疑态度”。因此,“国民党不要忙于同这些少数民族建立某种组织上的合作形式,而应暂时只限于进行宣传鼓动工作,随着中国国内革命运动的顺利发展,再建立组织上的联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43页。鲍罗廷则当面开诚布公地质问国民党人:“难道所有国民党人的活动能够让蒙古人或者西藏人相信,他们的命运问题会由这些国民党人作出公正的解决吗?”鲍还强调,国民党即将发表的《宣言》声明“在革命取得胜利以后少数民族在统一的中华民国境内实行自决”,只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步”。但“这样一个声明是不够的”,必须以观后效。因此,国民党不应立即同这些少数民族建立联系与进行合作。否则,“少数民族只能看到老帝国主义的复活”*《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48—450页。。
对于苏俄政府在外蒙古问题上的立场,已经确立“积极底民族主义”政策的孙中山是肯定不会同意的。早在1923年1月下旬,在与苏联政府外交代表越飞会谈时,孙中山就强烈要求对方“再度切实声明”第二次对华宣言各条款。而越飞在得到苏俄政府授权表面上承认中国对外蒙古主权的情况下,“正式”向孙中山宣称:“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文越飞联合宣言》(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全集》第7卷,第52页。1922年8月,俄共中央政治局曾致电正在与中国北京政府谈判的越飞,称:“中央认为,在同中国谈判时,从1919到1920年的总宣言(指1919年7月25日和1920年9月27日苏俄两次对华宣言,引者注)中得出直接指示是不能允许的……至于蒙古,关于它的国家法律地位问题和从蒙古撤军问题应通过俄中蒙签订协议来解决。解决这个问题时,不允许排除蒙古本身。这与我们承认中国对蒙古的主权并不矛盾。”(《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24号记录》(1922年8月31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115页。蒋介石访苏期间,针对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所说“蒙古人怕中国人”,还曾致函反驳。蒋说明,“蒙古人所怕的是现在中国北京政府的军阀,决不是怕主张民族主义的国民党……国民党正想快把他能够从自治的途径上,达到相互间亲爱协作底目的,如果苏俄有诚意,即应该使蒙古人免除怕的状况。须知国民党所主张的民族主义,不是说各个民族分立,乃是主张在民族精神上做到相互间亲爱的协作。”*蒋介石:《致俄外长齐采令(即契切林)函》(1923年10月26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1887—1926)》,九州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页。
现在,共产国际、鲍罗廷明确要求国民党暂时不与蒙古等少数民族建立联系,自然会遭到国民党人的坚决反对*《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50页。。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当天,孙中山在欢迎各地代表的宴会上发表演说时,不但在称呼中把蒙古人巴丹尊置于第一位,称“蒙古巴先生和国民党各省代表诸君”,而且开场就讲:“今晚是本总理来欢迎诸君;本总理又来同诸君共同欢迎巴先生。”在演讲最后,孙中山还专门讲了一段“蒙古问题”。他强调:“这次巴先生到广东的来意,还是想蒙古再同中国联合,造成一个大中华民国。”演讲结束,孙中山又提议,“诸君来公祝巴先生一杯”*《欢宴国民党各省代表及蒙古代表的演说》(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04、107页。关于“蒙古巴先生”的身份、来由等,请参见李吉奎:《龙田学思琐言:孙中山研究丛稿新编》,中山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5—66页。。作为一名政治家,孙中山在演讲中这样突出强调蒙古代表,显然不是无的放矢,更不像是无心之语。
由于孙中山态度坚决,《国民党一大宣言》最终非但没有采纳共产国际的这条建议,反而说明:“今后国民党为求民族主义之贯彻,当得国内诸民族之谅解,时时晓示其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之共同利益。今国民党在宣传主义之时,正欲积集其势力,自当随国内革命势力之伸张,而渐与诸民族为有组织的联络,及讲求种种具体的解决民族问题之方法矣。”*《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9页。
正是因为共产国际和孙中山对蒙古问题的态度相差十万八千里,所以国共两党刚刚实现合作,就围绕外蒙古问题发生了龃龉。这年2月至4月间,苏联政府与北京民国政府展开谈判,中方要求苏联从外蒙古撤兵、废弃苏蒙协定,遭到苏联拒绝。对此,中共党员公开主张外蒙古理当享有民族自治甚至独立的权利;相反,国民党员却大加反对,激烈抨击中共党人“维护俄国人的利益”,要求予以严惩,就连孙中山也对中共立场公开表示了不满的态度*参见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台北“中国学术著作奖助委员会”1973年版,第300—301页。。蒋介石也在私下毫不掩饰地对廖仲恺说,苏联“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彼之所谓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者,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蒋还把苏联与英、法、美、日等国对比,认为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蒋介石:《与廖仲凯书》(1924年3月14日),《蒋介石年谱(1887—1926)》,第150页。。
再次,反对国内外资产阶级问题(详见表1第2—4项)。布尔什维克宣扬无产阶级专政和暴力革命,其最终目的不但要消灭本国资产阶级,而且要打倒全世界的帝国主义。苏俄在中国选择国民党作为其同盟者,一方面是其国家利益使然,另方面则是从支持世界各国民族革命的立场出发,认为国民党是一支能够承担起反帝革命任务的“人民的政党”,是“代表那些为争取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的民族力量”*《有国民党代表团参加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会议速记记录》(1923年11月2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37页。。基于这种判断,在苏联主导下的共产国际自然希望把其革命理念灌输给国民党。《共产国际决议》建议,国民党应该这样来解释其民族主义:“国民党依靠国内广大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各阶层,为反对世界帝国主义及其走卒、为争取中国独立而斗争。对于上述每一个阶层来说,民族主义的含义是,既要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也要消灭本国军阀制度的压迫。”《决议》还强调,“对于国内各劳动阶层来说,民族主义就不能不意味着消灭封建专制的压迫,就不能不意味着,不仅要消灭外国资本的残酷剥削,而且也要消灭本国资本的残酷剥削。”*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1923年11月28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42—343、344—345页。
孙中山自从与苏俄接触开始就对“共产制度”抱着警惕的心态,此时对这种带有强烈的共产党色彩的革命理念,无论如何都是难以认同的。因此,《国民党一大宣言》在接受“帝国主义”、“民族解放”等名词的同时,采用曲笔的方式,把共产国际要求无条件地“消灭本国资本”的建议修改为:“其在实业界,苟无民族主义,则列强之经济的压迫,自国生产永无发展之可能。”“其在劳动界,苟无民族主义,则依附帝国主义而生存之军阀及国内外之资本家,足以蚀其生命而有余。”*④⑤《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1924年1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19、119、122—123页。而这种解释,结合《宣言》提出的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办法来看,实质上抽去了《共产国际决议》阶级革命的精髓。
对于《共产国际决议》提出的“消灭外国帝国主义的压迫”的建议,《国民党一大宣言》修正说,“民族主义对于任何阶级,其意义皆不外免除帝国主义之侵略。”④至于如何“免除”,《宣言》阐述道:
(一)一切不平等条约,如外人租借地、领事裁判权,外人管理关税权以及外人在中国境内行使一切政治的权力侵害中国主权者,皆当取消,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之条约。
(二)凡自愿放弃一切特权之国家,及愿废止破坏中国主权之条约者,中国皆将认为最惠国。
(三)中国与列强所订其他条约有损中国之利益者,须重新审定,务以不害双方主权为原则。
(四)中国所借外债,当在使中国政治上、实业上不受损失之范围内,保证并偿还之。
(五)庚子赔款,当完全划作教育经费。
(六)中国境内不负责任之政府,如贿选、僭窃之北京政府,其所借外债,非以增进人民之幸福,乃为维持军阀之地位,俾得行使贿买、侵吞盗用。此等债款,中国人民不负偿还之责任。
(七)召集各省职业团体(银行界、商会等)、社会团体(教育机关等)组织会议,筹备偿还外债之方法,以求脱离因困顿于债务而陷于国际的半殖民地之地位⑤。
这种主要依靠“修约”等和平手段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中国独立地位的做法,与共产国际所倡导的暴力反帝革命理念显然是大相径庭的。
最后,关于建立世界革命统一战线问题(详见表1第5项)。作为世界革命论者和正在遭受其他西方国家包围、干涉的新生政权,苏俄相信,自己必须与世界上其他所有革命运动建立统一战线。《共产国际决议》希望国民党同样这么做,“尽力利用在华的帝国主义者的内部矛盾”,同时“必须同工农国家苏联建立统一战线”,“必须使中国的解放运动同日本的工农革命运动和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发生接触和建立联系”⑥。在1924年1月15日召开的“大本营暨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联席会议”上,鲍罗廷据此向国民党人询问:民族和国家是“划分为被压迫的和压迫人的”,“你们打算同其中的哪些国家和民族携手前进呢?”鲍还建议,《国民党一大宣言》应载明:国民党“同其他被压迫国家的民族革命运动,以及与我党有着共同目的——为争取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解放而斗争的世界革命运动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及其在华势力的统一战线是必不可少的”*⑧《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第62—63、63页。。
对于共产国际和鲍罗廷的建议,孙中山虽然表示“完全赞同”,但同时又认为当下这样做“在策略上是不合时宜的”,立即予以否决。孙解释说,这样做,就会触动英、法等国的殖民利益,中国革命就会受到干涉。况且,越南、印度等国只有“一个主子”,而中国却被众多的“主子”所瓜分,中国革命的条件还不如他们呢?在此中国革命远未成功之际,就发表声明,指望着得到“英国工人运动或法国社会主义和激进分子的不可靠的支持”,显然是不现实的⑧。最终,这一点干脆没有被写入《国民党一大宣言》中。
显然,苏联、共产国际与孙中山及国民党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并不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还存在着实质性的差异。但是,国民党既要“师法苏俄”,争取苏联的援助,又须“容纳”中共入国民党,那么他就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结果,一方面,作为国民党“政治纲领”的一大《宣言》有选择地吸收了苏联、共产国际关于民族主义的某些概念;另方面,该《宣言》又按照孙中山等国民党人的理解,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对民族主义做出了自己的解释。换言之,《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民族主义的重新解释是双方妥协的产物,也是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一种表述。
正是由于《国民党一大宣言》对民族主义的解释是含混的,甚至前后矛盾的,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人后来各取所需,选择该《宣言》中符合自己理念的部分,做出自己的评价。
国民党一大闭幕后,鲍罗廷、苏联驻华外交使团团长加拉罕等人认为自己成功地向国民党灌输了苏联的民族主义理念,感觉不负使命,当即表露出不无得意的态度。鲍罗廷志得意满,认为国民党一大的“成果是很可观的”,“已经取得的成就是极其巨大的”*《加拉罕给鲍罗廷的信》(1924年2月13日)之附件“鲍罗廷给加拉罕的信”(1924年2月2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18页。。加拉罕也向俄国外交部反映说,“关于民族主义一条非常有意思,那里民族主义是按照共产国际的声明的精神解释的,而且还发挥了关于民族斗争的两个方面的思想,即一方面是同压制中国民族独立的帝国主义的斗争,另一方面是通过赋予中国境内各民族以自决权的办法实现各民族的解放,而这一条还发挥了去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的有关部分。”*《加拉罕给契切林的信》(1924年2月9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12页。“去年11月28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指《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关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国民党问题的决议》,详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342—345页。
毛泽东等中共党人虽然此前曾对该《宣言》中的民族自决权等问题表示过不同意见,但当时和此后也是予以肯定和接受的。1924年2月,蔡和森评论道:“凡是中国的人民”,对《国民党一大宣言》“都是不能故意反对的,都是满意而欲实现的”*(蔡)和森:《国民党大会宣言与国民》,《向导》第53、54合刊,1924年2月20日,向导周报社1927年影印版,第407页。。蔡和森言说的对象显然是包括“民族主义”在内的。到抗日战争时期,中共进一步肯定《国民党一大宣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是“新三民主义”,是“真三民主义”*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创刊号,1940年2月25日,第15页。,强调“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上述孙先生的民族政策”。中共还以此为矛,批评国民党把国内各少数民族称为“宗族”的做法,激烈抨击国民党对少数民族的“武力镇压”和“屠杀”政策,认为国民党“完全背叛了孙中山先生”*《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339页。。
三、孙中山对《国民党一大宣言》关于民族主义解释的迅速矫正
苏联、共产国际与国民党之所以会在“民族主义”问题上存在上述分歧与矛盾,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孙中山等许多国民党人并不认同苏联和共产国际所宣扬的阶级斗争、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等理念,甚至心存警惕。国民党一大召开前,为了打消苏联革命理念给国民党人可能造成影响,孙中山干脆说,苏俄革命的指导思想与三民主义“实在暗相符合”,三民主义本身也没有什么不妥或值得改进之处。国民党以往革命屡遭挫折,原因在于“专靠兵力,党员不负责任”,及“尚未有良好方法”。所以,孙中山宣传说,国民党员“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而非“主义”*《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员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孙中山全集》第8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36—438页。。在国民党“一大”闭幕会上,孙中山仍不放心,再次提醒与会代表,“我们所主张的三民主义是永远不变的”。国民党革命经年,而不能达到目的,“一是由于我们的办法不完全;二是由于各位同志不能同心协力,一致行动。”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目的就在于“订一个完全办法,划一同志的步骤,并议定党中的纪律,就是要大家能够实行三民主义,把这个主义的言论一定做成事实”*《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闭会词》(1924年1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76—177页。。换言之,在孙中山看来,虽然国民党要“以俄为师”进行改组,但苏联革命方法仅为“用”,三民主义才是“体”。
即便这样三番五次的重申,孙中山仍然担心苏联革命理念会超越“用”的层面,而凌驾于“体”之上。就在1924年1月23日下午国民党一大马上就要讨论通过《宣言》之前数小时,孙中山又打起了退堂鼓。这天上午,孙中山把鲍罗廷找来,说:“最好完全取消宣言”,以其“为全国政府起草的纲领”取而代之。在鲍罗廷看来,孙中山起草的这个“纲领”“根本没有触及中国目前的局势,也没有指出摆脱这种局面的任何出路”,其中“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空想”。鲍罗廷暗中叫苦:孙中山就是想“保持一切不变”。经过鲍罗廷反复劝说,孙中山才同意在下午的会议上通过《宣言》。由于担心自己向国民党灌输苏联革命理念的努力在最后一刻付之东流,鲍罗廷虚惊一场,事后想来仍觉后怕,感叹道:“这是真正危急的时刻。”①《鲍罗廷的札记和通报(摘录)》(不早于1924年2月16日),《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471—476页。
带着这样多的分歧和最后的“遗憾”勉强通过《宣言》,孙中山内心里的不情愿可想而知。作为一名政治家,为了避免苏联和共产国际向《国民党一大宣言》灌输的民族主义概念可能对国民党人造成影响,孙中山决定另辟蹊径,用一种非正式的方式进行补救和矫正。
1924年1月27日,国民党“一大”暂时休会。孙中山立刻抓住这个时机,亲自出马,开始宣讲“孙氏版本”的民族主义。到3月2日,孙中山已讲过6次。为了扩大宣传,孙中山立即下令把这6讲汇集成册,印成单行本,出版发行。孙中山如此急切,显然是为了及早把他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散布出去。并且,他在单行本序言中写道:国民党改组之后,“亟需三民主义之奥义、五权宪法之要旨为宣传之资。”②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自序”》(1924年3月3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3页。其中意思颇耐人寻味。
在这6次演讲中,孙中山对民族主义给出了与《国民党一大宣言》完全不同的解释。他首先对中国的民族状况进行了分析,并总结道,“就中国的民族说,总数是四万万人,当中参杂的不过是几百万蒙古人,百多万满洲人,几百万西藏人,百几十万回教之突厥人。外来的总数不过一千万人。所以就大多数说,四万万中国人可以说完全是汉人。”中国“同一血统、同一言语文字、同一宗教、同一习惯,完全是一个民族”。而这个民族因为一片散沙,又受到列强政治力、经济力、人口力的压迫,“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此时,“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③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一讲”》(1924年1月27日)、《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二讲”》(1924年2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88—209页。换言之,孙中山非但只字未提苏联和共产国际试图引入国民党的民族自决、联邦制度、革命反帝等问题,反而基本上回归到了国民党一大之前他对民族主义的解释。
对于如何聚拢民心,恢复民族主义,孙中山同样没有接纳共产国际建议的反帝、反封建、反资本主义、反军阀等办法,而是更多地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资源。孙中山指出,第一,要使全国民众都知道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第二,由家族联合为宗族,再由宗族扩充为国族,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第三,恢复中国“固有的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固有的知识”(指中国传统的政治哲学,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固有的能力”(科技发明能力);第四,学习外国的科学④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五讲”》(1924年2月24日)、《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六讲”》(1924年3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31—254页。。
对于列强侵略中国,中国必须奋起抵抗这一点,孙中山与共产国际的看法是一致的。但对如何抵抗,孙中山则大体发挥了《国民党一大宣言》的“和平”反帝策略。他坚持认为,反帝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积极的”,即“振起民族精神,求民权、民生之解决,以与外国奋斗”;二是“消极的”,即“不合作”,通过消极的抵制,“使外国的帝国主义减少作用,以维持[中国]民族的地位,免致灭亡。”⑤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五讲”》(1924年2月24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241页。
综上所述,《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民族主义的解释只能称作是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各取所需、互相妥协的产物,它并不能表明孙中山真正接受了共产国际的革命理念,更不能代表当时孙中山对这个问题的真实看法。在内心里,孙中山对民族主义学说的理解在国民党一大前后并没有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如果非要说其中有什么变化的话,大概也只有以废除不平等条约方式反对帝国主义这一个方面。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内蒙古因素研究”(14BDJ00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方英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5卷(上),第20页。。
Changed or Not:Sun Yat-sen’s Illuminating the Theory of Nationalism
Around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Kuomintang
LI Guo-fang
(Department of CPC History,the Party School of CPC Central Committee,Beijing 100091,China)
Abstract:Whe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mintern instill their ideology and revolution plan into KMT and Sun Yat-sen didn’t want to accept the nationalist policies recommended by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mintern,and he ultimately did before and after KMT held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Of course,Sun wished to obtain the aids and selectively “imitate”the revolution plan,the methods organizing and training party from the Soviet Union.Sun’s “positive nationalist policy”and strategy against imperialism through revising the treat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nations,which he newly illuminated since May Fourth Movement and now insisted in nature,was entirely contrary to the pattern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dvocated to launch Class Struggle and violent revolution.
Key words:Sun Yat-sen;nationalism;Declaration in the first National Congress of KMT;the Comintern;the Soviet Union
作者简介:李国芳(1970-),男,河北灵寿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教授,历史学博士。
中图分类号:K825.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05X(2016)01-006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