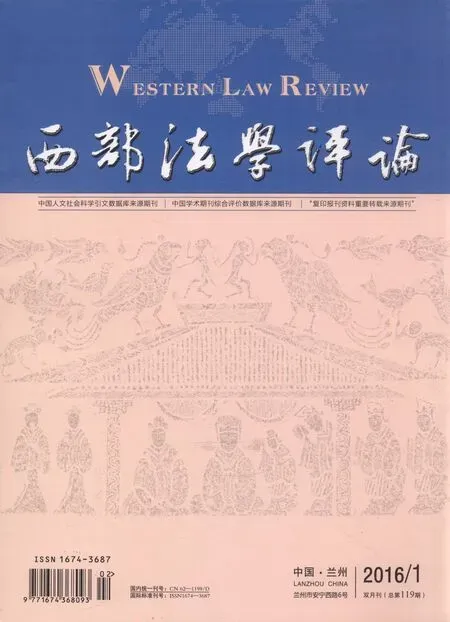犯罪记录制度与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兼容问题的比较研究
周子实
犯罪记录制度与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兼容问题的比较研究
周子实
摘要:目前我国裁判文书公开以实名制为原则,与犯罪记录制度的价值目标存在冲突。德语国家匿名公开源自其对人格权价值的优先选择,而英美实名公开是因为更强调宪政价值与程序价值。从人权国际公约的角度出发,前者直接体现为基本人权,而后者只能算人权的保障手段,德式方案更具合理性。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与犯罪记录制度都应以人权价值作为首要价值目标,实行裁判文书实名公开的英美港台等地的犯罪记录制度不完善,也正是因为忽视了这一点。我国应当立即贯彻裁判文书匿名公开,并尽快建立完善的犯罪记录制度。
关键词:犯罪记录制度裁判文书公开人格权人权价值
一、我国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对犯罪记录制度建设的冲击
2011年《刑法修正案(八)》免除了未成年人对轻罪的报告义务;2012年新《刑事诉讼法》第275条规定对未成年人轻罪的犯罪记录予以封存;随后两高三部颁布了《关于建立犯罪人员犯罪记录制度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就建立犯罪人员信息库、信息通报机制、规范犯罪人员信息查询机制、建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等方面作了原则性规定。这一系列举措标志着我国犯罪记录制度的初步建立,但要建立完善的制度体系依然任重道远。尤其是使犯罪人顺利回归社会为主旨的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将是中国未来法制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
而另一方面,根据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各级法院的裁判文书除特殊情况外都应当在统一的裁判文书网公布,删除家庭住址、通讯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健康状况等个人信息,但是对于当事人的姓名,则以实名公布为原则、以匿名公布为例外。这一规定旨在增强司法透明、维护司法公正,但是却引发了巨大的质疑。首要质疑自然是侵犯隐私权,其实裁判文书公开与当事人隐私保护之间的矛盾早已有之,在之前的一些案例中,一方当事人私自公布民事判决书造成对方当事人的起诉,法院虽然认定不构成侵犯隐私权,但也承认这种方式“不妥”、“未做一定技术处理,存在一定瑕疵和过错”。*李友根:《裁判文书公开与当事人隐私保护》,载《法学》2010年第5期。而现在这种“不妥”却通过《规定》实现了某种程度的合理化,是对隐私权保护的大幅退步。刑事判决实名公布所造成的危害更大,有着不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无法保障犯罪人及家人的安宁、可能导致遭受打击报复等诸多弊端,因此与犯罪记录制度的价值目标存在严重对立。*于志刚:《中国犯罪记录制度的体系化建构——当前司法改革中裁判文书网络公开的忧思》,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5期。
可以说,我国犯罪记录制度尚未真正建立,却已经面临着裁判文书公开制度的冲击。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犯罪记录法》即使将来被制定颁布,也只是奄奄一息的“死法”而已。本文以德语国家的犯罪记录制度与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比较法的视角寻求犯罪记录制度与裁判文书公开制度兼容的解决思路。
二、德语国家犯罪记录制度及对中国的借鉴价值
德国、瑞士与奥地利三个国家均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犯罪记录制度。德国在1971年颁布的《联邦中央登记册法》,是目前该国规范犯罪记录制度的唯一法律,至今已有多次修改。瑞士在《刑法》单设“刑事登记册”一章,2006年颁布的《刑事登记册条例》是对刑法规定的细化与补充。奥地利在犯罪记录制度方面有两部法律,1968年颁布的《刑事登记册法》主要包含主管机关、登记内容、机关之间的通知、答复与证明出具、刑事登记数据删除、为科研目的使用、与外国的信息交流等规定,1972年颁布的《勾销法》则涉及犯罪记录查询与消灭。
德语国家犯罪记录制度的最大特征是“犯罪记录册——犯罪记录证明”的二元分离模式,即犯罪记录册(犯罪信息库)中记载较为全面的内容,而在(无)犯罪记录证明中仅记载符合条件的内容。这一模式在犯罪记录查询与消灭制度上分别反映为二元查询体系与两阶段消灭制,具有灵活性并能兼顾多种利益:(1)在犯罪记录查询方面,实行国家机关申请查询犯罪信息库与当事人申请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的二元查询体系,并对不同主体赋予不同的查询权限与范围。特定国家机关通过直接查询犯罪信息库能够获取较为完整的犯罪记录,充分发挥犯罪记录在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的作用;当事人付费申请开具的证明则仅记载达到一定条件的犯罪记录,对于被免除刑罚、被判缓刑、初犯且轻罪等情形可以不予记载,以减少犯罪记录对其从事社会活动的影响。除国家机关与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如雇主),只能够通过要求当事人展示证明来得知当事人的犯罪记录,这既保障了第三方的知情权,也解决了犯罪记录公开或允许第三人直接查询影响当事人回归社会的问题。(2)在犯罪记录消灭方面实行两阶段消灭制。第一阶段为犯罪记录证明消灭,即一个较短的期限届满后,犯罪记录不再记载在(无)犯罪记录证明上,此时当事人在求职、入学等普通社会活动中便不受到任何影响,也免除了犯罪报告义务,但是国家机关仍旧能够查询得知,当事人在面对公检法等国家机关时仍有报告义务,并受到累犯等法律规定的制约。第二阶段为犯罪记录册消灭,即一个较长的期限届满后,将犯罪记录从犯罪记录信息库中封锁,此时连国家机关都无法查询,当事人在任何法律关系中都不再受前科的影响,而且面对国家机关时也不再有报告义务。法律还规定若干仍可能被使用的例外情况,比如为了国家安全时;也规定了若干不予消灭的情形,比如被判终身自由刑的情况。这种两阶段消灭制的优点同样在于其灵活地兼顾了多种利益,既能保证国家机关在履行职责、治理社会中的信息充分,又能帮助当事人能够尽快回归社会与最终归于清白。
我国目前的犯罪记录制度建设仍较为滞后。一方面,犯罪记录查询仍旧缺乏具体可行的规范依据,(无)犯罪证明记录开具的混乱无序影响了民众的生活与工作,2015年“安徽女子为办教师资格证申请开具无犯罪证明却被要求提供需要无犯罪证明的证明”、“广州明星检察官转型做律师奔波五地开不出犯罪证明”、“云南普洱派出所吐槽买房需开无犯罪证明”等一系列新闻引发了全国性关注;另一方面,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在整体上没有任何实质进展,这一制度性缺失也导致作为唯一进展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在实际适用中缺乏可操作性,学界呼吁将其“升级”为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声音很高。对于我国而言,德语国家这种基于二元分离模式的二元查询体系与两阶段消灭制值得借鉴。我国目前也存在犯罪人员信息库与(无)犯罪记录证明,已经具备了这一模式的雏形,因此借鉴成本较低,可行性较高。
三、德语国家裁判文书公开的制度与实践
德国的裁判文书公开(Verö ffentlichung von Gerichtsentscheidungen),在过去通常仅指出版(Publikation),但现在形式更加多样,网上公布成为了主要形式:联邦法院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裁判文书,州法院的网站虽有公布但并不全,此外还有juris等专业法律信息系统收录判决。尽管德国法院公开裁判文书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在过去这并非法定义务,因此真正得以公开的裁判文书并不多——根据研究,1987年至1993年间仅有0.5%的判决被公开出版,juris数据库在1991年也仅收录了当年1%的判决(包括1%以下的一审判决、10%的二审判决以及30%的联邦法院判决)。*Andreas Bock, Gütezeichen als Qualitätsaussage im digitalen Informationsmarkt - dargestellt am Beispiel elektronischer Rechtsinformationen, 2000, S. 101.直到1997年,联邦最高行政法院才通过判决的方式正式确立了所有法院均须公开裁判文书的义务,同时,为了防止对人格权的侵犯,要求在公开之前对裁判文书作匿名化(Anonymisierung)与无害化(Neutralisierung)处理。*BVerwG, Urteil vom 26.2.1997 - 6 C 3/96 .在实践中,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德国法院在公布裁判文书时就已经采取匿名化方式(包括自然人和法人),当然法官、诉讼代理人等不在匿名范围内。不过也存在少数例外,一是涉及名人或大公司时可能会实名公布,*Gerhard Knerr, Die Verö ffentlichung von Namen in gerichtlichen Entscheidungen, 2004, S. 73-74.二是法律另有规定,比如,《侵犯消费者权益或其他权利中的请求不作为之诉法》(Unterlassungsklagengesetz)第7条规定,原告胜诉后,有权申请将判决的基本内容在联邦公报(Bundesanzeiger)上公布并在其中提及被告的姓名;再如,诬告罪、侮辱罪的附加刑之一就是公布判决,但是法院在确定公布的方式与内容时也要遵循比例原则,防止传播范围扩大损害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利益。*Jürgen Wolter(Hrsg.), Systematischer Kommentar zum Strafgesetzbuch, 8. Auflage, Band 3, §200.匿名处理的规则同样适用于私人公布裁判文书,德国法院认为,没有重大公共利益而实名公布判决的,属于对人格权的侵犯;*OLG Hamburg, Beschluss vom 09.07.2007 -7 w 56/07.在商业竞争中,未经匿名处理而公布涉及竞争者的判决,损害其个人关系与商业关系的,属于不正当竞争。*OLG Hamm, Urteil vom 7.2.2008 - 4 U 154/07.
瑞士《宪法》第30条第3款规定了宣判公开原则,裁判文书公开是这一原则的派生。《联邦法院法》第27条、《刑事机关组织法》第63条、《行政法院法》第29条分别规定了联邦法院、联邦刑事法院和联邦行政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开义务,同时明确要求以匿名化为原则;《专利法院法》第25条规定了联邦专利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开义务,尽管未明文要求匿名,但在该法院官网数据库中公布的裁判文书也都进行了匿名处理。瑞士《刑法》第68条将公布判决规定为一种措施(Massnahme),当涉及公共利益、受害者利益等时,法院可以依申请公布判决,此时有可能会出现犯罪人的姓名。*Günter Stratenwerth/Wolfgang Wohlers, Schweizerisches Strafgesetzbuch, 3. Auflage, 2013, S. 182.至于各州法院,则缺乏裁判文书公开的统一规定,有的州建立了自己的数据库,有的州只列出了裁判文书的目的,还有的州仅仅公布裁判的统计数据,*Paul Tschümperlin, Die Publikation gerichtlicher Entscheide, in:Kommentar zum Publikationsgesetz, Editions Weblaw, 2011, S. 70.但在公布时也采取了匿名处理。
在奥地利,根据《最高法院法》第15条,最高法院应在向公众开放的互联网数据库中公布裁判文书,而且当事人的姓名及其他个人信息必须通过字母、数字、缩写等替代方式予以隐匿化处理。不过,奥地利法院体系较为复杂,联邦制下地方自治权较大,因此也不存在要求所有法院公开判决的统一规定。目前,官方的裁判文书数据库是奥地利联邦总理府建立的法律信息系统的一部分,已收录了数十万份裁判文书,但绝大多数都是最高法院、宪法法院或联邦法院等的判决,只包括极少数的地方法院判决,州最高法院、州法院和地区法院的收录判决总共仅为两千余份。笔者通过查询,发现该数据库中的当事人姓名也进行了匿名化处理。在经济法领域,一些法律会规定判决公开,至于公开的内容与方式,一般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予以确定。*比如《食品安全与消费者保护法》第85条、《著作权法》第85条、《专利法》第149条、《反不正当竞争法》第25条、《媒体法》第34条、《葡萄酒法》第57条以及《电信法》第110条等,但是公开的条件各不相同,比如,有的是可以公开而非应当公开,有的以当事人申请作为前提,有的要求多次构成某特定犯罪,等等。由于此类判决所涉行为可能触及经济领域的公众利益或在未来仍存在危害影响,因此当事人的姓名有可能出现在被公开的内容之中。此外,私自公布未经匿名化处理的刑事判决还可能触犯刑法。奥地利《刑法》第113条规定,以使第三人知晓的方式指责犯罪人的已服刑完毕的犯罪行为的,处三个月以下自由刑或者180日额以下的罚金刑。该法条的立法目的就在于保护犯罪人回归社会,因此,学界甚至有观点认为,即使只是“事实性”地提及,也应当构成该罪。*Frank Hpfel/Eckart Ratz (Hrsg.), Wiener Kommentar zum Strafgesetzbuch, 2. Auflage, 3. Band, § 113. 但是,这一观点在司法实践中并未得以采纳。
广义的裁判文书公开分为三种,第一种是法院主动发布所有判决(狭义的裁判文书公开),第二种是部门法规定的作为附加刑或特别措施的判决公布,第三种是其他组织或个人私自公布裁判文书。在德语国家,由于存在联邦法院与州法院“分而治之”的局面,因此不存在全国统一的裁判文书网,一些州法院也没有公布裁判文书。但是,那些公开裁判文书的法院,依据现有的法律规定与实践中形成的共识,除了第二种情况之外,在公开时都对包括姓名在内的个人信息进行隐匿化处理,并同样要求其他组织或个人在公布裁判文书时遵守这一规则。此外,对于狭义的裁判文书公开,德国学界还有着较为深入的理论研究,并存在一定的学术争议。
四、德国裁判文书公开的学理与争议
根据德国联邦行政法院的前述判决,裁判文书公开义务源自法治国家信条、司法保障义务、民主信条和权力分立原则——法院的判决具化了法律规定,进一步构成了法(Recht),因此公布裁判文书与公布法律有相似的意义,能够保障民众的预见可能;在民主国家中,包括法院判决在内的公权力都应当接受公众的批评,某些不被公众认可的判决被公开后能够引起公众的讨论,并推动议会修改法律,这也是法院对法律发展作出的贡献;公布判决可能引起学术讨论,推动法的发展;此外,裁判文书公开义务还以审判公开与宣判公开的程序法指导原则作为法理基础,但超越了这一原则。*同前引〔4〕。归纳而言,裁判文书公开的根本依据是西方国家所信奉的宪政原则,直接依据是程序公开的法律原则。这一判决是在考察了诸多理论学说之后所作出的,是德国主流学说的集中与提炼,当然也代表着学界的通说。
该判决还正式确立了裁判文书匿名公开制,理由是防止对人格权的侵犯。在学术界,匿名公开也是通说,人格权保护同样是其主要论据。人格权(Persö nlichkeitsrecht),是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所规定的宪法权利——“人人有权自由施展其人格”,并与第1条规定的人的尊严(Würde des Menschen)相关联。通过法院的一系列判决,该权利的外延十分广泛,学界将其总结为自主确定权(性自主、信息自主等)、自主展示权(姓名、肖像、话语等)、自主保护权(隐私等)三个主要方面。*Mario Martini, Das allgemeine Persönlichkeitsrecht im Spiegel der jüngeren Rechtsprech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in:Juristische Arbeitsbl?tter, 2009, S. 840-842.同时,德国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了“领域理论”(Sphärentheorie)*BVerfG, Beschluss vom 31.01.1973 - 2 BvR 454/71 .——私密领域(Intimsphäre)的人格权不可侵犯,私人领域(Privatsphäre)的人格权只有公共利益占据绝对优势时才退让,而社会领域(Sozialsphäre)中的人格权则遵循一般的比例原则。*Wolfgang Steiner, Die Grundlagen der verfassungsrechtlichen Rechtfertigung eines Eingriffs in das allgemeine Persö nlichkeitsrecht, 2014, S. 89-103.在刑事案件中,有观点认为,由于涉及罪责问题,实名公开对人格权的危害格外严重,同时还必须考虑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利益;*Bodo Pieroth , Gerichts ffentlichkeit und Persönlichkeitsschutz : Zur Fragwürdigkeit des § 169 S. 2 GVG, in: Hans-Uwe Erichsen/ Helmut Kollhosser/ Jürgen Welp(Hrsg.), Recht der Persö nlichkeit, 1996, S. 249 - 277.而联邦宪法法院的判决则将犯罪人回归社会的权利直接纳入人格权的范畴。*BVerfG, Urteil vom 05.06.1973 - 1 BvR 536/72.人格权保护说的缺陷在于,人格权这一概念宽泛又抽象,而该学说笼统地认为对人格权的保护不证自明、理所当然,*同前引〔5〕,S. 91.因此对许多问题都没有进行详细阐释。于是,又衍生出了具有补强性质的个人信息保护说,该说立足于《联邦数据保护法》(Bundesdatenschutzgesetz),从实定法的角度论证了匿名制的法律根据,*Brigitta Liebscher, Datenschutz bei der Datenübermittlung im Zivilverfahren, 1994, S. 122 ff.之所以称其为人格权保护说的衍生学说,是因为该法第1条就开宗明义地指出,保护个人信息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护人格权。
当然,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一种较老的观点基于程序公开的原则,主张对民事判决以实名公开为原则、以匿名公开为例外,裁判文书公开应与审判公开保持一致,仅在涉及个人私密、商业秘密、影响个人职业发展等不予公开审理的情况下才实行匿名。*Othmar Jauernigs, Dürfen Prozeßbeteiligte in veröffentlichten Zivilentscheidungen namentlich genannt werden? in: Festschrift für Eduard B?tticher zum 70. Geburtstag , 1969, S. 219-241.可推想,这种观点不会赞同实名公开刑事判决,因为它显然影响了个人职业发展。另一种改良的观点则主张不应绝对匿名化,而应当根据个案类型与情况具体权衡,但这一论者同样承认刑事案件的特殊性,认为仅应对纳粹罪犯等极少数情况予以实名公开。*Gerhard Knerr, Die Namensnennung bei der Publikation gerichtlicher Entscheidungen, JurPC Web-Dok. 73/2004, Abs. 1-54.
五、人权价值: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与犯罪记录制度的首要价值目标
裁判文书公开是我国当前司法改革的一部分,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曾考察了境外国家或地区的相关经验,考察的结果是,英美与港台实行实名公开制,且要求全部判决都须网上公布,欧陆国家则实行匿名公开制,且不要求全部判决都网上公布。*最高人民法院司法改革办公室:《裁判文书公开的域外经验》,《人民法院报》2013年11月22日第5版。最终,最高人民法院选择了前一种模式。这一选择的首要缺陷是忽视了判决对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意义不同,因为判决在英美法系是法源,而在欧陆和中国都不是。但其实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首先了解两种模式背后的价值取向。
在西方国家,裁判文书公开的理论基础无非两个层面:实质上是人民监督限制公权力的宪政理念(包含法治、民主、分权等基本政治原则),形式上是这一理念在法律原则与政府运作中的投射——程序公开与信息公开。实名公开还是匿名公开,这又涉及到另一种价值,即人格权价值。当价值之间存在尖锐矛盾时,立法者需要进行权衡,对其中一种价值优先选择,并适当兼顾其对立价值。在德国,裁判文书匿名制体现出的价值选择非常明确,那就是人格权保护优先于程序公开、优先于人民监督政府,这从德国《基本法》将尊严与人格规定在第1条和第2条就可以明显看出。尤其在刑事案件中,无论是主流通说还是少数派观点,都非常重视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利益,并认识到实名公开与犯罪记录消灭之间的冲突。*同前引〔5〕,S. 312.在这里,裁判文书匿名公开与以保障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为首要价值目标的犯罪记录制度产生了交集。而在英美国家,限制政府的宪政理念更为重要,比如美国《宪法》正文七条全部都是关于权力的分配与限制,为了实现人民对政府的监督,在政府运作中则格外强调信息公开。德国学者也指出,美国强调以民主监督为目的的信息公开甚于当事人的人格权,这与德国是不同的。*同前引〔5〕,S. 548.而且,英美法系长期信奉程序正义优先,因此对程序公开价值优先选择也在情理之中。
由于存在不同的文化环境、历史记忆和法制演变,德国模式或美国模式孰优孰劣不能进行直接的比较。在国际范围内,人权保护由于国际公约的签订而在世界范围内具有普遍性,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作为衡量的标准。程序公开是国际公约中所明确记载的,但是其优先性在人权法层面却无法得到很好的诠释。《世界人权宣言》第10条规定了人人有权获得公开公正的审判,《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1款和《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第1款在此基础上还规定了审判公开与宣判公开。作为基本人权的公正审判权,其理论来源正是英美法中的“法律的正当程序”(due process of law),但是,包括宣判公开在内的程序公开仅仅只是保障这一人权的手段之一,*熊秋红:《解读公正审判权——从刑事司法角度的考察》,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6期。因此,仅作为人权保障手段的程序公开,其价值位阶显然要低一些,不能抵触其他人权价值。同时,裁判文书公开是宣判公开原则的派生,后者本身就非绝对,存在若干例外的情形,前者则具有更大的相对性,必须考量其他的利益。德语国家同样签署了上述国际文件,瑞士甚至在宪法中明文规定了宣判公开,但是在裁判文书公开中均采取了匿名制,原因之一便是宣判公开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程序公开的价值。诚然,裁判文书的网上公开,进一步强化了对公正审判权的保障,但是如果采取实名制,则有可能严重侵害其他人权,这就违反了价值位阶的高低顺序。限制政府的宪政则根本未能直接体现在人权国际公约之中,因为它本身不是人权,同样只能算作通过法律保障人权与防止政府侵犯人权的手段,间接地体现在限制死刑、废除酷刑、程序公开等公约的具体规定之中。同理,宪政价值与人权价值直接对立时,也不应当具备优先性。
如果说英美国家习惯于通过间接方式保障人权,那么德语国家则侧重于对人权的直接保护。人格权是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权在宪法与民法中的体现,*马驹俊,曹治国:《人权视野中的人格权》,载《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6期。德国学界语焉不详且过于宽泛的人格权,可以上升为国际公约所明文规定的具体的人权。人权大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另一类则是《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规定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裁判文书匿名公开制与犯罪记录限制查询制,首要保护的就是公民权利中属于尊严权的隐私权与名誉权,这两项权利由《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和《欧洲人权公约》第8条规定。对于刑事案件,除了公民权利之外,还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应有机会凭其自由选择和接受的工作来谋生的权利”(工作权)、“高等教育应根据成绩,以一切适当方法,对一切人平等开放”(受高等教育权)、“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改善生活权)。服刑完毕的犯罪人,回归社会后仍旧享有工作权、受高等教育权和改善生活权这些基本人权,但是曾经的犯罪记录会成为实现这些权利的巨大障碍,导致他们在求职、求学中面临困境,更难以改善生活水准。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的价值正在于保护这些权利免受剥夺或不被过度限制,而裁判文书匿名公开也旨在捍卫这些基本人权。
综上所述,在制度设计的价值权衡中,英美国家优先选择的程序公开价值,仅仅只是公正审判权的一种保障手段而非基本人权本身,宪政价值也仅是手段性价值而不能与人权直接对立;德语国家优先选择的是对隐私、名誉、工作、受教育、改善生活等基本人权的直接保障,这些人权的价值位阶就普适性角度而言显然要高于宪政与程序公开,因此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可以说,人权价值是裁判文书匿名公开制度与犯罪记录制度共同的首要价值。但必须再次强调的是,人权价值与宪政价值、程序公开价值之间并非择一关系,在优先选择人权价值时必须还要兼顾另外两种价值,比如,裁判文书公开中,法官、诉讼代理人等非当事人的姓名必须公开,公权力部门作为当事人时也应当实名公开,等等,而且当存在重大公共利益且该公共利益处于绝对优势时,该人权价值应存在退让的可能性。
六、制度匹配:裁判文书公开制度与犯罪记录制度的对应规律
如前文所述,英美国家甚至我国香港、台湾地区均要求裁判文书实名上网公开,前者是基于英美法系宪政理念与程序公开优先的价值选择,而后者恐怕只能用邯郸学步来形容了。有意思的是,这些选择实名公开的国家或地区的犯罪记录制度都不完善。台湾地区“警察刑事纪录证明核发条例”虽然规定缓刑、免除执行等情形不记载在良民证上,但是却不存在犯罪记录消灭制度;香港地区《罪犯自新条例》规定的犯罪记录消灭一般仅针对“不超过3个月的监禁或不超过1万元罚款”;英国的《罪犯改造法》中的犯罪记录消灭不包括判处4年以上监禁刑的情形。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建有犯罪数据库,目前存有7700余万美国人的犯罪记录,相当于美国成年人口的三分之一,而且其记载内容极广,逮捕等非判决内容都会被记录,甚至被判无罪、因错抓而被释放也不必然导致数据库信息的自动删除,而信息泄露使得雇主、房东、银行和大学录取部门能够定期查询,导致许多人在就业、求学、租房以及与银行的交往中面临困境。*Gary Fields and John R. Emshwiller, As Arrest Records Rise, Americans Find Consequences Can Last a Lifetime, The Wall Street Journal, August 18, 2014.在犯罪记录消灭制度方面,美国各州的规定各不相同(比如加州刑法第1203.4条等),但其适用对象通常仅是逮捕和轻罪,不包含重罪。需要着重指出的是,在香港、英国和美国,犯罪记录消灭的效果非常有限,一是仅限于普通的社会活动,而且存在大量的例外情形(比如申请某些许可或执照),二是当事人面对法院等国家机关时依然需如实交待并受到前罪的影响。大体来看,这仅相当于德国第一阶段消灭的效果。
这些采取了裁判文书实名公开制的国家或地区,其犯罪记录制度并没有建立或者没有被体系化地完整建立,尤其在犯罪记录消灭的范围与程度上,都远远不及德语国家。这种制度的缺失或缺陷导致了诸多弊端,除了“一时犯错、终身有罪”的标签效应不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外,还有可能导致政治上的被动,比如,2014年香港的“占中”事件中,港府担心“占中”学生留下案底而不愿拘捕学生进行清场,*王欣:《梁振英:是可忍,孰不可忍》,《北京晚报》2014年12月2日第19版。这也是犯罪记录消灭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政治两难。而裁判文书网上实名公开造成了情况的进一步恶化,以实名公开的裁判文书为基础的商业化犯罪记录查询服务比比皆是,使得这些国家或地区本就羸弱的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形同虚设。反观实行裁判文书匿名公开制的德语国家,对于犯罪记录制度都有着全面而细致的规定,尤其是犯罪记录消灭制度,绝大多数犯罪最终都能够实现几近完全的消灭效果,而裁判文书匿名公开也防止了窥私者通过其他方式获取相关信息,使犯罪人能够以毫无污点与毫无顾虑的状态重返社会。行文至此,我们也可以发现一个制度上的对应规律——实行裁判文书匿名公开的国家往往建立有完善的犯罪记录制度,而推崇裁判文书实名公开的国家或地区的犯罪记录制度往往是不健全的。应当说,这也是价值选择不同所造成的制度差异,未将人权价值作为首要价值,就容易忽视刑事案件中犯罪人回归社会的利益,最终造成了犯罪记录制度的不完善。
七、对我国的建议:实行裁判文书匿名公开与建立犯罪记录制度
我国《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人格权在民法中体现为一种与财产权对应的主要权利,在刑法中也是侮辱罪、诽谤罪等所保护的法益。我国目前司法改革所推动的裁判文书网上公开,其直接目的当然是通过公开透明的程序手段促进审判公正并树立司法公信力,但绝不可忘记的是,司法公正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权。通过侵犯人权的方式维护司法公正,是本末倒置、得不偿失的。在那些采取裁判实名公开的国家或地区,当事人隐私遭受侵犯、罪犯无法回归社会的问题日益凸显,民间的反对呼声也日渐高涨,实不应当成为我国的效仿对象。我们应学习德语国家——在价值权衡中,以人权保护为优先,并兼顾程序公开与限制政府;在制度设计中,实行裁判文书匿名公开制,并建立完善的犯罪记录制度。若此,经常遭受美国人权指责的中国,至少能在刑满释放人员的人权待遇上比美国更有底气;同时,我国已经建立了全国统一的裁判文书网,要求所有法院公布判决,这在程序公开方面又远远走在德语国家前面。“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方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最终实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制度超越。
对我国而言,当务之急是对公开的裁判文书实行匿名处理,否则越往后修改成本就越高,实名公开造成的不良影响就越大。目前,我国已经呈现出裁判文书信息扩散化的趋势,私人建立的判决数据库开始出现,*比如openlaw.cn和www.itslaw.com.可以预见的是,类似美国、香港的商业化犯罪记录信息库也必将出现。随着此类网站的普及,越来越多的人将了解这一门槛极低的窥私手段,特别在职场中,将成为雇主筛选求职者的一大法宝。同时,立法应规定,私人未处理个人信息而公布裁判文书的,构成民事侵权,以防止有人以此方式恶意侵犯他人隐私与名誉。对于民事判决与行政判决,可以规定适当的例外情形,比如涉及公共重大利益时。但是对于刑事案件,是否可以设置例外?一些特殊情况,比如经过媒体报道而被广为人知的案件,或者关乎重大公共利益的案件,实名公布是否可行?德国对刑事案件是绝对匿名公开,对于那些经过媒体报道而受到普遍关注的案件——无论是涉及纳粹言论被判有罪的托本案*BGH, Urteil vom 12.12.2000 - 1 StR 184/00 - .,还是被控受贿但被判无罪的前总统武尔夫案*LG Hannover, Urteil vom 27.2.2014 · Az. 40 KLs 6/13.——法院在其公布的裁判文书中同样隐匿去了被告人的真实姓名。笔者也认为对于刑事案件不应当设置例外情形,一是因为媒体报道已经保证了公众对此类案件的知情权,二是因为制度实施成本高,不如采取“一刀切”的全部匿名。
接下来应当尽快建立犯罪记录制度,尤其是犯罪记录查询制度与犯罪记录消灭制度,具体的制度设计思路前文已经有所介绍。从整体的价值取向看,犯罪记录制度与裁判文书匿名公开制度是有一致性的,但在具体的规则设置上还必须考虑二者之间的兼容。对于刑事案件,还涉及单位犯罪这一问题。德国民法与公法均承认法人的人格,但刑法不承认法人人格,因此单位无法成为犯罪的主体。一方面,德国《营业法》(Gewerbeordnung)规定了营业中央登记册(Gewerbezentralregister),根据第149条第4款,当涉及外国黑工、截留侵占劳务报酬等犯罪时,经营单位将被记录在该登记册中,该法同样规定了完善的查询制度与消灭制度;另一方面,即便是在此类应被记录入营业中央登记册的案件,在公布裁判文书时也将所涉单位的名称进行了匿名处理。*BGH, Urteil vom16.4.2014 -1StR516/13-.我国刑法是有单位犯罪的,笔者认为,我国可以单独设立单位犯罪信息库,当单位是犯罪主体时,无论是单罚还是双罚,自然人的犯罪信息被记载入犯罪人员信息库,单位的犯罪信息被记载入单位犯罪信息库,两者可以实施相似却又不同的查询与消灭制度。在此时,可以考虑裁判文书实名公开的可能性,对于一些涉及重大公共利益或者可能造成后续影响的单位犯罪案件,在公布裁判文书时,对自然人予以匿名,对单位予以实名。
作者简介:周子实,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外国与国际刑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