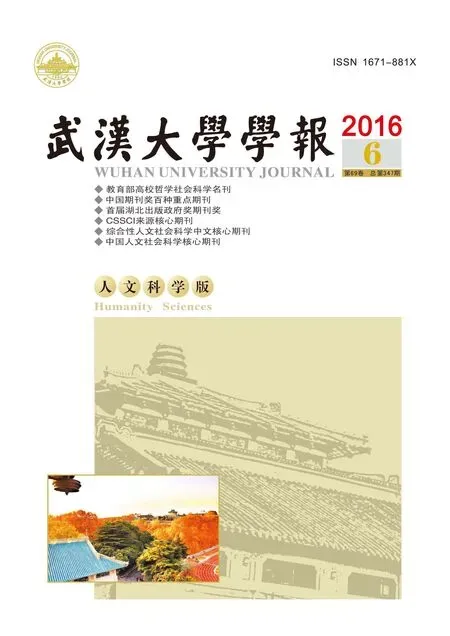亦学亦政: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论争——兼论民国政治学的学术谱系
阎书钦
亦学亦政: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论争
——兼论民国政治学的学术谱系
阎书钦
民国时期为中国政治学研究范式之重要形成期。由于此学科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联,各派论者均致力于相关论著的编撰,形成欧美派、国民党派、马克思主义派三种论述体系。欧美派学者承欧美余绪,注重运用欧美科学实证方法,构建起科学国家学研究范式。国民党派学者则将民生史观与欧美研究范式相结合,构建起适应国民党统治需要的理论体系。而马克思主义派学者运用唯物史观及其阶级分析方法,构建起革命式话语体系。由此而言,政治改良论与政治革命论之分野成为民国政治理论的分水岭。
民国时期; 政治学; 研究范式; 国家; 主权
政治学为民国显学,为各派学者共同关注,各种论著的涌现如雨后春笋。这缘于政治学在民国时期所富有的社会实践性。民国时期变动不居、矛盾激烈的政治局势,导致此学科在时人眼中有着比其他学科更独特的功利性价值。同时,就其学术方面言,民国时期亦为中国政治学之发轫期。中国政治学虽兴起于清末,但真正形成系统的研究范式则在民国时期*本文主要讨论民国时期政治学研究范式问题。所谓范式(Paradigm),指某门学科的研究模式及根本问题,大致包括该学科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或领域、研究方法等问题。具体就政治学而言,所谓研究范式主要指政治学的学科性质、研究对象或领域、研究方法等研究模式,以及政治与国家概念、作为国家研究核心论题的主权等政治学根本问题,有别于国家立法、政治制度、行政运作、国际法与国际关系、政治思想等政治学专题或专门研究。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论述主要体现于当时各种政治学概论论著中。对于民国时期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论述的系统梳理,目前学界相关研究较为薄弱。最具代表性的研究,当属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七)》(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尤其此书第八章《现代政治学谱系中的清华政治学》对民国时期欧美派学者和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讨论作了一定程度的梳理。但由于其分析以清华政治学者为中心,因而研究视野较窄,未对民国时期大量政治学论著进行全面收集、整理,尤其忽略了国民党派学者相关论著。而且,孙宏云未关注到美国实用主义理论对欧美派和国民党派政治理论的巨大影响。王冠中《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初建探析》(载《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3期)试图梳理民国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学科构建问题,但此文仅对恽代英《政治学概论》、邓初民《政治科学大纲》、秦明《政治学概论》、高振清《新政治学大纲》、傅宇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内容作了简要摘编与归纳,不仅对同时期诸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论著收集不全,且分析亦欠深入,未结合民国时期各派政治学学科构建的总体背景对这些论著所涉及的关于政治学研究范式的核心观点作深入分析与解读,同时,此文未注意到撰写《新政治学大纲》的“高振清”系高尔松的笔名。。民国学界所讨论的政治学研究范式,一改清末仅以日本为学术资源地之状况,而由欧美学界直接引入。然而,作为中国新学术资源地的欧美政治学界,亦非铁板一块。盛行自由主义的英国既与盛行国家主义的德国不同,美国学术与欧洲学术亦有相当差异,同时,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又异军突起。民国学者基于不同学术背景与政治立场,面对欧美相异的政治学理论,自然取舍各异。故通过梳理民国时期各种政治学论著,系统清理民国学界基于各自政治立场而对政治学研究范式所具的不同取向,应为一值得重视的学术问题。
一、民国政治学的流派与科学国家学观念的歧异
政治学强烈的社会实践性导致两方面结果:一方面,此学科较早即引起中国学界重视,在清末即出现若干国人自撰政治学论著*杨廷栋分别于1902年11月和1908年9月出版的《政治学教科书》和《法制理财教科书·政治学》系较早由国人自撰的政治学论著。,民国成立后,政治学论著更种类繁多;另一方面,各政治派别均将政治学视作政治斗争工具,大力阐发符合自身政治目的的政治学理论,导致民国各种政治学论著政治倾向泾渭分明。
单就学术研究而言,致力于引介欧美政治学理论(虽广义欧美政治学理论亦可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但笔者此处所言欧美政治学理论主要指西欧、北美等地学界阐发的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的欧美派学者显然构成民国政治学界中坚力量。此派学者主要以教学和科研为职事,其理论倾向虽有不同,但均以学术为目的,而与现实政治保持一定距离。此派论著中,1923年2月张慰慈撰《政治学大纲》、1930年2月高一涵撰《政治学纲要》极具示范作用。前者被诸多政治学论著广泛征引,如张天百于1928年12月所编知识普及读物《政治学纲要》即大段引用此书内容;后者出版后曾畅销一时,高一涵在《三版序》中即称,“这本书居然在一个月内消了两版,真是一件意外的事”*高一涵:《政治学纲要》,神州国光社1931年,第1页。。不过,《政治学大纲》实为张慰慈与高一涵在北京大学的合作成果*张慰慈在序言中称,此书编写缘起于其所编讲义。他于1917年始任北大教授,因讲课所需而编写讲义。他随编随将此讲义交于1918年始任北大编译委员会编译委员的高一涵修改。高一涵亦于1921年在北京法政专门学校和中国大学讲授政治学,对此讲义大加修订与增补。1922年暑假,他将两人讲义合并整理,成此书稿。参见张慰慈:《政治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26年,第1~2页。。且此书主要引述美国学者基特尔(R.G.Gettell)在康涅狄格州三一学院任教时出版的《政治学导论》(IntroductiontoPoliticalScience,1910)内容*杨幼炯称,“张氏此书仅为Gettell氏原著之编译,其文字清畅是其所长,但未能网罗众说,吸收西洋最新之政治学原理。”参见杨幼炯:《当代中国政治学》,胜利出版公司1947年,第42页。。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任上海法政大学(1929年更名为上海法政学院)、中国公学等校教授的高一涵以《政治学大纲》为基础,并参考美国伊利诺斯大学教授高纳(J.W.Garner)《政治科学与政府》(PoliticalScienceandGovernment,1928)新撰相当内容,出版《政治学纲要》*高一涵在《三版序》中介绍,此书有一两章与《政治学大纲》“大同小异”,“好在张先生在序文中已经表明过,说该书有些地方是我们两人合编的”。参见高一涵:《政治学纲要》,神州国光社1931年,第1页。杨幼炯称,高一涵此书多取材于高纳《政治科学与政府》。参见杨幼炯:《当代中国政治学》,第42~43页。。由在中国学界影响甚大的《政治学大纲》和《政治学纲要》主要参考美国学者基特尔和高纳著作来看,美国政治学研究范式对中国学界影响不容小觑*据孙宏云研究,基特尔《政治学导论》早期曾被清华大学、南开大学采用为政治学概论教材,之后,高纳《政治科学与政府》则被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南开大学等更多院校采用为政治学概论教材。参见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七)》,第144~147页。。实际上,20年代末30年代初为欧美派学者出版政治学著作的高潮期。在此时期,诸学者编撰了不少政治学普及读物。其中,朱采真先后于1929年5月和1930年8月出版的《政治学ABC》和《政治学通论》较有影响。此时期诸多论著系以教学讲义为基础编成,如陈筑山于1928年5月以其北京法政大学、朝阳大学和民国大学(1931年更名为民国学院)讲义为基础出版《最新体系政治学纲要》,任和声于1929年12月以其山东省立民众教育学校讲义为基础出版《政治学概论》,李剑农于1934年11月以其武汉大学讲义为基础出版《政治学概论》,王希和(河南大学教授)于1936年3月以其河南省政府及绥靖公署公务员学术研究班讲稿为基础出版《政治学要旨》(他又于1947年12月以此为基础出版《政治浅说》)。抗战时期,欧美派学者亦出版不少论著,如先后任广西省立第十一和第五中学、桂林西南商业专科学校校长的廖竞存于1939年1月出版《青年政治读本》,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原清华大学教授陈之迈于1941年4月出版《政治学》,佛学理论家黄忏华于1946年9月出版《政治学荟要》。
从20年代至40年代,国民党各类军事学校编印了不少政治学教材。黄埔军校系统(先后称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材为其大宗,如1926年12月潮州分校教员汪毅撰《政治学概论》、1937年3月该校特别训练班编《政治学概论》、1939年2月陈颐庆撰《政治学教程》、1940年12月杜久与张又新合撰《政治学教程》。柳克述于1938年12月出版的《政治学》亦属黄埔军校教材系统。柳克述编此书时虽任湖北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但他此前曾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且此书作为国民党军事学校战时政治教程出版。此外,重庆陆军大学曾于1944年印行该校政治教员蔡惠群撰《政治学讲义》。这些教材均以灌输国民党政治理论为鹄的。如杜久、张又新《政治学教程》编纂体例即强调“以三民主义为依归,以期思想统一,意志集中”,培养学员“忠党爱国之德性”*熊铭青:《政治教程及教授纲要编纂例言》,载杜久、张又新:《政治学教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40年,第1页。。不过,桂系南宁第四集团军干部政治训练班于1936年4月所印李一尘撰《政治基础知识》对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有所阐述,认为国家是“社会的发展到了私有制度的确立,有剥削者与被剥削者这两个社会阶层对立的阶段中,然后它才发生出来的,也必然发生出来的”*李一尘:《政治基础知识》,1936年,第23页。。
不少国民党党政系统成员亦致力于编撰政治学著作。CC系成员邱培豪和蒋静一先后于1930年1月和1935年6月出版《政治学问答》和《唯生论政治学体系》。邱培豪于20年代末任《湖州月刊》主编,受陈果夫、陈立夫、潘公展等指导。蒋静一自1931年起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工作,在其著自序中称陈立夫《唯生论》对此书影响“甚大”*蒋静一:《唯生论政治学体系》,政治通讯月刊社1935年,第3页。。其他国民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亦编撰不少政治学著作,如时任广东连县县长的黄开山于1932年12月出版《政治学的诸重要问题》,曾任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的邹敬芳分别于1931年10月和1933年4月出版《政治学概论》和《政治学原理》,先后任湖南省教育厅图书审查股股长、湖南省民政厅视察的马璧于1940年8月撰成《三民主义的政治学》,时任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和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会委员的陈顾远于1948年2月出版《政治学概要》。这些论著多强调以三民主义为理论指针。马璧在序言中即表示,其书“要想把中山先生的政治学说深切著明的组成有科学系统的书籍,有别于其他立场的政治学”*马璧:《三民主义的政治学》,世界书局1946年,第1页。。
诸亲国民党学者所撰政治学著作虽不像国民党政治理论宣传者那样以三民主义意识形态挂帅,但字里行间透露出明确的政治倾向。萨孟武于1928年任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编辑部主任,1930年后长期担任中央政治学校教授,40年代后期任广州中山大学法学院院长。其政治学著作主要有《三民主义政治学》(1929年7月初版)、《政治学概论》(1932年6月初版)、《政治学与比较宪法》(1936年8月初版)、《政治学原理》(1944年4月初版)、《政治学新论》(1948年7月初版)等。杨幼炯在20年代末以后历任中央大学和上海法政学院、中国公学、暨南大学教授,于1935年5月出版《政治学纲要》。他曾申明,“自信始终以书生致力于党的文化宣传,未尝间断”*杨幼炯:《当代中国政治学》,第68页。。罗敦伟虽在三四十年代大力宣扬统制经济和社会主义,但其政治观念倾向于国民党。1931年4月,时在北平大学讲授政治学课程的罗敦伟出版《社会主义政治学》。他试图以三民主义阐述“社会主义”政治理论,在弁言中表示自己“自始至终是真正的三民主义者”,“用民生史观立场研究社会主义政治理论,敢说是一件甚要的工作”*罗敦伟:《社会主义政治学》,北华书屋1931年,封面。。北平民国学院教授赵普巨似亦可归入亲国民党学者之列。他与陶希圣关系密切。他于1932年9月出版《政治学概论》,请陶为之作序。陶希圣在序言中称,政治学著作不仅应解答国家问题,还应解答帝国主义与革命问题,“这些问题在流行的政治学书里和传统的学校讲义里得不到解答”*陶希圣:《陶希圣先生序》,载赵普巨:《政治学概论》,立达书局1932年,第2页。。赵普巨与陶一样,深受唯物史观影响。如他认同阶级分析国家观,认为“关于国家本质的解释,此说算是最透彻了”*赵普巨:《政治学概论》,第68页。。此外,亲国民党学者编撰的政治学论著尚有王诗岩于1929年6月出版的《新的政治学》、李圣五任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时于1932年11月出版的《政治学浅说》、虞棠于1933年10月以其广州法学院讲义为基础出版的《新政治学大纲》、桂崇基于1933年12月以其广东大学、中央政治学校讲稿为基础出版的《政治学原理》等。
诸多马克思主义者在艰苦条件下亦致力于政治学著作的编撰,构建起系统的革命式政治学论述体系。此类论者大致包括三类人员:中共理论宣传工作者、曾参加中共后脱党但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人员、虽与中共无组织瓜葛但倾向马克思主义的人员。恽代英在黄埔军校任教期间于1926年9月编印的讲义《政治学概论》系较早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20年代末30年代初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出版的高潮期。陈豹隐(原名陈启修)与高尔松(笔名高希圣、高振清)政治经历相似。他们均曾加入中共,1927年国民党清共后与中共失去联系,但仍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陈豹隐于1929年8月出版的《新政治学》系其于国民党清共后流亡日本期间的作品。高尔松亦因国民党清共一度流亡日本,1929年6月回上海后,以高希圣为笔名,先于1929年出版《现代政治学》,后于1930年12月出版《新政治学大纲》(1932年10月以高振清为笔名再版),两书内容前后相承。实际上,高尔松两书依据其旅居日本期间所见日本大山郁夫撰《政治学》编写*高希圣在此书例言中介绍,《现代政治学》“取材大部分根据日本大山郁夫为普罗列搭利亚特自由大学所编《政治学》一书”。参见高希圣:《现代政治学》,现代书局1929年,第2页。。邓初民虽不像陈豹隐、高尔松曾加入中共,但思想观念却倾向马克思主义。他于30年代初在上海暨南大学等校任教,并参与发起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后于全面抗战时期加入救国会和民盟。1932年10月,他以田原为笔名出版《政治学》。1946年7月,他又出版《新政治学大纲》。此外,1929年11月秦明出版的《政治学概论》、1932年5月傅宇芳出版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1946年3月郑晖出版的《政治生活与政治学读本》亦为重要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著作。秦明力图划清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其他政治学的界限,批评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绝不是站在正确的科学立场出发,里面还充满着鸦片、酒精、麻醉青年的药剂”*秦明:《政治学概论》,南强书局1929年,第79~80页。。周绍张虽30年代初与叶青关系密切,但他于1933年2月出版的《政治学体系》仍受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此书为时在上海辛垦书店工作并任中共上海沪东文化支部书记的杨伯恺主持编撰的“体系”丛书之一种*参见杨伯恺:《“体系”序言》,载周绍张:《政治学体系》,辛垦书店1933年,第1~2页。。
自清末迄民国,中国学界承欧美余绪,多将国家视作政治学研究对象*孙宏云所谓“从国家学到实证主义政治学”命题,似不符合民国时期政治学研究范式的实情。孙宏云认为,清华政治学者受美国行政研究的影响,摒弃欧洲“玄理的国家论”,注重政府实际运作的行政问题研究。钱端升主张政治学应研究政府起源与发展、政府组织与职能、政治活动与原动力、国际关系等问题。浦薛凤主张政治学应研究政治思想及政治制度、国际关系、宪法等政治现象问题。参见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一九二六至一九三七)》,第351~360页。实际上,作为政治学根本研究对象的国家问题与上述政治学具体问题研究,均为政治学并行的研究领域,后者均可纳入国家研究范畴。陈之迈即言,现代政治活动研究多包含于国家范围之内。有人认为政治学的研究范围应更宽泛,应以一切人类政治活动为研究对象,人类社会各种政治活动并不限于国家范围。而现代的国家范围极宽泛,许多以前在国家范围以外的事情现在都可归纳于国家之中。所以,“政治学就是国家学”一语“就现在的情形说来是不错的”。参见陈之迈:《政治学》,正中书局1947年,第2~3页。。如杨廷栋于1902年11月表示,“凡考求政治学者,须先知国家为何物”*杨廷栋:《政治学教科书》,作新社1902年,第3页。。1933年2月,桂崇基亦表示,“政治学是研究一切关于国家现象的科学”*桂崇基:《政治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33年,第1页。。关于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表述,对民国学界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美国学者基特尔和高纳。如前所述,张慰慈《政治学大纲》主要依据基特尔《政治学导论》,高一涵《政治学纲要》一些内容则依据高纳《政治科学与政府》撰写。之后,1933年11月,孙一中将基特尔任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时出版的《政治学》(PoliticalScience,1933)译为中文出版。1933年10月和1934年9月,顾敦鍒和孙寒冰亦先后将高纳《政治科学与政府》译为中文出版。顾敦鍒称高纳此书“是一部完备与健全的政治科学书”*顾敦鍒:《译序》,载高纳:《政治学大纲》(Politic Science and Government),顾敦鍒译,世界书局1933年,第1页。。基特尔和高纳均将国家视作政治学研究对象。基特尔表示,“政治学的定义简单的说起来,就是国家的科学(Science of state)”*基特尔:《政治学》,孙一中译,大东书局1933年,第1页。。高纳亦认为,“政治科学是以国家为研究的出发点,亦以国家为研究的终止点”*迦纳:《政治科学与政府》第1册,孙寒冰译,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7页。。1939年2月,陈颐庆即引基特尔所言“政治学者,国家之科学也”,高纳所言“政治学是始于国家,终于国家的学问”,认为国家是政治学研究的主要内容*陈颐庆:《政治学教程》,黄埔出版社1939年,第1~2页。。
在政治学研究对象问题上,中国学界并未墨守西方成规,而是提出了诸多自己的见解。这呈现出两种观念,一是在承认国家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将诸多其他政治领域纳入政治学研究对象范畴;二是不少学者,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对仅以国家为政治学研究对象的论点提出质疑。张慰慈受基特尔影响提出,政治学一方面应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同时亦应研究人们在政治社会中的关系及政治心理与动作。他于1923年2月表示,一方面,国家是政治学的研究“题目”,另一方面,政治学应研究人们在政治社会中的关系与心理*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第2、4页。。1930年4月,他又将人们的政治关系与心理称作政治关系与动作,认为政治学所研究的“人群的现象”属于“人与人在社会上所发生的关系中的一种”,“政治学的目的,就是研究人与人在这种有政治组织的社会中的一切动作”*张慰慈:《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1、4页。。诸多学者发挥张慰慈所言政治学应研究人们在政治社会中的关系,提出政治组织亦为政治学重要研究内容。1932年9月,赵普巨认为,政治学研究的政治现象主要是国家,人们在政治生活中的相互关系和政治组织是其中要义。政治学要研究政府的体制、组织和功能,人民与政治的关系,国家与国家的关系*赵普巨:《政治学概论》,第14页。。1932年11月,李圣五认为,政治学研究对象不仅包括国家,还包括人们在政治社会中的相互关系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组织,政治学应研究“政治组织的形式、作用与发展”*李圣五:《政治学浅说》,商务印书馆1932年,第4页。。国民党派学者较关注国民党政府的社会控制与政党专政问题,所以,他们提出政府与政党问题应为政治学的研究重点。1931年10月,邹敬芳将政党专政与政府运作方式视作政治学研究重点,提出政府现象是政治现象的中心,而政党是政府的原动力*邹敬芳:《政治学概论》,会文堂新记书局1935年,第1页。。1937年3月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所编教材亦强调政府与政党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认为“国家各机关的组织与职权,人民对于国家的权利与义务,政党的结构与活动,以及国家与国家间的关系,都是政治学所不可忽略的现象或事实”*《政治学概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1937年,第5~6页。。
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对仅将政治学研究对象确定为国家的论点提出质疑。他们多强调政治学应以研究社会阶级性为中心,重点研究政党与革命问题。恽代英于1926年9月强调政治和政治学的阶级性,表示“政治学是什么?自有历史(有阶级制度)以来,政治总是统治阶级(压迫阶级)之治术”*恽代英:《政治学概论》,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宣传科1926年,第2页。。1932年5月,傅宇芳强调,仅以国家为政治学研究对象未把握政治学的实质,政治学的研究对象应为“阶级的统治权力”*傅宇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长城书店1932年,第20页。。1932年10月,邓初民感到,国家范畴虽可包括政权或政府,却难以包括政党与革命。他在《政治学》自序中介绍,自己撰写此书前后修改之处很多,“原来的讲义,是以国家为政治学研究的对象的,把政府、政党等等,都一起包括在国家中,但后来觉得这是不大妥当的,便把它改了,——改为政治学所研究的对象是政治现象”*田原:《政治学》,新时代出版社1938年,第1页。。他解释,政党、革命“决不能拿国家这一概念来包括”*田原:《政治学》,第5~6页。。
民国政治学界深受欧美科学实证论影响*中国学界迻译外国诸种政治学论著均大量阐述政治学科学性问题。如吴友三等于1932年8月译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政治学教授季尔克立斯(R.N.Gilchrist)《政治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Science,1921)将政治学称为“Political Science”,而非“Politics”,含有将政治学归于“科学”之意。参见季尔克立斯:《政治学原理》,吴友三、缪元新、王元照译,孙寒冰校,黎明书局1935年,第1~2页。。无论欧美派学者,还是国民党与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均认可政治学科学性,承认政治学是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国家等政治现象的科学。1923年2月,张慰慈即申明,政治学是“科学的国家知识”*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第10~11页。。1946年9月,黄忏华亦注意到,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名称“现在已经得世人底公认,用他称呼各种拿国家做研究中心底学问”*黄忏华:《政治学荟要》上册,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0~11页。。大家普遍强调政治学的任务为认知国家等政治现象的因果律。1930年2月,高一涵分析,人类社会现象存在因果律,政治学等社会科学即奠基于这种社会的因果律,“在那有因果关系的自然现象上,既然能够建设起来自然科学,那么,在这有因果关系的社会现象上,又何以不能建设起来社会科学呢”*高一涵:《政治学纲要》,第7~8页。。国民党派学者亦如是说。马璧于1940年8月表示,“政治学是一种社会科学”,所谓科学,乃是“有系统、有条理的学问,也就是研究对象的因果律”*马璧:《三民主义的政治学》,第20页。。1947年1月,杨幼炯亦指出,政治学的科学性在于考究政治现象“受定律所支配的连续性”和“因果关系”,从而寻求政治现象的“公律和原则”*杨幼炯:《当代中国政治学》,第1~2页。。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同样强调政治学的科学性。1932年10月,邓初民在《政治学》自序中称,“区区之意,即想以严格的科学的立场,在目前的政治学界,做一番‘除旧布新’的工作,也就是‘站在促进中国科学的进展而建设一种科学的政治学底见地上’来写这本书”*田原:《政治学》,第2~3页。。不过,他们从唯物论出发,更强调政治学的客观性,认为政治学的科学性体现于对政治现象的客观规律的探究。邓初民在《政治学》中即强调,政治学的科学性源于政治现象及蕴含于其中的因果律的客观性,“科学的对象,是离开研究者的主观而独立的客观的东西。对象之中的因果律,也是客观的东西。科学者的职责,就在于认识这种客观的对象,发现它的因果律”*田原:《政治学》,第7页。。
虽然大家一致认可政治学的科学性,但对于用以研究政治学的科学方法的理解却有相当差异。1923年2月,张慰慈提出,政治学研究应并用比较的、实验的、历史的、心理学的方法*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第30页。。1935年5月,杨幼炯认为,政治学研究应运用观察、归纳、演绎与比较等方法,“事实的观察,最为重要,尤应以事实为基础,由归纳法求到结果,再以这结果为前提,而行演绎法,以取出他的精神”*杨幼炯:《政治学纲要》,中华书局1938年,第6~7页。。美国实用主义方法受到欧美派与国民党派学者的共同推崇。他们均强调,政治原理与政治制度均为假定,判断其是否具有价值、是否为真理的标准全在其实际效果。较早从政治学角度介绍此种研究方法者,当属张慰慈。他于1923年2月强调,政治学原理是用以解释“政治社会中万事万物现象”、应付环境的人造假说,亦是“做救济某种环境的工具”。同时,各种政治制度应通过社会实验证明其价值,“凡国家公布一种新法律,发明一种新制度,或决定一种新政策,无一日不在随时试用,随时修正之中。要想判断他的利弊,必定要看试验的结果如何”*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第10~11、24~26页。。1929年5月,朱采真亦认为,虽然政治学的事项不能像自然科学那样在实验室求得解决,但无论哪种政治制度,在施行过程中,处处都有受到试验的机会。实验的方法就是根据试验所得的效果说明它的价值*朱采真:《政治学ABC》,世界书局1929年,第10~11页。。国民党派学者亦多接受实用主义理论。汪毅于1926年12月引用张慰慈《政治学大纲》所论实用主义方法,认为政治学原理是“人造的假设”和“应付环境的一种工具”*汪毅:《政治学概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潮州分校1926年,第8页。。1937年3月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所编教材亦认为实验方法重要,表示“一种政治制度在试验中得到最好的效果的,就是合理的有价值的制度”*《政治学概论》,第14~15页。。1938年12月,柳克述亦赞赏实验研究方法,认为“现在有一部分学者应用这个方法去研究政治,他们的前途,必大有希望”*柳克述:《政治学》,青年书店1938年,第7页。。然而,实用主义方法受到马克思主义学者的坚决否定。如邓初民于1932年10月以唯物论为视角指出了实用主义方法的非客观性,认为人的观念是对认识对象的反映,观念正确与否在于它是否与认识对象一致,“但实验主义,却主张观念的真理性并不在于它与对象一致,而在于它所显出的效用”*田原:《政治学》,第22~23页。。
是否并用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及其阶级分析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学理论与其他政治学理论的分水岭。马克思主义派学者不仅阐明了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政治学的重要性,还强调政治学研究必须采用唯物史观及其阶级分析方法。1929年11月,秦明一方面申明政治学必须运用“唯物辩证法”对政治现象“加以正确的观察或说明”,另一方面,又分析了社会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认为包括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在内的“生产关系”的总和是“社会的基础”;政治、法律等都是建立于社会基础之上的“社会建筑”。他同时强调,正确的政治观必须基于阶级分析方法,一些“支配阶级”的御用学者“把一切有利于支配阶级”的社会制度“永久化,绝对化”,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理论只是“含有麻醉意味的毒酒”*秦明:《政治学概论》,第2~3、3~4、14~15页。。1932年5月,傅宇芳强调,政治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应该是“唯物辩证法”,政治现象“是充满了辩证法的”,同时,“指导人类这种政治生活的基本观点,不能不是唯物论的”。而且,政治学应以“史的唯物论”为研究方法,此种理论以客观的社会经济现象为基础,重点分析阶级剥削与对立*傅宇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第29~30、38~39页。。邓初民于1932年10月将唯物辩证法称作“现实论理学”*1946年7月,邓初民直接把“现实论理学”称作 “唯物辩证法”,认为此种政治学研究方法包括五个方面:从经济生活的关系去说明政治形态;从社会矛盾、社会斗争中把握各种政治现象的发生、发展和变迁;全面观察和分析各种政治要素的关联形态,以构建统一的政治“形像”;从研究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提出政治的普遍发展法则;依据研究所得的具体政治原理,进行政治生活实践。参见邓初民:《新政治学大纲》,生活书店1946年,第20~21页。,认为这是“政治学上的唯一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他介绍,此种研究方法立足政治整体性,在全面分析国家、政权、政府、政党、革命等政治材料的基础上,普遍研究各种政治要素;以运动和“内部对立”(矛盾)的观念,研究政治的发展法则。他又指出,“现实论理学”立足“现实的经济生活关系”分析“政治形态”,而由社会经济关系导致的社会阶级关系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视角,“我们如果考察到那一个阶级为着那一种目的去使用国家的权力,就能够理解到那种政治形态的构造和机能,一切都是由社会的阶级关系规定着”*田原:《政治学》,第25~29、33页。。
而国民党派学者罗敦伟、马璧、蔡惠群等虽认可唯物辩证法,却不同意唯物史观。1931年4月,罗敦伟试图将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相分割。他承认唯物辩证法的合理性,认为“马克斯最大的功绩并不是别的,而是新的研究方法之发现,辩证法的唯物论成立以来,社会科学的基础,也就完全改变了”。但他反对唯物史观的阶级分析方法。他申明,其所言“社会主义政治学”不同于站在无产阶级立场说话的“无产阶级政治学”,并不具有阶级性*罗敦伟:《社会主义政治学》,北华书屋1931年,第7~8、10页。。1940年8月,马璧将唯物辩证法称作“现实论理学”,认为“现实论理学的方法的名词,不是狭义的社会主义学者所独占的”,“这当然是政治学进一步的研究方法”。但他不同意唯物史观论者“认为经济的关系决定政治的构造”观点,提出决定政治构造的并非经济,而是知识阶级,“有资产的人,不一定可以操纵政治,只是有智识的人才可以操纵政治”*马璧:《三民主义的政治学》,第32~33页。。1944年,蔡惠群亦将“唯物辩证法”称为“现实论理学”,认为“它在学理上已成立为一个无从否认的方法论”。但他反对阶级分析方法,认为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而非“代表一部分人的利益”*蔡惠群:《政治学讲义》,陆军大学1944年,第20、72页。。
各派学者对政治学研究对象、学科性质、研究方法的诠释可谓同中有异,异中又有同。欧美派与国民党派学者多认可国家为政治学研究对象,而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强调社会阶级、政党与革命等问题亦为政治学重要研究内容。欧美派与国民党派学者多强调政治学的科学性在于分析政治现象的因果规律,而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注重认识主体的认知客观性。欧美派与国民党派学者均追捧实用主义等欧美科学实证方法,而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强调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方法的重要。政治学理念的相异,隐含着各派学者不同的政治立场与动机。
二、政治与国家概念认知的各异
政治与国家是政治学的两个核心概念。由于其在政治学中地位之重要,民国时期各派学者对政治与国家概念的不同阐释便成为区别各政治学流派的重要标杆,并深切反映出各派学者相异的政治倾向。正如张慰慈所言,“大概一种科学的原理原则差不多都是包括在各该科学内重要名词之中的”。“各种的政治学说、政治学理,也是完全发源于不相同的‘国家’的概念”*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第31页。。
孙中山于1924年3月在《民权主义》演讲中阐释的政治概念影响广泛:“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第254页。不过,各派学者对孙中山此论各异其说。国民党派学者多由此强调政治对于社会及民众的强制管理内涵。1933年10月,虞棠肯定孙中山此论“实为确当不移”,并由此认为,政治组织相对于“普通社会组织”是一种“指导调和及强行的制度”,“现代社会的组织,譬如未成年的孩童,又如不健全的病者,而政治组织是其监护人,又为其医师”*虞棠:《新政治学大纲》,民智书局1933年,第3~4页。。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于1937年3月所编教材由孙中山此论认为,政治具有对民众人身、权力、财产的强制管理性质,“国家成立后,关于人民本身及其事与物的强制管理,叫做政治”。“管理”的对象不限于“民众的事”,亦包括“民众的本身及其共有或私有的物”,“管理”的性质“多少总含有一点强制性”*《政治学概论》,第2~3页。。诸多欧美派学者多据西方学界所下政治定义补充孙中山此论。1929年5月,朱采真认为,孙中山所言管理众人之事,只是对政治概念最广义的解释。而对政治概念狭义的解释,是将政治视作与国家根本活动直接相关的国民和国家机关的行为*朱采真:《政治学ABC》,第1~2页。。1946年9月,黄忏华认为,孙中山此论与伯伦知理所言“政治是统治国家底一切行为,是国家底实际行为”观点相近,其所言“众人”就是国民全体,“众人底事”就是国事*黄忏华:《政治学荟要》上册,第4页。。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指出孙中山此论未揭示政治的阶级对立与斗争本质。1932年2月,傅宇芳指出,“所谓‘管理众人之事’即不外是管理一部份人压迫其他广大群之事情而已。因此,可知这种说法,仅仅是布尔乔亚阶级麻醉普罗阶级的迷语”*傅宇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第9~10页。。1932年10月,邓初民分析,“国家”或“人民”并非“利害一致的整体”或“没有阶级矛盾的和谐体”,“所谓超然于国家与人民之上的‘管理’、‘治理’是绝对不会有的”*田原:《政治学》,第1页。。
各派学者对政治概念的上述分歧源于其对政治现象理解的歧异。而民国学界尤其是马克思主义派与国民党派学者之间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应从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角度解释政治现象。马克思主义派学者认为,政治现象的特征是“强制权力”,而“强制权力”的目的在于经济利益的攫取,这就导致政治的阶级剥削与斗争本质。1929年8月,陈豹隐认为,“人类关于强制权力的生活,就是政治生活”,而政治的核心在于夺取经济利益,“政治生活就是人类关于那些为经济利益的有秩序的取得而存在的强制权力的生活”*陈豹隐:《新政治学》,乐群书店1930年,第7、11页。。由以攫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强制权力,他们阐明了政治的阶级剥削与斗争本质。1932年5月,傅宇芳指出,“政治”二字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奴隶社会,进入阶级对立时代,“所表现出来的概念”。所以,“政治现象,就是阶级对立、阶级斗争的现象”*傅宇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第6、39页。。1932年10月,邓初民指出,我们在探求政治现象“发生、成长、没落之一般的与特殊的规律”时,“必需要论述到阶级,不,必需要以阶级的论述为其出发点”*田原:《政治学》,第35页。。国民党派学者多依据民生史观,从人类生存和共同生活角度理解政治现象。他们反对马克思主义派学者的经济基础决定论,更反对将政治现象的本质视作阶级矛盾与斗争。马璧于1940年8月认为,安全生存和共同生活是人类在复杂社会中需要解决的两个重要问题,“政治的目标就是人类在一定的社会范围里,发生合理的组织与活动,以求达到安全生存和共同生活的境地”。他反对以经济基础和阶级斗争解释政治现象,认为“有一部份的见解,以为政治便是阶级与阶级的矛盾,政治关系为经济关系所决定。这些论调便是布尔塞维克的口吻,这是把政治看做经济的附庸,也失去了政治的意义”*马璧:《三民主义的政治学》,第1、4页。。1948年2月,陈顾远亦强调,政治的目的在于为人类求生存,谋利益,“政治之目的即系为大众谋利益,至少亦须与最大多数人之利益相调和,而解决其求生存问题”,阶级斗争对于政治的影响“亦不过社会现象上之病态,当然不足说明社会现象或政治现象之全体”*陈顾远:《政治学概要》,昌明书屋1948年,第2、6~7页。。
关于国家概念,西方学界有国家三要素说与四要素说之别,或以为国家系由领土、人民、主权三要素构成的政治团体,或在三要素之外,加上政府要素*不过,民国学界所译西书多持四要素说。孙一中译美国学者基特尔《政治学》即申明,国家概念包括物质的元素、主权两大要素。物质的元素包括领土和人民;主权则包括组织和统一。所谓组织,指强迫人民服从的政府组织。参见基特尔:《政治学》,孙一中译,大东书局1933年,第11、14页。吴友三等译印度学者季尔克立斯《政治学原理》亦认为国家包括人群(人民)、一个固定居所(领土)、一个统一人民的组织(政府)、对内的最高性及对外的独立性(主权)四个要素。参见季尔克立斯:《政治学原理》,吴友三、缪元新、王元照译,孙寒冰校,黎明书局1935年,第24页。。对于应采三要素说还是四要素说,欧美派学者并无定论,有采三要素说者,亦有采四要素说者。朱采真、任和声、李剑农、陈之迈等采三要素说。如朱采真于1930年8月认为,“国家的成立须要具备下列三种要素:(一)人民,(二)领土,(三)统治权。所谓统治权,在政治学上常常称做主权”*朱采真:《政治学通论》,世界书局1930年,第71页。。而张慰慈、倪竞存、张天百、王希和、廖竞存、黄忏华等则采四要素说。如张慰慈于1923年2月认为,国家有四种要素:有为公共目的而活动的一群人民;占有地球上一定的土地;有表示和执行公共意志的机关;只受一个最高统治权的支配。简言之,就是土地、人民、组织和主权*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第36页。。相较于欧美派学者,汪毅、王诗岩、萨孟武、邱培豪、李圣五、杜久、张又新、蔡惠群、陈顾远等国民党派学者多宣扬国家四要素说。如萨孟武于1936年8月将国家解释为“大凡一群人民定住于同一领土之上,利用统治组织,以行使独立最高的权力,就构成一个国家”*萨孟武:《政治学与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1938年,第10页。。蔡惠群于1944年亦认为,“国家是人类的政治组合物,具备着精神和物质的两种要素,即人民、土地、主权与政府组织是也”*蔡惠群:《政治学讲义》,第27~28页。。他们之所以采四要素说,乃出于对政府社会功能的关注。李圣五于1932年11月即强调,一个国家“必须有政治组织,即必须有个政府以发抒实施人民之意志,决定公共的政策,并且对外以代表国家。假若没有政府,即无共同的意志与行动,仅属乌合之众而已”*李圣五:《政治学浅说》,第7页。。1940年12月,杜久、张又新亦强调,“从近代历史来看,有主权而没有政府,往往会成个有名无实的国家”*杜久、张又新:《政治学教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1940年,第24~25页。。
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从国家阶级性与帝国主义侵略角度,批评国家三要素说或四要素说。秦明于1929年11月指出,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等论著“历数土地、人民、主权等国家的要素”所下国家定义“究未能显示国家之本质”。例如,“封建国家”并无所谓“人民”,只有作为土地占有者的国王和贵族以及作为非土地占有者的农奴*秦明:《政治学概论》,第6~7页。。1932年2月,傅宇芳表示,一些不理解阶级国家论的政治学者复述欧美政治学者的意见,将人民、土地、政府、主权等视作国家构成的基本要素,不了解“国家存在的意义是统治阶级用以压迫或治服被榨取阶级”的事实*傅宇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第104页。。1932年10月,邓初民从帝国主义侵略角度指出,土地很难说是构成国家的必要要素,因为列强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即造成中国领土的不完整,“请问中国是不是国家?或者是的,而英日美等之实际的国家范围里,又同时各有各的中国”。他又分析,仅以抽象的人民为国家的要素,掩盖了人民属于不同阶级的实质,“至于近代资本阶级的社会里,明明分着阶级,而人民两字却是各阶级的总和的意思,其实即在以人民否认阶级”,国家的对内主权实际是“一阶级的独裁制”*田原:《政治学》,第109~110页。。
国家目的与功能亦为各派学者讨论的中心论题。西方学界多将国家目的与功能定位于维持社会秩序、谋求社会公平与公共福利。1939年1月,廖竞存即注意到,西方学者阐述的国家目的包括三方面:增进个人幸福,维持人民间的秩序、和平及公道;增进社会团体幸福,保护公共利益,做个人或自由团体不能做或做不好的社会事业;增进人类文明,发展世界文化*廖竞存:《青年政治读本》,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6页。。欧美派学者多接受西说。张慰慈于1923年2月即认为,“国家的目的,就想维持全体的和平秩序,裁判各社会的争议,使各种社会皆有平等发展的机会”*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第35页。。1936年3月,王希和表示,国家的目的有三方面:维持国内人民之间的秩序与正义;促进国民的群体福利与公共利益;促进“人类文化之增进”*王希和:《政治学要旨》,中华书局1936年,第14页。。
国民党派学者对国家目的与功能的阐释多遵循孙中山民生史观话语,将之定位于谋求人民生存。1933年12月,桂崇基认为,国家的目的是“谋全体人民的生存”,必须尽保民、养民、教民的职责*桂崇基:《政治学原理》,第21~22页。。1935年6月,蒋静一强调,国家是人类共同生存的组织,“换言之,就是人类想达到他们共同生存的目的,所以才有国家的组织”*蒋静一:《唯生论政治学体系》,第23页。。蔡惠群于1944年分析,孙中山将国家视作人类“用人为的力量”建立的组织,“国家既是人为力的制造品,可以证明中山先生是把国家看做人类为达到本身生存目的而造成的工具和方法”*蔡惠群:《政治学讲义》,第70页。。在此问题上,萨孟武的认识前后转向明显。其1929年7月出版的《三民主义政治学》仍受阶级分析方法影响,而此后出版的《政治学概论》《政治学与比较宪法》《政治学原理》《政治学新论》等论著则基于国民党民生史观。他在《三民主义政治学》中由孙中山民生史观生存话语推论到阶级压迫问题,认为对生存资料的掠夺造成“掠夺和被掠夺二种阶级”,“掠夺阶级”为了维持其支配地位而建立国家*萨孟武:《三民主义政治学》,新生命书局1929年,第26~27页。。之后,萨孟武放弃阶级分析方法。他在《政治学原理》中表示,人类的生存是国家产生的根本原因,“国家是人类为了解决自己的生存,乃用合群的武力,造成的一种团体”*萨孟武:《政治学原理》,黎明书局1944年,第4页。。
马克思主义派学者立足革命话语,将国家功能定位为阶级压迫的工具。恽代英于1926年9月指出,“国家是什么?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工具——国家机关,都是适合于用来压迫被治阶级的”*恽代英:《政治学概论》,第3页。。1929年11月,秦明强调国家是人类社会的阶级组织,“国家是与阶级生同床死同穴的一对恩爱的永恋的夫妻”*秦明:《政治学概论》,第8~9页。。1946年3月,郑晖指出,阶级压迫是国家存在的根本原因,“我们要深切的了解,国家的存在根本是在压迫阶级用以剥削被压迫阶级,榨取他们的剩余劳动价值”*郑晖:《政治生活与政治学读本》,潮锋出版社1946年,第20页。。他们对非阶级国家观提出批评。1929年8月,陈豹隐认为,把政治强制权力目的视作“谋自由幸福或一般利益”说法,“只图鼓吹国家至上主义,却忘记了在政治的下面常常有大多数人的牺牲和不自由”*陈豹隐:《新政治学》,第8页。。邓初民与陈豹隐几乎同调。他于1932年10月亦表示,“现在正自有人说,国家是谋自由幸福或一般利益的工具,但他们却忘记了在国家底下大多数人的牺牲和不自由;正自有人说,国家是处理一个公共集团的公共事务的工具,殊不知这也不过是一个乐观的空想”*田原:《政治学》,第104页。。
政治概念内涵、国家三要素或四要素说、国家目的与功能为政治学研究之基本问题。民国学界在此方面的阐释可谓截然分派。欧美派学者多承欧美余绪,强调政治现象即是与国家现象相关的国民与国家机关的行为,主张国家功能在于维持社会秩序,谋求社会公正与公共福利。国民党派学者则遵循孙中山所言“管理众人的事”理解政治概念内涵,并以民生史观为视角理解国家目的与功能。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基于革命需求,注重分析政治与国家概念的社会阶级属性。如此相异的阐述并非仅反衬各派学术理念的相左,亦反映出其现实政治倾向的各异。
三、一元主权论与多元主权论:对国家权威性的认知
主权是国家研究的核心论题。正如张慰慈于1923年2月所言,“国家既是最高的社会,主权又是这个最高社会的特征,所以,我们专以研究国家性质为目的政治学中,不能不以主权的研究为第一个重要问题。”*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第167页。同时,欲分析西方主权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不能不提到19世纪德国集体主义国家观与英国自由主义国家观以及20世纪初英国国家“团体说”。德国集体主义国家观主张强化国家权威,与一元主权论一样关注国家权威性问题,虽在清末受学界重视,但在民国时期饱受批评。而英国自由主义国家观与国家“团体说”则为多元主权论理论先导,受到民国学界更多肯定。
自16世纪法国学者布丹(J.Bodin)首次提出主权概念后,西方学界主要盛行一元主权论。张慰慈介绍,布丹于1576年在《共和篇》(DeLaRepublique,1576)中认为“主权是在公民和臣民之上的最高权力,不受法律限制的”,具有最高性、永久性、唯一不可分割性三种要素*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第167~168页。。清末至20年代初,中国学界大力介绍西方一元主权论。1908年9月,杨廷栋即认为“主权为无上无限之大权”*杨廷栋:《法制理财教科书·政治学》,中国图书公司1908年,第8页。。张慰慈于1923年2月亦表示,国家无论对内对外,必有最高无上的权力,各社团总要在国家支配权力之下*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第39~40页。。即便在20年代后期以后多元主权论对中国学界影响渐大的情况下,诸多学者仍赞同一元主权论。1928年4月,倪竞存认为,国家拥有对内无上、对外独立的“最高意志”,“对于这种意志,群内分子都得要服从他,其他各国都不得干涉他”*倪竞存:《政治学纲要》,文化学社1928年,第4页。。1929年12月,任和声表示,“主权(Sovereignty)之特性有五:一为永久性,其命运与国家相终始者;二为国家唯一意志之代表;三为最高无上;四为无限制;五为不能分割”*任和声:《政治学概论》,山东省立民众教育学校1929年,第16页。。王希和亦于1936年3月认为,主权对国内具有独立性与统一性,“主权有绝对的独立性,唯其独立,故在法律上言,对内对外,皆不受任何的限制,被限制之主权,则非国家之最高权力,换言之,即不成其为主权”*王希和:《政治学要旨》,第26页。。尤其全面抗战时期,出于举国团结的抗战需要,中国学界极关心增强政府权威问题,更关注一元主权论。1939年1月,廖竞存表示,“国家的主权是国家最高的权力,是绝对的、不可分的”。他之赞同一元主权论,乃出于对抗战时期强化政府社会功能的关注。他认为,“政府是为国家执行民意的机关,如认定国家当爱,则政府必须拥护,其理至显”*廖竞存:《青年政治读本》,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23~24、200页。。陈之迈特别强调国家对反侵略斗争的重要性,故于1941年4月肯定一元主权论,认为虽西方学者对主权概念有各种诠释,但主权是国家与其他社会组织的根本区别。在各种社会组织中,只有国家享有主权*陈之迈:《政治学》,正中书局1947年,第10~11页。。
19世纪德国集体主义国家观以伯伦知理(J.K.Bluntschli)和黑格尔(G.W.F.Hegel)等为代表。张慰慈介绍,伯伦知理提出“国家有机体说”,认为国家是“人类有机体的偶像”。人类的天性除个人的判别外,还有“协同一致”的倾向。这种倾向导致个人服从国家权力的本能*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第159~160页。。高一涵介绍,黑格尔提出国家“真我”与“真意思”说,认为在个人“日常经验的、意识的实在我”之上,还存在一个“理想我”,即“真我”。此“理想我”或“真我”就是国家。同时,在个人“日常经验的和意识的”“实在意思”之上,还存在一个“真意思”。此“真意思”即为国家的“意思”。故国家是个人的扩大,“个人的小我”必须服从“国家的大我”*高一涵:《政治学纲要》,第36~37页。。显然,德国此种国家观主张个人服从国家,在强化国家权威问题上,与一元主权论颇为同调。此种国家观招致民国多数学者批评。1923年2月,张慰慈批评伯伦知理把人民看作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忽视了个人的独立价值、人格、意志*张慰慈:《政治学大纲》,第160页。。1928年5月,陈筑山则指出黑格尔国家观的专制政治本质,认为其“以个人完全服从于国家的意志,美其名曰真自由,不外是带着假面具的专制”*陈筑山:《最新体系政治学纲要》,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1928年,第102页。。高一涵亦于1930年2月质问黑格尔“真我说”道,“现在人类的实际生活,果真把国家当作真我,当作最高道德吗?现在的国家果能真正成为真善美的理想体吗?人类到现在,不是还有许多行为,通同不受国家管束吗?”*高一涵:《政治学纲要》,第43页。1932年9月,赵普巨认为,黑格尔所论是19世纪国家主义的理论基础,造成“国家绝对尊严”、“国家万能”的观念,成为后世军国主义、侵略主义的理论根据*赵普巨:《政治学概论》,第61~62页。。
与德国集体主义国家观注重强化国家权威不同,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国家观与20世纪初英国国家“团体说”则成为多元主权论的理论先导。英国自由主义国家观初步提出,一国之内各种社会团体对于国家具有一定独立性。1928年5月,陈筑山将此种国家观称作国家的“互保会说”。他介绍,此种国家观始于洛克(J.Locke),经边沁(J.Bentham)、密尔(J.S.Mill)鼓吹,至斯宾塞(H.Spencer)大盛,主张国家目的为保护个人自由权;国家与其他“特殊组合”并立,并非包括其他一切“特殊组合”的“全体社会”*陈筑山:《最新体系政治学纲要》,第102、105~106页。。1930年2月,高一涵则将此种国家观称作股份公司国家观。他介绍,此种国家观基于人们的自由观念,认为国家是以个人的自由意志组成的“国民互相保护的股份公司”*高一涵:《政治学纲要》,第38~39页。。20世纪初以英属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麦其维(R.M.MacIver)为代表的国家“团体说”正式提出国家亦为社会团体,与其他社会团体具有某种平等地位。陈筑山注意到,此种国家观认为国家仅为一种团体(Association),与其他社会团体有“共通性”,麦其维《基本社会》(Community:ASociologicalStudy, 1917)为其主要论著*陈筑山:《最新体系政治学纲要》,第81、108页。。麦其维国家“团体说”对民国学界影响较大。1936年5月,陈启天将其《政治学》(TheModernState,1926)译为中文出版。陈启天介绍,此书“用多元和功能的观点讨论国家与政治”*陈启天:《译者序》,载麦其维:《政治学》(The Modern State),陈启天译,中华书局1941年,第1页。。民国时期,相较于德国集体主义国家观,英国自由主义国家观与国家“团体说”受到中国学界更多肯定。1928年5月,陈筑山一方面对英国自由主义国家观保障个人自由民主表示肯定,认为“互保会说”谓国家职能有一定范围,“尊重个人的自由”是“比较正当的国家观”,同时,又指出此种国家观过于放纵个人自由,过于强调其他社会组织对国家的独立性。陈筑山完全赞同国家“团体说”,认为此说在保障个人民主自由和社会团体自主性的同时,又指出国家有统治其他社会团体的“特殊性”*陈筑山:《最新体系政治学纲要》,第105~106、107页。。1930年2月,高一涵亦赞同国家“团体说”,认为“国家只是管理人类一部分事务的团体,在国家之外,还有许多社会存在,并且,关于那非政治的事务,个人往往与国家不生什么关系,他同别种特别团体的关系往往比同国家的关系更要密切”*高一涵:《政治学纲要》,第43页。。
西方多元主权论兴起于20世纪初。此种理论否认国家主权的至高地位和国家对主权的独占性,认为国家只是社会团体之一种,其他社会团体与国家一样在各自范围内享有某种主权。高一涵介绍,此种理论认为国家作为一种团体,与其他社会团体或组织的职能对等,故主权“不能为国家所专有”,应为各种团体或组织所同有*高一涵:《政治学纲要》,第77页。。法国狄骥(L.Duguit)以及英国拉斯基(H.J.Laski)、柯尔(G.D.H.Cole)等为此论主要代表者。狄骥否认国家主权的存在。萨孟武介绍,狄骥认为国家权力不是最高的,国家须受法律的约束,而法律又基于社会的“连带关系”。国家既然不拥有最高权力,也就没有主权*萨孟武:《政治学与比较宪法》,第13页。。而拉斯基、柯尔仅否认国家对主权的独占性,并不否认国家主权的存在。张君劢介绍,拉斯基学说“意在打破此至尊无上之主权,而造成各个人、各社团自发自动之习尚也”。依其学说,一国之内有各种社团,“所谓国家者,非能举人类一切活动而概括之,乃此种种社团中之一而已,”应承认国家之内各社团的“自主权”*张士林:《赖氏学说概要》,载拉斯基:《政治典范》(Grammar of Politics)第1册,张士林译,商务印书馆1930年,第5~6页。。朱采真介绍,柯尔在《产业自治》(Self-GovernmentinIndustry,1917)等书中将国家与基尔特(Guild)视作平等的团体,认为国家与基尔特拥有共同主权*朱采真:《政治学通论》,第100页。。
多元主权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大约始于20年代后期。1928年5月,陈筑山综合一元主权论与多元主权论,提出 “多样的统一说的主权论”。他认为,一元主权论与多元主权论皆有偏弊。前者使国家之内的团体与个人“毫无自由生活独立存在之价值”;后者“必至国家与一切团体及个人,各各自由独立而无共通一致结合统一之体制”。自己所提理论“一方承认一切团体及个人有一定范围之主权,一方承认国家主权除受其他团体的及个人的主权范围之制限外,有完全的最高性与惟一的中心性”*陈筑山:《最新体系政治学纲要》,第83~85页。。1930年2月,高一涵表示,“一元的主权论纯粹是一种悬想的假设”,无论何人,都属于从家族、村落到国家等各种“团体”,“国家的意志并不是处处可以通行,国家的权力有时候也受种种的限制”*高一涵:《政治学纲要》,第71~72页。。1930年8月,朱采真也认为,“主权本来不是国家的特性,其他各种团体也得保有主权。大凡从家族、乡村组织到国家组织,其间正不少经济的、政治的、宗教的团体,各有支配其所属分子的力”*朱采真:《政治学通论》,第99页。。
西方多元主权论对中国学界影响最大者莫过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拉斯基。拉斯基于1925年出版的《政治典范》为其多元主权论代表作,1930年10月,张君劢以张士林为笔名将其译为中文出版。张君劢对拉斯基政治思想评价甚高,认为拉斯基几为英国现代政治思想集大成者,拉斯基“虽以英国现代思想之先导言之,不如槐氏*即费边社主要代表人韦伯夫妇(Sidney and Beatrice Webb)。、麦氏*即英国首位工党首相麦克唐纳(J.R.MacDonald)。,然集合各派之长,而汇成一系统,非他人所能及也”*张士林:《赖氏学说概要》,载拉斯基:《政治典范》(Grammar of Politics)第1册,第2页。。中央大学教授杭立武等亦极追捧拉斯基理论。杭立武之推崇拉斯基在很大程度上出于师承。他于1929年获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政治学博士学位,为拉斯基学生。1932年秋,他出版《政治典范要义》。他在序言中称,此书由其撰《政治典范要义》和《读〈拉氏政治思想之背景〉书后》两文及萧公权撰《拉氏政治思想之背景》辑成*杭立武:《政治典范要义》,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1~2页。。杭立武高度评价拉斯基《政治典范》,认为此书“不特集拉氏个人思想之大成,且足使近代反政治一元主义之论说,得一系统结晶之作”*杭立武:《政治典范要义》,第4页。。不过,中国学界多注意到拉斯基对一元主权论的让步。张君劢即注意到,拉斯基将国家与其他社团相区别,认为国家是“公共职务之法人团体”,并将“平均酌剂”(Coordination)地位赋予国家,“是以多元主义者之资格,隐示对于一元主义之让步矣”*张士林:《赖氏学说概要》,载拉斯基:《政治典范》(Grammar of Politics)第1册,第6~7页。。萧公权亦指出拉斯基理论内在矛盾。他分析,拉斯基大体接受英国学者顾林(T.H.Green)伦理个人主义,承认国家中公善的存在,“故国家服役于众人之共同及普遍目的,而其他之社团皆不过满足人生片面之需要。此国家之地位所以必高出于一切组织之上也”。同时,依拉斯基所言,国家最高目的是保护个人人格的自由发展,如此,社会中就不可能有其他权威挑战国家的权威*萧公权:《拉氏政治思想之背景(附录一)》,载杭立武:《政治典范要义》,商务印书馆1947年,第66~67页。。
国民党派学者出于维护国民党专制需要,多主张增强国家权威。1935年5月,蒋静一强调,个人与国家联系密切。一方面,国家是人类共同生存的组织,“当然要代表全民族生存的意志”,另一方面,人们对国家的贡献和服务是国家进化的原动力,国家的发展需要人民“不间断地贡献其智能于国家”*蒋静一:《唯生论政治学体系》,第23、59~60页。。1937年3月编印的南京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教材强调国家的强制力,表示“若从法律方面观察,国家是立于一切团体之上的。无论什么团体,须经国家的允许,才能成立。国家为使它们不至逾越法律规定的范围,时时监视它们的行为,甚至节制它们的活动,一遇违法的事情发生,便强制解散”*《政治学概论》,第24页。。1944年4月,萨孟武认为,国家为了防御外敌与维持治安,“当然可以统制国民的行动,而在必要之时,尚须统制社团的行动,否则,工会、商会、学会、教会将各执己见,各行其是,而致治安不能维持了”*萨孟武:《政治学原理》,第8~9页。。故而,国民党派学者多赞同一元主权论。1932年12月,黄开山认为,现代社会各种社会团体“群雄割据”的状态只是由于社会生活的“中心势力”衰弱而导致的过渡时期,“一自旧势力恢复,或优越的新兴势力出现,则中心势力亦从而确立”。这表现为政治思想,便是“一元主义的思想”复活,“若不知时代及各种社会环境与政治思想之关系,而妄以多元的国家视为普通的真理,实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的”*黄开山:《政治学的诸重要问题》,神州国光社1932年,第245~246页。。1936年8月,萨孟武认为,“只惟国家才有最高主权,亦因国家有最高主权,故能维持社会的治安”。拉斯基的主张并不全面,如果国家与其他社团在各自范围内拥有各自最高主权,那么,“在同一领土之内,对于同一的人民,若因事项的不同,而存在两个以上的最高主权,实可发生许多纠纷”*萨孟武:《政治学与比较宪法》,第14页。。蔡惠群于1944年表示,“国家的意思可以拘束国内一切人民与一切社团的意思,如人民与社团发生争议时,最后由国家予以裁决,因之,国家之有最高主权,至无疑议”,“多元论者的国家主权学说,是不合实际情况的高论”*蔡惠群:《政治学讲义》,第46、49页。。
多数马克思主义论者并不关心一元与多元主权问题,而重点阐述了国家主权的阶级实质。秦明于1929年11月指出,国家主权具有“阶级性”,“社会人类因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把人类分裂为两阶级对立的时候,一阶级便不得不假强制力以维持于自己有利的社会关系,即经济组织与政治制度。同时,还要假此强制力抑制其他阶级。此种强制力就是所谓‘主权’”*秦明:《政治学概论》,第7~8页。。1932年5月,傅宇芳指出,资产阶级政治学者仅将主权视作国家统治中枢,是“空洞的主权理论”。所谓主权不过是统治阶级的工具,“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则以为主权即统治阶级之超越的力量表现于阶级统治的实权之主宰之意”*傅宇芳:《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教程》,第172、173页。。
清末至20世纪20年代前期,中国学界主要受一元主权论影响。20年代后期以降,多元主权论在中国学界日益兴盛。两种主权论在中国之消长,亦成为同时期民主与专制观念的重要学理基础。这表现在国民党派学者出于维护国民党当局政治权力需要,多宣扬一元主权论;而在中国学界看来,多元主权论与自由主义国家观以及民主政治有千丝万缕的关联。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基于革命立场重点辨析主权的阶级属性。
民国学界所言政治学研究范式仍为西来。总体而言,民国政治学者深受19世纪末欧美科学实证论影响。他们承欧美余绪,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形成科学国家学研究范式。然而,各派政治学者面临西说,由各自政治立场而有取舍与偏重。欧美派学者多注重遵循欧美政治学研究范式,强调运用美国实用主义等科学实证方法。他们出于中国民主政治关怀,日益关注多元主权论。国民党派学者则试图将欧美派学者阐述的欧美研究范式与孙中山民生史观相结合,构建适应国民党统治需要的政治学体系。马克思主义派学者则强调政治学研究应并用唯物辩证法与唯物史观方法,构建起革命式的政治学研究范式。而马克思主义派学者主张的唯物史观及其阶级分析方法成为另外两派学者辩驳的焦点。由此而言,政治改良论与政治革命论之分野几成民国政治理论之分水岭。问题在于,在以革命手段重构中国社会仍为民国社会主要发展趋向的情况下,政治改良论是否能够满足中国政治发展的需求?
●责任编辑:何坤翁
The Debate about Political Studying Paradigm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YanShuqin(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he period of Republic of China is an important time to form Chinese political studying paradigm.Owing to the close relation between politics and actual politics,scholars from different schools devoted themselves to write the political books,so as to form three expounding systems,such as European-American school,Kuomintang and Marxism.European-American school carried forward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ying paradigm,especially scientific positivism,formulating the paradigm of science of state.Kuomintang scholars tried to combineMinsheng(民生,people’s livelihood) historical idea with European and American studying paradigm,so as to formulate the theoretical system which serves Kuomintang’s rule.Marxist scholars devoted themselves to formulate the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system,using th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its class analytic method.Obviously,the dividing line between reformist political theory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al theory is the watershed of the various political theories in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e Republic of China; politics; studying paradigm; state; sovereignty
10.14086/j.cnki.wujhs.2016.06.004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A770049)
●作者地址:阎书钦,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Email:ysq02@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