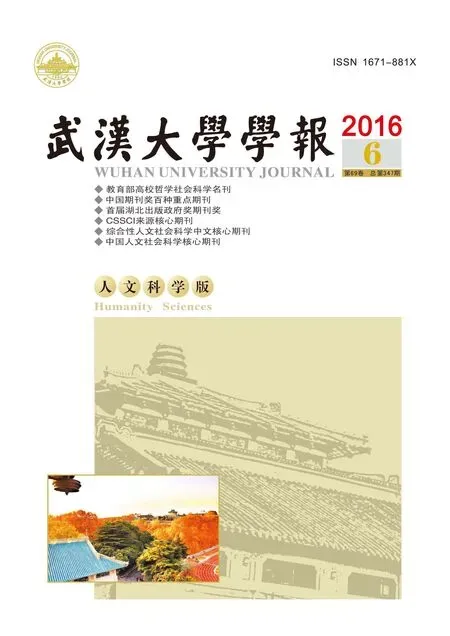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胡大平
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中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胡大平
马克思主义在产生和发展过程中,与人类学始终具有不解之缘。在形成阶段,人类学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了早期社会研究的支撑,证实了其科学价值,同时亦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叙事深化和拓展的基本路径。20世纪50年代以后,受结构主义等思潮影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动向,这一动向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解以及进行当代批评的视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人类学内部产生了诸多受益于马克思主义的新进展,在现代社会批判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多层次和多维度融合成为基本趋势。在整体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代表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方向。
历史唯物主义; 人类学; 马克思主义人类学
按照卢卡奇关于马克思主义性质的表述,“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归根结底就没有什么独立的法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科学等等,而只有一门唯一的、统一的——历史的和辩证的——关于社会(作为总体)发展的科学”*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95页。。这意味着,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简单地还原为今天的某种学科视角。不过,具有普遍性诉求的历史叙事(即历史科学),马克思主义与史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始终保持着融合和冲突关系,并且在各个学科内部占据着特殊的位置。实际上,与这些学科的互动,亦是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不断走向深入的基本路径之一。就此而言,理解这些互动的历史,亦是马克思主义自我理解的重要途径。本文聚焦于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关系*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关系,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在西方已经产生了一些文献综述与专题论述。例如,萨林斯在1976年的《文化与实践理性》(赵丙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中以两种不同的理性作为框架回应过围绕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的有关人类学争论;莫里斯·布洛克于1983年从人类学角度提供了一项至今仍然是极为深刻的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冯利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年);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在1984年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王铭铭等译,三联书店1998年)中以政治经济学问题的重要性为基点简要地描述和分析过相关动态;莱顿在1997年的一项研究中简要地梳理过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在欧美学界的主要动态(罗伯特·莱顿:《他者的眼光:人类学理论入门》,蒙养山人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通过马克思主义形成、20世纪5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兴起以及8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在现代社会批判事业中融合三个阶段,阐明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之间的对峙不是关于所谓“原始社会”基本特征和性质的判断之争,而是以这种社会结构为依据概括出来的普遍的文化模式(或文明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在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人类社会的一般前提(结构)、社会形态变迁的动力和机制(历史)、文明的意义(主体)等基本问题——层次上的竞争。不过,在现代社会(资本主义)判断上,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一般看法具有高度的一致性。由于这一点,两者的融合和相互促进成为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趋势之一。由是观之,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联盟,正是拓展历史唯物主义当代视域和推进社会批判理论深入的重要途径。
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与人类学
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类学的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具有基础性作用,特别是马克思晚年历史学笔记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相关研究拓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扩大了他们的视野。但是,包括第二国际在内的相关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早期学生对早期社会的关注,与今天流行的人类学学科旨趣有着较大的差异,他们只是利用这一领域的成果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性*胡大平:《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5期;《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的总体性框架》,载《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5年第4期。。
在此,我们不再重复有关研究,而只是强调如下两点对于今天理解历史唯物主义与人类学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一,无论是为人的本质提供论证的哲学人类学,还是今天包括体质人类学和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子领域的学科,它们都与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不解之缘,但马克思主义无意识建构自己的人类学。人类学的基本旨趣便在于揭示社会或文化之不受时间影响的普遍前提,作为历史科学,历史唯物主义必然要遭遇这个问题并给出自己的答案。正是因为这一点,列维-斯特劳斯强调,马克思首先肯定了历史学,其次也肯定了人类学,这两种研究方法是不可分割的*参阅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谢维扬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第一章。。对于历史唯物主义来说,特殊的是,按照经典作家对其科学性质的理解,一方面,它不会在历史之外寻求人性的支点,因此,无意识发展自己的哲学人类学;另一方面,它对早期人类经验的兴趣,绝非寻求对人类历史“一般发展道路”的解释,而是科学分析由于历史发展多样性道路造成的无产阶级解放在不同地域的实际条件。就前一方面说,正如我们看到的那样,历史唯物主义基本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草稿)中最初较为完整的表述,与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同体的,它明确地与后者的哲学人类学划清了界限。因此,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乃是哲学终结之后的产物这个观点,即历史哲学向历史科学的转换,其基本思想应该包含对一切试图在历史之外定义人的本质的哲学人类学进行批判这个重要立场。就后一方面说,1867年《资本论》第1卷出版后,马克思至死亦未完成第2、3卷以及其理论史计划,但却费力去研究古代社会或者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绝不是出于在理论上提供完备的世界通史需要,而恰恰源自对西欧之外不同社会发展道路和革命条件的考察需要。正如他对俄国问题的关注,这种需要乃是社会历史向他提出的。不正是在1877年“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他明确表达自己对“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或者“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的拒斥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2页。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卢卡奇将其历史唯物主义的最重要目的理解成“认识现在”*在《历史与阶级意识》第1版序言中,卢卡奇如此强调。在正文中,他又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最重要的任务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作出准确的判断,揭露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本质。”参见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41、312页。。
第二,固然,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文献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早期社会的看法,从而夯实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基础,但其目标恰恰不在于从细节上提供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细节的看法,从而建构某种终结性的完备的理论体系。恩格斯本人已经清晰地解释了自己的写作原因,摩尔根“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个解开了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解决的哑谜的钥匙”*《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页。,他的研究代表着原始历史观中的革命,亦证明历史唯物主义之科学性。因此,恩格斯并非像今天人类学研究那样,试图通过异文化之家庭、性、亲属关系和社会组织原则来证明欧洲并非“自古华山一条路”,而是通过以血族关系为基础的古代社会向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文明社会之变迁来实现两个重要目标:阐明唯物主义历史观之科学意义以及揭示现代社会之历史形成、打破其自然性和永恒性神话。
必须注意的是,在完成这两个目标的过程中,恩格斯的文本展示了一种特殊的张力。一方面,他把自己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发展出来的四种生产理论——即“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81页,或者,人类生存的四个前提性事实——重新概括为两种生产理论,劳动代表的生活资料以及由此必需的工具的生产以及家庭代表的人自身的生产。在恩格斯看来,这便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之内容,它们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依据古代史资料,恩格斯说明了人类历史的两种形态或阶段:主要受家庭(血族关系)支配的古代社会,主要受私有制支配的文明社会,它们代表着劳动的不同发展阶段。在这种区分中,我们看到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受制于不同的主导原则,这意味着经济决定论或暴力决定论所代表的那种单一因素决定的线性史观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在历史变迁之原因分析中,恩格斯始终坚持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立场,即以劳动生产率为代表的生产力进步是所有变迁归根结底意义上的原因,甚至是直接的原因,而这一点往往与经济决定论纠缠在一起。例如,在谈到私有制产生时,他自己也承认“至于畜群怎样并且在什么时候从部落或氏族的共同占有变为各个家庭首长的财产,我们至今还不得而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1页。,但他实际上还是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与分工之间的关系做出了经济决定论的解释,一个实际上循环的解释。在这个问题上,实际上,18世纪末的古朗士早就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指认,在西方私有权的起源分析上,“自然顺序就是先使收成私有化,然后才是土地,而希腊人的顺序却正好相反”*菲斯泰尔·德·古朗士:《古代城市》,吴晓群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90页。。那种自然秩序,在15世纪的印第安人那里仍然存在着,但它恰恰不是欧洲人的选择。古朗士从宗教信仰角度提供了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与私有制问题一致,在人群聚集形态及其变化问题上,文化因素与经济因素在不同的地域情况也是有差异的。这在今天仍然是人类学所面临的基本难题之一。在恩格斯的分析中,问题同样地被简化处理了。例如,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几个亲属胞族构成一个部落。在阿提卡,共有四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三个胞族,每个胞族有三十个氏族。这样细密的集团划分,是以有意识的和有计划的干涉自然形成的秩序为前提的。至于这是怎样发生的,什么时候发生的,发生的原因何在,希腊历史都没有提到,希腊人自己关于他们的历史所保存下来的记忆仅仅追溯到英雄时代为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2页。产生问题的现象与古朗士的描述一致,但解释原因时,略加讨论语言后,恩格斯立即把问题转向财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私有制与国家起源分析的焦点,即剩余产品的生产和占有问题。这个问题,也是20世纪人类学和相关领域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问题。不论那些批评是否正确,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恩格斯并没有完备地触及细节,因此在处理有关问题时确实过于简化了。并且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恩格斯的实际论证过程存在着一些明显的跳跃,能够解释国家的发展,但不能充分地说明希腊人口呈现那种聚集的原因。在整个文本中,恩格斯实际上通过欧洲、北美、亚洲等地区的早期社会资料的相互参照(即比较研究),描述了一个在世界各地逻辑一致的历史变迁模式。这正是成问题的地方。因为他的比较实际上是以异地经验来解释本地经验之缺失的环节,然而那种缺失的环节往往正是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之所在,并且正是这种偶然性本身造就了文明的丰富性。在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这一点。在理论史中,这是泰勒之后人类学所回应的主要问题之一。遗憾的是,在恩格斯这里,对欧洲历史之普遍性的怀疑还没有出现,他的首要目标仍然是以摩尔根等人的早期社会研究成果来捍卫唯物主义历史观并完善其关于历史的解说。就此而言,他的研究与后来的人类学也相去甚远。
当然,尽管恩格斯的研究存在着内部张力,但这并不影响其价值。如果对照《反杜林论》第二编关于暴力论的三章,我们同样可以看到,恩格斯关于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之对立以及前者向后者的过渡之分析,其关于分工、商品生产和奴隶制之间关系的揭示,不仅已经充分照顾了欧洲内部发展的不同道路(例如从氏族到国家之雅典、罗马和德意志人三种形式),而且逻辑上揭示了殊途同归这个事实所蕴含的问题,即现代社会的一般经济条件,这正是《资本论》的主题,亦是我们所必须面对的基本历史问题。就此来说,《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文构成了《资本论》的补充,它代表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拓展。在这种拓展中,体现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独特方法论,即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导言”中以“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这个比喻所表达的方法。这也说明一个问题,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如果不能科学地解剖现代社会,对古代世界的正确理解也是不可能的。甚至,我们可以说,正是这个原因,马克思主义关于古代社会史的研究或者回应今天以学科化方式提出的所谓“人类学”问题,必须建立在《资本论》基础之上。这正是我们评价马克思晚年古代社会史研究所必须坚持的原则。然而,遗憾的是,许多马克思主义研究都没有重视这个问题。由此,不能不谈及恩格斯这一文本的政治意义。
在这个文本中,恩格斯并没有从正面完整地展开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但他在引论中却强调摩尔根“对商品生产社会,对我们现代社会的基本形式进行了批评,而且还用了卡尔·马克思才能说的话来谈论这一社会的未来的改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页。。在更大范围内,包括1884年发表的《论原始基督教的历史》等文章,恩格斯晚年从不同角度谈论早期社会时,都是试图从历史变迁角度来说明现代社会和现代工人运动之命运的。正是这一原因,恩格斯的历史研究始终坚持了服务于现实斗争需要这一原则,其研究本身始终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改造世界之旨趣。借助这一特点,我们可以锁定古代社会史或者人类学研究在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性质和地位。
从第二国际至苏共“二十大”,主流马克思主义曾涉及古代社会所代表的人类学研究,但并非要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而是依据包括人类学在内的进展来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以拉法格为例,他的《财产及其起源》(1895年)便可以视为“人类学”的专题研究。在第二国际时代,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策略始终是争论的焦点问题,为什么这些领袖却一有空闲便研究古代社会、宗教和思想的起源问题呢?拉法格提供了一个解释,他强调:“资本形式比较晚出现这一现象提供了最好证据,证明所有制不是静止的、不变的,而是像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秩序的现象一样是在发展着和经历着各种不同的形式,由一种推向另一种。”*拉法格:《财产及其起源》,王子野译,三联书店1962年,第29页。简言之,这不是出于人类学的兴趣,而是利用古代史研究的成果来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暂时性。同样,普列汉诺夫也使用了不少有关非洲部落研究的资料来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例如奴隶制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间的关联*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载《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3卷,三联书店1962年。。至于以马克思主义来指导古代史或人类学研究,或者像考茨基那样,出于“写一部包罗万象的世界史的念头”*卡尔·考茨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叶至译,三联书店1973年,第12页。,完整地提供一份从史前史到今天的科学体系,那已经是另一回事了。
二、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兴起
从上文讨论看,马克思主义无意建构自己的人类学,试图把马克思打扮成发展了人本质学说的人类学家*例如,乔治·马尔库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马克思哲学关于“人的本质”的概念》,李斌玉等译,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也没有多大的价值,不过20世纪的学术史,还是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人类学问题”,如何看待这个事件呢?
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产物,而且只是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法国莫里斯·戈德利埃(Maurice Godelier,也有人翻译成莫里斯·郭德烈)才能说成为一种动态,尽管在这之前,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也有人翻译成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已经实质地打开了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视域。
一般来讲,直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术界才陆续出现一些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回应文化人类学经典主题的研究,例如沃斯利(Worsley)*P.M.Worsley.“The Kinship System of the Tallensi:A Revaluation”,in The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1956,86(1),pp.37~75.这个文本在人类学内部被视为马克思主义立场的研究。但值得注意的是,沃斯利在这个文本中并没有直接评论马克思或马克思主义,而是坚持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批评福忒斯把社会结构与经济割裂开来的做法。,但并没有出现严格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作品。当然,柴尔德(Vere Gordon Childe,1892-1957)的考古学亦可视为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前社会的成果,他丰富了从经济基础角度理解历史变迁的社会史研究*柴尔德多数文本都已中译,其中重要代表作如,戈登·柴尔德:《欧洲文明的曙光》,陈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只是,这些成果在今天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以及相关争论中并没有显著的位置。
更为特殊的是巴塔耶(Bataille),他在1933年发表的《耗费之观念》一文中引入莫斯关于赠予的研究,把经济学上所称的非生产性活动置于中心地位,另辟蹊径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批判。巴塔耶认为,必须把消费区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一是由保存生命和维持个体生产性活动所需要的最少必需品所代表的部分,这是维持生命和进行生产的基本条件;另一个是所谓“非生产性耗费”,它们包括奢侈、仪式、战争、崇拜、纪念碑的建造、游戏、表演、艺术以及其他反常性行为(例如,脱离了生殖目标的性活动),这些消费都没有超越自身的目的*Georges Bataille.The Bataille Reader.Fred Botting & Scott Wilson(eds).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97,p.169.。相似的区分,在古典政治经济学那里就已经存在了。不过,整个经济学都倾向于压抑后者,而在巴塔耶看来,财富的耗费而非生产才是经济学的真正主题。在生产逻辑中,消费只是实现生产目标的工具,它导致拜物教问题。在这里,他实现了与马克思的对接。巴塔耶认为,马克思的原创性在于,他试图仅仅以否定的形式,即通过克服物质障碍,来实现一种道德成就。这导致人们认为他只关心物质财富。不过,巴塔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主张是把(经济的)物之世界整个地从(对经济来说)外在于物的每种要素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换句话说,正是通过达及暗含在物之中的可能性之界限,马克思决心把物还原成人之状态以及把人还原成他自己的自由性情*Georges Bataille.The Accursed Share:An Essay On General Economy,Volume I:Consumption.New York:Zone Books,1991,p.135.。
巴塔耶与马克思的关系,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争论的问题。无论如何,他借助于人类学资料拓展了现代社会之物化的批判,无论对人类学还是对马克思主义,都提出了一些新课题。在法国语境中,巴塔耶的这种做法产生了复杂影响。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他将关注重心从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在其中,资本生产的内在矛盾决定其不可避免的危机和崩溃这个问题又始终处在焦点——转移到通过非生产性活动(即代表自由的耗费)克服拜物教的可能性。正是这一点奠定了后来人类学之中马克思主义视角的基本地平。
列维-斯特劳斯之结构人类学的兴起代表着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关系的重大转折。一方面,他借助于马克思主义改变了人类学格局,另一方面,则通过人类学实际地改变了西方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和表述。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形成系统的对马克思主义的解释,但对萨特《辩证理性批判》的批判,不仅摧毁了人本主义的基础,而且开辟了近代哲学之主体路线批判的新思路,后来的阿尔都塞和福柯,正是在这一思路上崛起的,他们许多重大的判断都可以在列维-斯特劳斯这里找到源头。
由于问题的重要性,需要我们就他与马克思的关系做一点澄清。列维-斯特劳斯不止一次声称,不仅自己的研究方法,而且还有许多重大观点都来自或得益于马克思。例如,他说过,“甚至结构概念也是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其他学者那里借用过来的。这样做,目的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推进上层建筑研究”*参阅列维-斯特劳斯本人的解释,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362页。。如果这一点属实,那么就应该将其纳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谱系,尽管其后来的研究内容和方法很难被主流马克思主义接受。他曾经断言,“马克思本人就建议我们揭示作为语言以及人与世界之间关系的基础的象征体系”,并强调自己的象征理论直接受益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因此是唯物主义的*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104页。。甚至,“在《人种与历史》中所论述的在静止的历史、波动的历史与累积的历史之间的区别是能从马克思本人那里推导出来的”*克劳德·莱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第367页。,马克思《资本论》关于亚细亚社会的论述提供了关键性证据。不管列维-斯特劳斯关于马克思的理解是否可靠,他关于自己与马克思关系的判断是否准确,至少他的主观意图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人类学领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他的这个结论是绝对正确的:正是关系体系决定了一个社会的面貌,人类学是一种关于关系的一般理论,而马克思主义最核心的贡献之一也是从关系的角度揭示人类历史变迁之谜,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都是关系,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又构成生产方式。当然,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史中,存在着两个极化的误读,一是主流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把生产方式分析不恰当地还原为经济决定论;二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的把唯物辩证法发挥为阶级意识决定论,萨特的辩证理性批判将这一主体哲学路线推至极端。列维-斯特劳斯以结构作为切入点,基本意图便是避免这两极而将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物化批判转换成科学语言。我们看到,尽管无法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人类学归结为马克思主义,但对萨特的批评和关于结构因果性的分析最终还是在马克思主义内部产生了爆破效应,亦决定了随后产生的人类学之马克思主义视角的范围和方法。
在列维-斯特劳斯之后,戈德利埃可能是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代表。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戈德利埃坚持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革命理论的有效性,但在人类学课题上,他亦坦然承认,马克思恩格斯接受的许多结论过时了。撇开细节不论,在他看来,传统人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遭遇的最大挑战,便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人类历史发展是多样的而非单一的。为解决这些问题,戈德利埃把社会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作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研究的基本方向*Maurice Godelier.“The Thought of Marx and Engels Today and Tomorrow’s Research”,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1972,2(2/3,Summer/Fall) (Structuralism and Marxism:A Debate).。他不仅就许多细节进行突破,例如修正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将之拓展为包括非洲古王国在内的更广大地域从非阶级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社会形态,而且在总体上形成对诸如“占统治地位的因素”分析等重大方法的独特理解,特别是他对阿尔都塞派结构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解读和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做出了认真的回应,强调马克思分析之结构特色在于将矛盾概念置于结构的历时性分析理论之中心*Maurice Godelier.“Comments on the Concepts of Structure and Contradiction”,i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1972,2(2/3,Summer/Fall) (Structuralism and Marxism:A Debate),p.182.。这些问题一直贯穿着戈德利埃的研究,并最终促使他形成了对人类社会根基进行重新评估的观点*莫里斯·郭德烈:《人类社会的根基》,董芃芃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其1973年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视角》,是最具价值的全部马克思人类学文献之一。在这一文本中,他不仅评估了马克思关于原始社会思想之当代意义,而且对包括“社会经济形态”等在内的重要概念工具之意义做出了澄清;更重要的是,他试图把马克思关于历史变迁和现代社会的批判贯穿到人类学研究之中,从而升华人类学之当代视野。总的说来,他认为,没有对结构之本质的任何偏见,马克思第一次揭示了功能差别的等级和结构因果性,它们在任何情况下都执行着诸如亲属关系、政治、宗教那样的功能,一个结构可能支持的功能也不存在数量上的限制。马克思所做的事情并不比这更多。但是,马克思提供的基本假设和方法论程序具有“一般的示范价值”,它“不仅是我们时代的认识论地平,而且实际上提供了主要的指南”。不过,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在人类学所直接面对的所谓“原始社会”问题上,还是对现代社会的基本理解,都没有提供完整的结论。因此,“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作为社会科学中的批判工作之认识论地平,我们必须创造一些新的方法来探究那个将形式、功能、接合模式和等级体系以及特定社会结构产生和消失等等联系在一起的不可见的原因网络”*Maurice Godelier. Perspectives in Marxist Anthropolog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2.。
20世纪70年代以来,尽管像戈德利埃那样同时对马克思主义和人类学都有深刻见解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家凤毛麟角,但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或者试图把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结合起来推动文化理论进展的做法却也较为不少。其中,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是比较引人注目的一位,其《文化唯物主义》(1983)在业界引起了广泛的重视。这本书的英文副标题是The Struggle for A Science of Culture,这清晰地表明其旨在为文化研究建立一种可靠的普同模式。不过,它最多只是借助了马克思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关系的理论方法论*马文·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而很难谈得上在马克思主义理解和人类学视野拓展方面有何明显的贡献,甚至连人类学同行都认为其与马克思的观点毫不相干*莫里斯·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第151页。。因此,哈里斯的这种作法并不值得重视。相反,值得重视的倒是那些并没有在整体上打出马克思主义旗号却在方法论上实质性地挪用马克思主义而产生影响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以来,无论是马克思主义领域还是人类学领域,试图以某种方式激活马克思的资源,这是一种十分显著的动态。在前一领域,连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都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政治人类学(political anthropology)”的主张*Terry Eagleton.Marx and Freedom.London:Phoenix,1997,p.23.;在后一领域,帕特森(Thomas Carl Patterson)的《马克思,人类学家》(KarlMarx,Anthropologist)则是较新的代表性文献*Thomas Carl Patterson.Karl Marx,Anthropologist.Oxford:Berg,2009.,它试图完整地对马克思著作及其意义进行人类学解读。这种动向充分表明:在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中进一步打开对当代社会的洞察,不只是加深了人类的自我理解,而且有助于推动人类克服物化的历史进程。
三、在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的融合中推动现代社会批评
随着文化人类学视野和方法的深化,特别是结构主义对整个人类学的影响以及当代民族志研究的兴起,马克思主义作为方法论在人类学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乔治·马尔库什(George Markus)等人的《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便对政治经济学与民族志之间的历史互动做出了有价值的解释。在这种互动的历史中,“作为一种对具有政治经济学旨趣的民族志的必要补充,悠久的马克思主义写作传统中十分完整而明晰的资本主义理解分析框架,仍是最强有力的大体系背景意象”*乔治·E.马尔库斯、米开尔·M.J.费彻尔:《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第126页。。在这种情况下,泛泛指认马克思一般理论影响,这种做法越来越失去理论的意义。例如,我们强调西敏司(Sidney Mintz)的《甜与权力》以及阿俊·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的研究与马克思主义旨趣和方法高度契合,除了那种迂腐的学院气息,有多大价值呢?勿宁说,新的势态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如何与各种具体研究结合形成对当代有穿透力的分析,通过理论的想象力促进思想的进步,并由此为介入改造世界的政治经济实践打开新的通道。这也正是人类学本身所思考的问题。1986年《写文化》发表之后,在人类学研究中隐而不现的诗学和政治学走到了前台,意识形态争论不复是学科发展的障碍。至少围绕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再成为问题了。因此,我们希望以三类不同的案例来说明在现代社会批判事业中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融合的可能趋势。
第一个案例是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的《文化与实践理性》。这一著作是很独特的。首先,它是纯理论性的人类学成果,即那类对既往民族志成果的再解读,这类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通过方法论的重新评估推进研究的反思。其次,它亦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人类学解读,这种解读实际上亦是以人类学成果对马克思主义许多重大观点的检验。再次,这个成果的基本旨趣在于重申文化人类学关于文化之意义理性的理解,并以此推进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所有这些特点结合在一起,便造成了其特殊价值。简言之,萨林斯区分了两种文化理论(即意义理性与实践理性之对立),而在马克思的话语中,他亦发现它们的对应形式。所以,他区分出两种马克思主义,一种是与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同路的历史唯物主义,另一种则是资产阶级意识合谋的经济决定论。萨林斯不是职业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因此,我们无法要求他对马克思主义内部的这种分裂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们亦可以说,客观上,他准确地描述了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解上存在着的那种分野,人本主义的对经济决定论的解释,甚至青年马克思反对老年马克思的思潮。对于萨林斯来说,似乎在马克思思想的全程,交织着他所称的两个环节或两种要素,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取舍是十分困难的。因此,我们亦无法指望萨林斯以人类学家的身份为我们指出一条简单的道路。对我们来说,这一成果的真正价值并不在其直接结论,而是这项研究本身提出的问题。为什么会在马克思主义这里以及人类学学科内部存在着相似的分野?为什么这两者不可能并行不悖?将马克思作极化理解以及对文化做单向度理解,将会丢失什么东西?这正是今天需要我们反思的问题,我们不能通过将之归结为马克思文本的矛盾而将问题取消。从人类学角度来说,“把社会放置在历史中,把生产置放在社会中,马克思在人类学科学尚未诞生之时就已为它构成造了大致的思路”*马歇尔·萨林斯:《文化与实践理性》,第220页。,如果萨林斯的这一论断是确实的,那么,需要我们追问的是,在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那里,为什么会同时出现对物化现象的深刻批判以及似乎(至少在表面上)与物化逻辑一致的经济决定论?对这些问题的深究将有助于我们深入唯物主义历史观本身,理解其从直接的物质生活生产和再生产出发理解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之形成的动力和机制以及在那种条件下社会生活的性质,从而把握其辩证法的精神实质。简言之,萨林斯提出的问题使我们看到了人类学与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相互比较和借鉴而打开对历史变迁的洞见和对当代社会进行批判的视野,尽管他本人并没有完成。
第二个案例是西敏司的《甜与权力》。《甜与权力》是关于我们今天餐桌上一种普遍食物——糖的人类学研究。在书中,他指出,“英国工人第一次喝下的一杯带甜味的热茶,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因为它预示着整个社会的转型,预示着经济和社会基础的重塑”*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王超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210页。。尽管这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但它在方法论上道出了历史研究的真谛:那些最初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偶然的、然而最终却成为日常生活普遍事实的那些事件,它们记录了人类物质生活生产中那些重大的、最终影响了人性的结构性变化,因此,通过这些物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能够发掘自身的历史。这就把我们的历史眼光投向那些决定今日社会的结构变化。通过西敏司的研究,我们看到,欧洲的需求定义,加勒比海地区生产结构的变化,这两者之间的变化是同一过程的不同方面,它们都涉及资本主义的历史。西敏司并没有说自己的研究与马克思有何相通之处,然而这却是一本在严格意义上与历史唯物主义旨趣和方法一致的研究,它比绝大多数打着历史唯物主义旗号进行的人文社会研究都要具备马克思主义的气质。这让人想起马克思与摩尔根的关系,恩格斯曾经如此清晰地描述了这一关系,“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我们并不急着以此类比得出结论:西敏司以现代社会生活之中一个如此普遍而平凡的物——糖——证明了唯物主义历史观是卓越的科学。这一结论是不需要证明的,更不是重要性之所在。我们面临的问题始终是如何做出一项好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好不好,或者要不要历史唯物主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许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把重心赌在后一方面的论证上,走得如此之远,甚至过度发挥了经院式论证而抛弃了马克思本人的教导:“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5页。
可以说,西敏司的这项成果,在人类学内部以出奇不意的方式强调了马克思的意义。说“出奇不意”,并非因为其讨论的问题与马克思在表面上风牛马不相及,而是因为,他并没有留下多少关于方法论的论证,是真实再现了那一方法论的价值。在人类学传统中,一直倚重于对“初民社会”的特殊偏好,虽然这种偏好产生了许多卓越的研究,它们为理解和改变今天树起了一面面明镜,但正如从巴塔耶到鲍德里亚对法国莫斯人类学观点的过度发挥,我们不仅不能借助于这些镜子反射的光照亮今天的世界,而且对它们的迷恋往往使我们错失进入现代社会的机会。与之相对,西敏司谦逊地主张“关于当下的人类学”,他问道:还有什么比对一种装饰每张现代餐桌的食物进行历史探究更缺乏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学味”呢?然而他又是如此坚定地强调:“正是这种对家用的、日常物品进行研究的人类学可以帮助我们澄清世界是怎样从它曾的样子变为它现在的模样,澄清它在变化的同时又是如何在某些层面上保持内在的一致性的。”*西敏司:《甜与权力:糖在近代历史上的地位》,第12页。在历史学领域,布罗代尔不是以相似的思路说明了我们所称的资本主义或现代社会是如何形成的吗?*费尔南·布罗代尔:《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顾良等译,三联书店2002年。历史唯物主义的旨趣当然不是解释世界,不过其对世界的改变难道不是以此作为基础的吗:揭示世界之变迁,洞穿其中变与不变之物,从而把握我们自己创造历史的可能性机会?
第三个例子是布若威的研究。作为当代具有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一,布若威(Michael Burawoy)是非常特殊的。这种特殊性在于,他身在学院,但却非诞生于学院。如他自己所言,他的马克思主义“不是通过与世界保持距离而得来,而是通过进入它的内部——矿井、机械车间、钢铁厂、香槟酒厂和家具厂——在赞比亚、美国、匈牙利和俄国,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之中”*迈克尔·布若威:《制造同意》,李荣荣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第2页。。因此,无论关于生产政治学的研究还是公共社会学主张,在布若威的理论中都深刻地体现了反思性民族志的精神,他将之视为打开社会主义新视野的方法之道。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布若威在下述两个层次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重要意义。一是布若威带领自己的研究团队,把视野投向这个问题:现代都市的日常生活是如何在那些表面上超出人类控制的制度影响下持续地变化的。他们深入社会运动、工厂、新移民、教室和社区,以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从微观层次上来再现当代社会变迁中的权力和抵抗*Michael Burawoy.Ethnography Unbound:Power and Resistance in the Modern Metropolis. 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二是从微观拓展到宏观,超越民族国家来思考当代世界变迁。布若威主张应该关注那些活生生的全球化经验,即全球力量、全球联系和全球移民支持、适应、抑制和争夺既存秩序的方式。在布若威看来,建立在精细的劳动分工、有组织的阶级间关系以及规模经济之上的经济秩序,聚焦于民族国家的政治秩序以及同容忍和相对同质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文化秩序,这些既有的秩序正在被弹性积累、全球—地方间互动以及新的杂交身份替代,因此要使民族志研究适应于新的变化*Michael Burawoy.Global Ethnography:Forces,Connections,and Imaginations in a Postmodern World.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0.。正是基于微观与宏观的研究,布若威主张有根基的政治学,通过它来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关切:劳动者的解放。
通过上述三个例子,可以认为,是否有必要像帕特森那样把马克思称为人类学家,是否有必要发展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这些问题是大可讨论的。不过,这些问题并不重要。马克思主义并非一成不变,人类学亦不断发展着,它们各自的内部在今天都具有多种甚至对立的自我理解。因此,试图把它们之间的关系固定在某种刚性的边界之中和单向的路线之上已经不再是恰当的做法。真正的问题是,通过理论上的互动,在当代社会的理解和批评上形成有说服力的见解从而推动人类改造社会的实践之发展。就此而言,布洛克的那个强调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不是仅仅出现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著作中的理论,而是应该被重新创造的理论*莫里斯·布洛克:《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第197页。。
●责任编辑:涂文迁
Marxist Anthropology in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HuDaping(Nanjing University)
Marxism has been always bonded to anthropology from its origin to today.During the phase of Marxism’s formation,anthropology support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with the evidence of its researches on ancient society,and basic path for the later to deepen and extend its historical narrative.After the 1950s,under the influence of Structuralism,Marxist anthropology beca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dynamic fields,which enlarges the vision of historical understanding and current critique for Marxism.Since the 1980s,there are many new trends benefited from Marxism in the field of anthropology,the union of Marxism and anthropology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and levels has been apparent.This paper holds that Marxist anthropology represents an important orientation of current creatives of Marxist theories.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thropology; Marxist anthropology
10.14086/j.cnki.wujhs.2016.06.006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089)
●作者地址:胡大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Email:hudacn@nj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