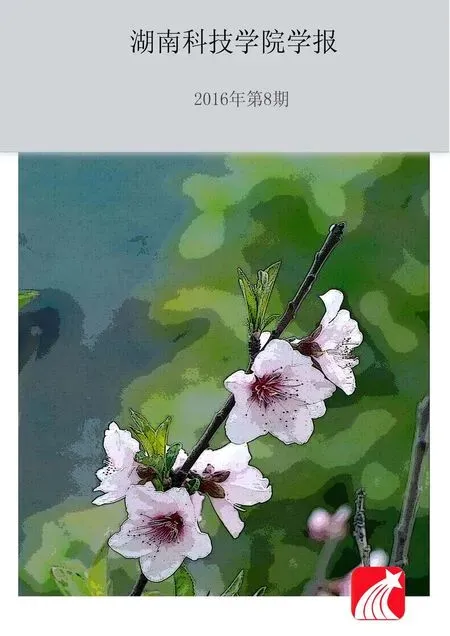柳宗元山水文学中的天台宗意蕴
范洪杰(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柳宗元山水文学中的天台宗意蕴
范洪杰
(北京大学 中文系,北京 100871)
摘 要:学界广泛注意到柳宗元的山水文学背后弥漫着深厚的佛教意蕴这一事实。柳宗元的山水文学,尤其是目前研究尚不透彻的山水散文中,这种佛教意蕴大体可认定是以天台宗教理为主的。从与天台宗思想的关系来看,柳宗元那些艺术成就高的山水文字可划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愚溪诗序》等与天台宗“圆顿止观”有直接体现关系的;另一种类型是与天台宗“圆顿止观”的关系虽然不能确切指实,但可以认定是在与之一致的朴素禅观上有精神上的相通之处的。
关键词:柳宗元;山水文学;天台宗
一
山水文学自南朝以来就是一种重要文学类型,柳宗元山 水游记和山水诗都取得了重要成就。可以说,柳宗元是中古山水文学的殿军人物①就诗而言,胡应麟:“靖节清而远,康乐清而丽,曲江清而淡,浩然清而旷,常建清而僻,王维清而秀,储光羲清而适。韦应物清而润,柳子厚清而峭”(《诗薮》),言下把柳子厚作为中古山水诗的殿军;葛晓音也把柳宗元作为魏晋南北朝隋唐山水田园诗派的殿军,见氏著《山水田园诗派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347页。。柳宗元好佛,是性之所近:
诚乐之,其于性情奭然。(《送僧浩初序》)
凡为其道者,不爱官,不争能,乐山水而嗜安闲者居多……吾之好与浮屠游以此。(《送僧浩初序》)
所以柳宗元的山水文学背后弥漫着一种佛教意蕴,便不奇怪了。学界对柳宗元的山水诗的解读已经注意到这一点②王国安先生对《巽公院五咏》的解读是重要成果,见其《读〈巽公院五咏〉——兼论柳宗元的佛教信仰》一文,《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但对他所取得卓越成就的山水游记的佛教意蕴方面的分析尚未达到理想状态。对柳宗元的山水游记和山水诗通观并察,发掘其佛教意蕴,是有意义的。笔者认为,柳宗元的山水文学背后的佛教意蕴与天台宗思想有紧密关系。
文人接受佛教思想,一般带有普泛性和随意性特点,很少独好某个宗派的思想而对其它思想进行排斥。柳宗元的思想也以同时代人对佛教的普遍接受水平为背景,以佛教的共义为知识基础。但同时柳宗元个性明敏善断,在唐文人中慧解突出。此外也由于他来到永州之后与重巽的特殊因缘,所以他所接受的佛教思想,确实是以天台宗为主导的。这也是性之所近致然。所以“统合儒释”之“释”,大体可认定为天台宗。
历来对柳宗元的思想和文学进行阐释的专著和论文比较多。③有代表性的有孙昌武《柳宗元传论》《禅思与诗情》﹑陈若水《柳宗元与唐代思想变迁》﹑ 张勇《柳宗元儒佛道三教观研究》﹑ 骆正军《柳宗元思想新探》﹑松本肇《柳宗元研究》等论著,此外尚有赖永海《柳宗元与佛教》﹑王国安《读〈巽公院五咏〉兼论柳宗元的佛教信仰》﹑《论柳宗元的佛教天台宗信仰》﹑杜寒风《柳宗元与佛教禅宗的问题》等论文;此外还有《柳宗元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梁超然﹑谢汉强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柳宗元的会议论文集和《啖助新〈春秋〉学派研究论集》(林庆彰﹑蒋秋华主编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0年版)等专题性的会议论文集。关于柳宗元受天台宗思想影响的表现,王国安先生《论柳宗元佛教天台宗信仰》一文做了很好的论述。该文列举了柳宗元受天台宗影响的种种具体表现,这都是正确的;孙昌武一直关注柳宗元的思想与文学,他的近作《柳宗元与佛教》[1],揭示了柳宗元接受天台宗的可能性途径,并对柳宗元在佛教影响下的思想创造进行了描述,论述较有创见,但似尚有进一步开拓的空间。笔者认为,柳宗元的天台宗思想成分并不局限于种种具体的表现,而是在天台宗的根本思想上,他都有深入的摄取。中道、现实精神、柳宗元的经权观等都是柳宗元基础性的观念,但都体现出在对儒学和天台宗教理的统合基础上的思想创造。如中道与既与儒学的“中庸”有关,又与天台宗的“中道实相”有甚深关系;柳宗元的现实精神既有取自儒学的一面,又与天台宗重视假谛的救世情怀相通;柳宗元的经权观虽有《春秋》学的背景,但体用一如的思维方式无疑主要是受佛教影响的,其具体见解与天台宗“开权显实,发迹显本”的思想的具有内在关联等。但本文不打算在思想层面上展开论述柳宗元与天台宗的关系,而尝试对柳宗元的山水文学通观并察,从文学的角度探讨天台宗的思想和意蕴是如何深入地渗透到其创作中的,从而对柳宗元与天台宗的关系以及柳宗元的山水文学(尤其是山水散文)的佛教意蕴有更准确的认识。
从与天台宗思想的关系来看,柳宗元那些艺术成就高的山水文字可划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愚溪诗序》等与天台宗“圆顿止观”有直接体现关系的;另一种类型是与天台宗“圆顿止观”的关系虽然不能确切指实,但可以认定是在与之一致的朴素禅观上有精神上的相通之处的。
二
《愚溪诗序》:
溪虽莫利于世,而善鉴万类,清瑩秀澈,铿鸣金石,能使愚者喜笑眷慕,乐而不能去也。余虽不合于俗,亦颇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而无所避之。[2]1607
鉴,即照,智顗:“法性寂然明止,寂而常照名观。”(《摩诃止观·明缘起》)鉴,即是“止观”。“莫利于世”的溪水与“不合于俗”的作者相类,溪水“善鉴万类”,而宗元“以文墨自慰,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可以说,澄澈的溪水是作者心体的意象化。作者的心体因为澄澈,所以能把外在万物都能在其中呈现。这些被呈现的万物杂然纷陈,有净有染,却不外在于心体。所谓天台宗的“性具善恶”之说便是如此。如果依照如来藏性说(如华严宗和达摩禅),此清净心体自是根本,把外在万物予以消泯,返归清净心体,即达成目的,而不必“无所避之”地去“牢笼百态”。天台宗的“性具说”很独特,迥异它宗,中唐湛然等人特别在此说上发挥,以示区别于它宗的优胜之处。在天台宗看来,心性本具善恶,一念心就能呈现三千大千世界,要成就“圆顿止观”,只需在一念心中观照此三千大千世界,观照此恶,从恶之上转成实相而又不离此恶,因为实相本就不离此恶。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柳宗元的山水文学可谓自有特质,它背后的精神就是天台宗的“一念三千”和“性具”说。所谓“漱涤万物,牢笼百态”背后的思想依据就是“一念三千”。
序文又说到“染溪”的得名:“或曰:‘冉氏常居也,故姓是溪为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谓之染溪。”笔者大胆猜测作者在这里采取了隐晦的笔法,欲显故藏,后一种说法才是宗元的本意,所谓“染溪”,即是染心,或曰善恶本具之性,与以“愚溪”之名意趣相同。可能这个溪本名是冉溪,但宗元倾向于染溪之名。后面又说:“今予家是溪,而名莫定,而土之居者尤齗齗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曰愚溪。”意思是大家在冉溪还是染溪上争执不下,所以索性另取名。实际上,柳宗元诗文中数次出现“冉溪”或“染溪”,绝大部分是“冉溪”。可见此溪原名是“冉溪”,那些诗文也具有纪实性质。另外取名“愚溪”,只是局限于本文和与此相配的一组诗,同解释“染溪”之名的含义一样,恐皆是作者私意。所以笔者认为柳宗元笔下的“染溪”和“愚溪”二名,实际上都在强化这样的命意:自性本恶本染,乐意以此自处。柳宗元私意可能是并存“染溪”和“愚溪”二名,相互映衬。只是在行文中多些曲折意趣。该文在文体上是一篇说心说性文字,行文中有遮显隐藏,与纪实性质颇不同。类似于陶渊明《桃花源记》,文笔上有一些诡谲。当然,这一点是笔者的猜想,姑陈于此。如果此说有一定道理,那么可以说,此文的内在意旨可能并不只是纯然地以反语自我解嘲,而是表达自己对心性的悟解。或者说,两个层面的意蕴都有,一个是感情上的,一个是思想上的。一个浅层,一个是深层的。正如同宗元在文中引用过的愚公的故事所体现的,自我嘲弄是古代失志士人表达失落情绪的传统。作者一定程度上沿用了这种手法,但又赋予其新的意涵
以愚辞歌愚溪,最后归结为:
则茫然而不违,昏然而同归,超鸿蒙,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
用玄学化的语言,实际上阐明的正是即空即假即中的“三谛圆融”的实相境,这个实相境并非纯然的空或无,而是真常妙有的,是一个“浑沦圆具之大全的虚空”①此语是董平先生对天台实相的概括描述,见氏著《天台宗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68页。。总的意思是悟得真实,更无所待。
上述分析可以与记录与天台宗人相过往的诗句和游记予以参照。《法华寺石门精室三十韵》写由精室见弘旷之景并抒发对天台佛理的妙悟:
结构罩群崖,回环驱万象。小劫不逾瞬,大千若在掌。体空得化元,观有遗细想。[3]
所谓回环驱万象,写精室位置高峻,有驱赶万象﹑含纳万象之势。这引发下句“小劫不逾瞬,大千若在掌”,即“一念三千”的解悟。这与《愚溪诗序》:“漱涤万物,牢笼百态”同义。“体空得化元,观有遗细想”,意思是即空即假即中的圆融之境,与“一念三千”一致,一为经,一为纬,是为中道实相。
《永州龙兴寺西轩记》:
夫室,向者之室也;席与几,向者之处也。向也昧而今也显,岂异物耶?因悟夫佛之道,可以转惑见为真智,即群迷为正觉,捨大暗为光明。夫性岂异物耶?孰能为余凿大昏之墉,辟灵照之户,广应物之轩者,吾将与为徒。
此处体现出“性具染净”和修善开悟的观点。正是天台宗的性具说和修行方法。在中唐,佛教的心性说大概有两种,一是天台的“性具善恶”说,一是华严宗和禅宗达摩禅②祖师禅是否是如来清净心系统,学界有两种看法,一是牟宗三和吴汝钧认为祖师禅是近于天台宗的性具善恶说的,与如来藏系统不同,其修行基础是染心。分见牟宗三《佛性与般若》,吴汝钧《中国佛学的现代阐释》二书论禅宗的部分。二是印顺法师认为祖师禅和达摩禅都是以如来藏清净心为根本,二者并无实质不同。见印顺《中国佛教论集》,中华书局,2010年,第87--90页。大部分人持后说。主张的性本清净说。前者主张众生与佛,都是性具善恶的,众生不脱善性,而诸佛不脱恶性,众生与佛的差别在于,众生舍弃修善而为无明所障,诸佛虽具性恶但断尽修恶,修善至解脱境界,众生要转凡成圣,必须修善开悟。[4]后者主张佛性是本来清净的,人之所以不能成佛,是因为这清净性为妄念所覆,只要悟得此身是妄念所致,那么就能复返本性,形成正觉。因此,前者修行以染心为基础展开,即染心而转净,并不断除性恶。善恶原本是一物,只是观照不同,因为善恶相即,所以就为观染心而成解脱提供了可能;后者是以净心(本体)为基础,去除外尘(现象)才能返回净心。善恶是对立的,本体与现象相对,最后返归本体。柳宗元所说,与复返初心的修行方式不同,是以“向者之室”(性)为基础进行,这“向者之室”是昏暗着的,通过“凿大昏之墉,辟灵照之户”,即修善开悟,使黑暗转为光明。作者感叹,“室”是“向者之室”,席与几也没变,但前后显昧不同,“性”和“室”也一样,是“性”和“室”本身变化了吗?明显没有,是观照方式变化了。“广应物之轩”,“止观”的目的并非纯然出世,并非排斥假谛的空,天台宗的实相境不离此间,所以“广应物之轩”。所以三千世界是无限广大的。此文又说“以贻巽上人焉”,是敬服并称许重巽为自家佛学导师,认同其天台教义之意。
其它作品也可与此参照。《永州龙兴寺净土院记》:
上人者,修最上乘,解第一义。无体空折色之迹,而造乎真源,通假有借无之名,而入于实相。境与智合,事与理并。[2]1867
巽上人已经悟到圆顿境界。“体空折色”,是空谛,“无体空折色之迹”,即是即空即假,与“通假有借无之名”意思一样,即空即假,也意味着不执取于空,不执取于假,即是即中,即空即假即中,即是“实相”。
《永州法华寺新作西亭记》也是以伐去障目之丛林以见大观的经历来寄寓佛理感悟。他感叹法照:
余谓昔之上人也者,不起宴坐,足以观于空色之实,而游乎物之终始。其照也逾寂,其觉也逾有。然则向之碍之者为果碍也?今之辟之者为果辟也?彼所谓觉而照者,吾讵知其不由是道也?岂若吾族之挈挈于通塞有无之方,以自狭也。
谓由止观得慧解,则性之善恶染净一并泯灭,原来的障碍并非障碍,获证的清净也并非清净,一并消泯于诸法实相,此实相即“一念三千”。一念中含具三千大千世界,所谓游乎物之终始,即是说此三千大千世界。不执著于“通塞有无”,即是不执分别心,否则以一念心作为观照对象时又起一种执心,执上加执,只有静观一念,不起执着,才能进入实相。
三
对此实相中的自由境界的刻画与《愚溪诗序》结尾可以相比照的,如《始得西山宴游记》:
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攒蹙累积,莫得遁隐。萦青缭白,外与天际,四望如一。……悠悠乎与颢气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心凝形释,与万化冥合。
这勾描出一种自由解脱的境界。心与“万化”相冥合,实际上是心境不二,境观合一。《钴鉧潭西小丘记》:
枕席而卧,则清泠之状与目谋,滢滢之声与耳谋,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
以上两处文字皆与写天台后学的承远法师的《南岳弥陀和尚碑》相类似:
一气回薄茫无穷,其上无除下无终。离而为合蔽而通,始末或异今焉同。虚无混冥道乃融,圣神无迹示教功。
《南岳云峰寺和尚塔铭》塔主是天台宗的法证,也说:“气混冥兮德洋洋。”也是以气的混冥来说明这种圆顿的止观体验。使用了玄学化的语言,但佛教与玄学本就关系甚深。柳宗元在此描述的“虚无混冥”之境,实际上还是天台宗的“中道实相”。因为天台宗的实相如董平先生所说,“它本身原是一浑沦圆具之大全的虚空”。[5]68悟得实相,实现了真正的自由,因此笔下活现出处处存在而灵动不居的佛性。《小石潭记》: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
此句妙在写出了对自由解脱之境的向往,这条鱼可以说是宗元向往的一颗自由心。水性为空,但又不舍离此空性之水,鱼游于其中,即空即假,在中道中妙得自在。此句又作:
披拂潭中,俯视游鱼,类若乘空。[2]1913
“乘空”一语,似更能妙得此义。
四
更广泛的意义上,柳宗元的许多美妙的描写都可视为止观或禅观下的境界。天台宗的止观,也就是佛教通义的“禅”,含义是相同的。太虚说:“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6],意思就是说在中国影响大的那些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等都是由禅修实践演化而来,只是各宗在义解上不同,所以称为各种宗派。但各宗的一些基础性的实践都是相同的。而对于圆顿境界,各宗对达到此境的义解往往不同,比如天台宗是以“三谛圆融”和“一念三千”作为实相的义解,而禅宗以去除杂然,返回清净心或直接顿悟清净佛性为义解,是不同的,但作为最终所证悟到的境界的特点也还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佛教普遍承认一种“根本无分别智”的直观认识,在此认识之下,全部是符合真理的现量境。柳宗元笔下的一些美妙的描写,很难指实为天台宗圆顿止观下的直观境界,但可以说是与天台圆顿境界相一致的各宗都追求的直观境界。其实从柳宗元对禅宗排斥态度来看,说他是天台止观境也是不错的。以下描述可称为朴素禅观下的灵妙境。
柳宗元对流水的描写,能在境上无住,得跳脱灵妙的妙趣。《袁家渴记》:
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浅渚,间厕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白。舟行若穷,忽又无际。
《石渠记》:
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鲜环周。又折西行,旁陷岩石下,北堕小潭。潭幅员减百尺,清深多鯈鱼。
《石涧记》: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为底,达于两涯。若床若堂,若陈筵席,若限阃奥。水平布其上,流若织文,响若琴操。
这种细致的观照隐然有一种游戏意味,是自由心的体现。其实禅观,或曰止观,本有两种形态,一是静态的,一是动态的,吴汝钧曾分别以“三昧”和“游戏”这两种表现来指称[7]。这两种禅法当然也存在于天台宗的完整的修行实践中。既有静默的止观功夫趋近“定”境,又有定境中灵动自由的境界。柳宗元的山水文字有的以静默证会见长,有的以灵动自由见长。就是相应的体现。
“超摅藉外奖,俛默有内朗。”(《法华寺石门精寺三十韵》)通过山水旷景对心境脱离尘染执着的“外奖”作用,促发“内朗”慧性的显现。宗元的山水文学与佛教的关系,是可以通过他的这句诗来做基本概括的。
柳宗元的性灵的感发不仅来自于他的止观实践和对实相的悟解,而且还与另一种思想有关。如前所述,在众生的佛性问题上,天台宗持乐观态度。湛然发展了智顗的佛性论,更明确地提出“无情有性”说。这在当时,是针对华严宗把佛性限定在有情众生的范围内而发的,同时禅宗的神会一系也认为只有有情才有佛性。湛然之说有很大影响,董平先生说:“尽管无情有性实际上并不是湛然的首创之说,经过湛然的竭力提倡,这一学说才真正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天台宗在中唐时期的中兴,在很大程度上须归结为湛然无情有性说在当时佛教界所造成的影响。”[5]232.“无情有性”认为草木瓦砾都有佛性,这带有泛神论倾向的观念与山水审美心理具有一致性。柳宗元的山水文学渗透了因这种观念而带来的灵性。五古《自衡阳移桂十余本植零陵所住精舍》写把桂木移植到龙兴寺后“路远清凉宫,一雨悟无学。南人始珍重,微我谁先觉?”清凉宫,即龙兴寺。无学,丁福保《佛学大词典》:“声闻乘四果中,前三果为有学,第四阿罗汉果为无学。学道圆满,不更修学也。《法华玄赞》一曰:“戒定慧三,正为学体,进趣修习名为有学,进趣圆满止息修习,名为无学。”又,荆溪湛然《摩诃止观辅行传弘诀》:“放心就枕。头未至枕,便得无学”,礼贤注此句:“台宗三祖慧思大师亦复如是,如云:‘夏竟受岁将欲上堂,将放身倚壁,豁然大悟法华三昧。”[8]柳诗正是写天台僧人重巽所主持的龙兴寺,所以“无学”意指法华三昧。在这里指得圆满实相。雨,比喻演说佛法。智顗《法华文句》卷第七上解:“如来即是云,闻法即是雨,读诵修行即是润,功德即增长。”又,佛经中经常用“雨花”表示演说佛法感引诸花降落,如《法华经序品》曰:“是時天雨曼陀罗花,摩诃曼陀罗花,曼殊沙花,摩诃曼殊沙花,而散佛上,及诸大众。”因此,“雨”在这里隐喻演说佛法。“路远清凉宫,一雨悟无学”,是说桂木因接近龙兴寺,感应佛智,使本有佛性得到开显。这首诗是对无情有性思想的形象化描述。末句“芳意不可传,丹心徒自渥”,作者感叹草木都能证悟佛性,但无法将这种证悟传达给自己;自己对之也深感惭愧。①牟宗三先生认为荆溪湛然的“无情有性”之说“‘有性’者亦有佛性,此所有之佛性即法性义之佛性……但此并不表示草木瓦石亦有觉性之佛性,而能自觉修行而成佛也”,(《智的直觉与中国哲学》,《牟宗三先生全集》第20册,联经出版公司,2003年,第412页)即认为草木瓦石的佛性只是“性理”,而非“性智”,因其不具“心”。这一说法在“圆教”背景的阐述下自有道理,但“法性”在天台宗这里本是“智如不二”的,而且“无情有性”之说本就具有明显的泛神论色彩,因此,在这一思想观照之下,草木瓦石未必不可以理解为有“性”有“智”(或“心”)的。《晨诣超师院读禅经》:“遗言冀可冥,缮性何由熟?道人庭宇静,苔色连深竹。日出雾露余,青松如膏沐。澹然离言说,悟悦心自足。”首先说明佛教经典是修持的依据,没有经论就失去了修行的引导。然后描写早上所见清新景色,“苔色连深竹”,让人联想到与“无情有性”同一意思的出于作为禅宗别支的牛头禅的另一种说法“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而在日出时经过雾露沐浴过的青松,给人爽然而深邃的感觉,也大概寄寓了“悟悦心自足”的自性圆满的意义。
也有一些诗中的植物隐喻作者的遭际和感情,这种手法古来有之,但在柳宗元手中,植物与作者的精神达到了融合不二的程度,体现出作者视植物为性灵之物的思想。《湘岸移木芙蓉植龙兴精舍》:“有美不自蔽,安能守孤根。盈盈湘西岸,秋至风露繁。丽影别寒水,浓芳委前轩。芰荷谅难杂,反此生高原。”木芙蓉美丽芳艳,但在低僻处与芰荷为伍,于是作者移到位置较高的龙兴寺,以保护它的孤洁。对拥有美质的事物的怜爱,带有作者自重自伤的意味。《新植海石榴》:“弱植不盈尺,远意驻蓬瀛。月寒空阶曙,幽梦彩云生。粪壤擢珠树,莓苔插琼英。芳根閟颜色,徂岁为谁荣。”海石榴植非其地,也是作者的化身。也有写与植物相互依存的情感,视草木为知己。《种白蘘荷》写寻找并移植白蘘荷,藉以庇护自己这多病之身:“崎岖乃有得,脱以全余身。纷敷碧树阴,眄睐心所亲。”《戏题阶前芍药》写芍药陪伴自己度过孤寂的夜晚:“孤赏白日暮,暄风动摇频。夜窗蔼芳气,幽卧知相亲。”元好问曾选名家花卉诗九首,以此为第一,即因作者在无情之物上见出特深之情,“怨之愈深,其辞愈缓,得古诗之正,其清新婉丽,六朝辞人少有及者”[9]。这些花草都是有性情的精神伴侣。
五
综合来看,柳宗元不但在思想上“统合儒释”,借助天台宗的思想资源有一定的思想创造,而且,在审美意识和文学创作方面,柳宗元在天台宗的教理的深入影响下,也创作出了一系列文学成就突出的山水文学作品。这些作品中所渗透的天台教理可以说是深透而细密的。柳宗元的山水文学,其佛教意蕴虽然曾得到学者们的注意,但如果不能清晰地认识到天台宗的教理对其山水意识的深入影响的事实,这种认识就是有欠缺的。笔者贡献自己的浅见于上,期待方家批评。
参考文献:
[1]孙昌武.柳宗元与佛教[J].文学遗产,2005,(3):73-81.
[2]柳宗元撰.尹占华,韩文奇校注.柳宗元集校注(第五册)[M].北京:中华书局,2014.
[3]柳宗元著.王国安笺释.柳宗元诗笺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8.
[4]赖永海.中国佛性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174.
[5]董平.天台宗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太虚.佛学入门[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0:8-9.
[7]吴汝钧.中国佛学的现代诠释[M].台北:文津出版社,1995: 128-129.
[8]隋智者大师说.章安灌顶录,荆溪湛然撰,定海沙门礼贤注.摩诃止观辅行传弘诀辑注[Z].自印本,2010:1059.
[9]章士钊.柳文指要[M].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1469-1470.
(责任编校:张京华)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219(2016)08-0006-04
收稿日期:2016-06-15
作者简介:范洪杰(1985-),男,山东泰安人,北京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