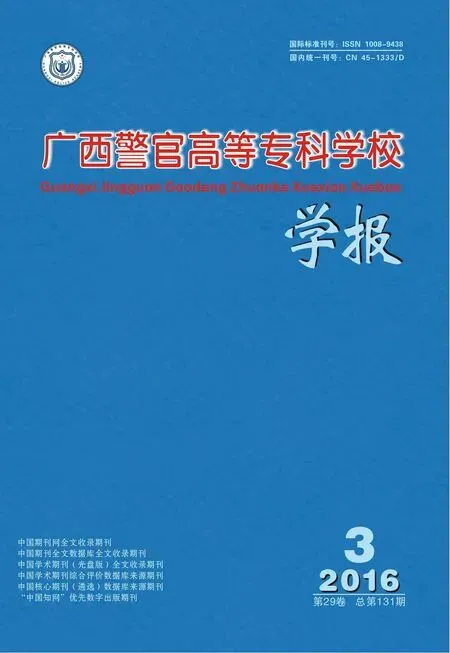亚文化理论视域下“疆独”暴力恐怖犯罪研究
吴丹
(江西警察学院 侦查系,江西 南昌 330010)
亚文化理论视域下“疆独”暴力恐怖犯罪研究
吴丹
(江西警察学院侦查系,江西南昌330010)
在亚文化对抗主流文化的过程中衍化出极端姿态及仇视情绪,则极易催生出犯罪行为。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具有的亚文化特征,是“疆独”暴恐犯罪生成的动因。因此,一方面应从宏观的中华主流文化引领层面促进新疆地区民族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从微观的文化治理技术层面建立应对“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传播与扩散的长效机制。
“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
近几年,“疆独”暴力恐怖犯罪活动有抬头之势,其暴恐行径嚣张猖狂,犯罪触角从新疆延伸至内陆城市,其犯罪手段之残暴令人发指,给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危害。“疆独”暴恐犯罪活动以对抗政府、破坏国家统一与民族团结为目的。本文拟从犯罪社会学亚文化理论视角出发,探析“疆独”暴恐犯罪的亚文化内涵及亚文化背景下“疆独”暴恐犯罪活动的生成,并从文化层面提出应对“疆独”暴恐犯罪策略。
一、亚文化理论
从亚文化视角研究犯罪现象早在20世纪50年代西方犯罪学界就已开展了,美国社会学家、犯罪学家艾伯特·科恩最早提出“亚文化”并用来分析犯罪行为。他在《少年犯罪者:帮伙文化》一书中从“亚文化”的视角解释少年犯罪问题。在他看来,犯罪活动中存在着亚文化现象。亚文化就是犯罪亚文化,犯罪(尤其是帮伙犯罪)与亚文化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两个概念[1]。美国犯罪学家沃尔夫冈和意大利犯罪学家费拉柯蒂基于科恩的亚文化理论分析范式提出了暴力亚文化理论,认为暴力亚文化环境对暴力犯罪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其中暴力是一些群体亚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渗透到群体成员的心理品质之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犯罪就是使用暴力作为手段来解决日常生活问题的结果[2]。随后,美国犯罪学界的研究学者将犯罪亚文化理论进一步发展,扩大了犯罪亚文化理论的解释范域,以解释不同类型的犯罪行为。犯罪行为的亚文化理论分析剥离出了犯罪背后的文化因素,但不是强调文化是导致犯罪生成的直接因素,文化作为诱因在一定程度上促成犯罪的产生。在亚文化理论视域内,社会成员被不同的文化模式赋予生存的意义,文化模式为社会成员提供行为规则与价值判断依据,社会成员正是以所处的文化模式作为行为参照系做出相应的行为选择。而在社会体系中,不同文化模式有主流与次流之分,在亚文化理论看来,主流文化是一种文化构建,规范着人们的行为举止,使社会形成普遍的行为模式,亚文化作为非主流文化(即次流),用直接或有意的方式对抗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3]。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对抗是文化冲突的表现,是两种文化体系在行为规则和价值观念的对立。若在亚文化对抗主流文化的过程中衍化出极端姿态及仇视情绪,则极易催生出犯罪行为。亚文化理论为研究犯罪现象提供了将微观个体行为选择与宏观文化环境相结合的分析视角,运用亚文化理论观点探析“疆独”暴恐犯罪使我们深刻认识“疆独”暴恐犯罪生成的内在文化因素。
二、“疆独”暴力恐怖犯罪的亚文化动因
“疆独”暴力恐怖犯罪是由“疆独”势力实施的以暴力恐怖为手段来谋求新疆“独立”的犯罪活动,“疆独”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的发生有一定的文化语境。正如严景耀先生所指出:犯罪“是依据集体的一般文化而出现的,它既不是一个离体的脓包,也不是一个寄生的肿瘤,它是一个有机体,是文化的产物。”①严景耀,《中国的犯罪问题与社会变迁的关系》,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疆独”暴力恐怖犯罪内含的文化要素与“疆独”势力的历史形成过程密切关联。在“疆独”势力历史形成过程中,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恐怖主义逐渐成为“疆独”暴恐犯罪的文化动因,是“疆独”暴恐犯罪的内在文化要素,共同作用着“疆独”势力的暴恐行径,对“疆独”暴恐犯罪提供意义支撑及“合法性”论证。所构成的“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与我国主流文化体系相对立,带有明显的越轨(犯罪)亚文化色彩,与我国主流文化相背离,并形成挑战。
(一)宗教极端主义亚文化
宗教极端主义是在信仰极端化、行为狂热化、宗教政治化和组织诡秘化过程中发生异化、演变而形成的[4]。宗教极端主义是宗教异化的产物,主张通过暴力和极端方式实现涉俗性目的,如推翻世俗政府,建立政教合一的神权政权。宗教极端主义具有极强的煽动性、蛊惑性,为以宗教名义而进行的违法犯罪活动予以价值认同。“疆独”暴恐分子在实施暴恐犯罪活动中从伊斯兰教中汲取精神力量,但伊斯兰教作为宗教本身并不是暴力恐怖犯罪发生的原因,而是伊斯兰教的“极端”取向转变引起的极端主义思想的形成,促使了暴力恐怖犯罪行为的产生。伊斯兰教中“极端”取向转变有历史与现实缘由,但离不开信奉者本身对伊斯兰教的曲解。可以说,伊斯兰教的“极端主张”是部分信奉者对伊斯兰教教义歪曲理解的产物,“极端”主张的体系化促使伊斯兰教极端主义的形成,为“疆独”分子实施暴恐犯罪活动提供了精神支柱。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摒弃了伊斯兰教中的积极有益成分,将伊斯兰教教义中的“圣战”观念进行歪曲解读。按照传统的伊斯兰教教义理解,“圣战”是出于自卫的反抗,是对抗压迫、伸张正义的途径,却被“疆独”暴恐势力曲解为对抗异族或异教徒。受伊斯兰教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疆独”势力积极鼓吹“圣战”,主张通过暴力恐怖活动来践行“圣战精神”以实现神权支配下的政教合一国家的建立,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伊斯兰教极端主义强调自身极端文化的合理性及唯一性,其追崇者在极力排斥他文化和对抗主流文化的基础上构建封闭、狭隘的宗教极端主义亚文化圈,而隶属于这种亚文化圈的“疆独”势力追逐的宗教理想已不是伊斯兰教所倡导的宽爱、人道与和平。在宗教极端主义亚文化的熏染下,“疆独”分子将自身的暴恐行径加上神圣的光环,为实施暴恐犯罪谋取神意支持,并在自身的合理性解释中论证所谓的暴恐“道义”。
(二)民族分离主义亚文化
民族分离主义,又称民族分裂主义,是指一个或几个民族的极端势力在一个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多民族国家内要求建立新的主权国家的主张。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主要通过政治诉求、暴力活动甚至武装对抗手段达到其政治目的[5]。在现实的民族分离活动中,民族分离主义势力以“民族自决”为行动的理论依据,打着维护本民族文化纯正性的口号,在排斥、损害他民族利益基础上极力强调本民族“利益”的至高无上性,主张以暴力恐怖手段来争取所谓的民族“独立”,进而威胁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是在民族分离文化的滋育与影响中产生。而“疆独”势力的民族分离主义文化是在“泛突厥主义”的传入、蔓延与扩张的漫长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疆独”势力的“泛突厥主义”思想,主张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联合起来在中亚、西亚和中国新疆地区建立“大突厥斯坦国”,为“疆独”势力从事民族分裂活动提供精神源泉与价值认同。“疆独”势力企图从“泛突厥主义”思想中找寻从事民族分离活动的理论根据,利用“泛突厥主义”思想塑造民族分离的心理及思维定势,并在此基础上编造分裂言论。在这一过程中“疆独”势力将“泛突厥”思想内化,逐渐形成民族分离意识,对其他民族文化予以排斥与疏离,以此固化“疆独”势力的文化疏离与民族分裂意识,促使“疆独”势力抵触、仇视与本族群文化传统相异的他民族文化体系,是一种极力强调自我封闭的民族分离主义亚文化。可以说,民族分离主义亚文化是建立在文化疏离意识基础上的与主流文化相对立的亚文化,而文化疏离极易导致政治分离[6]。政治分离是民族分离的国家政治话语表述,民族分离的最终目的是政权割裂,实现国家层面的政治分离。而“疆独”势力在以“泛突厥主义”思想为基础的民族分离主义亚文化共享中,错误地论证了其从事民族分裂犯罪活动的“合理性”与“价值性”。
(三)恐怖主义亚文化
恐怖主义主张通过使用暴力恐怖手段来制造社会恐慌,将不确定的多数人置于恐怖氛围之中,以此向国家主体施压,实质目的是要实现一定的政治要求。恐怖主义是暴力与政治相结合的产物,是基于某种政治诉求的暴力化和极端化的意识取向与行为表现。暴力恐怖和政治诉求是恐怖主义的本质,彰显着恐怖主义文化内涵,恐怖主义文化又为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提供了“合理化”解释。“疆独”势力的暴力恐怖犯罪活动是恐怖主义实践化的具体体现,恐怖主义是“疆独”势力进行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的理论主张。在“恐怖主义”理论主张的支配下,“疆独”势力塑造从事恐怖犯罪活动的“价值”及“道义”,开脱危害社会的罪恶感,他们构筑恐怖主义亚文化体系,破坏、侵蚀主流文化,并将恐怖主义亚文化凌驾于主流文化之上,用恐怖组织规则取代国家和国际法律规则,模糊、淡化乃至完全忽略其恐怖手段的非法性[7]。同时,受恐怖主义亚文化的影响,“疆独”势力将暴恐作为追求所谓本民族“独立”的重要方式,漠视生命价值,实施暴恐犯罪不计后果,而是充满所谓的“正义感”与“使命感”。“疆独”势力的恐怖主义亚文化是背离主流文化的越轨文化,其组织化、体系化的发展趋势加剧了同主流文化的抵触与对抗,已成为威胁主流文化和谐构建的现实因素。
三、亚文化视域下“疆独”暴力恐怖犯罪的生成
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是“疆独”势力以极端暴力恐怖方式从事民族分裂犯罪活动的文化因子,三大亚文化要素促成“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圈的形成,为“疆独”势力的民族分裂犯罪活动提供文化理解及意义论证,通过思想教化和行为示范影响了“疆独”组织成员的暴恐行为选择,助推了暴恐犯罪活动的生成。
(一)“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的思想教化作用
文化是构成社会不可或缺的因素,社会个体的价值取向、思维习惯和思想判断潜移默化地深受所处文化环境的影响。亚文化是存于主流文化内部而又与主流文化相异的文化体系,而带有越轨色彩的亚文化往往主张以犯罪和极端的行为方式抵触、排斥主流文化的价值理念。越轨亚文化体系内的个体成员在价值定位、思想观念方面接受越轨亚文化所倡导的文化理解模式,内化“越轨”思想,根植“对抗”与“冲突”思维,主张以非制度、非理性、非法化方式攻击、侵蚀主流文化,宣泄“越轨”情绪,并通过所谓的“合理性”与“合情化”的思维路径遑论越轨行为的价值与意义,在与主流文化的“对抗”中寻求“越轨”利益诉求的所谓“正当化”表现。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是“疆独”分子从事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的内在文化动因,是与主流文化对立的越轨亚文化要素。所构成的“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本身具有隐匿性、跨区域性、传染性特征,嵌入主流文化体系内,传播暴力恐怖和民族分裂的越轨主张,同时,促成了“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圈的形成。“疆独”分子的暴力恐怖犯罪行为深受“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圈的“辐射”效应影响,暴恐犯罪亚文化圈是“疆独”分子从事暴力恐怖、民族分裂犯罪活动的文化“场”。文化的“场”效应具有极大的穿透力、吞噬力和征服力[8],具有一定的思想“辐射”作用。“疆独”分子置身于暴恐亚文化圈内,受到以“暴恐”“分裂”为主导内容的价值判断模式的潜移默化影响,思想上接受暴恐和分裂亚文化的“洗礼”,内化“暴恐价值”,并把分裂主张作为暴恐犯罪行为的核心动因,形成了以民族分裂为最终目的的“暴恐犯罪”思维。
(二)“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的行为示范作用
社会存有多种文化形式,不同的文化形式为社会个体理解事物提供不同的视角与思考模式,为个体的行动实践提供不同的参照系。文化是个体存在的精神归属,也是规范个体实践的价值系统,为个体的行为选择铸造着意义框架,个体在意义框架中阐释着自身行动的意义。亚文化构筑的意义解释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有别于主流文化编织的价值意义系谱,且在某种程度上与主流文化的核心价值原则相冲突,越轨亚文化对主流文化价值的冲击与侵蚀是这种冲突的主要体现。受亚文化影响的行为个体,在行动实践中往往容易接受“越轨”文化的价值指引,认同“越轨”行为的价值意义,做出与主流文化精神内涵相背离的行为选择。“疆独”势力所构筑的以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为内容的暴恐犯罪亚文化,为“疆独”分子实施暴恐犯罪活动提供了“暴恐”行为范式与“暴恐”行为准则,强化了“疆独”分子对以民族分裂为目的的“暴恐”文化的认同,促使“疆独”分子为了追逐所谓的“民族独立”而不择手段地实施极端血腥的暴力恐怖犯罪行为。可以说,“疆独”暴恐亚文化中的“暴恐”行为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行为示范”的效应作用,置身于“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圈内的“疆独”分子,按照暴恐亚文化提供的行为参照系统进行“暴恐”行为。在暴恐犯罪亚文化的熏染下,依循“暴恐”逻辑为民族分裂和对国家危害的暴恐行为进行所谓“正当化”解读。在具体的暴恐犯罪活动中,通过“暴恐”实践化途径发挥暴恐犯罪亚文化的“行为示范”效应,形成“疆独”分子进行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犯罪活动的组织化和集团化发展趋向,也促使无意识、无理论的暴恐犯罪活动转向有意识、有理论层面。
四、“疆独”暴力恐怖犯罪文化应对策略
综上所述,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亚文化要素是“疆独”暴恐犯罪活动的意义源泉,构成了“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圈,通过思想教化和行为示范,直接影响“疆独”分子暴恐行为的选择,并为“疆独”势力实施暴恐犯罪活动提供了“合理性”“合法性”及“价值性”的意义支撑。“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的传播性和跨区域性决定了“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圈具有扩张态势。而“疆独”暴恐亚文化圈的层层扩大意味着以民族分裂为目的的暴恐亚文化影响效应的增强,间接拓宽了“疆独”势力的暴恐犯罪活动区域,增强了其暴恐活动能量,也增加了对国家安全的现实危害程度。因此,抑制“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的生长与扩张对有效预防打击“疆独”暴恐犯罪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何从文化视角遏制“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的生成与发展?一方面,从宏观的中华主流文化引领层面促进新疆地区民族文化的融合,增进民族文化的共荣与和谐,以消融民族分歧,瓦解民族分离的现实文化根基。另一方面从微观的文化治理技术层面,着手建立应对“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传播与扩散的长效机制。
(一)强化中华主流文化对新疆地区民族文化的整合力
主流文化是依仗国家权力、表达国家正统意识形态的文化体系,反映着国家的根本意志、文化趋向和价值观。其积极功能的充分和全面发挥是保证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步和民族团结的精神因素[9]。我国当代的主流文化蕴生于中华传统文化的意义命脉之中,立足于社会的流变与发展之中,当代主流文化的现代性诠释折射出主流文化的时代意涵。其实质是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影响下,构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核心内容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性质的中华主流文化,突出爱国精神,弘扬民族团结、国家发展、文化和谐和道德重塑的文化内涵。
一是发挥主流文化的引领和聚合作用。新疆地区民族文化的整合是建立在化解民族偏见、破除民族封闭的基础之上,以促进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强化民族文化的和谐共生,以实现民族共荣,消弭民族分离为目标。中华主流文化对新疆地区民族文化融合的引领与整合功用,体现在发挥主流文化的文化导向、文化凝聚、文化批判与文化调控作用上[10],同时发挥主流文化的国家认同功用。对于新疆地区少数民族异质文化,通过发挥中华主流文化的文化引领和文化聚合作用,以主流文化为轴心实现“精神”辐射,促进新疆地区民族文化与主流文化以及各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兼容,增进文化间的和谐与共生,减弱文化的相异性带来的意识分离与行为分离取向,以抑制新疆少数民族异质文化中分离和极端意涵的生成。
二是发挥中华主流文化的文化批判和文化调控作用。要提高新疆地区党政组织对宗教极端、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等越轨(犯罪)亚文化的管控能力,并提升新疆民众对危害国家安全文化的鉴别能力,营造文化安全的良好氛围,压缩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犯罪亚文化的生存空间。
三是发挥好主流文化的国家认同功用。“疆独”暴恐犯罪分子将民族认同置于国家认同之上,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及价值理念,极力强调本民族文化的异质特征及与其他族群文化的差异性。进而逐渐发展成民族自我中心意识,忽略国家认同的价值意涵,在损害其他民族利益乃至国家利益的基础上捍卫所谓的“民族独立”。对此,通过发挥中华主流文化国家认同的功用,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神内涵,突出爱国主义对国家发展、民族和谐共处的现实意义,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中和”精神,营造文化“和合”氛围,进而铲除滋生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暴力恐怖主义亚文化的瘟床。
(二)建立应对“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长效机制
“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的生存与扩散依托于特定的传播平台与渠道,是在一定的空间实现暴恐犯罪亚文化的扩张。要从微观的文化治理技术层面,压缩“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生存空间,切断宗教极端文化、民族分裂文化和暴恐文化的传播渠道,堵塞传播路径,摧毁传播平台。
一是针对“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的持续传播要建立监测、预警、处置和打击等多位一体的长效应对机制。形成多部门联动、多手段结合、多途径并进的应对模式,促成文化监控、情报预警、宣传动员和打击处置的治理结构。主要是通过完善文化管控工作制度,特别是对文化传播的传统媒介(电视、广播、图书、音像制品)及新型媒介(互联网、手机),要加强监控工作,以提升对“疆独”暴恐亚文化的监测、控制能力,及时发现民族分裂、暴力恐怖、宗教极端的文化因子,阻止其传播与扩散。
二是公安和国家安全部门应建立高效的情报信息工作机制。通过日常情报工作,鉴别和筛选出冲击主流文化,对危害国家安全的“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信息进行综合研判,提高对“疆独”暴恐文化防范水平。
三是动员社会力量,整合民间资源,针对“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信息,布建覆盖面广、触角长的“捕捉”网。从整体、全局层面提高社会对“疆独”暴恐怖犯罪文化的鉴别力、批判力和抵制力,扼杀“分裂”和“暴恐”苗头,防止“疆独”暴恐犯罪活动形成气候。
四是依法打击。针对“疆独”暴恐犯罪亚文化的传播人员和传播组织,要以“发现一个,处理一个”的原则依照法律坚决予以打击处置。对于“疆独”暴恐亚文化的传播渠道与平台,实战部门应加强与传媒、电信和新闻出版等机构的合作,从技术手段层面阻碍宗教极端、民族分裂和暴力恐怖文化的现实性传播,净化文化传播空间,不给“疆独”势力传播以“民族分裂”为目的的暴恐亚文化有可乘之机。
[1]吴宗宪.犯罪亚文化理论概述[J].比较法研究,1989(3):81.
[2]吴宗宪.西方犯罪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369.
[3]陶东风,胡疆锋.亚文化读本[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5.
[4]金宜久.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16.
[5]夏光辉.当代民族主义研究[D].北京:中共中央党校,2010:89.
[6]张友国.后冷战时期民族分离主义研究[D].吉林:吉林大学,2005:84.
[7]康均心,王均平.恐怖主义犯罪的文化解读[J].犯罪学论丛(第二卷),2004:87.
[8]车洪波.文化作用方式之分析[J].学习与探索,2004(1):18.
[9]许士密.大众文化和主流文化、精英文化良性互动机制的构建[J].求实,2002(6):69.
[10]贾友军.大力培育和弘扬中华民族精神、时代精神是维护新疆地区主流文化安全的关键[J].新疆社科论坛,2013(2):82.
责任编辑:蒋玉莲
[Abstract]Extreme attitudes resentment derived from the process of subculture vs dominant culture tend to give birth to criminal behaviors, the sub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n the part of religious extremism, national separatism and terrorism are the motivation for generation of violent terrorist crimes of Xinjiang's pro-independence.Accordingly,efforts should be made, on one hand, to promote national culture integration in Xinjiang region from macro Chinese dominant culture guidance, and on the other hand, to develop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response to subculture dissemination and diffusion of violent terrorist crimes of Xinjiang's pro-independence from micro culture-based management technology.
[Key words]violent terrorist crimes of Xinjiang's pro-independence; subculture; religious extremism; national separatism; terrorism
Research on Violent Terrorist Crimes of Xinjiang's Pro-independence:A Perspective of Subcultural Theory
WU Dan
(Department of InvestigationJiangxi Police Academy,Nanchang 330010,China)
D631
A
1008-9438(2016)03-0084-05
2016-01-12
网络出版:http://www.cnki.net/kcms/detail/45.1333.D.20160519.1546.036.html
吴丹(1987-),女,江西吉水人,江西警察学院侦查系助教,法学硕士,主要从事犯罪社会学和国内安全保卫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