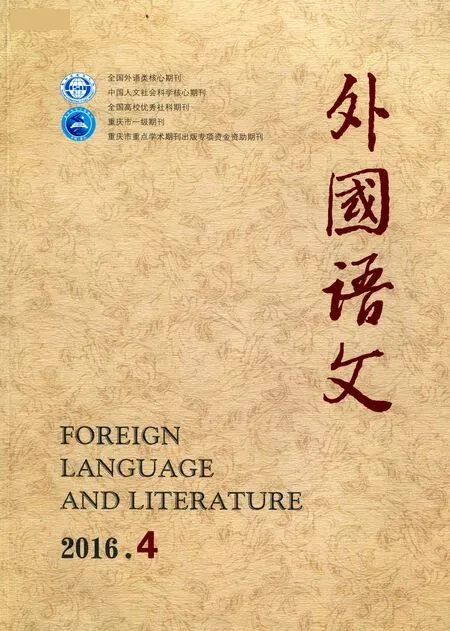西方重译研究述评
高 存
(天津商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134)
西方重译研究述评
高 存
(天津商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天津 300134)
西方的重译研究呈现出范式批评研究路径,主要体现在重译假设的建立以及围绕重译假设展开的承继性、系统性的实证研究中。这是西方重译研究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即在重译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呈现出动态连续性,试图通过“假设——实证——修正假设——实证”的论证方法,在不同程度上扩展或修正前人的重译假设,建立模型体系。与此同时,由于深陷于建立一套能描述一切重译发生规律、概括一切重译本发展趋势的重译假设的思维定势之中,以致无法触及重译过程中纷繁复杂的因素与现象,束缚了西方重译研究向前发展的脚步。
西方重译研究;范式批评路径;重译假设
0 引言
国外翻译界中的重译(retranslation)一词,一般而言有两层基本的含义,一是与我国翻译学者所谓的转译类似的“间接翻译”(indirect translation),二是指不同译者对同一原著的不同翻译,这与国内有些学者采用的“重译”概念相吻合。第一层含义主要源自甘比尔(Gambier)以及夏特尔沃斯和考伊(Shuttleworth & Cowie)分别于1994年和1997年对重译所下的定义,即“间接的”(indirect)、“中转的”(intermediate)或者“接力”翻译(Baker & Saldanha,2009:233)。第二层含义则更为通用,威廉姆斯与切斯特曼(William & Chesterman,2004:71)将重译定义为“某一文本被再次翻译到同一目的语的情形”。贝克和萨达纳(Baker & Saldanha,2009:233)同样认为重译主要指将此前曾译入同一语言的同一作品再次进行翻译的行为,或者指由这一行为产生的结果,如被重新翻译的文本本身。本文所探讨的重译,使用的是其第二层含义。
1 重译研究的历史与总体特点
1.1 研究历史
国外对重译现象开始关注并进行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法语期刊《重写本》(Palimpsestes)的特刊。在这辑特刊中,伯尔曼(Antoine Berman)提出了“重译假设”的概念。甘比尔在重译假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影响重译的几种因素,例如新译的市场销售潜力等,并明确号召对重译领域进行深入研究,这在重译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均未引起翻译学者足够重视的20世纪末,是较为可贵的。甘比尔与伯尔曼围绕重译假设进行的奠定性研究,构成了国外重译研究的第一次高潮(Paloposki & Koskinen,2010:29-49)。
依照帕罗波斯基和科斯金恩(Paloposki & Koskinen)(同上)的观点,重译研究的第二次高潮发生于本世纪初,是由凡德薛登(Vanderschelden)与巴拉德(Ballard)的研究引发而来的。凡德薛登受伯尔曼研究的启发,重点研究了后继翻译与前译相比之下的精确度与质量提升问题,同时还探讨了重译产生的动因,并做出如下的论断——“文学作品的一个译本被另一译本所挑战或超越,只是个时间的问题”;巴拉德参照歌德与伯尔曼的成果,一方面明确支持“每过一个世纪,伟大的著作便要被重译一次”的观点,但另一方面他也坦承,时间并非区分不同译本的唯一尺度,译者的风格倾向也是译本赖以区别开来的重要因素。科隆巴(Collombat)的研究与巴拉德一脉相承,也从译者的角度入手,研究重译问题,他认为正是因为不同时代的译者对所译文本与使用语境有着不断深入的理解,才使得新译本不断产生,译本的质量也得以不断提高。经过学者们在重译理论与实证领域的孜孜努力与不断研究,重译的高潮蓄势待发,此时,翻译研究杂志趁势追击,规模化推出重译研究的成果。2003年,《札记》(Cadernos)杂志推出了一辑“重译研究”专刊。2004年,《重写本》(Palimpsestes)再次推出“重译研究”专刊, 正式将国外的重译研究推向高潮。此后,国外的重译研究更是向着多元化的角度发展。威廉姆斯与切斯特曼(Williams & Chesterman,2004:78)将重译假设研究进一步深化,帕罗波斯基和科斯金恩(Paloposki & Koskinen,2010:29-49)则在总体梳理重译及重译假设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对重译假设的实证研究。同样就此论题进行实证研究的学者还有巴拉德、布朗利(Brownlie)、萨拉亚娃(Susam-Sarajeva)、普尔蒂宁(Puurtinen)等。他们的实证研究在部分证实重译假设的同时,均指向了其不足之处与过度简化的倾向。值得一提的是,布朗利在对重译假设进行验证的同时,还将叙事理论(Narrative Theory)引入了重译研究的领域。至此,我们大致完成了对国外重译研究历史的简单回顾。
1.2 总体特点
吕俊、侯向群(2009:212)曾明确指出,西方的译学研究主要采取范式批评的路径(paradigmatic approach),而我国的译学研究走的则是问题式路径(problematic approach),这样的划分虽然不是绝对的,但主流趋势是非常明显的。中西方译学上范式批评途径与问题式途径的区分,也体现在重译研究中。
在范式批评研究途径中,不同的研究者会按照某种科学观形成自己的“科学概念系统(scientific symbolism)”,建立“模型体系(scientific model)”,这样的理论模式或理论体系即被称为“范式(paradigm)”(吕俊、侯向群,2009:212)。西方重译研究中呈现的范式批评研究路径,主要体现在重译假设的建立以及围绕重译假设展开的承继性、系统性的实证研究中。这也是西方重译研究的第一个突出特点,即在重译理论体系构建过程中呈现出动态连续性,总体研究按照范式批评的路径,试图通过“假设-实证-修正假设-实证”的往复循环,在不同程度上继承、扩展或修正前人的重译假设,建立模型体系。第二大特点是在理论体系构建思路上呈现出一定的封闭性,深陷于建立一套能描述一切重译发生规律、概括一切重译本发展趋势的重译假设的思维定势之中,以致无法触及和解释重译过程中纷繁复杂的因素与现象。
2 重译假设与实证研究
2.1 重译假设研究
重译假设的建立以及围绕重译假设展开的一系列研究,构成了国外重译研究的一条主线。这一主线带动下的重译研究呈现出动态连续性,这是中西方重译研究中最大的不同之处。 “重译假设”这一术语源自法国翻译研究学者伯尔曼(Berman,1990:1-7)发表于《重写本》(Palimpsestes)特刊上的一篇论文。他的基本观点是,初译总是以文化或杂志刊登需要的名义,对原作进行同化,降低文本的“他者性”(otherness),重译则是面向源语文本的一种回归,因而翻译作为一种“不完整”的行为,只有通过重译才能趋向完整,翻译只有在贴近原作和表现出译者与源语的冲突两方面都获得成功时,才算达到了伯尔曼所谓的“完整”。在他看来,历来的翻译若以这一完整性加以衡量,都可算作失败,尤以初译本为甚(Baker & Saldanha,2009:233)。赞同伯尔曼所谓“重译回归论”的学者还有贝洛斯(Bellos),他指出:“重译是为保留原作结构与风格而进行的一种文本回归。”本西曼(Bensimon)认为,初译是为了将国外的著作介绍到目的语文化中而对其进行的一种“自然化”处理,换言之,初译就是为了确保一部著作在目的语文化中得到良好的接受而进行的一项介绍性工作,而后继的重译则更加关注原作的文字与风格,也更能保持译作与原作之间的文化差异(Dastjerdi & Mohammadi,2013:174-181)。甘比尔也认为,初译版本出于文化因素与可读性的考虑,经常会诉诸同化、删减与变译的手段。这些20世纪90年代之初提出的一系列理论假设,被统称为重译假设(Baker & Saldanha,2009:233)。
威廉姆斯与切斯特曼(Williams & Chesterman,2004:78)将重译假设的核心内容概括为“后世的重译本较之初译本有越来越接近原著的倾向”。帕罗波斯基和科斯金恩(Paloposki & Koskinen,2010:29-49)将重译假设描述为“初译本内在的同化性质激起了以源语为中心的后继翻译”,他们认为,重译假设首先具有阐释性,因为这一假设声称,只有后继的译本才有可能成为“伟大”的译本。与此同时,重译假设又具有描述性,因为它不仅自始至终在描述源语文本与译入语文本之间的贴近性与距离关系,而且还将后续翻译描述为“比初译本更加靠近源语的翻译”。近年来,重译假设在国外翻译领域日益受到关注,这一点可以从国外学术会议与报告中对于重译假设一词的使用频率上得到证明,与会人员越来越多地将这一发端于法国学者伯尔曼的重译假设称之为“切斯特曼重译假设”,这也得益于切斯特曼对于重译假设进行的进一步界定与研究。
2.2 围绕重译假设的实证研究
曾于20世纪90年代一度盛行的重译假设,经历了切斯特曼等学者的发扬光大之后,到了20世纪的最初十年,却受到了一系列研究者的挑战,他们通过自己的实证研究对重译假设提出质疑,在一定程度上对其进行了证伪。
科斯金恩和帕罗波斯基(Koskinen & Paloposki,2003:19-38)将实证研究推向了更加深广的领域。他们持续关注重译假设的发展,并一直以外国经典的芬兰语翻译为例,专注于证实或证伪重译假设的实证研究。他们最初的研究起步于外国经典名著芬兰语翻译的个别案例,并据此证明,重译假设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文学翻译个案规律的同时,远不能概括文学翻译发展中极其复杂的现实。经过对这一课题长期的跟踪与不懈的研究,他们从个案研究的模式,逐步拓展到对外国经典名著在芬兰语文化中翻译的整体历史与发展趋势的研究。如在统计2000年译入芬兰语的小说数量及其中新译小说、重译小说、重印小说的比例的基础上,选取了包括《爱丽丝梦游仙境》《鲁宾逊漂流记》在内的十大经典小说的译介情况,进行了详细考察。除了案例上的拓展外,他们研究的视角也紧跟当今数字化翻译的新动向。研究案例上的拓展与视角上的革新,使得他们在反观重译假设时展现出更加从容、更加开阔的研究思路,并大大超越了重译假设对重译进行的狭窄、有限、单一的描述与理解。在他们的理解中,重译远非一个趋向完善的渐进过程,而是不同时代、不同解读在不同层面共同作用下不断变化、摇摆不定的过程,非此即彼的二分法、“贴近原著”的单一标准,无法与重译复杂的现实相吻合。
夏佩尔(Chapelle,2001)对1823—1944年间《格林童话》中《白雪公主》的七个英译本进行了实证性研究,证明了重译发展的不规律性与不可预料性。夏佩尔从译者生平与撰文中寻找蛛丝马迹,论证了译者个人情况及其对待翻译的态度,会对译本产生影响,并发现《格林童话》中一些民间故事的译者,会因道德伦理以及读者对象的原因,故意淡化其中的暴力情节。这项以重译者为中心、旨在复原译者进行重译时的真实社会图景的实证研究,进一步打破了那些将实际问题简单化和规则化的重译假设。
奥德里斯科尔(O’Driscoll,2011:251-252)对凡尔纳《八十天环游世界》的英译进行了时间跨度长达130年的重译实证研究。他从1873年至2004年出现的所有12个英译本中选取了6个有明确译者的全译本,并通过文本细读与译本对比的方法,对包括伯尔曼等人的一系列重译假设提出质疑,指出伯尔曼的重译假设因忽略了重译本产生的复杂的多重因素而失之过简,并从各个重译本自身的风格、文学价值以及在重译史上占有的地位等角度,否定了重译假设中“文学经典翻译存在权威定本”的论断。与此同时,奥德里斯科尔的研究却证实了布朗利的重译假设,即重译的过程并非完全沿着从以译入语为中心、不甚精确的译本到以源语为中心、精确的译本的线性方式进展。在1879—1995年的时间段中,围绕该小说进行的重译活动基本符合线性渐进的发展规律,但若将初译本和最后一个重译本进行对比,其发展趋势却恰恰与这一规律背道而驰,1874年的初译本表现出以源语为中心的倾向,同时在精确度上也堪称典范,而2004年出版的最后一个重译本却呈现出明显的以译入语为中心的倾向。
达斯特杰尔与迪莫哈马迪(Dastjerdi & Mohammadi,2013:174-181)针对重译假设进行的实证研究,选取的案例是《傲慢与偏见》1995年的波斯语初译本和2007年的重译本。通过对两个译本风格的详细对比,他们发现,与初译本相比,重译本更加趋向以原作为中心,对原作文化的同化程度降低,同时捕捉到原著中更多的风格特征,实现了对初译本风格上的补足,实证研究的结果基本与重译假设相吻合。但同时,他们也坦承,重译本在风格上与原作的贴近并不等同于翻译质量的提高,一次对重译假设的证实也并不意味着重译假设具有普遍真理性,还需要更多学者拿出更多语种翻译的案例继续深入开展实证研究。
重译假设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实证性研究,是国外学者试图建立统摄一切重译现象的范式、运用范式批评研究路径的典型体现,重译假设的产生也有其内在的缘由。列夫维尔(Bassnett & Lefevere,2001:23)从西方的翻译传统中找到了重译假设产生的根因。他认为,在西方的翻译传统中,“形式”(form)较之于“内容”(content)历来居于次要地位,在《圣经》的翻译中更是如此。译作本来就不是为了替代原作而生的,更遑论将其抹杀了。原作自古希腊经典和圣经翻译起便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权威,推及到后世的文学翻译中,原作作为试金石的地位始终岿然不动,译作除在极其罕见的情形下,从未以独立的面目存在过。因此西方的翻译是在译者们不断回望原作、与原作比照的过程中发展的,这便解释了为何从古至今千千万万个原作不断被重译,前译不断被推翻,以期最大限度地再现原作内容的原因所在。而西方译学中这一“译作不求形式上替代原作,而在内容上再现原作”的传统思维,也在重译假设研究中得到了集中体现与延续。自20世纪90年代重译研究在西方兴起直至近十年的勃兴,期间无论学者们为各自的重译假设所设定的终极目标在表述上有何差异,大都理想化地以“接近(close)、准确(accurate)、提高(improvement)”为最终落脚点,将重译的复杂发展变化进程简化为不断追求内容贴近的过程,将重译本多层面的对比与价值衡量简化为内容,甚至信息量传达层面的定量分析。这一重译研究思维上的固化与方法上的漏洞,已逐渐开始为一些目光敏锐的学者所觉察,而这一固化思维最终也会束缚西方重译研究向前发展的脚步。
重译假设研究由于受传统翻译思维方式中“重内容”的影响,表现出试图将重译发展兴衰起伏的宏观描述系于内容、信息量传达精确与否这一标尺之上的极度简单化倾向,这也促使更多的学者不断向重译假设提出挑战,并将目光转向文本以外更加广阔的社会文化、历史变迁、意识形态等背景中,解释重译现象,找寻重译背后复杂的动因。
3 重译的动因研究
伯尔曼认为发生重译行为的主要原因是译本在时代变迁中会不断老化,而原作却永葆“年轻”,这是促使新译本不断产生的最大动力(Dastjerdi & Mohammadi,2013:174-181)。布朗利(Brownlie,2003:111-152)赞同皮姆“多重动因”的观点,认为翻译就如同一切社会现象一样,只有在多重动因的作用下才会产生,因此要在描述翻译结果的过程中,最大限度地发掘各种影响因素。罗宾逊(Robinson 1999)从“增补性”(supplementarity)的角度解释重译的原因。在罗宾逊看来,前译只是部分地传达出了原著的意味,重译从本质而言是增补性的,包括使得原作恒久切合时代发展的时间性增补(temporal supplementarity)、在语义和句法上更接近原作的数量性增补(quantitative supplementarity)和在灵感与才华上更接近原著的质量性增补(qualitative supplementarity),而在对前译进行增补、弥补前译空白的同时,也留下了可供后世继续重译的空间。在韦努蒂(Venuti)看来,重译本的推出,有时是出于重新确立与确保学术、宗教等特定社会机构权威的需要。在已知有前译的情况下,推出重译本,这本身便是以前译的不可接受性为前提,与前译展开的竞争,甚至是对前译的翻译规范进行的替换(Dastjerdi & Mohammadi,2013:174-181)。
切斯特曼(Chesterman,2002:145-158)认为,当前翻译研究的焦点已经转移到对于因果模式的研究上,而仅局限于从翻译研究这一学科中查找翻译的因果是不合常理的,极易陷入狭隘理解的误区。他提倡在翻译和重译研究中采用“半因果解释法”(quasi-causal explanation),即不局限于查找某一翻译影响因素与翻译结果之间直接、明确的因果关系的方法(Chesterman,2008:372-373),与皮姆多重动因的主张是相呼应的。
皮姆(Pym, 2007:80-81)主张翻译和重译研究可以借用亚里士多德描述事物存在与运动变化的四因说,即质料因(material or initial cause)、目的因(final cause)、形式因(formal cause)和动力因(efficient cause),并亲身将其应用于揭示重译现象背后复杂的多重原因之中,如在解释瓦格纳音乐剧的法语重译中出现的起起落落时,他便从战争的爆发、文学学派的对立、杂志的创建、翻译的版权、出版协议、翻译派别的论战等多重因素中找到了原因。值得一提的是,在翻译和重译的多重动因中,皮姆借用社会学研究的视角,强调了对译者动力因研究的重要性,并强调译者也参与对社会、对翻译和重译历史的塑造。
夏佩尔(Chapelle,2001)聚焦于皮姆多重动因之中译者动力因的研究,试图通过查找、收集和研究各个重译者的传记、生平和个人翻译观,来证明作为具有鲜明个性的、活生生的人存在的译者才是决定译本最终得以产生的主宰因素。科斯特(Koster)列举的“译者诗学观(translator’s poetics)、权力关系(power relations)、规范(norms)、翻译的策略(translational strategies)、翻译的阐释(translational interpretation)”等更为新鲜、全面的视角,拓展了重译动因研究的视野(O’Driscoll,2011:18)。奥德里斯科尔(O’Driscoll,2011)则综合借鉴了皮姆、布朗利、切斯特曼等人关于重译动因的研究成果,以及图里的翻译规范理论。在其对于《八十天环游世界》重译本的对比与历史描述中,触及的动因囊括了出版社、翻译政策、文学系统的中心与边缘地位、意识形态与诗学传统、译者(包括翻译观、翻译策略,心智作用,自身的文学影响力与地位)等因素,为将来的重译研究,特别是重译动因研究提供了范例。
达斯特杰尔与迪莫哈马迪(Dastjerdi & Mohammadi,2013:174-181)将各家研究的重译原因归纳为五大类,依次为:前译本中存在理解错误,或译入语的观念与语言规范发生了变化,导致前译面目出现了不完美之处;原作出现了新的规范版本;从文体的角度衡量,现有译本已经过时;出版社要推出具有特殊功用的新译本,如在英、美两个市场同时推出不同译本的情况;对原作的解读发生了变化。另外,出版社对名、利、成本与稳定市场销量的追逐(Milton)、译者对名声的追求(Vander- schelden)、出版商“复活被遗忘著作”的目标(Vanderschelden),都是催生重译本诞生的因素。
4 重译的综合研究
对重译的综合研究贡献较大的当属威廉姆斯、切斯特曼和皮姆。
威廉姆斯与切斯特曼(Williams & Chesterman,2004:71-73)从术语的定义、研究问题的确立、研究方法的选择、立论的提出、假设的建立与验证等方面,向我们展示了对重译进行的科学、系统的研究过程。他们建议对重译这一课题进行研究时,不应仅满足于提出诸如“某重译本与初译本有何不同”、“是否存在其他重译本”、“这些重译本的译者分别是谁”等研究问题,还应在解决与回答这些问题的基础上对重译中的种种现象进行分析、概括、提炼与总结,从译者前言、出版前言等处寻找蛛丝马迹,从翻译委托人、出版社、译者个人因素等角度分析不同的重译本之所以产生的原因,从中概括出整体的倾向,提炼出重译发展的规律性趋势,提出重译假设,进而走出单一重译文本的对比,与其他重译研究发生关联,以推进对翻译的整体研究。
皮姆(Pym,2007)通过将历史纬度和社会学研究方法引入重译研究,涵盖了韦努蒂所说三个视角中的两个,即历史研究和译者才能研究。皮姆展示了重译历史研究中较为切实可行的方法,包括编撰研究书目(corpora)、编制频率曲线图表(frequency curve)、建构网络(networks)等。编撰研究书目是为了检验一个或多个假设,经过严格的筛选程序选取一定量的译本和重译本的方法,虽然其完整性只是相对的,但对于绘制出展示作品重译与译介过程的曲线图表,它是基础性的一步。而编制频率曲线图表的方法则可以进一步直观地展示作品重译和译介的总体走向和发展趋势,有助于研究者证实或否定在研究过程中产生的许多想法或假设(Pym 2007:x-xi),使研究结论更具有可信度和说服力。书目编撰与频率曲线这些“自上而下”(top-down)的简化方法往往会将研究引入宏观层面,导致对译本和译者本身关注的不足,此时建构网络这一“自下而上”(bottom-up)(Pym,2007:86)的方法则有助于从具体、微观的层面弥补这一不足。为展示自己的重译历史研究方法,皮姆(Pym,2007:80)按照从1860年至1940年长达80年间翻译年份的划分,编制了德国作曲家瓦格纳歌剧法语初译本、初译再版本、重译本出版的频率曲线图(frequency curve),直观清晰地展示了原著初译、再版、重译的总体发展脉络与趋势。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促使皮姆关注到历来为翻译理论家所忽视的译者因素。他认为作为受制于社会因素的个体,译者可能具有多重职业身份,具有主观能动性、独特的经历和翻译观,是参与创造翻译历史和重译历史的动力因(Pym,2007:157-172)。另外,皮姆(Pym,2007:82-83)还对“主动重译”(active retranslation)与“被动重译”(passive retranslation)、“重译”(retranslation)与“再版”(reedition)等概念对进行了区分。皮姆翻译历史研究中独特的切入点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西方重译研究“假设-实证”的思维定式,增添了崭新的历史纬度与社会学视角,特别是对译者在翻译历史书写中所起作用的肯定与描写,走出了定量验证假设的困境,将西方的重译研究引向了纵深。
5 结语
与中国问题式研究路径所不同的是,范式批评的研究路径呈现出总体研究脉络清晰、学术立场与研究视角明确、学派意识明显等优点。特别是重译假设从提出到发展的过程,以及围绕重译假设进行的一系列实证研究,更凸显出范式批评路径的特点,这与西方学者所接受的理论训练模式有关。威廉姆斯和切斯特曼(Williams & Chesterman,2004:73-82)在《翻译路线图》一书中展示了西方翻译研究学者进行训练的一套典型思路:即首先训练学者试图建立自己的模式,然后在此基础上大胆尝试提出自己的假设。
也正是这一研究思路的限定,使得西方的重译研究同样显示出理论性强、继承性强、难以脱离“假设-验证”的固定思路。循着这样一条固定的思路,翻译研究模式中常用的二分法中一些老生常谈的术语,如“贴近原作”(source text oriented)、“准确”(accurate)等术语,再次成为重译假设中的关键词。未能突破西方传统翻译研究模式中老生常谈的术语,这是重译研究中的第一个不足之处。综观西方的重译研究,重译假设是开启与推动重译研究的主要动力与核心环节,可以说,西方的重译研究主要系于这一假设之上,而这一假设本身却是在脱离翻译市场的实际、脱离译者自身因素、将社会、历史、文化等因素排除在外、仅封闭于翻译活动本身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是重译研究中的第二个不足之处。西方重译研究试图在有限的语言基础上建立涵盖一切语言规律的重译假设,这本身便存在逻辑上的纰漏之处,特别是用于解释英汉语言之间的互译情景时。诚如许渊冲(许钧,2011:253)所言:“中英互译是今天世界上最重要的翻译,因为世界上有十多亿人用中文,也有十多亿人用英文,所以不能解决中英互译问题的理论,实际上不能起什么大作用。还有一个原因,中英文之间的差距远远大于英法等西方文字之间的差距。”看来,重译假设的真伪还有待于在其从未关注的英汉语言对比中进行一系列的、长期的验证。
Baker, M. & G. Saldanha. 2009.RoutledgeEncyclopediaofTranslationStudies(2ndedi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Bassnett, S. & A. Lefevere 2001.ConstructingCultures:EssaysonLiterary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Berman, A. 1990. La Retraduction Comme Espace de Traduction [J].Palimpsestes, 13(4): 1-7.
Brownlie, S. 2003. Investigating Explanations of Translational Phenomena: A Case Study for Multiple Causality [J].Target, 15(1): 111-152.
Chapelle, N. 2001. The Translators’ Tale: A Translator-Centered History of Seven English Translations (1823-1944) of the Grimms’ Fairy Tale, Sneewittchen [D]. Dublin City University.
Chesterman, A. 2002. Semiotic Modalities in Translation Causality [J].AcrossLanguagesandCultures, 3(2): 145-158.
Chesterman, A. 2008. On Translation[G]∥ A. Pym, M. Shlesinger & D. Simeoni.Beyond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InvestigationsinHomagetoGideonToury. Amsterdam and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372-373.
Dastjerdi, H.V. & A. Mohammadi. 2013. Revisiting “Retranslation Hypothesi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tylistic Features in the Persian Retranslation of Pride and Prejudice [J].OpenJournalofModernLinguistics(3): 174-181.
Koskinen, K. & O.Paloposki. 2003. Retranslation in the Age of Digital Reproduction [J].CadernosdeTradução(11): 19-38.
O’Driscoll, K.2011.RetranslationthroughtheCenturies:JulesVerneinEnglish[M]. Bern: Peter Lang.
Paloposki, O. & K. Koskinen. 2010. Reprocessing Texts: The Fine Line between Retranslation and Revising [J].AcrossLanguagesandCultures(1): 29-49.
Pym, A.2007.MethodinTranslationHistory[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Robinson, D.1999. Retranslation and Ideosomatic Drift[EB/OL]. www.umass.edu/french/people/profiles/documents/Robinson.pdf.Accessed on Dec. 30th, 2015.
Williams, J. & A. Chesterman. 2004.TheMap:ABeginner’sGuidetoDoingResearchinTranslationStudie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吕俊, 侯向群. 2009. 翻译批评学引论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许钧. 2011. 文字·文学·文化——《红与黑》汉译研究[M]. (增订本)南京: 译林出版社.
责任编校:朱晓云
A Review of Re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GAOCun
Scholars in the West tend to adopt a paradigmatic approach to retranslation studies, which is most vividly reflected through their efforts to formulate the so-called “retranslation hypothesis” and through the ensuing systematic researches done to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also points to the first characteristic of re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that is, there is a dynamic continuity in the construction of retranslation theoretical system. Through the cycle of “hypothesis—testing—hypothesis revision—testing”, revisions or expansions of previously formulated hypothese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made to certain extent to set up a scientific model. At the same time, re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have been hindered by its fixed research pattern in that those complicated factors and phenomena involved in the process of retranslations may easily be ignored or simplified when it focuses too much on covering the laws of all retranslations and predicting their trends through the formulation of retranslation hypotheses.
retranslation studies in the West; paradigmatic approach; retranslation hypothesis
2016-04-1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比较文学主题学研究”(12BWW007)与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外国文学经典重译研究”(TJWW15-021)的阶段性成果
高存,女,天津商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比较文学研究。
H315.9
A
1674-6414(2016)04-011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