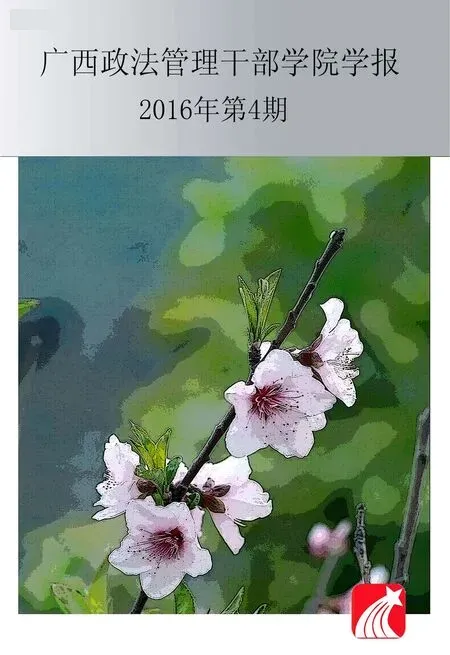劳务派遣同工同酬的批判与重构
戴玥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北京100088)
劳务派遣同工同酬的批判与重构
戴玥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北京100088)
以劳务派遣为代表的用工形式对传统的以稳固、长久为特征的劳动关系造成了挑战。劳务派遣在我国劳动合同法中由于其特殊的三方法律关系而得到较普通劳动关系更为严格的管制,而这些管制往往经不起严格的法律和价值判断的推敲。其中,《劳动合同法》第63条第1款关于“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的规定由于存在诸多不当之处更是需要被重构。
劳务派遣;同工同酬;管制;自治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下,企业无疑也要适用达尔文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在企业和劳工共同追求弹性的情况之下,逐渐出现异于传统思维的非典型劳动形态,[1]以劳务派遣为代表的用工形式对传统的以稳固、长久为特征的劳动关系造成了挑战。纵观各国劳务派遣的产生背景,无一不是为了突破当时劳动法体系下国家管制的桎梏,以满足企业灵活用工的需求。毫无疑问,劳务派遣既是一种社会存在,又是一种法律存在。[2]13劳务派遣在我国劳动合同法中由于其特殊的三方法律关系而得到较普通劳动关系更为严格的管制,而这些管制往往经不起严格的法律和价值判断的推敲,相较于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法治,其质量及强度都不高。[3]其中,对于《劳动合同法》第63条第1款关于“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的规定更是存在探讨的余地。
一、劳务派遣立法理念——自治与管制之间
劳务派遣相关规范作为劳动法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自然与劳动法有着相同的属性。劳动力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脱胎于民法中的自由市场理念,劳动关系也开始独立于民法中的契约自治作为特殊的法律关系而受劳动法规范。正如学者所言,劳动法的功能在于倾斜性强化保护劳动者弱势群体的正当性利益。[4]诚然,在劳动法的视野下劳务派遣自始不乏国家统合模式的色彩,企业与劳工组织在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由国家决定,企业的功能与活动范围也通过立法予以命令或禁止。[5]但从调整手段来说,劳动法的规范结构不同于公法,其法律规范的强制性往往混杂着自治的成分。从社会法的演进历史来看,也正是因为纯粹的民法关系无法实现对劳工权益的保护才催生了劳动法,不难理解劳动法常被作为特别私法而存在。因而不可忽视的是,劳动关系应该是在自治前提下的有限度的管制,这体现在法律适用上,劳动纠纷发生时往往先适用劳动法,当其无法调整时,合同法往往会被用作裁判规范参与进来。不难看出,劳动法与民法本质上即为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即使在劳动契约中,契约自由原则基本上仍然有其适用空间。[3]对于劳务派遣相关立法的分析也应秉承着劳动法的立法理念,在自治与管制间寻求一个恰当的平衡。
然而,劳务派遣作为彰显时代特征、实现企业组织成本集约的一种灵活的用工方式应该如何在劳动法的框架内实现自治与管制的平衡?不可否认的是,劳务派遣不仅仅迎合了现代劳动者灵活的工作愿望,同时也能降低企业成本、使产品具备需求弹性,使企业得以在全球化竞争中保持优势并且能够提振社会的就业率。而《劳动合同法》的立法宗旨在某种程度上与劳务派遣的本质相悖,前者追求长期性与稳定性的劳动关系,该刚性的立法理念与本属弹性工作的劳务派遣之间产生了法理上的悖谬。[5]尽管《劳动合同法》以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对于劳务派遣机构设置了一系列门槛,但是劳务派遣反而出现逆势增长的“非正常”繁荣局势。[5]这从反面折射出劳务派遣在当下有强大的现实需求,立法者应当将其纳入规范的轨道并顺其繁荣态势,而非以一种打压的态势将其置于灰色地带,从而使其“难以存在,只得消亡”。[6]
二、劳务派遣中同工同酬的法理矛盾与价值背离
《劳动合同法》第61条规定:“劳务派遣单位跨地区派遣劳动者的,被派遣劳动者享有的劳动报酬和劳动条件,按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的标准执行。”第63条规定:“被派遣劳动者享有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同工同酬的权利。用工单位无同类岗位劳动者的,参照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者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确定。”从上述两个条文可以总结出劳务派遣立法中被派遣劳动者劳动对价权益的两项原则:用工单位所在地标准和用工单位劳动者同岗同酬。[7]335立法上对于同工同酬的规定不仅在《宪法》第6条中可以寻找到源头,该条规定了关于“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这一经济制度的基础,同时也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按劳分配的劳动价值论的观点。然而,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薪酬制度的法律化不能达到法律所宣示的按劳分配,[7]339劳务派遣中的同工同酬也存在相当的法律矛盾和价值背离之处。
(一)以劳务派遣的法律关系为切入点
劳务派遣中通常涉及派遣机构、劳动者、用工单位三方主体。根据《劳动合同法》第58条第1款可得知劳动者与派遣机构之间存在劳动合同关系,而根据第59条第2款可知派遣机构与用工单位存在劳务派遣协议关系,该协议实际上是民法上的债权让与,因双方主体并无特别法上保护的必要,其法律关系与劳动法无涉。不同于上述两个基础的契约关系,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并无直接的法律关系,而是由此派生出来的拓展法律关系。其内容主要涉及劳动者对用工单位的忠诚义务,以及用工单位对劳动者的指挥监督权以及照顾义务,基本法律关系与拓展法律关系可以理解为主从法律关系。[2]152-153由此观之,劳务派遣法律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劳动关系,派遣机构与派遣劳工间乃是具有真正利他契约性质的劳动契约。[8]
《劳动合同法》第63条第1款赋予“被派遣劳动者”同工同酬权的比较对象是“用工单位的劳动者”,根据上文的分析,被派遣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并没有直接的法律关系,更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然而,工资请求权的来源应当是基于劳动合同关系,与用工单位给予其劳动者薪酬之高低并无直接关联。[3]被派遣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分别属于不同的劳动合同项下的法律关系主体,这是立法者的错搭。撇开关于公平正义价值判断的衡量,不同劳动关系下的劳动者不具有薪酬上的可比性,只有在同属一个劳动关系项下同工同酬才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宪法上的平等原则不能肆意解释和扩大解释,在劳动法上的同工同酬应当比照《劳动合同法》第11条或者第18条的立法原理,将同工同酬限缩在同一劳动法律关系内。否则不仅会架空用工单位中劳动集体所协商订立的关于劳动报酬等劳动条件,更有将同工同酬蔓延到《合同法》中加工承揽等关系中,这势必会危及到契约自由的神圣性。如果依据《劳动合同法》第63条第1款的逻辑,似乎可以进一步推导出在外包业务以及劳动租赁关系中的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享有同工同酬权,而这显然是对承揽等法律关系中意思自治的扼杀。因而,劳务派遣中的同工同酬应当仅指与劳务派遣机构签订劳动合同的劳动者之间享有对于派遣机构的同工同酬请求权,要求被派遣劳动者与用工单位的劳动者享有同工同酬权诚然与法学逻辑相背离。
(二)从法经济学的角度分析
结合当前中国劳动力的供需状况以及经济发展阶段,对劳务派遣中同工同酬条款立法效果做成本—效益分析可以在法教义学之外对该项规定做一番价值判断。我国所经历的持续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是由农村的廉价剩余劳动力所推动的,但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的富余劳动力逐渐枯竭,建筑类、餐饮类、制造业等劳动密集型行业出现了“用工荒”,[9]因而许多经济学家将上一现象描述为“刘易斯拐点”,普通劳动者工资将会因此上涨。[10]由于我国劳务派遣行业从业人员大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因而“用工荒”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劳务派遣行业劳资关系的力量对比,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卖方市场”。
在当前情形下,劳务派遣机构已然面临用工成本上升带来的企业生存压力,在“卖方市场”下,劳动者的议价能力显然已经强大到无需公权力保障即能很好实现其利益诉求。派遣机构若负有同工同酬条款所规定的义务,势必会造成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负担过重而加速产业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区,使得被派遣劳动者遭遇失业的风险。回过头来反思劳务派遣中的同工同酬条款不难发现,立法者对于劳动者的保障过于强势,而对企业的保护十分不足,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最终损害了劳动者的利益。[11]
与立法者所欲达到的保护被派遣劳动者权益的意旨相反,劳务派遣同工同酬条款会给劳务派遣机构反向的行为激励。由于同工同酬条款为派遣机构设置了过高的义务,同工不同酬的问题依然突出,劳务派遣工与正式工收入差距少则30%,多则4、5倍甚至更多。[12]笔者认为,《劳动合同法》确立的刚性化用工机制是导致劳务派遣超常发展的直接原因,其中有悖于经济学规律的严苛规定几乎对派遣机构“毫发无损”,[13]显然无法遏制当前劳务派遣同工不同酬的现象。为了规避该严苛的强制性规定,许多劳务派遣机构会以隐名派遣、自设派遣、虚拟(合谋)派遣等名义,[14]实质上从事着派遣业务,以免除其在劳动法上的同工同酬等法律责任。这种以“假外包,真派遣”为代表的现象横行就使得同工同酬条款形同虚设,立法效果聊胜于无。
另外,从劳务派遣同工同酬条款的实施成本来看,由于同工同酬并没有细化的法律定义、适用标准以及操作细则,同工同酬的裁判遭遇到很大的困境,[15]裁判者需要在该条款的适用上耗费大量的搜寻成本。即使在同一劳动法律关系项下,付出等量劳动就要求取得等量报酬也是不现实的,[6]对同工同酬的裁判更是需要考察双方的工作岗位、工作强度、学历、技能、工作经验、劳动成果等因素。
在现有的情形下,劳务派遣中的同工同酬条款所产生的社会收益,相较于其所带来的社会成本而言,可能仅在于提升派遣劳工的薪酬而对社会福利并无较大助益,相形之下显得捉襟见肘。从法经济学成本—效益的角度分析,该条款是缺乏效率的,并且也无法真正实现保护被派遣劳动者利益的立法意旨。
三、比较法分析
(一)英美法系立法例——以欧盟和美国为例
为了对灵活用工进行更好地规制,欧盟秉承着对于临时性劳动者(Contingent Workers)的权益保障这一初衷制定了一系列指令和规范。起初,欧盟于1997年公布了《部分时间指令》,并在这一指令中提出了同工同酬原则。其后,在2002年欧盟委员会制定了《派遣劳动者劳动条件相关法案》(The EU Temporary and Agency Work Directive),其中第5条规定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条件应与用工单位能相互比较的劳动者均等,[16]其中的劳动条件包括工作时间和薪酬。虽然一直遭到英国、德国、丹麦等国家的反对,该法案一直到2008年通过。这一条款与我国劳务派遣中同工同酬条款基本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这一指令遵循着英美法的思路,没有“互负义务”(mutual obligation)的概念,其对于雇员和雇主的定义也不同于大陆法系,同工同酬的提出也并非出于法律逻辑的推理,而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假设该派遣劳工直接在用工单位从事同一工作”。[17]但第5条并非强制性条款,欧盟的成员国可以排除适用,当没有特别规定排除适用的情形下方适用该同工同酬原则。另外,这一条文还有一个适用除外,也即如果用人单位劳动者的薪酬是在集体协议下制定的,那么被派遣劳动者不能向用人单位行使同工同酬权。[17]
美国法上并没有对劳务派遣有专门立法,而是将性质和内容相似的租赁劳动、外包和劳务派遣统一置于“暂时性劳务提供”(Temporary Help Supply)这一劳动形态之下。其共同的特征在于都涉及三方当事人,存在三角法律关系,劳动者提供劳务的对象与地点都是劳动力的使用者,而非劳动关系下的雇佣者。[18]尽管临时性劳工在美国较为普遍,但迄今为止尚未有暂时性劳务提供的专项立法,所有规定都散见于州以及联邦的劳动立法中。1987年,《兼职及临时劳工保护法案》(Part-Time and Temporary Workers Protection Act)曾提送立法院讨论,该法案最终未能面世。另外,在1994年,美国曾提出《不定性劳动力平等法案》(Contingent Workforce Equity Act),该法案提出被派遣劳动者的工资待遇不因其性别、宗教、年龄及残障状况等因素而受到差别待遇,[18]这其实也是同工同酬待遇的体现,只不过与我国立法定义不同,这里的同工同酬与国际劳工组织的定义相近,是从排除歧视的角度考量的。遗憾的是,这一法案也最终没通过立法程序。因而,在劳务派遣这一领域,美国法上并没有关于同工同酬的强制性立法,对于被派遣劳动者的保护主要是基于其“共同雇主”(joint employer)理论让用工单位承担劳动法上的法律责任。
(二)大陆法系立法例——以日本、台湾地区为例
检视其他大陆法系的立法例,囿于其传统的规范法学的立场,同工同酬的理论前提基本上局限于同一法律关系项下。在劳务派遣领域,日本于1985年制定了专门的《派遣劳动法案》,并最近一次于2008年进行修订。从历次修法的历程来看,日本立法者对于劳务派遣的理念有了不小的变化,从最早防止以被派遣劳动者取代正式劳工的雇佣安定理念转变到现在的被派遣劳动者自身的雇佣安定及其劳动条件的保护。[16]即便在日本社会面临日益扩大的收入差距以及劳动条件的差距,日本仍然反对在劳务派遣领域实行同工同酬,其反对意见主要集中于以下两点:一是日本尚未建立起企业横断的职业种类薪资体系,于劳动派遣法修正之际引入该条款在实践上存在困难;二是用工单位与派遣机构并非统一雇主,无法强制保障均等待遇原则。[16]
台湾地区在立法上经常对日本的动态有所借鉴,在劳务派遣上也同样如此。虽仿照日本体例制定了《劳动派遣法草案》,但因各方对此意见激烈,故而尚未正式通过。现行立法中仅以《劳动基准法》等相关立法规范该劳务派遣业,在其《劳动基准法》第25条“性别歧视之禁止”中规定“雇主对劳工不得因性别而有差别之待遇。工作相同、效率相同者,给付同等之工资。”其中的“禁止差别待遇原则”实质上是禁止性别歧视条款,同工同酬也只能做限缩解释,不能扩大解释为被派遣劳动者与用工单位劳动者享有同工同酬权。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台湾地区的制度现状和基本法理在被派遣劳动者的同工同酬概念是被派遣劳动者内部的同工同酬,而不是被派遣劳动者外部的同工同酬。[7]342
四、劳务派遣中同工同酬条款的重构
结合以上的分析和比较法经验,我国《劳动合同法》中对于劳务派遣同工同酬的规定存在与传统法理和中国现状诸多不和谐之处,需要在现有的法框架内对其做限缩解释,并需要在《劳动合同法》修订的背景下重构劳务派遣劳动者劳动对价的法律制度,在现有的基础上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以实现对被派遣劳动者更好、更周全地保护。
(一)同工同酬的限缩解释路径
同工同酬条款如果严格按照文义解释,不仅与法理和实践相悖,也在操作中难以实现,笔者认为应当对其做目的性限缩解释。将《劳动合同法》第63条第一款中的“同工同酬”解释为反歧视条款。这种解释路径其实也可以在《宪法》中找到支撑,其中第4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国家保护妇女的权利和利益,实行男女同工同酬,培养和选拔妇女干部。”这样就可以将“同工同酬”解释为被派遣劳动者享有男女平等的劳动待遇,不受歧视。另外一条解释路径便是将劳务派遣中的同工同酬条款视为任意性规范或倡导性规范,不将同工同酬解释为强制性规范。《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暂行规定》等相关法律法规也并未对派遣机构违反同工同酬进行法律责任的设置,各个地方对于同工同酬的具体规范也不尽一致,这在很大程度上减损了同工同酬条款的效力,也可以从中反映出立法者并非想要将该条文成为强制性规范。①从劳务派遣中同工同酬条款的立法背景和历程看来,在人大2006年公布的一审草案中并无同工同酬的规范,仅在2007年征求意见的二审草案中始有规定。虽然很难在官方文件中找寻到该条文的逻辑推理,但是李海明博士认为该条款的逻辑在于对不真正派遣的遏制或者对不当派遣行为的纠正,从而强化同工同酬精神。详见李海明:《劳动派遣法原论》[M],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第344页。同工同酬条例可以作如下解释:在相同劳动条件下,立法者倡议和诱导派遣机构为其派遣劳动者提供与用工单位劳动者相同的薪酬水平。
(二)强化被派遣劳动者权益保障机制,将不当派遣统一立法
在对劳务派遣同工同酬条款进行限缩解释后,难免会适当削弱被派遣劳动者的劳动权益,因而需要完善其他制度以强化对被派遣劳动者的保护。诚然,现实中派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遭遇到一系列歧视和不平等待遇,并且被派遣劳动者不管在派遣机构还是在用人单位都没有归属感,这是立法上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笔者认为,劳务派遣的许多问题都是由于劳动者的雇佣和使用相分离产生的,虽然劳动者与用工单位没有劳动法律关系,但是由于工作地点和劳务提供均指向用工单位,《劳动合同法》需要进一步加强用工单位对于被派遣劳动者的基本劳动保障,这一点甚至比所谓的“同工同酬权”更为重要。笔者建议从以下几个方面重构派遣劳动者的保护机制:一方面强化用工单位在劳动法上的责任,在劳动法中设置对用工单位设置基本劳动保障义务,如工作时间、工作条件、劳动保险等保障条件,应明确被派遣劳动者有权要求用工单位告知同类岗位的直接雇员的劳动条件和劳动报酬。[19]另一方面在侵权责任法中明确派遣机构与用工单位的责任分配,适当情形下可以加重两者的责任承担,适用连带责任原则。最后劳动者作为社群中的一员,为了让其体验到劳动集体的归属感,在现有《劳动合同法》第64条的基础上,强化被派遣劳动者在用工单位或派遣机构工会组织的维权机制,形成独特的诉求表达机制和集体维权渠道。
由于现有的劳动法体系下对于劳务派遣的规定涵盖范围狭窄,并且管制过严,使得许多派遣机构打着外包的幌子以逃避劳动法上的法律责任。对于现实中存在的不当派遣非正常繁荣的现象,执法机构往往因为无法识别其背后真实的法律关系而难以打击,笔者认为可以将其他不当派遣行为一并纳入劳动法的规制。鉴于在灵活用工的劳动形态下可以衍生出不同的法律关系,比如加工承揽、人事代理等,而加工承揽关系项下也呈现出不同的业态,如业务外包、人力资源外包、自雇。在纷繁复杂的灵活用工形式下,劳动法仅对劳务派遣进行规制难免会有挂漏之处。笔者认为,上文所介绍的美国经验值得我国借鉴,对不同形态的暂时性劳动者统一保护,不仅让其享有基本的劳动保障条件,也可以根据其灵活的特性对其进行特别立法。扩大立法范围的另外一个好处还在于能够有效遏制派遣机构假借其他法律关系的名义逃避劳动法上义务,使得所有提供劳务服务的劳动者能够在将其劳务换取公允对价的前提是获得劳动法上的保障。
[1]简建设.台湾劳动派遣法规草案与中国劳动派遣法制之比较[J].台湾劳动评论,2009(1),第3页。
[2]李海明.劳动派遣法原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第13页。
[3]杨通轩.劳务派遣之法律定位及法律选择—兼论中国劳务派遣规定[J].中正大学法学集刊,2010,第8页。
[4]赵红梅.劳动法:劳动者权利义务融合之法——社会法的视角且以加班工资为例[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2(2),第26页。
[5]黄越钦.劳动法新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第78页。
[6]董保华.劳务派遣的题中应有之义——论劳务派遣超常发展的“堵”与“疏”[J].探索与争鸣,2012(8),第40页。
[7]李海明.劳动派遣法原论[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
[8]黄程贯.德国劳工派遣关系之法律结构[J].政大法学评论,1998(6),第14页。
[9]余颖诗,黄倚彤.广东用工缺口峰值达100万又是一年“用工荒”?[EB/OL].大粤网财经频道,http://gd.qq.com/ original/fqreader/fq20160226.html,2016年2月26日。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5月6日21:36
[10]蔡昉.刘易斯拐点与人口红利[EB/OL].http:// finance.sina.com.cn/zl/china/20140609/155819356001.shtml,新浪财经,2014年06月09日。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5月6日22:10。
[11]楼继伟.下一步要修改劳动合同法[EB/OL].财新网,http://economy.caixin.com/2016-02-19/100910617.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6年5月6日22:30。
[12]全总劳务派遣问题课题组.当前我国劳务派遣用工现状调查[J].中国劳动,2012(5),第25页。
[13]董保华.劳务派遣的题中应有之义——论劳务派遣超常发展的“堵”与“疏”[J].探索与争鸣,2012(8),第41页。
[14]郑尚元.不当劳务派遣及其管制[J].法学家,2008(2),第8页—第9页。
[15]柯菲菲,蒋彦龙,蒋天成.劳务派遣工主张“同工同酬”的裁判困境分析[J].中国劳动,2011(12),第18页。
[16]邱祈豪.2008年日本勞動派遣法草案及派遣實態之研究[J].台湾劳动评论第二卷(1),2010(6),第23页。
[17]McGaughey E.Should agency workers be treated differently?[J].SSRN Electronic Journal,2010,第4页。
[18]郑津津.从美国劳务派遣法制看台湾劳务派遣法草案[J].中正法学集刊,2002(10),第46页。
[19]林嘉,范围.我国劳务派遣的法律规制分析[J].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1(6),第79页。
[责任编辑:袁翠薇]
Labor Dispatch Critique and Reconstruction of Equal Pay for Equal Work
DAI Yu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Beijing China 100088)
The labor dispatch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traditional forms of employment to stable,long-term labor relations characterized by causing a challenge.Because of its unique tripartite legal relationship,Labor dispatch in Labor Contract Law and to give more general labor relations more stringent controls,and these controls often cannot withstand strict legal scrutiny and value judgments.Among them,Article 63,paragraph 1,“dispatched workers have the right to equal pay and the employee labor unit”requirement in“Labor Contract Law”for there are many more irregularities that need to be reconstructed.
labor dispatch;equal labor equal pay;regulation;de-regulation
DF471
A
1008-8628(2016)04-0061-05
2016-06-01
戴玥,男,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经济学(民商经济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