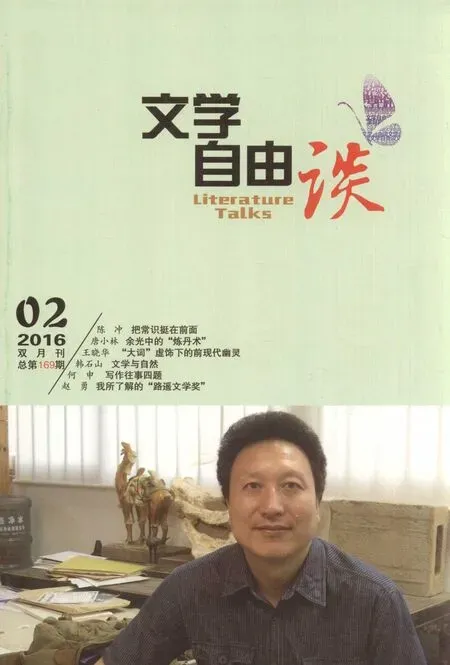作家与忏悔(外一章)
狄青
作家与忏悔(外一章)
狄青
199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国作家君特·格拉斯2006年出版了自传《剥洋葱》,如其所料,旋即引发了德国社会的一次“核爆炸”。
在这本自传里,君特·格拉斯披露了他鲜为人知的一段往事:1944年11月,16岁的格拉斯应征加入了纳粹党卫军;次年4月,他所在的坦克连被苏联红军包围,他脱掉了军服,偷偷跑掉了……就是这样的一段经历,只有几个月的时间,但人们质疑并且指责格拉斯:为什么要隐瞒这么久!要知道,君特·格拉斯曾被称为德国知识分子的良心,是德国民众最信赖的作家。还记得前西德总理勃兰特在华沙的惊天一跪吗?当时格拉斯就在场,之后他还随勃兰特出访以色列,为德国正视二战历史而奔走呼号。《剥洋葱》一出,有人指责格拉斯是骗子,有人要求他归还诺贝尔文学奖,就连德国总理默克尔都说:“我希望我们一开始就完全知道这部自传。”人们的愤怒不在于君特·格拉斯当了几个月的党卫军,而在于他为何隐瞒了自己的这一段经历,而且隐瞒了那么久。当然,也有人指责格拉斯为何要把这段经历说出来,这不仅损害了他自己写作的道德权威,更损害了大量喜爱他的读者的利益。
没错,那五个月的经历,如果格拉斯自己不讲,很可能永远不会有人知道。他的形象依旧高大上,甚至算得上道德完人。可是他说了,尽管他是应征入伍的,尽管他当时只有16岁,尽管在此后数十年的时间里他都在用自己的笔和影响力持续提醒着每一个德国人要牢记过去、不能让历史重演……可他依旧选择了坦白,并且忏悔。
2015年,在君特·格拉斯去世前,《寡居的一年》作者、美国作家约翰·欧文写信给他:“对于我来说,你依然是一个英雄,又是一个道德指南针,你作为一个作家和公民的勇气值得效仿。”
欧洲民族多半是具有自我忏悔意识的民族,这与他们的宗教有关,也与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艺术的辉煌成就密不可分。尤其对于作家而言,从奥古斯丁到但丁,从卢梭到阿尔弗莱德· 德·缪塞,几代作家前赴后继,不断在自己的作品里解剖内心、忏悔自我。及至晚近,在欧美,作家的文章与言行甚至具有了某种宗教的精神效用,可予人疗伤,可让人信任,可供人依傍。而作家也不隐晦自己的卑微乃至龌龊,他们写出“另一个自己”,对自己而言是自愈,对读者是忏悔。就像普希金的《秘密日记》,因所述内容“过于令人震惊”,而至今无法在许多国家正式出版。
2003年,来自阿富汗的移民卡勒德·胡赛尼在美国出版了自己的第一部小说《追风筝的人》,一举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并蝉联了创造畅销书榜单历史的130周,从此跻身美国一线作家行列。今天,胡赛尼已然成为美国主流社会公认的著名作家,但他却陷入了越来越深的痛苦:“我写的人在阿富汗受苦受难,我却靠讲述他们的故事获得了成功。这让我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写作仿佛成了一种偷窃,我为了自己的成功偷取了别人的经历和生活片段,换取了他人的赞许和金钱。”对同胞的深深愧疚让胡赛尼拿出钱来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基金会,至今已帮助了359位阿富汗穷苦人获得安居之所。即便如此,他依然无法得到内心的安适。回到故乡,他多次在讲话里提及自己内心的不安,和对自己离开阿富汗却以阿富汗为题材而创作的忏悔。
中国近现代作家中,以鲁迅、郁达夫、巴金为代表,包括比他们稍早一点儿的苏曼殊等,是敢于解剖自己、勇于忏悔的一群人。鲁迅无疑是中国最具有忏悔精神的人之一,而巴金则是20世纪晚期最具有忏悔意识的中国作家。当所有人都在控诉林彪、“四人帮”的罪行,仿佛那场浩劫只是因少数人蛊惑而与己无关的时候,巴金却说,在这场罪恶的表演中,有自己的一份罪。他在忏悔的同时,选择了“讲真话”,因为他曾在特定的情境下讲过几句假话、错话。
当初,余杰等人揪住余秋雨不放,质问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余秋雨的委屈在于,他是“文革”期间某大批判写作班子的骨干不假,但人们却不去追剿“石一歌”里的其他人,唯独对他一个人穷追猛打,“难道就因为我是名人吗?”
对许多人而言,是不是名人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作家的身份与光环,是文学的教化与启智功用,以及文学传统在作家身上所赋予的独有的忏悔精神。
书单与喜欢
每到岁尾年初,各种排行榜竞相出炉,其中与书有关的格外多,媒体、机构、出版商、各大网站的读书频道,乃至所谓的专家学者,都在向读者推介各式各样的“年度书单”,而且还排出座次,区别出哪个是“重磅推荐”,哪个是“温馨提醒”。除此之外,诸如“2015年十大好书”“2016你终将不能错过的十本书”“全国十大民营书店老板票选2015十大畅销书”“荧屏暖男某某某为您细数2016十大暖暖的书”“顶级商学院推荐2016十本必读书”,更有那些“比尔·盖茨拿起就放不下的书”“马云床头的过夜书”“改变世界的50本书”“影响世界的100本书”“一生不得不读的100本书”……图书市场好不热闹。说实话,这些被千方百计推荐的书有的我看过,有的听说过,但大多数既没有看过,也没有听说过;这让我这个所谓爱读书的人未免郁闷:这么多“十大”,这么多“不能错过”“不看后悔”的书竟然没有去涉猎!这是不是应该有点压力山大的感觉呢?
先前一本书的好坏,很多时候是靠读书人的口耳相传,虽说范围有限,却最是靠谱。然而,不看后悔,我怕的是看了会不会更后悔呢?
王小波当年说卡尔维诺小说好,喜欢王小波的读者就去追卡尔维诺,卡尔维诺果然也没让大家失望;王小波还推荐过莫迪亚诺,后者在2014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证明王小波的眼力的确不差。村上春树在中国拥有庞大粉丝群,由于他喜欢雷蒙德·卡佛和乔治·奥维尔,粉丝们也爱屋及乌,而这二位无疑都是好作家,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好过村上春树。读书与创作有一点儿相近地方,我们怕的其实不是眼高手低,怕的是眼低手也低。
我一直觉得某些人每逢岁尾年初便忙于给人开书单、评“十大”这些事比较不靠谱。其实,一本好的书与一位好的人一样,要有个性,并且一定要有时间的检验,所以很难说哪本书就该位居“榜首”。当然,给出建议无妨,尤其对青少年而言,对书的选择还需要引导。《红楼梦》里,薛宝钗谆谆教诲林黛玉,说自己小时候原本也是一个淘气的,怕看正经书,《西厢》《琵琶》等这些杂书倒看了不少,后来大了才丢开了。想当年,《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都曾不算“正经书”,甚至还历经“禁毁”命运,但时间最公正,大浪淘沙,好书终是无法埋没。
书单之外,书籍腰封上的文字也越来越哗众取宠,基本上都是推荐人语,而推荐人嘛,大约皆是各行各业的名人。比方伦茨的《德语课》,就曾被国内某网站列入“欧洲五十大小说”之一,这“五十大”是谁评的?哪来的依据?一概没有解释。其实,《德语课》应该算是本不错的小说,可看推荐语,我却感到了迷惘——“一本余华借了舍不得还的小说”“一本S.H.E随身携带的小说”。余华是谁,想必不用科普;至于S.H.E嘛,不过是流行乐坛上一个少女组合。出版商将二者并提,或许是为了表现该书的雅俗共赏?而在我看来,越是这种所谓雅俗共赏,越让人搞不清它到底是要写给谁看的。
金庸写武侠,但他自己常看的却是经史子集,从他小说里的人物姓名就能瞧出他的博览群书。比如《天龙八部》里的木婉清,灵感就来自于《诗经》——“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阿朱和阿紫取自《论语》——“恶紫之夺朱也”,《书剑恩仇录》中李沅芷的名字来自屈原的《九歌》——“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射雕英雄传》中的穆念慈之名则出自《尚书》——“帝念,念慈在慈”……以此推断,金庸怕是从来不信书单的。
如今在网上买书,你点击进入购书页面,最先弹出的永远是商家最想卖给你的书单,而你想找到你要的书,非要下一番苦功不可,并且还要随时去除自动弹出的推荐书籍广告。但聪明的读者应该明白自己喜欢什么,哪些是炒作的书,哪些是虽生来冷寂,偏居一隅,却注定是有价值的书。对于读书人而言,我的意见是,书单还是算了吧,不看书单,就看自己的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