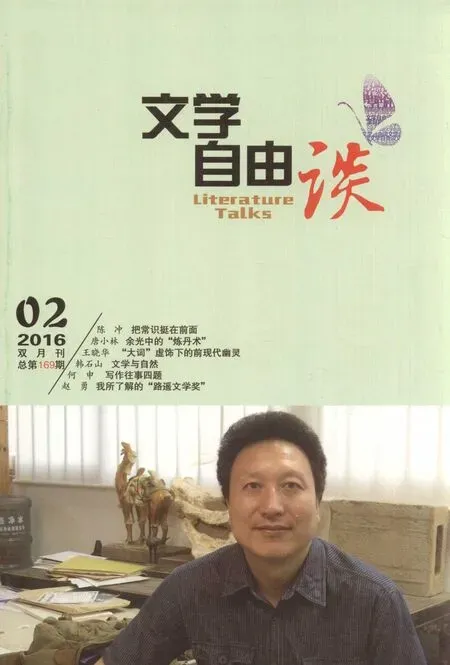文人与高人
张传伦
文人与高人
张传伦
想写这篇闲文很久了,一旦动笔写下标题,又怕生出些许悖论。文人与高人往往相伴而生,高人中文人不少,文人中也不乏高人,有时很难厘得清。
清朝“扬州八怪”中最具才情的郑板桥在山东遇一老者,实属就是高人中的高人。初见此人寻常老态的样子,很像乡间里闾那些上了年纪的老乡绅,几分儒雅之气。闲聊了几句,郑板桥便觉老者谈吐不凡,遂大为折服,这便有了他平生所作最有名的那一件行书横幅“难得糊涂”。
故事发生在乾隆年间。话说某日郑板桥去莱州文峰山观摹“郑文公碑”,看得兴起,不觉夕阳西下,只好借宿山间茅屋一老儒家中。屋舍颇宽敞,主人也颇有几分不俗,寒暄几句便觉投机。主人自号“糊涂老人”,板桥稍觉有趣,心下思忖:其人自云糊涂,且以糊涂自相标举,恐非常人。及见室中置一大小如桌面的砚台,形制古雅,题刻俱佳,而“糊涂老人”论砚之语,大见隽奇,于是生出几分欣赏之情。又见案上笺纸笔墨之精良,绝非村夫野叟之所用,板桥不免有些技痒。老人适时进言,恳请墨宝,跋题砚铭,板桥稍加睇视,即题写“难得糊涂”四个大字。因砚石太大,留白过多,板桥便邀老人写上一段跋文,老人挥毫立就数语:“得美石难,得顽石尤难,由美石而转入顽石更难。美于中、顽于外,藏野人之庐,不入富贵之门也。”板桥觉其书法、题词大有功夫颇有见地。有感于“糊涂老人”雅号之不俗,便又补写了“聪明难,糊涂尤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放一着,退一步,当下心安,非图后来福报也”。板桥写好,退身两步,上了一眼,也还称心,于是盖上了那一方在板桥印章中最负盛名也最是牛气哄哄的印章:“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糊涂老人”见状,不紧不慢自印匣中摸出一印,随手钤盖,印文同为十二字:“院试第一乡试第二殿试第三”。板桥视之既惊且惭,感慨良深,敬仰之心油然而生:此老非“野人”,实是高人,曾居庙堂之上,功名亦远在我之上啊。
郑板桥的进士名次与此老相比,的确相差太多,得中乾隆元年丙辰科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其实已是相当不易。后来的中兴名臣曾国藩不过得中道光十八年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进士。由进士而点翰林须应翰詹大考,最重二甲进士,三甲很难入选——正所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今观不少“年度评选”“岁末精品”之类读物,常常有“最佳作品”等字样,此种冠名其实很值得考量,须谨慎才是,莫为博读者眼球而失了分寸。
高人未必尽是阅世极深之老者,巾帼闺阁之中,亦不乏其人。据传康熙时,江阴缪某,有才学,颇自负,而终身不得志。其自云“未得黼黻休明,至老经猷莫展”,因而命笔,撰《野叟曝言》庞然巨帙,借以泄愤抒怀。此书托言明弘治年事,有讥刺时政之语,倘令付梓,必招奇祸,而缪某惘然不知。适康熙南巡,“缪乃缮写一部,装潢精美,外加以袱,将于迎銮时进呈,冀博宸赏”,全然不知大祸将临。康熙朝文字狱虽不及雍乾之惨烈,罹祸之文网亦密。幸“其女亦通文墨,且明晓世事,知此书进呈,必酿祸,又度其父性坚执,不可劝止”。
有一路人之所以为高人,就在于关键之时、危难之际,可想常人所不能想、可做常人所不能做之事。缪家女儿正此中翘楚,所出缓急止险之招数,鬼谷子转世,亦当三折肱,服其绮思狡黠,不让高冠峨带,“乃与父之徒某议乘夜用白纸装钉一部,其精美与原书无殊,即置袱中而匿原书于他处。次日,缪将迎驾,姑启袱出书,重加什袭,则见书犹是,而已无一字矣。缪大哭,以为是殆为造物所忌,故一夕之间,书遽羽化也。”
古人多迷信,缪氏以为天意不令其获御赏。缪女待其父稍致平静,以温慰话语,彻底打消缪氏邀宠念头:“乃徐劝之曰:‘既为造物所忌,似不进呈亦佳,免召杀身之祸。’缪无如何,始罢进呈之意,由是郁郁而死。”虽亦憋屈,然与横遭斩首戮尸之祸相比,算是善终。
缪家姑娘固孝女无疵,其于忠孝,无违无失。父死后,她“乃将其书重加润饰,凡秽亵之语,删除略尽,始付刊,即世间流传之本也”。
《野叟曝言》,“书凡一百五十四回。其中讲道学,辟邪说,叙侠义,纪武力,描春态,纵谐谑,述神怪,无一不臻绝顶”。此书若有不逮之处,则如“昔人评高则诚之《琵琶记》,谓用力太猛,是书亦然”。
似缪氏女儿之聪慧,寒云凄雨间,小试弱腕纤手,救得老屋于既倒,向使临文操觚,芸编瑶笺,一定比《野叟曝言》更好看。
此故事见于《清稗类钞》。著一“稗”字,可知为野史。虽云野史可补正史之不足,发覆史乘所不能发,然多不若正史之谨严。《野叟曝言》一书作者并非缪氏,实为夏敬渠。此作至光绪七年(1882年)方始公开问世。据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引述其“序言”,可知作者夏敬渠“以名诸生贡于成均,既不得志,乃应大人先生之聘,辄祭酒帷幕中,遍历燕晋秦陇……继而假道黔蜀,自湘浮汉,溯江而归,所历既富,于是发为文章,盖有奇气”,“屏绝进取,一意著书”。
古人所云“若士”,向为隐逸之高士。高士中有耸然高迈者,气节彪炳,意气蹈厉,不为世用,此辈又岂是世用之人。正明朝士人所赞喟:“茫茫海宇不能容一若士,若士心中容一海宇。”
宋朝大词人姜夔于《白石诗说》“原序”中尝记一衡山若士,然细析其事,缘起于白石昔年曾读唐代韩愈“石鼎联句诗序”中所叙一故事:唐人侯喜和刘师服相与论诗,衡山道士轩辕弥明在其侧。侯喜自视清高,鄙其老丑,而师服表面敬之为高人,实不知弥明有无文采。“弥明指炉中石鼎邀与联句,大折二人。二人因请问读何书,弥明不应。二人坐睡。及觉,觅弥明不得。”
南宋淳熙丙午,孝宗十三年(1186年),立夏之日,姜夔“游南岳,至云密峰,徘徊禹溪桥下上,爱其幽绝,即屏置仆马,独寻溪源,行且吟哦。顾见茅屋蔽亏林木间,若士坐大石上,眉宇闿爽,年可四五十。心知其异人,即前揖之,相接甚温。便邀入舍内,煎苦茶共食。从容问从何来,适吟何语?余以实告,且举似昨日《望岳》‘小山不能云,大山半为天’之句。若士喜,谓余可人,遂探囊出书一卷,云:‘是诗说。老夫顷者常留意兹事,故有此书。今无作矣,径以付君。’余益异之,然匆匆不暇观,但袖藏致谢而已。问其年,则庆历间生。始大惊,意必得长生不老之道。再三求教,笑而不言,亦不道姓名。再相留瞰黄精粥,余辞以与人偕来,在官道上相候。告别出,至桥上马。偏询土人,无知者。惟一老夫叹曰:‘此先生久不出,今犹在耶!’欲与语,忽失所在,怅然而去。晚解鞍,细读其书,甚伟。常寘枕中,时时玩味。”
姜夔衡山所遇这位若士高人,诗才不让唐代衡山道士轩辕弥明,更令姜夔惊钦不已,极欲向此无名氏高人,拜求彭祖高寿秘诀。姜夔观此人年纪不过四五十岁,竟然“庆历间生”,屈指数来,实乃一百四五十岁。庆历为北宋仁宗时年号,庆历元年值公历1041年;姜夔衡山遇此高人,时在1186年,沧海巨变,由北宋至南宋,其间换了七个皇帝。然此若士“眉宇闿爽”,不见些微老态衰相,难怪姜夔《白石诗话》“原序”五百言,泰半文字状写若士,视此若士之奇,不亦神仙洞府之人也。
古人寿至一百四五十岁,代不乏人,而言彭祖命寿八百,则太过夸张。长久以来,彭祖始终作为长寿之象征。最是清代一学子,沾了彭祖大光,姓王名寿彭,时也运也!利在此人刚好连捷光绪二十九年(1903)癸卯科考,这一年正值西太后大寿,老佛爷一见这名字,好!“寿比彭祖”,考卷的文彩、书法、格式也还谨严无误,于是便不顾中程之闱墨到底够不够一甲一名的水平,只管一意擢拔,点了状元。
老佛爷也好,王寿彭也罢,最终是哪个也没活到一百岁。《黄帝内经》认为,人只要合乎以下养生之道,皆能怡然而过百岁:“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由此看来,能不能长命百岁,是可控的。国人对寿数最敏感,亦可理解。若有人在序齿年龄上矫情太过,虚夸岁老,则要问一句居心何在。当代适有一文坛大佬,曾风度翩翩,然近年来风光不再,并非韬光养晦,而是被灵通人士揭露出不少无行之事,销声匿迹,实属不得已。此老将年龄由八十飙至九十,很有一阵子,以此虚了十岁之鹤发童颜,招摇于荧屏内外,尽享人瑞之尊荣。然究此老之意终不同于齐老。白石先生也曾在两个人生重要时间段各自虚了四岁,是以避“七十三”“八十四”之“圣人坎”,自延寿考,而又未致非议,只因白石老人除此别无机心。
清朝中期,京浦名士钱师竹有事乘船将赴他乡,唤仆人招船至,不意得识船主非寻常舟子。其人旧日门第高耸,中年家境式微,而风雅不弱当年,亲操桨舵。船“小如一叶,净无纤尘”,舱房“中悬书画,皆国初名人真迹。杂列弦管,其泽如新。舟子自谓弄桨之暇,藉以自遣,不敢附庸风雅也。钱入舟,坐甫定,茶具酒铛,一一罗列。茗碗制工色古,非近世陶瓦器。钱问何自来,舟子曰:‘我家旧物也。’因论诸窑优劣,旁及金石真赝,宣和博古图,如数掌上纹。”
钱师竹不禁肃然起敬。落魄公子,毫无措大潦倒相,一味风雅,宛若儒宗岿然挺经,其人足以雅士深蔚,而入高人之列。钱遂“详叩氏族,答姓叶,无字。人以五官相唤也”。
高人之谓,实至名归,多以德高、艺绝而当之,亦有虽系凡人,小有专长,吉星多所照应,际遇、运势极佳,偶入高人之列,其事亦奇。
有清一代,小说家言者,奇书两部而已:言情之作,则莫如曹雪芹之《红楼梦》;讥世之书,则莫如吴敬梓之《儒林外史》。清人书评寥寥数语,绝妙之致,最见机锋:“曹以婉转缠绵胜,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有将军欲以巧胜人,盘马弯弓故不发之致;吴以精刻廉悍胜,穷形尽相,惟妙惟肖,有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所谓各造其极也。”
《红楼梦》一经问世,最先倾倒京都皇族、士夫阶层,其后各种版本迭出不穷,伪作赝本居多。殆至民元,据称以胡适所藏脂砚斋庚辰本为善。四九鼎革前,胡曾借与周汝昌阅览数月。然此本终不可与京师书贾一朝撞大运而得之精楷手钞全本《红楼梦》一较高低。
书贾陈姓,光绪庚子事变前,设书肆于琉璃厂,国难避于他乡。待返京,则家产、古籍荡然无存,懊丧欲死。真是天无绝人之路,一天,访友于某乡村,友人与之言:“乱离中,不知何人遗书籍两箱于吾室。君固业此,趣视之,或可货耳。”陈贾比之友人外家子,浑不知善本书籍为何物,高明寡识,何啻霄壤!视此,谓陈贾为高人,虽不中,亦不远矣。
陈检视其书,小端楷钞写,一笔不苟,“每页十三行,三十字”。此书非一人誊录,状元公陆润庠等数十人钞之,各标注姓名于中缝。陈贾睿目,知为大内禁中物,遂匆匆揖别友人,“急携之归,而不敢示人”。秘藏半年,经由某同行驵侩介绍,陈贾以巨资售于京师史家胡同某国公使馆秘书某,从此不虑衣食之忧。“其书每页之上,均有细字朱批,知出于孝钦后之手。盖孝钦最喜阅《红楼梦》也。”
孝钦为咸丰帝后,同治帝生母。光绪末年,宫中兴土木,一应古物陈设,不敷工用,“孝钦后思移热河行宫物入大内,载一百八十巨车,入京师,计瓷玉雕漆及紫檀器十八万件。自是而热河珍异,半入内廷矣”。
距之五十年前,有两位钦差大臣,声闻遐迩,为官做人却大为不同。前者为虎门销烟的林则徐,后者乃琦善是也。林则徐主战英夷被黜,接任者即为时任直隶总督的琦善。二人有一点相同之处,即仕途官运都折在广州。
清道光二十年七月,浙江定海失守,英军乘舟北上,锋芒直逼京都。道光帝闻报英船或至天津,初,谕示琦善:“英船倘至天津求通贸易当告以不能转奏”,倘英夷有桀骜情形,“即统率弁兵相机剿办”;未几,旨意又变为“对英船不必遽开枪炮,并可将英人所递禀帖进呈”。此一圣旨,为清廷在鸦片战争期间“抚夷”国略之起始。历史赋予琦善首次和谈之重责,此一角色亦决定了日后琦善误国、误君、误己的悲剧命运。督抚,为封疆大吏,职系所在,保一方平安;直督地位尤其显赫,郡治大片为京幾之地。琦善的天津交涉,事关重要,不仅是从地方考虑,将英军“劝退”那样简单。劝退“成功”,使琦善不由自主地走上“和谈解决中英冲突”之路,且于道光帝有所误导,产生不切合实际的和平了事之幻想。
正是在此时代背景下,钦差大臣琦善来到广州。
琦善由开始的“抚夷”妥协以解决中英纠纷,至道光二十年十二月,英军攻占大角、沙角炮台,抚夷失败。“剿夷”,琦善更是既无信心,也无能力。不料,道光王朝对英政策发生了大转弯:“对英军奋力剿办。”琦善不解圣意,未能随之转换角色,仍要履行抚夷和议使命。道光帝拿到琦善《英人寄居香港通商章程底稿》,御览之时,不禁龙颜大怒。琦善仍不知趣,及至在其钦差大臣一职等待被撤换的微妙时刻,竟“恪尽职守”,上了最后一道《酌拟准英人寄居香港及来粤通商章程底稿》的“昏折”。终于,道光帝忍无可忍,于二十一年二月初六日,下旨将琦善“即行革职抄家锁拿严讯”。
琦善府中有一刘姓杂役,可称义仆。琦善籍没家产之日,这位刘姓杂役尽现人格之高尚:“树倒猢狲散”,琦善合府下人,全体行动,趁火打劫,纷纷抢夺主人家产,独刘氏廊下冷眼观之,抚柱而立。宵小劝其“不拿白不拿”,刘氏答曰:“非吾物吾不取。”遂返京东老家乡下荷锄务农。然其事,不翼而飞,尽传于京都王公贵族。适有一王爷,备赏刘氏高义,差人延入王府,聘为管家。
一府仆下,尚有此高士,可堪慰人之处,远胜于今。某高速公路有货车颠覆,货物尽散于地,附近村民,权当天降横财,闻风而动,车拉肩扛,不消半个时辰,一扫而光,呼啸而去,行动之快、效率之高,远超事故清障车。
恃绝艺在身,世人目为高人者,倘入得“琼楼最高处”,展现才艺,蒙上青睐,荣耀非比寻常。袁世凯欲称帝之时,内心颇纠结。“跛脚大太子”袁克定为讨父皇欢心,觅得一江湖奇士,奇门绝技,海内独此一家,非大户高斋出巨资相邀,不肯献艺。奇士奇矮,寡和少语,负一硕大烟斗。克定带其入瀛岛一便殿,袁大总统斜倚卧榻,正待欣赏。克定示意开场。此人卸下烟斗,探囊取火镰,点燃烟斗,猛吸几大口,腹涨如鼓,忽然喷出一股浓烟。先是缭绕殿中,距地丈余间,化为烟云数朵;再吸再喷,如是者三。渐渐汇聚一龙,头角峥嵘,矫矫云间,依稀现五爪,烟云不接处,支股间断,讵意“神龙见首不见尾”,是此形状。烟云莫测,幻奇幻诡,云聚云散,龙形倏忽不见,恍入紫虚深处。
陪观数人见袁大总统欣悦其艺,微微颔首,皆拊掌称善,克定更是大呼“看赏”。高人高艺,高在投其所好。恰逢袁世凯称帝前夜,有龙显灵,焉能不获厚赏?一千块袁大头,民元之初,可于京华首善之地,购一两进四合院落,绰绰有余。何怪乎杨皙子事后趣言:“学得变龙技,卖于帝王家。”
与之同时代,亦有一街头卖艺人,养黑、黄蚂蚁两箱,挥动白旗,两窝蚁群倾巢而出,于担案上撕搏,如两军接阵。挥动黑旗,蚁群如闻鸣金之声,徐徐而返,鱼贯入箱。观此艺奇耶趣耶?媲之口吐云龙,终是小巫见大巫。倘求此技现之于今日,戛戛乎难觅。
无论大哉“变龙技”,抑或区区“驱蚁技”,方家作手审其艺,皆为真功夫,唯憾不知用何方法练成。绝不似当世之魔术,虽可隐山遁城,将偌大飞机变为乌有,不外乎倚仗现代科技声光电而已,恃此何幻不成,又何足夸能?
扯远了。诸如高人炫技,得道升天,享荣华富贵,而有些文人,口吐莲花指鹿为马,于今竟也能蒙骗一时。
可叹可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