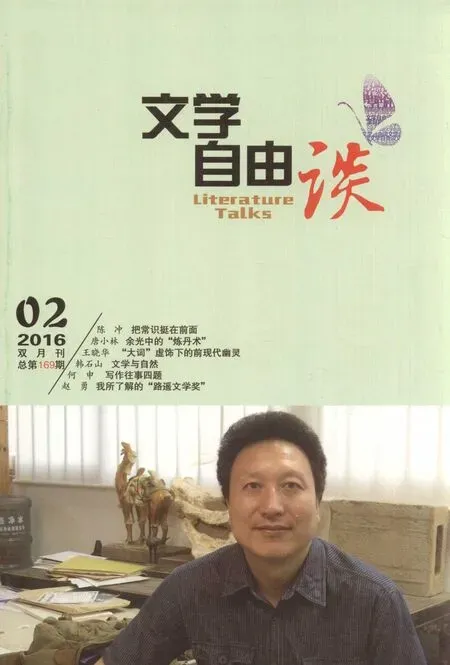在新年的阳光中悼念
李美皆
在新年的阳光中悼念
李美皆
我与褚钰泉老师只有一面之缘,在《悦读》的作者座谈会上,在北京。当时我虽然已调到北京,但人常在南京,忙着写博士论文,我是专门为这个会从南京赶到北京的,开完会马上又赶回南京。这个会似乎可以不来,但我还是来了,因为这是褚老师让我来的。对他总怀有一份特别的尊重与信任,相信他所做的事一定是有价值的。他说,希望年轻人也参加进来。作为一个内行的编者,他很重视作者的梯队构成。在这次会上,我确实算是年轻的与会者了。那是一个很有思想含量的会,与文学的会不同。无论向思想致敬、向良知致敬,还是向勇气致敬,同时都是在向褚老师这样的编者致敬。没有他们的敬业精神和职业经验,那些带着尊严的睿智的文字都不可能从容面世。在后来的邮件中,他说,时间匆匆,未能细谈,颇憾,但总算见过面了。是的,总算见过面了。我所见到的他,与我感觉中的他完全一致,低调的、谦逊的古君子之风。此前的邮件中,他称我“美皆同志”,这样的称谓,在私信中真是久违了,严肃得让我不知如何回话。这次见面,他称我为“李老师”,我说“折煞我”也是真心的。我想他是不会随意说话的人,他恪守着自己做人的一种规范,正如他恪守着编辑出版的一种文化价值。
我对褚老师的感性认识就是这些。但一种编者与作者之间坚韧的默契的神交,让我对他有种依靠感。这种依靠,就是靠谱、托底这样的意思。比如,以前有了某种想法,我会自我怀疑:写吗?往哪发呢?写了也白写,算了吧。但是,自从认识了他,想到有他,我就有了写出来的动力。不需要多话,我就明白和相信,只要有价值的,他都会想方设法发出来,即便有过犹豫,也终究会是不舍。偶尔,他会从专业的角度给予提示:文章内容有助于解开历史真相,但引用的材料有没有版权问题?尖锐的部分可否缓和含蓄一点?用事实的陈述让读者自己得出结论是不是更好?我是要让矛头刺出来,他是要让矛头包在包袱里,但无论如何,矛头都在,彼此连说明和解释都不用,都懂。我们共同看得见,一条通往自由和尊严的暗道。
我们这个时代,纯正郑重的主编太少了,有足够文化含量的刊物也不多。自己去订阅喜欢的刊物,是对主编最好的致敬,同时也是一种道义的支持。我邮购了两份《悦读》,一份送给一位尊敬的朋友。褚老师在邮件中说:其实你不必去订阅,我会每卷给你寄的——顺便说一下,《悦读》因是出版社出的,邮局是无法征订的,不知你是如何办的。《悦读》出版后,各方反应尚可,出版社有意要我改为定期的刊物,还准备了刊号,让邮局发行。但我未同意,因为现在我一个人在编,时间固定了,太框着自己的手脚了,所以,《悦读》现在还是由书店发行。——这是我第一次知道,编辑《悦读》,居然是凭他一人之力。真的看不出来,《悦读》不仅宏观上把握得好,而且细处也极其用心,比如“补白”,就是细小又恰到好处,给人一种小家碧玉的欣喜。
褚老师的用心,在其他地方也体现出来,查看以前的邮件,有一封他写:为了让你先睹为快,特地将样书快递给你;最近发现快递也会遗失,于是惦记着你是否收到,见信知你收到,我就放心了。他还不忘告诉我:昨天遇到某教授,对《悦读》上你的某篇文章表示赞赏。听起来,对这样的反馈他比我还要欣悦。还有一封邮件,他写:有一件事有点遗憾,7月上旬曾收到你的一篇稿件,当时我正在南昌,为新的一卷忙碌。在那儿不便复信,没给你回音。回到上海,见到这篇文章已被刊登,颇觉遗憾,这是我的疏忽。其实我是很喜欢这篇文章的,我觉得我们的文学批评应该多发些这样的文章。他实在太爱自己的刊物了!像对孩子一样爱。作者的敬重与感动,亦因此而生。
第一次收到《悦读》的稿费时,我发现比想象的高很多,高到让我不好意思。给他发邮件说,这种文化含量高的刊物,办起来不容易,不用给这么高的稿费。他回复道:严格地说,这样的稿酬,与你文章还不太相称,这完全是你应该得的。《悦读》的成本不高,就我一个人在“折腾”,从组稿到出版,以至扫描,寄书……事务工作,都一个人干。作为我来说,也仅是从中得到一点乐趣。另一点,很重要,这家出版社的社长,事业心很强,并不要我追求盈余,因此干得就很愉快。如今这本书仍放在南昌出版,每次出版前我都要去一下。明天,就要去为下一卷奋斗了。
褚老师就是这样,以文人之骨,为同仁们经营着一片苗圃。他没有猛士的姿态,但他的坚韧,无论如何低调都会渗透出力量,让作者感受得到。他就是一个不着一字也力透纸背的人。就连他的可敬,都浸润在心、很难表述。
总以为,这样的依存,可以源远流长,从来没有去想过终止、消逝的问题。
收到《悦读》44卷,我第一时间看了。2016年1月12日,又发短信问他有没有给一位朋友寄,他没回。我跟褚老师一般都是电子邮件往来,极少发短信,我想,也许他是不适应发短信吧。再等等。年底忙,这事暂且搁下了。1月18日下午,快递员让我到门口取件。是什么呢?我去的时候想,这几天并没“淘宝”啊。拿到快件,是文件袋,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我知道肯定与《悦读》有关。是什么呢?我往回走的时候又想,征订单?稿费单?稿费以前都是直接打到卡里去的,现在方式变了吗?我边走边漫不经心地打开了文件袋。只有一张纸,第一句话:惊悉褚钰泉先生不幸离世……
没说因何去世。我急匆匆地赶回办公室。手机即将没电,等不及充电,借了同事的手机打过去,徐泓老师接的。我有点语无伦次。由徐泓老师处得知,褚老师9日心脏病突发去世,11日火化,13日家人才告知朋友们,包括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的同事。出版社要出纪念集,没我手机号,才发的快件。我终于知道褚老师为什么没回我短信了,那时他已经去世三天……
记得,我还对徐泓老师说,知道是心脏病,我就放心了。想想不妥,又赶紧解释,至少,不是抑郁症什么的。我们这个圈子里抑郁症高发,这几年我实在是被抑郁症吓坏了。记得有一次在某地开会,我看着一位女士,面色枯黄双眼空洞地仰靠在墙上,好像在场的只是她的躯壳。我能够直白地读到她内心的生趣全无。旁边有人告诉我,她有抑郁症。我说,怎么又是抑郁症!那个人又随手指着另外两桌说,那个,那个,都是抑郁症。三桌人,居然就有三个抑郁症!简直令人头皮发麻,怕到自己身上来,有种想逃的欲望,唯恐被抑郁症这个魔鬼追上来。所以,你知道,首先排除抑郁症,对我来说简直是一种自救。
电话里跟徐泓老师谈到,与褚老师之间的一切,都是超越于物质意义的生活之上的。我们所感受到的褚老师,是完全一致的。谈到某篇稿子,徐泓老师告诉我,褚老师曾对她说,我们要尽可能地把真实的历史告诉后人,不要让后人以为我们这代人是不敢说话的。褚老师貌似平凡,却有这样不凡的担当,令我们喟叹。
虽然与褚老师只有一面之缘,所有的邮件电话短信都是谈稿子谈刊物,并不交心,对彼此的人生也不了解,但还是很难过,很难过。胸口的沉闷滞重,让我觉得必须写点什么才得纾解。写作的人,唯有文字可以倚重。
那几天我都缓不过神来,好像被抽走了什么,胸腔里少了一口气。早上来到办公室,看见褚老师编的最后一期《悦读》,如同看见他的心血、生命。身体如倒下一般颓然坐到椅子上,两眼发直。以为固若金汤的链条戛然断掉,看着那断头,心里可能就是这般空空如也吧?年轻时候,健康从来不在考虑之列,因为无须考虑。随着年纪渐长,身体的信号把“健康”二字变成一号黑体红色,标注在我们的生活中。亲友的离去,更使我们不断地听到彼岸的敲门声。一次次感受到生命的脆弱和不可信任。我们走着,说着话,我们的房子和家还有一应生活物事都在,淘宝依然红火,生命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死亡遥远得好像根本不存在。可是,猝不及防地,它来了,转瞬即到,好像一直就在门外等着。害怕这样的惊扰,所以,真想对所有珍惜惦念的人说:请你们,好好活着。
有句话说,珍惜眼前人。其实,要珍惜的,岂止眼前人,也未必眼前人。褚老师倾一己之力,惜护一种文化价值,坚守一种文化品格,我们对他的悼念,也是对一种文化价值和文化品格的悼念。我想,我们所有人对于褚老师的尊敬与怀念,都是基于这样一种共同的东西。我们共同尊敬和惜护着一种东西,这使我们像亲人一般。《悦读》在知识界已有良好口碑,但褚老师走了,《悦读》或许就要停办了。世上再无褚老师,亦无他的《悦读》。
那几天尽是为活着而忙碌。一切的过程中,褚老师不止一次在我脑海中出现,构成那段时间的心理背景。片刻的停止中,禁不住自问:我做这些,为了什么?鲁迅先生说:“人类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了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是的,忙忙碌碌,但有价值的很少。我为凡夫俗子的生活深深懊恼着,同时,还有一篇答应的文章已经到了交稿时间。这篇稿子要查很多的资料,而我根本没有写作的状态。隔着这篇稿子,去眺望很想为褚老师写的悼念文章,愈发感到沮丧和绝望。我不能在忙乱之中写他,那是对他的不敬。那种状态下,我也无法写,我甚至感觉不到自己,又怎能去触探他的精神脉动。那是要沉静下来才能写的,可是,何时才能沉静下来?
有一天下午,我本来准备在家写一会儿文章,微信上看到单位通知开会,赶快换衣服,准备去办公室。刚穿完一只鞋子,催稿的微信来了:要排版了,要么说一下大概多少字,先把版面留出来?我放下手中的另一只鞋子,回复:别等了,我不在状态;版面也不要空,我不知道会写多少字。虚位以待的文章,那种紧张局促的瓶颈状态,是写不好的。写作与生存,如剪刀的双叉,一齐剪过来,我只有抽身而退。这些天,我一直在为那篇稿子而努力,哪怕一天只能写几十个字,我都没有放弃。刀子在头顶悬了好久,最终不了了之,这种事是很不符合我性格的,也是第一次发生。抱歉的同时,也感到解脱。到了办公室,因为人不齐,会又不开了,改到第二天上午。我坐在办公桌前,突然一阵空虚迷茫袭来,不知道要干什么。再回家赶文章,我也不乐意,而且这一来一回,一下午差不多废了。有一种被抽空耗尽的感觉。孩子不在家,生活尤其有种真空感。无从恢复的疲惫,因长期的身不由己所致。这时,有人约着喝酒,正好。但喝完之后呢?且不管它。我需要清空,需要停止奔突,回到有质量的生命状态。
我以为,我已经废了,状态再也回不去了,我不会写文章了,至少一段时间内。可是,放假了,不再被生活流裹挟,我又是自己了。经过一个下午的过渡,上班生活已恍如隔世,我又能写了。没想到这么快就好了,人的修复能力意想不到地强大。我竟然顺顺当当地完成了那篇我以为会永远成为“烂尾楼”的稿子。
根据我的规律,每完成一篇稿子,我都会消停一下,读一些一直想读的东西,犒赏自己。这次也不例外。可是,说好的要为褚老师写的悼念文章呢?
那几天北京的阳光和空气都格外好,我宅在家里,打开窗户看看外面的蓝天,又满意地关上。阳光暖暖地照在床畔,让我莫名地想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坐在阳光中,捧着一大杯红茶,茶色与阳光相遇,美好,熨帖。空气里有阳光的味道,周身摸上去是阳光的感觉,我简直想跪下来,感恩!感恩的对象,都不具体,只是充满感恩。心中只须想着自己要读要写的东西,再无凡尘俗事的羁绊与纠缠,这种云清月朗的状态,是多么好!
绿植,电子琴,孩子的桌椅,在光影里生动地呼吸着,存在着。自家的墙之内,一切如此美好!然而我知道,生活并不仅有这些就足够了。巴金的《灯》中有一句话:“我们不是单靠吃米活着的。”褚老师一定也是这样想的,所以他会选择那样的活法。
然而,无常无法抵御,有常也难以抵御。我在年味的时光中晒着太阳,日渐慵懒下去。是的,我有点抗拒去写文章了,尤其去写一篇悼念的文章。鲁迅先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写:“离三月十八日也已有两星期,忘却的救主快要降临了罢,我正有写一点东西的必要了。”鲁迅先生也在提防着“忘却的救主”,提防着情感的分量在日常的时间中淡漠下去。每个自省的人可能都遭遇过这样的情形。我唯有警醒着自己:如果连这样的东西都可以这么快地淡漠下去,这日子,就过得太混了。为了抵制麻木与惰性的围剿与包抄,为了不使这种抵抗与挣扎转变为对自己的绝望,我一定,一定要写出来。平常生活中包含的惊心动魄,就在于我们必须时时战胜自我怀疑,战胜麻木和惰性。我其实已经不仅是为褚老师,也是为自己而写了,因为其中浸透着自我拯救的努力。
褚老师,一切有价值的,都不会消亡。我们永远沐浴着同一种精神的阳光。
似乎有悖,在新年里,写这样一篇悼念的文章。然而,褚老师过不上这个新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