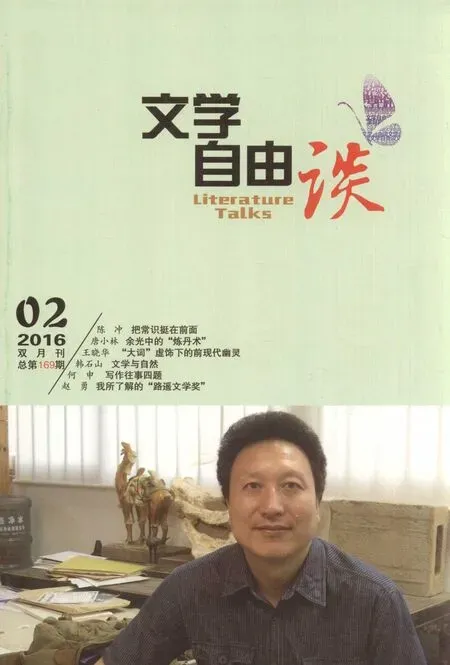桌面的张鸿
黄咏梅
桌面的张鸿
黄咏梅
写作、旅行、摄影、编刊物,在张鸿的身上,有着多样的色彩。她新浪的博客,题签为“行者张鸿”。在语不惊人死不休的网络时代,这题签实在太朴素,也太不起眼了。可是,在“行者张鸿”的博客里,却总有一些新朋旧友纷至沓来,真应了那句古话:“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些游客在浏览博客之余,总会忍不住要留下“到此一游”的痕迹,就如同到某地游历,眼见美丽的景色,不由生发感慨,忍不住咏叹一番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张鸿在博客里,以她独特的视角,用镜头记录下了自己的脚印,我们得以沿着她的足迹,重新行走一遍“张鸿之路”。在这一路途中,往往能拾获一个文艺女青年的感性情怀,亦会邂逅一位巾帼女性的英姿飒爽。
从前,因为工作需要,我常向张鸿约摄影作品。她的作品里,没有大摄影师那种盛气凌人的架势,也没那种剑走偏锋标新立异的野心,她的镜头,看到什么,想拍什么,就认认真真地拍。一树屋顶上的花,一片东北的雪地,一洼还没解冻的水面,一个幽怀心事的陌生女子,一只山坳里落了单的羚羊……她认认真真安安静静地拍下了这些突然闯入她视线的物事,不扭捏不摆谱,自然地成为她镜头下的对话。在她的摄影作品里,没有你看不懂辨不清的不明物体,它们明白地存在着,它们就是张鸿行游至某个地方,觉得有意思,觉得应该与朋友分享,便从那里装了回来,拓了回来,裁了回来……可是,却又不那么简单——最让我欣赏的是,她能把彼时心里感受到的“有意思”,一并都装了回来,一点都没遗漏。所以,在她的片子里,我总是能找到她想要告诉人们的那些“有意思”。这无疑是一幅幅心思缜密的作品,内里的时间地点构图,有着文字难以表达的意味。
那时为了版面需要,我多次向张鸿提出要求,希望她给每张摄影作品都起个标题。按说,作为一名文学期刊的资深编辑,又是散文作家,为照片取个标题还不是区区小事,信手拈来?可是,张鸿发来的照片,每个标题依旧是相机自动生成的缺省编号,诸如“DSC-0739”什么的,让我很是郁闷。她回答我说,要起标题,还真的很难,想来想去都想不好,只好放弃。她最后把难题交给我,我只好望图生义,草草取些虚虚实实的题目了事。有一次,在编发她一张拍摄水的照片时,我照例要给它取一个名字,没想到,我身边一个毕业于广州美术学院的美术编辑,看着这张构图新颖角度别致的照片说,取标题实在多此一举,就无题,让别人自己去领会好了。我恍然大悟。可不是吗?这照片上拍的,可不就是水吗?何须解读?又何能解读?
张鸿试着用自己的镜头告诉我们,世界可大可小,可远可近,因为,世界不仅在人的眼里,更多的时候,它就藏在我们心中。即使一粒尘埃的起降沉浮,一旦有了心的注视,亦可构成一个完整的大世界。
所以,我将行者张鸿的每一张摄影照片都命名为——心的注视。
说实在话,在同张鸿的日常交往中,总是被她嘻嘻哈哈、大大咧咧的行事风格所感染,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她过去当兵的精气神来。很多时候,我这个一贯慵慵懒懒的人,也禁不住受到她的影响,甚至羡慕起她四处行走的生活。前几年一个春天的晚上,在深圳海边的一个度假村,我们有过一次深夜长谈。
这是一次让我起“鸡皮疙瘩”的长谈。
那天晚上,我们分到度假村顶楼住宿,天花板比别的房子要低一些,是那种复古的瓦顶。我们围着一个小茶几,喝一道一道的功夫茶。张鸿坐在我对面的一张沙发里。在她正上方的屋顶上,开着一扇透明的小天窗,皎洁的月光正好照在她身上。整个晚上,张鸿都在兴致勃勃地跟我讲她这些年来,多次在藏区游历的各种奇事、趣事。很多事情,倘若不是因为发生在她身上,而她又是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兼有照片作证,我几乎要怀疑她是不是在虚构。最后,她讲到有一次在云南藏区,一个朋友要顺路接她,让她在奔子栏路边的一个餐馆等他。她早到了些,就在那儿安心地等着。一个女人过来和她打招呼,然后,女人带她到了自己那个破烂的家,找到一袭陈旧的藏袍,穿在身上,带着她到村外的河边,唱歌跳舞,当张鸿的人模。后来,女人长久地坐在河中央的一块大石头上,或者冥想,或者远眺,各种神态,让张鸿拍来拍去。张鸿跟这个奇怪的女人相处了整整两个小时后,又跟着这个女人回到餐馆。这一路上,她发觉所有人都奇怪地看着自己。当她回到餐馆,见到了那个接她的当地朋友,他同样很奇怪地看着她。张鸿这才知道,这个跟自己相处了两个小时的女人,是全村出了名的疯女人,患有精神病,谁都不敢走近她的。张鸿告诉我,她知道真相之后,一点都不害怕,这个从不跟人说话的疯女人,一路上竟然跟张鸿说了好多好多她的故事,包括她曾经受到的感情创伤等等。女人说的那些,张鸿深信不疑。张鸿说,河中心的那块大石头,那女人天天去坐,就是为了等她的感情。张鸿拍了女人好多照片。回来之后,她挑出女人坐在大石头上等待的照片,一直想要寄给她。可是,照片要寄到哪里去?那疯女人在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没有地址寄存的人,跟她的感情一样无法寄存。或许,她对于很多人来说,就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但是,她在张鸿的心里,始终都是一个难以放下的记忆。说到最后,张鸿叹了口气说,这个女人,是一道伤口,这伤口里因为长期居住着爱情,所以久久不能愈合,索性,就敞开了。
讲完这次经历,我们一下都陷入了安静。张鸿头顶上的那扇天窗,月光仿佛将要离去,很是光亮地在她身上照了一下。我看着她,竟然感到皮肤上起了“鸡皮疙瘩”。我知道,我不是在害怕,而是在激动、感动。
记得张鸿曾经跟我讲,可能因为自己是属猴的,所以特别好动。这种简单的宿命论骗三岁小孩还差不多。我现在想,为什么张鸿身上总是有着一些“不安分”的元素,这些元素构成了她总是要出走的动力,催促她不断出发,催促她去看去听,催促她去结识不同的人,记录有意思的故事,因为她真的是热爱这个世界啊,因为她的一腔热爱也无处寄存啊,只好让它们如流水般如行云般如风般,带着自己的眼睛和心灵,不断地走向远方……这是一个会因为热爱而疯狂的女人。她那天不怕地不怕的耿直性格里,裹挟着的感性简直一塌糊涂。她会为听到一句不顺耳的话挺身反击,也会为听到一句感人的话内心一热流下泪来;她会拿出走四方的大无畏来对付一些无理取闹的小人,也会拿出万丈柔情来对待她欣赏的朋友知己……
“一个有使命感的行者,他重视的是自己的成就和心灵感受,而这所得必以一种精神为代价的,那就是‘殉道’。”这是张鸿曾经在一篇散文里写的一段话。无疑,这是张鸿对自己人生的一种领悟,或者说是一种方向。她行走在旅途上,四处寻找着那些温暖的心灵感受,这些感受让她不再孤单,让她对这个世界不再拒绝而是敞开怀抱,让她对身后的一切纠结鄙然视之,让她相信,天大地大,有自我容身之处……为了换取这样的心灵感受,就算“殉道”也在所不惜。
只有读懂张鸿的内心,看她那一张张“无题”的照片,才更能接近“主题”。
我把张鸿的一张照片,设置为我的电脑桌面。这张照片,远处是蓝天白云,青山由远而近。最近的两座山坳处有两匹马,这两匹马由于离镜头远,所以显得很小。两匹马之间相距很近,一匹在俯身吃草,另一匹,则什么都不干,低着头发呆。那匹吃草的马,正陷入了一片阴影里却浑然不觉,而不远处站在阳光下发呆的那匹马,对于身后那片就要蔓延过来的阴影,更是浑然不觉。这阴影,不是张鸿用特殊曝光处理造成。通过近处山体上同样覆盖着的那片参差不平的阴影,我判断,那是天上的乌云导致。乌云恰好笼罩在吃草的马的身上,而我坚信,要不了一会儿,乌云也即将要笼罩到那匹发呆的马的身上。因为风起云涌的缘故,两匹马此刻身处两种不同的命运,被张鸿的镜头定格了。然而,一切却那么地恬静。山也好,马也好,谁都没有对乌云的戏弄而感到一点点在意。即使乌云压顶,也照样泰然处之。这境界,大自然都懂得,马都懂得,人还会不懂?往深处想想,实际上,人的确很多时候都不懂。
拍回这张照片期间,张鸿正身陷一些无中生有的是非当中,因为郁闷和伤心,她逃避到了藏区。回来时,给我打电话,中气十足地通知我——我回来啦!人黑了瘦了,想通了!随后又照例传来一组照片。这组照片,天高云阔,除了藏区风景特有的干净和静谧外,我还从中感受到了一种澄明。那绝不仅仅是镜头聚焦光线的效果,而是张鸿内心的力量穿透了人世迷津而获得的透亮。
每天,只要我打开电脑,我就会对着这张照片看上一会儿。人生在世,一半透明一半阴影,实属常态,而能与阴影和透明共处却浑然不觉,这需要智慧和历练。张鸿说过,这一生,文字和摄影是她说话的两种方式。那么,这张在我电脑桌面的照片,就是张鸿想要对我说的话。在这里,我充分运用我的想象能力,力图还原她的话——她挑起那两道充满英气的眉毛,头一扬,利索地说了一句:这世上,真的有意思,太有意思啦……
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在我桌面的张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