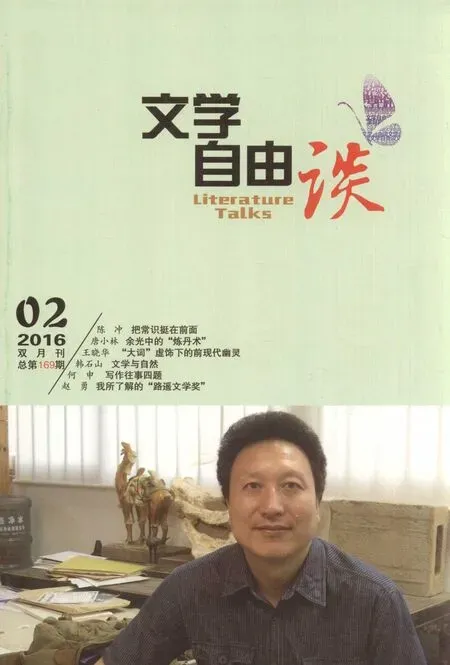我所了解的“路遥文学奖”
赵勇
我所了解的“路遥文学奖”
赵勇
2013年9月初,我收到一条陌生的短信,来信者名叫高玉涛,邀我至《收藏界》编辑部参会,商议一些有关路遥文学奖的事情。犹豫了片刻之后我答应了。此前我曾浏览过路遥文学奖启动的新闻,也知道此奖甫一面世便引发争议,心中便有些疑惑。现在既然让我参会,便可借此弄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可以说,当初接受邀请,除了路遥的名字感到亲切之外,满足我好奇心的成分更大一些。
9月5日上午,我换乘地铁,摸到了潘家园附近的华威里一号楼。大概是以前对唱《马儿啊,你慢些走》的马玉涛印象太深了,我一直也把高玉涛想象成了女性。但见面之后,才发现此玉涛是个大老爷们儿,一位敦实的陕北汉子。那天参会的人还有萧夏林、李建军、旷新年、邵燕君、王向晖等,主要议题是讨论《路遥文学奖评奖条例》,征求意见。此前他们似乎已经讨论过两三轮了,而我则是第一次入伙。记得当时邵燕君主要在讲读者的变化:原来有可能读路遥小说的更年轻的读者,现在都跑到网上或用手机去读玄幻小说了,所以要弄清楚路遥的读者是谁很重要,搞清楚类似于路遥那种现实主义风格的读者是谁更重要。李建军则谈到了好作品主义,他认为这个奖项不一定局限于长篇小说,因为现在的纪实类文学更有意思,小说看的人已经不多了。
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开始与路遥文学奖打交道的。而经高玉涛先生解释之后,我也大体明白了这个奖项的一些情况:此奖由他(其身份是《收藏界》社长)和高为华先生(收藏家)共同发起并筹资设立,是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学奖项。因是民间办奖,既无官方机构撑腰壮胆,又要“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它最初受质疑、被批评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但我也能感受到,虽然面临的压力不小,高玉涛要把这件事情做成的决心也很大。李建军当时提醒他,一定要注意报批环节,因为在中国,什么事情都是可能发生的。高玉涛则很坦然且信心十足,他说:这个奖既不敛财,传递的又是正能量,能会有什么问题呢?
后来与高玉涛先生接触稍多,对他也就多了一些了解。他是做企业起家的,用他的话说,“在家乡陕北、古城西安、首都北京、南粤广东、闽乡福建、西夏古都银川等地,曾创办过食品、乳业、制药、包装、广告、设计、饭庄等十多家工厂、公司、研究所、杂志社、书画院、艺术馆、美术馆、全国性收藏协会以及规模较大的企业集团”(《一首歌·一句题词·一生的敬畏》),可谓一位名副其实的实干家。但许多人可能纳闷:企业做得好好的,干嘛还要来文学界插一杠子呢?依我理解,这其中,感恩的意味要更浓一些。据他言,1990年代初,他与路遥曾有过三年左右的交往,其间曾请路遥去他经营的厂里做过讲座,也请路遥为他创办的普惠集团创作过《普惠之歌》(赵季平作曲)。他至今仍保留着路遥写给他的一封长信。信中路遥先是鼓励他克服困难,勇于创业。写到最后,他甚至向这个小老乡吐露了自己的心情:“我埋头写那个随笔,也相间应付一点杂事,因个人私生活的原因,心情不是很好,只能是走到哪里再说哪里的话。身体状况也不好,时有悲观悲伤悲痛之情默然而生。自己祝福自己吧。”(《路遥的影响——一段尘封了20多年的往事》)能把话说到这个份上,说明了路遥对高玉涛的信任。
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高玉涛是路遥的崇拜者,是路遥作品的受益者——借用现在的网络用语,他算得上是路遥的“脑残粉”。他在文章中曾经说过:“路遥的著作,我视为心中的《圣经》,时常在读。路遥之精神,我当作个人的信仰,一世追求。从知道、认识路遥那一天起,他既是我平凡生活中必然念想的人,又成为自己人生紧要关头多次产生重要影响的人。”他还说:“《平凡的世界》,我曾通读过两遍。生活顺畅的时候,我会翻开《在困难的日子里》。尤其事业遇到了不顺或发生重大变故的时刻,我都会静心阅读《早晨从中午开始》,先后阅读过近十遍,而且常常放在枕头边,读后会坚定自己做事的意志,帮助树立信心,战胜困难,启发自己如何建构某项事业的发展体系,特别是提升自己不卑不亢、坚持到底的精神品质与思想境界。”
路遥对中国千千万万的读者都产生过影响,但能影响到高玉涛这种程度的毕竟不多,而影响到终于有一天要以路遥的名字办成一个文学奖的,也就高玉涛一人了。所以,在我的想象中,当高玉涛办奖遇到重重困难和阻力时,他一定又读起了《早晨从中午开始》。他既要从这篇五万字的随笔中汲取力量,显然也是在用这种设奖的方式感念路遥。记得我曾经问过他一个问题:为什么陕西那边的官方机构不抓住路遥弄成一个奖,却让你这样一个民间人士奔走呼号呢?高答曰:那边挺复杂。
我还想到,以后我们谈到路遥文学奖时,一定不应该忘记发起者与路遥的这种特殊情谊,这是作家影响粉丝、粉丝回报作家的一个经典案例。
那次参会之后,我大概就算正式入伙了,后来高玉涛逢会必邀,我也尽量抽出时间参与其中,为它的完善尽绵薄之力。2014年初,路遥文学奖召开新闻发布会,标志着这个奖的正式开评,我则被邀请担任该奖的二审评委。从此之后,我便与路遥文学奖拴在一起,读作品,写评语,参加中间的评审会和年底的终评会,至今已整整两年矣,其中的感受似可在这里说出一二。
就先从路遥文学奖秘书长萧夏林先生说起吧。
我应该是1990年代中期知道萧夏林这个人的,其后他主编过“抵抗投降书系”,张承志的《无援的思想》(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就是其中的一本。因我那时对张承志的文字喜欢得一塌糊涂,他的书自然是要悉数买到的。而读过《无援的思想》后,免不了要对这位主编者想象一番:萧夏林是谁?抵抗投降?这策划还挺有想法的嘛。
真正见到萧夏林是2005年,那是在北大中文系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初次见面,我就觉得这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与他相熟者就不客气了,说:还是人家萧夏林长得有特点,跟电影里的汉奸似的。大家就乐,他也不恼,抿嘴一笑,仿佛这么被调侃已是家常便饭了。
又一次与他打交道是四年之后。2009年10月的一天,老萧突然给我打电话,让我第二天参加一个聚会,说是要审读一部长篇小说。跑到万圣书园附近的避风塘见面,他掏出一摞打印稿,名为《我的大学》,依次分发给赶去赴会的几位,让我们读后写个千字左右的审读意见。他叮嘱道:一定要实事求是,但也要提点建设性的意见,以便作者修改。我完成了老萧布置的任务。一年之后,偶然得知这部小说已经出版,作者于怀岸,书名已改成了《青年结》(金城出版社2010年版)。
后来,我们仿佛就相忘于江湖了,直到在商量路遥文学奖的时候相遇。
就这样,我成了萧夏林领导的部下。当一个季度结束时,他便把一审评委看好的两部小说快递一圈,让二审评委审读并拿出审读意见。许多时候,他只是给大家预留十天半月的时间,结果催要得又很急,跟黄世仁似的。去年4月29日,他一大早就用短信给我发布命令:“赵勇,上午把意见给我。”我的回复也斩钉截铁:“给不出来。五一期间读,然后给,如何?最近已进入农忙季节,大量的硕博士论文需要看。”他不依不饶:“明天要开发布会了,本来今天要开。你一向最稳妥的啊。你看了没有?看了,先给我个意见。”我说:“还没看,最近忙死了。你以后给大家信息,告一下交评审意见的最后期限才好。我不知道这两天要开发布会。”但说归说,做归做,那天我放下所有事情,“挑灯夜读牡丹亭”,又半夜三更给他发意见,第二天起床,感觉整个人都昏沉沉的。
这大概就是老萧的风格。
老萧长得像坏人,实际上是好人,读作品这件事他就很敬业。加了微信之后,我就见他隔三差五在朋友圈里发图片,不是晒地瓜(他似乎在山东种了二亩地),就是晒杂志——他把看过的二三十本文学期刊码在那里,让人觉得惊心动魄。记得十年前,北大邵燕君还很有心气儿,带着一干人马办了个“北大评刊”的论坛,天天忙着读期刊,发高见,搞得文学期刊大小主编心旌摇荡。几年之后她却金盆洗手了,用她的话说,是文学期刊“非常边缘化,没有向上的生长力”(《网络文学完全有可能成为主流文学》,《新京报》2013年3月16日),于是她一头扎进网络文学的汪洋大海之中,不冒泡了。应该是老萧劝她苦海无边,她才开始上岸歇脚(邵燕君也是路遥文学奖评委之一)。在今天这样一个手机阅读或“悦读”的时代,谁还有闲心去读期刊呢?我看也就剩下老萧率领的我们这个团队了。因是二审评委,我只看挑上来的小说,阅读量毕竟要小许多,但老萧和一审评委却要在众多的文学期刊中披沙沥金,干的是“众里寻他千百度”的事情。
老萧早有文坛“骂将”之名,他“骂”过余秋雨、杨绛、巴金、王蒙、贾平凹,连香港的金庸和台湾的南方朔也没放过。所谓“骂”,其实也就是心直口快,有甚说甚,批评的火力过猛,不像文坛上以表扬为业的评论家那样温良恭俭让。这种风格自然也被他带到了路遥文学奖的评审里。记得去年年初他主持新闻发布会,一开口就说茅盾文学奖如何,华语传媒文学奖怎样,指名道姓批评一些当红的评论家。有人发言时就劝他:路遥文学奖现在还是在争生命权和生存权,不必搅和进他们的是非之中。但老萧本性难移,去年“茅奖”评过后他又开骂了。
老萧的骂法并非全无问题,但它依然让我想起了马克思的谆谆教导:“向德国制度开火!一定要开火!这种制度虽然低于历史水平,低于任何批判,但依然是批判的对象。”
为什么我会加入到路遥文学奖的阵营中呢?借这次写作之机,也许我需要清理一下自己的心路历程了。
首先当然是路遥。路遥是我敬重的一位作家,我在文章里、课堂上曾表达过如下意思:“重要的是路遥把文学当成了一项神圣的事业,而不是像他的后来者那样把它当成了一种可以开发的产业。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写作所营造出来的神话依然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今天我们怎样怀念路遥》)因此,我常常把路遥的写作看作一种古典行为,他不取巧,不跟风,认认真真地思考,踏踏实实地劳作,最终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路遥病逝于1992年,而正是从这一年开始,“市场经济了,文学怎么办”的呼声此伏彼起。从此往后,大部分作家的写作心态和状态为之一变。有时候我会想,英年早逝对于路遥来说诚然是一个悲剧,但倘若换一个角度,是不是也算不幸中的万幸?记得盲人歌手周云蓬曾如此评价过海子之死:“如果他还活着,估计已经成为了诗坛的名宿,开始发福、酗酒、婚变,估计还会去写电视剧。站在喧嚣浮躁的九十年代的门口,海子说,要不我就不进去了,你们自己玩吧。”(《绿皮火车》)这种说法或许也适用于路遥。如果路遥还活着,面对时代战车的呼啸与喧嚣,他将怎样调整自己和把持自己呢?他还能写出《平凡的世界》那样的作品吗?
不得而知,一切都是未知数。
路遥文学奖应该是对路遥精神的延续。在那个反复推敲的《评审条例》中,开篇就有这样一段文字:“路遥文学奖面向整个汉语文学写作,坚守现实主义文学理想,鼓励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提高汉语作家和社会公众对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视和关注,推动汉语文学的发展。”(《生活的大树》)显然,“现实主义”是路遥文学奖中的关键词,它也让我想到了路遥当年对现实主义的反思:“如果认真考察一下,现实主义在我国当代文学中是不是已经发展到类似十九世纪俄国和法国现实主义文学那样伟大的程度,以致我们必须重新寻找新的前进途径?……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早晨从中午开始》)在我看来,当路遥有了这番表白时,他固然是在为现实主义文学鼓劲,但无疑也是在与当年盛行的先锋文学较劲。而实际上,就在他较劲的时候,那些先锋作家已纷纷转辙改道,回归到了现实主义的传统叙事之中。
于是有必要继续追问:路遥之后,现实主义成熟起来了吗?发展到了法、俄现实主义文学那样伟大的程度了吗?
很可能就是为了弄清楚这些问题,我才决定到路遥文学奖中走走看看。而这样做的好处是,我可以回到文学现场。
但是,带着任务读小说并不是一件美差。
记得汪曾祺曾说过他读小说的办法:随便翻开某一页试读,若语言好,便从头读起;若语言糟,小说就被扔到了一边。
作为二审评委,我想我们每个人都无法像汪曾祺那么潇洒。一旦一个季度的小说被“推送”上来,那就意味着必须从头读起,而且还必须读得仔细。听一个人唱歌是不需要全部听完的,许多时候,你只要听他唱两句,大体就知道他的段位了。但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却没办法偷工减料,你得跟着作者的叙述进入小说的情境之中,随着故事的讲述形成感觉,做出判断;不仅仅是要关注语言,还要琢磨细节,结构,人物塑造,等等。
除了文学性,小说的公共性(介入性、批判性)是我形成判断的一个重要尺度。大概,这也涉及到对路遥精神的理解。
在我的印象中,路遥精神一直就有形无形地伴随着路遥文学奖评奖的全过程,但明确把它提出来讨论,却是在去年的终评会上。《当代》杂志社的社长杨新岚女士发言时指出:我们这个奖既不是茅盾文学奖,也不是鲁迅文学奖,而是路遥文学奖。既如此,评选最后的年度大奖时,这部小说就更应该向路遥精神靠近。
说得有道理。但什么是“路遥精神”呢?
在我看来,路遥精神至少涉及两个层面:其一是路遥所践行的写作精神,其二是路遥所倡导的文学精神。
在《早晨从中午开始》等文章中,路遥的写作精神已有了充分的呈现。如果要寻找更精炼的表达,那么,《个人小结》(未刊稿,写于1989年初)中的文字或许更具有代表性:“我认识到,文学创作从幼稚趋向于成熟,没有什么便利的捷径可走。因此我首先看重的不是艺术本身那些所谓技巧,而是用自我教育的方式强调自身对这种劳动持正确的态度。这不是‘闹着玩’,而应该抱有庄严献身精神,下苦功夫。”(转引自厚夫:《路遥传》)
这里的关键词是劳动、献身、自我教育。也就是说,通过写作这种诚实的劳动达到一种身心的自我完善,应该是路遥追求的初始目标。因此,在路遥的思考和实际操作中,生活与写作是合二为一的,它们不是两张皮,不是热中人作冰雪文,而是强调言行一致,言文一致,强调“为伊消得人憔悴”,不到黄河心不死。当然,除此之外,我们还不应该忘记,路遥是最具当下意识和读者意识的作家之一。为当下写作而不是为虚妄的未来写作,为千千万万的读者写作而不是为自己写作,曾被他反复强调过。这也应该是路遥写作精神中的一个重要支点。
那么,什么又是路遥所倡导的文学精神呢?宽泛而言,这种精神自然便是现实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讲过,马克思、恩格斯也讲过,已不需要我在这里重复。而具体到路遥,我觉得他所奉行的现实主义更注重回到生活现场,直面社会矛盾,关注普通人心灵的歌哭。此外,他还在这个主义中抹上了一笔理想主义的色调。于是,它温暖人心了,它给人希望了,它励志了,它也改变许多人的情感结构了。
但也必须指出,路遥的文学中还缺乏一种批判现实主义的力度。当我们谈论路遥的文学精神时,一定不要以为那种精神已完美无缺。路遥精神中值得继承的自然要发扬光大,而欠缺的方面则应该充实完善。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画地为牢,才能打通路遥精神的“任督二脉”,让它与古今中外的现实主义精神完美对接。
大概也正是“路奖”评委对路遥精神的理解存在着差异,所以终审投票时才会有些分散。记得2014年的终评会上,评委在讨论阶段很是热闹。有评委说,《活着之上》里的人物是功能性人物,相对于《沧浪之水》是一个退步;还有评委说,《活着之上》并没有让人看到理想主义的曙光,不如《黄泥地》;更有两个评委认为,当年评上来的几部小说均未达到评奖标准,于是他们投了弃权票。当然,为《活着之上》叫好的评委也不少。而我虽对这部小说也不甚满意,但反复权衡,最终还是把票投到了它那里。促使我如此投票的动因之一是,这部作品延续了批判现实主义的精神。也就是说,我这么投票,既考虑到了路遥精神,也考虑到了批判现实主义。毫无疑问,批判现实主义精神比之于路遥精神,会具有更为丰富的内涵。
2015年的路遥文学奖年度大奖,尽管何顿的《黄埔四期》(《收获》2015年长篇专号春夏卷)已经胜出,但在介入现实和批判现实的力度上,我以为它不如陶纯的《一座营盘》(《中国作家》2015年2-3期)。
转眼之间,路遥文学奖已经两岁了。它已度过了蹒跚学步阶段,但毕竟走得还不够稳健;又因为那个民间身份,它还没有得到文学界的广泛认同。但所有这些,我觉得都不是什么问题。古人云:日中则昃,月满则亏。它离如日中天还有不小的距离,也就意味着它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和发展前景。而我本人置身其中,也从最初的好奇者成为了这个奖的参与者和关心者。如果没有特别的原因,我还想伴随着这个奖再走一程。我把“路奖”也当成了一部值得细读的长篇小说,我才看了两章,更多的细节还没读到呢。
也想起路遥在写完《平凡的世界》时曾引用过托马斯·曼的一个说法:“……终于完成了。它可能不好,但是完成了。只要能完成,它也就是好的。”(《早晨从中午开始》)
只要把“完成”换成“开始”,这几句话同样也适用于路遥文学奖。
那么,就让我们一起为这个奖祈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