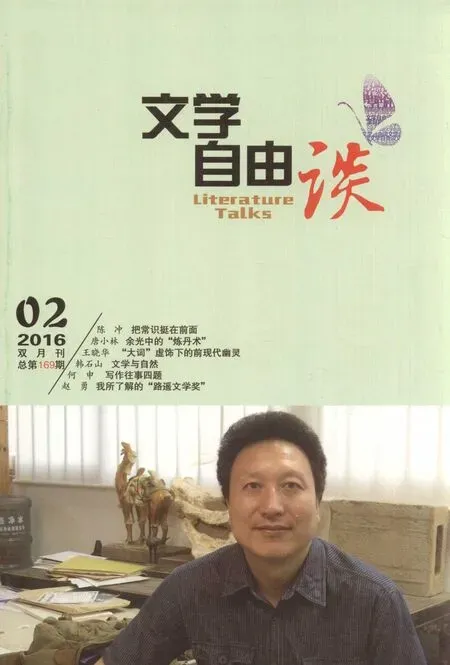文学批评的五条命
赵月斌
文学批评的五条命
赵月斌
1
曾几何时,有人宣称文学已死或小说已死,但就文坛实际状况而言,最可堪忧的却是文学批评。尽管从事理论批评的文学评论家大有人在,与文学有关的论文每天都在大量产生,但这只是一种徒有其表的繁荣;如果说文学尚且徘徊在奈何桥上,那么文学批评很可能已经堕入忘川。所以目前我们的文学评论就像一头溺亡的大象,虽然它浮胀的样子有似宠然大物,其灵魂则不知飘到了哪里。文学评论由此沦入极其尴尬的境地,如同家道中落的豪门望族,很少有人否认它的重要,也很少有人真拿它当回事。不仅作家,不仅读者,连同评论家自身,都持了一种聊胜于无的态度;文学评论,成了可食之亦可弃之的软骨头,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尊严。
眼下的文学评论症候多矣,背离文本,曲意逢迎,泛泛空谈,言不及义,等等,诸多病相让它基本上乏善可陈,即便未必一无是处,也很少能找到值得夸扬的东西。其实无论是饱受诟病的红包批评、人情批评,还是受制于市场、学术机制的广告批评、僵化批评,其共同的表现都是外热内虚,病根则在于评论家主体意识的严重萎缩——他们俳优一般只会取悦或献媚于买方市场,却没有像秉正持中的知识分子那样做出“英雄式的努力”。所以,我们与其悲叹文学评论行将就木、评论家已死,不如置之于死地而后生,重新找回批评的灵魂,让批评家在痛苦的自我锻烧中涅槃更生。
那么,怎样才能起死回生,怎样才能重铸批评的尊严?其实,早在八九十年前,鲁迅先生就已做出了表率。他的文学观念,他在文学批评上的“业绩”,足以说明他不仅是伟大的文学家,也是伟大的批评家。一说起“伟大”,好像只能高山仰止,但是从鲁迅躬身力行的批评实践来看,却只是平常和实在,并不需要三头六臂,或是什么特异功能。他对批评家的希望,无非是“愿其有一点常识”,不要食洋不化食古不化,不要抛开作品信口开河。“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才于作者有益。”当然,从“有一点常识”做到“坏处说坏,好处说好”也不容易,不但要有学识、有眼力,而且还要有胆识、有心力,只有具备了坚定的主体意识,才有可能成为有尊严、有灵魂的批评家。在我看来,一个优秀的批评家,应该具备以下几个特质——
2
知性。批评家首先应该是一个读书家,是学识精深的文艺通才,他应该像神农尝百草那样尽其可能广博地涉猎古今中外的文学经典,在拥有深厚的文学涵养的基础上,构筑自己的专业高地;否则,即便术业有专攻,也可能只是一名挖井似的学问家,很难成为可以振翅高飞的批评家。鲁迅之所以具备宽广的批评眼光,与他长期大量地搜读天下好书不无关系。批评家有如美食家,假如他尝过的菜肴极少,怎么可能培养出高端的品位?可是由于过于严苛的学术规范,过于精细的学科分工,导致文学研究过于学院化,许多教授现当代文学史的批评家,往往只是通晓某一阶段干巴巴的“史”,甚至很少触及原著,更不用说打破专业界限去招惹古典文学、外国文学了。所以,一个置身于当代文学现场的批评家,哪怕少去关注某些炙手可热的作家、作品,也要尽力增加自己的文学储备,让自己的学识足够雄厚眼界足够宽阔。就像建造一座金字搭,你在最底层投入的石头越多,这塔就会越牢固,越高大。
以文学作品为研究对象的批评家又称“专业读者”,但是对批评家来说,多读、深读只是他的准备工程。死板、教条的“专业读者”也很可怕,因为博览群书、学富五车,所以专业;因为专业,所以专家,于是牛气哄哄,高屋建瓴,所作批评反而大而无当,总是隔靴搔痒。伍尔芙、桑塔格即对此保持了足够的警惕,她们更喜欢以“普通读者”自居。伍尔芙的文论集便以《普通读者》为题,在自序中,她引述约翰生的话,对“未受文学偏见污损”的普遍读者给予了由衷地赞扬。桑塔格则多次谈到,她论文写作的基本立足点,是“作为一个读者,从自己的体验出发,阐述读后感及看法”。定位于“普通读者”并非自谦,而是出于一种真诚的清醒。要做一名合格的批评家,先要做一名合格的读者。假如伍尔芙和桑塔格丧失了普通读者的心态,恐怕也写不出《一间自己的屋子》《反对阐释》这样极不普通的“读后感”。
3
理性。批评家的理性当然来自他的理论素养。即便不是文学科班出身,基本的文学史、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史自是不可忽略的;若要致力于文学批评,恐怕还要啃一些诸如《文心雕龙》《结构主义》《影响的焦虑》之类的专业书籍,至少要熟记一批可以显示学问的术语名词。这样,就可结合自己的阅读经验,做出有理有据的“批评”。照此说来,当一个批评家似乎并不太难,很多经过学术训练的业内人士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善于用一套舶来的大道理装入与之匹配的文学,就像卡夫卡说的那样:为一个笼子找一只合适的鸟。生吞活剥的理论加上一部分原文摘引再加上啰里啰嗦的内容复述,几乎就是某些“学术论文”的常规模式,这样的文学批评根本谈不上批评,跟文学也不沾边,只是一种简单的体力活罢了。理性的批评绝非贩卖半生不熟的文学理论,而是要建立在一个相对恒定的价值观念之上,这样才能确定自己的立场,不会摇摆无定,也不会人云亦云。
在这个信仰和价值轰然崩溃的时代,更需要“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鲁迅先生的话道出了批评家的另一特质:不仅要治“文艺”,还要治“思想”,要有能力通过独立的思考作出个人的分析和判断,从而“理解文学和评价文学”。鲁迅本身就是思想家,其文学批评自然不乏思想的锋芒,他的很多观点都是一针见血,至今仍不失为真知灼见,足以让我们心有戚戚焉。鲁迅何其高蹈超迈,一般人怕是难以望其项背,但是他的批评精神却是值得仿效的。一个批评家未必是哲学家、思想家,可是一定要有见识,有看法,如此,哪怕他的“理论”相对薄弱,他的批评也能做到振聋发聩、大音希声。
4
感性。说到感性,似乎与批评无关。作家、诗人讲究感性思维,批评家却是要避开感性的。批评总要客观、要严肃、要以理服人,一沾染了感性,好像就免不了主观臆断,感情用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强调“学术水准”“影响因子”的文学批评,绝不会让感性抢了风头,甚至不允许夹带个人情感。所以,我们看到的文学批评,往往是干巴巴的“产品说明书”,是冷冰冰的“质检报告”。在这样的学术论著中,找不到批评家的影子,无从感知他的心跳,也搞不清他到底什么是态度。他只是抓安全促生产的文学技师,不说自作主张的话,也不说来路不明的话,总之严守操作规范,注重科学统筹,把文章做得正经八百,确保无任何闪失。此类以复制粘贴甚至抄袭为基本工艺的学术论文产量巨大,多数都是无心、无情之作,它们唯一的作用就是增加资料库的基数,加重搜索引擎的负担。这些生于资料库也死于资料库的僵尸文件,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个论文炮制者把它唤醒。真正有生命的批评并不避讳感性色彩,反倒会因感性的成分而深入人心。
实际上,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总体都是感性的,像《人间词话》,虽然谈的是苏东坡温庭筠,呈现的则是王国维的个人性情。鲁迅的批评文章,毫不掩饰个人的好恶,在为一些年轻作家所写的文论中,更可看到他的真挚情意。宗白华、李健吾等前辈学人所作批评文章,也是不避个人情怀。其实即使是讲逻辑重理性的西方也不排斥感性,举凡影响深远的批评家,如本雅明、伍尔芙、艾略特、苏珊·桑塔格,大都具有鲜明的个性,其行文立论多是感而发之,哪怕有些主观、偏颇,也不妨碍他们成为耀眼的星宿。
我所理解的感性,首先应是一种敏锐的艺术直觉,是对文学发自于内心的本真感受。桑塔格即十分看重“感受力”,她说:“要确立批评家的任务,必须根据我们自身的感觉、我们自身的感知力的状况。”所以她提出要“恢复我们的感觉”,去除对世界的一切复制,直接地体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只有具备了未遭毒害的直感,才可能拥有犀利的艺术眼光,从而做出自己的艺术判断。基于此,便能做到“坏处说坏,好处说好”,而不必骑在墙上看风头,随大溜。再者,从感性出发,才能贴近文本,“看到作品本身”,才有可能调动我们的阅读经验和理论资源,进而上升为深刻的理性认识,形成明心见性言之成理的文学批评。所以,与从理性到理论的批评相比,由感性到理性的批评才是顺其自然;前者好比强买强卖,后者则是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5
诗性。说到诗性当然不是教唆批评家去写诗,而是希望批评家有点诗人气质。翻翻中外文学批评史,确有为数不少的诗人批评家。桑塔格就曾指出:“诗人同时是批评性随笔的能手,并不有损于诗人身份;从勃洛克到布罗茨基,大多数俄罗斯诗人都写出色的批评性散文。事实上,自浪漫主义时代以降,大多数真正的批评家都是诗人:柯尔律治、波德莱尔、瓦莱里、艾略特。”其实,这个名单还可拉长,像席勒、马修·阿诺德、博尔赫斯,既是一流的诗人,也是一流的批评家。勃兰兑斯、本雅明、苏珊·桑塔格等人,虽然并不写诗,也都洋溢着诗人的激情,他们的作品虽是理论著作,却并不枯涩沉闷:他们的文字灵动飞扬,而且,真情流露。我想,这应该就是一种内在的诗性。苏珊·桑塔格说过:“做一个诗人,即是一种存在,一种高昂的存在状态。”这高昂的存在给了她自由不羁的翅膀,也让她生出了批评家特有的反骨、重瞳。桑塔格之所以有别于以治学为要务的案牍型学者,是因为,她年轻时就决意不以学究的身份来苟且此生,她带着某种程度的天真进行批评的写作。桑塔格得益于具有“作为作家的能量”——凭藉“从小说创作中漫溢而出进入批评的那种能量”,她像是掌握了一种神奇飞行术,可以凌空高飞,可也俯冲而下,让她“发现那些蒙受他人不公看待的东西的重要性”,从而看到她所看到的那些东西,理解她所理解的那些东西。桑塔格在谈及“新感受力”时,曾多次申明大多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不在其列,在她眼里,只有少数诗人和不易归类的散体作家算得上“有创造性的艺术家”。她本人自然和本雅明、罗兰·巴特一样,属于“不易归类”的那一类。他们的共通之处便是都有一种诗性的能量,这种能量让他们对作品有一种本能的感应,并且让他们“处在顶峰之上”,与平庸、僵化拉开了距离。由此,诗性批评家总有一种怀疑的气质和激进的立场,他们的写作总也少不了透明的批评精神。
不仅如此,诗性的文体意识也是这类批评家的长项。他们偏爱片断和简洁,不囿于逻辑,不追求连贯,他们无意去写一本正经的专题论文,只是以审慎而灵活的方式表达出那种“独特的难以捉摸的感受力”。在论述罗兰·巴特的文体特点时,桑塔格曾说:“用片断或‘短文’的形式写作,产生了一种新的连载式(而非直线式)的文章布局。这些片断可以任意加以呈现。例如,可以给各片断加上序号。”在《关于“坎普”的札记》中,她又说:“札记的形式似乎比论文的形式(它要求一种线性的、连贯的论述)更恰当些。”桑塔格的批评文章大都以序号、星号或者空白彼此隔开的松散的札记片断,而不是讲究章法、学理的规范化论文。这种片断化写作当然是有意而为的形式主义,也体现出桑塔格对“体系”的警觉和冒犯。但是我们却不得不承认,这样的写法的确有其诗性特征。不光有诗的形式感,表达也多显诗意。他们不会废话连篇,不会离题万里,而是常像禅宗公案一般有甚说甚点到为止。他们简明扼要,直击要害,但不会把话说尽,而是留有诗意的空白,从而激发我们的感受力。
当然,我们无意把罗兰·巴特、苏珊·桑塔格作为批评的范本,就我个人而言,只是认为他们的诗性气质和诗性文本都有值得瞻慕之处。至少,我们可以把心灵从种种桎梏中解放出来,把文章写得洒脱一些,明白一些。
6
血性。一沾到“血”字,好像就很暴力,但是我还是要用这个词,来渲染批评的勇气。仅以挑刺为乐、专门让人难堪的“酷评”,当然没意思;那种挠痒痒、打哈哈的泡沫化批评,更是没有一点意思。也难怪人们常把评论家讥为寄生虫。萨义德曾在《作家和知识分子的公共角色》一文中谈到,评论家属于略微有些受人贬低的寄生阶层——“他们被看作令人讨厌的、喋喋不休的家伙,除了吹毛求疵和寻章摘句之外就没什么能力”。不过目前我们的文学评论却总是十分讨喜:虽然它寄生在文学的皮上,却绝不会伤及宿主的血肉,而是靠舔噬其冗赘的皮屑饱食终日。所以这种互惠互利让作家和批评家达成了一种默契,文学批评看上去尉为大观,却像得了虚胖症一般,缺铁,贫血,苍白,疲软乏力。打秋风、打酱油的评论到处招摇过市,真正挺直腰杆的批评家却不知何处容身。
陈平原先生曾感慨五四时期的众声喧哗、生气淋漓,单从学术上看那个年代也确实气象万千。就像鲁迅先生,之所以号为“战士”,是因为他有挑战,也有应战,他有与之交锋的论敌,如契诃夫说的“大狗叫,小狗也叫”,在那种多声部的语境中,鲁迅的声音也是其中之一种。但是现在,虽然权威遍地走,大话满天飞,却多是空洒口水。好些热闹、激烈的研讨、评论,不过是一堆让人腻歪的唾沫星子。鲁迅希望评论家“直说自己所愿意说的话”,可如今能够“直说”的批评几乎绝迹,人人都是好好先生,人人都会怎么说怎么是,既没有一个相对稳定的标准,也没有态度明确的价值判断。这样的批评环境如同壮观的海市蜃楼,虽也眩惑迷人,终究还是一片空无。因此,很有必要唤醒批评家的血性,给批评以勇猛无畏的灵魂。
本雅明写过一个《批评家守则十三条》,其前两条即为:“批评家在文学斗争中是战略家”,“不能选择立场就应该保持沉默”。可见这位卓然不群的批评家多么看重批评的战斗精神及其立场。他敢于孤军奋战,敢于固执己见,甚至不惜以偏激的方式充当一个破坏者、毁灭者。桑塔格称他为“最后的知识分子——现代文化的具有土星气质的英雄”,“他占据了许多‘立场’,并会以他所能拥有的正义的、超人的方式捍卫精神生活”。其实桑塔格对本雅明的评价亦属惺惺相惜,她本人也是这样一位具有英雄气概的批评家。她的自画像即是:“我把自己看作是一场非常古老的战役中一位披挂着一身簇新铠甲登场的武士:这是一场对抗平庸、对抗伦理和美学上的浅薄和冷漠的战斗。”激进、深刻、好斗的桑塔格,始终主张一种警醒的严肃态度,即便在有关严肃的观念本身显得不切时宜,她仍坚定不移,像堂吉诃德一样挑战时代的虚无,以个人的声音反抗世界的冷漠。若非如此,桑塔格也不可能成为“美国的良心”——真正的知识分子。
批评家理应成为文学的良心,批评家理应有一种敢说敢当的血性:哪怕他只是一根折断的苇草,也要削出尖利的锋芒。然而自五四以来,中国的文学批评似乎总在钝化、软化、媚俗化,鲁迅那样的硬骨头批评家几近覆灭,甚至持论相对公允的批评家也鲜有其人。批评或许已经死去,批评或许仍然有救,那么,就让我们先找回一点血性吧,让我们看准自己的立场,为批评的尊严,为批评家的良心而战。
——芭芭拉·秦访谈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