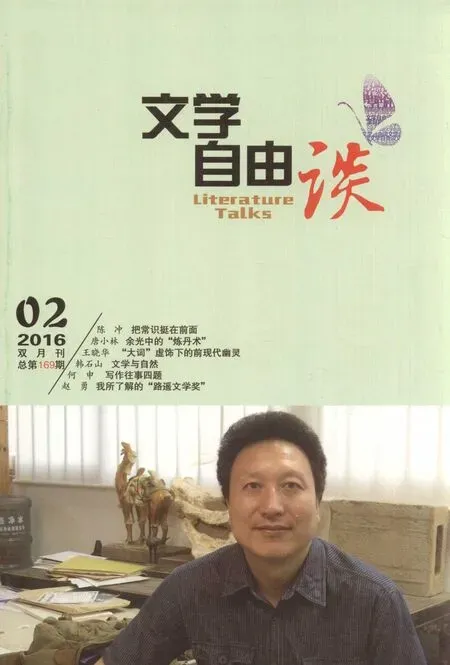诗歌的“纠结”
石华鹏
诗歌的“纠结”
石华鹏
诗歌的命运,总是令人唏嘘不已。有时,她是神,飘荡在云端,供人膜拜;有时,她是草,被人踏在脚底,忍受孤寂;有时,她是怪物,被人挖苦、取笑。当人们遭遇巨大灾难和不幸时,诗歌显得很重要,她如灰暗天空下的一枝玫瑰、一豆烛光,抚慰伤痛,拯救灵魂;当世界欢乐无比或者忙碌逐利之时,诗歌又不重要了,她沉默于角落,被人遗忘,如晴天的雨伞、夏天的棉服,落满尘埃。
我们都有过类似经历:年轻时,人人都是诗人,一点一滴的青春荷尔蒙就是一首诗歌,那些布满愁绪但模仿痕迹明显的分行文字,至今仍藏在变形的硬壳笔记本里,稚嫩的笔迹如一张青春的脸,布满青春痘;不再年轻时,诗歌与生活重量失衡,文艺气的诗歌与烟火气的生活总是不搭界,诗歌仿佛从生活中撤离了。其实,虽然许多人不再写诗,但在失魂落魄或者云淡风轻的那一刻还是会想起诗。
这是诗歌的命运。诗歌的兴与衰、冷与热、繁盛与荒凉,无不与这些人——诗人、半路诗人、诗心未泯的读者——相关。这也是诗歌为何会在这个浮华享乐的物质时代,偶尔掀起精神世界阵阵大风大浪的原因,这也是小众诗歌为何有时能挑动大众神经的原因——诸如“余秀华现象”等。诗歌是人们内心“纠结”之树上的果实:甜美与苦涩、热闹与孤寂、自由与压抑、绝望与希望、怀念与遗忘等等,都隐藏在“诗歌果实”的汁液里。调制这些汁液的诗人和饮下这些汁液的读者,等于共同品尝了意味深长的“纠结”。
没错,诗歌总处在“纠结”的风暴中。外在的“纠结”以诗歌事件呈现,而内在的“纠结”,则以一行行诗句示人。外在的“纠结”由偶然与必然的社会、文化等诸因素“发酵”而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内在的“纠结”似乎单纯而深沉许多,由诗人的诗写“制造”,因其单纯而深沉,所以我们愿意来谈谈诗歌内部的“纠结”——一种长久的无法盖棺定论的“纠结”。
懂或者不懂:诗歌海洋中永远的礁石
参加过一些诗歌研讨会或诗歌论坛后,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只要谈论起诗歌,无论绕多大个弯子,最后总有人绕到懂或者不懂的问题上。
事情变得很是有趣。假如谈论一首晓畅易懂的诗,谈着谈着就谈到不懂的诗上了:这首诗比起那些难懂、不知所云的诗强多了,那些难懂的诗不是挑战人的智商,而是侮辱人的智商。假如谈论一首难懂的诗,谈着谈着就谈到更难懂的诗上去了:这首诗有些难懂,但还是能感受到一点懂,比起那些更难懂的诗还算好多了。说到难懂,谈论者甚至“激动”“愤怒”起来:我也是大学中文系毕业,也读过许多名家的诗,我都读不懂的诗,像天书,能是好诗吗……看来,难懂的诗是惹祸者,它一定“伤害”过许多读者,要不人们怎么会总是绕到它头上来呢?
诗歌的晦涩与易懂的纠结由来已久,从新诗诞生的那一刻起就成为问题了,只不过每个时代都有新读者把它当作新的、难缠的问题对待。
懂或者不懂,是诗歌海洋中的一块礁石。在诗海中遨游的读者和诗人,都无法绕过这块礁石。当与这块礁石碰头的那一刻,读者和诗人各有自己的理由和态度,水火难容。
诗人会为晦涩寻找理由。英国文学评论家、诗人威廉·燕卜荪在1930年出版过专门谈论诗歌晦涩话题的专著《朦胧的七种类型》。他认为字义越含混就越丰富,诗的价值就越高。美国现代诗人、文学评论家艾伦·泰特在1938年出版的《论诗的张力》中认为,诗歌“可以从字面表述开始逐步发展比喻的复杂含意”,“最深远的比喻意义并无损于字面表述的外延作用”。这些外国评论家的理论为诗歌的晦涩提供了“合法”证据。
中国的资深诗人们不仅写出过不少晦涩的诗歌,也为晦涩做过不懈的辩护。诗人臧棣有篇文章叫《新诗的晦涩:合法的,或只能听天由命的》,意思是说,新诗的晦涩是理所当然的,是合法的,是爱咋咋地。臧棣说:“谈论新诗的晦涩时,人们应避免一种先入之见,把诗歌的‘晦涩’仅仅归咎于诗人所采取的表现手法。诗歌的晦涩有它的认识论方面的来源,人的认识本身就包含着晦涩的成分。”诗人王家新说:“令人费解的诗总比易读的诗强,比如说杜甫晚期的诗,比如说策兰的一些诗,它们的‘令人费解’正是它们的思想深度所在,艺术难度和精髓所在。”
读者,或者一部分谨慎的诗人并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深刻、有艺术难度就一定晦涩难懂吗?有多少美妙深刻的诗歌是多么易懂。美国小说家凯鲁亚克是晦涩的反对者,他的质疑也有说服力。在谈到那种所谓后现代诗的“拼接法”时,他说:“任何人的意识都是支离破碎的。换句话说,如果你愿意将此记录下来,也许就可以成为那些人正在创作的‘诗’。而很多时候,一旦他们的‘诗’遭到质疑,他们会将这种冷遇转换为一种艺术上‘曲高和寡’的优越感。”
很显然,懂和不懂的辩论是没有结果的,因为礁石永远在那里。诗评家唐晓渡说得中肯:“所谓晦涩主要是隐喻系统的个人化造成的,根源在于价值观、文化观、审美观的主观化、碎片化。”对读者来说,读不懂,可以选择不读,懂到什么程度,可以选择智力训练。但是对诗人来说,究竟谁有资格晦涩难懂?这是一个问题,“曲高和寡”的优越感并不能隐藏诗人内心的“虚妄”。诗人西默斯·希尼说,诗是“一念之间抓住真实与正义”,说得非常好。“一念之间”或许会带来“晦涩”,但“晦涩”是否抓住了“真实与正义”呢?如果没有抓住,那么“晦涩”就是欺骗与虚假,只有抓住了“真实与正义”的诗人才有资格晦涩难懂。比如,托马斯·艾略特的《荒原》晦涩难懂,但他是艾略特,他有资格。因为他的思想深度、他思考的前沿位置,我们已经难以企及,他必须以“先锋”姿态为他的发现和思考“命名”,所以真正的大师必须晦涩难懂。但是,我们周围有多少思想浅薄、眼光短浅的诗人也在晦涩难懂,这不是“虚妄”的故作高深吗?或许尽其所能地写出“真实与正义”才是诗歌正道,何必管他晦涩与否呢。
说到底,懂或者不懂不是诗歌的标准问题,而是诗歌的“哲学”问题:一,你不懂,别人懂;你懂,别人不懂。二,今天不懂,明天会懂;今天懂,明天不懂。三,不懂的有的是经典,懂的有的是垃圾;不懂的有的是垃圾,懂的有的是经典。
真或者伪:没有终结的辩护词
如果说懂与不懂是诗的“哲学问题”,那么真与伪则是诗的“真理问题”。
艺术的唯真正理即为真理。诗的“真理问题”实质上是诗的标准问题,就是判断和确证哪些诗是真诗,哪些诗是伪诗。诗不存在懂与不懂,但诗存在真伪。真伪之判断,是对读者鉴赏力、感受力、道德力的考验。
有人一言以蔽之,说,有无灵魂的写作,即辨别真伪的标准。
此话不假,但终究有些宽泛。作为真伪标准,越明晰,越条理,便越好。为诗的真伪而辩——这份辩护词是难以终结的,但还得辩护下去——
无关灵魂,无关生命的气息与力量,凡是“做假”一般“做”出来,“生造”一般“造”出来的诗,是伪诗。
个人诗、政治诗、说教诗都偏离了诗人的本分,是伪诗。
与个体性、主体性和真实丰富的内心体验无关的诗,是伪诗。
简化、粗糙到无原则、无向度、无底线的诗,是伪诗。
廉价的反讽和批判,献媚的赞扬和歌颂,拔高的抒情,肤浅的忧郁,是伪诗。
只展示、传递良好的一面,而把不幸和缺点严密看管起来,由此带来的表达不自由的诗,是伪诗。
政治花圃上的“假大空”,人性废墟上的“假丑恶”,是伪诗。
吃了喝了拿了别人的,而写下的应酬诗,是伪诗。
淡而无味的大白话,颠三倒四的拗口语,是伪诗。
大众包装的软语,过分甜腻的耳边私语,是伪诗。
装神弄鬼、装疯卖傻、装模作样、装腔作势的一切假先锋、假传统,是伪诗。
枯燥、自恋、与外界隔绝,拒绝参与到时代的智力建设中去发现恶的新形式、善的新品种的诗,是伪诗。
第二首梨花体、第二首乌青体、第二首羊羔体……是伪诗。
…………
那么,什么是真诗呢?我只能说不是伪诗的诗才可能是真诗。
如果一定要追问,我以为以下两位能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一位是中国的文论专家周振甫,一位是波兰诗人、诗评家亚当·扎加耶夫斯基。
周振甫说:“由诗之源以求乎上,诗人之作,思深意远,苦心焦虑,情系家国,恫瘝在抱,有不能已于言者。其言则关乎世运,系乎民生,如屈原之《离骚》,恫宗国之危亡,哀生民之憔悴;如杜甫之“三吏”“三别”,伤唐代之衰乱,悲人民之血泪,以第一等怀抱,抒爱国忧民之情。而其艺事之精能,或则惊采绝艳,难与并能;或则声情并茂,摇荡性灵,斯为最上之作。凡此最上之作,于国族危亡,世运隆替之际,常能遇之,不局于汉魏六朝与三唐也。文山之作,亭林之篇,下及人境庐之诗,于中往往遇之,皆足以震荡人心,此仆所谓取法乎上,由诗之源以求乎上也。”(《棕槐室诗》序)
亚当·扎加耶夫斯基说:“我并不完全反对一种自由的、明智的、优美的诗歌,一种力图联结起近与远、低与高、凡俗与神圣的诗歌,一种力图记录灵魂的运动、情人的争吵、城市街景,同时还能注意到历史的脚步、暴君的谎言的诗歌,一种经得起时间审判的诗歌。我只是恼怒于那种小诗歌,精神贫瘠,无智慧,一种谄媚的诗歌,卑躬屈膝地迎合这个时代的精神刺激,那种懒惰的职业官僚似的东西,在一团幻觉的污浊的云里迅速地掠过地面。”(《捍卫热情》)
简言之,真诗是“关乎世运,系乎民生”,拥“第一等怀抱”,“艺事精能”“震荡人心”的诗,是“自由的、明智的、优美的”,“记录灵魂运动”,“经得起时间审判的”精神丰饶的大诗歌。
当然,要写出真诗,有些难,要不为什么伪诗如此泛滥呢?
流传或淹没:等待时间的裁判
对诗人而言,诗歌有一个超级魅力,也叫超级诱惑,就是作品可以洞穿时空,进入人类精神宝库,供给后人长久的精神能量,写作者也因此名垂青史,被人铭记。生命须臾即逝,而文学永恒。在诗歌中,人可以得到永生。
不过这魅力和诱惑,多少有些如海市蜃楼般绚烂和虚无,一个再“牛”的诗人也无法主宰和决定自己作品是流传至千古还是湮没于瞬间。
流传与淹没是一笔糊涂账。时间是一方面:流传10年?50年?100年?还是1000年?大部分“流传”终究逃不出“湮没”的命运,但是终究有诗人和诗作永久地流传下去。运气也是一方面:有的作品运气好能流传下来,有的作品运气霉被湮没——作为诗歌流传载体的选本,其中包含了多少偶然和运气?究竟有多少好作品被毁于脆弱的竹简和单薄的纸张,毁于无知自大的决策,毁于无情的时间?谁能说得清呢。
不过现在,事情变得更有想象力了。自数字化传播以来,无限量的作品以数字的形式“沉睡”在无数的存储器中,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轻点鼠标,它便“复活”过来,呈现在你的眼前。这种“沉睡”或“复活”与时间无关,只要互联网的云数据不消失,它便可以无限期地“沉睡”,也可随时“复活”。那么,我们就不得不重新定义作品的流传与湮没了:每一部作品都可以视为“湮没”在数据库中,每一部作品同时也可视作“流传”在读者中间。在个体阅读、自我阅读、各取所需的阅读时代,即使仍会出现公众群体性阅读狂欢所催生出的“经典性”“流传性”的作品,但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流传”的泡沫幻觉。时间的遴选机制在作品的云数据库里丧失了裁判能力——今天流传的诗歌,明年后年还会流传吗?今天沉睡的诗歌,谁又能保证五年十年后不会苏醒?每一部作品都“流传”着,同时也都“湮没”着,它们都等待着鼠标轻点的那一刻,这个等待可能是10年,50年,100年,或者1000年……只要没有消失,都有“复活”并且流传的那一天。
尽管作品流传与淹没的现实,让我们陷入欣慰与伤感的交替情感之中,但面对诗写价值的迷茫、对诗写深度的孜孜以求以及对自我声名的渴望,今天的诗人们仍会陷入“流传”与“湮没”的纠结中;这种纠结,实质上是对诗歌本质的一种追问:什么才是永垂不朽的诗歌?怎样才能写出永垂不朽的诗歌?每一次对诗歌的质疑和重新定义,无一不是这种纠结的“刺激“和“成果”。而每一次真正的纠结,都是诗歌的一次进化。
前不久,在一次新世纪诗歌论坛上,中国诗人和评论家共同选出了保罗·策兰、华莱士·史蒂文斯等十位“最具影响力外国诗人”。这些诗人有的还在世,大多已离世多年。很显然,在中国诗界看来,这些倍受推崇的名字和他们的诗作,是不折不扣流传下来的经典。我无力对这份名单说三道四,但我从对这份名单的解释中,窥见了这些诗人“经典化”的某种缘由,如果将这些缘由分列出来,它们就共同构成了诗歌的“真谛”——经得起时间审判的诗歌元素,进入人类精神宝库的诗歌遗产,不断开辟新的表达可能和新的精神空间。
比如,德国的保罗·策兰——揭示出语言自身的神秘性,到达了一个不可言说的陌生领域,对20世纪的历史苦难进行深刻质问;美国的华莱士·史蒂文斯——关注想象力的转换和对现实的重建作用,重新激活、丰富了浪漫主义传统;法国的伊夫·博纳富瓦——通过语言的创造从日常经验上升到空灵无上的境界;波兰的切·米沃什——与极端的主观化和极端的形式主义两种倾向进行抗争,语言力量溢出了诗歌的自律边界;美国的伊丽莎白·毕肖普——富有清晰扎实的细节和丰富奇妙的寓意,诗作意外地简洁利落,“少即是多”;俄罗斯的约瑟夫·布罗茨基——对抗现实,制造语言内部的紧张,让语言与现实在摩擦中形成呼应;爱尔兰的谢默斯·希尼——以饱含抒情美感与道德深度的作品,赞扬日常生活的奇迹;瑞典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清晰之中抵达某种高度,保持着某种不可简约的现实的神秘性……
这段漫长的复述,证明了每一个伟大的诗人都是诗歌的独一份,不可复制。这启示了我们:如果梦想着流传下去,就要创造自己的、接近诗歌本质的那“独一份”,而不断地去思考去对抗诗歌的“纠结”——与传统对接的“纠结”、技术求新与守旧的“纠结”、个人经验与现实关系的“纠结”、语言的质朴有效与突破表达边界的“纠结”,或许美妙的诗歌创造之门才会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