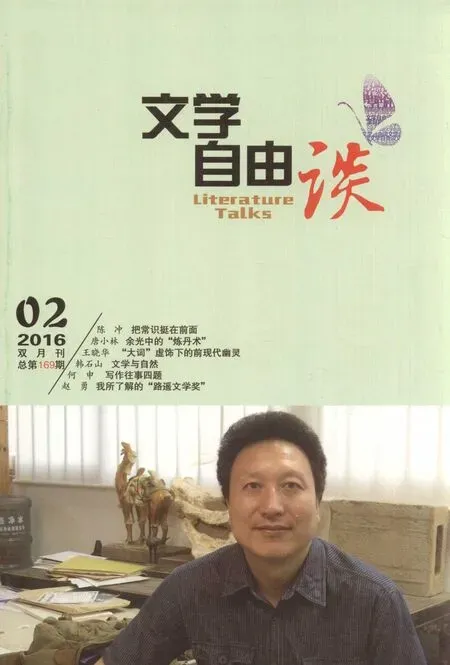并非奢望的期待
刘金祥
并非奢望的期待
刘金祥
文学批评始于阅读作品。一个从事文学批评的人,首先是一个痴迷执着的阅读者,一个挑剔刻薄的欣赏者。当然,如果借助披沙沥金、剥茧抽丝式的阅读,从中发现文质俱佳、衔华佩实的优秀作品,一定是件激越难耐、感奋惬意的快事幸事。
在笔者近年时断时续、杂乱无章的阅读经历中,一些中国现当代作家的名字连同他们的作品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印痕,比如钱钟书的《围城》、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老舍的《骆驼祥子》;比如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受戒》、萧红的《呼兰河传》、阿城的《棋王》、韩少功的《爸爸爸》、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商州》;比如张承志的《心灵史》、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莫言的《红高粱》、余华的《活着》、格非的《迷舟》、苏童的《1934年的逃亡》,等等。阅读这些名篇佳作,不仅可以充实着精神世界、丰富着鉴赏经验,而且还能矫正着评论视角、磨砺着批评锋芒。
感悟之余,我又略有所思。不可否认,构成小说艺术感染力的主要因子固然是故事情节,而支撑故事情节的基本元素无疑是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作家笔下的人物不仅坚实地支撑起故事情节和框架布局,也为小说作品葆有艺术生命力提供了有力依据。一段时间以来,我有限地重温了部分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作品,在回味作家精神体验的同时,也被小说中隐含的“感染力”所征服,而凡是具有感染力的小说,必然蕴含着某些“经典”属性。对这些“经典”小说作品的每一次重读,都会产生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感觉;而越是重读,我们就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别致。
在中国现当代小说的长廊中,有两部中篇小说于我具有难以磨灭的“丰碑”印记,它们分别是沈从文的《边城》和萧红的《生死场》。《边城》为我们讲述了沈从文那“天堂般的故乡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活着一个“古朴、正直、本分、尽职”的祖父,活着一个“明慧温柔,明朗豁达,口角伶俐,娇中带点野”的少女翠翠……沈从文用他“一首将近七万字的长诗”告诉人们:“边城”绝不是偏远、边缘,那里面所蕴含的生存之美、人性之真,是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相反,它会像一块带有灵性的古玉,愈久弥香。《边城》的行文如潺潺流水,虽然没有扣人心弦的悬念,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氛围,更没有曲折跌宕的情节,但沈从文能够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以简练而又细腻,散淡而又自然的笔法刻画出人物的心理,使你情不自禁地融进人物的心灵世界。《边城》隽永的文字弥漫着边地山村的浓郁乡野气息,展示出湘西世界和谐本真的生命形态。正如沈从文先生谈及《边城》时所说,它“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
同《边城》一样,《生死场》的问世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不同的是,《边城》的背景是南中国的湘西凤凰古城,《生死场》的原发地则是北中国的呼兰河畔,一南一北,构筑了中国现代社会的两道风格迥异的自然生态和民俗风景:一个是“边城”的静穆与柔美,一个是塞北的凄冷与荒寒。与《边城》刻画中心人物“翠翠”不同的是,《生死场》着力塑造的是一组群像。由于作家“力透纸背”的警醒,加之“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使《生死场》透出了一片北国苍茫的辽阔与凝重。在“生死场”上苦熬着的王婆、金枝、月英、赵三、二里半、平儿们,不仅给人们以“坚强和挣扎的力气”,还“显示着中国的一份和全部,现在和未来,死路和活路”。(鲁迅语)在那样的年代,北中国落雪也流血流泪,但《生死场》昭示着:“我们有必要勇于面对所有的痛苦,并把软弱的时刻和暗弹的泪水减到最低量。然而,我们并不必以流泪为耻;毕竟眼泪证明了我们有承担痛苦的最大勇气。”(弗兰克《活出意义来》)《生死场》是不死的,如同诞生了这部力作的北方厚土。
《边城》和《生死场》塑造的人物闪烁着简约、率真的人性,蕴籍着真诚、质朴的情感,成为承载“民族寓言”的经典文本。当今时代,我们渴望得到真爱,却又总是疑虑重重,总想一切确定无误之后才付出感情,不然就马上抽身离去。不仅对爱情如此,对待别的事情也存有如此可笑的想法,只有即时的眼前的利益才能让现代人付出,任何遥远的美丽都被视为可笑的不现实的,不值得人们守望和等候。如果翠翠生活在现在,那她一定被看作是一个奇怪的异数。也许不是身边已经不存在美丽,只是我们有意无意地在扼杀美。也许当我们还年轻,当我们还不知道生活压力的时候,还会为翠翠而感动,还会为心中的那份美丽而痴迷和坚守。可是当生活给我们的压力越来越大,把我们变得越来越现实的时候,这种对美丽的痴迷和坚守就变得异常脆弱,甚至不堪一击。
重温《边城》和《生死场》,我在惊异于中国现代小说起点之高的同时,不由得想到当今文坛的“喧哗与躁动”。一批批匆忙而短命的、缺少感染力和震撼力的小说,浮云般在我的眼前散去。但在感叹之余,我依然心存幻想与期待,幻想着当代《边城》的不期而至,期待着现实版《生死场》的早日来临。但近年来的小说创作现实一再提醒和告诫我,这种期待和幻想可能将无限期地推迟。当代作家由于先天不足后天乏力,当市场经济大潮席卷而来之时,当经济全球化狂飙突进之际,很少有人以自身的创作,对陷于物欲困境中丧失自我的存在价值进行深挚的忧虑,和对人本身进行苦涩而绝望的寻找。这说明中国作家对人类在当代的处境非常隔阂,对真实的血肉人生非常漠视,还不充分具备现代人的精神特征和价值取向。读他们的作品,总感到缺少一种哲学的意蕴和风采,缺少一种形而上学的打量和审视,缺少一种近乎宗教的执著、一种对人本身的终极关怀。读者从中难以发现那种令人头晕目眩的“临界”思考,即对独一无二的生命存在和即将永逝的短促人生穷根究底式的追问——这种追问,本来很容易让人在阅读中产生因发现自我而悚然体验到的、对沉沦的紧张或焦虑;这是微不足道的、思维着的孤独个人,面对包围着人并对他所提出的一切问题永保沉默的宇宙时所引起的形而上学的紧张或焦虑。而缺乏这种追问,就很难为灵魂开启一扇通向更高境界的窗口,很难激发读者对人生意义做更自觉、更深入地思索,很难唤起他们重新选择生活的勇气,并对享有一种真正意义的人生所怀有的渴望。
记得旅美作家哈金曾给“伟大的中国小说”作过这样的定义:“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有鉴于此,作为一名喜欢批评的人,衷心希望当代中国作家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作为一名寻找中的阅读者和批评者,我愿为中国作家的“有说服力的作品”写出自己的“读后感”,用真诚的文字表达自己的“认同感”。
我们期待的是文学圣徒的良知与清洁,呼唤的是文学大师穿古越今的巅峰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