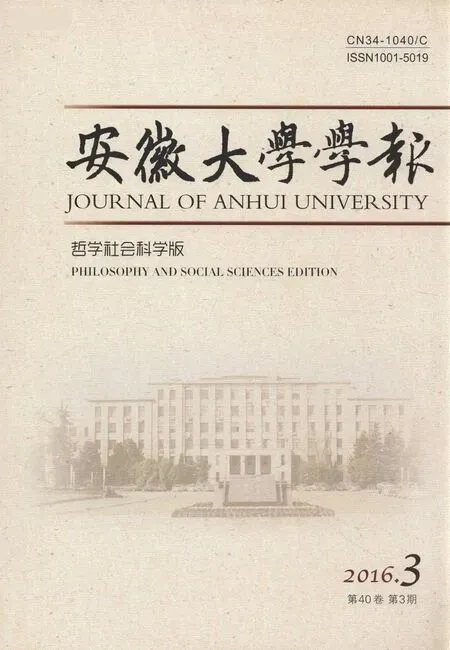谱牒纷争所见明清徽州小姓与望族的冲突
郑小春
谱牒纷争所见明清徽州小姓与望族的冲突
郑小春
摘要:记录血统源流的谱牒其实是一纸“出身符”,而谋买谱牒则是徽州小姓企图获得望族血统以改变身份地位的一种手段,暴露了小姓与望族之间天壤之别的生存状态和激烈的矛盾冲突。造成小姓与望族持续冲突的根源,是封建宗法制度所实行的身份等级制度。清政府对主仆名分法律进行了多次调整,但在多重因素影响下其实际成效有限。只要导致身份等级制度产生和顽固残存的特定历史条件一息尚存,小姓与望族之间的冲突就势必持续下去。
关键词:徽州;谱牒;小姓;望族;宗族;徽学
明清时期的徽州,小姓与望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来自小姓的反抗斗争,自明嘉靖、隆庆以后日趋激烈。他们或则挖坟盗葬,侵占吉壤;或则抗交田粮,拒绝服役;或则私下斫木,变卖谋生;或则携妻并子,弃主出逃;或则揭竿而起,英勇起事。与以上冲突形式不同,谋买谱牒,冒认名宗,则是小姓惯用的另一种非常特殊的斗争方式,其将焦点最终指向了当时实行的身份等级制度,给封建宗法秩序以巨大冲击。比较而言,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此类斗争方式更能彰显封建宗法制度的特点,对于宗族研究具有相当独特的价值*目前学界主要关注的是徽州小姓与望族之间的政治冲突、经济冲突以及雍正五年开豁世仆之后的主仆诉讼,如傅衣凌《明代徽州庄仆文约辑存——明代徽州庄仆制度之侧面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60 年第2 期)、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年)、卞利《清世宗开豁世仆令在安徽的实施》(载欧阳发等主编《经济史踪》,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 年)、[日]中岛乐章《明代乡村の纷争と秩序——徽州文书をして》(汲古书院,2002年)、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村落社会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陈瑞《清代徽州境内大、小族对保甲组织主导权的争夺——以乾隆年间休宁县西乡十二都三图渠口分保案为例》(《徽学》第7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11年),而围绕谱牒纷争进行专论者尚付阙如。。
一、“鬻谱案”与婺源清华胡氏宗族的应对措施
小姓通过谋谱冒认名宗,一直是明清徽州较为常见的一个现象,也是徽州宗族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民国婺源《清华胡氏宗谱》记载了该族谱牒在明清时期频繁被小姓谋买的信息,为考察徽州小姓与宗族问题提供了宝贵素材。
婺源清华胡氏自唐光启年间徙居以来,历朝有人为官出仕,实为“冠盖蝉联”“朱紫相仍”之簪缨世家*(明)戴廷明、程尚宽等:《新安名族志》前卷《胡》,合肥:黄山书社,2004年,第300~301页。。“尊祖”必叙谱牒,谱牒的编纂和延续是宗族的头等大事,胡氏对之极为重视。据载,南宋以降直至民国初年,胡氏宗谱共有十次纂修*民国《清华胡氏宗谱》卷之首《谱序·修谱世次》,1916年刻本。,可谓源远流长。然而,“有连城即有碔砆,有蚌胎即有鱼目”*民国《清华胡氏宗谱》卷之首《谱序·重修族谱序》。。为保证宗谱正传,杜绝不肖私鬻货利,非族妄买乱宗,胡氏宗族在明景泰朝之前就曾两次制定祖训,训诫后人谨守而勿怠*民国《清华胡氏宗谱》卷之首《祖训诫谕》《再诫谕》。。
就是在如此看重谱牒渊源的胡氏宗族,明景泰年间还是发生了一起“非族”谋买谱牒的纷争(下称“鬻谱案”)。《清华胡氏宗谱·事迹类考》载有《具诉情状》《鬻谱非族记》《革弊重修赞》《赠族长正义序》《辩正知单》等五件记事文书,内容都是围绕胡氏族人胡庶背族鬻谱这一事件而展开。现略述如次:
“鬻谱案”发生于景泰元年(1450)五月,不肖之子胡庶贪财忘本,为了“嫁女”收受“白银贰两五钱”,将其父胡尚文原来掌管的本宗谱牒,私卖给“祖宗从来出处卑微”、依靠经商“暴富”的同姓不宗之小姓胡否兄弟抄写。胡否兄弟“冒认所迁祁门支派,插写其名于下”,妄图扳援认宗。胡氏宗族知晓后很快做出反应,认为“谱系自祖流传,尊卑已定”,况且先祖有遗训诫谕,非族不书,于是“陈正纪纲”,与之言辩。没想到胡否兄弟反又买通胡庶,捏词妄诉至官。为了避免名分不辨,族长胡汝器在宗族的强力支持下,“与词诉官,以正其弊”。最后,该案在“拘缠期月”之后,以胡氏宗族“追出谱牒”胜诉而告终。
以上记事并非诉讼案卷,因而详细的互控过程难以详知。就诉讼本身而言,“鬻谱案”并不复杂,一个月即告结案。但从胡氏宗族在诉讼过程中采取的一系列应对措施中可看出,这起纷争对这个望族来说一点也不轻松。
首先,来看诉讼过程中的宗族联合。
记事文书《具诉情状》记录了这方面的信息。《具诉情状》实为胡氏宗族在诉讼开始时向各地支裔发出的共同赴讼的一纸联宗告示,目的是为了“追出原谱还众”,防止“非族添插以乱宗族”。囿于资料,胡氏宗族各地支裔具体如何联合诉讼、规模有多大等都已无法考证。但从其透露的信息看,这起谱牒纷争给胡氏原本平静的宗族秩序造成了很大冲击,该族为此特地采取彼此联络、举族告控的方式。如此做法,不但可以为争取胜诉提供组织和经费保障,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利用纷争之契机加强宗族内部的联合。
其次,来看诉讼结束后胡氏宗族采取的三项应对措施。
一是每岁各房聚会,增强宗族的凝聚力。从胡庶背祖卖谱仅仅是为了“得银嫁女”的事实来看,胡氏宗族内部贫富差别与矛盾分化已经相当严重。“鬻谱案”的发生,应当是这种族内矛盾的一次暴露。为改变这种局面,族长胡汝器等人于景泰元年十二月,即“鬻谱案”解决之后不久,“邀率本宗亲支子孙,每岁于正旦各房聚会”*民国《清华胡氏宗谱》卷之首《谱序·胡氏本宗会序》。。希望通过各房聚会的形式,“互相训诫守望,相互患难相恤”,共同应对外来的侵扰。显然,这是“鬻谱案”中联宗行为的进一步延续和强化。
二是重修世系,维护宗族的血缘秩序。据记事文书《革弊重修赞》记载,在“鬻谱案”胜诉后的第二年,胡氏宗族又郑重其事,专门召开宗长会议,决定对本宗世系革弊重修。这次世系重修由族长胡汝器等人担纲*民国《清华胡氏宗谱》卷之首《谱序·重编世系录》。,首次采用了“十干字序次编号”防伪措施,并“书定所掌有合同者”,以杜绝鬻谱之类事件再次发生。重修世系主要为了“力扶纲常”、“以正名分”,让本族的宗派血统得以正本清源。重要的是,它还把族人原本日益涣弛的宗族认同心理重新凝聚起来,使族人的祖先崇拜意识和血统意识得到了加固。
三是给胡汝器作赞文,强化族人的宗族意识。在“鬻谱案”中,族长胡汝器成了维护宗族血脉正统、捍卫宗族声望的英雄。四年之后,亦即景泰五年(1454)冬月,宗族特意为尚健在的胡汝器*民国《清华胡氏宗谱》卷1《十六世至二十世·清华日新公房》记载,胡梿“字汝器,号正齐。洪武辛酉生……享年九十有三,恩赐寿官,以天年终”。由此推算,景泰五年作《赠族长正义序》时,胡汝器尚健在。撰写了一篇赞文《赠族长正义序》。应注意的是,徽州人一般不为生者立传记事,祁门善和程氏即有“其(族人)在生,即有功德善行,均不应书”*光绪《祁门县善和程氏仁山门支修宗谱·凡例》,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木活字本。的规定。胡氏宗族的破例之举,显示其用意深远:表面上是对胡汝器个人的褒扬,实际上是用之诫谕后人以强化宗族意识,即全体族人都应以“念祖敬祖为重”、“正名定分为务”,行者即会万古流芳,否则就会受到责惩。受到大肆褒扬的胡汝器,同因盗卖族谱而被“痛惩”并以“败类”弃祖之名削谱不书的胡庶形成了鲜明对比,就是很好的说明。
二、小姓与望族的生存状态及矛盾冲突
胡氏宗族发生的这起谱牒纷争,“鬻谱案”是焦点,其他一系列应对措施都是围绕“鬻谱案”暴露出的诸多问题,以重振族人的宗族认同、维护宗族的血脉正统和等级秩序为目的而展开。这起谱牒纷争看似简单,却暴露了徽州小姓与望族迥然有别的生存状态,以及彼此之间激烈的矛盾冲突。
明清时期,徽州人的望族心理极其浓厚。徽州望族大都为中原世家宦族迁徙而来,明清时期发展到鼎盛。清初歙人赵吉士曾对之作过精彩描述:“父老尝谓,新安有数种风俗胜于他邑:千年之冢,不动一抔;千丁之族,未常(尝)散处;千载之谱系,丝毫不紊。”*(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泛叶寄·故老杂纪》,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刊本。字里行间洋溢着对徽州望族的赞扬之意。其实,徽州人的望族心理很早就形成了。自元迄明,徽州人就编纂了诸多“名族志”“大族志”以示炫耀。这种望族心理,在徽州宗族谱牒虚构世系和攀附贵胄等现象中显得尤为突出*卞利:《明清时期徽州族谱的纂修及刊刻等相关问题研究》,《徽学》第5卷,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0页。。此外,只要有显赫的人物和历史,宗族谱牒皆不惜笔墨一一记述。义成朱氏就认为:“录诰敕者,所以记先人受朝廷之盛典也。名贤传状、序赞、赠诗、墓志、祭文,亦皆金石之道,足以表扬先烈。故并载之,以冀子孙景仰而兴奋起之心。”*宣统《(古歙)义成朱氏宗谱·凡例》,清宣统刊本。济阳江氏甚至还规定:“妇之祖父、女之翁夫与子有德望名爵者,书之。非涉洿滔本,昔人重门第之意。出嫁女以节孝著者,亦附载之,所以增母党之光。”*乾隆《济阳江氏族谱》卷1《凡例》,清乾隆四十二年(1777)刻本。就是在这种有意识的传承和宣扬下,在徽州宗族中形成了对祖先的极度崇拜以及因先祖而血统尊贵、等级优越的望族心理。这种望族心理在族谱的承载和维系下世代承袭、根深蒂固,容不得丝毫毁损和玷污。
明清徽州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社会群体——小姓。“小姓”是佃仆的一个别称,又叫“小户”*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241页。,所谓“徽州有小姓。小姓者,别于大姓之称。大姓为齐民,小姓为世族所蓄家僮之裔,已脱奴籍而自立门户者也”*(清)徐珂:《清稗类钞》第四册《种族类·小姓》,1917年刊本。。关于小姓,新编《婺源县志》指出:“本县村落多聚族而居,有些较大的村庄有‘大姓’、‘小姓’之分。称为‘大姓’的,祖先多系当官的贵族,其家奴后裔即成了‘小姓’。在封建制度下,‘大姓’统治‘小姓’,规定‘小姓’男人不得读书求仕,女子不得缠足,不能与‘大姓’人家通婚,只能嫁给外村‘小姓’人;凡‘大姓’人家婚姻喜庆和殡葬,均由‘小姓’人抬轿、抬棺、鼓吹等,谓之‘下等事’。”*婺源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婺源县志》第七十一章第二节《习俗》,北京:档案出版社,1993年,第535页。以上有关小姓的说法,在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的《陶甓公牍》中也有记载*(清)刘汝骥:《陶甓公牍》卷12《法制·休宁风俗之习惯·婚娶》、卷12《法制·黟县风俗之习惯·乐歌》,清宣统三年(1911)排印本。。可见,徽州小姓的社会地位十分低下。而且,小姓即便有了雄厚的经济实力,其社会地位也不会得到改变,所谓“臧获辈即盛赀厚富,终不得齿于宗族乡里”*道光《徽州府志》卷2《舆地志·风俗》,清道光十年(1830)刻本。。在尤重名分等级、讲求门第的宗法社会里,没有高贵的出身血统,就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一些政治权利也因此受到制约,甚至被剥夺。比如科举入仕,由于受到等级身份的限制,明清两代的小姓就曾长时间被取消了科考的权利,直至清乾隆朝才有所改变*(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9《户律之一·户役·人户以籍为定》“条例”,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刻本。。而在封闭的徽州,此等风气则一直延续到清朝末年科举废置*“隶仆籍者不与通婚姻,不得应考试,至光宣间,科举制停,城乡设学,此风乃革。”民国《歙县志》卷1《舆地志·风土》,1937年铅印本。。又如婚姻,徽州尤重门第差别:“婚姻论门第,辨别上中下等甚严。所役属佃仆不得犯,犯辄正之公庭。”*万历《祁门县志》卷4《人事志·风俗》,明万历十八年(1590)刻本。“徽俗重门族。凡仆隶之裔,虽贵显,故家皆不与缔婚。”*(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泛叶寄·故老杂纪》。赵吉士还将此风与其他地方做了对比:“他里则否。一遇科第之人,即紊其班辈,昧其祖先,忘其仇恨,行贿媒妁,求援亲党,倘可联姻,不恤讥笑。”并认为这种风气是“最恶风也”。“嫁女门户须相当,若贪赀财许嫁小姓,及与人为妾者,族众攻之。”*民国《济阳江氏统宗谱》卷1《江氏蒙规》,1919年刻本。有的宗族甚至规定:“婚姻不计良贱者,悉削(谱)不书。”*隆庆《休宁率口程氏续编本宗谱·凡例》,明隆庆四年(1570)刻本。咸丰六年(1856),祁门历溪王氏宗族王际膘等由于不遵祖规,与“不重之门”张、汤二姓通婚,以致宗族将之“诣祠削除,不载入谱”*张海鹏、王廷元主编:《明清徽商资料选编》,合肥:黄山书社,1985年,第32页。。由此可见,由于出身卑微,小姓的社会生存状况非常艰难。正因如此,借助于谋买望族谱牒以攀高认宗,就成为那些小姓试图改变卑微出身和恶劣生存状态的最佳捷径了。
然而,记录世系源流的谱牒是宗族得以维系的重要手段,小姓谋谱这种做法势必引发激烈的矛盾冲突。对于徽州望族来说,“谱也者,礼之善物也”*万历《(休宁)程典·程典序》,明万历刻本。,族谱是维护封建礼教的载体;族谱“溯远以统同也,详迁以辨异也”*万历《休宁范氏族谱·新安范氏会通谱序》,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刻本。,又是辨异统同、收族统宗、维护宗法制度的工具;“族之有谱,上以征祖宗之渊源,下以绵子孙之血脉”*道光《新安歙西沙溪汪氏族谱·谱成告祖文》,清道光五年(1825)刻本。,族谱又是祖先信仰的承载和血脉秩序的维系。由此,徽州望族对于族谱极为看重,决不容许私鬻“非我族类”现象的发生。如休宁范氏即规定:“或有不肖辈鬻谱卖宗,或誊写原本,瞒众觅利,致使以赝混真、紊乱支派者,不惟得罪族人,抑上得罪祖宗,众共黜之,不许入祠,仍会众呈官,追谱治罪。”*万历《休宁范氏族谱·谱祠·统宗祠规》。歙县方氏也规定:“家之有谱,如国之有史,所系匪轻。虑有不肖子孙,或奉守弗谨而失之,或贪牟货利而鬻之。如此者,众声其罪,追出原谱,仍逐出祠。”*乾隆《歙淳方氏柳山真应庙会宗统谱》卷1《凡例》,清乾隆十八年(1753)刻本。绩溪涧洲许氏则规定:“本祠宗谱……切不可妄贪重利,售与伪派,致乱吾宗。如违,以不孝论。”*民国《绩溪涧洲许氏宗谱》卷10《领谱字号引》,1914年木活字本。一致对鬻谱卖宗行径规定了严厉的处罚措施。
基于以上分析,也就不难理解“鬻谱案”对于一个有着辉煌家世的胡氏宗族来说是何等的冲击了。仅就“鬻谱案”而言,显然是对本族尊贵血统和身份等级的恶意玷污和挑衅,诚如胡氏后裔胡良乾所言:“非我族类者,窜名以紊真,狗尾而继貂,羊质而虎皮,黑白虽自较,然朱紫未免相夺,其为我名宗之累非小也。”*民国《清华胡氏宗谱》卷之首《谱序·重修宗谱序》。而对胡否兄弟来说,谋买谱牒则是借胡氏之血统以改变自己出身的一种手段,获得望族身份,进而平等地享受各种权利和地位才是他们的根本目的。看似简单的谱牒纷争,实则暴露了小姓与望族之间围绕着身份等级秩序而展开的激烈冲突,触动了封建宗法制度的神经。换言之,封建宗法制度实行的身份等级制度,规定和维系了小姓与望族之间的不平等,导致二者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天差地别,这才是他们持续发生冲突的根本原因。对此,明末歙县知县傅岩一针见血地指出:“今人片语不合,一刻颜变,小则斗殴,大则告状不休。歙俗之尚气如此,只是强户弱民、大姓单丁之见牢不可破耳。”*(明)傅岩:《歙纪》卷5《纪政绩·修备赘言》,明崇祯刻本。
三、小姓与望族之间矛盾冲突的持续和境况
类似的谱牒纷争绝不仅限于胡氏宗族。明嘉靖朝,新安琅琊王氏就指出:“乙亥给谱,徒有字号而无纪录,以致诈伪纷纷而出。”*嘉靖《新安琅琊王氏统宗世谱》首卷《凡例》,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刻本。清乾隆年间,休宁古林黄氏也感叹道:“每见世家之谱滥授匪人,据为讼柄,甚有私增私删欺人耳目者,为弊滋多。”*乾隆《休宁古林黄氏重修族谱》卷首上《凡例》,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刻本。此类记载甚多,足见小姓扳援认宗现象之普遍。实际上,小姓与望族之间围绕身份等级秩序而展开的冲突,可谓跌宕起伏,贯穿了整个明清时代。
就清华胡氏宗族来说,小姓谋买谱牒的事件远没有结束。到了嘉靖中期,“不期胡否兄弟子孙、奸诈之徒胡应龙、应时,无耻生员胡襄表,诈冒胡濋名字,刊启遍谒各宗,求讨支派,私地刊板(族谱),族众骇惊”。可见,在景泰元年发生的“鬻谱案”中,胡否兄弟虽以失败告终,但几近百年之中,谋谱认宗之念头在其后世子孙中从来就没有泯灭过,足见其执意改变卑微出身之决心和无奈。据载,清华胡氏宗族发生的谱牒纷争一直持续到了清代,自明嘉靖至清康熙朝,又是一百多年,“考诸祖训,三代一修之期则过矣,借鬻非族之弊又兴矣”*民国《清华胡氏宗谱》卷之首《谱序·永思祠修族谱序》。。
面对胡否兄弟及其后世子孙的持续滋扰,胡氏宗族也不断地采取相应措施加以应对。当胡否后世子孙再次企图谋谱时,胡氏宗族重演故伎,采取“辩正知单”*民国《清华胡氏宗谱》卷之首《事迹类考·辩正知单》。这种形式,遍告各地支裔,以联合起来共同防范。“知单”一语点破其伪:“清华本宗正传谱系,古今并系写本,自无刊刻。”说明胡否后人这次“私地刊板”应当仍归失败,胡氏宗族在“鬻谱案”之后采取的严密防范措施显然取得了成效。此外,当小姓谋谱四处风行时,为了维护本宗正脉,与景泰朝一样,胡氏宗族又分别于嘉靖朝和康熙朝,运用缮书誊写的方法两次重修世系,以期杜绝小姓滥侵念头。
康熙年间纂修的《新安程氏世忠原录琼公支谱》,也记录了一起盗卖谱牒纷争。康熙二十四年(1685),劣衿程士培陡起贪心,把“仆子奴孙”录入谱中,刊板印卖。程氏宗族深恐“千年清白悉遭污辱”,于是在康熙二十五年二月,联名把程士培告至官府,并终以“焚书毁板、拟罪立案”胜诉*康熙《新安程氏世忠原录琼公支谱》卷10《禁伪谱碑文》,清康熙刻本。。本案中,程氏宗族似乎并没有与小姓直接发生冲突。但要注意的是,案中买谱的恰恰就是那些小姓——“仆子奴孙”。因而,虽然这次事件直接惩罚的是卖谱人程士培,实质上挫败的则是那些执意买谱冒宗的小姓。其背后同样隐含着小姓与望族之间的冲突,与清华胡氏谱牒纷争没有本质区别。与胡氏宗族一样,程氏宗族事后也采取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在谱牒纷争胜诉后的第二年,为杜绝“劣棍私造伪谱”之类的事件再次发生,程氏宗族共35位族绅联名向徽州府申请给示严禁、阻盗勒石,以求垂之久远。康熙二十七年七月,最终如愿以偿*按:朱平、陈琪《清代徽州宗族维护血缘秩序的主观努力——以新发现的三通碑刻为例》(《安徽史学》2012年第3期)一文,引用了一件康熙二十六年正月“徽州府正堂禁碑”(现存屯溪区博物馆),该碑文与本文引用的康熙二十七年“禁伪谱碑文”记载的实属同一案件,但二者文字差别很大。通过解读两件碑文,并结合康熙《安庆府志》卷10《府职官》、道光《徽州府志》卷7《职官志·郡职官》的记载,可以判断康熙二十六年“徽州府正堂禁碑”是由“安庆府督粮厅”通判谢玺在署理徽州知府时批准的,康熙二十七年“禁伪谱碑文”则是由正式出任徽州知府的朱廷梅批准的。由此来看,谢玺与朱廷梅的身份毕竟有所不同,于是在新安程氏一再呈请之下,才出现了对本案连续两年给示严禁的情况。。
在遭到小姓持续冲击之时,以上两个宗族皆采取了有力措施以恢复和稳固宗族统治秩序。值得注意的是,与胡氏宗族相比,程氏宗族所采取的防范措施发生了很大变化。胡氏宗族主要采用联宗和重修世系等方式加以防护,而程氏宗族则是在官府给示之下“立石永禁”,亦即主动邀请官方力量参与,具有官方保障的法律效力,从而使其威慑力和约束力大大增强。显然,这是地方官府与宗族在维护宗法秩序中彼此联手的一个重要表现。正是在宗族处心积虑的防范以及与官府的联手合作下,小姓企图谋谱改变出身之努力一再陷入困境。
康熙年间,祁门县令姚启元对本县受理案件进行统计后指出:“审其案牍,视其情词,非先祖之坟墓,则名分之等级。”*康熙《祁门县志·序》,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刻本。可见,在徽州,小姓与望族围绕着身份等级秩序而展开的冲突非常频繁。这其中除了谋买谱牒之外,小姓在现实中所运用的手段也多种多样。根据记载,至少还有以下几种情况:
冒认望族之先祖。嘉靖二十年(1541),休宁范氏宗族先祖范品被同姓不宗之小户石匠范姓冒认,该族由此与之“讼于公庭三年之久,所费千金有奇”,使得小户石匠范姓攀高认宗的图谋落空*万历《休宁范氏族谱·谱茔》附录。。
妄祀望族之祖冢。祁门县黄昆等与黄忠元二户公有宦冢一处,历祀无异。顺治初年,同姓不宗之伪黄黄珍等,竟然谋继黄忠元幼子,并私贿黄忠元“连宗合祀”。黄昆得知后告到官府,最后判定只许黄昆与黄忠元二户祭祀、照旧标挂。为防止黄珍等日后盗占霸祭,冒行标扫,黄昆等又于顺治十六年(1659)向祁门县乞求抄招给帖以作凭证,得到准许*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收藏整理,王钰欣、周绍泉主编:《徽州千年契约文书·清民国编》第1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50页。。
盗用望族宗祠之名号。乾隆五十一年(1786),本非左田黄氏支裔之黟县溪头黄姓,擅用左田黄氏宗祠“一本堂”之名,升竖匾额,希图认宗。左田黄氏得知后告至官府,最后将匾额撤毁。为避免日后生端无常,左田黄氏特向官府乞求给示严禁,以儆效尤,也得到了准许*《清乾隆五十一年祁门社景黟县正堂严禁伪派盗紊左田黄氏宗支告示》,原碑现嵌于祁门县横联乡社景村一本堂墙上。。
以上“小户”“非族”“伪姓”的身份看似复杂,但从他们竭力攀宗认祖的事实来看,其出身并不为徽州宗族社会所认可,应当属于小姓范畴。他们所采用的种种手段,尽管形式上有别于谋买谱牒,但最终都把矛头一致指向了封建宗法制度下的身份等级制度,目的完全相同,可谓殊途同归。然而,在望族与官府彼此联手之下,以上方式同样大都以失败而告终,小姓的努力始终在困境中持续着。
四、主仆名分法律的调整与封建宗法势力的顽固
明清时期,徽州望族与小姓之间的身份等级主要是由主仆名分维系的*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268页。。主仆名分不仅是终身关系,而且延及子孙,世代相承,所谓“主仆之严,数十世不改”*(清)赵吉士:《寄园寄所寄》卷11《泛叶寄·故老杂纪》。。建立和维持主仆名分的重要力量是实际存在的土地关系,因为沦为小姓的种种原因最终都与“佃主田、葬主山、住主屋”有关*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第240~247页。。主仆名分又以小姓签订的一纸“立还文约”为依据,文约一旦订立,主仆名分立刻形成且得到法律维护,主仆之间天壤之别的身份等级即被固定下来。
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实行宗法制度,历来国家法律都对宗法制度所规定的身份等级秩序竭力维护。为此,主仆名分自宋代被法典化之后,得到了后世统治者的维护,国家法律一直都没有什么大的调整。然而,这种状况于清初开始发生变化。重大调整始自雍正朝,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将徽州小姓有条件“开豁为良”的诏令。
雍正五年(1727)四月,朝廷正式发布开豁谕旨:
朕以移风易俗为心,凡习俗相沿不能振拔者,咸与以自新之路。如山西之乐户、浙江之惰民,皆除其贱籍,使为良民,所以励廉耻而广风化也。近闻江南徽州府则有伴儅,宁国府则有世仆,本地呼为“细民”,几与乐户、惰民相同。又其甚者,如二姓丁户村庄相等,而此姓乃系彼姓伴儅、世仆,凡彼姓有婚丧之事,此姓即往服役,稍有不合,加以棰楚。及讯其仆役起自何时,则皆茫然无考。非实有上下之分,不过相沿恶习耳。此朕得诸传闻者,若果有之,应予开豁为良,俾得奋兴向上,免至污贱终身,累及后裔。着该抚查明,定议具奏。*《清实录》第7册《世宗实录》卷56,雍正五年丁未夏四月癸丑,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63~864页。
旨下礼部,再层层下达到徽州府。徽州府遵旨查讯,又将结果逐级上报,后经安庆巡抚魏廷珍覆奏,雍正六年(1728)二月遵旨议准:
嗣后绅衿之家,典买奴仆,有文契可考,未经赎身者,本身及其子孙,俱听从伊主役使。即使赎身,本身及在主家所生子孙,仍应存主仆名分。其不在主家所生者,仍照旗人开户之例,豁免为良。至年代久远,文契无存,不受主家豢养者,概不得以世仆名之。永行严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58《户部·户口》,清光绪刊本。
乾隆三十四年(1769)六月,安徽按察使暻善就小姓问题再次奏请朝廷,并得到批准:
臣以为,主仆之名分全以卖身契为断。其有年代虽远,而其祖父卖身文契现存,其子孙仍在主家服役,或虽不在主家服役,而伊主给田佃种,确有凭据,自应仍存主仆名分,不便悉行开豁。其有并无文契,惟执别项单辞只字,内有佃仆等类语句者,此即当日之佃户受豪强凌压所致,应请悉准开豁为良。其有先世实系殡葬田主之山,子孙现在耕种田主之田,饬令地方官查讯明确,或令其结价退佃,以杜日后葛藤。*(清)暻善:《条奏佃户分别种田确据以定主仆名分》(乾隆三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嘉庆十四年(1809),安徽巡抚董教增奏请将远年小姓分别开豁。刑部遵旨纂定条例如下:
安徽省徽州、宁国、池州三府民间小姓,如现在主家服役者,应俟放出三代后所生子孙,方准报捐考试。若早经放出,并非现在服役豢养,及现不与奴仆为婚者,虽曾葬田主之山,佃田主之田,均一体开豁为良。已历三代者,即准其报捐考试。*(清)薛允升:《读例存疑》卷9《户律之一·户役·人户以籍为定》“条例”。
道光五年(1825),安徽巡抚在祁门县周容法殴死其主李应芳一案中遵旨题准:
若无卖身文契,又非朝夕服役,受其豢养,虽佃大户之田,葬大户之山,住大户之屋,非实有主仆名分者,应请除其贱籍,一体开豁为良。*(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二)》卷39《良贱相殴·安省细民殴死大户分别拟罪》,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420页。
由上可见,主仆名分法律的调整历经几代皇帝,各个时期开豁的条件显然存在一定的差别。雍正开豁为良谕旨,最终确定以文契尚存、受家主豢养为依据。乾隆朝改为“全以卖身文契为断”。嘉庆十四年(1809)条例以在主家服役、受主家豢养为准。道光五年(1825)的规定基本沿袭了嘉庆年间的规定。总体上看,调整后的法律所确认的主仆名分的范围在逐步缩小,尽管没有最终彻底废除主仆名分的法律规定,但较之过去还是破天荒地开了个口子,为小姓争取权利和地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依据和空间。
那么,主仆名分法律调整究竟给徽州小姓的抗争带来了怎样的变化呢?
从手段来看,小姓开始积极把握机会并将多种手段相结合与望族周旋。在一起发生于乾隆三十年(1765)休宁县汪氏与胡姓之间的互控案*《清乾隆休宁县状词和批示汇抄》,原件藏安徽省图书馆。中,胡姓为摆脱小姓的身份,就曾创造性地运用了多种手段:为了凝聚更大的力量而联合其他十一姓小姓共同叛主,为摆脱汪氏直接奴役而主动向官府申请与汪氏分立保甲,为假造出处尊贵的历史而妄认水口神庙为自家宗祠,攀缘同姓不宗的府学教谕胡老师,等等。此外,在汪氏投递的禀状中又提到,胡姓还曾“倡各姓仆众赴黟(县)赴婺(源)谋谱”,妄图插入清华胡氏支下,以改变卑微出身。由是观之,通过单一的诸如谋买族谱、攀高认祖,已经不再是小姓抗争的唯一手段了。这也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小姓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按,本案胡姓在外地经商,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认识水平的不断提高,小姓与望族之间的矛盾冲突非但没有淡化,反而日趋激烈,各种抗争手段也显示出小姓非凡的智慧和胆识。
然而就结果而言,本案中的小姓尽管运用了种种策略和手段,但还是以败诉而告终,依旧没有摆脱主仆名分这个套在脖子上的枷锁。本案与前述一系列案例说明,希图通过谋谱之类的非暴力方式来根本改变小姓的生存处境,显然是很难实现的,即便是在国家法律做出重大调整之后也是如此。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主仆名分法律的调整并不彻底,地方官府在执行时瞻前顾后,使得小姓的反抗束缚重重,难以根本获得成功。首先,各个时期调整后的条文规定不尽明确,容易给地方官府和望族在执行时钻空子。如雍正和乾隆时期的两次调整就比较粗略,雍正朝规定的所谓“受主豢养”就被地方官府解释为“佃主田、葬主山、住主屋”,这就使得一直相沿的陋习继续合法化。而乾隆年间调整的附带条款,由于对卖身文契界定不明确,又给望族继续役使小姓留有借口。因此,这两个时期的开豁其实并没有起到实际作用。唯有嘉道时期相对明确的规定,方才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徽州“沿于积习”、“大姓逼勒”等现象非常严重,因此实际效果仍然有限。其次,清统治者对于主仆名分法律的调整其本身诚意也有限。其实,清政府对主仆名分法律进行主动调整,除了小姓反抗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雍正初年“摊丁入亩”政策的颁行,将人丁应纳丁银按照土地数量摊入田赋之中,在此情况下,那些获得开豁且拥有土地的小姓,必须和编户齐民一样向国家纳税服役,显然这对国家财政收入“开源”非常有利*据《清乾隆休宁县状词和批示汇抄》记载,雍正五年八月二十三日,徽州知府沈一葵在呈布政使司详文中指出,徽州佃仆“地产丁粮,必寄居主户完纳”。可见,佃仆由于身份低微,被排除在编户齐民之外,无独立缴纳税粮权利。。可见,雍正朝开豁谕旨的本意,并不完全在于对小姓人身束缚的彻底释放,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控制向政府服役纳税人口的考虑。最后,无限制地开豁小姓,对宗法秩序的影响非常大,容易引起大族的不满和激烈抗争,因此地方官府在执行时总是顾虑重重。雍正六年(1728),休宁知县朱鹭就曾向徽州知府沈一葵提议:“此辈(即小姓)因家主贫弱,早有尾大不掉之势,今倚恃恩例,愈肆欺凌,诬告其主者有之,辱骂其主者有之。卑职虽加责惩,若辈反以悖旨挟制官长。仰恳宪台俯鉴,名分攸关,刁风渐不可长,饬颁严示。”*《清乾隆休宁县状词和批示汇抄》,原件藏安徽省图书馆。该提议逐级详请,得到了布政使司和抚院的高度重视,最终准许了朱鹭缩小开豁范围的意见。可见,地方官府在实际执行时对各方面利益都作了权衡,目的是为了维护地方社会稳定,不要产生太大的动荡。其最终结果,显然是倾向与政权相呼应的族权统治。
另一方面,徽州宗族势力强大而顽固,并且与地方官府相互联手,使得小姓抗争最终多以失败告终。雍正五年(1727)开豁为良谕旨下达后,地方官员就一度对开豁条件的认定制造重重障碍,继续维系宗族对小姓的控制。如安庆巡抚魏廷珍、休宁知县朱鹭等人,就曾先后有如次之提议并得到批准:只要是“葬主山、住主屋、种主田”者(魏廷珍),甚至只要是具其一者(朱鹭),“尤在不应开豁之例”*《清乾隆休宁县状词和批示汇抄》,原件藏安徽省图书馆。。如此之认定,更加强化了实际存在的土地关系的力量,从而把可以开豁的人数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对小姓极为不利。此后,尽管乾隆、嘉庆两朝多次重申对徽州小姓进行开豁,甚至道光五年清政府还明确地废除了约束小姓开豁的“葬主山、住主屋、种主田”的规定,亦即国家法律很大程度上取消了形成主仆名分的根据,但是徽州的强宗大族依靠封闭的自然地理环境,并通过实际存在的土地关系、族规家法、习俗惯制等力量,还是顽固地将之保留了下来,小姓社会地位卑微的状况也因此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年。关于此,民国《歙县志》载:“小姓之制,各大族皆有之,在昔分别极严。隶仆籍者不与通婚姻,不得应考试,至光宣间,科举制停,城乡设学,此风乃革。”*民国《歙县志》卷1《舆地志·风土》。民国《婺源县志》亦载:“主仆之分甚严,役以世,即其家殷厚有赀,终不得列于大族。或有冒与试者,功(攻)之务去。”*民国《婺源县志》卷4《疆域七·风俗》,1925年刻本。总之,法律的调整尤其是涉及松动宗法秩序的调整,统治者本身的诚意首先就非常有限,特别是地方官府不能彻底遵照执行,加上宗法势力的顽固抵制,此类法律调整最后成为具文一点都不意外。
当然也应看到,地方官府在执行谕旨的过程中,的确打击了一些气焰嚣张的豪族大姓,一些被强压为小姓者也确实获得了开豁,但这并不意味着开豁令的执行就比较彻底了。如雍正五年(1727)十二月二十一日,徽州府发布严禁“巨族欺凌小户”的告示*《清乾隆休宁县状词和批示汇抄》,原件藏安徽省图书馆。。告示即提到何庆等三十余家良民,被冯氏大族压为小姓。由于本年冬至祭祀时,何庆等没有按冯氏的要求前去服役,冯氏竟统众搬其粮食、牲畜、衣物,甚至缚其妇女,勒逼服役,致使何庆等状告到府。知府沈一葵认为,虽然冯氏称何庆等祖先系冯氏始祖自唐带来,但身份凭据已不可考,“明为良民”,判定冯氏欺凌小户是实,枷示在案。可见谕旨的发布激发了小姓的斗志,确实有一些小姓因此摆脱了人身束缚。但要提醒的是,此案正赶在谕旨刚刚发布这个政治风口上,因此地方官府不得不拿一些臭名昭著的大族开刀,以向朝廷交差。随后,安庆巡抚魏廷珍、休宁知县朱鹭等人很快就对可以开豁的对象圈定了一个很小的范围。这恐怕正是地方官府的本意,因为这样做既可以杀杀某些豪族大姓的嚣张气焰,对上有所交代,又不会过分损伤大族的整体利益,使得矛盾激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又如嘉庆十四年(1809)开豁条例下达后,据《宦游纪略》记载,徽、宁、池三府一时开豁为良者竟达“数万人”*(清)高廷瑶:《宦游纪略》卷上,清同治刻本。。但是,这个条例还是不能被彻底遵照执行。道光五年(1825),安徽巡抚在祁门县周容法殴死其主李应芳一案题奏中即指出:“嘉庆十四年定例开豁之后,亦因沿于积习,未经改图。”“安徽徽州等府细民一项,久经钦奉世宗宪皇帝圣谕,开豁为良,因或被大姓逼勒,或系自甘污贱,致有仍执贱业之人。”*(清)祝庆祺等编:《刑案汇览三编(二)》卷39《良贱相殴·安省细民殴死大户分别拟罪》,第1420页。根据嘉庆十四年条例,周容法符合开豁条件,但考虑到主家李氏不依以及开豁后“别无生计”,因而不得不照常服役。后来,周容法因受其主李应芳凌辱,愤而将之殴死,从而酿成惊天大案。可见,积习相沿、“大姓逼勒”,尤其是实际存在的土地关系的严重约束,致使经济实力微弱的小姓在没有新的谋生之业保障的情势下,根本就不敢改业自新、开豁从良,只得“仍执贱业”、“自甘污贱”,继续忍受望族的百般欺压。
五、结语
宗法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特点之一,实行的是普遍的身份等级制度,规定着不同血统出身者之间的等级秩序。这种身份等级制度,垂几千年不变,维系着社会权利和地位分配的一系列等级差别,其与宗法血缘关系互为因果的作用,大大强化了封建时代“血统论”的社会地位和权利世袭继承制。徽州小姓与望族围绕着谱牒持续冲突的现象,即是他们因血统出身的不同从而导致彼此社会地位和权利分配严重失衡的结果,归根结底还是封建宗法制度所规定的身份等级制度的产物。明清时期的徽州“最重宗法”*嘉庆《黟县志》卷3《风俗》,清嘉庆十七年(1812)刻本。,宗族始终竭力维护名分尤重、等级森严的社会秩序,小姓因血统出身的不同而与望族存在着难以逾越的等级差别,由此决定了二者迥然有别的生存状态。而记录血统源流的谱牒其实就是一纸“出身符”,是社会地位与权利分配的身份证明,一定意义上承载和维系了小姓与望族之间不可逾越的等级差别。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小姓与望族之间围绕谱牒而展开的冲突势不可免。当然,谱牒纷争所呈现的仅仅是小姓与望族矛盾冲突的一个方面,小姓与望族的斗争,或者说不同血统出身者之间的冲突,其实一直在更为广阔的空间和领域里频繁地发生和持续着,封建宗法制度下的身份等级秩序也始终处于一种不太安宁的状态。
小姓的努力尽管难以根本实现他们所期望的目标,然而毋庸置疑的是,那些持续的抗争还是有力地冲击了身份等级秩序,为小姓争取社会地位和权利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清政府对于主仆名分法律的一再调整,说明身份等级制度有松动的迹象,这本身就是小姓努力抗争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诚然,主仆名分法律的调整似乎为松动身份等级秩序开了个口子,但是封建的身份等级秩序绝非仅仅依赖法律来维系,实际存在的土地关系和顽固不化的宗法势力等也是非常重要的维护力量。最为根本的,封建宗法制度的主旨是要建立以家族为基础的专制统治,族权与政权始终两相呼应、息息相关,政权不可能根本触动族权的利益,因为族权的稳固是其统治的基础。因而,主仆名分法律虽然做出了相应调整,但法律毕竟是统治者自己制定的法律,其目的还是为了自身的根本利益,所以通过法律调整彻底开豁小姓绝不是统治者的本意,更不意味着统治者是要彻底取消身份等级制度。宗族和地方官府对最高统治者调整法律的根本意图始终心领神会,尤其像在徽州这样偏僻封闭且宗法势力极其顽固的地方,根本就不要指望他们会不折不扣地响应执行。由是观之,只要导致身份等级制度产生和顽固残存的特定历史条件一息尚存,小姓恶劣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就不可能根本改变,其与望族之间的冲突也必将持续下去。
ZHENG Xiaochun, Ph. D. of History, Professor of Chaohu College, Chaohu, Anhui, 238000.
责任编校:张朝胜黄琼
Small Families in Conflict with Prominent Families of Huizhou Area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Exhibited in Genealogy Disputes
ZHENG Xiaochun
Abstract:Buying genealogy was the means for small families in Huizhou to change their social status by becoming prominent families by descent, which exhibited the sharp differences between small families and prominent ones in living conditions and their fierce conflicts as a result of hierarchy in status within feudal patriarchal system. The Qing government revised the law of master and servant several times, but its actual effectiveness was limited due to various reasons. As long as the historical conditions that led to the hierarchy in status lasted, their conflicts would never cease.
Key Words:Huizhou; genealogy; small families; prominent families; patriarchal clan; Hui Studies
DOI:10.13796/j.cnki.1001-5019.2016.03.010
中图分类号:K29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6)03-0094-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5JJDZONGHE001);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点项目(2010sk483zd)
作者简介:郑小春,安徽大学徽学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安徽 合肥230039),巢湖学院思政部教授(安徽 巢湖238000),历史学博士。
◇徽学:社会史专题(主持人 卞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