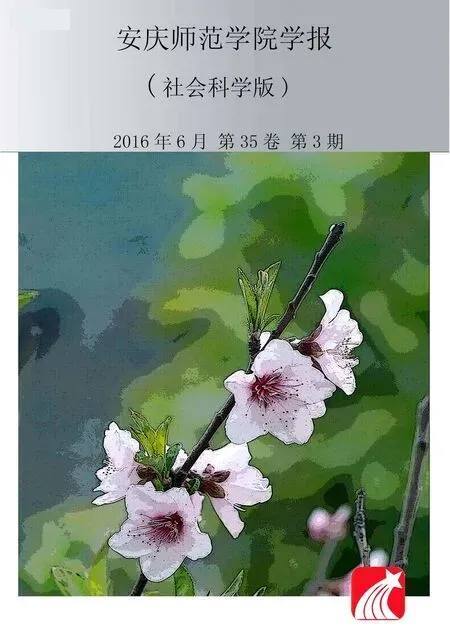从徽州文书看明清徽州地区的盗葬
陈 雪 明
( 安徽大学历史系, 安徽 合肥 230039)
从徽州文书看明清徽州地区的盗葬
陈 雪 明
( 安徽大学历史系,安徽合肥230039)
摘要:徽州宗族向来有保护祖墓的习俗,但祖墓被侵盗的现象却屡见不鲜。宗族内部或宗族之间为了解决祖墓被盗葬的问题订立了很多文书,从这类文书合约角度考察和探讨徽州地区盗葬现象的具体情况以及徽州宗族面对祖墓被盗葬时所采取的具体措施,可以深化对徽州宗族的了解。
关键词:明清;徽州宗族;徽州文书;盗葬
DOI:10.13757/j.cnki.cn34-1045/c.2016.03.005
徽人向来聚族而居,素有尊祖敬宗的传统。坟墓在当地被视为祖先“体魄之所藏”,是宗族的根本所在,正如歙县江氏宗族所言:“盖闻葛藟犹庇其本根,草木不差其臭味。物固有之,人亦宜然。”[1]一方面,徽州宗族非常重视保护祖先坟墓,另一方面,盗葬现象时有发生,徽州文书中便留存了很多关于处理民间盗葬问题的合同文约。本文拟从这类文约的角度出发,考察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盗葬现象,勾勒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地方宗族面对盗葬问题的具体应对情况。
一、徽人的风水观念与护墓举措
历史上徽州素有崇尚风水的习俗,弘治《徽州府志》载:徽人“泥于阴阳,拘忌费事,且睨鬼神,重费无所惮”[2]。“且江南风水关乎祸福,葬者必卜兆,择术以作,作后不敢擅动,此风水之故俗也。”[3]选好吉穴,还要选择利年吉日安葬。对穴内安葬的顺序,徽人也有规定。有的宗族是按照昭穆顺序进行排列,有的则是选择抓阄的方式来确定最后的安葬顺序,顺序确定不得随意改变。同时,对穴内已确立的安葬性别也不得擅自改动,如祁门陈氏宗族曾议定:“所有男棺女棺,毋得以男作女,亦毋得以女作男,如违查出,定行圮举,毋得异说。”[4]312且“夫人之魂体居墓,受山川淑气则灵,灵则魂安,安则致子孙昌衍而不替。”[5]由此可见,风水观念在当地深入人心。
徽人的风水观念根深蒂固,对堪舆家的说辞深信不疑,甚至将自己的命运全部押到死者墓地的选择上。纵观徽州各个宗族族谱所载祖墓之地,它们大多选择山水环聚之处,正所谓“山峦拱秀,冈陇回环,后必有兴者”[6],这类地形不仅可以使祖墓免受外界的侵扰,还被认为可接受山水灵秀之气,有益于后世繁衍昌盛。徽州宗族大多处于聚族而居的状态,如祁门陈氏宗族自称:“缘我陈氏自显,始祖文公勤劳王事,子孙由唐居祁,聚族虽繁,而支派世系厘然不紊”[4]431,这也为祖墓的日常维护提供了有利的社会条件。所以,在徽州地区,各个宗族都采取了一定措施以保护祖墓。“坟墓之修,后昆之贤,家道之兴可睹也。”[7]
一般而言,明清徽州宗族对祖墓进行维护,首先会选择吉日,对祖墓修缮,砌石拜台,在祖墓周围埋石立界,与邻人划清祖墓范围,使其完固。同时他们会在祖墓附近种植松楸等树木,这不仅可以起到培土的作用,还可以维护祖墓不受侵害。在墓地范围内的树木则被称为“荫木”,严禁后人砍伐。另外,有些宗族为了防止不法之徒或不孝支丁的蓄意破坏,还会寻求官府的保护,在祖墓附近树立禁碑,以期避免日后各类侵扰。如新安汪氏宗族在其祖墓禁碑中便称:
顾墓自晋迄今千有余岁,梅雨淋渍倾圯塌泻,仅存尺余之地,行路罔不心伤,子姓更深目怵。今职等鸠工兴修,傋石运料,诚恐该处附近无知之徒或搅扰中途,或窃发清夜,或日后樵苏,纵其斧斤畜牧,任夫践踏,或奸强贪吉,盗占阴谋,或游客逗留潜踪,止宿种种,衅端不一而足。与其匡救于巳灾,孰若绸缪于未雨。为此请示严禁,庶顽民敛迹宵小潜踪,并恳严饬捕保时加巡察,俾樵苏毋刈祀荫,畜牧不致戕茔。豪强无觊觎之心,祠宇得肃清之奉等情,据此合行示禁,为此示仰[8]。
很多宗族为了保证维护祖墓的经济来源和日常管理,还会设立专门的祀田,并成立专门的祀会。徽州宗族为了维护祖墓安宁,也是耗费了大量心力,其目的便是为了防止祖墓被侵损。即便如此,仍有各种破坏祖墓现象的出现,其中,最令各个宗族无法容忍的事情便是盗葬。
二、徽州地区的盗葬问题
徽人认为祖墓之事乃“子孙命脉所关”,即便墓地附近被人侵损,伤墓惊塚,已是宗族大事,况乎盗葬?对此,休宁县林塘范氏家族就在《祠规》中明确提出:祖墓“或被人侵害盗葬,则同心合力复之。患无忽小,视无逾时。若使缓延,所费愈大。此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道,亦圣谕孝顺内一件急务,族人所宜首讲之。”[9]出现祖墓盗葬现象即是对本族的极大侮辱,此事决不能容忍,族人自是要与其理论,到官府起诉立讼。从各类徽州文书中可见,徽州地区的盗葬从性质上,可分为族内盗葬和族外盗葬两类。
(一)族内盗葬。族内盗葬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1.族内恶丁恃强盗葬。随着时代变迁,“风俗浇漓”的状况日益严重。徽州宗族里便有叛丁逆徒无视族权,肆意盗葬祖墓。如康熙年间祁门环砂程氏便有祖墓被族恶“持势盗葬,占山惊塚”的问题,于是合族人决定鸣官立讼[10]。道光七年,祁门县二十一都陈氏宗族也出现族内逆丁盗葬的情况,为此,合族立下齐心合同文约以杜效尤,全文如下:
立齐心合同文约全、暹公秩下立信、鼎昌等原三十世祖立公葬浮比长宁都,土名小惟坑口,其山四至,东路,西降,南有诚地,北施家垄。自来迄今数百余年,从无侵犯。今被秩下坑口逆丁陈怀德等听使兆棺,在 祖茔右边盗葬壹穴,身等知觉具帖声名,明合族公议章程,以杜效尤。倘有不测,所有费用公议,丁股出俻,丁七股三摊派,如各公秩下瞒丁数者,永不昌盛,不得累及出身之人。其出身之人亦不得拖委退缩,狥私肥己,有此情者亦不昌盛。各当踊跃,照名出俻。自立合文之后,秩下各祠子孙,毋得借端执拗梗众等情,如违,鸣 官究治,准不孝论。今欲有凭,立此合文拾玖纸,各祠收一纸存照[4]421。
祁门县陈氏宗族向来有保护祖墓的传统,该族祖墓数百年来基本安宁,直到道光年间因为族内逆丁盗葬,合族人公议章程进行处理,所有费用丁股摊派,并鼓励族人踊跃参与。陈氏宗族在维护祖墓的过程中,对全族人进行了团结和整合。
2.由于岁远年渊,族内后裔不明情况意外盗葬。徽州地区有族大者,族内各支除了祭祀共同的始迁祖之外,还会分别祭祀各支的祖先。这样,宗族各支之间也会因为各自的祖墓问题发生争执,相互之间也会达成一定协议,互不侵扰墓穴。但是由于时间的流逝,老契失散,各支子孙在不明情况的状况下也会出现无意盗葬。如祁门十三都凌氏宗族“自唐迁居祁邑,安葬祖塚,代代皆然”,先祖便曾因为墓祭问题“互相口角,以致鸣公理论”,后经劝息,“立有合墨,前后左右毋得侵害等语,至今数代”。然而,由于“日远年湮,未知前文合墨”,秩下子孙“复蹈前辙之弊,埋葬龟形祖坟右侧,是以投族长鸣公理论”。最后经过族人调解,让侵葬者“鼓乐祭坟”,之后不许再行扦葬,“如违,听凭鸣 官处治。倘梗顽不遵者,私自侵葬,悉听合众起扦,无得异言。”[11]这一问题,最后经过族人的劝息调停,由侵葬者鼓乐祭坟并保证不再侵葬,这才得以解决。
3.族内支丁私葬。由于墓穴内的安葬顺序一般在开穴时便已确定,合葬人也必须相互遵守约定,日后同时安葬,不得私自改动安葬顺序或先行安葬,如有这类情况在徽州地区也作为盗葬情况论,所以本文也将此类情况纳入到盗葬问题中进行探讨。如祁门环砂程氏族人在其合葬文约中便规定:“二家均葬均厝,悉照穆列坐,不得临时争论,所有费用照棺均出,毋得私行盗葬。”[12]黟县胡氏族人在议定迁葬合同时,也约定“日后择于眼同扦葬,不得以强欺弱,私自盗葬,如有盗葬,经公理论。”[13]未葬前,穴位若进行买卖,买者也必须遵守之前开穴时的合同文约,若有私自买卖并强葬的情况,卖者将受到惩罚并承担相关诉讼费用,而强葬者则会被要求立行起迁。
(二)族外盗葬。族外盗葬的具体情况也有以下几种:
1.盗葬人对地业“不知来历”,寻得吉穴便举棺安葬,或因山界不明而导致误葬。由于徽州地区山业买卖众多,常有一山多卖的现象,导致业主不明,日久年远,有些山业便不知来历,后人不明山内墓穴坟地情况,便会出现盗用他姓墓地情况。如祁门十八都方氏族人早年将方家墓林和郑村岗庶上末头两块地业卖给叶氏,明万历三十二年方氏后人不知其详,在不明山业的情况下,将族人葬入叶氏祖坟墓地内,叶氏族人得知,要告官究治,方姓自知理亏,“托凭亲邻劝谕”,叶氏“念此地是身(方姓)祖卖出,情义为重。如免起夆外,(方姓)自愿谢醮以谢贤等气忿。”[14]284方氏立下谢醮息忿文约,以明确山业并保证后人不得再行侵葬。另外,未经墓地主人应允的情况下,在墓域内开造坟穴,安葬棺柩,也被视为盗葬。如休宁县二十八都张天碧与王天诒便曾因此订立一则文约,由于王氏早年先葬于山,划定墓域,保护风水。为此,两姓议定日后双方均不得在山开造坟穴,侵害风水,如有此类情形,即被视为侵害盗葬问题而论[15]。
2.族内人将墓穴私自卖出,造成族外人盗葬。如果是由于族内人将祖墓穴位卖出被发觉,本族人定要通知各个保甲头户,不得盗葬,议定即使这类私卖文约日后拿出,也不得使用。如乾隆十五年,祁门县三四都王氏宗族便出现这类情况,该族户丁立下文约:
立议文约头户王大用、子户王顺、代守人黄孟三,今因本都各处山场向有祖茔,垒垒在上。近被大用户内有不法之辈擅将各处山业私卖黄孟三丘葬管业,是以合众公议,闻官治罪。蒙中劝谕,孟三自知理亏,日后倘有厝葬材柩等事,务要通知头户,不得私自魆买盗葬等情,如违,听自王姓执文理论,倘有各门先年擅相私受文约,日后赍出,不得行用,悉照此文为准。今欲有凭,立此文约一样二纸,各执一纸为照[16]。
上述文约即是一份因为王氏族内山业被盗卖与族外黄姓安葬管业被发觉,由于该山业内有王氏祖墓在上,因此合族公议,欲送官处置。但是黄姓自知理亏,没将事态扩大,最后双方自行立定合同,议定黄姓日后若有安葬行为务必通知王氏族人,不得擅自盗葬。而经过此番折腾,王氏宗族为了避免同类事情再度出现,同时也议定族内若再有私相买卖文约,日后均不得使用。
3. 族人管理不善,外姓趁机盗葬。虽然徽州宗族一般选择聚族而居,围绕于祖墓附近,便于及时修缮和保护祖墓。黟县莫氏宗族便在族谱中规定:“如后世繁盛,欲另迁居,当于近地卜筑,以祖墓在望,不可远也。近则可无时省察,不致被人放牧践踏。”[6]但是由于家族变迁,有些宗族在其繁衍发展过程中,后裔子孙还是会因为各种原因,不可避免四散而去,这就给墓地附近有心盗葬之人以可乘之机。如祁门十八都方姓便见山主居住遥远,乘机盗葬三棺,山主叶氏得知,便要闻官惩治,但方氏托凭中人哀求,叶氏念在方氏草莽无知,便罢讼,为此方氏便立一“还主文约”,承诺“日后子孙,再毋得在前山侵葬盗葬,如有仍前,日间主住远,在山侵葬盗葬等情,听主究官,一并重究服显”[14]319。
(三)徽州人对盗葬问题采取的措施。针对如上各种盗葬的情况,徽州宗族也会根据其盗葬的严重程度来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主要分为民间调处和官府诉讼两种形式。
一般而言,情节较轻者,如葬入祖墓禁步内导致惊塚,或议定合葬却先行私葬等诸如此类情况,被侵损一方则会采取相对温和的方式,如理论调解、劝息等途径解决问题。若是占地惊塚,盗葬者一般会则被要求起葬另迁或者立约承诺不再私葬;若是约定合葬之人私自安葬,先行私葬者则会被要求举棺起葬,并不许再葬,从此便丧失了在吉地安葬的权利。如祁门磻溪陈氏在一则嘉庆十五年的合同中便规定“私相授受强葬,听凭照约加倍处罚,并所有理论费用尽系葬人承值办还。……倘外人攒谋分籍,贪吉盗葬,立行起迁”[17]211。属于这类情形的基本在族内或者宗族之间,通过调解等方式自行解决,而不必经过劳民伤财的官府诉讼。
盗葬情节严重者,盗葬人属于故意盗葬,被侵损一方将认为这是对本族的侮辱,此乃宗族深恶痛绝之事,“斩关伐祖之仇,不共戴天,冤不能伸,万不依息”,“若不严行,非被占此,各业难存”[18]。为了“以警不孝,上可以保先祖,下可以警后人”[17]315,保护祖墓的安宁与不可侵犯的权威,徽州各个宗族则会不惜一切代价,采取更加激烈的方式,以“鸣官”和“以不孝罪论”来处理问题,诉讼使费则由族内各支均摊。如祁门磻溪陈氏宗族祖墓在乾隆年间被附近朱李二姓盗葬,该族议定立讼,合议“共议银八伯两四椿,各出五十两,仍陆伯两,搃共照丁出俻。倘有不足,日后仍照丁加出,不得推委,累及出身之人。至出身之人,亦必视众事为己事,务要尽心竭力,不得怠忽及狥私苟且等弊,如违,执约理论。”[17]173有些宗族为了夺回被盗占的祖墓,即使历经百年,耗费巨资,也会不惜动员家族各支,以家族全部资产作为诉讼费用,踏上艰难的诉讼之路。如休宁县率水首村朱氏宗族,该族于唐代迁入徽州地区,在宋代一支族人定于休宁县开枝散叶,由于始迁祖春公墓被龙湾黄氏宗族盗占,此后,首村朱氏宗族便展开了长期的诉讼活动以夺回祖墓,虽申诉“百有余年”,却依然“祖冤莫雪”。即便如此,朱氏宗族也不曾放弃,至康熙四十七年,该族又发起宗族总动员,重整并振兴家族,筹措资金,制定更加完善的管理制度,希望“今日一举,毋负平日报复之素志”,“以雪积世之仇”[19]。
三、 结语
坟墓是祖先躯体魂魄之所在,对祖坟的侵葬行为,在聚族而居、最重宗法的明清徽州乡村,是最不能容忍的严重事件。明清时期的徽州宗族为了更好地保护祖墓,制订了很多相关族规。如康熙黟县《横冈胡氏支谱》在《壮卿公老家规》中将各处祖墓坟冢视为“上妥先灵而下荫子孙”之地,告诫族人“历年既久,福庇攸深。若盗一抔之土,神既不宁,祸必旋至。凡支下子孙不得魆行侵害,蔑祖自便。如违禁者,族众即行起举鸣官,以不孝罪论罚。”[20]但现实情况却是徽州地区的盗葬问题一直无法根绝,随着时间的流逝,很多宗族都发生过祖墓被盗葬的情况,以致“祖坟荫木之争,辄成大狱”[21]。究其根本原因,实则为民众利益之间的冲突和纷争,包括宗族与宗族之间的利益冲突和宗族与个人之间的利益冲突。盗葬的根本原因不在于那单纯的一二分地,而在于那块土地的风水吉凶,不论是宗族还是个人均是受利益的驱使,希冀将祖先葬于风水宝地,借以庇佑本族本家的富贵之势。从明清时期徽州地区民间各类处理盗葬问题的相关合同文约来看,徽州宗族对于祖墓被侵损或盗葬是绝对不能忍受的,这不仅受根深蒂固的尊祖敬宗、报本追远的观念影响,更是由于恐惧宗族的运势会因此受损,影响整个宗族的兴旺发达。在徽州地区的正面表现为数百年来坚持祭祀祖墓并及时修缮维护,而从反面则表现为在祖墓被侵被盗时不惜一切代价进行的争夺。有的宗族还会通过夺回被侵盗祖墓这一事件来整合整个家族的力量,以“尊祖敬宗”为旗号,借此机会调整本族的财力和组织机构,团结全族民众,加强本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最后达到强化对族人控制的目的,进而维护封建社会基层统治秩序。如祁门县二十一都陈氏宗族在道光七年为了夺回被盗葬的祖墓,团结秩下各支,包括全公秩下乡保堂等七堂和暹公秩下嘉会堂等十二堂子孙,并规定各秩下子孙不得推诿退缩、徇私肥己,鼓励各自踊跃参与。宗族统治者借此机会加强各支的联系,巩固宗族制度。
参考文献:
[1]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三辑·第3册[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31.
[2](弘治)徽州府志·卷一·风俗[O].明弘治十五年刊本.
[3]吴氏永慕集·吴氏墓典[Z]//方观承.中国祠墓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4:28.
[4]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一辑·第9册[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5]戒后侵祖迁坟伐木说[O]//歙县城东许氏世谱·衍庆录.明崇祯年间刊本.
[6](嘉庆)黟县五都月塘莫氏宗谱·卷一·凡例[O].清嘉庆十四年刊本.
[7]丘墓表[M]//(民国)新安大阜吕氏宗谱·卷五.民国三十四年刊本.
[8]重修始祖墓禁碑[O]//(道光)新安汪氏宗祠通谱·卷四.道光年间刊本.
[9](万历)休宁范氏族谱·统宗词规[O].明万历年间刊本.
[10]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一辑·第6册[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09
[11]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三辑·第9册[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65.
[12]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一辑·第8册[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28.
[13]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二辑·第4册[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13.
[14]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二辑·第2册[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15]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五辑·第10册[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324.
[16]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二辑·第1册[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40.
[17]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五辑·第2册[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8]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三辑·第3册[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515.
[19]刘伯山.徽州文书·第三辑·第4册[Z].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436.
[20]壮卿公老家规[O]//横冈胡氏支谱·卷下.康熙四十三年刻本.
[21]歙县志·卷一[M].民国二十六年铅印本.
责任编校:徐希军
收稿日期:2016-01-1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民间规约文献集成”(14ZDB126)。
作者简介:陈雪明,女,安徽泾县人,安徽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中图分类号:K248;K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730(2016)03-0025-04
网络出版时间:2016-06-23 16:44网络出版地址:http://www.cnki.net/kcms/detail/34.1045.C.20160623.1644.00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