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觉平生未整人
张建智
2015年3月3日4点43分,曾彦修先生仙逝,享年96岁。虽也是高寿了,但仍不免垂泪。远在南方的我,不能亲去送他远行,惜矣。因为,前不久还得曾老《平生六记》一书,而我也快递了一册拙著《绝版诗话》给他,以作他茶余饭后的消遣。那时,得他儿子发来短信:“父亲正住在协和医院,说他看了这本小书,很高兴。他很快会出院,只是有点重感冒而已。”
上次那回,果无大羔,但是,曾老后来听觉极差,当我与他通电话,他总提高嗓音说话,尔后只能由人代听了或由小凉转告。但当他给我写信、或赠书签名时,字迹却没多大变化,还那么老辣有力。
想不到不多久,他又住进协和医院,开始只是肺感染,后发展成严重肺心病,医治无效,终回不了家,真可谓“一叶随风忽报秋,纵使君来岂堪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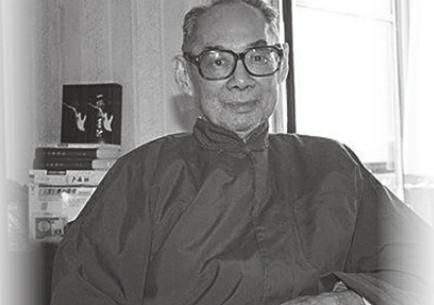
我赞同朱正先生所云:“读罢《平生六记》,深深感到:这,是一部奇书;作者曾彦修老前辈,是一位奇人。”这话说到点子上。朱先生还说“他是出版界排名第一的右派分子;他是第一个上《人民日报》的党内右派分子,1957年7月13日《人民日报》刊出批判他的文章,引题特别提出‘党内也有右派分子,这就有一点特殊性了。不过最为奇特的是,这时他是人民出版社五人小组的组长,正在主持本单位的反右派斗争。他这右派分子是他自己决定要划的。”
但我认为,令人更奇的是,曾老在回忆这右派20年生活时,却并不沉重,也毫无怨言,反有些智者的幽默。他曾说:“身而为一个负责人,在1957年能够免于去打他人为‘右派,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在‘打人与‘被打之间,无意中得到了后者,这不是大幸是什么呢?”
是大幸吗?也许是,也许不是。因为,对于别人是大幸,但对曾彦修自已却是大不幸。他打成右派,发落至上海劳动后,由于政治压力及多种原因,他在上海过的,是妻离子散、漂泊无依的生活。有关这方面的事儿,他鲜少对人提起,在个人著作中,也未着一字。余生也晚,但对曾老那段时期的生活,略知一二。因他曾经是我的姨夫,我的阿姨周宁霞曾是他相伴多年的妻子。曾彦修先生被带上右派帽子,流配到上海后,我在上海见过几面。那时,他似已经与我阿姨周宁霞分居而住,只身一人在《辞海》编辑部里。
曾彦修作为右派,已有三个子女,至上海后那段生活,今天的人们,大致是可以设想的,坎坷、苦难,政治与各种压力都很大,物质与精神均是匮乏。曾虽未进入“鬓有丝”的年龄,但物质的匮乏,精神上困厄,是免不了的。“梦里依稀慈母泪”也是常有的事。这从曾彦修晚年的口述中,有说一二。当年作为右派状元,人民日报当时有标题为“曾彦修腐化变质”的消息刊出。1964年他回四川万县,看望他母亲和哥哥,他走在街上,有些人就马上认出这位大右派。这不就是他“梦里慈母泪”的一个象征。
但是,就在这么的一种生活状况下,曾彦修却置之度外,怡然自得。他自已戏谑为“半饥半饱,强作风流”。他是怎么来对待呢?大右派曾彦修在上海的生活:一是逛旧书店,在旧书店买线装书,或是《四库备要》《四库丛刊》,也买《西廂记》之类的书。二是逛旧货店、古董店。买些价不高的小玩意儿,有竹的、有玉的有花梨木的。三是听音乐,那是1963年,饥饿有所缓解之时,可去上海音乐厅一坐。再则,坐公交车逛郊区,他从小生长于四川宜宾,对大自然格外热爱。以上略举几例,你看他在如此困境中,还怡然自得。这些在上海之事,他晚年总喜欢谈起,我每次去北京,都会听他讲这些在上海的生活。
有时总想,曾老为何能在逆境中如此洒脱?包括他后在奉贤的劳动。我认为主要原因,还是他在《九十自励》诗中,自已所道:“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一个扪心无愧的人,才能具有这样的精神境界。也如黄一龙、曾伯炎先生在《悼曾彦修》联中所云:“坚拒整人自划右派入苦海,苦心诲世甘为孺子做老牛。”一个在世大写的人,才能有此气度。
曾彦修老,作为一个新闻出版界资深出版家,为我们留下的血与火的史料,以及那些他亲历之国事,已有人谈及,将来还会有人作研究。以上我谈的只是作为他是我姨夫的家事。另则,我想再谈谈二三小事。
姨夫曾彦修,1978年8月离开上海,结束了他的右派生涯后返京赴任,隔了十多年,后经王春瑜先生打电话给我,说曾老在杭州开会,欲买湖笔写字,于此,我们在杭晤面叙旧。他对毛笔,可谓嗜笔为命。他为振兴地方笔业,曾写了达十多张纸的信给我。并且他在经济并不宽裕的情况下,要无私捐几万元给笔庄。此事虽未成,但这钱是他多年稿费之积畜,就当年来说也是个大数目,事虽小,足见他对文化事业之看重,也见证了他的良知和心胸,见证了他的人品和性格。
曾老的生活一直是保持艰苦朴素的,只要有书读、有文写,他什么也不在乎。记得,有一天下午,我们到曾先生原在方庄的家,一进入他家的客厅,真有点似到了延安时期那模样,见一只破长桌上,披了一块白布,他手边是一堆零乱的稿纸,瓶瓶罐罐,到处堆放。甫坐下,我就问他,“曾先生近在写什么?”他说了一个莫名的书名,由于听不懂他含糊的四川话,更一时不解他说些啥,所以直到我们泡了带去的“碧螺春”茶后,一边喝茶一边聊天,他才给我们用纸写了书名,方知名为《白头宫女说玄宗》,当时一听这书名,真不太懂,他老究竟要写什么?他只是说要写一部前苏联的事。
的确,那时期在《随笔》上,差不多每期都能读到他写苏联的事。为此,我也曾问他,怎么能积累这么多前苏联的资料。他告说,当年在四川读小学时,就关心起苏联,后来在他任人民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时(那时还没社长)因看不惯有些左的冒牌马列主义者,就大量注意收集苏联历史资料。当时没时间写,之后,反右开始,他“自评”了右派,更没机会。
那日下午,坐在他家咯吱咯吱发响、破旧不堪的板凳上,真疑惑不解,一个部长级干部,怎么家中的桌椅板凳,都破成这样还在用,也同时对他写这部书,有点儿吃不准。
忽忽,几年过去,他写的书,终于出版问世了。但是书名改了,是上下两册,书名叫《天堂往事略》。为何改了书名,曾先生没有说明,也不便去问他。但该书闻世后,我即收到他的来信。现把信录之以下:
建智同志:
你好!
久未通信,拙作久未奉上,希谅。现寄上三册书请收。拙作《天堂往事略》,是我自费印行赠人。浙江一带目前已无熟人,因此,我恳请你替我推荐若干人,喜欢读书的人,能否告我详细地址,由我处秘书直接寄发。大致是杭州一二人,宁波一二人,其它温州也可。赠书对象当然是喜读书有影响的开明人士,极左者不送。江苏省尚未赠书,因我不知该赠谁,故请你也推荐几位,我会嘱人民出版社老干处直接寄送邮寄。麻烦了,谢谢!
曾彦修上
2010年12,20
之后,曾老又寄我《略觉平生未整人》,这也是一部坦诚心灵之书,没有丝毫的掩饰,没有华丽的辞句。把一颗心掏给了世人。当各种运动横生叠出时,当其他部门,纷纷汇报肃反运动成果的时候,曾彦修所领导的肃反或其它运动,他不但没有增加一个有问题的人,反而给一批人解除了问题。他曾坦诚地说:“我以衰败之年,……还写着这些书,当然无异于自寻早死。但《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真的,90岁已过,求什么?但我们切不能如此看,当历史已成为过去时,人们再回头细想、推敲,那可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事。
曾老非但是一个资深出版家,一个有良知的杂文家,他还是位严谨的科学工作者。但最重要的是:在多灾多难的20世纪中,曾彦老,宁可自已受难吃苦改造,但居中高位上的他,却具有正义感,去解放别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无愧地吟出如此之诗:碌碌庸庸度此生,八千里路月和云。夜半扪心曾问否,微觉此生未整人。
贺李锐88岁米寿时,曾老写了一贺诗。对于这诗他改了又改,直寄我几信,还征求我意见。我算老几呵,曾老是大家,还用得着我置喙?但大家往往谦虚,他特地用宣纸写了送我。还附信说:“附上贺李锐同志八八米寿句一纸。谈不上诗,一无含蓄蕴藉,二音意俱太急切,犯了诗作大忌,不过一种变相口号而已,寄上仅供一笑。曾彦修拜 零四年,五、一日,在此顺录其诗,以飨读者,也为此文作结。《贺李锐同志八八米寿》:
湖湘风物好,南粤莽芲芲。
斑竹秆秆涙,芙蓉阵阵香。
维新小开放,嵩焘粤海梁。
流血谭黄始,悲歌慨以慷。
东方天欲晓,湘潭出凤凰。
润之千载客,仗剑平八荒。
戎元真有德,志圆行更方。
浏阳双岳峙,长歌哭耀邦。
汩江流不尽,屈子自芬芳。
青史凭谁问,直笔在平江。
今日,曾先生已化鹤而去,但他给我们留下的榜样尚在,多册著作还在。有《诗》云:“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他自已曾说,90岁已过,求什么?我想,作为一个老布尔什克,作为一个大杂文家,他追求的是一种境界,虽路漫漫其修远兮,他的一生,永在上下而求索。这一种精神,是一种超然之思想。若仔细读他留下的文章,以及上录之诗,曾老是在寻求、乃或求索着一个大历史的答案。求诸方家,不知然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