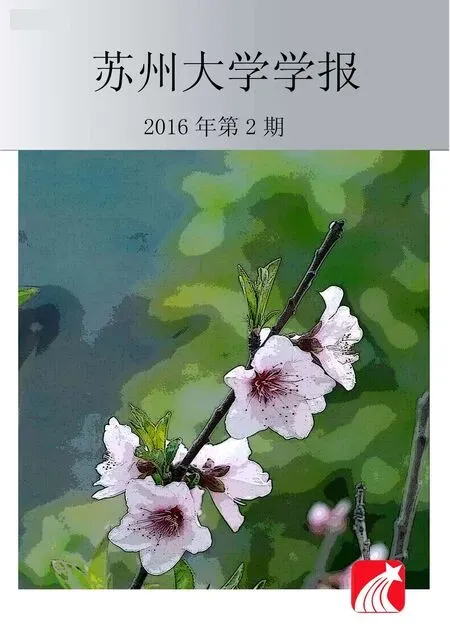教育学本土实践的历史与现实论略
吴 全 华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教育学本土实践的历史与现实论略
吴 全 华
(华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31)
摘 要:教育学本土实践即他国教育学在中国大陆的实践。强国、救国的民族主义是西学东渐中的教育学被引进和较普遍实践的根本动力。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教育学本土实践具有多样化、自主性、多元化、全面化、自由化的特点。体现这些特点的教育学本土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现今主动开放时期并不比被动开放时期的教育学本土实践的效果更好,其根本原因是囿于个性的教育学中国化取向、文化相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教育行政化对教育学本土实践的阻隔。今天我们缺乏文化教育的保守开放的保守主义。如果文化教育的保守开放的保守主义能够兴起,就会开掘出一条教育学本土实践的自由而更富成效之路。
关键词:教育学;本土实践;教育家;文化相对主义;经济民族主义
一般而言,所谓本土,即本国、本地区,它是相对于他国、他地区而言的;而本土实践是指他国、他地区的理论、技术在本国、本地区的实际运用,以产生人们所期待的实践效果。本土实践的机制是以本国、本地区人士为主体的相关人士对他国、他地区的理论、技术的认同、引进、借鉴、吸收、实践转化。其中,关键环节是他国、他地区的理论、技术与本国、本地区社会实际相契合的实践转化。教育学本土实践主要是指他国、他地区(以下简称他国)的教育学理论在本国、本地区(以下简称为本国或本土)的实践。从我们自身出发,所谓教育学的本土实践即他国教育学理论在中国大陆的实践。与其他学科的本土实践一样,教育学的本土实践也须经由认同、引进、借鉴、吸收、实践转化几个环节。在笔者看来,在探讨教育学本土实践的历史特点、成效和不足的基础上,从历史与现实的宏观比较视角出发,揭示教育理论本土实践的现实障碍,对于探寻未来教育学本土实践的更有效路径是一种有意义之举。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学本土实践
我们可将一百多年来教育学的本土实践划分为三个时期,即从教育学最早出现于中国大陆到新中国成立、1949年到“文革”结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这样三个时期。本文在此论及的新中国成立前教育学本土实践属第一个时期的教育学本土实践。
教育学是西方人对教育进行专门化认识、研究而产生的学术成果,它在我国成为一知识门类,最早在文化上是因西学东渐而引进的。但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化上的学科建设事件。西方教育学的发生是因师资培养的需要,教育学在中国的发生也一样,是先有师范教育的实践,后有教育学的传入。这也就是说,教育学的传入是因应当时师范教育之需,是为了培养新式学校的合格的有“教之术”的教师。而之所以要培养有“教之术”的教师,是为了作育强国、救国图存之人才。尽管当时有人认为不能笼统地提倡教育救国,例如,民国期间曾任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郭一岑先生认为,“只有有主义的政治教育才能救国”[1]3,但教育强国、救国是当时有着士人气质者的较普遍的信持,强国、救国的民族主义这一信持是西学东渐中的教育学被广泛引进和普遍实践的前提,是教育学在我国发生、发展、实践的最根本动力。
在强国、救国的使命感的激励下,他国教育学开始了其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激进主义路径的本土实践。这里的自由主义路径指的是借重科学、民主、自由、个人权利等西方文化价值的启蒙,以实现中国文化教育的改良。尽管当时的自由主义阵营中也有如易白沙、吴虞、胡适、陈序经、丁文江、吴稚晖等人主张全盘西化式的文化教育改革,但总体而言,那时的全盘西化的主张是胡适所谓的文化教育改革的“取法乎上,仅得其中”的策略。与自由主义路径不同,以章士钊、梅光迪等为代表的保守主义者主张中国文化教育建设应走保守主义之路,即应走一条既能安顿传统,又能与时俱进、推陈出新之路,应采取在保守传统中革新更化的演进方式;它不反对引进西方文化,但强调应融西学于中学之中以实现中西文化教育的调和。所以,它既反对将全盘西化作为文化教育变革的手段,更反对将全盘西化作为文化教育变革的目的。不同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路径的文化教育变革主张以渐进性变革的方式来实现文化教育的改良,当时由左翼意识形态占支配地位而引发的激进主义路径的文化教育变革主张“纲常革命”、“圣贤革命”,强调通过革命性变革使文化教育等社会问题一并得以终极解决。这种路径的文化教育变革的主张后来渐次发展为强调政治、文化教育的变革取法苏俄革命的道路和学习苏俄创造的新文化。上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路径的教育学本土实践具有以下特点①本文对激进主义路径的教育学本土实践的特点之所以不作详论是因为我国教育学者,如瞿葆奎在他的《中国教育学百年(上、中)》(《教育研究》1998年第12期、1999年第1期)、李涛在他的《借鉴与发展 中苏教育关系研究1949—1976》(浙江教育出版社2006第1版)中,对此都做了较充分的论述。:
1.多样化
这里的多样化包括教育学本土实践的取法对象和途径的多样化两个方面。一是实践取法对象的多样化。新中国成立前,我国不仅引进或译介了日本的教育学,还引进了德国、美国、法国等国的教育学。引进的对象不可谓不多样。就依照他国教育学而开展的中国本土实践而言,也是如此,取法对象是多样化的,“今日取法日本,明日取法美国,今日采取严格主义,明日又采取放任主义,任何制度都试过……”[1]19这在胡适看来属“没有胃口”的“浅尝而止”现象。但是,这种“浅尝而止”现象却成就了教育学本土实践的取法对象多样化的结果。二是实践途径的多样化。他国教育学本土实践除了师范院校的教育学教学这一基本途径外,还有通过自主办学以试验他国教育理论、依照他国教育理论进行教育教学改革等途径。
2.自主性
教育学在我国的出现,最初以译介为主,后来自主性逐渐增强。这一是体现为国人自编的主要作为师范学校教育学课程的教材之用的教育学文本越来越多,“从量上看,几十家出版社或机构出版了本国学者编著的七八十种版本的教育学”[2]。国人自编的教育学教材既一定程度地综合了国外教育学知识,也对他国教育学知识作了适合中国文化语境和教育实践的“过滤”、转化,或者说我国教育学者在自编教育学教材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结合国情对原作作了变通。[2]二是体现为本国学者对教育学的自主建构。例如,“教育学家吴俊升、王西征编著的《教育概论》融合国内外各家,自成一家[2]”。国人的诸如此类的自主努力成为他国教育学在我国广泛和有效实践的前提。
3.多元化
当时将他国教育学作本土实践的主体是多元化的,既有外国传教士和日本人等在内的外国人,也有归国留学生、师范生、教育学教师。(1)传教士。最早将西方教育论著引入我国的是外国传教士。并且,外国传教士也将外国教育思想、理论实践于他们在我国举办的教会学校。(2)日本人。日本人对教育学本土实践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1899年,由日本人剑潭钓徒节翻译的奥地利教育学家林度涅尔的《教育学纲要》是我国最早的教育学译著。再有,我国师范学校曾经一度设日本教习,由日本教育学者向我国师范生讲授教育学。(3)留学生群体。当时,我国有一大批赴日、法、美、德等国的留学生,其中不少是专门学习他国教育学的。留学生回国后,有的通过翻译传播自己在国外所学的教育学知识,有的则直接参加教育实践,在实践中践行和宣传外国教育学理论。[3]73可以说回国留学生群体是教育学本土实践最积极的分子。蔡元培、张伯苓、陶知行、郑通和等是这一群体中的佼佼者。(4)师范生。我国自己培养的师范生是当时教育学本土实践的主体。我国最早出现的教育学文本形式多是直接翻译、编写的教材,而较少教育学专著。之所以会这样,是为了满足师范学校的学生学习教育学的需要。因而,当时的教育学本土实践一定意义上是教材教育学知识的本土实践。(5)教育学教师。当时有一大批西方教育学理论造诣较深的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师寻找机会到地方中学从事教育实践。例如,东南大学的汪懋祖、姜琦、程湘帆、郑晓沧、孟承宪等人[4]便是如此。这些人中的许多人成为既有较高的教育理论水平,又有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的教育家。
4.全面化
在当时,通过翻译国外的教育学著作,创办刊物刊载教育学译著,留学生以及来华外国人(如杜威、罗素等)的直接宣传、演讲等,教育学知识得到较广泛的传播,以至“建国以前,西方教育的所有科目在中国已基本上能找到,西方各类教育理论论著总是被很及时地译成中文出版或是刊于各类杂志上”[5]67。在教育学知识得以较广泛传播的同时,那时既有实验教育学、国家主义教育学的本土实践,也有实用主义教育学的本土实践;既有借鉴他国教育理论和实践经验而开展的普及教育、公民教育(又称国民教育)的本土实践,又有专门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农村教育等本土实践。
5.自由化
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虽然出现过后来的国民党的训育和党化教育期,但总体上,那时的我国文化教育环境是较为自由的。例如,国外的教育学可任人翻译,毫无限制;对教育学知识的传播、践行,无意识形态禁区和行政干预,人们运用教育学理论对教育问题的讨论绝不至于因为某种禁忌而藏着掖着;教育学者“该批评政府的,便批评;该警示教育界的,便警示。既无党派之争,也无山头意识,清清净净,就事论事”[1]10。
体现以上特点的教育学的本土实践取得了显著成效。这一是体现为那时人们青睐的教育学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得以实践。例如,“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对于我国中小学教学实践方面曾经产生过的影响,几达半个世纪之久”[2];杜威的教育学在教育实践界产生了很大反响,“当年,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写在许多中小学的墙上,挂在许多教育界人士的嘴上,成为时髦”[2];由克伯曲将杜威的问题教学法推演成的设计教学法在我国不少地方得以应用。[2]二是体现为教育学理论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教育和社会政策。例如,就教育学之公民教育理论的实践对政府教育政策的影响而言,“政府不但在各级学校开设‘公民’课程,‘公民教育’一词亦变得相当流行,官员向公众演讲‘公民常识’亦很常见。是故,‘公民’一词作为行政程序的运用越来越多,如‘公民训练’、‘公民登记’、‘公民宣誓’亦成为不同时期的政策内容”[6]。诸如此类的新的教育和社会政策的出现,对教育和社会的改造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不仅如此,那时涌现出了一大批有抱负、教育学理论水平较高和实践经验丰富的被今人赞誉为“民国范儿”的教育家。西方教育学经由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路径的本土改造而形成的本土化的自由教育或博雅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和由此形成的欧美化的大、中、小学的自由教育制度,至今为人们所称道和念想,被视为今天教育改革的楷模、成功范例;对中学与西学、地域性文化与世界性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自由传统与西方文化教育的自由主义作会通与互补而在当时被誉为中华民族之光、“民主堡垒”、“自由堡垒”的“西南联大”,被今人视为大学的精神“教父”。可以说,与其他外国理论的本土实践相比,当时教育学理论的本土化效果是最好的,“在外国理论与本国实践相结合这一点上,从西方传入的其他现代社会科学学者在导入阶段就没有教育学者做得好”[4]。
在所有的教育学中,实践效果最好的教育学莫过于批判教育超政治、超阶级、将教育作为革命的手段、培养革命人才的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这似乎具有必然性。因为风起云涌的革命派从当时复调的社会变革的文化场景中“异军突起”,成为“大革命”者而掌握文化的话语权。因而当时文化革命主义或文化激进主义相对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是优势话语,它远胜于改良主义式的“小革命”主义。当时,文化激进主义影响下的对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学习和本土实践不是如胡适所说的中国人对外国文化“没有胃口”,而是“很有胃口”。被誉为崭新的科学知识且深感“很有胃口”的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及其本土实践一路高歌猛进,至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期(即1949年至1956年)在中国大陆占绝对优势地位。
尽管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学本土实践的成效是显著的,但那时教育学本土实践的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就其不足,可作如下列举:一是教育学本土实践存在忽视本国社会实际和文化教育传统的现象。尽管当时有章士钊、吴宓、梅光迪、杜亚泉、梁漱溟等人努力寻找一条既能安顿传统又能与时俱进、中学与西学合璧、“自由与传统的会通”、“意识重叠”的或保守主义路径的文化教育演进方式,但教育学的本土实践仍存在对他国教育理论“不暇作审慎之抉择”[7]而忽视本国社会实际和文化教育传统之弊。民国时期的出版家、教育学家舒新城就这种弊端做了较全面的检视。他说:“清末改行新教育制度以来,一般教育家、政治家不明此种情形,只努力于模仿工商业国家的教育制度,一面将学校教育工厂化,而以整批生产的方法出之;一面将中等以上学校集中都市,而使乡村青年不能不向都市求学。此种整批制造的学校教育制度,原是欧洲工业革命社会环境所造成的,我国社会至今还是小农制度,社会环境本无此驱策,而贸然行之数十年,以至弊端百出,现在则此种不合人性的教育的制度,在欧美日趋衰败(美国教育家组织之Progrissive Education,与世界教育家组织之The New Era两种季刊,抨击现教育制度与提倡个别教育学的文章极多),中国仍然竭力提倡,而将中国旧日书院制、私塾制的师生的人的关系与独力自学的精神完全不顾,已算失策。……所以三十年来新教育在数量上可言成绩者只有都市的教育,内地乡村则反而日趋日下。”[1]226舒新城在此对教育学本土实践的弊端所作的检视是有鲜明的针对性的。二是教育学本土实践在注重实现强国、救国的目标的同时,较为忽视个体的发展。当时的公民教育、普及教育、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平民教育思想和实践都将服务于社会、特别是政治视为第一位的,而将促进个人发展视为第二位的,是从属于、服务于社会的,即成人、成民是为了成国。例如,就公民教育而言,公民这一概念的核心旨趣是作为公民个体的公权,但是,“相对而论,在南京政府统治时期中日矛盾日益尖锐化的氛围中,强调人民公权的‘公民’概念也多被更带民族主义意涵的‘国民’一词所取代。在当时的战争语境下,它亦意味着对民众有更强烈的义务责任要求”[6]。这里,之所以将这种情况当作一个问题,是因为它属于李泽厚所谓的“救亡压倒了启蒙”的总问题。这一总问题即“救亡的局势、国家的利益、人民的饥饿痛苦,压倒了一切,压倒了知识者或知识群对自由平等民主民权和各种美妙理想的追求和需要,压倒了对个体尊严、个人权利的注视和尊重”[8]33。三是教育学本土实践总体上对促进教育向现代性转型无甚起色。教育学本土实践是后发型现代化国家的现代性发展的必要构成,其根本目的是促进人的发展形态的根本改变。就我国而言,这种改变应是将过去教育培养有着由士而谋仕的心性品质的人转向培养农、工、商等各行各业的合格人才、社会的合格公民。但总体上,当时的教育学本土实践对促进教育向现代性转型的作用不大。这正如民国时期的政治学家楼桐孙所指出的:“学校里面出来的人,依然是些农学士、工学士、商学士,依然脱不了是士,而并非农、工、商,照以前的教育,农、工、商如果都进学校,进去以后,就很少回到本业的,一定弄到田中无农,厂中无工,市中无商为止,那就是国中无民了。还能成为国么?所以像那种教育,不幸而普及,惟有亡国而已。”[1]38
二、开放改革时期的教育学本土实践
对外开放是他国文化本土实践的基本前提,是他国文化在本土获得认同、引进、借鉴、吸收、实践转化的肇端。教育学的本土实践也不例外。一百多年来,教育学本土实践经历了开放、封闭、开放三个时期,即上文述及的从教育学最早出现于中国大陆到新中国成立的开放时期、1949年到“文革”结束的闭关锁国时期、20世纪70年代末至今的开放改革时期。这三个时期的两次开放是两种性质不同的开放。前一次开放属国家主权受侵害情势下的被动开放,后一次开放属主权在我的主动开放。主动开放期的教育学本土实践的总体样貌,可从如下几个侧面进行刻画。
1.全方位、宽口径引进、翻译出版外国教育学
这一时期,我国对外国教育学呈全方位、宽口径开放态势,翻译出版了大量外国教育学教材和理论著作。从过去的教育学发展中心——英国、法国的教育学到新近的教育学发展中心——德国、美国的教育学,从西方国家的教育学到东方国家日本的教育学,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学到社会主义国家苏俄的教育学,都做了翻译出版;从实验教育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精神科学教育学、实用主义教育学到存在主义教育学、批判理性主义教育学、解释学教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教育学、后现代主义教育学等影响较大的外国教育学理论流派的著作,也都做了翻译出版。另外,还翻译出版了一批作为国际组织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著的教育学论著。这些教育学教材和著作的翻译出版为教育学本土实践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自主编著了一大批教育学教材和著作
这一时期我国教育学者编著了一大批供师范生学习和教师培训之用的正式出版的教育学教材和教育学专著、教育学丛书。例如,在教材方面,出版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育学教研室主编的《教育学讲授提纲》(1980),“五院校”协作编写的高师本科公共课《教育学》(1980),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编的高师教育系基础课程《教育学》(1984),顾明远、黄济主编的中等师范学校《教育学》(1987),扈中平主编的作为高师本科公共课教材的《现代教育学》(2010),供教育学类本科生使用的袁振国主编的《当代教育学》(2004)和柳海明主编的《现代教育原理》(2006)等;在教育学著作方面,出版了厉以贤主编的《现代教育原理》(1988),成有信主编的《现代教育引论》(1992),陈桂生的《教育原理》(1993)、《“教育学视界”辨析》(1997)、《回望教育基础理论——教育的再认识》(2008),孙喜亭的《教育原理》(1993),黄济、王策三的《现代教育论》(1997)等。这些教材和著作迥异于以往以政策汇编、政策诠释学、语录学为模式的教育学。同时,这些教材和著作在具体内容上具有自主性强,同时又思想解放、放眼世界、四海择珍、广泛搜集教育信息等特点;西方国家、日本、苏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著的教育学教材、著作中的理论、思想,都不同程度地在我国学者自主编著的教育学教材和著作中得以体现。
3.“跑马场”现象较为明显
这里的所谓“跑马场”现象是指我国教育学者在论说教育时存在的因尊奉西方教育学而导致的充斥西方教育学理论话语的现象。这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青年学人们似乎是若不频频引述西方学者的概念与观点便不足以展开任何问题;在自己的论著结尾不开列一长串西方参考文献目录便不足以表明论著本身的思想深度与学术蕴涵,以至于到了张口西方学者、闭口还是西方学者的地步,否则,便几乎处于完全‘失语’的状态。而细细地研读之后,这些学人的论著中除了对西方学者的概念与观点的引用、转述或‘阐释’之外,确实也别无他物,他们充其量只是扮演了西方思想的消费者、西方学者的代言人的角色。”[9]
4.教育学中国化的自觉意识不断增强
教育学中国化或本土化问题是我国自有教育学以来教育学界一直关注的问题。例如,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教育学中国化思想就从“经验层次”上提出来了;但是,“逐步深入地研究教育学中国化是建国之后……”的事情。[10]新中国成立之后,教育学中国化意识较以往更为自觉,且不断增强。20世纪50年代,教育学界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苏联教育学与中国教育实践相结合的新中国的教育学;60年代,教育学界提出要建设总结自己的经验、整理自己的遗产、有选择有批判地吸收外国教育学的中国的教育学;80年代,教育学界又提出了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的任务。本世纪以来,教育学界的教育学中国化的自觉意识空前增长。这体现为教育学界从教育学如何中国化到如何创建中国教育学进行了较广泛、深入的探讨。其中有学者主张应创建具有中国特点、中国气派、中国元素、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教育学;有的学者还倡导教育学的原创性,认为我国教育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原创性都不足,存在着针对其他学科和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失语现象,因而主张应将原创性研究作为建设中国教育学的必由之路。
5.出现了完全否定教育学本土化的极化思想
“教育学中国化源起于对外来教育学的思考,是中与外的问题,是教育学领域中的中外关系问题。”[10]一直以来,建立新中国的教育学、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和建设中国教育学等诸如此类的议题,教育学界均是将它们作为教育学领域中的中外关系问题而从中外既相对举、又勾联的角度来论说的。但本世纪初,却出现了完全否定探讨教育学中国化或本土化与外国教育学相勾联,甚至否定教育学本土化议题的极化主张。例如,有人认为所谓教育学本土化“‘实际上是一个自内的文化殖民过程,与其说它是非西文化的复兴,倒不如说西方文化真正开始了对非西方文化的浸淫’。在精英文化层面,本土主义知识分子所竭力倡导的‘本土化’,却恰恰是要让西方文化合法地深入本土文化的骨髓中去”[11];“如此一来,披着中国化外衣的西方教育学理论不仅不能指导中国实践,而且彻底‘入侵’中国教育学,中国教育学在‘西化’中消失。”[12]59显然,这种将教育学本土化视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入侵”的极化主张与民族的“创伤记忆”有关,而“创伤记忆”是我们的历史教育和“东方主义”这一西方国际政治关系理论影响的结果。
开放改革时期教育学本土实践可谓成绩斐然。这一时期,由于对外国教育学做了全方位、宽口径的译介,加上外国教育学的理论、思想在我国学者自主编著的教育学教材和著作中得以一定程度的体现或引用,因而增进了人们对外国教育学理论的了解;并且经由教育学的教学,柏拉图、洛克、斯宾塞、卢梭、福禄倍尔、裴斯泰洛齐、蒙台梭利、苏霍姆林斯基、赞可夫、巴班斯基、杜威、布鲁纳、布鲁姆等人的名字及他们的部分理论、思想主张,对很多中小学教师来说,可谓耳熟能详。将外国教育实践经验和理论作本土化改造而开展的教育改革实践也在一些地方出现。例如,东部地区有深圳中学在王铮“主政”时期参照外国教育理念的以“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为目标而开展的教育改革实践,西部地区有成都华德福学校以奥地利科学家、教育家施泰纳的教育理念而开展的教育实践。一些国际教育理念也深入人心。例如,在中小学的建筑物上,除了“三个面向”字样外,标立最多的恐怕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著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提出的教育的“四大支柱”——“学会做人、学会做事、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及与此类似的字样了。在高校,西方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和通识教育、博雅教育理念得以一定程度的实践。受西方教育研究方法的影响,“在教育研究中运用客观化、数量化、形式化方法的风气在一些方面初步形成”[10];行动研究等质性研究方法在一定范围得以普及。
有关教育学本土实践的成效,我们还可作其他列举。但无论怎样,教育学本土实践的成效可以说总体上是不尽如人意的,没有取得人们所预想的在主动开放期因更为开放所带来的更加显著的成效。这集中体现为对他国教育学的引进与借鉴、吸收、实践转化相差悬殊:对外国教育理论的关注、引介多,而借鉴、吸收或基于本土脉境、本土实践的对他国教育学的再赋义、再改造而开展的实践转化少。在主动开放期,虽然出现过一些借鉴外国教育学理论而开展的教育改革和试验,但没有出现如被动开放期那样的较大范围的对外国教育理论的长期追慕和实践,也没有产生如被动开放时期那样的借鉴外国教育学理论进行教育改革而成长起来的一大批教育家。与被动开放期相比,主动开放期的教育学本土实践的效果不好说就一定比被动开放期的效果更差,但一定不比被动开放期的效果更好。
三、新时期教育学本土实践成效不足的审视
以上对主动开放期的教育学本土实践成效不足的这些判断,如属不谬,那么,在笔者看来,其原因除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两者有效互动的体制、机制存在瑕疵和由外在干预而形成的“去专业化”的教育价值取向使教育学者和广大教师遭遇无法借鉴、吸收、实践转化外国教育学理论的阻力外,还可作如下审视:
1.局囿于个性的教育学中国化取向导致对他国教育学的选择性忽视,使教育学的中国化、本土实践的共性、时代性不足
教育学的本土化或创建本土教育学,“可有几种抉择:一是排他性的本土教育学;一是人类教育文明背景上的本土教育学”。“所谓‘排他性’的本土教育学以一国文化排斥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价值,或者以一国文化为标准裁剪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价值,这是一种狭隘的民族观念和文化保守主义,不利于教育学的发展”[13];“所谓‘人类教育文明背景上的本土教育学’,是以人类共同文化为基础,立足于本民族的教育文化遗产,享受国外的优秀文化,形成有民族特色的本土教育学”[12]57-58。显然,创建本土教育学的合理选择应是“人类教育文明背景上的本土教育学”。而要成就“人类教育文明背景上的本土教育学”,“我们不能脱离当代高度发展的世界这样的背景来考察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学问题。在建设我们的教育学时,必须采取开放的、面向世界的政策。在我们所建成的教育学结构之中,共性的因素应显得更为突出。”[14]就此而言,建构“人类教育文明背景上的本土教育学”应不断增加“共性”因素,以使共性因素更加突出。尽管相对于1949年到“文革”结束的闭关锁国时期,“80年代以来也许可以认为不少教育学在共性寓于个性之中的中国化道路上毕竟不断取得了一些新的进展”[10],个性中的共性比过去更为突出了,但是,在当今由全球化而衍生的全球共同的社会实践背景,包括教育实践背景不断增加的形势下,教育学的中国化、本土实践的共性、时代性,可以说还显得相当不足。而之所以共性、时代性还相当不足,原因是囿于个性的教育学中国化取向导致对他国教育学的选择性忽视。
我们知道,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转型离不开从属于、服务于也反作用于社会转型的教育转型或教育改革。而教育改革需要教育理论,包括需要经由借鉴、吸收而形成的本土化的他国教育理论的指导。但现实中,教育理论,包括他国教育理论未为教育改革、教育转型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就基础教育的课程教学改革而言,在新课程改革即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八轮“新课改”逐步展开以后,“人们越来越觉得教育学教科书对中小学普遍关注的课程改革反应迟钝。其中有的人甚至诊断如今通用的教育学大抵还是‘凯洛夫《教育学》的那一套’”[15]32。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国教育学多年来对英美国家从关注一种课程形式转向关注多种课程形式、从关注“教程”转向关注“学程”、从关注如何教转向关注如何学、从关注教与学的手段转向关注课程目标及课程评价的“敏感程度相当有限”[15]36。而教育学之所以会出现“敏感程度相当有限”的状况,不是因为教育学界对国际上教育学在课程教学论方面所发生的种种“转向”缺乏了解,而是因为强调走自己的路或囿于个性的教育学中国化取向导致对外国教育学理论的屏蔽或选择性忽视。多年来,与课程教学的改革相类似,我国教育改革的其他领域也不同程度地遭遇这种选择性忽视现象。而正是由于对他国教育学的选择性忽视导致教育学的中国化呈强个性—弱共性(转化)、强保守性—弱时代性格局。这种格局一定意义上可视为对“跑马场”现象矫枉过正的结果。
2.由过度发展的经济民族主义而产生的文化教育上的优越感,使教育学者和教师对他国教育学理论的了解和学习与教育的本土改造不甚相干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抓住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机遇,经济获得高速发展,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高速的经济发展不仅极大地提高了国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且对国人的文化心理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经济民族主义开始兴起,并逐渐成为国人审视自身的一种普遍的弥散开来的社会意识。这里所谓的经济民族主义指的是由高蹈的经济成就而产生的爱国主义。如今,经济民族主义已然替代以往的政治民族主义或政治爱国主义的地位,成为占主导地位的爱国主义形态,并且呈过度发展的态势。“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泰山而小天下。现代人登喜马拉雅山而小东亚,登月球而小地球。站得越高,看得越远,自己就相对地显得越缩越小。”[16]48但在过度发展的经济民族主义的主导下,国人中的一部分人在审视自己时已“不登山”,缺乏从世界来看中国的高度,往往只是从中国来看中国,甚至只从中国来看世界。因而,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一种文化教育上的优越感和自负心理,将自身文化教育看作是优越于他国的。这种认识的理据是我国之所以会取得辉煌的经济成就、我们的物质生活之所以更加富裕是因为我国的政治、社会更为优越;就教育而言,不仅我国基础教育是更为优越的,甚至有人认为我国的高等教育也是更为优越的。既然我国的教育是更优越的,那么,学习和实践他国教育理论纯粹就是多余的;否则的话,会拉低我国的教育质量。
经济民族主义与其他形式的民族主义一样,有助于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团结、增强民族自信心、激发人们建设国家的积极性,但在社会总体稳定的时期,过度发展的经济民族主义与其他形式的过度发展的民族主义一样,其消极性是十分明显的。由过度发展的经济民族主义生发出的“一好百好”的文化心理封闭了一部分人的对外开放的意识,闭锁了一部分的精神、心灵,以致在一些场合张扬国外教育理论者会被扣上“言必称美”的右倾主义、自由主义的帽子,以致一些付出了高额经费的教师赴美、英、法、德等国的教育考察、学习成了单纯的“国外游”而与教育的本土改造不甚相干。
历史传承性、自觉能动性、时代性是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世界各民族之间相互交流、相互引进、相互吸收、相互促进的开放性也是民族精神的基本特征。相对于被动开放期,主动开放期的民族精神的开放性应体现得更加充分。但实际上却不尽然。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吊诡。上述由“创伤记忆”所导致对教育学本土化议题的完全否定,一定程度上使这种吊诡现象得以强化和合理化。
3.文化相对主义成为接纳他国教育学理论、进行本土实践的障碍、壁垒
新中国成立前,他国教育学的引进和自觉实践,在文化上是由于那时国人较普遍将日、美、法、英、德等国的文化视为文明演进论意义上的上位文化。与作为上位文化的他国文化相比,中国文化属落后的下位文化。因而改变中国文化落后乃至整个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必须“谦逊低头”,借鉴、学习作为上位文化的他国先进文化。尽管这一定程度上是导致当时教育学本土实践忽视本国社会实际和文化教育传统之弊的原因,但这也是当时他国教育学本土实践的基本文化动因。而自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结束前,这种文化动因因将资本主义文化视为落后的、腐朽的、必然消亡的人类文化而完全消失,并且在激进革命的过程中,还刻意涤荡新中国成立前所受资本主义文化教育理论的一切“不良”影响,过去教育学本土实践所取得的欧美化成就皆被彻底否定和祛除。例如,对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及其实际影响大加挞阀、彻底清除;再如,大学彻底摒弃了欧美化的通识教育而采行苏俄式的专业教育,并将民国时期形成的自由教育制度改造成集权式的大一统的公办教育制度。对西方资本主义教育学及其本土实践的否定,加上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对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代表的苏俄式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批判,使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教育学只剩语录教育学、政策教育学,教育学的实践只有语录教育学、政策教育学的实践。“文革”结束后的80年代,由于全国上下都处于长期封闭后的对外开放的兴奋期,上位文化与下位文化、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的意识又如民国时期那样成为经济社会改革的基本社会意识,向他国先进文化,包括教育理论学习成为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思想动力,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正因为如此,整个80年代被人们称为“文革”结束以来中国改革的黄金时期。
但好景不长,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国力的增强而产生的文化自觉意识日益突显,文化相对主义开始兴起。在文化相对主义看来,文化是相对的,是不分高下的,是“各美其美”“各善其善”“各德其德”“各行其是”的,因而不存在所谓的“普适价值”。文化相对主义的认识论一种典型形式是国情论。一方面,在国情论者看来,他国教育学理论是不适合中国的,因为中国有中国国情;另一方面,在国情论者看来,凡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无论其性质、意义如何,无论合理与否都是合乎国情的,且皆为合理的。例如,在一些人看来,教育行政管理的非法治化,学校管理的官本位、官僚化、非民主化,等等,皆为合乎中国国情的,因而皆为合理的,或者说它们是合理的,是因为它们是合乎国情的,因而是无须改造的。对这种现象,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教育家艾思奇先生曾评论道:“近代中国的一切反动思想,都有着一个特殊的传统,如果要给它取一个名字,那也许可以叫做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它)强调中国的‘国情’,强调中国的‘特殊性’,抹煞人类历史的一般的规律,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只能依循着中国自己的特殊规律,中国只能走自己的道路。……即便退一步说,有某些外国的东西可以学习和接受,也应该以保持中国旧有的东西为基础……也就是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立场上学习接受。”[17]471-472在国情论的文化主张的主导下,“普适价值”被否定,他国教育学理论被忽视、受抵制和排斥;在国情论的文化主张的主导下,中国教育以合乎中国国情的一整套价值来抵抗他国教育学理论及其所申张的价值,成为与他国教育学理论所疏离的教育。可以说,建立在文化相对主义基础上的盲目的对国情的维护已成为我们接纳他国教育学理论,进而进行本土实践的最大障碍、最顽固壁垒。
阻碍他国教育学理论本土实践的文化相对主义与上述过度发展的经济民族主义两者相互为用、互为前提、相互加强,聚合为主动开放期我国教育向他国教育学理论开放,进而作本土实践的巨大阻力。
4.教育行政化阻遏了学校教育者将教育学作本土实践的人格力量
民国时期,既使在被今人视为大学精神“教父”的西南联大这样的大学,也有人如沈从文所说的,只要有机会,就“……挤进银行或相近金融机关作办事员”,“……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高的认识”[18]79-80。但民国时期的教育学者、实践教育理论的教育家或“民国范儿”,普遍具有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即有修、齐、治、平的志向,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格理想,具有充当中流砥柱的主见与风骨。当他们在面对国家贫、弱、愚、私、散的现实和亡国亡种的危机时,他们的精神品格便生发出“建国以教育为先”、文教救国、通过学校作育新民、造出新的社会的抱负。这种抱负成为他们将教育学作本土实践的人格力量。这种抱负及由此产生的实践热情是那时教育学本土化取得一系辉煌成就的精神力量,而那时教育学本土实践的诸种不足,与他们的人格、精神无关。但现今的“管办评”不分所造成的教育行政化遏制了学校教育者的应有的人格精神。受以往计划经济模式和管控型的教育行政体制的影响,我国目前大、中、小学与教育职能部门之间的关系仍是一种过度的纵向支配关系,大、中、小学仍处于外控的管理模式之下;相关职能部门越权、扩权、集权,代替学校管理教育,对学校管得过多、过细、过于简单的现象较为严重,以致学校难以依法自主办学,难以成为真实的自主办学实体。正因为这样,现今每所学校的教育者的大脑一定意义上不是长在自己的肩膀上的,而是长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首脑的肩膀上的。既然学校教育者的大脑是长在别人肩膀上的,他们也就不可能真正按照自己的教育思想、理念、价值主张来办学和行教。学校领导者只能依照行政命令办学,学校教师只能依照行政性计划来教学。尽管他们掌握了较为丰富的教育学理论知识,但他们所掌握的教育学理论与他们的教育实践属“两张皮”。例如,现今,相关职能部门、中小学和广大教师较以往更加重视教师继续教育。这本是好事。但我们却会发现这样一种现象:一方面,教师继续教育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越来越频繁;另一方面,教育教学质量总体上却未有大的改观甚至无任何改观。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管办评”一体化的体制下,教育职能部门以学生考试分数为唯一标准的教师绩效评价使教师难以将继续教育所习得的教育学,包括外国教育学理论运用于教育教学,教师继续教育所取得的成效难以转化为现实的教育“生产力”。因为对教师个人和学校来说,只有遵从教育职能部门的评价才是最保险、最稳妥的,才合乎上级领导的要求。
所以,教育行政化在使教育实践与教育学理论严重疏离的同时,使教育实践成为长官意志的实践,成为令人眩晕、使人异化的权力的实践,而不是教育学理论知识的实践(因为权力成了知识),以致教育者成了得过且过、没有理论和价值信持、恢诡谲怪、因是因非、无可无不可的“犬儒”,以致无论教育者有着怎样丰富的教育学理论知识、多么富有聪明才智,他们却没有发挥理论作用的空间,他们的聪明才智被用来追求“升学率”和“升重率”,用来扼杀学生独立思考与个体觉悟。
四、余论
发生于新中国成立前的教育学本土化是复调的,它由三个文化思想谱系汇合而成。它既有以穆勒、杜威等功利主义(实用主义)以及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等人的思想作为思想资源而形成的自由主义,也有主张中西文化调和的文化保守主义,还有受法国大革命和俄国“十月革命”影响而形成的文化激进主义。无疑,这三个文化思想谱系都缘起于当时的对外(被动的)开放,其中的文化激进主义也是依托社会的对外开放而生成的,并一定程度上进一步促进了文化教育的开放和教育学的本土实践。这其中最为典型的当属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学的本土实践。在苏俄“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李大钊、毛泽东等“在介绍、宣传马列主义的同时,开始全面地批判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教育,开始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为争取工农受教育的权利而斗争”[19]190;在“五四”运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积极领导工农运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同时,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批判地继承了古今中外的教育遗产,大力从事革命骨干的培养和广大工农群众的教育工作”[19]201。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指导下的各个时期的教育工作或教育实践,提高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和革命觉悟,培养了大批革命领导干部。但是,由新中国成立前延续至成立后的激进主义曾经一度是在封闭的环境中发挥作用的,并在封闭中变得异常激进。这种异常或过于激进的激进主义阻隔了文化教育的对外开放。
现今,尽管激进的年代早已过去,但并不意味着我们就走上了敞开心扉的真正的开放之路。上述局囿于个性的教育学中国化取向导致的对他国教育学的选择性忽视、经济民族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共同熔铸为一种主动开放的新时期的文化保守主义,即保守封闭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主义”使现今主动开放时期的开放一定意义上是形式上的而非实质的开放。因而对我们来说,要促进教育学的本土实践,需要祛除形形色色的保守封闭的“保守主义”而倡导保守开放的保守主义。这种保守开放的保守主义要保守的是新中国成立前和20世纪80年代向他国教育学开放的传统。这样,如今主动开放时期的开放就会是实质性的开放,就会是精神、心灵的开放,进而就能化解现今主动开放期并不比被动开放期更开放的这样一种不应有的反常,就会开掘出一条教育学本土实践的更富成效之路。
当然,由保守开放而形成的实质性开放不是由开放而失去自我,而是在向他国教育学开放而进行的本土实践中更好地成就自我。因而这里所谓开掘出一条教育学本土实践的更富成效之路不是东方主义和后殖民主义论所揭示、批判的西方对东方的扭曲式、控制式的本土实践之路,而是对话式的教育学本土实践之路。这一教育学本土实践之路是我国教育学者基于我国本土教育的历史与现实思想资源与他国教育学之间的对话式实践之路。采行这样的道路的教育学本土实践是主权在我的具有高度自主性的实践,是与我国社会、教育转型要求和社会环境、文化教育语境相适应的比较而非比附的实践,是“世界性”与“对话性”相结合的互动、互证、互补式的实践。
参考文献
[1]许骥.给教育燃灯[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2]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上)[J].教育研究,1998,(12).
[3]郭瑞迎.中国教育知识生产研究(1901—1937)——基于“互动仪式链”的视角[D].广州:华南师范大学,2015.
[4]黄国庭.民国时期教育学者的中学办学经历及其对教学与研究的影响[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4).
[5]金林祥. 20世纪中国教育学科的发展与反思[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
[6]冯筱才.近代中国的“僭民政治”[J].近代史研究,2014,(1).
[7]朱家骅.教育部九月来整理全国教育之说明[J].教育周刊,1933,(142).
[8]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
[9]吴康宁.“有意义的”教育思想从何而来——由教育学界“尊奉”西方话语的现象引发的思考[J].教育研究,2004,(5).
[10]瞿葆奎.中国教育学百年(下)[J].教育研究,1999,(2).
[11]项贤明.教育:全球化、本土化与本土生长——从比较教育学的角度观照[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2).
[12]冯建军.教育基本理论研究20年(1990—2010)[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2.
[13]陈桂生.略论教育学“中国化”现象[J].教育理论与实践,1994,(4).
[14]鲁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学管窥[J].教育评论,1988,(1).
[15]陈桂生.回望教育基础理论——教育的再认识[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6]周有光.地球村需要村民教育[M]//周有光.拾贝集.北京:世界文献图书出版公司,2011.
[17]艾思奇.艾思奇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18]沈从文.云南看云[M]//沈从文.沈从文文集.香港: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
[19]车树实.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史初稿[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罗雯瑶]
作者简介:吴全华(1964— ),男,江西永修人,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教师教育、基础教育改革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人性的教育学意义及教育人性化的实践策略”(项目编号:BAA13007)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16)02-0068-11
收稿日期:2015-10-08
A Brief Discussion of the Practice of Foreign Education Theories in China: History and Reality
WU Quan-hua
( School of Education Science,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31, China )
Abstract:Nationalism, containing the will to save and revive the nation, is the basic driving force of the introduction and common practice of foreign education theories during the period of “ introducing western learning”. The national practice of conservative and liberal education theories is diversified, independent,comprehensive, and liberal. With these characteristics, it has made great progress. However, challenges such as unreasonable localization of foreign education theories, cultural relativism, economic nationalism, and the subjection of education to executive administration are hindrances to the Chinese practice of foreign education theories. If reasonable conservatism in cultural education, which is absent today, re-emerges, a more liberal and effective practice of education can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education; native practice; educator; cultural relativism; economic nationalism
——《教育学原理研究》评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