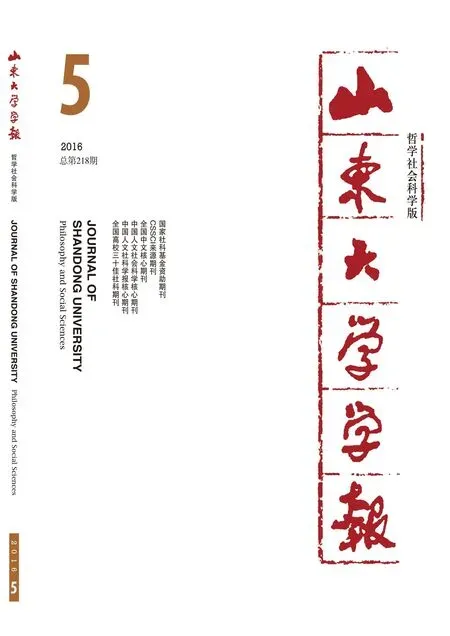对波斯纳和法律经济分析的一个争辩式解读
——兼与林立先生商榷
王博阳
对波斯纳和法律经济分析的一个争辩式解读
——兼与林立先生商榷
王博阳
林立先生的《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是目前华语世界唯一一部系统研究波斯纳的理论著作。然而,由于林书没有恰当地界定理性人假设和效率标准,也没有认识到波斯纳所追求的是社会成本视角下的机会平等而非分配正义,是潜在的帕累托而非实际上的帕累托改进,从而全书作为一个批判性的探究并不成功,没有完成推翻财富最大化的既定目标。而林立先生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作为替代性选择,在理论上没有实质的进步,而在操作性上却是一种倒退。鉴于波斯纳秉持实用主义而非本质主义的立场,这使得目前类似林立先生的观点没有真正超越波斯纳。
财富最大化; 分配正义; 效率; 实用主义; 成本
林立先生的《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一个批判性的探究》最先由我国台湾地区学林文化出版社于2004年出版,一年后上海三联书店发行了大陆简体版。林书自然成为国内大部分研究波斯纳和法律经济学的重要读物。然而遗憾的是,林立先生并非冷静理性地看待波斯纳的学说,该书三联版也省却了“一个批判性的研究”的副标题,“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作为一个中性书名,诱导了不少尝试了解波斯纳和经济分析的人误入歧途。而德国博士、教授、洪堡学者和上海三联背书等光环的加持,也使得该书的误读很容易变成正解。先入为主的成见有了,就很难再加以改变。不得不说,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法律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掩盖了波斯纳应有的价值。需要交代的是,我国台湾地区学者简资修先生早在该书一出版,就发现了书中存在的巨大问题,并为法律经济学做出了一个辩护式说明①简资修:《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一个辩护性说明》,《月旦民商法》2005年第8期。。然而,这篇简短的书评由于种种原因,被国内研究者所忽略,未见有直接引用。成书十年,林书引证不断,随着近年研究波斯纳和法律经济学文献的日趋增多,林立先生所代表的观点并不鲜见,而诸多“新林立先生”的出现为本文写作提供了现实意义。
林书写作目标很明确,就是要反复论证波斯纳缺乏人道关怀伦理价值,从而彻底否定经济分析作为法理论的正当性。着眼于这个目标,林立先生用大量篇幅论证了波斯纳提出的财富最大化及相关问题。其实,波斯纳提出财富最大化是美国上世纪七十年代论战的需要,当时很多学者已基于自己的知识传统对其进行了全方位的讨论,或许编一本批判波斯纳的著作并不是什么难事。在林书中,引用了来自法经济学内部如库特的商榷,也有如德沃金等非法经济学家对波斯纳的质疑。但有趣的是,在撰写本书前不久,林立教授刚完成了对德沃金的批判②参见林立:《法学方法论与德沃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正如简资修先生所指出的,在林立看来,敌人的敌人显然不是朋友,书中对于德沃金的批判,倒是很多也可以出自波斯纳之口③简资修:《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一个辩护性说明》,《月旦民商法》2005第8期。。一人而持两说,相互攻击必相互矛盾,这也使得林立先生的观点变得琢磨不定。而在全书的最后,作者并没有如读者所希望的,在完成“破”的工作后提出自己的构建,却只是推出了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不得不说,
对于本书的写作,林立先生只是用了一种比较的写法,有为写书而写书的嫌疑。尽管如此,林书确实集中展现了很多对波斯纳和法律经济学的疑虑,从这个意义上讲,它又是绝佳的分析范本。
一、理性人假设的前提性澄清


二、效率对公平正义的描述
在芝加哥学派看来效率作为一种法律标准来强调是无需争论的。而林书认为,波斯纳只考虑“低级趣味”的效率,连正义都不顾了。其实,做此批评的人,往往仅诉诸主观,并无一个客观的正义说法。实际上,正义本身就是一种托词:正义是一种地域性的概念,只有在特定的范围里才有具体的内涵,我们显然找不到一个能放诸四海而皆准的正义标准;而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正义也被赋予或填充了不同的内涵。正是由于时空的交错,自古以来对“正义是什么”这个问题一直众说纷纭。
由于正义无法真正解说清楚,导致处理正义和效率的关系成为一个古老的难题。然而,这个难题在很大程度上是人们假想出来的。正义与效率之间有着惊人的联系*大卫·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杨欣欣译,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第20页。。一个公平的方案通常是有效率的,一种追求效率的制度也很少会在哪个地方违背公平。也就是说,效率标准是一个比例上的概念,它意味着在比较中做出选择,在不同的选择中挑选最优方案。而法律的正义观念就是在长期历史中,在无数次社会博弈和选择中逐步形成的,而推动这种博弈的力量,正是建立在社会本位之上的效率标准*邓峰:《经济法漫谈》,《经济法学评论》(第4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3年,第75页。。可以说,社会效率是对正义的一种描述和具体化,正如波斯纳所言——效率是正义那个最普遍的定义*理查德·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蒋兆康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第27页。。如果从社会视角和长期眼光看,正义和效率就是相一致的,而只有过份注重个体短期利益时,二者才有可能发生冲突。林立先生显然没有搞清波斯纳或法律经济学关于效率的定义为何,他对效率的理解仅限于字面意义或个体视角的理解,进而“缺乏人文关怀”的效率观自然与其所提倡的正义标准不符。
可以说,法律经济学并没有抛弃公平正义,恰恰相反,经济分析是解说正义这个神秘主义概念的好方式。正义面向的多元性决定了公平正义永远都只能是针对某种特定情况的特殊理论,在不同语境下公平正义的含义必然不同。同时,解释框架的过剩也导致公平正义缺乏一个共同的选择标准。而在公认的经济学范式中,只承认两三个效率标准,这克服了正义评价标准多样化的问题,也能够获得更为科学的解释力*乌戈·马太:《比较法律经济学》,沈宗灵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4页。。波斯纳意识到,经济效率其实正是数个世纪以来,驱动法律发展背后那股隐藏的力量。公平是有价格的,被大众所接受的公平,只能是那些价格合理的公平。即使赋予个人权利是基于公平原则,但在实际做法上一定会面临成本收益的取舍。而法律上的程序正义、有限正义、迟到的正义非正义等提法亦是其表现。可以说,基于成本考量的法律正义,与林立先生在伦理学层面描绘的正义是两样的。法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对于正义的理解需要基于经验层面,而过多的高尚情感并不见得会有效提升法律的作用和地位。假如同林书一样认为效率和公平正义无法通约,对于社会效率缺乏一致性的理解,那么作为效率尺度的财富最大化理论就会显得很荒谬。
三、作为效率尺度的财富最大化
如同亚里士多德的“善”、边沁的“全体的福利”,波斯纳选择将财富最大化作为法律经济学的规范性基础。尽管财富最大化受到诸多的批评,但目前其依旧是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效率尺度。
(一)从功利主义到财富最大化

法律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可以从功利主义开始起算。功利主义和经济分析的相同之处在于,都是通过结果而不是动机来评价行为*张芝梅:《美国的法律实用主义》,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149页。。然而,无论把功利主义作为个人道德的体系,还是作为指导社会决策的指南,都有一些严重的缺陷*理查德·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59页。。波斯纳认为功利主义过于抽象,效用也很难度量,无法转化成具体的可计算可比较的操作标准。而功利主义把人作为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细胞而非个体来对待,为了总量的最大化可以牺牲无辜,这一点是为人所熟知的功利主义道德之野蛮性根源*理查德·波斯纳:《法学理论的前沿》,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1页。。从而把功利主义推到底线,可能很荒唐。因此,波斯纳提出了财富最大化这个替代性标准。在波斯纳看来,就基于自愿的市场交易模型而言,追求财富要比古典功利主义更尊重个人选择,标准也更为客观。可以说,财富最大化是在对功利主义效用最大化批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是为了改变人们常把经济分析和功利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现状。而波斯纳主张用“财富”替代“效用”,以财富最大化作为法律经济学的分析基础,这在当时一个很重要的进步。
(二)财富最大化释义
财富最大化这一概念来源于理性人假设,其基本假定是人们总是理性地最大化其满足度。最大化其“满足度”是比“物质财富最大化”、“利益最大化”或者“效用最大化”更原始、更直白的一个假定。如果一说财富最大化就认为是物质财富,这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误解。实际上,货币性满足和非货币性满足,都进入个人最大化的算计,而且财富最大化对于人们想要什么或者应该要什么并无任何立场*理查德·波斯纳:《法学理论的前沿》,第101页。。经济人也可能为自己的某种特殊的爱好,甚至为了利他主义的信仰付出。林书指出,由于个体满足度之间的差异性导致它们无法进行赋值和比较。其实,如果不在严格意义上纠结于基数效用和序数效用的争论,基于对个体效用进行的常识性比较和加总可以被用来作为评价社会政策的规范标准。也就是说,借助于替代和边际,非经济行为一样可以实现相对的比较和加总。

(三)一种具有可操作性的标准
财富最大化可以说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一种描述,它并不是偏好的汇总,而是一个典型的偏好,其他偏好物以财富为标尺进行计价。可以说,德沃金对财富最大化的误解,是前提条件不明导致的。德沃金在强制性转移资源的例子中,忽视了波斯纳所隐含的财产权结构不受影响的前提条件。全知全能者的独裁成本未必小于一,而交易双方尔虞我诈的成本未必大于一。尽管如此,波斯纳依旧认为财富最大化有局限,他承认并非法律遇到的所有问题都能不费吹灰之力地转化为经济学问题*理查德·波斯纳:《超越法律》,苏力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页。。例如,关于人工流产的争论是两个不同阶层的妇女权利的冲突和竞争,它无法仅仅通过论证就可以解决。换句话说,判决的公正与否很大程度上是力量对比折射到人们的政治共识或者道德共识的结果*张芝梅:《法律如何解决政治性问题》,《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这种案件没有正确的答案,只有好和坏的答案,而德沃金却试图为各种涉及价值的问题提供一个可靠的基础。其实,波斯纳早在上世纪90年代已经放弃了对财富最大化进行规范性阐述。财富最大化作为当时论战的产物,容易被别人批评,但却不易进行反驳。在面对类似于人工流产等问题,波斯纳也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论证,尽管这些质疑很大程度上是共同的难题。目前,行为法律经济学有一种回到边沁的主观效用的提法,试图挑战和重构传统经济分析的理论基础。然而,受限于技术水平和研究手段,行为法律经济学并未提出有效替代财富最大化的标准。因此,承认行为法律经济学取代或建立起什么,都言之尚早。可以说,财富最大化用金钱作为量化的比较物,仍然是一种靠谱的操作性标准。
四、财富最大化与分配正义
林立先生认为波斯纳的财富最大化理论不注重社会财富的平均分配,导致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从而社会的基本公平正义和道德伦理秩序都无法得到保障。然而这种质疑看起来正气凌然,但如果忽略了分配平等和机会平等、帕累托改进和潜在帕累托改进的区别,林书的观点却并非当然成立。
(一)分配平等与机会平等
尽管经济学家经常声称经济学帝国主义,但这与林立先生所假设的经济学万能主义却并不是一回事。即使是追求分配平等的功利主义者,试图内化再分配到效用最大化中,也必须使更大平等的收益与扭曲激励的损失保持平衡。换句话说,为了使总效用最大化,政府不会也无力使社会完全平等*曼昆:《经济学原理》,梁小民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29页。。因为,在通常情况下司法和政治是相分离的,而有效率的再分配政策需要征税和公共开支的权力,这恰恰是法官们所不具备的。相比之下,立法机关则可以更容易、更有针对性地调节成本和收益*詹姆斯·哈克尼:《非凡的时光》,榆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65页。。因此,明智的做法是将司法注意力集中于馅饼面积的增长上,而将切分馅饼的工作留给立法机关和税务机关*大卫·弗里德曼:《经济学语境下的法律规则》,第21页。。基于此,林书质疑司法分配不公并非一个有效的论据,但如果提出即使是立法机关和政府也不能很好的解决分配问题却是一个有效的论点。由于初始分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制度本身,即使初始分配能够用一致同意解决,差别最多会在三代后消失*理查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第472页。。正因为如此,波斯纳才认为机会平等比收入平等更重要,而政府的作用在于确保每个人有同样发挥自己才能并获得成功的机会。

(二)帕累托效率与潜在的帕累托改进
帕累托原则在道德上的诱惑力近似于“一致同意”的诱惑力,使其成为伦理学所尊重的一种主张*理查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第485页。。在帕累托效率中,假设没有第三方的影响,交易能使两个人的处境都有所改善而没有人的处境变糟。然而,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法律规则的变化不太可能只产生收益而没有成本,交易也很难不对第三方产生影响,所有法律和公共政策必然会有赢家和输家,以帕累托标准作为法律决策的依据是难以操作的。在芝加哥学派内,效率的标准定义是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或者财富最大化。波斯纳将其所用的方法基于一致同意,而一致同意是建立在事前补偿的基础之上*尼古拉斯·麦考罗:《经济学与法律——从波斯纳到后现代主义》,第77页。。可以说,基于事前赔偿的卡尔多-希克斯效率或财富最大化所构筑的是机会平等,而不是解决帕累托理想化意义上的分配问题,帕累托改进并非完成财富最大化之交易的必要条件*理查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第447页。。简单来说,法律经济学追求的是向前看的机会成本,而非沉没成本。
如果说分配标准是事后标准,那么效率标准就是事前标准,传统的分配正义和法律经济学的效率标准之间的区别就在这里*柯华庆:《法律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制度经济学研究》2005年第3期。。法学研究中有一种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的倾向,总想发现本质,而不是去拥抱经验的涌流。当仔细分析律师和法官所使用的“公正”和“平等”这两个词时,它们就归结为对后果的考虑。如果程序合理的平衡了错误的风险与减少错误的成本,那么它就是“公正的”。当事前的效率与事后的分配发生冲突时,事后标准应该服从于事前标准*张维迎:《信息、信任与法律》,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第72页。。故考虑到现实条件的限制,财富最大化可能是我们能为法律找到最简单、也最明确的指导原则。而林立先生追求的分配公平恰恰是帕累托意义上的,这种分配所需要高昂的费用使其只能作为无法操作的理想状态。即使是最好制度都会出现大量法律结果的不平等*理查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第417页。。这也是为什么亚里士多德所谈更多的是校正正义而不是分配正义。林立先生所言的分配正义,实际上是政治正义的同义词,而并非一个单纯的法律问题。
五、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林立的理想国?
其实,正义、道德和财富最大化都是法律的一种理想状态,而法律的实现却是一个公共选择问题。由于分配正义受制于社会物质发展水平制约而无法真正解决,林立先生没有也无力给出一个可行的替代理论,林书不得不再次援引其他学者。在林书最后的“伦理奠基篇”中,林立先生给出了他心中的理想国:罗尔斯的正义理论。尽管,林立先生只是被罗尔斯这种有正义理论的表象所吸引。
罗尔斯的名著“A Theory of Justice”被翻译成了《正义论》,原本关于正义的一种哲学被认为成正义本身,造成了不少误解。罗尔斯所讲的是一种政治理论或者说是分配正义理论,其探寻在什么条款的制约下能够进入文明社会的抽象协议。罗尔斯认为人具有很高的理性,如果每个人都处于无知之幕背后的原始状态,那么在取舍时就会特别关注收入分配最底层的可能性。基于此,罗尔斯制定了平等原则和差异原则两个抽象原则。尽管他认为平等原则更为重要,但显然差异原则才是罗尔斯正义理论的主干。差异原则并不具体要求哪种特定的不平等是可以被允许的,也并非真正的补偿。如果在一个世界里贫富差距能让最不幸的分子得到最多的照顾,那么这个世界就是合乎正义的*熊秉元:《黑猫、白猫和好猫:对世事人情的经济学思考》,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6页。。因此,在设计公共政策时,应当遵守最大最小准则,以提高社会中状况最差的人的福利。可以说,罗尔斯的理论是结合了无知之幕和极端风险规避这两个因素。

波斯纳和罗尔斯都是基于自由主义观点对功利主义学说进行的反思。所不同的是,波斯纳从社会生物学的视角,指出了人与人的差别,而罗尔斯在波斯纳提出的现实情况中做了一个思想实验,反推在何种情况下社会成员对公正能有一致的认识。如果说罗尔斯基于一个无知之幕,那么波斯纳则是一种有知之幕。可以说,波斯纳的思路是从个体出发,无数的个人利益组成社会利益。相反,罗尔斯是从社会出发,通过社会的公平分配取得个人利益。从表面上看,罗尔斯这种着重分配正义的思路,解决了德沃金关于波斯纳不注重平均分配的批评。然而,风险回避的人会选择一个以牺牲更多个体经济自由来换取社会保险的原则,这使得罗尔斯的社会正义原则类似于边沁的收入平等最大化的原则*理查德·波斯纳:《正义司法的经济学》,第59页。。因此,罗尔斯也没有解决功利主义“没有认真对待人与人的差别”的问题,他只不过将强调全体福利的“边沁主义”和强调个人自由意志的“康德主义”折衷起来*邓峰:《经济法学漫谈》,《经济法学评论》(第5卷),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4年,第7页。。
林立选择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或许是受了德沃金的影响。可以说,德沃金的权利论就是以罗尔斯关于社会正义的两个基本原则为基础的*沈宗灵:《现代西方法理学》,第98、109页。。尽管罗尔斯的立证方法建立在极端风险厌恶的人性假设以及信息筛选之上,不过林立先生显然无视于此,因为他为正义论中推导出的社会资源分配状态以及因此生出的人之高贵情操所感动!*简资修:《波斯纳与法律经济分析-一个辩护性说明》,《月旦民商法》2005第8期。然而,自1971年以来,《正义论》所强调对收入和财富从富裕者再分配给贫困者的观点看上去开始过时。尽管收入和财富分配的不平等不断增加,但是公众对这个问题的兴趣已经降到了近乎消失的程度。平均主义关注点已经转向收入更为同质化的群体内部的不平等,而《正义论》对这些问题没有涉及*理查德·波斯纳:《道德和法律理论的疑问》, 第56页。。所以,如果林立认为波斯纳没有走出功利主义,那么他所认可的罗尔斯也并没有走的更远。而鉴于罗尔斯的理论前提过于抽象,涉及到具体问题很难得出一个确实的答案,相比之下,波斯纳的有知之幕可能更为现实。可以说,用罗尔斯来替代波斯纳,在理论上没有实质性的进步,而在操作性上却是一种倒退。
六、实用主义:逻辑的起点和回归
或许不是波斯纳的冷酷,而是其实用主义观点让林立先生感到不适。而实用主义和基础主义的分野,也使得林立先生或者“新林立先生”与波斯纳之间较量,只不过是隔空挥拳,并不能分出高下。
(一)实用主义的有无之境
人们通常认为法律经济学是反法哲学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律经济学没有哲学基础。法律经济学和其他学科一样,都是从哲学的怀抱中发展出来的。法律经济学首先出现在美国而不是欧洲,是因为美国所注重的法律实践特质本身就带有强烈的实证主义色彩。而美国上世纪的实用主义思潮和现实主义法学已经为法律经济学运动铺垫好了基础。波斯纳适用实用主义并非独树一帜,而是顺应科学研究的号召。波斯纳把实用主义看做重塑法律和政治理论的基本步骤*张芝梅:《实用主义司法理念的价值及限度》,《学习与探索》2008年第3期。。波斯纳将法律实用主义界定为实践性和工具性的,而不是本质主义的,它感兴趣的是什么东西有效和有用,而不是这“究竟”是什么*理查德·波斯纳:《超越法律》,第4页。。这种实用主义态度使得林立先生基于本质主义立场不同而产生的批评不会有什么答案。
实用主义承认有些问题可能永远无法回答,但实用主义试图充分利用一切可能的证据及科学创新。波斯纳认为实用主义既是有用的,但又没什么用,它的没用恰恰说明它是有用的。实用主义并非和自由主义一样是一个拥有特定立场的政治流派,也不类似于现实主义是一个有着特定视角的法学流派。实用主义没有一个独特的公式可以计算出任何一个法律问题的答案。它是把法律当成政策科学,但是又不等同于政治,一切取决于法官在个案面前对于后果的权衡。而实用主义的“公分母”就是一种努力以思想为武器,使更有成效的活动成为可能,并以未来为导向的工具主义。这种构建性是实用主义对法律最大的贡献,波斯纳认为其价值体现在:它使法学学术更为接近社会科学,促使司法游戏更为接近科学的游戏。实用主义标志着一种态度,同时也标志着一种方向的改变。
(二)超越抑或理解波斯纳
林立先生的观点不过是重复美国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论战观点。然而,九十年代以后,关于财富最大化的规范性争论逐渐冷却,因为得不出什么结论,是否有本质主义或伦理上的基础也不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尽管有人对法律经济学的简约论、反再分配倾向还疑心重重,但法律经济学的洞见如今已是常规科学*Lawrence Lessig, “The Prolific Iconolast: Richard Posner,” The American Lawyer, Dec. 1999, p.105.。“仅仅是一种批评的进路缺乏持久的力量;并且,即使是摧毁性的批评也不能摧毁,如果批评者没有什么可以取代他希望摧毁的废墟”*理查德·波斯纳:《超越法律》,第25页。。时隔十年,林立先生并没有如人们所期待的十年磨一剑,而是放下的就放下了。
之所以旧书重提,是因为林书这层窗户纸仍然没有捅破,而林书近年的引用量和相似观点却有增长的趋势。如果不能推翻这种嫁接在过时论战残骸上的批评,对于波斯纳和经济分析的理解将很难向前推进。特别是波斯纳三部曲中的很多章节就是当时论战的产物,有很强针对性,并非是无的放矢的说法,断章取义并不可取。而在解读波斯纳的同时,很容易将自己的认识替换了波斯纳,而稻草人的立论和批评方式会掩盖波斯纳的理论价值*张芝梅:《实用主义地拒绝实用主义——对批评波斯纳的反批评》,《法律和社会科学》2013年第12卷。。近年《法律和社会科学》和《北大法律评论》先后设立专题 “批评波斯纳”,使得波斯纳再次被国内学界所聚焦。其中比较有针对性的是艾佳慧的论文,同专题的伊卫风指出艾文根本在诠释波斯纳,并非真正地批评波斯纳*艾佳慧:《单向度或互动的法律经济学——与波斯纳法官的跨洋对话》,《法律和社会科学》2013年第12卷;伊卫风:《反思波斯纳的实用主义》,《法律和社会科学》2013年第12卷。。笔者对此看法并不认同,艾文还是想超越波斯纳的,但单向度思维实际上是艾文的臆造。“单向度还是互动视野的法经济学”根本是伪命题,科斯定理强调的是权利的相互性,而侵权法的经济学分析从一开始基于科斯定理的洞见就是当事人对预防和损害成本的分摊,而非艾文说的古典经济学的视角。不得不说,就整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于批评波斯纳有点操之过急。
本文认为,现阶段能做的可能更多是理解波斯纳。波斯纳在芝大暑期学校上说中国更适合形式主义,并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如果把足够的强调放在审判的系统性后果上,那么法律实用主义就同法律形式主义合二为一。尤其在以法典为基础的法律体系中,法律形式主义可以是一种合理的实用主义策略*理查德·波斯纳:《法律、实用主义与民主》, 凌斌译,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79页。。尽管波斯纳一再强调实用主义也许只能在美国适用,只限定在普通法系。但如果我们仅这样认为,就还是把波斯纳的实用主义理解为一种特殊理论,而不是一种态度。波斯纳将经济分析的有用性限制在普通法,这并没有与波斯纳所贯彻的实用主义相悖,也并不是向中国学员泼冷水。有学者认为由于司法公信力不足等原因,中国法院不会也不应该采用法律经济学*张巍:《法经济学与中国司法实践》,《法律和社会科学》2015年第1卷。。然而,中国司法公信力是否能由目前的法律形式主义所提升,答案依旧仍有待观察。近年,有一种回到科斯的原旨主义提法*参见简资修:《科斯经济学的法学意义》,《中外法学》2012年第1期;吴建斌:《从波斯纳到科斯的回归》,《法律和社会科学》2013年第2期。。科斯一直将自己界定为经济学家,并反对波斯纳和卡拉布雷西对其理论进行规范性的扩展。其实波斯纳和科斯都没有错,只是研究偏好上的不同而已。科斯更注重个案实证研究,而波斯纳更在意经济分析的统一解释力。科斯的方法或许是由于个案的研究方法更容易借鉴和模仿,从而更容易接受。然而,法律必须具有规范性,如果仅如科斯所言只能解释具体事例而不讲规范,那也就无所谓法律了。因此,本文认为没有必要将科斯做原旨主义的理解,上升为一种唯一正确的理论。如果非要有什么的话,只能是有些人习惯性的造神情结。
总之,通过以上分析,林立先生和“新林立先生”并未对波斯纳的理论构成实质性的批评。法律经济分析的基础并不是不可言说的,而是因为现有关于财富最大化的阐述已经足够,与其纯粹去完善它的有关定义、深入阐述福利主义或者实用主义,不如把力气用在具体问题的经济分析上*吉奥加卡波罗斯:《法律经济学的原理与方法》,许峰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9页。。波斯纳的理论在经验主义者看来不是没有问题的,但却不是林书的那些理由。比如随着行为经济学的兴起,学者已经提出用主观效用单位细化并重塑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而行为法律经济学在后来遇到的一些瓶颈恰恰说明波斯纳早期选择财富最大化的必要性。在《法理学问题》出版之后,美国秉持类似林书观点,就已经基本绝迹。本文认为国内的相关研究和评论也不应该再纠结于此。有鉴于波斯纳法官旺盛的创造力,意图全面读懂波斯纳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任务。至少目前,国内对波斯纳的批评多数流于表面和偏颇,并没有在实质上超越波斯纳。或许我们所描绘的世界在未来不久会被证明是粗糙的,甚至错误的,但我们正在努力发现。
[责任编辑:李春明]
An Argumentative Interpretation on Posner and the Economic Analysis of Law—— A Discussion with Professor Lin Li
WANG Bo-yang
( Law and Politics School,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100, P.R.China)
RichardA.Posner&LawandEconomicswritten by Prof. Lin Li is the only theoretical writing which studies Posner’s theory in Chinese-speaking world. However, Lin’s book does not properly define the hypothesis of rational man and efficiency standards and does not recognize that what Posner chases for is the equality of opportunity in the perspective of social cost instead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which is a potential Pareto improvement instead of Pareto improvement in practice. Therefore, Lin’s book as a critical inquiry does not succeed and does not complete the goal of overthrow wealth maximization. Prof. Lin Li chooses Rawls as an alternative option, and there is no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theory. But in the operation it is a kind of regression. In view of the position of Posner’s pragmatism instead of essentialism, this makes the current view of Prof. Lin not really go beyond Posner.
Wealth Maximization; Distributive Justice; Efficiency; Pragmatism; Cost
2016-03-17
王博阳,中国海洋大学法政学院博士研究生(青岛 266100)。
——充满艺术的实用主义者Eva Sol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