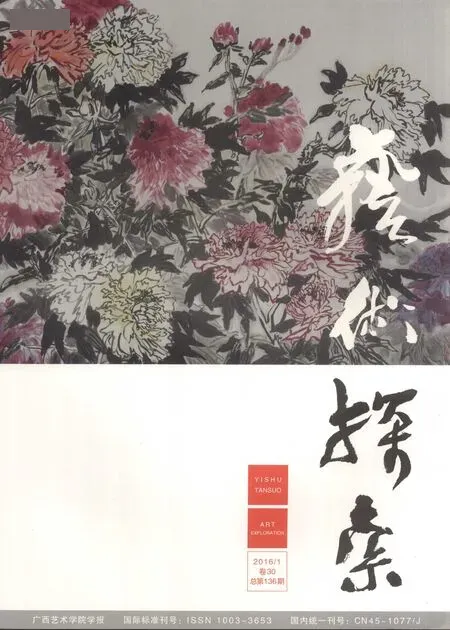“冰魂”:李方膺“墨梅”隐喻与镜像
李倍雷(东南大学 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1189)
“冰魂”:李方膺“墨梅”隐喻与镜像
李倍雷
(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江苏南京211189)
[摘要]李方膺的“墨梅”被郑板桥喻为“冰魂”,这一隐喻显示了作为“墨梅”母题具有镜像的价值与意义。李方膺的“墨梅”不同于其他画家的“墨梅”,在于它的隐喻还有更深一层意义:三两片似雪如飞的“瘦蕊”,飘凝在凌空横斜的枯枝上,“冰花雪蕊”作为墨梅的母题意象,如同镜像影射出画家尘世宦海种种境遇,隐喻画家“冰魂”般的孤寂与高洁,将画家的一生透亮地凝结在“冰花雪蕊”的墨梅上,“冰魂”由隐喻转向镜像。
[关键词]李方膺;冰魂;墨梅;镜像;孤独者;精神叙事
“扬州八怪”之一的李方膺,他的墨梅图独具孤寂冷傲、似冰如雪、“痩骨清像”的意象特征。王冕的梅花图结构很满,密不透风;扬州八怪其他画家如汪士慎、金农、罗聘的墨梅,呈“欣欣向荣”之态,如冬天里的春天,错位于时间;李方膺的“墨梅”图式,疏稀消瘦,冷若冰霜三两朵,晶莹剔透,如“千秋古雪”孤寂傲气,恰如一片片镜像,影射李方膺的性格和宦海沉浮的一生。正是由于李方膺的墨梅孤冷又自怜,剔透如玉,被郑板桥隐喻为“冰魂”,墨梅这一母题意象的象征意义便凸显出来,并将李方膺一生宦海经历凝固在枯枝上,成为透明的镜像。诚然,要深度理解与诠释墨梅的母题隐喻与镜像,还需要文献支撑,如李方膺的墨梅图自题是诠释“冰魂”最可靠的文献。
一、梅花夜月耿冰魂
“冰魂”见于郑板桥为李方膺题的一首四言诗:“梅根啮啮,梅苔烨烨,几瓣冰魂,千秋古雪。”①诗见郑板桥《题李方膺画梅长卷》,1760年,南通市博物馆藏。“冰魂”是对李方膺“墨梅”母题最准确、最有深意的解读,也是我们探讨李方膺“墨梅”母题隐喻与镜像的关键词。李方膺的墨梅图与其他画家最大的不同在于,李方膺的墨梅不是属于“欣欣向荣”(如王冕、汪士慎的墨梅)或“欢喜漫天雪”(如金农的墨梅)一类,倒是诚如“千秋古雪”凝结在转折枯劲梅枝上的“几瓣冰魂”。这不禁使人们想起元四家之一的倪瓒(1301~1374年)曾留下的诗句:“梅花夜月耿冰魂”[1]。大概郑板桥对李方膺墨梅的评鉴来于倪瓒的这句诗,如此可以理解为月之精华被李方膺墨梅取之,凝固为饱藏精神的冰魂。
李方膺(1695~1755年),通州(今江苏南通)人,字虬仲,号晴江,别号秋池、抑园、白衣山人等。寓居金陵借园,自号借园主人。一生为官磕磕碰碰,喜弄诗文,更善绘画。在李方膺绘画母题中,梅花是他最喜之物。有一段故事说明李方膺喜欢梅的程度:“李方膺性爱梅花,到滁州代理知州,一到任先打听欧阳修手植梅花所在,当得知在醉翁亭,便急忙前往,在梅树前铺下毡毯,纳头就拜。”[2]1260从这则故事看,李方膺喜欢梅花可能还与对欧阳修(1007~1072年)人品、学品、官品等的崇敬有关联。
关于李方膺墨梅技法和师承,相关研究比较多,也比较深入,最可信的评论是:“纵横跌宕,意在青藤白阳之间,而尤长于梅”[3]。再如,“善松竹梅兰及诸小品,纵横排奡,不守矩矱,笔意在青藤竹憨之间”[4]。青藤(徐渭,1483~1544年)、白阳(陈淳,1521~1593年)并称“青藤白阳”,对李方膺的影响较大。那么,李方膺是否学过王冕(1287~1359年)等画梅大家?我们看一首李方膺自题画梅花诗就明白了:“铁干铜皮碧玉枝,庭前老树是吾师。画家门户终须立,不学元章(王冕)与补之(扬无咎)。”①诗见清李方膺《梅花图》卷之二,1755年,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院馆藏。说明王冕、扬无咎对李方膺的墨梅影响极小,当然我们可以把影响极小的范围缩小在画家对梅花的态度与精神方面。的确,我们能够从李方膺的墨梅、墨竹图中,多少能看到青藤、白阳的气息和笔意。在图式结构方面画家则“自立门户”。李方膺有自己独特的“减笔”图像与结构,一两折枝墨梅成为隐喻与镜像,从而使“墨梅”这一纯粹的母题隐喻了非同寻常的“梅花月夜耿冰魂”含义。这里涉及母题变迁的问题,即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艺术家,使用同一母题时,母题发生变异甚至与“原型”相差很大。某种意义上,这是“母题学”需要探讨和解决的母题流变的问题,不过“母题学”不是我们这里要探讨的。
郑板桥《题李方膺画梅长卷》,是在李方膺逝世五年之后所题,我认为是对李方膺“墨梅”母题意象最合理的总结:
兰竹画,人人所为,不得好。梅花,举世所不为,更不得好。惟俗工俗僧为之,每见其几段大炭,撑拄吾目,其恶秽欲呕也。晴江李四哥独为于举世不为之时,以难见奇,以孤见实。故其画梅,为天下先。日则凝视,夜则构思,身忘于衣,口忘于味,然后领梅之神,达梅之性,挹梅之韵,吐梅之情,梅亦俯首就范,入其剪裁刻划之中而不能出。夫所谓剪裁者,绝不剪裁,乃真剪裁也;所谓刻划者,绝不刻画,乃真刻画。岂止神行入画,夫复有莫知其然而然者,问之晴江,亦不自知,亦不能告人也,愚来通州,得睹此卷,精神濬发,兴致淋漓。此卷新枝古干,夹杂飞舞,令人莫得寻其起落,吾欲坐卧其下,作十日功课而后去耳。乾隆二十五年五月十三日板桥郑燮漫题。[5]
前引“冰魂”的四言诗,也是郑板桥题在这幅画上的(1760年)。这里提到了李方膺画梅“为天下先”的原因:“领梅之神,达梅之性,挹梅之韵,吐梅之情”,还分析了李方膺墨梅图像的图式结构与处理方式:“所谓剪裁者,绝不剪裁,乃真剪裁也;所谓刻划者,绝不刻画,乃真刻画”。高手画家评论高手画家的绘画技法与表达范式是到位的、准确的,也是可信的。李方膺喜欢画梅,在他自题诗中表露了心迹:“我与梅花信得真,梅花命我一传神。叮咛莫写寒酸态,惨淡经营天上春。”②诗见清李方膺《梅花图》,1752年,无锡市惠山街道提供。这首诗题于《梅花图》,落款乾隆十七年(1752年)秋八月,属李方膺晚年所题。以一种清高狂气率真自信地以梅花性格隐喻,多少显露出李方膺在世俗生活状态中的另一面,尤其是为官之道的“不入道”。反过来说,世俗为官的境遇又迫使李方膺在梅花中诉求与隐喻,通过这种方式以“墨梅”母题意象的隐喻与镜像反观自己,以澡雪而精神,求灵魂通达与畅明。后面我们还会看到李方膺的自题,可与我们这个观点相印证。
李方膺的为官之道,始终起伏磕碰。他性格刚直,不会拐弯。这种性格使他“不落俗套”,亦不知攀附,如其父所言“性戆,不易官”。自然,李方膺在官场上难以施展才华,无法得志,即使有点志,也惹出牢狱之灾,终蹉跎半世。关于李方膺为官之道,我们来看一段杨挺(1785~1854年)《一经堂诗话》对李方膺合肥为官时的记载:按当地习俗,岁末给太守奉上“馈岁礼”,李方膺送的是“盐齑二翁”,哪知太守不满于李方膺送之物。以李方膺的性情,他不仅索回所送之物,还愤愤然道:“如尔死艺,脑满肠肥,岂知吾辈菜根中滋味耶。”[6]这种性格导致李方膺官场不顺,蹈罢官之命。这也看出了李方膺个性的“狂气”,这种“狂气”在他的一幅《风竹图》(1754年,天津博物馆藏)中有所体现。愤愤然的笔墨,昭示了《风竹图》中的“凌乱”之竹在乱风中怒摆,真有点借用了青藤笔墨的精神。当然这种愤愤然的笔墨一点也不“冰”,而是相反。正如画中自题:“波涛宦海几飘蓬,种竹关门学画工。自笑一身浑是胆,挥毫依旧爱狂风。”这狂傲之气可见一斑,也揭示了他对“波涛宦海几飘蓬”一生命运的总结,他感慨万千,思绪如该图风中之乱竹。但画家不可能一辈子这样永远地“狂气”下去,也有需要反思自己的时候,否则他活得很困难。这种感受其实他在早几年前就意识到了。在1751年画的《潇湘风竹图》(南京博物院藏)中,他就自题到:“画史从来不画风,我于难处夺天工,请看尺幅潇湘竹,满耳丁东万宝孔。”“我于难处夺天工”已经暗示了晚年遭到罢官正处于苦境之中。该图尽管与《风竹图》都采用了秃笔横扫竹叶的方法,亦能让人感受到写竹之人的狂气,但从他的自题来看,他已经意识到自身所处的“难处”——“难处夺天工”是一种理想和愿望了。李方膺能够把“难处”写出来,说明他彻底感受到自己的处境很艰难,同时也意识到应该有所隐藏一下自己的狂气。但是他的狂气还在延续,中国古代文人“禀性难移”。一如词曲家蒋士铨在《忠雅堂诗集》中评李方膺为“怒目撑眉气力强”。到了画墨梅图时,狂气依旧在笔墨中。但有一种转化出现在墨梅的图像中,这就是将处世的“狂气”转化为笔墨的“魄气”。这一转化也是李方膺在墨梅图作品中作为“母题”隐喻转变的开始,把原来的狂气隐匿在墨梅图的图式中,将所有心思都寄托于梅,眼中所有物象都视为梅,隐喻一种对世俗与官场的态度,含蓄地表达他对世俗与官场的批判。李方膺的这种“冰魂”般的心迹,从他《梅花图》卷(1755年,南通市博物馆藏)以及他的自题中可以看到:“予性爱梅,即无梅之可见而所见无非梅,日月星辰梅也,山河川岳亦梅也,硕德宏才梅也,歌童舞女亦梅也。触于目而运于心,借笔借墨,借天时晴和,借地利幽僻,无心挥之,而适合乎目之所触,又不失梅之本来面目,苦心于斯三十年矣。然笔笔无师之学,复杜撰浮言以惑世诬民,知我者梅也,罪我者亦梅也。”这实际已是李方膺乾隆二十年(1755年)生命的最后一年所写,是冥冥中对自己一生的总结。李方膺把世界一切所见都视为梅,无论是日月山河、德行才智还是歌童舞女皆为梅。梅是李方膺表达世界的主要母题意象,所以郑板桥精确地看到了李方膺的“墨梅”母题意象,说李方膺是“领梅之神、达梅之性,挹梅之韵,吐梅之情”,最终得到了梅之魂,而梅是整个冬季唯一开放花朵,它是整个冬天孤独之的“冰魂”。其实我们在解读李方膺“墨梅”母题意象时,应该反过来诠释,是李方膺的神、性、韵、情移入梅花这个自然母题中,自然中生长的梅花构成了李方膺的隐喻之意象,墨梅便是李方膺之隐喻的实体,孤独的“冰魂”是李方膺之镜像。
二、“冰魂”者的孤独
李方膺一生两过青州。乾隆四年(1739年)再次路过青州时,写下《青州题画诗》一首:“市上胭脂贱是泥,一文钱买一筐提。李生淡墨如金惜,笑杀丹青手段低”①诗见清李方膺《牡丹图》,1739年,重庆市博物馆藏。,如此也算得上“江左狂生”。李方膺在艺术上狂傲,不与世俗同流,更看不上欺世盗名之作,他以“淡墨如金惜,笑杀丹青手段低”的态度蔑视那些一文不值却讨好世俗人之画。他把那些“一文钱买一筐”的画——用我们今天的说法就是“行画”(“商品画”)喻为贱如泥的“胭脂”,实是一文不值。这见出李方膺的狂气和清高甚至面对世俗的自命不凡。但正是这一年,一个意外使李方膺有了变化,使他觉得自己是心灵的孤独者。
清乾隆四年(1739年)李方膺父亲去世,随后母亲亦病而卒。此刻的心情在李方膺《题诗》四首之一中披露出来:“披开不禁泪痕枯,辗转伤心辗转孤。十七年前漳海署,老亲命我作斯图。父子衔恩遭际殊,涿州分路泪如珠。谆谆农事生灵本,三代耕图记得无?”[7]按照中国传统丧葬习俗,丧父需守孝。李方膺通州守孝,过着没有官场那种如履薄冰的轻松生活,真有一种陶潜所说的“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的心境。这种心境自然在他所画的墨梅中得到印证:“幽芳独秀在山林,密雪无端苦见侵。驿使不来羌管歇,与谁共话岁寒心。乾隆七年八月五日写于梅花楼。”[8]102另一幅墨梅自题:“梅花一夜遍南枝,销得骚人几许诗。自去何郎无好咏,暗香唯有月明知。”[8]101他的这种心境,与陶渊明极为相似。陶渊明虽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心境与自然交融的境界,但又写有《读山海经》其十:“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晨讵可待。”[9]所以他被鲁迅评为“猛志固常在”的那种隐士。李方膺在家守孝看似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其实他的题画诗文,暗自透露出一种欲罢不能的血性宏愿,尽管性格不宜为官,但志向犹存,依旧“猛志固常在”,所以他诗中的惆怅显而易见:“驿使不来羌管歇,与谁共话岁寒心”。李方膺心中还是暗自期盼“驿使”带来外面的消息。孤独者自有孤独者的“寒心”,极少有人理解,“与谁共话”,这种孤独者的心境一如“暗香唯有月明知”。这便是一种“墨梅”母题意象的镜像,透射出李方膺心理孤独的经历。
为父守孝之后,因母亲去世,再为母守孝。此其间,李方膺一直在通州。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有一幅李方膺的《竹石梅花图》(1743年),这幅作品便是在通州守孝时期所绘。该画自题:“烟锁空山晓未开,暗中顾影自怜才;岁寒标格不可掩,消息已从天上来。冰雪寒天阳气转,幽香飞动老龙鳞;平生不肯居后人,十月严霜占得春。乾隆八年前四月,写于梅花楼,晴江李方膺。”与梅花顾影自怜的李方膺,始终被孤独的心境所困扰,与其说是“烟锁空山”,不如说是烟锁李方膺的“空心”。大约在清乾隆十一年(1746年),李方膺50岁,守制期早满,便由家乡入京候选,试图再登仕途。他途经扬州小住几日,在僧舍又作《梅花册》数幅。他在《梅花册》之二(1746年,南通市博物馆藏)自题云:“官阁成尘事已凋,我来僧舍画梅条。扬州明月年年在,收拾春光廿四桥。”在《梅花册》之一(1746年,南通市博物馆藏)题云:“知己难逢自古来,雕虫小技应尘埃。扬州风雅如何逊,瘦蕊千千笑口开。”也许是在家太久,“消息已从天上来”,欲想入京等候,心情自然如梅花轻轻绽放,梅之意象不断地缠绕着李方膺的所有心思。我们注意到,李方膺这里用了“瘦蕊”这个词,的确,在他的墨梅图中,极少能够看到如王冕、汪士慎、金农等所画梅花那样“饱满”地绽放,李方膺的墨梅图用一个“瘦”可以概括——梅花瘦,枝干瘦,图式瘦,结构瘦,笔墨也瘦。“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隐喻了某种孤寂。李清照的“人比黄花瘦”,就是这种隐喻。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也隐喻了某种孤寂,正是有了孤寂才会有了思念。“瘦蕊”不仅仅是形态的“瘦”,而且隐喻了某种精神叙事。
图像的“瘦”最大特点在于删繁就简。李方膺的墨梅正是着笔不多的删繁就简。虽然他亦喜欢王冕的梅花,也欣赏同时代汪士慎、金农的梅花,但不学他们。作为性有“狂气”的孤独者,李方膺的梅花,是孤独之梅,是“夜月耿冰魂”之梅,不像其他画家笔下的梅花一片欣欣向荣的盎然景象。有什么样的心境必有什么样的墨梅,这是墨梅之镜像的反射。李方膺有自题画梅诗云:“写梅未必合时宜,莫怪花前落墨迟。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10]心高气傲者必然为孤独者,孤独者的墨梅也必然孤独,“触目横斜千万朵,赏心只有两三枝”,这显然是孤独者的心境。三两朵梅花如飞似动地飘凝在一两枝遒劲的树枝上,恰似飞雪,飞雪似梅,梅雪相融。他在另一幅《墨梅图》(1748年,故宫博物院藏)自题:“雪拥梅花傲岁寒,秀才风味画图有。人言结实溅牙齿,未解调羹尚借酸。”“岁寒”实则是画家对自己境遇的隐喻。该作整个图式结构中,占有最大空间的是空白,空白中最孤寂的墨梅便是李方膺自身。我们这里重点讨论作为母题的“墨梅”——“冰魂”,孤独者的隐喻与镜像。
我们先借李方膺密友袁枚(1716~1797年)给李方膺的赠诗开始分析。袁枚诗云:“我爱李晴江,鲁国一男子。梅花虽倔强,恰在春风里。超超言锯屑,落落直如矢。偶遇不平鸣,手作磨刀水。两搏扶摇风,掉头归田矣。偶看白下山,借园来居此。大水照窗前,新花插屋底。君言我爱听,我言君亦喜。陈遵为客贫,羲之以乐死。人生得友朋,何必思乡里。”[2]232这既是对李方膺墨梅的欣赏,更是通过对墨梅隐喻地赞赏李方膺这位“鲁国一男子”。袁枚这里对墨梅的隐喻已经有了一种镜像的意义。作为有镜像意义的墨梅反射的便是李方膺的“魄气”,“魄气”即“冰魂”之气。“梅花虽倔强,恰在春风里”隐喻了李方膺的性格柔情的一面。接下来袁枚对李方膺墨梅隐喻了一个有关超越时间的概念。袁枚《送李晴江还通州》三首,第一首有云:“才送梅花雪满衣,画梅人又逐花飞。一灯对酒春何淡,四海论交影更稀。”[2]240刚刚送走“雪满衣”的梅花,梅花的主人又随冬雪飞到初来的春天。墨梅是他的镜像,纵然是初春,依然是“一灯对酒”“影更稀”,这就是冰魂者的孤独。或许,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诠释“冰魂”的含义。李方膺《梅花册三开》之二(1739年,浙江省博物馆藏)自题云:“挥毫落纸墨痕新,几点梅花最可人,愿借天风吹得远,家家门巷尽成春。”“夜月耿冰魂”的墨梅——我们把它看作李方膺的自喻,“愿借天风吹得远,家家门巷尽成春”。孤独者把春风都给了家家门巷,却留给自己一片空寂,这便是“冰魂”者的胸襟与境界,是心高孤傲“江左狂生”的李方膺。
将梅花作为母题的图像中心的意象,在“扬州八怪”其他画家中也有,如汪士慎、金农、罗聘就是如此,他们以梅花为母题创作了不少的墨梅图。但他们的墨梅追赶时间太紧迫,恨不能冬去春来,追赶得太像春天脚步,梅花繁多,喜气盎然,似乎并不喜欢漫天飞雪,少了许寒意与淡远,少了些“冰魂”者的孤寂。当然,这也是另一种喻梅的意境。
李方膺的墨梅则是一番“千古秋雪”傲骨的意境。正如袁枚评价其墨梅云:“孤干长招天地风,香心不死冰霜下。……傲骨都作梅树根,奇才散作梅树花。”[2]209难怪李方膺希望通过“天风”吹得“家家门巷尽成春”。“春”不过是李方膺借梅之“香”的隐喻罢了,所指的正是“香心不死冰霜下”。墨梅的隐喻性是李方膺精神叙事结构的修辞方式。李方膺的墨梅图,的确放弃了“似”的追求,不像汪士慎、金农、罗聘画梅尽可能按照对象取舍,在笔上体现对象的特质,还遵循了梅花生长的形态与方向。李方膺的梅花树干是凌空横枝,极为简略与坚挺,不在乎对象的结构与形似,只重视梅花梅枝傲骨之气。他的墨梅册页几乎都是这种“骨气”横贯的图式,傲然挺立,凌空横斜。在凌空横斜的梅枝上,悬凝“冰魂”三两朵。“墨梅”作为母题不是一朵简单的梅花,而是意象的表达,它隐喻的是“冰魂”的象征意义,同时也映射李方膺的一个镜像——“冰魂”。这个镜像的分辨率很高,分辨出一个历经世态炎凉,傲然决绝官场和红尘世俗的清晰身影。“冰魂”的隐喻与镜像的成像,还是被李方膺的密友袁枚意识到。袁枚在《白衣山人画梅歌赠李晴江》中说的很明白:“人夺山人七品官,天于山人一只笔。笔花墨浪层层起,摇动春光千万里。……白发千丈头欲秃,海风万里归无家。傲骨都作梅树根,奇才散作梅树花。”[2]209李方膺失意官场还不仅在于官场上的你争我夺,更在于官场对他傲骨狂气与正直秉性的难以相信。人生经历就是如同梅花,冬去春来反反复复,但每复却不同,每个冬天的“寒冷”不一样,如同人生或宦海此一时彼一时,难以预料。梅花作为母题意象,在李方膺的“墨梅”那里看似语言简洁,着笔不多,但隐喻的是“傲骨都做梅树根,奇才散做梅树花”的“冰魂”。李方膺《梅花册十一册》之十(年代不详,安徽省博物馆藏)的自题也隐含了这层意义:“香雪凝华冷淡生,并无浓艳动人情。”这表面是对梅花的写照,实际隐喻自己孤独的“冰魂”。
三、母题镜像的精神叙事
袁枚在给李方膺的《李晴江墓志铭》中写到:“蟠塞夭矫,于古法未有,识者谓李公为自家写生,晴江微笑而已。”[2]1260这隐藏了个“天机”,即李方膺“为自家写生”。这个问题也被很多研究者注意到并有研究,但我要说的是,“为自家写生”实为前面我们所提到的“精神叙事”,叙事的是李方膺的“冰魂”精神。
中国古代文人大多因为秉性等因素总是官场不顺,对于宦海沉浮,他们总是以其他方式消解“失落”的情绪。长于善画弄诗文的文人,多是将消解的渠道寄托在书画世界里。诗、文、书、画、印为一体图像形式,成为中国绘画主要表达方式与主体结构,也许与文人的这种消解途径有关。我们谈“叙事”一般都是讲有“事件”发生,才考虑图像的叙事问题。如《洛神赋图》《女史箴图》《采薇图》《步辇图》《历代帝王图》《韩熙载夜宴图》《重屏会棋图》等,而较少将纯粹的山水画、花鸟画作为叙事因素来对待分析。如果我们把有“事件”的叙事称为事件叙事,那么对于有很多山水画和花鸟画隐匿的叙事结构,我们可以称之为“精神叙事”?何以要称为“精神叙事”,因为文人在不得志的时候,往往寄托于山林溪泉之间,寄托于花翎竹梅之间,寻求精神上的慰藉或依附。“猛志固常在”的陶渊明,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情画意中寄托自己的那份“惦记”,他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都是属于精神叙事的典型,以至于《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成为后世画家笔下的“归隐”母题,不少画家借此母题创作绘画作品,如传李公麟《归去来兮图》、周臣《桃花源图》、仇英《桃源图》、谢缙《溪隐图》、王绂《隐居图》等均是“归隐”母题。历代画家境遇不同,即使他们使用同一母题,其表达的方式与叙事结构也是不同的,这就是我们提到的母题变迁问题。但这里我们只探讨“精神叙事”。
我们看到宋元的文人,把一些概念视为一种意境或境界,如“寒荒”“萧简”“平淡”“消散”“简远”。这些概念往往是品评山水画的标准之一。文人把“平远”视为最高境界,本质上它隐含了精神叙事的结构。这个结构,郭熙说的很明确:“平远,意冲融而缥缥缈缈”[11]。这是“平远”的内涵,是“平远”意境的精神叙事;而“自近山而望远山,谓之‘平远’”,这是对“平远”的造景,为的是达到“精神叙事”的要求。这种精神叙事多少包含了古代文人对世俗现实或官场的不满,隐匿或归隐山林,寻林泉之心,求精神寄托。所以某种意义上讲,“寒荒”“萧简”“平淡”“消散”“简远”是精神叙事的主题,只是这种主题,一般在探讨绘画时被作为层面来分析主题意义,但亦有“意境”作为“美学”层面来分析(作为“美学”层面分析近乎荒唐)。我们可以认为,“意境”有不同层面,有不同的主题,都可以纳入精神叙事层次中进行探讨与分析。意境毕竟是有内容的,不是空洞虚无的。如苏轼《题渊明〈饮酒〉诗后》评陶渊明诗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12]“见”是会“意”,自然而然的悠然状态;“望”是刻意寻找,无“意”可言,便无意境,所以被苏轼批评为“俗”。神与自然的相会,便是苏轼评价的陶渊明的“意境”——精神叙事。那么绘画的意境是怎样进行精神叙事的?唐人朱景玄说:“至于移神定质,轻墨落素,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13]“移神定质”全在“轻墨落素”。这一逻辑思路在李方膺那里继承了下来。正如李方膺《梅花册》之七(1746年,南通市博物馆藏)自题:“梅花此日未生芽,旋转乾坤属画家。笔底春风挥不尽,东涂西抹总开花。”梅花的移神定质,全靠画家“旋转乾坤”来确立,“有象因之以立,无形因之以生”,所以“东涂西抹总开花”。我们找到这个逻辑路径,就容易理解李方膺通过“墨梅”母题的镜像完成他的精神叙事。
李方膺墨梅图的“叙事”结构,前面我们有所分析,他的墨梅的精神叙事主题就是郑板桥说的“冰魂”。“冰魂”者,洁白透明之魂。《说文》云:“魂,阳气也。”[14]188这冰之“魂”便是洁白透明之精气。李方膺“为官”一心为民,且因“为官”为民作想,得罪上级官僚而落狱。尽管如此,李方膺依然如故,丝毫不后悔。郑板桥用“冰魂”来品评李方膺的墨梅,实际上是品赞李方膺为官之道的品质与精神。我们看一看李方膺《庐州对薄》中的几首诗。
其一:“堂开五马气森森,明决无伦感更深。关节不通包孝肃,钱神无籍谢思忱。官仓自蓄三千秉,暮夜谁投五百金。能使余生情得尽,拂衣归去独长吟。”
其二:“三年缧绁漫呻吟,风动锒铛泣路人。是我不才驱陷阱,信天有眼鉴平民。情生理外终难假,狱到词繁便失真。念尔各收囹圄后,老亲稚子泪频频。”
其三:“公庭拥看欲吞声,愁听羁囚报姓名。万口同词天尺五,片言示法眼双明。肯从世道如弓曲,到底人心似水平。两度寒温诛父老,却因对薄叙闲情。”
其四:“红尘白发两无聊,赢得归来免折腰。七树松边花满径,五株柳外酒盈瓢。是非终古秋云幻,宠辱于今春雪消。莫笑廿年沉宦海,转从三黜任逍遥。”[15]
这里虽然有抱怨,但更有为官为民的愿望。同时,他把一切是是非非、得失荣辱都放下了,“是非终古秋云幻,宠辱于今春雪消”,谁对谁错,留给后世评判。
需要注意的是,精神叙事不同于事件叙事,它没有明确的时间、地点、事件或人物。如《韩熙载夜宴图》有历史文献记载,有相关的历史背景,有具体的人物、地点和时间等关键性的叙事要素。精神叙事需要更多的相关的其他外围资料,来帮助山水花鸟等母题的意象分析,再进入到主题学的层面进行解读与诠释。如上面我们借用了画家自题诗文,帮助我们阐释李方膺墨梅图的精神叙事。当然我们还是要依据图像本身所显示的母题、意象、套语、隐喻等叙事结构要素与修辞手段,来分析作品所传递出来的精神叙事主题。李方膺墨梅图是分析精神叙事的基本依据,研究者要仔细辨认图像中给出的各种母题元素,分析相同母题在不同艺术家那里乃至在不同时期的使用情况和方式,观察母题与图式结构变化。李方膺的墨梅如他自己所言是“瘦蕊”,这就是母题的微妙变化。其实仔细观察李方膺的墨梅,不仅仅是“瘦蕊”,整个墨梅的表达的都是“瘦”的形态(前已有论),墨梅的形状也脱离了梅花的原型,如同飘零的雪片凝结在树枝上。李方膺的墨梅不同于其他画家,正在于他的精神叙事主题是“冰魂”。
结语
冰魂如玉,以玉比德。“一片冰心在玉壶”,如冰似玉。这些修辞性的词语就是隐喻。孔子曰:“夫昔者,君子比德于玉。”[16]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云:“玉,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尃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洁之方也。”[14]10文人常自比“岁寒三友”,性格同构的缘故而喜好画梅、画竹、画松。扬州八怪都或以“岁寒三友”一物作为母题表达自己。李方膺独好梅,即无米之炊之时也以画梅为乐趣,他在《墨梅图》(1754年,故宫博物院藏)自题“十日厨烟断米炊,古梅几笔便舒眉”,便是写照。冰花雪蕊不仅仅使画家“满肚春风总不饥”,同时还更能使世人或画家自己“冰花雪蕊解人醒”(自题《墨梅图》,乾隆十又一年[1746年],端阳写于合肥五柳轩)。更何况“精神满腹何妨瘦,冰玉为心不厌寒”(自题《梅花图》,乾隆十六年[1751年]嘉平,写于合肥五柳轩),由好梅转向赞梅。这一转向,隐喻了李方膺性情转向人格精神,转向心灵,程度之深,深精入魂。故郑板桥称其为“冰魂”,赋以人格之喻。
参考文献:
[1]倪瓒.清閟阁集[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235.
[2]袁枚.小仓山房诗文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3]蒋宝龄.墨林今话[M].中国书画全书本.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958.
[4]冯金伯.国朝画识[M].中国书画全书本.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648.
[5]卞孝宣,卞岐.郑板桥全集[M].增补本.南京:凤凰出版社,2012:470.
[6]薛永年.李方膺其人其画[M]//中国古代名家作品丛书·李方膺.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04:4.
[7]周时奋.扬州八怪画传[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3:159.
[8]何平华,编.李方膺[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04.
[9]陶渊明.陶渊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7.
[10]袁枚.随园诗话[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1:125.
[11]郭熙,郭思.林泉高致[M]//潘运告,主编.宋人画论.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0:24.
[12]茅维,编.苏轼文集[M].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2092.
[13]朱景玄.唐朝名画录[M].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1985:2.
[14]许慎,撰.说文解字[M].徐铉,校订.北京:中华书局,1963.
[15]崔莉萍.江左狂生李方膺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114.
[16]孙希旦.礼记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9:1446.
(责任编辑、校对:李晨辉)
"Soul of ice ": Li Fangying's Inked Plum Blossom as Metaphor and Mirror Image
Li Beilei
[Abstract]Zheng Banqiao referred to the inked plum blossom by Li Fangying as the "soul of ice", which shed light on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image image as a motif.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inked plum blossom by Li Fangying lies in that with the ice- like thinned petals, the inked plum blossoms attach on cursive boughs, which mimics the thicks and thins the painter went through and the moral rules he stuck to in his career. The snow- flake- like inked plum blossom mirrors the noble life led by the painter, in which sense the image is a metaphor and a mirror in one.
[Key Words]Li Fangying;Soul of ice; Inked plum Blossom;Mirror Image; Loners; Spiritual Narrative
[作者简介]李倍雷(1960~),男,重庆人,博士,东南大学艺术学院美术系主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美术史论、艺术理论、油画创作。
[收稿时间]2015- 12- 23
[文章编号]1003- 3653(2016)01- 0018- 06
DOI:10.13574/j.cnki.artsexp.2016.01.002
[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