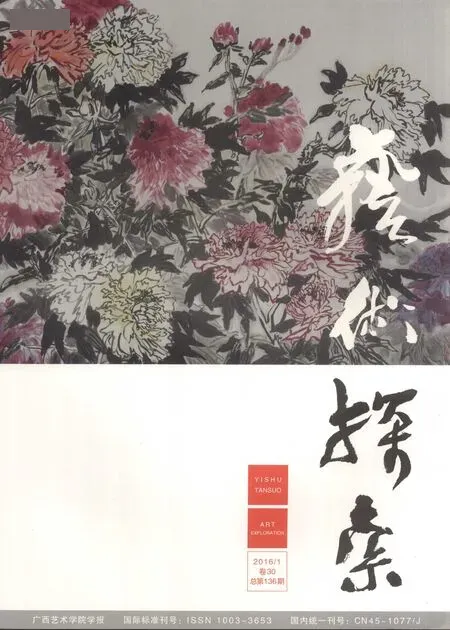艺术中的变形问题研究
向丽(云南大学 文学院,云南 昆明 650091)
艺术中的变形问题研究
向丽
(云南大学文学院,云南昆明650091)
[摘要]在美和艺术的形构中,变形是一种令人瞩目的表现手法。变形所蕴藉的情感与力量及其折射的世界往往是令人费解而又异常真实的。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艺术是社会生活关系的微妙刻写,它给予人们重新“看”世界的诸种可能性。在某种意义上,艺术作品中形象的变形乃是意识形态变形的产物。因此,研究艺术中的变形问题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描述艺术在形式方面呈现的面貌和特征,而在于尝试探究变形艺术的内在精神,探寻被遮蔽的现实生活关系如何在变形中得到显现和表征。在美学和艺术学研究中,艺术何为艺术以及艺术的功能和意义始终是不可逾越的问题,而艺术中的变形问题将以其特殊的存在方式成为这些问题的某种聚集。
[关键词]艺术;变形;意识形态;审美变形;审美人类学
在人类艺术创造的历史长河中,变形是一种令人瞩目又极富意味的表现手法。尽管变形所蕴藉的情感与力量及其折射的世界往往是令人费解的,但也是异常真实的。在某种意义上,艺术是社会生活关系的特殊写照,它给予人们重新“看”世界的诸种可能性。
无论人们是否将“变形”作为一个严肃的话题加以研究,在人类的各个艺术领域,形象变形的脚步却从未停歇,并为该艺术的永恒魅力添加了色彩。如古埃及的狮身人面像、古希腊神话中的蛇发女妖美杜莎、维吉尔《埃涅阿斯记》中凶恶的人面鸟身女妖、奥维德《变形记》中因观看招致惩罚而变为女性的忒瑞西阿斯、拉伯雷《巨人传》中力大无穷、智慧超群的巨人卡刚都亚和庞大固埃、卡夫卡《变形记》中变形为甲虫的人,中国上古神话中人面蛇身的女娲和伏羲,吴承恩《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等形象,都是人、神、怪多重属性杂糅。作为一种特殊的表现方式,变形的原因及其效果值得深究。变形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如为战胜自然灾害的变形、作为理想化身的变形、惩恶扬善的变形以及揭示和超越资本主义异化现实的变形等等。由变形而创造的艺术形象往往有一种能让人在陌生化的情境中重新体验人类情感的审美效应,甚至能激发出一种摄人心魄的精神力量。因此,变形在艺术创作和鉴赏中的作用以及变形与审美之间的关系问题就成为美学和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议题。
然而,在以往的美学研究中,变形与美的关系并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和探讨,即使有也多限于对文本艺术及现代、后现代艺术作品的分析,对于无文字社会和前现代社会中变形艺术的机制、特征及意义的发掘和阐释仍然留有空白。此种探寻的意义不在于描述艺术在形式方面呈现的面貌和特征,而在于尝试探究变形艺术的内在精神,感知那些曾经不可言说的和将要言说的存在。
一、形象变形与意识形态变形
从视觉角度看,变形一般表现为人或事物在身体或形式方面的形变和转化异于人们的习惯认知,然而,这绝非变形的全部内涵,甚至并非变形最为根本的意义所在。就形象变形的动机而言,此种变形实为意识形态变形的某种产物,也因此,当其与人类心灵再次相遇时,才会让人在震惊中重新体验人类曾经经历和将要经历的奇幻的世界。
在表现派、立体派、未来派、达达派、超现实主义、抽象主义、波普艺术等西方现代派艺术作品中,变形是一个常见的主题,作者往往借助形象、色彩等艺术质料的变形营造出一个荒诞不经的非人的世界。以绘画作品为例,挪威画家爱德华·蒙克的《呐喊》以极度夸张的手法描绘了一个高度变形的尖叫的人物形象,圆睁的双眼与深深凹陷的脸颊犹如骷髅,与画面中阴郁的色彩一起将视觉符号直接转化为那声凄厉的尖叫。这是蒙克在忧郁、惊恐的精神状态下,以扭曲变形的线条和图式表现他眼中的悲惨人生:人不再是人,而是一个找不到任何出路的尖叫的鬼魂。在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中,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女性的柔美和优雅,而是一群经过几何变形的怪诞的女人身体,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拉斐尔的《草地上的圣母》《美丽的女园丁》等画作中描绘的表现人性至善至美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在此画中,出卖爱情的身体之丑陋被毕加索肆意渲染。作者以立体主义的手法将多个视角所见之物叠合在一张平面上,通过身体各部分的倒错、叠加表现人物的失常。其中画面右边两个女人犹如戴着面具的狰狞脸孔让人禁不住想到从地狱爬出的鬼魅,给人以阴森恐怖之感。这种表现形式源于毕加索对于失却神性和人性的肉体的憎恶,是画家对于畸形倒错的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关系的扭曲以及人沦为机器的现实的揭示。然而也恰是这些丑陋的身体肆无忌惮挑战的模样构成了对矫饰人生的无情嘲弄。此外,达利的超现实主义绘画《记忆的永恒》中那似马非马的怪物,《西班牙内战的预感》中那个身体残缺不全、四肢彼此错位的人体,频频出现于德国画家巴塞利兹作品中的倒立的人像……这些作品展现的不再是一个正常的世界,而是一个光怪陆离的、破碎的、颠倒的、残酷的、疯狂的、无法修补的世界,或是一场渎神的狂欢。
我们该如何看待20世纪西方现代派艺术中的这种变形主题及其带来的诸多令人难忘的不安“表情”呢?尽管“美是什么”“艺术是什么”仍然是美学和艺术学研究无法完全解答的问题,但也正因此,与此相关的以新的方式展开的关于审美和艺术的探讨才令人如此着迷。马克思在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划分的论述中,将艺术明确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形式”来看待和加以探讨。不仅如此,在马克思主义美学视域中,作为意识形态的艺术又以两种方式存在:作为一般社会意识形态的艺术和作为特殊意识形态的艺术。前者强调艺术与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叠合性,因而侧重考察艺术的社会功用及其现实基础;后者强调艺术作为一种剩余价值与一般价值不同,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缺失的征兆,是对现实生活与意识形态之间发生断裂的表征和审美修复。因此,对这两种艺术的区分是把握艺术作为意识形态形式的特殊性的关键,它引发的问题是:艺术如何在社会内部建构反抗社会的维度?
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艺术不再是现实或理想的直接摹写,而是以特殊的方式成为现实生活关系的某种表征,或者说,它实质是一种对于缝合好的意识形态的重新撕裂,将那层温情脉脉的外衣直接剥开,让血淋淋的现实毫无遮拦地展露出来。具体而言,现代派艺术中的变形与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及其所影响的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表达方式之间有着紧密联系。现代工业社会中“人的异化”的日趋严重以及人与自然、社会、上帝的疏离,使得现代人笼罩在浓郁的孤独、苦闷、恐惧、无聊和绝望等情绪中。现代人的心理感觉与外在的世界不再处于和谐的状态,而且再也没有达到和谐的希望。因此,作品在欲望对象化的方式中往往以变形、破碎、荒诞、丑陋等不和谐的形象将那种欲望与满足之间的对立和分裂加以强化性的显露。[1]这是人们对于现代社会的一种独特的精神体验,尤其是当我们意识到在“洞穴人”卡夫卡的作品中,变形竟然成为人类自我解脱的方式时,这种体验似乎就更为令人震撼了,因此这些作品都不可作寻常看。在当代美学和艺术学研究中,艺术及其他审美感知形式如何作为人的更为精妙的延伸方式构成不合理现实生活关系的“反题”从而超越异化的现实,已成为一个重要课题,它首先需要进入到现实的内核才能解析艺术对世界独特的“看”的方式及其意义。
在无文字社会和前现代社会中,怪诞变形的形象更是不胜枚举,然而这种变形的价值和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和研究。按照西方传统认知,这种形式特征往往被归结为原始民族幼稚、写实能力低下以及表达方式拙劣的结果。例如比利时裔美国人类学家贾克·玛奎(Jacques Maquet)指出:“非洲的想象具有概念性的风格(conceptual style),欧洲人将其设想为由于手工艺人的无能而造成的变形和扭曲。”[2]36无可否认的是,在西方关于他者文化的认知和评价中,单线进化主义意识形态的幽灵仍然是难以消释的,它常常纠缠着人们的头脑,甚或梦魇般地游荡在人们的闲谈中,抑或向他人不经意投去的一瞥。例如凯·安德森(Kay Anderson)在《种族与人文主义危机》中揭示了西方19世纪晚期一种典型的种族话语,这些种族话语坚信种族特征及其差异根深蒂固地植根于人的身体之中,土著被认为是劣等种族,即使是被放在文明化工程之中,仍然被视为位于从自然进入文化的入口处,表现了人类进化的零度发展。[3]将自然形成的种族差异在文化的意义上加以夸饰性地区分,甚至将之作为常识嵌入人类的各种权术政治中,同样构建了关于人类审美习性的殖民史。
在很大程度上,这种殖民史表现于人们看待和处理“原始艺术”的方式中。无可回避的是,“原始艺术”本身就是一种神秘的无法完全被分类和阐释的事物,在某种意义上,它其实是原始民族制作的人工制品与西方人的兴趣以及将它们当作艺术品的翻译法相结合的产物。[4]139艺术史上常用的“原始”(Primitive)这个词,在以往有三个不同的指涉:第一是指在拉斐尔之前,介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两时期中间的艺术;第二是用来标示从殖民地带回帝国首都的战利品和“珍玩”;最后指的是贬低由出身于工人阶层(无产阶级、农人、小中产阶级)的男女艺术家所创作出来的艺术。这三种用法无疑都是在延续欧洲统治阶层的优越性。[5]许多学者对于“原始”的提法发出了质疑并提出了相应的替代方案。因为它在人们既有的意识形态中似乎已必然暗指落后的、野蛮的、幼稚的等基于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它自身也内含着诸多矛盾性和歧义。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在其著作《原始思维》(俄文版)的自序中表达了对于使用“原始”一词的矛盾心态:“‘原始’一语纯粹是个有条件的术语,对它不应当从字面上来理解……必须注意,我们之所以仍旧采用‘原始’一词,是因为它已经通用,便于使用,而且难于替换。”[6]1因此,我们可以在一种约定俗成的层面上仍然沿用“原始艺术”的称谓,只是需要尽可能地过滤掉附着在它身上的意识形态指涉和想象。
原始艺术中的变形与原始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有着紧密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原始艺术是集体表象的特殊呈现。“这些表象在该集体中是世代相传;它们在集体中的每个成员身上留下深刻的烙印,同时根据不同情况,使该集体中每个成员对有关客体产生尊敬、恐惧、崇拜等等感情。”[6]5因此,探究原始艺术如何表现原始形象与情感不乏是解析原始艺术“神秘性”的较好方式。而由于原始民族的表象与我们的表象有着较大的区别,这也带来了其表达方式上的差异。例如,“在原始人的‘表象改造’中,那些在一个对象物中最具生命原力的部分,在形状上也要变大,比如牛、鹿的角,鹰的嘴,兽的爪,等等。这在我们看来,它们又是变形的、怪诞的”[7]41。再如,“面具所代表的不是人们通常所熟悉的面孔,它是一种常人没有的面孔,它要引起的是陌生感而不是亲切感,因为面具所代表的不是人的表情,而是神秘世界中某种神灵所可能有的表情。正因为它要引起陌生感甚至恐惧感,因此它是不受人脸五官比例的支配的。它可以按照它的创造者的意图任意夸大某一部分或缩小某一部分。只有这样它才像另一个世界中的神灵”[8]。于此,如何使神性显现,如何通达人与神的交往和沟通就成为原始艺术变形的一个重要主题。
“力”(亦可称为生命力、生命原力或魔力)在原始部落中被视为一种特殊的存在,他们在表现改造活动中,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在力图激活出此种“力”以让渡人类的恐惧并表达出对于它的无限尊崇。西非许多部落所表达的“尼耶玛”(Nyama),东非、中非一些部落所表达的“玻瓦恩格”(Bwanga),以及美拉尼西亚人的“马纳”(Mana)等都指向了此种“力”的理念。这是一种无形的亦即无法用肉眼所能捕获到的存在,却是一种能够主宰和形构人类和自然秩序的力量。这种力可以来自神灵、祖先或自然本身,与各种信仰体系相互交织互渗,共同建构出原始民族所生活的精神现实,也因此,变形、奇幻、怪诞的艺术风格就自然生发出来了。如定居于象牙海岸北岸的塞努福族在被称作“克鲁布拉”(Korubla)的秘密结社中所使用的“喷火兽”面具(Fire-spitter mask)就以变形的方式表达着此种“力”。这种面具主要由每种动物最具神力的部位如羚羊的角、野猪的牙等组成一个神话式动物形象,此外,在羚羊角间还有一个鸟的形象,据说是塞努福族人的图腾。[7]167这是一个具有超凡能力的神圣实体,也唯有当我们意识到这一点甚至被它所感染时,作为一种独特的表现方式,变形的力量才会真正显现出来。
关于变形所赋予的力量,李泽厚在解析关于青铜时代艺术的“狞厉之美”时作了很好地阐释。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一书中指出,以饕餮纹为突出代表的青铜器纹饰属于“真实地想象”出来的“某种东西”,因为在现实世界中并没有对应的这种动物,它是统治阶层的“幻想”和“祯祥”,亦即其意识形态的一种转译形象。饕餮是一种高度变形、风格化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然而正是在那看来狞厉可畏的威吓神秘中却积淀着一股深沉的历史力量,因为它极为成功地反映了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时代,它的神秘恐怖正是与这种无可阻挡的巨大历史力量相结合,才成为美—崇高的,也由此展现出一种巨大的美学魅力。[9]53-63从艺术构型的角度看,艺术家之所以要采用变形的表现方式,是因为他们要表达的对象是不可用既有的语言和质料表达的一种更隐秘的存在,亦即变形要表现的恰恰是那不可表现之物,因此它所聚集和释放的恰恰是一种崇高之物。
事实上,当我们不再把艺术当成单纯的物质形态,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时,艺术将有可能以其存在方式给予我们某种答案。法国当代著名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较为明确地表达了艺术与意识形态之间的特殊关系,他指出:“每一件艺术作品,都是由一种既是美学的,又是意识形态的意图产生出来的……一件艺术作品能够成为意识形态的一个成分,就是说,它能够被放到构成意识形态、以想象的关系反映‘人们’同构成他们的‘生存条件’的结构关系保持的关系的关系体系中去。”[10]537尽管“意识形态”这个术语诞生的历史仅二百多年,但它却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庞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11]。这使得任何试图给意识形态一个明确的定义和界定的想法最终都是令人沮丧的。即便如此,阿尔都塞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是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的想象性关系的一种‘表征’”[12],仍可谓关于意识形态的较好诠释,其中“想象”作为链接个体与其真实存在条件之间的中介之作用被加以强调,它能够以最大限度的空间承载着现实生活关系在人们头脑中委婉而真实的显现方式,这恰好能够解释艺术表达的多元性与复杂性。因此,阿尔都塞特别强调:“艺术作品与意识形态保持的关系比任何其他物体都远为密切,不考虑到它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特殊关系,即它的直接和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效果,就不可能按它的特殊美学存在来思考艺术作品。”[10]537而这种特殊的美学存在如何显现恰恰是解答某物何以能够成为艺术品的关键,这是审美人类学①审美人类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近年来在国内当代美学、文艺学以及人类学领域中值得关注的学术发展动态之一。从现代知识体系不断互渗和融通的学术背景来看,审美人类学作为一门复合型交叉学科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中有效整合美学与人类学并超越其各自既定的局限性,激扬学科新质的有力尝试,同时也是深入探讨审美与现实生活以及历史进步之间关系的必然要求。在学理上,审美人类学尝试着厘清审美现象与其他文化现象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它将对审美和艺术进行考察的重点聚集在特定的审美感知和活动得以形成的社会文化机制之中,亦即探讨人们在关于“什么是美”以及“如何审美”方面所形成的观念和实践是如何被建构和规范的,“美”又是如何在这种建构中被遮蔽和显现。值得深究的极富意味的话题。
依着这样的研究路径,我们将发现,无论是原始艺术还是西方现代派艺术,其变形主题及其方式实则都是意识形态的一种表征,亦即作为表象的形象变形乃是意识形态变形的某种产物。然而,也正由于不同的个体/集体、不同的存在条件以及不同的想象方式,造就了原始艺术和西方现代派艺术变形的不同文化诉求和旨归。简言之,尽管两者的共同点都在于力图以特殊的方式使不可表现之物得以显现,但它们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是为了使对象变得可以理解,而后者则是使对象变得更为怪诞和不可理喻,甚至要穷极对象的荒谬性,从而显现另一种可能性的在场。有意味的是,意识形态自身的复杂性和诡异性在此可见一斑。然而,这似乎仍只是一个开始,当我们不囿于形象的变形,而关注到艺术现象中一种更为隐在的变形时,也许诸多与艺术相关的问题将浮出水面并最终聚集。此种变形归属于意识形态变形的范畴,指向的是一种隐而不显却异常真实的“艺术”资格授予与罢黜仪式,我们暂且以变形与“艺术”的“诞生”这样的话题来讨论一下。
二、变形与“艺术”的“诞生”
“某物何以能够成为艺术品?”这也许应当是每一位艺术评论工作者在对艺术品进行鉴赏和品评时首先要面对的问题,然而恰恰是这个问题,往往在人们的心照不宣中被当作一个习焉不察的常识轻而易举地打发掉了。对于这种有趣的现象,德国哲学家阿多诺(Theodor W. Adoeno)曾笑称之为一种“美学的不安全感”②阿多诺指出,传统美学理论家对具体的美学和艺术问题缺少关注,根源于他们有一种避免不确定性和争议性的普遍的惯例化倾向,不愿使美学暴露自己,进入无处隐藏或遮蔽的开阔之地,即不愿放弃从科学那里搬来的安全感有关。对于这种华而不实的安全感,阿多诺持强烈的否定和批判态度。参见(德)阿多诺《美学理论》,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59页、第593-594页。使然。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若是继续凭着形而上学的冲动尝试为艺术寻找一个“科学”式的界定,我们将很快发现,这是徒劳无益的。事实上,当我们首先从人类形构艺术的事实出发,事情也许会有一个好的开端。贾克·玛奎指出,在西方社会,艺术的形成主要诉诸两种方式,并因此区分了两种艺术:“有意制作的艺术”(art bydestination)和“通过变形产生的艺术”(artbymetamorphosis)。[13]其中,“有意制作的艺术”即属于被预设为具有审美特性的用于观看(tobelooked at)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艺术,它们被假定为将以其最高形式体现着人的审美追求。而“通过变形产生的艺术”则是西方审美意识形态的产物,即“它们被那些在历史上和地理上远离其雕刻者和观者的人通过变形使之成为艺术品”[2]33。这实则表明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通过变形产生的艺术”是一个极富意味的跨文化概念。首批由于变形而成为艺术对象的事物来自那些已丧失自身独立性的异域社会以及在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如农民生产的人工制品,这些物品在博物馆的脉络中变形为艺术。这部令人惊叹的艺术史,因为一种冠冕堂皇的授予仪式而开始于一场掠夺,而且此种掠夺还将继续。
众所周知,博物馆是一个将物集中起来供人观看的场域,但它又绝不仅仅是物的展示,而是物、人与社会秩序的特定建构,它是情境性的。或者可以说,博物馆具有特定的政治需求,并通过改变其表征实践而寻求自身的表达方式。而早期博物馆与殖民掠夺是脱不开干系的,因为展演其中的物本身就是这段历史的呈现。自此以后,“原始艺术”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形态进入西方人的眼中,并开始了它们奇妙的历程。根据审美人类学考察资料表明,“原始艺术”在此种历程中一般有两种境遇:因其在形式上契合西方人的审美眼光而被视为艺术品;因其形象的变形、怪诞被视为偶像或神物而非艺术品。在这两种境遇中,“原始艺术”看似遭遇了升格和罢黜的不同命运,但都是源于西方人“看”的方式的某种结果。
在贾克·玛奎看来,“将来自远方和被统治国度输入的物品吸纳为艺术一类的过程,在人类历史上,是古老而常见的。那些‘具艺术性’物品的制造者本身的语汇中,常常是没有‘艺术’一词的。是征服者把‘艺术’这项特质加诸于这些物品上,而战胜国的军队则将掳自战败国的战利品,并入母国的艺术现实中”[14]43。毋宁说这是一种建立在掠夺行为之上的艺术资格授予仪式,也因此,被征服者授予的战败国物品的“艺术”之称谓本身是值得考究的。首先,在这些战利品中,哪些被选择并被授予为艺术品,是由西方人“看”与阐释的方式所决定的。阿瑟·丹托(Arthur Danto)指出:“把某物视为艺术必须具有某种肉眼不能看到的东西——艺术理论的氛围、艺术史的知识,即一种艺术界。”[15]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在此基础上强调社会框架结构对于艺术的建构作用,并且主张把对象放到它们的制度性背景中进行考察。于此,“原始艺术”在西方社会中的遭际就不难理解了。
在西方传统美学①从西方美学发展史来看,传统美学一般指从古希腊到德国古典美学的美学形态。它建构于传统的形而上学基础之上,力图对审美和艺术的本质加以明确界说并在此基础上相应地提出一整套标准和规范,对人们关于审美和艺术的理解以及具体的审美活动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的理论视域中,某物之为艺术品,就在于它本身暗含了基于审美特性之上的诸种特征。以视觉艺术作品为例,它应是手工制作的,它需要某种技巧或技术,此外,它应是独特的,看上去是“美的”(beautiful),并且它应当表现某种观点,等等。其中,“美的”往往成为“艺术之为艺术”的更为根本性的规定。与此相应的是,追求关于美和艺术的一般概念或共相,把目光主要集中在那些作为美的典范的古典艺术作品和艺术美,青睐规范化和类型化的艺术形象以及情理统一和典雅的艺术风格也就成为西方传统美学的一个显著特征。在这种艺术界氛围中,被选择并被授予艺术品资格的物品往往在形式上表现出诸如对称、平衡、清晰、明亮、平整、光滑、富于装饰性、精妙等特征,从而营造出一种克制、内敛、冷静、明朗的美学风格,例如尼日利亚以利以非地区的约鲁巴人铸造的皇室祖先的金属头像就因其现实主义的理想化形式而闻名世界。[16]显然,这种授予是令人为之振奋的,因为它再次证实了非西方人能够表达自己审美观念这样一个长期被西方人误解的常识。
但同样令人遗憾的是,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这种在形式上符合西方人眼光的艺术品背后的思想与激情并没有得到更深入地发掘与阐释。因为某物之所以能够“升格”为艺术,通常是因为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与西方关于艺术品的观念相一致,也可以说,人们对于这些来自非西方社会的物品的关注仅仅是在它们从西方人的视野中变形为艺术之后。与此相应的是,人们并没有更多地从它们所由产生的特定语境和文化脉络中去考察。不仅于此,在这种神圣化的授予仪式中,由作为与日常生活或特定仪式融为一体的世俗或神圣的物品转变为艺术品,其中必然地包含了对它曾经的功用和宗教内涵的某种抛弃或悬置。简言之,它们更多地仅仅是因为表面上显得“美”而被冠以“艺术”的誉称,这无异于人们从艺术当中抽取了最表面的成分,然后用一种华丽而空洞的辞藻将其粉饰一般可笑。至少,这对于我们理解非西方艺术的审美价值是远远不够的。
在某物通过变形而成为艺术品的过程中,授予其实只是一种征象或为一种结果,而阐释则是更为关键性的。因为,某物之所以能够获取“进入”艺术现实的资格,中间必然经过阐释。而在阐释具有把实物这种材料变成艺术品的功能的同时,阐释本身是变形的。[17]另一方面,阐释同时也是一种区分。在将那些来自非文字社会中的人工制品与在文明社会中尤其是西欧和北美社会中的艺术品相比较中,它们往往被视为是拙劣和低级的,甚至仅仅因为能够作为维护和强化西方文明秩序的权力和荣耀才获其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正如当代英国文化研究著名代表人物托尼·本尼特(Tony Bennett)指出的,“尽管博物馆在理论上是民主的,向每个人开放,但在现实中已经证明是一种发展那些社会区分实践的非常显著的建设性技术……”[18]无疑地,这种区分同样构成了美学王国中殖民权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此种精妙的策略可能带来的结果是,某物也恰恰正是通过变形而被拒绝在艺术现实之外。令人称奇的是,这与某物通过变形而成为艺术的进程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在《美感经验——一位人类学家眼中的视觉艺术》一书中,玛奎以15世纪末从刚果王国运抵欧洲的人工制品为例,解释了非洲雕像为何难以成为艺术的两个主要原因:其一,非洲雕像身上奇怪的附加物及人形面部与神态的可怕威胁性,暗示了伤害的意图,其所代表的力量被认为与基督敌对,并且拒绝被收服,因此在西方现实的宗教范畴中,它们只能被看作是来自魔鬼阵营的作为负面实体的偶像和神物,但不是艺术雕像。其二,非洲雕像所呈现的概念性风格与当时在西方社会居于主流的理想自然主义(Idealized Naturalism)相冲突,这对于尊崇古典与情理统一的艺术美的西欧人而言,非洲形象很难不给人以丑陋而怪异的印象,也因此它们与艺术毫无关系甚至构成对于艺术的某种挑衅和中伤。不仅如此,在殖民地博览会与博物馆中展示这些物品,顺其自然地成为促进公众支持殖民扩张的公开宣传。[14]110-118于此,基于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之上的审美进化论使殖民掠夺变得有意义且可以被接受,这不能不说是西方艺术界对于非西方艺术实施罢黜所带来的让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由此可见,无论是“有意制作的艺术”还是“通过变形产生的艺术”都是源自西方特定意识形态的凝视。在以包含和排斥为潜在逻辑的制度性神圣化原则中,“艺术”被历史地生产与再生产出来,而“变形”成为保证这种生产与再生产的必要的幻象与中介。关于艺术的“是”与“不是”并非一种完全客观的判断,正如我们不可能抵达一个完全不需要中介的现实,“变形”在此成为我们理解艺术复杂性的一种不可忽视的文化现象。至此,“某物何以成为艺术”或与此相关的问题——“某物何以成为审美对象”又如何与“变形”相关?这似乎是一个更耐人寻味的问题。
三、审美变形:艺术形构的力量
一般而言,在审美人类学研究领域中,变形与艺术的相关性主要表现为以上我们谈及的两种方式:作为艺术表现的变形和作为艺术资格授予与罢黜的变形,前者涉及我们如何看待艺术作品中的变形及其价值意义,后者指向的是我们如何重新审视艺术现象中的意识形态,两者实则都是对于“‘美’的遮蔽与显现如何可能”以及“艺术将以怎样的方式让我们看见此种美的显现”问题的某种聚集。于此,“审美变形”将以其特殊的存在方式将“美”从其晦暗不明的空间带出。
审美变形首先是人类表现世界的一种特殊能力,具体而言,它指的是“人类运用其以想象力为核心的主体审美创造能力,通过激活和塑造人类精神活动所获得的意识形态材料,使它们摆脱认识属性与伦理属性的功利性束缚,从而使人类与对象世界的审美关系得以表达出来”[19]。可见,审美变形本身既是意识形态的产物,同时它又能够将意识形态作为凝视的对象,从而表现出历史与现实的真实镜像。因此,“研究审美变形问题的根本意义,不是为了说明审美变形在生理学和心理学方面的基础,而在于探询被遮蔽着的现实生活关系怎样在审美变形中得到显现和表征”[20]45。与此相应的是,在审美人类学领域中,我们关注的重心将不再是艺术怎样变形,而是艺术变形之后让我们看见了什么。而此种转向并非一蹴而就的,因为,艺术给予人的快感与痛感永远是相伴而生的。
当代美国分析哲学家简·布洛克(Gene Blocker)在《原始艺术哲学》一书中提出了“原始艺术是原始的吗”与“原始艺术是艺术的吗”两个结构相似的问题,集中探讨了原始艺术研究的两难境地。在他看来,这种困境与原始艺术如何进入人们的视野以及原始艺术自身的特性有着密切的联系。“事实上,原始艺术与别的艺术不同之处在于:它之所以成为艺术,不是由于那些制造这些物品的原始人类,而是由于那些购买和收藏它的欧洲人。它之所以是艺术,并非是因为那些制造和使用它的人说它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因为我们说它是。它是由于外来的宣判成了艺术。”[4]3于此,布洛克再次强调了“原始艺术”是作为“通过变形产生的艺术”而形构的这一跨文化概念之事实。跨文化的理解与阐释的困难早已是不言而喻,而尴尬往往在文化语境的“跨”与“观看”视点的凝固相对撞时发生。
布洛克指出,面对原始艺术,我们处于这样一种令人棘手的两难境地:一方面,如果我们从自己的文化出发主观地描述这些物品,我们就有可能造成一种认识上的混乱和错误,无法忠实于甚至会曲解这些物品制造者的真实意图;另一方面,如果我们试图客观地采用这些物品的原初制造者和观者的观点,那么该物用于巫术、宗教、仪式中的功利性意义的显现又会妨碍我们对于其审美和艺术价值的评析,它们作为艺术品的资格甚至在这种实用性中被自行取缔。[4]21这种美学上的感伤主义可谓再正常不过,我们甚至有理由相信,那些被美学宠坏的人们更愿意沉醉于第二种纠结所带来的快感。事实上,这与人们认为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与“美”有某种根深蒂固的联系有关。
在传统西方哲学和美学批评中,“艺术品”一般被认为“应当而且可以被熟练地划分为两个亚刺激,一种是语义的,一种是形式的,分别引起一种认知的、非审美的反应和非认知的审美的反应”[21]76。对于这种将形式与内容的严格区分作为审美与非审美的评价标准的常识性作法,荷兰美学家范丹姆(WilfriedVanDamme)认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错误的,并且他指出:“我们应当提出,审美反应是由形式—意义或者形式—语义刺激所引发的,并且将这种观念贯穿在整个研究当中。”[21]77这种提法将在很大程度上破除“美”寄寓于形式以及审美无功利的审美幻象,使“美”与艺术能够以更真切的“形式”得以展现。
抛却形式上带来的困扰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回到这个问题:“艺术变形之后我们看见了什么?”如前所述,在植根于原始宗教意识形态的高度变形、怪诞的形象中,仍然充满了我们今人所无法能“看到”的奇谲的想象。这主要源于在原始民族的眼中,世界是由人类既不能看见也触摸不到的超自然力量主宰的,或者毋宁说是一种填满了神性的虚空。因此,使神和不可知事物形象化从而成为可视或可把握的对象就成为他们的基本欲望所在。而那些在18世纪中叶后被西方美学命名的艺术门类——绘画、雕塑、音乐、舞蹈、诗歌等等,这些“奢侈的艺术”①“奢侈的艺术”在此是强调原始艺术所诉诸的形式和方式的繁复和精致性往往与当时社会的物质发展水平之间形成了强烈的不相称性,而这种“奢侈的艺术”则深刻体现出原始民族“看待世界”的独特方式。便在原始民族渴望与神灵、自然和他人沟通以及让渡恐惧的各种仪式中产生和延展开来,并且成为原始社会意识形态的表征方式。事实上,这些“艺术”最初并不是作为艺术出现的,而是他们的宗教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②与许多原始艺术一样,饕餮纹青铜器在其制造的最初并非是作为艺术品而出现的,李泽厚在《美的历程》中指出:“在宗法制时期,它们并非审美观赏对象,而是诚惶诚恐顶礼供献的宗教礼器,在封建时代,也有因为害怕这种狞厉形象而销毁它们的史实……而恰恰在物质文明高度发展,宗教观念已经淡薄,残酷凶狠已成陈迹的文明社会里,体现出远古历史前进的力量和命运的艺术,才能为人们所理解、欣赏和喜爱,才成为真正的审美对象。”这无疑为我们力图解答“原始艺术是否是艺术”以及“某物何以能够成为审美对象”等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成功的范例。它们往往与一些最原始的精神状态如交感和互渗巫术等扭结在一起,即使有也极少是为了纯粹的审美目的。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将它们当作艺术品加以看待,因为一种来自形式—意义刺激所引发的原始审美的巨大力量,正在于它能促使其制作者和观者体验到那种完全情感化、社会化、魔幻化乃至审美化的经验。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艺术的真正力量在于,它所表现的不是人的肉眼所能见之物,而是一种划破意识形态屏障之后人类所能体验到的最高存在。这种最高存在在中国表现为“道”,在西方表现为“神”,尽管人们对于“道”和“神”的经验不能完全等同于审美经验,但它至少提供了与审美经验类似的经验,即它能够使主体“自失”于一个与最高存在同在的想象的艺术世界之中。在原始艺术中,我们同样看到了原始民族表现这种最高存在的渴望,而且也正是由于这种最高存在的遥不可及、不可捉摸以及原始民族“野性的思维”,原始艺术在形式上采用变形的表现风格也就自然生发了。
于此,我们回到李泽厚解析的饕餮纹青铜器,它之所以能够作为艺术品体现出一种狞厉的美,就在于它能够恰如其分地表达出人类早期宗法制社会的无限光辉与荣耀。在那个时代,社会必须通过血与火的凶残开辟历史前行的方向,而吃人的饕餮恰好能够成为那个时代的最佳注脚。因此,正是以这种“真实地想象”出来的高度变形的可怖形象和雄健的线条才能表现出超世间的权威神力。对于此种怪诞的形象,用感伤态度是无法理解的。不仅如此,李泽厚还提出,远不是任何狰狞神秘都能成为美。后世那些张牙舞爪的各类人、神和动物造型,由于没有与这种不可复现的历史力量相结合而徒显其空虚可笑。[9]60-65因此,能够表现艺术力量的真正的变形绝不是为了变形而变形,它指向的是人类的更高存在经验。分析至此,我们是否可以尝试着做出以下结论:能够作为一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形式,表征出人类与世界的真实想象关系以及最高存在经验,并且选择了能够充分表达此种经验的形式的,我们可以认为它具备了被称为“艺术品”的资格。于此,是否发生了审美变形可以成为我们评判某物何以能够真正成为艺术品的一个重要标准。
除却这种评价机制自身无法完全涵盖的艺术复杂性之外,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让我们超越形式上的障碍,从形式—意义共同激发的艺术事实中去探讨真正的艺术法则。在这个问题上,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Ernst Grosse)说得非常清楚:“最野蛮民族的艺术和最文明民族的艺术工作的一致点不仅在宽度,而且在深度。艺术的原始形式有时候骤然看去好像是怪异而不像艺术的,但一经我们深切考察,便可看出它们也是依照那主宰着艺术的最高创作的同样法则制成的。”[22]这种艺术的法则不是别的,它正是审美变形的彰显。
或者说,审美变形居于艺术表现的核心。也如前文所述,西方现代派艺术作品正是通过选择与现实相疏离的变形形式力图超越异化的现实,从而指向一种更高的存在,是审美变形而非自然的摹写构成了它们向现实挑衅和召唤未来的力量。尽管原始艺术和20世纪西方艺术在审美变形的机制和指向上有着很大区别,但审美变形所赋予的力量仍是相通的。有意味的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1984年举办了一场以“20世纪艺术中的原始主义”为题的大型展览,尽管该展遭致“是否仍是民族中心主义宣传”的质疑,但至少使原始艺术的面孔更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无可否认的是,非西方艺术的表现力量及其付诸的特殊表达方式正在获得当代艺术家的肯定。例如,早在20世纪初,乌拉曼克、德安、布拉克、毕加索和马蒂斯等立体派艺术家就惊讶地发现,非洲雕像早已成功地完成某些类似的作品。那些非洲的传统雕刻师不拘泥于模仿视觉印象,大胆地用量块合成面具与雕像,而西欧图像(主要指基督或圣徒像)所呈现的人类特征则缺乏这种表现手法。艺术史学者维尔纳·哈夫特曼(Werner Haftmann)写到,他们(非洲雕刻师们)唤醒了为表现而变形的权利。桥派画家发现了在非洲面具和雕像的无书写形式的世界里,一种从临摹自然中解放出来的自由。这些法国和德国画家,率先认识到无文字社会雕刻品的形象具有的美学价值,艺术评论工作者也随之进入此探索的征程。[14]114-116然而,这仍然仅限于对原始艺术的变形在艺术表现方式上的肯定,对于其变形背后所包蕴的特殊精神世界,仍然是审美人类学亟待进一步纵深发掘的。
结语
将事物进行分类并建构一定的秩序,这是人类天生的需要。力量往往根源于结构中的关键位置,而危险则存在于结构中黑暗而又模糊的领域。“那些不能被明确划分为二元对立中某一极的事物就成为禁忌。比如讲,二元对立的两极分别是A和B,有一些事物既不能划分到A中去,也不能划到B中去;这些既非A又非B,或者既有A也有B的事物,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就成为人类焦虑的目标。他们焦虑得居然无法将这些事物明确地分类,而这是违反人类思维本质的。于是,干脆将它们列为禁忌。”[23]在某种意义上,艺术中的变形便以其异样的方式成为人类艺术批评史中的“禁忌”,因为,当分类与区隔成为社会控制的隐秘策略时,与众多“美的”艺术形式相较而言,它更多地只是游走在艺术的边界之外。但人类的发展史同样表明,重新表达“禁忌”是危险的,同时也是令人兴奋的。
在审美人类学研究中,“变形如何与艺术相关”是一个富于意味的话题,它聚集了人们关于“某物何以成为艺术品”以及“艺术的内在力量是什么”等问题的探讨。在既往的传统美学研究视域中,这些问题或许可以得到“安全的”界说,但它却无法公正地对待单一的艺术作品,宏大叙事的尴尬也许正在于此。
尽管如此,关于艺术必须是“美的”的审美意识形态仍然如幽灵般在人们的审美鉴赏中挥之不去。审美人类学研究表明,对于此种审美意识形态的认同,只会加剧艺术研究自身的限度。罗伯特·汤普森(Robert Thompson)在研究非洲文化时对有意制造的“丑陋艺术”(Intentional Ugliness)给予了特别关注,他引入“反美感的”(anti-Aesthetic)这一术语来讨论约鲁巴中有意制造的丑陋面具。他指出,严格地说来,“审美的”等同于“美的”,从该视角而言,有意制造的“丑陋艺术”就会被排除在美学研究的范围之外。①Robert Farris Thompson.AestheticsinTraditional Africa.Jopling, C.F., ed..Art and Aesthetics in Primitive Societies.New York:E.P. Dutton, 1971:379-381; Robert Farris Thompson, Black Gods and Kings. Yoruba ArtatUCLA, Berkeley,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1.这种排斥是应当避免的,例如,丹尼尔·比拜克(Daniel Biebuyck)用“丑陋中的美感”(aesthetic of the ugly)此表达来指涉莱加人(the Lega)有意制造的丑陋雕塑。[24]而范登霍特(Vandenhoute)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指出,只要把对艺术作品的审美经验构想为等同于对美的感知,那么,我们将“审美的”这个词语用于民族学研究领域以及一般社会学中,则会很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一旦我们将“审美的”等同于“美的”,那么,就会有大部分的审美生产和接受会被排斥在我们的研究领域之外。我们应当不仅为对美的感知经验,而且也要为“丑陋艺术”、喜剧、悲剧以及其他艺术形式的研究留有空间。[25]同样地,“变形”与“艺术”和“美”的显现如何相关应当成为美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美国当代艺术学学者埃伦·迪萨纳亚克(Ellen Dissanayake)曾这样向我们提问:人类已经被称为使用工具的人、直立的人、游戏的人和智慧的人,但为何就没有被称为一种“审美的人”呢?她指出,人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人类天生就是一种审美的和艺术性的动物。在许多时候,当“艺术”和“美”被提起,它们总是被看成人类智能的一种显现,一种需要专业的文化训练才可能获得的特殊能力。然而,艺术和审美远非被如此狭隘地界定,它们是人类最重要、最严肃也最为日常的事情的组成部分。[26]事实上,人们完全能够在不意指和阐释抽象的“艺术”和“美”的概念的时候,深刻而形象地感知和表达“美”。并且,只有当我们重新审视“变形”在艺术资格的授予与罢黜这段仍在继续着的历史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发掘艺术审美变形的真正力量时,我们才有可能“看见”更为丰富的“美”。无疑地,这将是审美人类学以其特殊的“看”的方式所能给予我们的有益思考。
参考文献:
[1]王杰,廖国伟,等.艺术与审美的当代形态[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76-82.
[2]Jacques Maquet. Art by Metamorphosis[J].African Arts.1979,12(4). [3]托尼·本尼特.文化、历史与习性[J].陈春莉,译.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2009(2):34.
[4]简·布洛克.原始艺术哲学[M].沈波,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39.
[5]约翰·伯格.看[M].刘惠嫒,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6]列维-布留尔.原始思维[M].丁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7]牛克诚.原始美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8]朱狄.原始文化研究——对审美发生问题的思考[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500.
[9]李泽厚.美的历程[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10]陆梅林,编.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文选[M].桂林:漓江出版社,1988.
[11]季广茂.意识形态[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12]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项研究的笔记)[M]//斯拉沃热·齐泽克,泰奥德·阿尔多诺.图绘意识形态.方杰,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61.
[13]Jacques Maquet.Introduction to Aesthetic Anthropology[M].Malibu:Undena Publications,1979:35-38.
[14]贾克·玛奎.美感经验——一位人类学者眼中的视觉艺术[M].伍珊珊,王慧姬,译.台北:雄狮图书出版有限公司,2003.
[15]ArthurDanto.TheArtworld[J].TheJournalofPhilosophy.1964,61(19):580.
[16]米歇尔·康佩·奥利雷.非西方艺术[M].彭海姣,宋婷婷,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27.
[17]阿瑟·丹托.艺术的终结[M].欧阳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 36-41.
[18]托尼·本尼特.文化与社会[M].王杰,强东红,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168.
[19]王杰,主编.美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144.
[20]王杰.马克思主义与现代美学问题[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45.
[21]范丹姆.审美人类学导论[J].向丽,译,民族艺术,2013(3).
[22]格罗塞.艺术的起源[M].蔡慕晖,译.北京:商务印馆,1984:235.
[23]万建中.禁忌与中国文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62.
[24] Daniel P Biebuyck. The Decline of Lega Sculptural Art[M]// Graburn, N.H.ed.. Ethnic and Tourist Arts.Berkeley,Los Angeles,London: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6:346.
[25]P.Jan Vandenhoute. Comment on Methods of studying Ethnological Art,by H.Haselberger [J]. Current Anthropology.1961,2(4):375.
[26]埃伦·迪萨纳亚克.审美的人[M].户晓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3.
(责任编辑、校对:关绮薇)
On Metamorphosis in Art
Xiang Li
[Abstract]In the shaping of beauty and art, metamorphosis is remarkable way of expression, with strength and inspiration puzzling and real at the same time. As special ideological presence, art is the subtle and vivid presentation of social life, which enables human beings to perceive the world in different perspectives. The fundamental significance of the present research does not lie in describing the formality and characteristics of art, but rather in interpre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metamorphosis of art and the ways it reveal the underlying truth of life. In the research on aesthetics and art, the definition of art as well as the function and significance of art can never be neglected, which finds eloquent expression in the metamorphosis of art.
[Key Words]Art; Metamorphosis; Ideology; Aesthetic Ideology; Aesthetic Metamorphosis;Aesthetic Anthropology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美学的基本问题及批评形态研究”(15ZDB02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审美人类学的学理基础与发展趋势研究”(12CZW019)。
[作者简介]向丽(1978~),女,广西桂林人,博士,云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美学、审美人类学。
[收稿时间]2015- 12- 23
[文章编号]1003- 3653(2016)01- 0051- 09
DOI:10.13574/j.cnki.artsexp.2016.01.008
[中图分类号]J02
[文献标识码]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