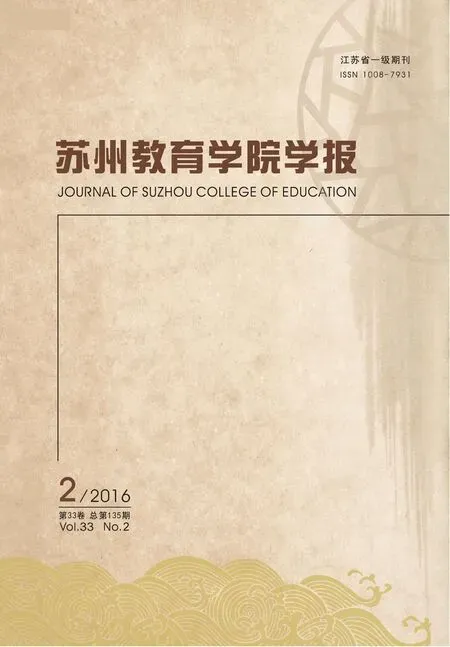小学儿童尴尬情绪理解能力、情绪状态对其合作行为的影响
丁 芳,范李敏,张 露(苏州大学 教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小学儿童尴尬情绪理解能力、情绪状态对其合作行为的影响
丁 芳,范李敏,张 露
(苏州大学 教育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摘 要:采用自编的小学儿童尴尬情绪理解能力测量材料和经典囚徒困境改编的合作游戏范式,考察76名小学4~6年级儿童的尴尬情绪理解能力和情绪状态对其合作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1)小学儿童的尴尬情绪理解能力对其合作行为有显著影响,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小学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2)尴尬情绪状态对小学儿童的合作行为有显著影响,体验到尴尬情绪的小学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3)在尴尬情绪状态下,高、低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小学儿童均倾向于做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在中性情绪状态下,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小学儿童比低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小学儿童倾向于做出更多的合作行为。
关键词:尴尬;尴尬情绪理解能力;情绪状态;合作行为;公平意识;小学儿童
引文格式:丁芳,范李敏,张露.小学儿童尴尬情绪理解能力、情绪状态对其合作行为的影响[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6,33(2):84-89.
一、引言
作为一种与个体认知能力和社会经验相关的自我意识情绪,尴尬情绪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有着重要作用。它不仅可以提高个体的人际交往能力,也影响着个体道德行为的发展和道德品格的养成[1]。尴尬情绪是个体因处于公众注意中心、失礼或棘手情境时而产生的一种别扭、紧张、懊恼、难为情、不知所措的情绪体验[2]。情绪作为一个基本的信号系统,它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他人对外在事件的真实反应,因而个体可以通过分析他人的情绪表现对其作出某种判断;同时,情绪作为一种重要的动机系统,往往能够激发情绪个体做出某种行为,比如合作行为。作为一种亲社会行为,合作行为是指两个以上的个体为了共同的目标,相互协调,共同完成某一任务的行为[3]。对成人面部表情的研究发现,囚徒困境中采取合作策略个体的面部表情更丰富[4]。有研究发现,丰富的表情比仅仅表露正性情绪更能体现个体的合作性[5-6],这表明情绪的表现能够使得他人将情绪个体视为更具合作性。而对于尴尬情绪的研究表明,发生违规行为后,表现出尴尬情绪的个体比没有表现出尴尬情绪的个体更受信任和喜欢[7],进而他人更愿意与这些表现出尴尬情绪的个体进行合作。可见,尴尬情绪是一种诱发个体合作倾向的有效信号。尴尬情绪理解是个体在具有一定自我认知的基础上,通过自我反思进而形成的对尴尬情绪的认知[8]。已有研究表明,高情绪理解能力的个体往往更倾向于做出亲社会行为[7]。随着年龄增长,小学儿童自我的独立性增强,形成了“别人怎么对我,我就怎么对待别人”这种简单的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公平意识[8]。小学儿童自我意识情绪理解能力与其亲社会行为水平呈显著正相关[9]。移情、道德推理、观点采择是影响亲社会行为发生的三个重要因素[10]。这三者可能属于亲社会行为产生的内因,而亲社会行为的真正引发还需要有外在诱因的呈现[11]。
我们认为,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尴尬情绪的展现很可能就是诱发个体亲社会行为尤其是合作行为的外在诱因。一方面,尴尬个体意识到自身所处尴尬状态,为避免自我形象受损,维护已有的人际关系和自我形象,进而试图采取弥补策略,如合作行为、助人行为等亲社会倾向;另一方面,旁观者对个体尴尬情绪表现进行识别和归因,进而对尴尬个体采取宽容和信任的态度。尴尬情绪理解能力高的个体更能在社会交往过程中识别他人的尴尬情绪,并倾向对尴尬个体做出亲社会行为。国内以往有关尴尬情绪的研究被试多集中在大学生等成人被试上,缺乏对小学阶段儿童的研究,并且国内也未见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尴尬情绪对合作行为影响的实证研究。因此本研究拟探讨小学儿童的尴尬情绪理解能力和尴尬情绪状态对合作行为的影响,以考察尴尬情绪在儿童道德行为发展中的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被试
随机选取苏州工业园区某小学4—6年级学生130人,采用自编的小学儿童尴尬情绪理解能力测量材料[8]进行测查,选取得分较高的27% 儿童分配到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组,得分较低的27%的儿童分配到低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组,每组38人共76名被试参与研究。其中男生40名,女生36名,平均年龄为11.68岁,标准差为1.05。
(二)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2(尴尬情绪理解能力:高,低)×2(情绪状态:尴尬情绪,中性情绪)的组间实验设计,因变量是合作行为。
(三)实验材料
1.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测量
采用自编的小学儿童尴尬情绪理解能力测量材料。收集到的尴尬情境故事来自小学儿童常见的生活事件,主要分为注意中心情境、失礼情境和棘手情境。每种故事情境各有2个故事,共6个尴尬情境故事。每个故事后都附有两个问题:主人公当时是什么感觉?主人公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经过一致性评定和内容效度的评定,最终确定的尴尬情境故事可以用于正式研究。
被试在每种情境中的尴尬情绪理解分是各情境中尴尬情绪体验分加尴尬情绪原因理解分。每个情境故事中,当被试的尴尬情绪体验分数为0时,该情境故事的情绪原因理解也记0分。每个被试的尴尬情绪理解分是3个情境的尴尬情绪体验分外加情绪原因理解分。具体记分如下:(1)情绪体验:①正确的情绪描述,如尴尬、害羞等,记2分;②相关的情绪描述,如不好意思、难为情、紧张、丢面子(脸、人)、别扭、不知所措、难堪、糗等,记1分;③错误的情绪描述,如高兴、自豪、害怕、惭愧等,记0分。(2)情绪原因理解:①他人评价归因,即他人对其行为的评价或看法等,如他这样做别人不高兴等,记2分;②行为归因,即自身行为或行为结果,如他说错话了等,记1分;③错误归因,如不知道等,记0分。
2.尴尬情绪强度评价表
提供一排数字(0—10)供被试选择,让被试在参加完活动和阅读完故事后选择所体验到的情绪强度,数字越大表示情绪越强烈,0则表示没有体验到。
3.合作行为的测量
采用由经典的囚徒困境两难游戏改编而来的合作游戏程序来评估被试的合作行为[12]。白色纸质卡片2张,大小一致,字母C或D印在卡片的中央(字体、大小一致,C代表合作,D代表竞争)。合作游戏共18次,6次为一组,在事先分发的记录表中分别记下被试自己和合作伙伴所选择的字母。写有游戏规则的小卡片:如果两人都出C,则各得3分;如果一个出C,一个出D,则出C者得1分,出D者得5分;如果两人都出D,则各得1分。当被试选择C时即为合作行为,每选择一次C就记l分,分数越高表示合作行为越多。被试在18次游戏中所出的C的次数就是其合作行为的分数。
(四)研究过程
实验过程配备主试和助手各1名,均为心理学硕士研究生。实验前主试对助手进行相应的培训,确保在实验过程中的操作保持一致性。本研究过程如下:
首先,将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组和低尴尬情绪能力组被试在匹配年级和性别后随机分配到4个组合中,即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尴尬情绪组、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中性情绪组、低尴尬情绪理解能力+尴尬情绪组、低尴尬情绪理解能力+中性情绪组,每组19人。然后,尴尬情绪组被试首先被要求参加一个“怎么说就怎么做”的活动以诱发其尴尬情绪。活动中,尴尬情绪组被试被带到一个教室,然后被随机分成5组,分别当众完成:学牛叫、唱儿歌《两只老虎》、学公鸡走路、互相恭维对方3个不存在的优点、扮3个鬼脸。中性情绪组被试则阅读一篇中性情绪故事。
其次,将被试按照尴尬情绪组和中性情绪组分到两个教室。被试首先需要在事先发给被试的表格上,从0—10之间选择一个数字并打钩来描述在刚才活动中所引发的尴尬情绪的强度。待确定被试填完后,主试向所有被试发出指导语1:
亲爱的同学:你们好!接下来你将要和一位伙伴玩一个卡片游戏,而这个和你一起玩的伙伴就是刚才人群中的某一位同学,他(她)看到了你刚才所做的所有动作。此时你的伙伴在另一个教室,你看不到他(她),也无法和他(她)说话。请你仔细想象当你知道你要和这样的伙伴一起玩游戏时,你会怎么做。
接着宣布指导语2:
游戏的规则是这样的:每次游戏时你和你的伙伴各出一张牌,你们出完牌之后,老师会告知你的伙伴出的是什么。这时你要在发给你的表格上记录下来每一次你自己出的什么牌、伙伴出的什么牌以及相应的得分。如果两人都出C,则各得3分;如果一个出C,一个出D,则出C者得1分,出D者得5分;如果两人都出D,则都得1分。这些游戏得分规则写在你面前桌子上的小卡片上,你随时可以参照得分规则来出牌。游戏结束后按照两人得分之和算出小组得分,排出全部小组的前三组发奖品,同时按照个人得分高低排出个人前五名发奖。每次游戏中每个人的分数都是由你和伙伴共同决定的,所以你要认真想好再出牌。游戏共进行三轮,每轮6次,共18次,每三次中间休息半分钟,每两轮中间休息2分钟。
待被试理解游戏规则后开始游戏。游戏过程中,主试走出教室,假装到另一个教室收取其伙伴的出牌,因此故意在教室外停留一段时间。停留期间,在确保被试没有发现的情况下,由一名专门负责分发牌组的助手将事先准备好的牌按照轮数依次递给主试。然后主试回到教室,发给被试,并要求被试将对方出牌记录在表格上,并强调保持安静,不得交流出牌信息。实验中,被试收到的对方出牌为主试事先抓阄决定,顺序为:C-C-D-C-D-C-C-D-C-C-C-D-C-D-C-D-C-C。
三、结果
(一)小学儿童不同情绪状态诱发结果的比较
在进行合作游戏之前,尴尬情绪组被试的诱发情绪为尴尬情绪,而中性情绪组被试为中性情绪。结果表明,尴尬情绪组别是(M=7.67, SD=1.88)比中性情绪组被试(M=2.33, SD=1.96)报告出更高的尴尬情绪体验,且差异显著(t(70)=12.79, p=0.000<0.05)。这说明用以诱发被试尴尬情绪体验的活动是有效且能够产生区分的。
(二)小学儿童尴尬情绪理解能力和情绪状态对其合作行为的影响
以小学儿童的合作行为得分作为因变量,以尴尬情绪理解能力和情绪状态作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表明,尴尬情绪理解能力主效应显著(F (1,72)=11.52, p=0.001<0.05, η²=0.15),说明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被试比低尴尬情绪理解能力被试更倾向于采取合作行为。情绪状态主效应显著(F (1,72)=12.77, p=0.001<0.05, η²=0.16),说明处于尴尬情绪的被试比处于中性情绪的被试采取更多的合作行为。尴尬情绪理解能力与情绪状态之间交互作用边缘显著(F (1,72)=3.02, p=0.087, η²=0.15),进一步简单效应检验表明,在尴尬情绪组中,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被试与低尴尬情绪理解能力被试都倾向于做出合作行为,不存在显著差异(F (1,72)=1.30, p=0.258>0.05);在中性情绪组中,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被试与低尴尬情绪理解能力被试在合作行为上存在显著差异(F (1,72)=13.91, p=0.000<0.05, η²=0.28),前者比后者做出更多的合作行为。
四、讨论
(一)不同尴尬情绪理解能力和情绪状态对小学儿童合作行为的影响
本研究发现,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被试比低尴尬情绪理解能力被试更倾向于采取合作行为,并且处于尴尬情绪的被试比处于中性情绪的被试采取更多的合作行为。这与我们的假设相符。有研究表明,小学儿童自我意识情绪理解水平与其亲社会行为呈显著相关[9]。这是因为自我意识情绪作为一种与自我意识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的情绪,个体自我意识情绪理解能力越高,表明其自我意识水平也越高,自我意识水平高的个体对自身和他人的情绪有着更为准确和精细的把握,进而对情绪原因作出情境性和心因性解释,认识到外部事件通过个体的愿望和信念对个体情绪的影响,从而设身处地地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13]。这种从他人角度考虑问题的能力就是移情或共情。其中,移情分为情绪性移情和认知性移情,情绪性移情是与生俱来的,其发展呈现U型轨迹,即从婴儿期直到成年期呈现下降趋势;认知性移情发展相对较晚,从个体出生直到成年呈现上升趋势[14]。有研究表明,学龄儿童的移情水平随年龄增长而增长,其认知性移情[15]和情绪性移情[16]均与亲社会行为成正相关,而与反社会行为成负相关[17]。同时随着年龄增长,儿童与生活环境中的人和物体不断互动,逐渐把自己与其他人和物体区分开来,并学会使用言语表述主观我和客观我,能够对自己进行消极和积极评价,自我概念不断发展[18],并逐渐形成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公平意识,使得自身行为遵守并符合社会规范[8]。最近有研究者提出,尴尬作为一种消极情绪,不仅仅扮演一种非言语的道歉和安抚功能,同时也是一种亲社会行为和信任的标志。旁观者将个体尴尬情绪的出现视为一种亲社会性和承认彼此亲密关系的信号,进而旁观者对尴尬个体表现出亲近行为,包括对尴尬个体更多的信任以及更强烈的亲近倾向[7]。
在本研究中,相比于低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儿童,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儿童更容易识别和注意到参加情景游戏后个体所表现出的尴尬情绪,这种认知性移情所带来的情绪识别和采择有利于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儿童站在对方的角度体验和理解对方的感受,进而对表现出尴尬情绪的个体更具信任和理解,也就更愿意与其进行合作;而相比没有激发情绪的被试,通过在公开场合举行情景游戏以激发其尴尬情绪,这些被试意识到自身不当行为可能影响到同伴和同学对其个人形象和人际关系的影响,这种情绪性移情使得尴尬被试在参加随后举行的卡片游戏时,更多倾向于采取合作行为,以便能够重新获得认可。因为个体越倾向于合作,其个人总分和团队总分也就越高,因而能够获得公开奖励和公开表扬,进而恢复先前其因尴尬行为带给自身的不当影响。这可能就是尴尬情绪理解和尴尬情绪状态主效应显著的原因。
(二)尴尬情绪理解能力和情绪状态在小学儿童合作行为上的交互作用
数据分析结果表明,尴尬情绪理解能力与情绪状态对小学儿童合作行为的交互作用边缘显著。进一步的简单主效应检验表明,尴尬情绪激发组,无论被试尴尬情绪理解能力高低,均更倾向于做出合作行为;在中性情绪组,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被试比低尴尬理解能力的被试做出更多的合作行为。简而言之,相比于个体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高低(即认知性移情),尴尬情绪的激发(情绪性移情)对个体合作行为促进作用更显著。这体现了尴尬情绪对合作行为的激发功能。因为个体合作行为的激发需要个体存在强烈的动机,而动机的强弱又与个体内驱力的大小有关。尴尬情绪的激发使得个体内驱力的信号得以放大,进而唤醒和激发个体的合作行为[19]。同时根据抚慰说的观点,个体体验到尴尬情绪后,感受到社会关系因自身行为受到影响,为避免自我形象受损,维护已有的人际关系和自我形象,个体更表现出具有安抚作用的顺从和合作行为[20]。
至于在中性情绪组,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被试比低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被试做出更多的合作行为,这可能与个体情绪理解能力中观点采择部分有关。在儿童情绪情感认知的发展过程中,观点采择能力起着重要作用,移情是儿童观点采择能力在情绪情感认知发展中作用的集中表现[21]。在缺少情绪激发的状态下,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个体更能够从对方的角度和立场来体会和感受其内部心理活动,进而推测和理解对方的观点和态度,为自身作出合作倾向的判断提供依据。而且高情绪理解能力的形成往往来源于儿童在丰富的社会交往过程中对他人、自我、其他社会关系的认知和理解。同时对个体社会排斥的研究发现,个体受到的社会排斥会显著减少其亲社会行为[22]。为避免这种潜在的社会排斥,在缺乏情绪激发的状态下,高尴尬理解能力的个体能够通过观点采择,最大化地充分利用情境和事件线索来体会和理解对方情绪状态和观点,以便作出合作行为的选择。
五、结论
(1)小学儿童的尴尬情绪理解能力对其合作行为有显著影响,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小学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
(2)尴尬情绪状态对小学儿童的合作行为有显著影响,体验到尴尬情绪的小学儿童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
(3)在尴尬情绪状态下,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和低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小学儿童均倾向于做出更多的合作行为;在中性情绪状态下,高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小学儿童比低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小学儿童做出更多的合作行为。
参考文献:
[1] 俞国良,赵军燕.自我意识情绪:聚焦于自我的道德情绪研究[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9,25(2):116-120.
[2] SABINI J, SIEPMANN M, STEIN J,et al.Who is embarrassed by what?[J].Cognition and Emotion,2000, 14(2): 213-240.
[3] 赵章留,寇彧.儿童四种典型亲社会行为发展的特点[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22(1):117-121.
[4] SCHUG J, MATSUMOTO D, HORITA Y, et al.Emotional expressivity as a signal of cooperation[J].Evolution and Human Behavior, 2010, 31(2):87-94.
[5] BOONE R T, BUCK R.Emotional expressivity and trustworthiness: the role of nonverbal behavior in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J].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2003, 27(3):163-182.
[6] KRUMHUBER E, MANSTEAD A S R, KAPPAS A, et al.Facial dynamics as indicators of trustworthiness and cooperative behavior[J].Emotion, 2007, 7(4):730-735.
[7] FEINBERG M, WILLER R, KELTNER D.Flustered and faithful: Embarrassment as a signal of prosociality[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2, 102(1):81-97.
[8] 丁芳.小学儿童尴尬情绪理解能力的发展[J].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60(2):11-20.
[9] 王昱文,王振宏,刘建君.小学儿童自我意识情绪理解发展及其与亲社会行为、同伴接纳的关系[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1,27(1):65-70.
[10] EISENBERG N, ZHOU Q, KOLLER S.Brazilian adolescents’prosocial moral judgement and behavior: relations to sympathy, perspective taking, gender role orientation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J].Child Development, 2001, 72(2):518-534.
[11] 余宏波,刘桂珍.移情、道德推理、观点采择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进展[J].心理发展与教育,2006,22 (1):113-116.
[12] 丁芳,郭勇,王晓芹.小学儿童心理理论、合作行为、“马基雅维里主义” 的关系[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0,28 (3):61-67.
[13] 宋尚桂,佟月华.小学儿童情绪理解的发展特点[J].心理科学,2009,32(3):709-711.
[14] 黄翯青,苏彦捷.共情的毕生发展:一个双过程的视角[J].心理发展与教育,2012,28(4):434-441.
[15] EISENBERG N, LIEW J, PIDADA S U.The longitudinal relations of regulation and emotionality to quality of Indonesian children’s socioemotional functioning[J].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4, 40(5):790-804.
[16] 耿耀国,叶青青,夏丹,等.初中生悲观人性观和情感移情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J].中国公共卫生,2011,27(10):1308-1309.
[17] 冯维,杜红梅.国外移情与儿童欺负行为研究述评[J].中国特殊教育,2005(10):63-67.
[18] 董会芹.学前儿童问题行为与干预[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162.
[19] 陈少华.情绪心理学[M].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8:140-141.
[20] KELTNER D, ANDERSON C.Saving face for Darwin: the functions and uses of embarrassment[J].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0, 9(6):187-192.
[21] 庞丽娟,田瑞清.儿童社会认知发展的特点[J].心理科学,2002, 25(2):144-147.
[22] TWENGE J M, BAUMEISTER R F, DEWALL C N, et al.Social exclusion decreases prosocial behavior[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7, 92(1):56-66.
(责任编辑:宋现山)
The Influence of Primary School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Ability of Embarrassment and Emotional State on Their Cooperative Behavior
DING Fang, FAN Limin, ZHANG Lu
(School of Education, Soochow University, Suzhou 215123, China)
Abstract:With the measuring materials for primary school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of embarrassment compiled by the co-authors and the classic prisoner’s dilemma model, the research explored the influence of 76 primary school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ability of embarrassment and emotional state from grade 4 to grade 6 on their cooperative behavior.The results are shown as follows: (1) Primary school children’s understanding ability of embarrassment had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ir cooperative behavior, i.e.children with high understanding ability of embarrassment showed more cooperative behavior.(2) Embarrassment emotional state had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primary school children’s cooperative behavior, namely, children experienced embarrassment showed more cooperative behavior.(3) In an embarrassment state,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with high and low understanding ability of embarrassment tended to conduct more cooperative behavior; in a neutral emotional state,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with high understanding ability of embarrassment tended to conduct more cooperative behavior than children with low understanding ability of embarrassment.
Key words:embarrassment; understanding ability of embarrassment; emotional state; cooperative behavior; awareness of fairness; primary school children
中图分类号:G44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931(2016)02-0084-06
DOI:10.16217/j.cnki.szxbsk.2016.02.018
收稿日期:2015-12-01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14SJB512)
作者简介:丁 芳(1971—),女,回族,山东泰安人,教授,博士,研究方向:儿童认知与社会性发展;范李敏(1988—),男,湖北武穴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张 露(1989—),女,江西玉山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