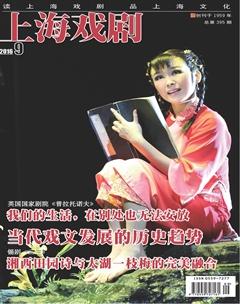白嘉轩为何而哭?
千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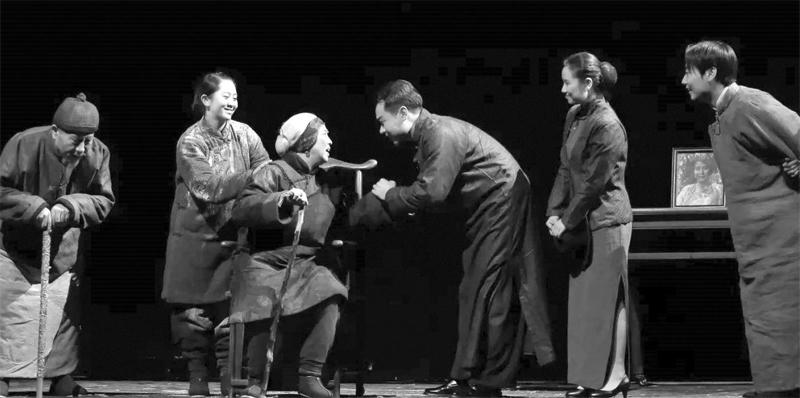
看完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的第一感受是“眼花缭乱”,《白鹿原》的主要情节如走马灯一般被剪贴上舞台。相比电影《白鹿原》从黑娃、田小娥这条线索叙述白鹿原白、鹿两家与大时代的故事,话剧《白鹿原》野心更大,要在两个多小时里演绎五十万字的小说,其叙述密度之大、节奏之紧凑可见一斑。看到了小娥奔月化蝶之凄美;鹿三杀死小娥后的疯魔;孝文从面上有笑到面上有刀;鹿子霖的贪欲阴险与可悲。然而原本是小说第一主角的白嘉轩却激不起人更深层次的悲悯,反而让人疑惑,这是白嘉轩吗?
或许由于篇幅的限制,陕西人艺版《白鹿原》给白嘉轩中心舞台的机会寥寥无几。大幕拉开,白嘉轩与鹿子霖在冷先生、朱先生的陪同下签换地契约,不知内情的白母赶到,阻挠嘉轩卖地,嘉轩不顾母亲气晕,坚持与鹿子霖完成交易。白嘉轩换地是白家从没落转向兴旺的转折点,换地之前的白嘉轩是个接连遭遇命运打击的落魄后生,做人做事都不那么有自信。北京人艺版《白鹿原》在演绎此场时,白嘉轩穿着破棉袄,换地时的口气带着几分谦卑几分狡黠,更令人信服;陕西人艺版的白嘉轩则一身华服,秉承着“腰杆很硬”的形象说话、做事,似与当时白嘉轩的心境不符,但这或许也是本剧给白嘉轩定下的基调决定的。
白嘉轩在白鹿原担任族长时的那些“义举”在剧中并没有呈现,仅以歌队交代了白家家境好转后的一些境况,捎带说了一下寡妇卖地嘉轩接济的事宜,难以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然后便是第二场,白鹿原上三个后生晚辈白孝文、鹿兆鹏、黑娃的婚事。在小说中,这三人的婚事并不在同时,为满足话剧舞台对戏剧冲突的强调,将此三人的婚事放在同一场戏中,彼此映衬,也是高妙的做法。而我们亦可以从舞美设计、人物设计看出创作者的态度。第二场戏发生在白鹿原的祠堂里,舞台上有高耸的牌坊,厚重的《乡约》石碑,高挂的“仁义白鹿村”牌匾,一排排祖宗的牌位,冷冷的侧光打在这些“建筑”上,充满了神秘、阴冷的气氛。这些小说中的核心意象,在剧中由于没有背景故事的交代,剩下的恐怕只有标签化的所指。婚礼上,白嘉轩端坐一方,他的儿子明媒正娶、门当户对,儿子恭顺、媳妇乖巧,却也最死气沉沉;与之相对的,鹿子霖的儿子鹿兆鹏要追求新思想,拒绝封建包办婚姻,是我们熟悉的“五四”话语;而黑娃与小娥的亮相最为惊艳,小娥一身红袄,仿佛萌萌的“傻白甜”,要把白鹿原当作月亮,当白嘉轩拒绝他们进祠堂祭祖,便一把拉起黑娃说要去奔月。创作者这样处理的意味是不言而喻的,白鹿原祠堂与《乡约》作为束缚人性与自由的意象,白嘉轩作为封建家长的形象呼之欲出。
接下来,白嘉轩为数不多的几次亮相中,先是让母亲与妻子规劝儿媳闺房事宜,再是把白灵锁在家中,禁止她上新学堂,导致白灵离家出逃;白孝文被小娥诱惑时,白嘉轩在屋外大喊“如果你在里面,就死在里面,别出来了”,祠堂内毒打孝文,赶出家门……一连串这样的事件非常容易唤醒观众记忆库里熟悉的“封建家长”形象,而忽略了白嘉轩身上其他的可能性,以至于当“农会”批斗鹿子霖们、田福贤们批斗闹“农会”的人、黑娃几次被捕时,白嘉轩的下跪或求情会因为缺乏铺垫,让人觉得有些苍白与突兀,难以成为丰富人物形象的表征。最后当“仁义白鹿村”的牌匾被倒置在舞台上,白嘉轩坐在一边大哭时,观众更不禁要问,白嘉轩究竟为何而哭呢?
白嘉轩究竟为何而哭呢?白嘉轩是在为鹿子霖的悲惨境遇而哭?还是在为自己欺骗鹿子霖换地遭遇的良心谴责而哭?他又为何在这个倒置的“仁义白鹿村”牌匾边哭呢?从整剧给我们的印象来看,一个落后“封建家长”为被打碎的“封建枷锁”而哭,又有什么能引起观众悲悯的呢?这原本应该激发更多意义与思索的一幕或许因为白嘉轩这个人物本身意义的失落而失落。
我们还是回到小说里吧,白嘉轩是白鹿原上白、鹿两家的族长,家境殷实,有号令全族的权威。熟悉20世纪革命历史叙事的读者不难发现,白嘉轩这样的人物是革命小说中的“旧人”“地主”,是被讨伐批斗的对象。而在陈忠实心里,白嘉轩就是白鹿原,用一部《乡约》撑起了原上的仁义与纲常,“去革命化”叙事的意图不言而喻。陈忠实的《白鹿原》成稿于80年代末,虽然正式出版是在1993年,究其精神内涵来说,仍是一部带有浓重80年代气质的书。那个年代,我们的文学从“伤痕、反思文学”起始,到“寻根文学”“新历史主义”“新写实小说”……消解了“崇高”、告别了“革命”“民族”“历史”“人性”“欲望”成为小说的主题。诚如《白鹿原》的题记“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所示,陈忠实也希望通过这部小说对中国传统文化、近现代史做更为深入与复杂的思考。
陈忠实找到的人物是白嘉轩,依托的文本是宋代蓝田《吕氏乡约》所倡导的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白嘉轩的传奇由娶妻与换地开始,在接连死了六个妻子后,他发现了白鹿原上的秘密,一个长在鹿家土地上的白鹿图腾,于是他装作家道中落急于卖地变现,拿自家“天”字号地换鹿家那块有白鹿图腾的“人”字号地,终于顺利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成为白鹿原上的腰杆挺直的“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白嘉轩违背《乡约》精神求得发迹后却以之作为自己的人生信条。他翻修祠堂、新建学堂;皇帝没了,他请朱先生写《乡约》,刻写在祠堂两边,作为规范乡民为人处事的依据;乡民偷鸡摸狗、赌博败家,按照《乡约》被严厉惩治;女人露天哺乳有伤风化,也开始懂得收敛;寡妇卖地,白嘉轩与鹿子霖起了风波,最终化干戈为玉帛,不仅地归原主,还接济寡妇,传为美谈;白嘉轩待家里的长工鹿三如兄弟,凡事与他商量,送鹿三的儿子黑娃上学,超越了阶级的区隔;儒家文化借着《乡约》、白嘉轩、朱先生,走进白鹿原乡民的日常生活,县志上对此地的评价是“民风淳厚”,县上颁发的“仁义白鹿村”牌匾也似乎实至名归。
白嘉轩靠着《乡约》应对白鹿原上的日常生活,直到发现自己的知识已无法解释这瞬息万变的世事。清廷被推翻后,新政府横征暴敛引发的“交农事件”是第一桩,他向秀才先生请教,确认“反昏君是大忠”后带头“交农”;不让黑娃、小娥进祠堂拜祖,“黑娃小娥们”一会成为砸祠堂、毁《乡约》的“农会”领头人,一会儿又成为受尽凌辱的阶下囚;自己最为倚重的长子白孝文被小娥引诱,逐出家门后竟然变卖家产,继续堕落;自己最深爱的女儿白灵离家出走投身革命,嘴上当她死了,心里却无时无刻不惦念。面对着世事纷纷,白嘉轩秉持的依旧是以《乡约》建构起的心理结构与性格,训导乡民是乡约,接济寡妇善待鹿三是乡约,“交农”抗争是乡约,为黑娃们下跪求情是乡约,不让黑娃小娥进祠堂是乡约,惩治白孝文不认白灵也是乡约。只是原外世事变迁、翻天覆地,《乡约》的效力已日渐衰微,白嘉轩也从白鹿原的中心舞台逐渐旁移至看台,人物的丰富性与悲剧感,对传统文化的反思似乎也正由此而来。小说《白鹿原》不带价值评判地建构了这样一个乡约中国,它曾带给人稳定的心理结构、安身立命的处事准则,亦在大时代的到来后分崩离析、迅速衰落。作为《乡约》最后一个继承者,白嘉轩又如何能不哭呢?
我们期待的白嘉轩似乎是这个能哭出意义的白嘉轩,而综观整剧,少了那点白嘉轩的前传,少了白嘉轩心理结构的揭示,少了《乡约》、“仁义白鹿村”牌匾之于他及白鹿原的意义的呈现,少了他从族长到看客,从中心舞台到看台的位移过程,便少了人物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观众更容易陷入贴标签的立场,而难以对人物与人物所代表的传统文化在大时代面前的局限与没落产生反思,这或许是最后白嘉轩大哭的那一幕难以使人动容的原因。在这一版《白鹿原》中,“旧人”依旧是“旧人”,高光依然给予了“新人”。这也就可以理解剧中除了重点突出“被压迫”的小娥的悲剧命运外,为何还在有限的篇幅里细致刻画白灵、兆鹏、兆辉的儿女情长,并且浓墨重彩地突显了小说中“多智于近妖”、超然党派之外的关中大儒朱先生的爱国成仁。
陕西人艺版话剧《白鹿原》借着原著,讲了一个故事好像是白鹿原的,又好像不是。不是的那部分或许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症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