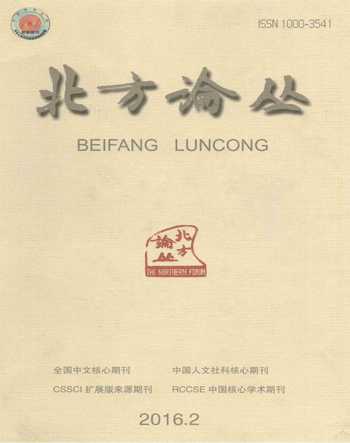“学衡派”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
汪树东
[摘要]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学衡派”是以文化保守主义身份,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共同构成“五四”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相对于前两者,“学衡派”确立了典型的反现代性文化选择立场。他们严厉地批判现代性的进化论、进步观念、功利主义、个人主义、主体自由和民主取向等,执着地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浪潮中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认同。这种文选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但也存在理论倡导和现实需要之间脱节的局限,也很容易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专制主义,并在现代化浪潮中再次走向文化的自我封闭。
[关键词]“学衡派”;反现代性;文化保守主义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3541(2016)02-0045-07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浪潮中,“学衡派”是以文化保守主义身份,与以陈独秀、李大钊等为代表的激进主义、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鼎足而立的,共同构成“五四”众声喧哗的文化景观。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共享着相同的现代性价值基设,在脱旧入新的进化论、功利主义、民主科学等猎猎大旗之下,推动着老旧中国的现代转型。相对而言,“学衡派”却更痴迷于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性心存狐疑,在强烈的批判意识中屡屡流露出鲜明的反现代价值取向。
要梳理“学衡派”的反现代性价值取向,首先自然需要大致观照一下该流派的源起和背景。《学衡》杂志创刊于1921年1月,最初以南京东南大学为基地。从1922年到1933年,《学衡》在吴宓等人的主持下,克服了种种内忧外患,断断续续出版了79期,主要撰稿人除了吴宓,还有梅光迪、胡先骕、汤用彤、柳诒徵、缪凤林、王国维、林宰平、陈寅恪等。《学衡杂志简章》中,曾如此概述《学衡》宗旨:“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1]宗旨就体现出“学衡派”的文化坚守之意味。至于该流派兴起背景,存在多种错综交织的因素。
其一,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全球思想文化界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多种反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基督教普世福音、日新月异的现代科学技术、欧美国家殖民进程的影响下,高视阔步的现代西方文明被视为人类文明的唯一方向;但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熊熊燃烧,高度发达的现代科技变成了绞肉机,现代西方文明的阴暗面瞬间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全球思想文化界对它的反思也风起云涌。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1918年)预言现代西方文明的没落,荣获1913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泰戈尔对东方文化的宣扬,是最昭彰显著的例子。受这股思潮的影响,中国学术界也相继反思现代西方文明,例如《东方杂志》主编杜亚泉在1914年就认为中国人要重新审视西方文明,不能照搬西方文化;梁启超的《欧游心影录》(1920年)则构造出一个现代西方物质文明破产、需要中国文化救度的神话;梁簌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0年)则构造出一个中国文化必将取代西方文明的神话。“学衡派”诸公对现代西方文明的反思和批判延续的就是这股思潮。
其二,是对屡受挑战的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日趋增强。与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批判反思相伴而生的,就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自觉意识。从晚清洋务派的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到维新派与辛亥革命的制度层面的现代化再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文化层面的现代化,中国现代化之路遵循的是后发外生型的逐层深入的道路。到了“五四”时期,一方面是像胡适、陈独秀等人对传统文化的颠覆性批判;另一方面,反激出来的却是梁启超、梁簌溟、张君劢,以及“学衡派”等的对传统文化的自觉坚守意识。若放大到更大的世界范围,这种文化自觉意识,则是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文化民族主义的反思和抗击。
其三,是和美国白璧德、穆尔等人的新人文主义影响息息相关。“学衡派”的诸位主将梅光迪、胡先骕、吴宓、汤用彤等人均曾受业于白璧德门下,深受其文化保守主义思想的影响,而白璧德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推崇更是增强了“学衡派”诸君的传统文化自信。梅光迪就曾说:“归根到底,衡量一位导师伟大与否的尺度就是他帮助学生找寻自我的能力。白璧德对儒家人文主义的评价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向他的中国学生指明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为他们在当今行形形色色的文化价值观和文化主张中指明了正确的道路。”[2](p190)对于吴宓、陈寅恪等人而言,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一
“学衡派”的反现代性价值取向,表现于“破”和“立”两个方面。
先看“破”的方面。
其一,对进化论、进步观念的批判。众所周知,进化、进步是现代性的底座,没有这个底座,整个现代文明就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也都是在进化、进步观念的提摄下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引颈翘望现代西方文明的。弃旧图新就是进化、进步观念的平易表达。汪叔潜在《新旧问题》中就说:“如以为新者适也,则旧者在所排除;如以为旧者适也,则新者在所废弃;旧者不根本打破,则新者绝对不能发生,新者不排除尽净,则旧者亦终不能保存。新旧之不能相容,更甚于水火冰炭之不能相入也。”[3]陈独秀也如此主张:“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4]只有在进化、进步的单维的线性时间观上,新旧才表现出像汪叔潜、陈独秀所说的如此水火难容之势。至于胡适倡导白话文学、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也都是进化、进步的现代性价值观念的具体运演。
“学衡派”对维新是趋的进化、进步观念深表鄙薄,不予认同。吴宓在《论新文化运动》一文中认为:“原夫天理、人情、物象古今不变,东西皆同。盖其显于外者,形形色色,千百异状,瞬息之顷,毫厘之差,均未有同者。然其根本定律,则固若一。”[5]因此,新旧相对而言,新并没有价值论意义上的优先权,“论学应辨是非精初,论人应辨善恶短长,论事应辨利害得失。以此类推,而不应拘泥于新旧,旧者不必是,新者未必非,然反是尤不可”[5]。就物质文明而言,吴宓认为,也许存在进步现象,但绝对不能把进步观念泛化到其他领域,例如,人事领域。吴宓曾说:“物质科学,以积累而成,故期发达也。循直线以进,愈久愈详,愈晚出愈精妙。然人事之学,如历史、政治、文章、美术等,则或系于社会之实境,或由于个人之天才,其发达也,无一定之轨辙。故后来者不必居上,晚出者不必胜前。因之,若论人事之学,则尤当分别研究,不能以新夺理也。” [5]细致辨析吴宓的论辩,我们可知,他反对进化、进步观念最后的理据还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经典古训,背后依托的是超越时空的永恒天理,这无疑显示了其鲜明的前现代性素质。现代性恰恰是告别前现代的终极性,突入喧嚣变化的世俗世界的结果。此外,吴宓区分出物质和人事的不同领域,把进步观念驱回物质—器物层面,保证人事领域免遭机械化观念的蹂躏,无疑也是非常富有洞见的。
无独有偶,胡先骕在《文学之标准》一文中,也力排众议,重申文学古今中西不易的终极标准,反对现代文学专在推翻标准、表现自我的多元化倾向,他也认为,进化论、进步观念不能运用于道德、文学等人事领域。“自天演进化之名滥用之后,而思想纷乱以起,于是对于一般无进化与天演可言之事物,亦加以进化天演之名。故道德观念,除在榛丕时代而未进于文明之域者外,无进化天演之可言也。圣贤之徒,不能世出,孔子、苏格拉底、释迦、基督诸圣,距今皆已数千载矣,未见后人能进化天演以胜之也。其言行之精微,似已尽得人生哲学之究竟,后人之思想未见能进化天演以胜之也。今人则以唯物主义自然主义为进化天演矣。文学亦然,自商周至于唐千余年而有李白杜甫,自乔叟数百年而有莎士比亚、弥尔顿。以古况今,犹自可言进化与天演也。唐至清千余年而诗人未有胜于李白杜甫者,自十七世纪至于今日,英国诗人未有胜于莎士比亚、弥尔顿者,则不得谓文学之变迁为进化与天演也。今则以破弃规律之自由诗、语体诗为进化为天演矣,种种花样,务求翻新,实则不啻迷途于具茨之野,无所归宿,皆误解科学误用科学之害也”[6]。
从吴宓、胡先骕的言论可以看出,“学衡派”对进化论、进步观念的批判,内在逻辑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重返前现代的终极标准,拒绝以新旧之分抛弃传统文化,在承认现代科技文明、物质文明的进步前提下,不承认进步观念能够移用于其他人事领域,从而为文化保守主义开辟出足够的发展空间。
其二,对现代性的功利主义取向的猛烈批判。白璧德在《文学与美国的大学》中就认为,培根和卢梭代表着现代性的两种偏至的人道主义,与重节制、遵纪律、守传统的人文主義不啻霄壤。其中,培根就是现代科学主义、功利主义的典型代表,他过于关注科学技术、关注物质功利的价值取向造成了现代文明的偏枯。吴宓接续白璧德的批判锋芒,也大肆归罪于现代性的功利主义:“略以西洋近世,物质之学大昌,而人生之道理遂晦。科学实业日益兴盛,而宗教道德之势力衰微,人不知所以为人之道,于是众惟趋于功利一途,而又流于感情作用,中于诡辩之说,群情激扰,人各自是。社会之中,是非善恶之观念将绝,而各国各族,则常以互相残杀为事。科学发达,不能增益人生内心之真福,反成为桎梏刀剑。哀哉,此其受病之根,由于群众昧于为人之道。盖物质与人事,截然分途,各有其律。科学家发明物质之律,至极精确,故科学之盛如此。然以物质之律施之人事,则理智不讲,道德全失,私欲横流,将成率兽食人之局。”吴宓为胡先骕的文章《白璧德谈中西人文教育》写的按语,见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上卷,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版,第72-73页。若联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吴宓之语当不为过。
胡先骕在《说今日教育之危机》中,更深入地剖析了当时中国人为何会深中功利主义的流毒。他认为,自洋务运动以后,中国人向欧美学习,最为关注的就是物质科学,对西方人的基督教信仰不加措意,从而遗失了西方教育中最重要的人文学问,又以物质科学的专长了否定了本民族的传统道德,于是就成为典型的偏枯的功利主义人格。因为缺乏人文主义教育,修身之学晦暗,专于治学的欧美留学生回到国内往往会陷入各种泥沼中,“就其最佳者而言,亦只能以其专长供社会之用,不为社会之恶习所熏染,不失为洁身自好之士而已。再进则亦仅能热心研究提出其专门之学,引起国人重视此项学问之心而已。至于立身,则以无坚毅之道德观念,故每易堕入悲观,进退失据。若不得志,固不免怨天尤人。即处境较佳,则又因物质欲望之满足而转觉人生之无目的。盖此类学者,其求学时代之惟一愿望,厥在名成业就,及此目的已达,则惟一之精神刺激已去,乃渐觉其十数年来学校中胶胶扰扰之生活,为无意义矣。此纯粹之知慧主义之流弊也。若再遇一二拂逆之事,精神将益委顿,结果则惟抱混世主义,其下者,乃浸为社会恶习所软化,否则抱厌世观念,甚或至于风魔与自杀矣。其次者则纯为功利主义之奴隶”[7](p80)。胡先骕对现代性的教育中,人文精神旁落造成的人格养成之问题的分析无疑是相当深入的,富有启发性;即使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绝大部分中国人依然在为这种功利主义的教育偿付着不菲的道德代价和社会学费。此外,他对中国留学生疏离于基督教信仰的后果也洞若观火。西方社会大力发展现代科学技术,物质财富剧增,但他们的社会道德水平并未降低,关键就在于基督教信仰的引导、扶持和奖掖。而欧美留学生对西方社会的基督教信仰往往具有文化上的选择性失明,这直接导致现代性的功利主义失去最为有效的遏制,从而毒害了整个中国社会。
其三,对现代性的个人主义、主体自由取向的猛烈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多宗奉卢梭、尼采、易卜生、托尔斯泰等思想家、文学家,他们大多持较为强硬的个人主义立场,更关注情感的奔放、主体的表现,个人对社会的反抗和冲决。胡适在《易卜生主义》中就重申易卜生的“世界上最强有力的人就是那个最孤立的人”的震撼名言。鲁迅小说也大多展示孤独个人和庸俗社会的对抗悲剧。郭沫若《女神》式的诗歌更是觉醒的孤独个人的狂飙之声。因此,郁达夫才说:“五四运动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从前的人是为君而存在,为道而存在,为父母而存在,现代的人才晓得为自我而存在了。”[8]个性解放、情感解放、主体自由,恰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根本特征。但“学衡派”却对此展开猛烈批判。胡先骕就认为,新文化运动放弃节制,为祸甚烈。他说:“近日之新文化运动者,虽自命提倡艺术哲学文学,骤视之,似为今日功利主义之针砭,实则同为鄙弃节制的道德之运动,且以冒有精神文明之名,故其为害,较纯粹之功利主义为尤烈焉。”[7](p89)在胡先骕看来,精神文明只能和节制相关,而不能与自由、放任有染。在《论批评家之责任》中,胡先骕更是批评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缺乏必要的节制,“则立言务求其新奇,务取其偏激,以骇俗为高尚,以激烈为勇敢。此大非国家社会之福,抑亦非新文化前途之福也。夫家庭制度,数千年社会之基础也,父慈子孝,人类道德之起点也,乃不仅欲祛除旧家庭之缺点,竟欲举家庭制度根本推翻之……”[7](p65)偏激,几乎是“学衡派”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最常见的批评用词。
在《文学之标准》一文中,胡先骕严厉批判卢梭的丧失节制和中庸:“自卢梭创民约论以来,乃以人性为至善,所以为恶者,厥为社会礼法束缚节制所致,于是创返诸自然之论,以为充其本能,即能止于至善之域。其结果则人生之目的不在收其放心而在任情纵欲,不以理智或道德观念为节制情欲之具,而以冲动为本能之南针,不求以小己之私勉企模范人生之标准,而惟小己之偏向扩张为务。结果则或为尼采之弱肉强食之超人主义,或为托尔斯泰之摩顶放踵之人道主义,两者皆失节制与中庸之要义。其影响于文学者,则为情感之胜理智,官骸之美感胜于精神之修养,情欲胜于道德观念,病态之现象胜于健康之现象,或为幻梦之乌托邦,或为无谓之呻吟,或为纵欲之快乐主义,或为官感之唯美主义,或为疾世之讽刺主义,或为无归宿之怀疑主义,或为专事描写丑恶之写实主义,或为迷离惝恍之象征主义,舟张为幻,不可方物。”[7](p254)从现代性角度看,卢梭、尼采、托尔斯泰等恰恰代表了现代人的个性张扬、主体自由的飞扬风度,但在文化保守主义的胡先骕看来,恰恰是他们造成了现代文明的丑陋与病态。视角不同,判断顿然有别。
吴宓和胡先骕持论一致,他从白璧德学说中获知“精约之世”和“博放之世”的区别,“西儒谓通观前史,‘精约之世与‘博放之世常交互递代而来。不惟疆域之分合,政权之轻重,而学术思想,忽而归于一致,忽而人自为主。精约之世,趋重克己与潜修;博放之世,趋重服人与任情尚气。当精约之世,众之人生观皆同,而精神安定;当博放之世,众之人生观各不相同,而时刻变转,遂致精神迷惘,无所归依。大凡精约之世,宜以博放之精神济其偏;而博放之世,则需以精约之功夫救其乱。近人有谓博放之世必胜于精约之世者,实未尽然”[9]。五四时期是“博放之世”,而吳宓等人就是要以“精约之世”的功夫来挽救。因此,他强调人生实践道德之法,还是被归结为前现代式的克己复礼、行忠恕和守中庸。
其四,对现代性的民主取向的严厉批判。“民主”和“科学”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面大旗,民主尤其关涉于整个社会的制度架构和价值导向。“五四”先驱们之所以大力推行白话文,其实也是为了打破言文不一的藩篱,提高普通民众的文化水平,利于通达民主之治。胡适早就说:“吾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10](p153)陈独秀倡导国民文学,周作人提倡平民文学,还有“五四”作家们开始关注社会底层的芸芸众生,无疑都是民主精神的体现。
在对待现代性的民主取向方面,“学衡”诸公也都表示疑虑乃至鄙视。梅光迪在《民权主义之流弊论》一文中,认为,民权主义的流弊有三个方面:一是人自为说无所宗仰;二是奖进庸众,人群退化;三是道德堕落。其实,说民主导致人自为说无所宗仰,就是抨击民主时代不尊重权威,信奉权威。说民主奖进庸众,体现的是梅光迪的文化保守主义式的贵族主义立场,他曾说:“然欧洲自十八世纪以还,可谓之凡民时代,议政操于乡愿,与论谋诸市侩。高等教育,志在普及,而新大陆大学数百,以生徒集合学位授受之多寡,决成绩之优劣也。其大学风气,尤不斗智而斗力,精科学而擅诗文者,如坠九渊,而万劫不复。而竞走赛船之健儿,其荣誉不亚于攻城略地之名将焉。且经济之学兴,而事事求便利、求速成,教科之书,简易详尽,而脑力无用矣。著作之业,公诸人人,而名士如林矣。古人之洪文巨制,弃之蠹鱼,而诲淫诲盗之小说家言,唯利是图者,而纸贵一时矣。绝世之哲人硕学,举世无闻,而龌龊之政客,贪顽之教徒,则神圣目之矣。民权主义之流弊,至此而极。”[2](p14)至于说民主导致道德堕落,则无疑是在强调义务重于权利。
胡先骕在《论批评家之责任》一文中,还担心民主过度会异化为民粹主义,害处就更大:“今日一般批评家之宗旨,固为十八世纪卢骚学说创立以来,全世界风行之主义之余绪,即无限度之民治主义也。有限度之民治主义,固为一切人事之根本。无限度之民治主义,则含孕莫大之危险。主张此种学说者,以为人类根本上一切平等,智慧才能道德,无一不相若。彼智识阶级之所以优秀者,非其禀赋异乎常人,不过因其处于优越地位,能得完备之教育,以充分发展其智慧才能耳。苟一般平民得同等之机遇,其才智必不在知识阶级之下。故遇事皆须为一般大众着想,而不宜仅顾少数知识阶级也。即道德亦莫不然,甚且谓知识阶级之道德,为文化所濡染,反不如一般之平民,至一般平民之罪恶,初非其道德较为低下,而为环境逼迫濡染之所致也。此种论调,犹为较和平者,其甚者竟谓文化为不祥之物,不如绝圣弃智,返乎自然,凡一切文化为平民所不需要所不能了解者,皆为无益有害之物,故文化须尽力迁就平民云。”[7](p68)因此,他认为,批评家要拒绝的就是这种过度的民主、民粹倾向,更要拒绝可能的反智主义,要引导社会在精神上向上发展。
“学衡派”诸人对现代性的民主取向的批判,显示了他们持守的还是贵族主义、精英主义的立场。他们反对白话文,反对中国文学走向更为广大的社会底层,都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前现代性价值取向使然,他们看不到民主的未来路向。易峻在《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中曾说:“至标榜所谓平民文学,欲使文学普及于平民,是则非使文学艺术愈开倒车,愈趋下达,以迎合普遍一般人之低级趣味,不为功。文学进化云乎哉!夫文章大业,本存乎文人相与之间,非可以期于人人者。”[11]由此看来,五四文学启蒙的现代性事业对于“学衡派”而言还是天方夜谭。
二
在对“学衡派”批判现代性的“破”的方面做了条分缕析之后,我们再看其“立”的方面。
“学衡派”之所以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现代性的诸多方面展开全面彻底、严厉激烈的批判,就是因为他们要固守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性的浪潮中,通过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来表达自我的文化认同。如果考虑到“学衡派”诸人都是在美国留学时深受白璧德的影响才坚定了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那么我们的确可以说:“通过白璧德的人文主义学说,梅光迪们得以摆脱近代以来由于国家贫弱所造成的自卑心理,重建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心。”[12](p45)换而言之,像“学衡派”这样的知识分子,生活在国家衰败、民生凋敝、欧风美雨接踵而至的过渡时代里,无法像中国传统士人那样,在通过奉献宗法家庭—家族来获得家庭—家族认同,或者通过科举进入官场接触权力获得社会认同,就只能固守于儒家文化领域,通过逆潮流而动的传统文化认同来获得坚实的自我存在感。
梅光迪在《人文主义和现代中国》中曾说:“我想,《学衡》的创办者一定是将捍卫中国的传统当作了自己的主要目标。现代中国的激进文化运动有两个突出的特点:只专注于传统的瑕疵;鼓吹低劣而不加选择的‘世界主义,以此为自己的主要内容……这场运动所扮演的‘反弹琵琶的角色大行其道,带走了仅剩不多的一点点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将现代中国推入了自我诅咒的无边深海中。《学衡》的作者们并非对自身民族传统中的问题熟视无睹;而是坚信目前更为紧迫的任务是要对已取得的成就加以重新审视,为现代中国重塑平稳、镇定的心态。在他们看来,这不仅对真正的文化复兴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批判性接受西方文化中有益且可吸收的东西必不可少的条件。”[2](p193)在梅光迪看来,如果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的底子,中国人也不可能批判性地接受西方文化,像“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全盘反传统只能摧毁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学衡派”要固守的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丰富复杂、多元共生的传统文化,而往往被归结为道德化的儒家传统。胡先骕说:“至吾族真正之大成绩,则在数千年中能创造保持一种非宗教而以道德为根据之人文主义终始勿渝也。中国二千六百年来之文化,纯以孔子之学说为基础。”[7](p83)吴宓更是对儒家的道德钟爱有加,儒家的道德化立场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远。他曾说:“国家之盛衰,不在其政体,不在其一二人物,亦不尽由财力兵力之如何。处今之中国,而言兵与财,尤急不能成。所恃以决者,国民全体之智识与道德,故社会教育、精神教育尚焉。苟民智开明,民德淬发,则旋乾转坤,事正易易。”[13](p514)在《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的译者按里,吴宓也说:“夫欲杜绝帝国主义之侵略,而免瓜分共管灭亡,只有提倡国家主义,改良百度,御辱图强,而其本尤在培植道德,树立品格。使国人皆精勤奋发,聪明强毅,不为利欲所驱,不为瞽说狂潮所中,爱护先圣先贤所创立之精神教化,有与共生死之决心,如是则不惟保国,且可进而谋救世。”[14]吴宓的这种论调后来甚至明确为“道德救国论”。这种儒家特有的泛道德主义明显和现代性扞格难入,可以视为固守传统的学院派知识分子的大而无当的迂阔之论。
更有意味的是,“学衡派”诸人大都有在乱世维护圣道、挽狂澜于即倒、滔滔天下舍我其谁的精英式的自我想象。梅光迪曾说:“豪杰之士每喜逆流而行,与举世为敌,所谓‘顺应世界潮流,‘应时势需要者,即窥时俯仰、与世浮沉之意,乃懦夫乡愿成功之秘术,岂豪杰之士所屑道哉。今之‘世界潮流、‘时势需要,在社会主义白话文学之类,故彼等皆言社会主义白话文学,使彼等生数十年前,必且竭力于八股与‘皇帝尧舜之馆阁文章,以应当时之潮流与需要矣。夫举世皆以‘顺应为美德,则服从附和效臣妾奴婢之行,谁能为之领袖,以创造进化之业自任者乎。”[15]像“学衡派”诸人那样敢于固守文言、儒家传统的人就是逆流而动的豪杰之士。缪凤林在《文德篇》中更是慷慨激昂:“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顺应潮流之声浪,喧盈耳鼓,因有旧有文学皆死文学等谬论。岂知文学之可贵,端在其永久性,本无新旧之可分。古人文学之佳者,光焰万丈长,行且与天壤共存,而文家所贵,尤在屹然独立,惟道是从,能转移风气而不为世所污。将为人群之明星,导之于日上之途者也。末世横流,必有不趋时势者出,作中流之砥柱,或能挽狂澜于即倒。非然者,其不由顺流而趋下流,复返野蛮者几希矣。”[16]这就赋予“学衡派”一种易水寒式的悲剧色彩。
三
“学衡派”是在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上展开其反现代性的活动的。这种反现代的特点和意义都非常鲜明。
首先,在急剧变化的现代性大潮中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固守,无疑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稳定和延续。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无论是激进主义,还是自由主义,都倾向于对传统文化的全面批评和毁弃。从好的方面说,这有利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更新;从坏的方面说,却可能导致转型阶段的中国社会在缺乏传统文化的内在支撑陷入动荡和颠簸,甚至秩序瓦解、道德崩溃的可怕绝境。而“学衡派”打破了人们对维新是从的现代性价值体系的盲目信仰,指出文化传统对于现代人的自我认同的重要性,无疑也是一种先见之明。如果说激进主义、自由主义是社会前进的发动机的话,那么“学衡派”式的文化保守主义其实扮演着社会的制动机制的角色。没有发动机,汽车是废铁,而没有制动机制,没有刹车,汽车也必然无法畅行。如果在“五四”之后的中国社会里,“学衡派”所代表的文化保守主义能够发挥一定的作用的话,整个中国社会必定可以少几分不必要的躁动,多几分传统的安稳。
其次,面对西方文化的压倒性优势,“学衡派”志在阐扬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有利于中国人的文化自觉。从晚清到“五四”,中国社会从物质、制度、文化层面逐层深入地向西方学习,展开逆向的现代化历程,就是西方文化由浅入深全方位地介入中国社会的过程。这一现代化过程,对于早已被沉重的封建文化传统压迫得气喘如牛的中国社会而言,无疑是必需的。但如果这一现代化过程过于西化,竟至于完全丧失本民族的文化传统,那样也是得不偿失。“学衡派”通过不断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促进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重建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自信心,对于中国人的现代化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上述两个方面看,“学衡派”的确并不是简单的守旧、顽固的文化代名词,“学衡派”的保守主义和激进主义、自由主义一样都构成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阵营的多元取向,都分享了现代性的多元意义。换而言之,即使“学衡派”的反现代性,也是一种现代性框架中的一种合理选择。
当然,虽然“学衡派”文化保守意义上的反现代性具有特定的意义和价值,但考虑到具体的时代语境,我们还是可以看出其矛盾和局限。
其一,理论倡导和现实需要之间的脱节。“学衡派”诸人深受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理论的影响,但白璧德的人文主义是在美国已经成功实现现代化之后的社会土壤中提出来的,是已经充分发展的现代性的解毒剂,而“学衡派”当时所处的中国从主体上看,却依然是一个前现代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封闭社会,现代化水平还很低。这样一来,白璧德的人文主义理论和当时中国的现实需要之间就存在鲜明的脱节,从而也直接导致“学衡派”诸人的理论阐释的失效性。梅光迪曾在《自觉与盲从》中,批评当时中国青年不顾现实需要对西方理论的盲从:“现在吾国所流行之各种主义,果适用于吾国今日之社会乎?近世西洋各种主义之发生,皆有其特殊之社会制度为之因。例如有资本主义之弊害,而后能发生社会主义;有帝国军国主义之弊害,而后能发生大同主义。吾国工商业始萌芽,正苦无资本以振兴之。吾国削地丧权,外患方剧,正宜整顿军备,以雪国耻……况西洋资本主义之弊害,非社会主义所能救正;西洋帝国主义之弊害,非大同主义所能救正。西洋学者类能言之。乃吾国人好作无病之呻吟,又欲取不对症之药,以治想象中之病,此真作者所大惑不解者也。”[2](p59)其实,这种情况在“学衡派”身上也昭然若揭。當几千年来中国人的思维始终被“天不变道亦不变”“天道循环周而复始”“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等循环论观念牢牢制约着时,“学衡派”却迫不及待地批判着具有思想突破意义的进化论、进步观念;当中国社会的现代科学技术还幼稚至极时,“学衡派”却开始批判科技的功利主义取向;当中国社会绝大多数人还是被宗法势力牢牢地束缚、个性尚未萌芽时,“学衡派”却开始展示卢梭式的个性解放理论的阴暗面了;当中国社会的生机正被前现代的专制制度斩杀殆尽时,“学衡派”却对民主评头论足,疑虑不已;这些无疑是理论和现实的深度隔膜,是真正的无病之呻吟。
更为可怕的是,“学衡派”的倡导者都是一些学院派知识分子,他们的文化理论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和延续的立足点出发的,而不是从当时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的,这几乎注定了他们的理论倡导是对现实需要的严重遮蔽。如梅光迪曾说:“现代中国人最大的责任就是保存自己的传统文化并维护它的声誉,因为这种文化是许许多多优秀人物用他们的才华和情感铸就而成的;也正是有了这种文化,我们至今仍然可以听到这些人的声音。”[2](p196)而鲁迅则说:“我們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17](p69)比较梅光迪和鲁迅的话,二者的立场迥然有别,鲁迅真正尊重的是当时中国人的现实需要,而梅光迪尊重的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保守和延续。如果在保存中国传统文化同时,也能满足当时中国人的现实生存与发展的需要,那样自然是万事大吉;但如果越是保存中国传统文化,越是加强传统文化自觉和自信心,就越是遮蔽了当时中国人的现实需要,就越是不能很好地解决当时中国人的现实生存困境,那样所谓的传统文化的自觉和自信,往往只能蜕变为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
其二,文化保守主义容易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文化专制主义,从而导致在现代化浪潮中传统文化的再次自我封闭。“学衡派”在阐扬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时,总是以文化特殊性、文化地方性来对抗现代性的普遍性,力图指出现代西方文明的局限性来消解其普世性。梅光迪就曾说:“历来西洋贤哲,只知西洋一隅,未尝知有东方,此亦种族之不同,地理文字之阻隔使然,无足怪者。故其言论思想,率根据于西洋特殊之历史民性风俗习尚,或为解决一时一地之问题而发,皆与东方无涉。在彼所称适用者,行之吾国,或无当矣。昔罗马诗人卢克利侠斯(即卢克莱修)有言曰:‘此人之食,或为他人之毒。若英美德法,同在西洋文化范围之中,犹有不相通者,况东西之殊乎?故吾人之所介绍,必求其能超越东西界限,而含有普遍永久之性质者,则此事之需要乎审慎可知矣。”[18]西方启蒙思想家大都相信现代文明的普遍性,但是,像“学衡派”这样来自后发现代化国家中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总是倾向于把西方现代文明再次加以地域化、狭隘化,从而为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保留一定的生存空间。如此一来,文化保守主义就很容易蜕变为文化民族主义,甚至以民族性、民族精神为旗号来审视文明的价值,对那些出自西方现代文明而不是出自本民族传统文化的优秀东西以民族性、民族精神为由加以排斥,从而造成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固守和封闭。
有论者曾指出:“《学衡》诸公的传统主义之不同于国粹派者首先在于他们不是以复古制,而是以‘阐求真理来‘昌明国粹、翼护传统的。他们探求的是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永恒性的人文价值。”[19](p12)表面看来,“学衡派”阐扬的是具有普遍、永恒性的传统文化,从而也是具有开放性的。但实际上,“学衡派”最为关注的就是中国儒家传统,他们要“融化新知”,也只是融化能够和儒家传统融合的“新知”,而对于和儒家传统相异、相反乃至冲突的“新知”是不可能融合的。因此,归根结底,“学衡派”所谓的“融化新知”依然是儒家传统的自我复制而已,而不可能是真正的“新知”。
当“学衡派”把中国传统文化简约为儒家传统,进而把孔子塑造成为最高的人格楷模,也就从文化保守主义向文化专制主义蜕变了。吴宓曾说:“孔子者理想中最高之人物,其道德智慧,卓绝千古,无人能及之,故称圣人。圣人者模范人,乃古今人之中第一人也……孔子者中国道德理想之所寓,人格标准之所托。”[20]而王富仁在评价新儒家时,曾经指出:“他们没有看到,把一种人格模式当做全人类或全民族惟一一种完美人格模式来肯定、来提倡,恰恰是儒家文化走向文化专制主义道路的根本原因之一。大至人类文化,小至一个民族、一个社区、一个社会集团、一个社会团体的文化,都不是由一种确定的人格类型创造的,而是由各种不同的个性创造的。”[21](p95)的确,吴宓等“学衡派”在反现代性的文化保守主义立场如此沉醉于儒家传统,重提圣人楷模,大倡道德救国时,无疑是在通向文化专制主义之僻路上狂奔。至今为止,这依然值得那些国学热中的硕学鸿儒真正加以警惕与反思。
[参 考 文 献]
[1]学衡杂志简章[J].学衡,1922(1).
[2]梅光迪.梅光迪文存[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3]汪叔潜.新旧问题[J].青年杂志,1915(1).
[4]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J].新青年,1919(1).
[5]吴宓.论新文化运动[J].学衡,1922(4).
[6]胡先骕.文学之标准[J].学衡,1924(31).
[7]胡先骕.胡先骕文存:上卷[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
[8]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
[9]吴宓.我之人生观[J].学衡,1923(16).
[10]段怀清.新人文主义思潮——白璧德在中国[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9.
[11]易峻.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J].学衡,1933(79).
[12]周佩瑶.学衡派的身份想象[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3.
[13]吴宓.吴宓日记:第1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14]吴宓.白璧德论欧亚两洲文化[J].学衡,1925(38).
[15]梅光迪.评今人提倡学术之方法[J].学衡,1922(2).
[16]缪凤林.文德篇[J].学衡,1922(3).
[17]鲁迅.鲁迅作品精选集[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8.
[18]梅光迪.现今西洋人文主义[J].学衡,1922(8).
[19]孙尚扬,等.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M].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
[20]吴宓.孔子之价值及孔教之精义[N].大公报,1927-9-22.
[21]王富仁.中国现代文化指掌图[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作者系武汉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 吴井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