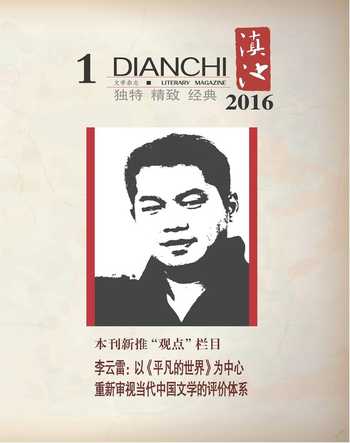“新农村”和“老农民”的分裂
跨越将近三十年的沧桑巨变,《平凡的世界》再度被搬上荧屏——1988年小说出版后,1989年曾有 14集的电视剧上演。经历了春节城乡间大回流、故乡亲情洗涤、怀旧潮冲击,目睹了故乡的或繁荣或萧条,或昂扬或消沉,观众在荧屏前共享黄土地上孙氏兄弟和众乡亲的人生悲欢浮沉。劳动与爱情、成长与挫折、普通人的尊严与亲情、日常生活的悲欢离合与大时代的跌宕巨变,一一在荧屏中呈现。成长于 80、90年代,如今已成“社会中坚”的中年人士,似乎劈面看到了三十年前的自己,更年轻的 80、90后似乎也看清了某种“来路”——这属于他们的父母辈,也属于经过某种折射后的自己:1975——1985年,“改革”的起点处,也是农村与“改革”最为融洽的最初十年,摆脱饥饿和贫困的奋斗的勇气和决心如此强烈;青春涌动,意志强悍,“世界”遥远而美好,人可以“平凡”,却要走向“世界”;卑微的“平凡世界”中,因为诚实的劳动,“平凡的人”获得了尊严,镌刻在当代社会结构中的“身份政治”也才有了打破的可能;在这个“新历史”的起点上,改革是上至省地县各级干部,下至普通农民的“共识”,而正因为有了对幸福、尊严、诚实良善的上下一致的追求,改革的真正动力便恰恰来自“平凡的世界”中的平凡的人。在电视剧的结尾,俯瞰节日中烟花灿烂的双水村,远游者归来,病痛和衰老者携手站立,一种根基于普通中国农民的“中国梦”似乎在空中开放。是啊,“平凡的人照样也能过得不平凡!”这不正是改革开始时的某种共识和动力吗?
《平凡的世界》的上映,是春节后中国百姓享用的第一顿“文化大餐”,与众多行色匆匆从都市回归家乡与家人团聚的游子一样,它也是“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短暂回归,是进入新一轮改革的中国人对改革起源的再次回顾。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无疑已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它不仅深刻地记录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那段跌宕起伏的历史,而且在一代代人的精神成长史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而不可否认,电视剧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对原著的忠实有关。
大约在最终完成三卷本《平凡的世界》四年后,路遥又写了长篇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在这篇创作谈的结尾,他写道:“无疑,这里所记录的一切和《平凡的世界》一样,对我来说,都已经成了历史。一切都是当时的经历和认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社会生活以及艺术的变化发展,我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和发展。许多过去我所倚重的东西现在也许已不在我思考的主流之中;而一些我曾轻视或者未触及的问题却上升到重要的位置。”由于路遥的英年早逝,我们无从知道在他的认识和思考中,问题意识的升降变化;我们也无从知道,假如路遥活到今天,让他来评价他这部长篇作品的电视剧改编,甚至由他自己来操刀改编,会是什么样子?有一点我们可以推测,路遥是一位关心政治、与社会变化栖息与共的作家,面对 30年沧桑变化,双水村、黄原和黄土高原上的“平凡世界”肯定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所以,尽管电视剧编剧声称尽量“忠实于原著”,而且采取了“正面强攻”的“写实”手法——电视剧对 80年代前后陕北农村生活场景的描述不可谓不细致。但正如路遥所言,“一切都已经成了历史”,任何改编其实本身都是某种改头换面后的当代叙述,在电视剧的改编中,我们还是能解读出很多当代文化、社会和思想的症候,其中最为显著的就是从小说到电视剧,第一主人公如何从孙少平变成了孙少安。“平”“安”的浮沉,究竟意味着什么?
《平凡的世界》有三条线索,分别以三个 /组人物来组织。一条线由田福军贯穿,这可称为一个改革题材的小说,提供了一条从省、地、县到公社、村的线索,故事的展开主要围绕要不要改革以及如何改革的矛盾进行。改革题材小说在 80年代风行一时,为改革的全面推行提供了合法性叙述,改革小说也征用了中国现代文学中深厚的启蒙叙述传统。另一条线围绕孙少安,可以称作农村题材小说,将农村的社会变革与乡村的日常生活结合起来,主要展示乡村的日常生活及其矛盾。农村题材小说在中国当代文学中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当代小说主要的题材和类型,当代中国农村巨大的变化和农村生活丰富复杂的细节,几乎都能在这类小说中得到体现。第三条线以孙少平为主,是一个关于青年人“成长”和“出走”的故事,这一类型的小说源头可以追溯到 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传统,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也不乏著名的先例,关于青年的故事,本身就是“少年中国”现代性之路的主要主题之一。因此,从小说史上看,《平凡的世界》中每条线都有其“原型”,但也都有变异,改革题材不再有那么清晰的“改革”和“反改革”两条路线之争,也不再诉之于对旧体制的大量控诉;农村题材方面,农村社会变革和乡村日常生活叙述大量集中于乡村伦理和苦难叙述;而“成长小说”方面,则主要集中于城乡分治、爱情、劳动和个人尊严的叙述。评论家李陀认为,中国当代文学创造了自己的“红色通俗小说”传统,这一传统融中国叙事传统、现代追求和革命价值于一体,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应放在传统中理解,而路遥超越“红色通俗小说”传统之处则在于对时代和日常生活整体性和超越性思考的努力。
再回到电视剧的改编,电视剧保留了小说中的上述三条线索,但作了相应变动,其中最大改动之处是极大限度地扩大了孙少安的线,保留和适当增加了田福军的线,收缩和改变了孙少平的线。具体而言,电视剧用大量的篇幅,围绕孙少安,增加了很多故事和桥段,如集体化时期少安如何反抗过“左”的农村政策;年纪轻轻,如何为承担家庭重担含辛茹苦;旱灾中如何孤身一人,深入上游罐子村和石圪节村,以头拍砖的江湖手法,几乎只手力挽狂澜;还有诸如没用彩礼,只身到山西柳林醉娶媳妇,从运砖挖得第一桶金到办砖厂中的几起几落,以及与田润叶缠绵悱恻、深情哀怨道义具备的爱情故事,再加上演员王雷略带强势和混不吝气息的表演,完全把孙少安塑造成了一个具有先知先觉的个人英雄主义气质,同时又带有一丝乡村“无产者”的“爱谁谁”的习气,却又不失乡村伦理中孝义仁厚、勇于承担、有情有义的“当代农村英雄”,这与小说中塑造的那个既想改变现状却又有些逆来顺受、安于现状的孙少安确乎判然有别。
令人惊奇的是,在最近 20多年关于路遥和《平凡的世界》的讨论中,几乎很少涉及孙少安的评论。换句话说,在当代文学批评和研究中,孙少安几乎是一个无法言说的角色,相比于电视剧中的浓墨重彩、极尽渲染,这确乎是意味深长的现象。在原来的叙述机制中,是什么因素抑制着孙少安,使他在感人之余,一直无法被言说呢?今天,又是什么原因使得他从一位原来无法言说的角色,上升为这个时代的“当代英雄”呢?粗略说来,原因有二:其一,农村改革经过三十余年的沉洗,似乎格局已定,联产承包、解放农村生产力的势能一朝用尽,经过市场社会的淘炼,如今的农村已是“能人”的天下,曾经试图摆脱脸朝黄土背朝天命运束缚的孙少安在电视剧的叙述中,就快步迈进了农村“能人”的行列;其二,在所谓高扬传统文化价值,文化保守主义强势崛起的今天,孙少安身上重情义、仁厚朴实、承担牺牲的品格被轻松嫁接到了当代农村社会的变迁叙述中,孙少安因而成了一个能被言说和理解的“当代人”。
田福军那条线与孙少安的线是相互呼应的。田是一位改革家,本来,改革意味着什么?改革对不同社会阶层的人意味着什么?对改革者本身又意味着什么?在改革的过程中,普通人,其利益和位置如何安置?都是需要思考和追问的,
但在电视剧中,改革的逻辑被简化了,田福军一再强调,内心驱动他投身改革的唯一目的似乎就是让“黄原农民从吃黑面馍变成白面馍”,而全然没有顾及改革是涉及到社会关系的重组、利益关系的重新调配、新的价值观的确立等一系列问题的全面工程。所以,编剧在电视剧末尾添加了一段田的妻子无意中收受装了钱的茶叶罐,从而造成受贿的事实时,既显得突兀,又显得意味深长。可能也正是在这时候,作为地委书记的田福军才真正面对了他一直推行的“改革”的真实内容,套用一句现在经常说的话:改革进入“深水区”了。
孙少平那条线本是路遥小说中用力最著之处,通过少平的“成长”和“出走”,时代巨变过程中遗留在普通人身上的伤痛、挣扎、自尊等价值得以显现,也只有在少平这里,“平凡”才最后通向了“世界”。但在电视剧中,孙少平的故事线被简化为爱情线,他关键的“出走”,由于离开了对尊严、价值、无限的可能性的追求,在一种物质回报的逻辑里,变得无法理解。有年轻批评者曾指出孙少平身上“特殊地具有的不假外求的自我创进的力量,从未丧失‘对那个不管多么狭小但在其中我们选择做喜欢之事的领域的信念,在不断放弃中自由选择”的作为“文学青年”的气质,扩大而言,这种“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寻求自我磨练、改造的“气质”恰恰是推动二十世纪中国巨变的“现代”品质。遗憾的是,在成长就是日益世故,成熟即是加入利益争夺的今天,这种品质已日益罕见并变得不可理解。
因此,在电视剧中,我们能感觉到孙少安是一位“今人”,是今天农村中的“当代英雄”。无论是在“农村强人和乡镇企业家”的逻辑中,还是在后寻根和文化保守主义的语境下,他的故事和人格都充满魅力和可书之处,因为在前一个逻辑中,少安是农村“新历史”的创造者,在后一个语境下,少安身上被想象出的无论是强悍、精明还是仁义、担当,都成了想象中的传统文化的投射,实际上,“孙少安的故事”也在相当的程度上笼罩了当今的农村叙述。
相反,电视剧中的孙少平却如一位“古人”,一位作为“打工仔”前身的历史中的人,他固执的“出走”,他持守的自尊,他对知识和“远方”的执着,已显得古板、莫名和可笑,他只能披上一些当代的外衣,比如他与田晓霞的“罗曼蒂克”的精神之恋,才能被辨认为一个当代的人物塑造。而事实上,更符合揽工汉孙少平身份的,似乎应该只能作为 90年代大量出现的打工者的前身。
孙少平的“被历史化”是一个当代悲剧。我们无法将孙少平当代化,因为在今天,我们已很少有可能看到孙少平身上体现出来的通过个人奋斗实现个人价值的可能,我们也很难理解凝结在一个底层人身上的基于劳动和自我超越之上的自尊和动力。在农村,随着集体经济的解体,为集体劳动失去了价值依托,劳动只是在换取物质报酬的意义上才能被理解,用马克思的概念,劳动被等同于它的交换价值,劳动的绝对价值,也就是劳动创造世界的本质被无限制地掩盖起来了。在这样的理解中,劳动只能是一种纯粹的“受苦”,或者是一种技术,少平在煤矿的师父就因为是一个优秀的斧子工才受人尊敬,相反,单干后,王满银、孙玉亭却因为没有农业劳动的技能和体力而变得十分凄惶。也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理解孙少平因下煤矿不缺工而用多领到的工资换取同屋工友的各种“稀罕物”——这是一种交换的原则,却不能理解他自虐式的揽工汉生活,更不能理解他将劳动变成一种精神的磨砺,一种人格上的蜕变的举动。
今天我们已处在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所谓纯粹乡村共同体已经解体的时代,几亿农民工进城打工,大规模的城镇化正在展开。实际上,文学批评界讨论“乡村叙事的终结”也已历多年——在我的理解中,离开城乡二元结构的历史和现实的理解,离开对劳动、尊严的理解和诉求,离开对镌刻在当代历史和现实中的身份政治的控诉,而谈论“乡村叙述的终结”,如果不是文化精英们的傲慢,也应是毫无心肝的批评的呓语。按照这样的逻辑,当我们讲述今天的中国农村时,我们的想象中只会有“老农民”,而当农民“老”去,农民在形象和人格上也不再能直起腰来,我们只能以既有的历史和文化安排去图解一种类型化、抽象化的“老农民”,正像去年热播的电视剧《老农民》那样,这部按照已有主流历史观图解 60多年当代农村变化的电视作品,将已经在历史叙述中被传奇化的一些著名故事拼凑进来,如二杆子式的破产农民分地主的地、占地主的房、睡地主的女人;《创业史》中梁生宝买稻种的段落;集体化后期小岗村式的农民摁手印签生死文书私分土地的传说等等,以构成一种粗陋、生硬的历史观的图解式表达。而且,“老农民”们在形象上也肮脏、猥琐,目光短浅,一切行为似乎只能在追逐私利的逻辑上才能被理解。在这点上,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的一种处理方式颇具症候性:每当镜头拉远,双水村或黄原就被笼罩在一个看似用电脑做出来的梦幻般的天穹下,虚幻的、变幻不定转瞬即逝的背景,似乎就是一个关于当代农村的隐喻。
事实上,怎样表现作为底层的农民的自尊和奋斗,表现农民中的“新人”的成长,一直是中国当代文学中最具挑战性的议题,离开了“新人”的塑造,当代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无法想象。在我的理解中,路遥小说中孙少平这个不断游走的,奋进而自尊的“文学青年式”的“新农民”,也可以被理解为当代农村“新人”画廊中的形象之一。也是在这一意义上,我相当程度上肯定也是去年热播的另一部农村剧《马向阳下乡记》,它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向当下农村问题及其情感和人心的开放姿态,而且,农民也并未“老”去,农村里的事似乎还可以“有的商量”,而并未事件化、喜剧化。也正是从这样的角度,我愿意寄望于更多贴近农村和农民的作品的出现:真正的乡村叙述不是终结了,而是还没有开始。
何吉贤,文学博士,60年代后期生人,曾从事专职翻译,现为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 20世纪中国文学和文化。
本栏责任编辑 张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