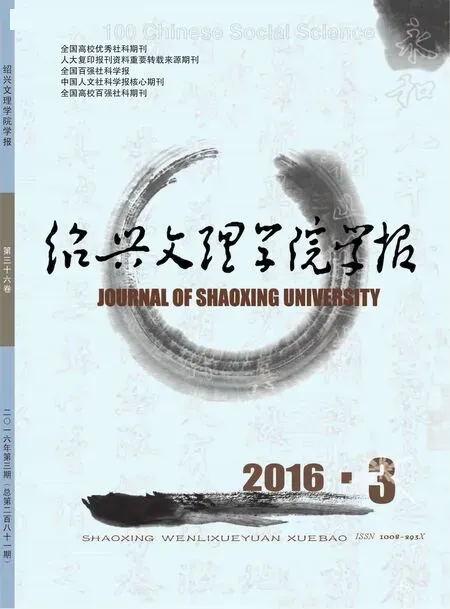浙东士人妈祖书写的人文精神
潘承玉
(绍兴文理学院 越文化研究院,浙江 绍兴312000)
浙东士人妈祖书写的人文精神
潘承玉
(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浙江绍兴312000)
摘要:妈祖信仰是一种赢得封建统治阶层长期尊崇的民间文化,是中国从内陆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海洋文化和贸易文化,也是一种融少女崇拜、母亲崇拜为一体的尚女文化。作为毗邻妈祖文化发祥地的浙江特别是浙东地区,其马祖信仰也源远流长,成为福建之外马祖文化积淀较为丰厚的地区之一。面对这一久远的民间信仰趋势,浙东精英士大夫群体或顺应妈祖信仰推动各方与民间社会的仰重期待,或自居这一趋势的疏离自外者甚至反对者,展开多方面的妈祖书写;不论以宗教信仰还是以历史理性为本位,均体现出一定的人文精神。
关键词:妈祖信仰;浙东;精英士大夫;人文精神
从宋代发祥的妈祖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作为一种民间文化,它把一个民间小人物作为偶像,赢得封建最高统治者的一再折腰,影响力远远超过其他民间文化;作为一种海洋文化,它是中国从农耕文明走向海洋文明的一块里程碑;作为一种贸易文化,它见证宋元明时代中国远洋贸易的辉煌和艰辛;作为一种融少女崇拜和母亲崇拜为一体的尚女文化,它构成对男尊女卑的传统宗法社会的反驳,而与现代人文主义精神息息相通。
近千年间,妈祖信仰遍及整个中国东中部,以及日本、韩国、越南、新加坡等诸多东亚和东南亚国家,不仅构成中华民族精神凝聚力的一个重要因素和台湾海峡东西两岸的共同文化血脉,也构成东亚文化共同体的一条精神纽带。作为毗邻妈祖文化发祥地的浙江特别是浙东地区,其马祖信仰也源远流长,成为福建之外马祖文化积淀较为丰厚的地区之一。面对这一久远的民间信仰趋势,浙东精英士大夫群体或程度不同地顺应妈祖信仰推动各方和民间社会的仰重期待,或以这一趋势的疏离自外者甚至反对者自居,从而展开多方面的妈祖书写。
一、浙东民间妈祖信仰的悠久程度和庙祀密度
根据权威记载,“妈祖信仰最早传出福建的省份是浙江”[1]。元代宁波籍名儒程端学(1278-1334)《积斋集》(《四库全书》本、民国《四明丛书》本)卷四收其元统元年至二年间(1333-1334)作《灵济庙事迹记》一文曰:
惟天阴骘下民,凡涉大险,必有神物效灵以济之,若海之有护国庇民广济福惠明著天妃是已。我朝疆宇极天所覆,地大人众,仰东南之粟以给京师,视汉、唐、宋为尤重;神谋睿算,肇创海运,较循贡赋古道,功相万也。然以数百万斛委之惊涛骇浪、冥雾飓风,帆樯失利,舟人隳守,危在瞬息,非赖明神有祷斯答,其罔攸济。故褒功锡命,岁时遣使致祭,牲币礼秩,与岳渎并隆,著在祀典。前年冬,庆、绍等处海运千户所达鲁花赤、前进士纳臣公至官,廉静易简,庶事毕理,神庙适迩治所,以累朝加封锡号之典、发祥降祉之迹*《湄州妈祖志》此处句读误作“神庙适迩治,所以累朝加封锡号之典,发祥降祉之迹”。见莆田湄州妈祖庙董事会.湄州妈祖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第451页.,未刻于石,惧久将湮,乃谋诸寮寀,具本末请记。
谨按:神姓林氏,兴化莆田都巡君之季女,生而神异,能力拯人患难,室居未三十而卒。宋元祐间,邑人祠之,水旱疠疫、舟航危急,有祷辄应。宣和五年,给事中路允迪以八舟使高丽,风溺其七,独允迪舟见神女降于樯而免,事闻于朝,锡庙额曰顺济。绍兴二十六年封灵惠夫人。三十年海寇啸聚江口,居民祷之,神现空中,起风涛烟雾,寇溃就获,州上其事,封灵惠昭应夫人。乾道二年*此处《至正四明续志》卷九收此文作“乾道三年”。,兴化大疫,神降曰:“去庙丈许,有泉可愈疾。”民掘斥卤,甘泉涌出,饮者立愈。又海寇作乱,官兵不能捕,神迷其道,俾至庙前就擒,封灵惠昭应崇福夫人。淳熙十一年,福兴都巡检使姜特立捕温台海寇,祷之即获,封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既而民疫、夏旱,祷之愈且雨。绍熙三年,特封灵惠妃。庆元四年,瓯、闽诸郡苦雨,唯莆三邑祷之霁,且有年,封灵惠助顺妃。时方发闽禺舟师平大奚寇,神复效灵,起大雾,我明彼暗,贼悉扫灭。嘉定元年,金人寇淮甸,宋兵载神主战于花黡镇,仰见神兵布云间,竖灵惠妃旗,大捷;及战紫金山,复见神像,又捷;三战,遂解合肥之围,封灵惠助顺显卫妃。嘉定十年,亢旱,祷之雨;海寇犯境,祷之获,封灵惠助顺显卫英烈妃。嘉熙三年,以钱塘潮决堤至艮山祠,若有限而退,封灵惠助顺显卫英烈嘉应妃。宝祐二年旱,祷之雨,封灵惠助顺嘉应英烈协正妃。三年,封灵惠助顺嘉应英烈慈济妃。四年,封灵惠协正嘉应慈济妃。是岁,又以浙江堤成,加封灵惠协正嘉应善庆妃。景定三年,祷捕海寇,得反风,胶舟就擒,封灵惠显济嘉应善庆妃。宝祐之封,神之父母、女兄以及神佐,皆有锡命。
皇元至元十八年,封护国明著天妃。大德三年,以漕运效灵封护国庇民明著天妃。延祐元年,封护国庇民广济明著天妃。天历二年,漕运副万户八十监运,舟至三沙,飓风七日,遥呼于神,夜见神火四明,风恬浪静,运舟悉济,事闻,加庙号曰灵慈。纳臣公言:“至顺三年,予押运至莱州洋,风大作,祷之,夜半见神像,转逆以顺,是岁运舟无虞。”其随感而应类此。神之庙始莆,遍闽浙。
鄞之有庙,自宋绍兴三年来远亭北舶舟长沈法询,往海南遇风,神降于舟以济,遂诣兴化分炉香以归;见红光异香满室,乃舍宅为庙址,益以官地,捐资募众创殿庭,像设毕具。有司因俾沈氏世掌之。皇庆元年,海运千户范忠暨漕户倪天泽等,复建后殿、廊庑、斋宿所,造祭器。
余既序其事,乃作诗曰:
粤稽古昔,人道事帝,在传具陈。帝皞神芒,祀于世世,或君或臣。洛神湘妃,爰以阴类,生人殁神。
婉婉天妃,捍患御灾,自其居室。祀于莆田,拯溺湊财,庙号肇锡,遂遍闽浙,鄞庙崔巍,百世血食。
济险驱疠,霁霪雨旸,擒贼解围。宋自灵惠,封十五更,曰夫人妃。迨我皇元,万斛龙骧,绝海达畿。
东南庶邦,岛夷蛮商,献琛是职。波晏不扬,如履康庄,神惠孔硕。天子曰嘻,精意以享,毋怠毋斁。
徽号四加,表此殊廷,以报玄功。鄞江洋洋,潮汐送迎,神惠周通。我作铭诗,刻石之贞,式昭无穷。
首先我们探讨一下上文提到的沈法询自福建分炉香以归的“绍兴三年”时间。《至正四明续志》卷九、《康熙鄞县志》卷九、《乾隆鄞县志》卷七等收录此文时,此处均作“绍熙二年”;《雍正宁波府志》卷十亦载,宁波最早的妈祖庙天后宫,位于鄞县东东渡门外,始建于“绍熙二年”。《成化宁波郡志》卷六又载,宁波最早的妈祖庙天妃庙,位于鄞县东东渡门外,建于“绍兴二年”;《嘉靖宁波府志》卷十五亦载,宁波最早的妈祖庙灵慈庙,一名天妃宫,位于鄞县东东渡门外,建于“绍兴二年”。方志文献引据程文的淆乱,不免令今天的不少研究者甚至权威文献对此有些迷惑不解*如莆田湄州妈祖庙董事会编《湄州妈祖志》,既于“大事记”宋代部分明确记载绍兴三年,宁波船长沈法询自湄洲祖庙分炉返里,舍宅建庙,又于“分灵传播”、“文献史料选辑”部分称程文绍兴三年时间后被改为绍熙二年,“不知何据”,“亦难理解”,见莆田湄州妈祖庙董事会.湄州妈祖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年版.第509、161、453页.;宁波当地一些学者也都认为,《四库全书》本《积斋集》中的上文“绍兴三年”,应是“绍熙二年”之讹误*如宁波大学张如安就认为“四库本‘绍兴’当是‘绍熙’之抄误”,“宋绍熙二年(1191)乃是妈祖信仰正式落户甬上之始”,见张如安.南宋宁波文化史:下册[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952-953页。伍鹏引录程文时直接写作“鄞之有庙,自宋绍熙三年(1191年)”,但下面自己的文字又说,“宁波第一座妈祖庙始建于宋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为福建船主沈法询所建”,则其实际认定还是“绍熙二年(1191年)”,而“绍熙三年(1191年)”表达则属技术上的双重疏误(绍熙三年的公元纪年为1192年),见伍鹏.浙江海洋信仰文化与旅游开发研究[M].北京:海洋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笔者认为,这一时间还应以第一个考述宁波妈祖信仰传承的程氏别集中之“绍兴三年”为确凿无疑。此有两点旁证。其一,程文“庙号肇锡,遂遍闽浙”,紧接“鄞庙崔巍,百世血食”,说明宁波妈祖庙当其撰文时已“百世血食”,绍兴三年(1133)较之绍熙二年(1191),其去至元二年(1336),更当得“百世血食”之称。其二,程端学之兄程端礼(1271-1345)《畏斋集》(民国《四明丛书》本)卷五载其至正元年(1341)作《重修灵慈庙记》一文,内有“惟是庙在鄞之东角者,岁久弗葺,门堂室寝,木朽瓦摧,像设漫漶,甚非所以揭虔妥灵也。庆元、绍兴海运千户所朱侯奉直,莅事谒庙,顾瞻咨嗟。念官无储钱,首捐俸为倡,同僚暨市舶官吏欣助,漕户协力,鸠工市材,剔蠧易坚,瓦石丹艧,内外一新,侯日程督,无敢苟且,虽修实建,兴工于至元五年夏六月,越三寒暑而毕”,云云;卷六又载《庆元、绍兴等处海运千户朱奉直去思碑》云,“奉直大夫朱公彦文以至元二年十一月为庆元绍兴等处海运千户”。据此,至元二年(1336)朱彦文所见到的宁波妈祖庙,乃是“岁久弗葺,门堂室寝,木朽瓦摧,像设漫漶”,以至后来的重修不得不“虽修实建”,工程之大,要“越三寒暑而毕”。绍兴三年(1133)较之绍熙二年(1191),其去至元二年(1336)的时间距离,也更易造成这种残破景象。
更重要的力证在于,沈法询的身份是来远亭北舶舟长,而来远亭即来远局,乃是北宋末新设接待高丽使节的外事服务机构,仅存在于北宋末到南宋初年。如《宝庆四明志》卷六所载:“政和七年(1117),郡人楼异除知随州,陛辞,建议于明置高丽司曰来远局,创二巨航、百画舫,以应办三韩岁使,且请垦州之广德湖为田,收岁租以足用。既对,改知明州,复请移温之船场于明,以便工役;创高丽使行馆,今之宝奎精舍即其地。金国既盛,高丽乃禀金正朔。绍兴三十二年纲首徐德荣至明州,言本国欲遣贺使,有旨,令守臣韩仲通许之。殿中侍御史吴芾言:‘高丽与金人接壤,为其所役。绍兴丙寅,常使金稚圭入贡至明州,朝廷惧其为间,亟遣之回。方两国交兵,德荣之情可疑。今若许之,使其果来,则惧有意外之虞;万一不至,即取笑夷狄。’乃诏止之。孝宗皇帝朝始复通使。嘉定十七年,高丽乃弃金正朔,以甲子纪年,历法与中国等。”据此,当绍兴初年北方女真族的金朝日趋强盛之时,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家是奉金朝正朔,而与赵宋断绝朝贡关系的;绍兴十六年丙寅(1146)、绍兴三十二年壬午(1162),高丽使者两次欲重修旧好,均为赵宋朝廷驳回。可以想象,整个绍兴年间的绝大部分时间,赵宋与高丽都没有外交关系,其当初设立以隆重接待高丽使者的来远局,也就自然废置。其后,“孝宗皇帝朝始复通使”,但高丽仍奉北方金朝为正朔,彼此猜疑顾忌,双方的往来也就必然既遮遮掩掩,又不情不愿,从赵宋一方来说,也就没有恢复来远局运作的任何必要与可能。高丽放弃金正朔,“以甲子纪年,历法与中国等”,重新奉赵宋为正朔,两国恢复传统藩属关系,要迟至嘉定十七年(1224)以后。那是又后于绍熙二年(1191)达33年的事了。
回到正题。这篇妈祖信仰传播史上极为重要的文献,不仅全面地载录宋代以降民间口碑中的妈祖灵应传说和封建朝廷的累世褒封尊号,真实再现“在其流行的区域内,妈祖具有仅次于观音的神格,明明赫赫,令其他相似神祗相形见绌”[2]的早期情形,而且明确记载自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宁波船长沈法询“诣兴化分炉香以归”,建妈祖专庙崇祀以来,“鄞江洋洋,潮汐送迎”,“鄞庙崔巍,百世血食”,其庙宇管理并有“沈氏世掌之”的固定制度。证诸明正德十五到十六年(1520-1521)出任宁波府同知的河南祥符人李濂*《嘉靖宁波府志》卷二载其到任时间为正德十五年,继任者的到任时间为嘉靖二年,似乎正德十五到嘉靖元年均在任。但《顺治祥符县志》卷五载李濂以38岁盛年致仕归前的任职是山西按察司佥事,而《雍正平阳府志》卷十载:“虞士师庙,……嘉靖元年巡按王秀檄知县孙巨鲸增修,韩忠定文、佥事李濂胥撰记。”《雍正山西通志》卷一百六十六亦载:“七烈士庙,在西北三里,明嘉靖二年佥事李濂建。”可见李濂嘉靖元年已到任山西按察司佥事。《嵩渚文集》(嘉靖二十五年刻本)卷二十七《明州迎春宴上作》所咏,“天妃宫前生暖烟,灵桥门外鼓阗阗。鞭牛南国彩丝杖,走马谁家青锦鞯。箫管满城迎令节,风云协律兆丰年”,确实可以看出宁波民间漫长的崇祀妈祖历史。
绍兴三年宁波即建妈祖专庙,这是妈祖信仰传播史上的一个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因为,妈祖信仰在福建本土的最初形成,也就是在北宋末年;而封建国家中央朝廷将民间信仰中的妈祖女神加以认可褒封,随后又正式列入祀典,使之从民间“淫祠”神升格为国家“正祀”神,也在此前后不久。《咸淳临安志》卷七十三载丁伯桂《艮山顺济圣妃庙记》云:“莆(田)临海有堆,元祐丙寅,夜现光气,环堆之人一夕同梦曰:‘我湄洲神女也,宜馆我。’于是有祠曰圣堆。”刘克庄《后村先生大全集》(《四部丛刊》本)卷九十一《风亭新建妃庙》载:“妃庙遍于莆,凡大墟市、小聚落皆有之。风亭去郡六十里,有溪达海。元符初,水漂一炉,溯沿而至,夜有人感梦,曰湄洲之神也。迎致锦屏山下,草创数楹祀之。既而问灾祥者、祷水旱者远近辐辏。”元祐丙寅(1086)、元符(1098—1100)初,都距绍兴三年甚近。而赵宋国家对妈祖女神的最初两次褒封,并列入国家祀典,乃分别在宣和五年(1123)或六年及绍兴二十六年(1156)。如上引《灵济庙事迹记》已载:“宣和五年,给事中路允迪以八舟使高丽,风溺其七,独允迪舟见神女降于樯而免,事闻于朝,锡庙额曰顺济。绍兴二十六年封灵惠夫人。”丁伯桂《艮山顺济圣妃庙记》亦承前引续载:“宣和壬寅,给事路公允迪载书使高丽,中流震风,八舟沉溺,独公所乘神降于樯获安济。明年奏于朝,锡庙额曰顺济。绍兴丙子,以郊典封灵惠夫人。”《宋会要·神女祠》同载:“莆田县有神女祠,徽宗宣和五年八月赐额顺济。高宗绍兴二十六年十月封灵惠夫人。”
实际上,赵宋国家对妈祖女神的这最初两次褒封,也和宁波紧密相关。第一次,“宣和五年,给事中路允迪以八舟使高丽,风溺其七,独允迪舟见神女降于樯而免”,使得“八舟沉溺,独公所乘,神降于樯,获安济”,这个“神异”事件发生在路氏出使途中具体哪个地方呢?衡诸史料,其实就在宁波出海途中。《宝庆四明志》卷六载:“熙宁二年(1069)……高丽欲……由泉州路入贡,诏就明州发来,自是王徽、王运、王熙修职贡尤谨,朝廷遣使亦密往来,率道于明。”从北宋熙宁年间开始,中国和高丽王朝的使节都是经浙东运河-宁波-舟山-外洋一线往来的。这在其他文献中也有大量记载。如王辟之《渑水燕谈录》(《知不足斋丛书》本)卷九:“元丰(1078-1085)中,高丽使朴寅亮至明州,象山尉张中以诗送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四库全书》本)卷十四:“崇宁(1102-1106)中,高丽自明州海道入贡。”蔡绦《铁围山丛谈》(《知不足斋丛书》本)卷四:“任宗尧……大观(1106-1110)末,从尚书王宁、中书舍人张邦昌使高丽……至四明则放洋而去。”《宝庆会稽续志》卷三载:“昭顺灵孝夫人庙,在(会稽)县东七十二里曹娥镇。……政和五年(1115)十一月以高丽遣使入贡经从,适值小汛,严祭借潮,即获感应。”《嘉泰会稽志》卷六载:“萧山县……宁济庙,在县西南一十三里西兴镇。政和三年赐今额,六年(1116)高丽入贡,使者将至,而潮不应,有司请祷,潮即大至。”《宋史·河渠志》亦载:“越州……都泗堰,因高丽使往来,宣和间(1119-1125)方置闸。”宣和五年路允迪一行的出使自亦如此。这在宁波、舟山地方志中有明确记载。如《嘉靖定海县志》卷九载:“昭利庙,县东北五里。宋宣和五年,侍郎路允迪、给事傅墨卿出使高丽,涉海有祷,因而建。”第二次,绍兴二十六年十月被朝廷封为灵惠夫人,其诰敕文是宁波学者所撰。查鄞县楼钥(1137-1213)《攻愧集》(《四部丛刊》本)卷三十四《外制》收其任职吏部尚书兼翰林侍讲、资政殿学士时撰《兴化军莆田县顺济庙灵惠昭应崇福善利夫人封灵惠妃》诰敕文曰:“明神之祠,率加以爵;妇人之爵,莫及于妃。倘非灵响之著闻,岂得恩荣之特异?具某神,壸彝素饬,庙食愈彰。居白湖而镇鲸海之滨,服朱衣而护鸡林之使。舟车所至,香火日严。告赐便蕃,既极小君之宠;祷祈昭答,遂超侯国之封。仍灵惠之旧称,示褒崇之新渥。其祗朕命,益利吾民!”
迨至明清时代,由于信仰的长期沉淀、扩散和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的叠加,浙东沿海、沿江各城镇、乡村,甚至山区地带,凡有聚落皆有妈祖庙存在,其密度甚至远超妈祖信仰的发祥故里福建莆田。仅以明代绍兴府城内外的情况来说,张天复撰《嘉庆山阴县志》卷十二载:“天妃宫,一在水沟营,一在铁甲营,一在线场营,一在塔下营。”是城内山阴县管辖范围(历史上山阴、会稽两县治与绍兴府治一直同处一城)内就有四座妈祖庙。《万历会稽县志》卷十六又载:“天妃宫,绍兴卫一所五,每一所领伍者十,每一伍置宫者一,祀其神以护海运。左、前、中三所之宫凡三十,及左(右)所亦有数宫,悉属会稽。”《万历绍兴府志》卷二十二亦载:“天妃宫,绍兴一卫五所,每一所领伍者十,每一伍置宫者一;临山卫、观海卫、三江所、沥海所、三山所、龙山所,各置宫一,祀其神以护海运。”是绍兴府城以北至东北的沿海军事卫所要塞内,又有多达56座妈祖庙,其中处在会稽县管辖范围的有30多座。无独有偶,《民国海宁州志稿》卷二十引《明复古庆善寺记》亦载,“明兴,设守御所于盐官,分建十天妃庙于诸营”,是则明代与绍兴一水相望的海宁千户所所城盐官一地,竟也有多达10座妈祖庙!
宋元以后浙东民间妈祖庙的密度,妈祖信仰在浙东之悠久和虔诚,几为今人所不可想象,除了福建商帮、当地漕运与海防官员的大力推动这些直接因素之外,还自有其浙东现实和历史文化的多重原因。就现实原因而言,在晚近一千年左右的时间内,内陆外海的浙东一直是中国对外贸易的前沿和重心所在。如陆游有《明州育王山买田记》(《渭南文集》卷十九)云:“惟兹四明,表海大邦……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宝庆四明志》卷一:“南通闽广,东接倭人,北距高丽,商舶往来,物货丰溢。”卷六载:“宁宗皇帝更化(1194)之后……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元音》(《四库全书》本)卷九载元人张翥《送黄中玉之庆元市舶》:“是邦控岛夷,走集聚商舸。珠香杂犀象,税入何其多。”这是宁波的情况,也是整个浙东的区位优势。由于这样的优势,浙东也就同时成为晚近一千年左右中国向外部世界(主要是东亚太平洋地区)开放的最前沿地区和海洋文明的代表地区。
就历史文化原因而言,浙东自古就同时有尚女与好鬼崇祀之风。以尚女之风而言,从《列女传》所载深明大义、勇于献身的“楚昭越姬”,《吴越春秋》所载忍辱负重、功成玉陨的西施,精通剑道、教习越军的无名“越女”,《后汉书》所载号父投江、孝诚动天的曹娥,一直到后来方志中津津乐道的才女祝英台,以及真实人物唐婉、秋瑾等等,浙东一直是中国女性文化最发达,尚女之风最重的地方。以好鬼崇祀之风而言,作为先秦越国腹地的浙东及其所在的两浙、江南地区,一直就有浓厚的崇祀鬼神的信仰氛围。如《吕氏春秋·异宝篇》云:“荆人畏鬼而越人信禨。”《史记·封禅书》载越人勇之之言:“越人俗鬼,而其祠皆见鬼,数有效。”《风俗通义》复云:“会稽俗多淫祀。”一直到唐代,据《旧唐书·狄仁杰列传》,垂拱四年(688),狄仁杰出任江南巡抚使,“吴楚之俗多淫祠,仁杰奏毁一千七百所,唯留夏禹、吴太伯、季札、伍员四祠”;《旧唐书·穆宗本纪》又载,长庆三年十二月(824),“浙西观察使李德裕奏去管内淫祠一千一十五所”,足见其间民间信仰的生生不息。
正是由于这样一些因素,以海洋文化、贸易文化、尚女文化和鬼神崇拜为基本特征的妈祖信仰在浙东得以落地扎根,也就自然而然。
二、浙东士大夫群体多元选择中体现的人文理性
众所周知,宋元时代是中国民间信仰和相应的庙会活动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明清时代亦踵事增华,愈演愈烈。在这种“文明返祖”面前,封建国家有自己的取舍选择。如《宋史·徽宗本纪二》记载,政和元年正月,“毁京师淫祠一千三十八区”。这从封建国家来说,“所谓‘正祀’与‘淫祀’之间的差异,其实是一个权力分配问题,也就是权力对祭祀合法性的垄断”[3]。但就士大夫群体而言,在这一趋势面前的褒贬取舍态度,则基本上是一个宗教信仰本位还是历史理性本位的问题。
浙东精英士大夫群体一直是妈祖信仰推动各方和民间社会期待仰重的力量。然而,面对这一久远的民间信仰趋势,浙东精英士大夫群体有的顺应妈祖信仰推动各方和民间社会的仰重期待,有的疏离自外于这一趋势,甚或以其反对者自居,从而以散文方式展开了不同的妈祖书写,显示出多元价值取向。
浙东精英士大夫群体的妈祖书写大约可分四种类型。其一,像程端礼、程端学昆仲那样,在应邀撰写的庙碑文字中,几乎完全认可妈祖女神的灵异和妈祖信仰的合理性,对妈祖信仰在民间的普及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如《天启舟山志》卷四所载明末鄞县人、曾任礼部郎中的文学家屠隆(1543-1605)万历三十二年(1604)所撰《天妃圣母祠记》*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出版、汪超宏主编《屠隆集》12巨册,搜罗极为宏富,但此文仍失收。:
许多工程施工单位都在档案管理人员的分配上存在着较大的问题和矛盾。第一,专职档案管理人员较少。现在一些工程施工管理单位的档案管理人员具有以下特点:业务技术人员兼职多、年轻从业人员多、专职人员较少,甚至没有。这样的情况极为普遍,而且这些从业人员大多没有专业的培训经验,缺乏相应的档案管理知识和技能,很难满足档案管理的工作需求。第二,业务技能掌握不熟练。道路工程档案管理人员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并且有很大一部分人还缺乏相应的工程技术知识和工程管理经验,致使在实际的档案管理工作中归档质量不高、档案材料积累不全、卷宗收集质量较差、档案整理不规范的现象比比皆是,严重影响了道路工程档案的归档效率。
四明东维海上,为古翁州地,地仅弹丸尔。然岛夷内讧,此实鼓舰之道,以是兵民杂处,艨艟凑泊,盖戎马之郊云。州治南去里许,阻山下即南关津渡处;山之阳,天妃圣母宅焉。颓垣败宇,焚修久废,登览者凄然。夫东南恃舟师以宁,舟师恃圣母以济;圣母之灵弗妥,当事者之过也。
万历辛巳,参戎袁侯持天子命,来守是邦。下车提疆事,巨细轻重,布之策画理甚。展春登谒圣母,顾前叹曰:“泽国洪济,寔式凭之;我军民所共乞灵者,屑越之也。”辄捐俸如干,倡为更始;偏禆捕校,亦无不捐者。聚财鸠工,命善官郭镐,善人赵兰、翁洋、王祖仪,住僧如清经纪之。为之筑宫,为之结楼,为之门庑阶戺,度工列墙,涂垩完整。洪流汇前,蓉峰环错,朝暾夕晖,顿成胜览。于是庙貌聿崇,人有瞻而神庥普矣。甲辰春,告成事。会侯拜京营督帅,新命去州,人士感泣,相与谋镌诸石,志不朽。
余时之补陀,取道翁州,过圣母,登礼览胜徘徊。镐等父老数十人前叩致辞,乞余言以记。余喟然曰:“诸葛武侯入蜀道,途无不理者;独照之臣,荩诚极虑,寄意幽远,大都尔尔。”侯宿抱伟略,建旗鼓,科名材望,觭重海内;冰蘖之操,贞于金石。以故牙纛所至,肤奏烂然。先是守淮阳,淮阳素多闾巷之豪,奸纵骚动,侯悉按之以法,民赖安居,无不以手加额者。矧兹东南障塞,圣母显济,而侯之存注,有不并心禔福也者!且神所捍圉,冥不可知,尚尔虔祀如此,则凡筹略,显关帷幄者,劻勷又当何如矣。
余尝观士马战舰,从海上来者,无不精简异常时;而士戢民安,边鄙不惊,有司廑奏保障;即今威灵远叠,海波不扬者,业已数岁。侯真大有造于东南哉,且与武侯千载比肩。若夫清操质神明,圣母又鉴之久矣……
这篇文章把妈祖女神称为“天后圣母”,恐怕是历史上极少数先例之一*笔者检索,在此之前,仅有《万历六安州志》(万历十二年刻)卷七所收刘垓万历九年作《游九公山记》,提到该地九公山山半神祠,“凡三祀:玄帝及东岳并天妃圣母”。然此天妃还未必是林氏天妃。,清代康熙、乾隆以后妈祖逐渐被称为“天后”“天上圣母”[4],其最主要的源头恐即在此。屠隆不仅几乎前所未有地把妈祖推崇为“圣母”,“圣母”一词前后七见,而且明确提出“东南恃舟师以宁,舟师恃圣母以济”,妈祖女神乃“我军民所共乞灵者”,相信“士戢民安,边鄙不惊”是妈祖“威灵远叠,海波不扬”的结果;对侯氏的冰蘖清操,妈祖亦“鉴之久矣”,似乎妈祖不仅是保障东南的唯一依靠,也是一位精准的人格鉴定师。屠隆褒美侯氏“大有造于东南”,“与武侯千载比肩”,主要还是基于他修复妈祖庙,使“人有瞻而神庥普矣”之政绩而言,根本意旨还是等于说妈祖女神才“大有造于东南”。屠隆对妈祖神威可谓揄扬之至。后来矢志抗清的张煌言在戎马倥偬中一再瞻礼妈祖庙宇,并形成不少诗文,就是这种取向的延续。
其二,基本认可、包容妈祖信仰,但对妈祖作为海洋之神的灵异神通并无实质张扬,而是在顺应民间信仰的同时,开导民众体认海、敬畏海,与海善处,阐述了一种更高层次的人生智慧。如《民国临海县志》卷十一所收青田刘基(1311-1375)至正十三年(1353)为临海天妃宫重建所撰《天妃宫记》*《四库全书》本、《四部丛刊》本《诚意伯文集》不收此文。今人林家骊据正德刊本《诚意伯刘先生文集·覆瓿集》收入《刘基集》时,题作《台州路重建天妃庙碑》,文亦微异,见林家骊(点校).刘基集[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175页.:
太极散为万汇,惟天为最大,故其神谓之帝;地次于天,其祇后也;其次最大者莫如海,而水又为阴类,故海之神降于后曰妃,而加以天,尊之也。天妃之名,古不见经传。国家建都于燕,始转粟江南,过黑水,越东莱之罘、成山,秦始皇帝之所射鱼、妖蜃之市悉帖妥如平地,皆归功天妃。故薄海州郡,莫不有天妃庙;岁遣使致祭,祀礼极虔。而帆舶之往来,咸寄命于神;即有变怪,风恶涛疾,呼神乞灵,有若火见桅樯间,其光辉辉然,舟立自定。由是海邦之人,莫不知尊天妃,而天妃之神在百神之上,无或与京。
台州故有天妃祠,在城东五里。延祐中,守土者病其远,弗便于祀事,乃徙置其神像于城南垣外水仙之楼,故祠遂废为墟。今至正十有一年,方国珍复乱海上。明年夏五月,寇台州,自中津桥直上登楼,骑屋山,内薄临城。城中人方拒击,楼忽自坏,登者尽压死。贼遂纵火焚郭外民舍,楼并毁。又明年,中书参知政事帖理帖穆尔出为江浙行省左丞,领征讨事,贼闻之,因温州守帅吴世显纳款请降。奏上,有诏命左丞公与南台侍御史左答纳实理同往,察便宜以行招讨。二公既受命,至台州,遣使宣谕,方氏兄弟大感寤悔罪,悉归所俘民,愿岁帅其徒防漕粮至直沽以自效。
于是海上既宁,惟天妃之神无所于栖。遂召其父老谓之曰:“呜呼!古先哲王所以致敬于神者,非所以为民乎?夫神无依,惟人是依。人尽其礼,而后神降之福。今此邦之民士负盾槊、冲锋镝、蒙荆棘、披霜雨数岁,惟近在海滨之故。海之神,天妃为灵。今人既获定,而神未有居,无乃于典祀有阙,而札瘥夭厉之咎无所归乎!”众拜曰:“然。公命,吾欲也。”乃即故祠之墟,买民地以广之,命达鲁花赤孛颜忽都治其役。及十月己酉,庙成,后带平原,前拖长江,环以群山,清宫回廊,丹碧照耀,高门缭垣,墁瓦辉赫,修篁美木,列植左右。台人观之,无不乐神之有依,而惠福是邦也。
于是括苍刘基既叙其事,复作迎享送神之章,俾歌以祀神。其词曰:
洁珍兮羞肥,芳椒兰兮菲菲,盼灵舟兮注云旗,神不来兮渺予思。
轻霞兮长烟,风颼飀兮水漪涟,神之来兮翳九玄。伐鼓兮铿钟,吹羽笙兮舞霓幢。焱回旋兮留六龙,乐具奏兮齐雍雍,鸿熙洽兮釐祝从。
江安流兮恬波,伏蛟龙兮偃鼋鼍。蔚桑麻兮穟麦禾,有寿考兮无夭瘥。穆幽潜兮动天和,于神功兮世不磨。
文中虽然高谈元朝国家“转粟江南”云云,“皆归功天妃”,又高称“天妃之神在百神之上,无或与京”,这些都是冠冕泛言,难以否定,也难以肯定。但他指出台州天妃宫重建的前提事实,是打劫台州城的方国珍兵匪武装踩塌形同废墟的天妃庙故祠,而倒塌的天妃庙故祠朽楼又反过来压死这些寇掠者。这里的“楼忽自坏,登者尽压死”并不神秘,绝难看出是妈祖威灵的表现,而是“故祠遂废为墟”与“贼”“自中津桥直上登楼”两种因素的叠加结果。文中又反复提出,“海上既宁,惟天妃之神无所于栖”,“夫神无依,惟人是依”,“人既获定,而神未有居”,一读之下,稍有理性者都会想到,这样楚楚可怜、孤苦无依的妈祖女神,又哪会真有什么神通,可使“帆舶之往来,咸寄命于神”!这两者都构成对妈祖信仰的消解。在此同时,刘基又提醒民众,天地之外,“其次最大者莫如海”,“今此邦之民士负盾槊、冲锋镝、蒙荆棘、披霜雨数岁,惟近在海滨之故”,滨海民众一切生存活动的关键因素还是海;“人尽其礼,而后神降之福”,在海滨生存的民众不能抛弃“礼”,只有人尽其礼,才会“神之来兮翳九玄”,“蔚桑麻兮穟麦禾”,形成一个人神共享同乐的美好家园。这与其说是在张扬妈祖信仰,毋宁说是给滨海民众开示一种深远的生存哲学。
其三,表面上也认可妈祖信仰,参与推动妈祖信仰传播,但历史理性使他们不能不发现其中的附会性质,因而有关笔墨又有意无意地透露出对妈祖信仰其实有所保留,某些表述甚至构成对妈祖信仰的无形动摇。如清初萧山毛奇龄(1623-1716)《西河集》(《四库全书》本)卷六十八,载其康熙二十三年(1684)为杭州城北天妃宫所撰《重修得胜坝天妃宫碑记》:


康熙甲子,同官汪君曾为册立使,封琉球中山,驰波倾樯,几于不免,乃祷天妃再,而舟竟以渡,其神如此。因于其飨祀而续为之歌,歌曰……

其四,直接质疑妈祖信仰。这样的浙东士大夫其实不少。如《光绪上虞县志》卷四十七所收洪武初山阴唐肃(字处敬)撰《征朱娥诗序》(程敏政《皇明文衡》卷三十九、黄宗羲《明文海》卷二百五十六所收题《上虞孝女朱娥诗序》,文并微异)云:“昔序曹娥庙,著论云:娥未事人而死,汉称孝女,礼也,今庙祀乃以夫人祀。夫有君子,而后为夫人;生而女,死而夫人,可乎?娥之孝,不以女薄,不以夫人厚也。及至吴,见海滨有庙祀天妃某夫人者,云本闽中处女,死为海神,则又叹曰:妃,配也,天之主宰曰帝,天妃者,岂帝之配耶?处女,死为神,称夫人,谬矣;而又谓之天妃,可乎?今年来,上虞邑人魏士达谓予曰:‘吾邑有朱娥者,宋治平三年,以十岁女子死大母难,当时里人为立祠邑南……今祠宇碑碣毁于兵火矣,里中长老犹能言其故处,往往嗟悼,以不得复旧为恨。宋熙宁间,会稽令董楷尝以娥配享曹娥庙。……吾长老子弟所以悲悼慕向者,则谓非专祠于吾境不可;且旧庙实作于民,官此者未尝请封请额于上得若曹娥,尤邑人之恨也。吾党咸追咏其事,集诗若干首,丐公序之,将持此以吿有司,庶几有所感动,得转闻之上而遂其请焉。’呜呼盛哉,邑人之心也!夫孝,风俗之本,苟以孝名者,千载犹一日也。朱娥之死二三百年,人犹思而悲之,不忍废其祭,而恳恳视为亟务。……顾娥之未得封谥,若可憾;即使得之,而加以非礼之称,若曹娥、天妃者,亦未为得也。今国制一新,为宗伯者必有知礼之君子,于异代之失庶几革而正之,肯踵其谬哉?”明邱浚《琼台会稿》(《四库全书》本)卷十七《天妃宫碑》中有载,“我太祖高皇帝革去百神之号,惟存其初封”,根据史料可知,这指的是洪武五年朝廷宣布革去元朝对妈祖的“天妃”封号,恢复南宋的“圣妃”称号。因此,此文(如果撰写于洪武五年朝廷诏旨布告天下之后)对“天妃”的非议或有政治上的从“圣”投机之嫌。但他到底以朴素的历史理性对妈祖信仰起源于闽中处女崇拜的合理性,提出明确质疑,指出,“处女,死为神,称夫人,谬矣;而又谓之天妃,可乎”,希望对此“革而正之”,不要再“踵其谬”。作为明初绍兴“二肃”的另一肃,上虞谢肃也十分赞同唐肃在这一问题上的理性。其《密庵稿》(《四部丛刊三编》本)庚卷《孝女朱娥诗序》云:“孝女朱娥诗者,士大夫之所赋,吾邑马志远氏之所裒,而同郡唐处敬氏之所序也。……处敬之言,足以正谬。”
对民间妈祖信仰的全面否定还以乾隆间鄞县全祖望(1705-1755)的文字为最。《鲒埼亭集》卷三十五《天妃庙说》称:
今世浙中、闽中、粤中,以及吴淞近海之区,皆有天妃庙。其姓氏,则闽中之女子林氏也,死为海神,遂有天妃、夫人之称,其灵爽非寻常之神可比,历代加封焉。
子全子曰:异哉,圣人之所不语也。生为明圣,死为明神,故世之死而得祀者,必以其忠节贞孝而后尊。以巾帼言之,湘夫人之得祀也,以其从舜而死;女媭之得祀也,以其为弟屈原;曹娥之得祀也,以其孝。若此例者,不可屈指。若夫流俗之妄,如蟂矶夫人祠,亦以讹传其殉汉而祀之;至于介山妒女之流,则所谓俚诞之不足深诘者也。若天妃者,列于命祀,遍于南方海上,州县其祀,非里巷祠宇所可比,然何其漫然无稽也!夫妇人之为德也,其言不出于阃,其议不出于酒食之微,其步趋不出于屏厅之近;其不幸而嫠,所支持亦不出于门户之间,所保护亦不出于儿女之辈;若当其在室,则尤深自秘匿,而一无所豫。林氏之女即云生有异禀,其于海上楼船之夷险,商贾之往还,亦复何涉,而忽出位谋之,日接夫天吴紫凤之流,以强作长鲸波汛之管勾,以要鲛人蜑户之崇奉,甚无谓也!
古来巾帼之奇,盖遭逢不幸,出于变故之来,勃菀烦冤以死,故其身后,魂魄所之,不可卒化,世人亦遂因而祀之,以励风教,以维末俗,是三礼之精意,不可废也。天妃果何居乎?自有天地以来即有此海,有此海即有神以司之。林氏之女未生以前,谁为司之?而直待昌期之至,不生男而生女,以为林氏门楣之光,海若敛袵奉为总持,是一怪也。天之配为地,今不以富媪为伉俪,而有取于闽产,是二怪也。林氏生前固处子耳,彼世有深居重闼之淑媛,媒妁之流突过而呼之,曰妃曰夫人曰娘,则有赪其面避之惟恐不速,而林氏受之而不以为泰,是三怪也。为此说者,盖出于南方好鬼之人,妄传其事,鲛人蜑户本无知识,展转相愚,造为灵迹以实之。于是梯航所过,弓影蛇形,皆有一天妃在其意中,在其目中,以至肸蠁之盛,惟恐或后,上而秩宗,下而海隅官吏,又无深明典礼者以折之,其可叹也。
前乎吾而为此说者,明会稽唐氏也,然略示其旨而未畅,吾故为之申而明之,以俟世有狄文惠公其人者。曰:然则海上之应祀者,谁也?曰:海之濒于南者,祝融是也,是真海神也。祝融为火,而海为水,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相配,故海之濒于南者,其神有妃之称,而东西北三方之海无之。后人不知,妄求巾帼以实之,吾怜其愚也,是则唐氏所未及发者也。[5]
该文先严厉批评妈祖信仰以莆田林氏之女为崇拜对象,“何其漫然无稽也”,“甚无谓也”,又进一步提出这种信仰的三大“可怪”和一大“可叹”;作者既“俟世有狄文惠公其人者”,希望有狄仁杰那样的人物出来对妈祖“淫祠”予以扫荡禁毁,又指出妈祖信仰的形成乃是“好鬼之人,妄传其事”与社会低等族群“本无知识,展转相愚”的结果,“吾怜其愚也”。如其末段自道,这确实是对明初唐肃妈祖信仰质疑论的一个继承和大胆发展。在浙东史学大家全祖望的历史理性面前,妈祖信仰全然成为一无是处的精神怪胎。比全祖望更早的浙东史学大家和伟大思想家黄宗羲,也借《明文海》选收他人之作,表明类似态度。如除收录唐肃前文,《明文海》卷一百十六又收嘉靖间朱浙的《天妃辩》一文,其中就说:“世衰道微,鬼怪百出。俗所敬信而承奉之者,莫如天妃。……夫上天至尊,以海滨村氓弱息作配于天,其无礼不经、谬恣舛逆,与邺人为河伯娶妇之事,尤为怪诞也。”[6]
浙东精英士大夫群体的妈祖书写,按其精神旨趣,有以上四种类型之分;但仔细辨析,根本差别还在以宗教信仰为本位还是以历史理性为本位。然以宗教信仰为本位也好,以历史理性为本位也罢,其中都蕴涵一定的人文精神,未可简单臧否。
参考文献:
[1]莆田湄州妈祖庙董事会.湄州妈祖志[M].北京:方志出版社,2011:160.
[2]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宋元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55.
[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58.
[4]蒋维锬.妈祖研究文集[M].福州:海风出版社,2006:241-247.
[5]朱铸禹整理.全祖望集汇校集注:上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678-679.
[6]黄宗羲.明文海: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1150-1151.
(责任编辑张玲玲)
The Humanistic Spirit Practiced by Mazu in East Zhejiang Province
Pan Chengyu
(Institute of Yue Culture Research, Shaoxing University, Shaoxing, Zhejiang 312000)
Abstract:The Mazu belief is a folk culture which was long respected by the feudal ruling class; it was a marine culture and trade culture when China changed form inland agricultural civilization into ocean civilization, and a female worship culture which included girl worship and mother worship. In Zhejiang province, especially East Zhejiang province, which is adjacent to the birthplace of Mazu culture, the Mazu belief has a long history and has become one of the richest areas of Mazu culture heritage besides Fujian province. In the face of the old folk belief trend, the elite intellectuals of East Zhejiang province are trying to rewrite on Mazu either by adapting themselves to the Mazu belief to promote the belief expectancy of all societies or by labeling themselves as the followers of the trend to alienate the outsiders or opponents. Their rewritings exhibit a certain humanistic spirit by following or repelling the Mazu belief based on religious belief or historic rationality.
Key words:Mazu belief; East Zhejiang province; elite intellectual; humanistic spirit
中图分类号:I209.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293X(2016)03-0040-10
doi:10.16169/j.issn.1008-293x.s.2016.03.009
收稿日期:2016-04-25
作者简介:潘承玉(1966-),男,安徽桐城人,绍兴文理学院越文化研究院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博士。
———评郭庆财博士《南宋浙东学派文学思想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