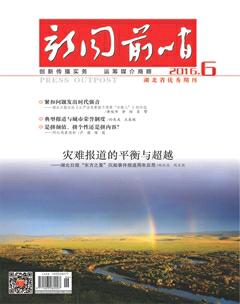典型报道与城市荣誉制度
孙发友 王春晓
[摘要]典型报道是中国新闻事业的特有报道式样,曾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典型报道的生态环境发生了转变,其影响日渐式微。近年来,荣誉制度在国家层面上的提出及其在武汉市的成功实践表明,典型报道的媒介生态环境出现了新的制度和文化因子,或对其产生有益影响。
[关键词]典型报道 媒介生态学 城市荣誉制度
[基金项目]本文为武汉市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新时期武汉市典型人物的媒体建构与社会价值研究》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WH-15030)
媒介生态学于20世纪60年代在北美地区兴起,是媒介学和生态学进行学科交叉的产物。它从生态学视角对于传播学和媒介学问题进行重新审视与认识。在系统论的基础上,媒介生态学把“媒介及其所处其中的社会类比成一种生物圈,并按照生物系统的方式理解媒介及其环境”[1]。我国媒介生态学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主要以媒介为中心,把对媒介的生存发展影响巨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人文环境、市场竞争环境等作为一个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在媒介的生态系统中,除自然生态因子之外,包括政治因子、经济因子、文化因子、讯息因子和科技因子等生态因子,这些因子相互联系并共同发挥效能,对媒介产生影响。
典型报道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报道方式,是“社会主义新闻最重要的特征, 是横亘于中西报道形式之间的分水岭”[2],曾经在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社会生产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新闻改革的不断深入,典型报道的影响力日渐式微。近年来,党中央和政府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数度提出确立国家荣誉制度,为新时期的典型报道带来发展机遇。本文尝试从媒介生态学的视角,梳理典型报道的诞生、发展与影响力式微与媒介生态的关系,以武汉市首届荣誉市民的评选和表彰前后的媒体表现为例,探察城市荣誉制度与典型报道的关系及其带来的新生态。
一、计划经济发展需求与典型报道诞生
典型报道的诞生与发展,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折射,是社会主义生产竞赛的重要组成部分。生产竞赛是计划经济体制下一种重要的经济手段,通过对各行业先进典型进行评选、奖励、报道,能够有效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热情和积极性,促进社会经济的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竞赛最早发端于斯大林时期的斯达汉诺夫运动。1935年,采煤工人斯达汉诺夫屡创单位时间挖煤的惊人记录,成为了轰动世界的新闻人物。在媒体的广泛宣传下,斯达汉诺夫成了先进劳动工作者的代名词,全苏联展开了学习斯达汉诺夫的运动。斯大林对斯达汉诺夫做出了高度评价,认为“它表现了社会主义竞赛的新高涨,是社会主义竞赛的新的更高阶段的标志”[3]。不久,斯达汉诺夫运动传入中国,对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乃至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渡过因国民党顽固派经济封锁而造成的经济困难,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开展大生产运动,并以生产竞赛的方式推动。在宣传和推广生产竞赛过程中,典型报道诞生了。1942年,4月30日,改版后的《解放日报》头版头条对吴满有积极开荒、踊跃交粮的先进事迹予以突出报道,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产生了强烈反响。这篇报道的成功,不仅让吴满有成为劳动模范,报道本身也成了解放区其他新闻工作者效仿的榜样。吴满有之后,赵占魁、刘建章、南泥湾359旅等各个领域的典型人物纷纷涌现,形成中国典型报道的第一个高潮。据统计,仅1943年上半年《解放日报》上各条战线刊登的先进人物就有600多名[4]。在各大报刊的大力宣传下,陕甘宁边区的生产竞赛迅速发展成为大规模群众运动,充分激发了生产热情,提高了生产效率,推动了边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典型报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更是推出了农业大寨、工业大庆等先进劳动集体,其对生产发展的促进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典型报道的诞生与发展壮大以计划经济为土壤,是整合社会成员、发动广大劳动者、树立党和政府威信的重要方式,它诞生于生产竞赛,同时又反过来有力地支持和推动了社会生产运动。计划经济体制是典型报道最重要的生态环境因子,对其产生和发展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市场经济制度确立与典型报道失落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行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市场机制带来的红利让人民的劳动热情空前高涨,劳动竞赛这种经济组织方式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随着旧的生存土壤逐渐消失,典型报道的发展空间也不断缩小。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典型报道的价值产生质疑,陈力丹提出“典型报道消亡论”,认为典型报道观念“将随着文明的发展而逐渐消亡”[5]。这一观点在学术界掀起了一场长达一年多的关于典型报道和宣传的必要性与市场需求的学理论争,更多学者主张改进典型人物报道,拓展新空间,认为这种报道方式仍有存在必要。2009年,陈力丹再度撰文对其观点进行补充,认为尽管典型报道不再具有轰动效应,但是社会仍然需要典型,它能够“提供一种温馨的相互激励的道德环境,一种和谐的社会气氛”[6]。
实际上,改革开放以来,在报道实践上,典型报道开始寻求新的传播和表达方法。报道题材由劳动典型、革命典型转为侧重于道德典型;报道目的由推动劳动生产竞赛转为塑造新时代的道德标杆,以弘扬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提升社会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报道模式也从旧式的“高大全”转为“成就与困惑”并存。然而,新时期不断改革中的典型报道并未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关于典型报道效果的实证研究数据大多证明,典型报道在今天的受众接受度和信任度很低。值得注意的是,2006年,《青年记者》联合大众网进行的“新闻从业状况网上调查”表明,媒体着力打造的“先进典型宣传”在“新闻人平时最爱看的新闻信息”一项中所占比例竟为0。尽管新时期的典型报道尝试从题材、形式等多方面进行转变,其报道实践中的有限效果让人不得不承认典型报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初期,由于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影响力逐渐降低。
如今,典型报道的媒介生态环境与其产生和巅峰时期已不可同日而语。经济上,市场经济制度的确立瓦解了典型报道的经济生态因子,即社会生产运动;社会思想上,价值观多元化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政府的权威性,使得典型报道的社会效果和评价下降。
然而,媒介生态环境的改变并不意味着典型报道不再为社会所需要。相反,正是由于新时期,社会转型和改革的进程加速,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和信息网络的高速发展,多种思想观念相互撞击和交融,尤其是如后现代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等社会思潮的影响,社会大众的个体意识以及民主化意识增强,价值取向、评价标准日趋多元化,社会价值失范、道德危机等社会问题频频出现,对国家和社会的团结和稳定产生不良影响。因此,榜样的精神力量才被突显出来。
三、城市荣誉制度与典型报道的新生态
城市荣誉制度是地方国家机关通过特定权力确立并授予荣誉称号的规则的总称。一方面,为了落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建立国家荣誉制度”的精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另一方面,为了增强城市凝聚力和向心力,提高市民素质,增加城市知名度、美誉度等城市软实力,武汉市在全国率先提出“建立武汉城市荣誉制度”的战略目标,制定相关条例并实施。
2013年,武汉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文,出台《关于建立武汉城市荣誉制度的通知》。经过2年多的筹备和推选工作,于2015年产生了首届武汉市功勋市民、模范市民和文明市民,包括3位功勋市民、18位模范市民和1个模范市民群体。在此次评选过程中,新闻媒体既是重要的信息发布和公众投票渠道,也是重要宣传单位之一。武汉本土报纸、电视台、网络媒体在评选前刊登“评选办法”原文,并开辟专栏,刊发与活动相关的评论员文章;评选中期在收集投票信息的同时对候选者的先进事迹进行传播;评选结果公布后,围绕产生的功勋市民、模范市民及群体集中刊发了一大批报道,也对荣誉市民所引发的社会各界的反响进行了报道。在此次评选活动中,新闻媒体在前期扮演的是旁观者的角色,作为信息沟通和互动平台为受众所接受和信任;在后期扮演的是宣传者的角色,由于前期的良好铺垫,关于获奖者的典型报道也就水到渠成,获得较好的社会效果,强化了城市的精神共同体性质,激发和唤醒了市民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宿感,从更高层次推进武汉市精神文明建设的水平。
荣誉制度的确立与实施,为武汉市典型报道的媒介生态带来了两重变化:一是在典型报道的媒介生态环境中增添了制度因子。城市荣誉制度,是城市管理者行使荣誉权力的规范化,其实质是通过评选和表彰符合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典型代表,以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社会整合。可以说,荣誉制度是典型报道的制度化形态。两者在传播方法和目的上相一致,皆期待通过树立权威符号形象,即道德标准和政治标准的象征,为社会提供一种导向,统一思想、稳定形势、维持道德规范、弘扬主流价值观、增强社会凝聚力。城市荣誉制度的确立,既为典型报道提供信息和内容,更重要的是,它为媒体塑造典型、宣传典型予以制度推力和保障,并促使先进典型的推出过程成为良性运转的机制。因此,制度因子的增加,为典型报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与路径。
二是提升了文化因子在典型报道媒介生态中的重要性。文化对于城市而言,不仅是超然于社会存在的意义和符号的集合,更是维持与建构社会关系的关键维度。城市荣誉制度的主要功能即通过对为城市发展做出杰出贡献的市民进行表彰,树立时代城市精神标杆,促进城市文化的建设和繁荣。武汉历史悠久,从商代的盘龙城至今已有三千余年的城市史,深受古代的楚文化、明清时期形成的码头文化、近代的革命文化的影响,逐渐形成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和文化。同时,武汉也是一座英雄辈出的城市,近年来,在推进创新武汉、和谐武汉的建设中,全市各行业、各阶层都涌现出一批自觉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典型,包括爱民为民,情系百姓,永远做党和人民的好儿子的吴天祥;全国特级优秀人民警察徐斌;用亲情为失足少年撑起一片蓝天的妈妈法官邱建军;为残疾人群撑起一片蓝天的鲁桂珍;扎根教坛情感育人的桂贤娣;抗洪抢险大英雄王占成等。这些城市英雄的发掘和传播,是城市文化的载体,同时也丰富了城市文化的内涵。城市荣誉制度能够促进城市文化的凝练、繁荣和传播,兴起学习楷模的社会风气,从而为新时期典型报道提供生存和发展土壤。
武汉市在建立城市荣誉制度上的积极探索和实践,为当地媒体典型报道的生态环境增添了新制度因子和文化因子。对处于困境的典型报道而言,是一次新的发展机遇。典型报道可摆脱其价值和实践的诸多困惑,重新确立其社会价值,提升影响力,从而充分发挥价值导向和人才激励作用,引导人们重塑正确的价值观和时代精神,增强社会主义凝聚力,进一步提升全民族的精神价值和道德情操境界,强化和巩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注释:
[1]邵培仁等:《媒介生态学:媒介作为绿色生态的研究》,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张威:《典型报道: 渊源与命运》,《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9期
[3]高海波:《斯达汉诺夫运动与典型报道》,《国际新闻界》2011年第11期
[4]丁淦林:《中国新闻事业史新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5]陈力丹:《典型报道之我见》,《新闻学刊》1987年第1期
[6]陈力丹:《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典型报道演变的环境与理念》,《当代传播》2009 年第5期 <\\Y8\本地磁盘 (F)\2011-新闻前哨\2016-2\BBBB-.TIF>
(孙发友: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春晓: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