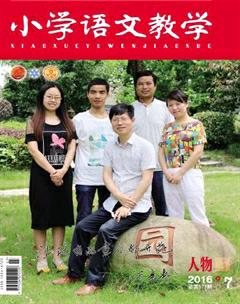顺从自然
何夏寿
听到过这样一个课例。
小学一年级儿童诗《春天》一课。
春天对冰雪说了什么,冰雪那么听话,都化了。
春天对小草说了什么,小草那么听话,都绿了。
春天对花儿说了什么,花儿那么听话,都开了。
一位教师在教学这首诗的时候,问了孩子们这样的问题:春天对冰雪说了些什么呢?真的是春天在说话吗?请大家说一说,冰雪化了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春天》这首诗写了以冰雪、小草、花儿等为代表的大自然的生灵,在春天到来的时候,一种和谐融合、天真烂漫、蓬勃向上的生存形态。诗歌其实无意要向读者说明“说了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第一个问题“春天对冰雪说了些什么”还可以看作是教师偏离了诗歌阅读的轨道,而第二个问题则完全毁坏了诗性的美妙,因为藏在这个问题背后的显然是“春天真的不会说话”或者“春天根本就不会说话”,至于第三个问题简直是从根本上否定了这首诗的艺术价值,说白了就是否定了这首诗——因为潜台词是:冰雪化了的真正原因是天气暖和了,温度升高了……
儿童时期是“理性的睡眠期”,作为一名低年级的语文教师,这么“心急”地向孩子硬塞科学知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由此看来,“文学是审美的,感性的,抒情的”,这些差不多嚼烂了的俗语,也不见得人人都能心领神会,更不见得人人都能付诸文学课堂。故而,能否真正落实文体意识,将文学教成文学,依然任重道远。
当然也有十分“文学”的课堂。一位教师在语文课上问小朋友:“花儿为什么会开呀?”一个小朋友说:“她睡醒了,她想看看太阳。”另一个说:“她一伸懒腰,就把花骨朵顶开了。”有的说:“她想看看小朋友是否会把她摘走。”还有的说:“她想听听小朋友唱歌。”突然孩子们一起问:“老师,您说呢?”老师想了一会儿说:“花儿特别懂事 ,她知道小朋友都喜欢她,就仰起她的脸,笑了。”听到老师这么一说,孩子们的脸比花儿还灿烂。
这位教师的成功,倒不是因其能随机应变,而是在于具有一定的儿童文学素养。他能用儿童逻辑(也是文学逻辑)想象花儿会说能笑。我之所以这么说,因为事后我知道,这位教师备课时准备的标准答案是:“花开了,因为春天来了。”但当他听了孩子的发言后,更换了一个更为儿童化、生活化,当然也是文学化的答案,将一本正经的“标准”转化为诗性烂漫、意味深长的“童话”。着实为他叫好!
两位教师,几乎相似的教学内容,完全不一样的教学理念,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教学追求:前者功利,后者诗性;前者心急,后者从容;前者在拼命吆喝着孩子们快快长,后者在深情款款地牵着孩子们玩。
选哪种?还是卢梭说得好:“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我们就会造成一些早熟的果实,它们长得既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快就会糜烂。”
窃以为:教育不可以与孩子的天性为敌,而应该与之为友,把天性作资源,作起点。文学教育,务须顺从儿童的“自然”之法、文学的“自然”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