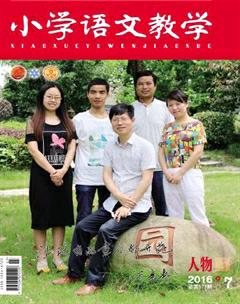童话,可以这样教
本刊记者
记者:何老师,您30多年钟情于童话教学,是当今教坛童话教学的高手。您的经典童话课教学,在小学语文界引起了广泛的好评,如童话习作课《推陈出新写童话》、童话阅读课《鲤鱼报恩》等。今天,我想请您先谈谈,开展童话教学要注意些什么。
何夏寿:童话因其拟人、幻想、非写实等表达特点,囊括了儿童文学的全部艺术特质,如天真、朴素、温暖、诗意等。自儿童文学产生以来,童话一直占据着儿童文学的半壁江山。儿童对童话具有天生的、十分纯粹的迷恋之情。当下,童话成为小学语文重要的课程资源,在很多公开教学活动中,童话也常常有头有脸地被冠以“专场教学”的身份和地位。
前不久,我听了两场“童话教学观摩课”。也许是格外钟情于爱的主题,或者是对文学大师的特别推崇,两堂课上两位教师都将俄国大文豪托尔斯泰的《七颗钻石》作为公开教学内容。从课的呈现形态上说,施教的两位青年教师比较投入,上得也有一定水准。但凭我对童话的理解,有些地方教师对文本的解读是不当的,或者说是误解。
在第一堂课上,执教的女教师分别在黑板上挂上画有木罐、银罐、金罐和七颗钻石等事先准备好的图片,请小朋友用自己的话说说小姑娘做了件什么事。一个男生说,故事讲小姑娘用自己找到的水,救了小狗、妈妈、过路人这三个人……还未等男生说完,教师马上“敏锐”地更正:“小狗不是人。所以,故事主要讲小姑娘用水救了两个人和一条狗……”
无独有偶,第二堂课上,一位男青年教师切出了大块时间,和孩子们谈小姑娘的木罐之变,并且特别强调罐子变化的层次性、递进性。教师意味深长地说:“由于小姑娘施爱对象的不同,罐子变化的珍贵程度也不同,救小动物(小狗),木罐变银罐;救亲人(妈妈),银罐变金罐;而救陌生人(过路人),金罐里冒出七颗钻石。”……
这两个教学片段有一个相似的观点,就是人是人,狗是狗。无论是前一位女教师直截了当的“小狗不是人”,还是后一位男教师的“救小动物”一说,他们犯了一个共同的且是致命的文本解读错误——童话逻辑等同于生活逻辑!
记者:请您具体说说童话逻辑是怎样的,在实际教学过程中又该如何运用童话逻辑来进行文本解读呢?
何夏寿:众所周知,童话是以假定的手法创作的非写实性儿童文学,以幻想的形式,调用夸张、象征,特别是拟人等手法进行写作,是童话的基础性“功课”,也是童话之所以称为童话的标志性“风景”。试想,要是童话不拟人,不让小狗小猫说人话,做人事,那还能算童话吗?童话中的小狗小猫绝不等同于现实生活中的小狗小猫。童话里的小狗小猫,被赋予人的思想、情感、价值,他象征、代表着生活中各种各样的人。如果能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不会去特别“更正”小狗不是人,不会去特别强调小狗是小动物。反过来,我们会去肯定小狗就是人,小动物就是特别需要我们去爱护、去关心的弱小、困难之人。
造成教师这种对于文本的误读,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是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影响,语文教学就是语言文字教学,就是听、说、读、写教学,这种功利主义、应试主义的教学理念,造成了不少教师普遍缺乏儿童文学教育的理念和素养。因而,即使教材中选入了诸如《七颗钻石》这样的童话故事,不少教师还是简单化地把它当作识字造句、思想教育的一般性文体和进行所谓的语言文字训练、文以载道的教学工具罢了。
其实,作为一种非写实性儿童文学样式,童话拥有独特的叙事风格和美学特色。童话逻辑指的是童话中幻想与现实相结合的规律。这种逻辑对应着儿童万物有灵、物我不分、自我中心、任意组合等心理特点,成为孩子喜欢甚至痴迷童话的依据。在一个成功的童话中,童话逻辑重点表现在童话世界各种假定性事物的存在方式上。其实,文学都是假定的,和小说等写实性文学相比较,童话的非写实性与小说等写实性文学在“假定”度上有大小、深浅不同之分。小说等假定度小,或者说浅,与现实生活比较接近,甚至比较近似现实;而童话的假定意识强烈、夸张,所呈现的艺术世界或艺术形象远离现实,甚至根本不可能出现在现实生活中。如现实生活中,狗是不会说人话的,而童话让狗像人一样说话;在现实生活中,猫是不会自己拿着鱼竿去钓鱼的,而童话让猫像人一样去钓鱼;在现实生活中,个体生命都是有限的,一个人不能永远地生活下去,更不可能死而复生,可是在童话里,可齐天地,可无生死。说到底,童话逻辑是一种情感逻辑,即“上帝说要有光,于是便有了光”的那种逻辑。童话正是借用这种贴近孩子心理实际的思维、情感逻辑来对谬误实施保护,而这一点也只有具有缪斯天性的孩子才能真正领会它的含义。在孩子们看来,童话中动物开口说话、灰姑娘穿上玻璃鞋、睡美人睡了一百年仍美丽如初就如同现实生活一样自然,任何一个孩子都不会因此而大惊
小怪。
可惜我们成人总是爱好遗忘,遗忘了自己曾经的纯真和稚拙,而且又喜欢用居高临下之势审视儿童,用自以为既严谨又严密的因果逻辑、事理逻辑去指责儿童的纯真、超然。出现了案例中的“小狗不是人”“狗是动物”,出现了“人的生命比动物重要,救动物,上帝奖励银罐;救路人,上帝奖励七颗钻石”这种成人化的解读。如果我们能真正读懂童话逻辑,根本无须用坐实的成人逻辑、成人价值去“更正”孩子的“谬误”,去灌输“同样是生命,人比动物重要,他人比亲人重要”这种成人价值。因为在童话里,狗就是“人”,是有思想、有情感、能说会笑的“人”;在童话里,王子与小鹅,国王和小狗,他们的生命一样重要。至于罐子质地之变,我认为无需特别强调,孩子也不会像守财奴一样去关注什么金的银的。如果一定要解读,要深究,我以为罐子之变是对小姑娘坚持行善的累积性肯定,如同我们肯定一个人做一次好事和长期做好事,因行善的偶然性和一贯性不同,采取的奖品就不同是一个道理,而不是人比动物珍贵的价值呈现。
记者:听您这么一说,我对童话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本来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同样的稻草人,在不同的童话里却呈现出截然不同的表现。有的稻草人依然是个“稻草人”,不会说不会动,例如叶圣陶先生笔下的《稻草人》;有的稻草人,不但能说会道,而且还会跟人打斗,像《绿野仙踪》里的稻草人。原来,这都是童话逻辑在从中“调度”啊。
何夏寿:可以这么理解吧!
记者:何老师,我还想请教一下,有人说真要教好童话,必须阅读一些童话教学的理论。请问,您对这个问题持什么看法?
何夏寿:这个问题也不是专为“童话”而备的。哪一种文体的课,真要教好可以不需要理论支撑?所以这是一个共性问题,而不是童话的“专供”。不过,我是十分赞同一线教师在教学之余,读些童话方面的理论,这样可以提高我们的教学效果。
记者:在理论满天飞的当下,就您的学习视野,哪些理论对童话教学较有帮助?
何夏寿:哦,我说三个文学理论吧。先说“天真阅读”理论。“天真阅读”即要天真地、孩子般地投身到阅读中去,对作品的写作没有任何怀疑、保留或者咨询,任由作品将你带到他所描写的国度。这是美国文学理论家希利斯·米勒在《文学死了吗》一书中阐释的一个文学阅读理论。
我以为,在小学低年级,天真阅读尤其值得重视,低年级的童话教学,尤其要采用“天真阅读”法。
人教版一年级上册有篇课文叫《雪孩子》。故事讲了一个大冬天里,兔妈妈要去外面找吃的,给自己的儿子小兔子堆了个雪孩子。雪孩子和小兔子成为了一对很好的玩伴。后来,小兔子睡觉时,不小心引发了一场火灾,雪孩子奋不顾身救出了小兔子,自己却融化了,变成了一朵很美很美的白云。
有位教师带学生朗读了这个故事后,告诉学生,这个故事运用了童话的形式,用了拟人的写法。为了解释什么是拟人,教师对学生说:“你见过小兔子和雪孩子真的在一起玩耍吗?”教师的意图很清楚,生活中小兔子是动物,小雪人是人堆出来的状物,小雪人根本不会行动,当然不可能和小兔子玩耍。他要用这个事理告诉学生,故事把小兔子和雪孩子当人一样写,写得有思想能玩乐,两人还能做朋友,这就是拟人。可一年级的孩子不理解,回答说真的见过小兔子和小雪人在玩。教师急了,问在哪里见过的。极大多数小朋友说课文里写着的,有个小朋友站起来说:“有一个下雪天,我看到小兔子躲在小雪人背后玩捉迷藏。”这个学生这么一说,其他小朋友也纷纷举手回答了差不多的说法,弄得教师十分尴尬。其实,教师“非天真”的提问,实在多余至极,甚至弄巧成拙。他这一问,除了根本没有解释清楚什么是“童话的形式”,什么是“拟人的写法”,反而让原本干净、简洁的课堂变得拖沓臃肿。这种与儿童“为敌”的“反天真阅读”,严重破坏了学生对文学的美好想象。
我认为,对小学低年级学生是用不着这样心急地进行文体特点、修辞知识讲授的。对小孩子来说,不讲这些文体特点和修辞知识,不但不会影响他们欣赏、理解文学,反而会使他们走进文学的深层,保持对文学丰富而旺盛的热恋。另外,儿童的心性是泛灵的。他们看到小兔子跑过小雪人面前,完全可以想象成他们在玩捉迷藏。即使我们向他们保证“一个是动物、一个是状物,真不可能做朋友玩捉迷藏”,我估计他们也是不信的:那《拔萝卜》中,小花猫、小老鼠这些小动物不就是和老爷爷、老奶奶做朋友,一起拔萝卜吗?
记者:是的,您举的例子很有意思。我还想听您说第二个理论呢。
何夏寿:第二个理论叫“延迟怀疑”。“天真阅读”是不是只适合在小学低年级?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有的人一生都保持一颗纯真的童心,保持儿童的天真和想象力。能天真时且天真,这不仅仅只是良好的阅读习惯,也是现代人良好的生活态度。
但是话要说回来,我们在倡导“天真阅读”童话时,也要警惕天真主义,更不要人为地、故意地让孩子去相信文学里的事情和人物一定在现在生活里真实地存在。
那天,我听我徒弟上《丑小鸭》,在结课之前,他安排了请学生说说读后体会这一环节。学生们说以后我们要保护所有鸭子,要劝阻大人不杀鸭子,更不吃烤鸭什么的。我觉得,学生由“丑小鸭”这个文学形象激发了他们潜在的善良和爱心,这正是童话教学所要追求的效果之一。可是我不赞成孩子们“劝阻大人不杀鸭子,更不吃烤鸭什么的”的说法,因为这不是“天真阅读”的范畴了。照此逻辑,读了《丑小鸭》就不吃烤鸭,那读了《鸡妈妈的新房子》就不吃炸鸡了,读了《七颗钻石》就把水全给了小狗,读了《女娲补天》还一天到晚指望着天什么时候塌下一角,好去学女娲做个补天英雄。“天真阅读”是指阅读过程中对文学的想象世界充满信任,而不是阅读过后还确信绝有此事。
这里需要引入一个文学理论,即柯勒律治的“延迟怀疑”。所谓“延迟怀疑”是指文学达到的一种效果——读者在开卷之前或掩卷之后,能够意识到这个故事是作家虚构出来的。需要强调的是,在阅读作品的过程之中,却要宁愿相信作家所讲述的故事是真实的,作家并没有在编织谎言骗人。在小学高年级学生的童话教学中,笔者以为要保持“延迟怀疑”,在课堂上教师没有必要过早地去捅破“虚构”这层“窗户纸”。即使在高年级学生中,哪怕已经有学生认为童话里所写的只是“写写而已”,并不能“当真的”,教师也要运用“延迟怀疑”,至少以“情感是真实的”这一底线去守卫作品的真实性。如读《巨人的花园》,要让小朋友感受到荒诞美、隐喻美;读《去年的树》,要让小朋友感受到诚信美、凄凉美;而读《从现在开始》,则要让人感受到故事的稚气美、怪异美。
但“掩卷之后”,就需要“转换频道”了。要让学生明白,故事只是故事,而不是生活写真,更不可一味沉浸在文学的想象世界里不能自拔。文学作品里的“鸭子”和生活中的“鸭子”,虽然字面上是一样的,但毕竟是两个不同概念的“鸭子”。前者是包含作家主观情感、赋予象征意义的鸭子,而后者是客观的、生物意义上的鸭子。一般情况下,即使是低年级的学生,也不会产生将童话中的鸭子和现实中的鸭子混为一谈的现象。个别故事读得少而且偏于理性的学生,即使问到这样的问题,教师也不要过于放大,像我的徒弟那样“故事里的鸭子和生活中的是不一样的”的模糊说法,一句带过,不失为一种策略。如果能再加上一句“故事就是故事,不是什么都是真实的”,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记者:听您这么一说,我想起以前我听一位名师上过的一节《卖火柴的小女孩》,他在结课时要求学生全体起立,双手合十,配着悲凉的音乐朗诵道:“这样一位可爱的小女孩,这样一位可怜的小女孩,就这样永永远远地离开了我们,让我们永永远远地将她记在心中。”这场景让全场学生潸然泪下。听您这么一说,这课原来是偏离文学轨
迹的?
何夏寿:是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文学缺失症”:将虚构的文学形象当作真实的生活人物,将一个根本没有与我们生活过的人物,说成永永远远地离开了我们,而且还要双手合十,为她祈祷,为她祝福。这也不是“天真阅读”,而是教学的病态。可能有人会说,文学作品不是培养学生悲天悯人的文学情怀吗?问题是,学生在教师导演般的指挥下,集体起立,“表演”祷告,先问问这位教师自己真有对小女孩之死的怜悯和祈祷吗?如果没有,还组织学生举办这种“仪式”,那就只能说表达的是虚假的感情,这就是矫情。不但与文学精神相敌,且与人性培植相违。
记者:太有道理了。说实话,听了这样的课,我心里也“咯噔”一下,也有点“不舒服”,但具体要我说说为什么会“咯噔”,为什么“不舒服”,我也说不出个子丑寅卯。听您用文学理论一分析,豁然开朗了。请再说说第三个文学理论吧!
何夏寿:当下,有一种童话教学走向,那就是将童话教学和哲学、伦理学、文化研究阅读连在一起教,认为光把童话教成童话显得太浅显、太单薄、太小儿科。笔者认为,从建构论的角度讲,童年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任何时代的儿童都是社会文化建构的概念。我们不能囿于儿童是“天真的”,我们就只有教“天真的”这种狭隘的教学观,童话教学当然可以教儿童“天真的”以外的很多东西。但对于诸如“文化研究阅读”教学,我认为应该浅尝辄止,并且只能在小学高年级中进行“尝试”,而且要把握好这个“度”。
这实际上涉及一个理论概念,即“文化研究”。所谓“文化研究”是特指文学阅读中的一种方式。米勒认为:文化研究阅读是一种批判性阅读,它“质疑文学作品如何灌输关于阶级、种族或性别关系的信条”。也可视作拓展性阅读,拓展了文学作品除文学性以外的文化外延。
我曾经听到有位教师教完安徒生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女孩》一文后问学生:“同学们,你们觉得小女孩和奶奶一起飞走了,是幸福还是悲伤的?”学生们一边倒地说是悲伤的。因为,天堂根本是没有的,小女孩的飞走,其实就是冻死了。这时,教师这样告诉大家:“对于我们来说,小女孩飞走了,你觉得是悲伤的,没错。但对于安徒生爷爷生活的那个叫丹麦的国家,一个善良的穷人安静地死去,其实还真是幸福的事。因为,他们国家的人们是相信此生有人间、来生有天堂的。能够早日升入天堂,这当然是幸福的!”
我觉得这样的教学,介绍了不同的文化语境,加深了对文学的多元理解,同时,拓展了学生的文化视野。对于六年级学生来讲,还是比较贴切和自然的。
但我也听过类似问题的不同文化解读。一位教师的文化视野比较开阔,在讲授这一问题时,讲到了文章安排了小女孩卖火柴,而没有安排小男孩;安排了小女孩的奶奶,而没有出现小女孩的爷爷。这是为什么?学生当然答不上来。继而教师讲了西方男权主义视野下的女性观,讲到安徒生对女性的观念、认识,等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教师还引入了安徒生的另两篇童话,一篇是《海的女儿》,另一篇是《野天鹅》。《海的女儿》中美丽善良的小人鱼公主渴望进入人类社会,得到王子的爱情,付出的代价是她那甜美的嗓音和动人的歌喉;而在《野天鹅》中,艾丽莎为了拯救她的十一个哥哥,听从仙女的告诫:“从你开始工作的那个时刻起,一直到你完成的时候止……你也不可以说一句话……他们的生命是悬在你的舌尖上的,请记住这一点。”通过提取这两篇童话的共同观点,让学生们感受到安徒生的男权主义倾向的严重性。我觉得对小学生讲这些文化背景就显得太拔苗助长了,简直有为难学生之嫌。
记者:是的是的。何老师,您将多年来阅读文学理论的体会和一线的童话课堂教学结合起来的解读,真令人大开了眼界。您的这些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我相信对于广大教师开展童话阅读教学会有很大帮助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谢谢!
责任编辑 郝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