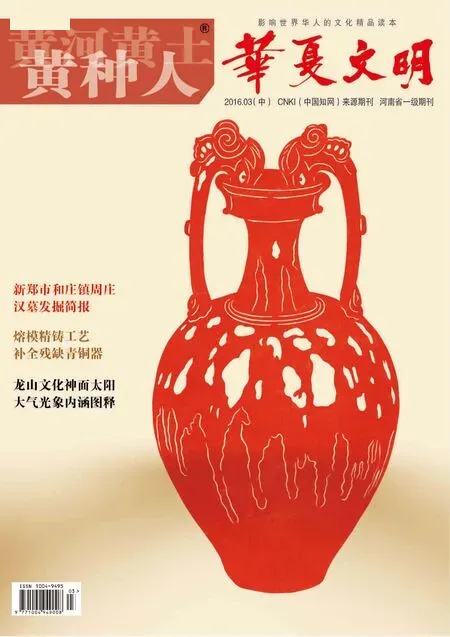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墓主族属浅析
□侯新佳 李根枝 张 芳
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墓主族属浅析
□侯新佳 李根枝 张 芳

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中的壁画
1998年,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在陕西蒲城洞耳村发掘了一座保存较好的元代壁画墓[1]。此墓壁画保存完好,且有确切纪年,为蒙元墓葬中少见。学术界人士对此颇为关注,多位学者对此壁画墓进行分析研究。蒙元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大融合的一个重要时期,其种族之复杂在中国历史上可说空前,蒙元墓葬考古资料的发现侧面反映了这一历史现象。从目前考古发现来看,蒙元墓葬中有确切纪年的蒙古人墓葬数量不多。洞耳村元代壁画墓《简报》中认为,墓主夫妇二人为蒙汉合璧,即男主人为蒙古人,女主人为汉人。对此,笔者所持看法略有不同,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斧正。
一
洞耳村元代壁画墓形制为八角形砖室墓,由墓道、墓门、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组成,坐北朝南,墓顶为穹隆顶。这种墓葬形制是宋金以来中原地区汉人特有的墓葬形制,汉文化因素明显。墓室内装饰有壁画,在墓室壁上装饰着 “堂中对坐图”“侍从图”“行别献酒图”“醉归乐舞图”“双雁图”;墓室顶部分四层,装饰着帘幔、梁枋彩画、戏花童子、火焰珠和如意云头,每种图案绕墓顶一周。墓室壁画中人物形象为蒙古装束打扮,壁画中还有表现蒙古习俗的 “行别献酒图”“醉归乐舞图”等生活场景,反映了当时蒙古人进入中原之后,蒙古文化随之在中原地区传播的社会现象,具有浓厚的草原生活气息。但是,我们还应该看到墓葬中装饰了中原宋金墓葬中常见的传统壁画,如有夫妇对坐图、侍从图,包括梁枋彩画、戏花童子、如意云头等传统装饰图案。可以说,洞耳村壁画墓在整体风格上真实地反映了蒙汉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情形,体现了蒙元墓葬的时代特色。那么,我们如何来判断墓主人的族属情况呢?蒙元时期社会情况复杂,各民族相互融合、不同宗教共同发展等诸多因素形成了蒙元时期社会文化的多元化特征。因此,我们必须将该问题置于大的历史背景下去考虑,才能更好地判断墓主人的族属,以求更真实地接近历史原貌。
洞耳村壁画墓中有墨书题记“大朝国至元六年岁次己巳”,据原文考证,该墓年代为1269年,属蒙古时期墓葬。蒙古时期即大蒙古国时代,指从成吉思汗1206年统一蒙古各部到1271年忽必烈改国号大元之前的这段历史。
大蒙古国时期,蒙古人的统治中心基本上是在蒙古草原,汉地不是帝国的政治重心,而且汉人也不是主要的统治对象[2]。蒙古人初入中原,由于语言、文化差异太大,造成了和汉人之间的隔阂。首先,从语言上来看,蒙古语和汉语差异较大,蒙古人和汉人之间交流多有不便,这样也不利于两种文化的交流融合。大蒙古国时期,蒙古统治者多汉语造诣不深,君臣之间、官员之间进行政事交流尚需通事进行翻译。李志常 (1193~1256年)在《长春真人西游记》中记载:“师有所说,即令太师阿海以蒙古语译奏,颇惬圣怀。”此处,“师”即指长春真人,“圣”即指成吉思汗。可见当时成吉思汗对汉语知之甚少,在和全真教邱处机交谈时,还需要由汉化较深的契丹人耶律阿海担任传译。蒙古统治者是如此情况,其中下阶层汉语能力也应相去不远。宋人徐霆在《黑鞑事略》中记载[3]:“鞑人本无字书,然今之所用,则有三种,行于鞍人本国者,则只用小木,长三四寸,刻之四角,且如差十马,则刻十刻,大率只刻其数也。”从史料中可知,蒙古人本无文字,其文明程度相当落后,可以说,蒙古人初入中原对汉文化及习俗尚未深入接触。
陕西蒲城洞耳村元墓中有墨书题记,上书“娘子李氏云线系河中府人”“张按答不花系宣德州人”等字句,据此可知墓主张按答不花是从宣德州(今宣化)迁居此处,后娶河中府人李氏为妻。墓中墨书题记墓主人“系宣德州人”,这里涉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籍贯问题。籍贯在旧时主要指从自己家族开始生发繁衍的主要地域,大至国或省,小至县市或村、里等聚落均可成为籍贯。古代所谓籍贯通常指父、祖的长居地[4]。根据“张按答不花系宣德州人”的语意推断,张按答不花的祖上曾在宣德州长期居住。金代末期,蒙古人南下侵金,元太祖八年(1213年)攻克宣德,至此蒙古人才逐渐进入中原。蒙古太宗六年甲午(1234年),金亡。
据史料记载,蒙古统治者南下平金,很多蒙古人因从军有功得以镇守某地,并居住于此,其后人亦常以该地为祖籍地。但是,陕西蒲城洞耳村壁画墓墓主人的情况略有不同。 据《元史》(卷 58)《地理志一》记载:“顺宁府,唐为武州。辽为德州。金为宣德州。元初为宣宁府。太宗七年(1235年),改山东路总管府。中统四年(1263年),改宣德府,隶上都路。至元三年(1266年),以地震改顺宁府。”从史料看,宣德州为金代设置,蒙古人灭金后此地名称多有变动,宣德州是金人的旧称,因此只有久居此处的居民才会沿用旧名。2004年,河北宣化葛法成墓出土有买地券,上书“经大元国上都路宣德府南开永宁坊”等字,墓葬纪年为至元十四年即1277年,据此可知,当时本地民间称呼也多改为宣德府,而不是宣德州。假设墓主人为蒙古人的话,那么其祖先或本人应该是在元太祖八年(1213年)以后在宣宁府著籍长期居住的,之后的某年迁往陕西居住。但是,蒙古人攻克宣德后,已将其改名为宣宁府或山东路总管府或宣德府,并不再使用宣德州这一名称。如果墓主人是蒙古人的话,那么他或其后人对更名之事肯定知之甚详,更不应该书写“张按答不花系宣德州人”,故墓主人很有可能不是蒙古人。墓中题记“张按答不花系宣德州人”该如何解释?据《金史·田琢传》记载,蒙古人攻打金朝时,“河北失业之民,侨居河南、陕西,盖不可数计。”袁国藩先生曾著文考证金元之际江北之人民生活,战争来临,“人民逃亡,出于兵劫,亦由赋重。盖太祖南下,河北之民,多窜身河南。”[5]《元朝名臣事略》“内翰王文廪公”记载:“开州东明人……会河朔乱,举家南渡。”可知金末战事频繁,烽烟四起,河北等地接壤蒙古草原,最先受到影响,当地居民南迁更是情理之中。
从上述情况来推测,墓主极有可能为金代宣德州人,受战事影响,迁徙至陕西,并在当地安家落户。
二
史学界认为蒙元时期有四等人制——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第三种人为“汉人”,此处汉人是广义上的汉人,即北方的契丹人、女真人、高丽人、汉族人等,元代的汉人不等同于汉族人。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地区且多已汉化,故蒙古人统一北方地区后,统称这些人为“汉儿”。
据墓中题记知,墓主人姓张名按答不花,此姓名是汉姓加蒙古名合在一起使用的情况。那么,此人到底是汉人还是蒙古人,是汉人的蒙古化还是蒙古人的汉化?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一个民族融合的时期。当时,蒙汉之间相互涵化,有蒙古人采用汉式姓名与字号的,也有甚多汉人采用蒙古名的,萧启庆先生在其文章《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中说,蒙古、色目人采用汉式姓名字号与汉人采用蒙古名之原因全然不同。由于蒙古人在政治上居于主宰地位,而汉人在文化上占优势,汉人采用蒙古名者或为接近权力源头的宫廷近臣,或为冒充蒙古人身份而谋求一官半职的猎官之徒;而采用汉式姓名之蒙古、色目人则皆系汉化较深者。蒙古人如改就亡国之俗,放弃蒙古认同,在政治上有害无利,自为智者所不为[6]。蒙古人使用汉式姓名的情况多在元代中后期 ,其汉化程度相对较高,而汉人采用蒙古名的现象则自大蒙古国初入中原之时就已存在。
蒙古本无姓,习惯把所属部族名称冠于其名前,汉人以“氏”译称之。《黑鞑事略》记载:“霆见其自上至下,只称小名,即不曾有姓,亦无官称。”[7]由此来看,蒙古人在名称使用上只有名并无姓。墓主人张按答不花生活在蒙古人刚进入中原的蒙古时期,其姓名由汉姓张和蒙古名按答不花构成,而当时蒙古人才入中原,受汉族影响不大,因而也无添加汉姓之道理。元代中后期,蒙古人受汉文化影响较深而常见取汉名的,并且取名方式很少有以汉姓加蒙古名的。
20世纪后期,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出土一方墓碑,该碑立于元顺帝至正丙戌年(1346年)。当地刘姓居民称,此墓碑是纪念到临淄来的高祖营丘刘公名为五公的。碑文说,高祖五公“系斡罗那歹人也”。他作为蒙古军士,驻扎在山东,并经历了“李侯兵革”[8]。 “李侯”是李璮,降蒙古人后为山东地区的汉侯,专制山东三十余年。元世祖中统三年(1262年),叛元降宋,即碑文中所说的“李侯兵革”。从时间上看,营丘刘公比洞耳村壁画墓墓主张按搭不花要晚上数十年。据杨志玖先生的文章可知,立此碑的是第二代僧住和忽都二兄弟,似乎在第二代时已以刘为姓。但时至元世祖统治时期,元朝已经建立,定都中原,受汉文化影响更甚;同时我们还了解到,在谱系上前四代或者前五代还是用的蒙古名字,可见蒙古人更为注重保持其民族独立性。相反,洞耳村壁画墓墓主张按答不花生活在蒙古人刚进入中原的时期,却已然被汉化了,这种情况稍显悖逆于常理。
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十)《元汉人多作蒙古名》记载[9],元初,蒙古统治者有赐名习俗,故“自有赐名之例,汉人皆以蒙古名为荣,故虽非赐者,亦多仿之,且元制本听汉人学蒙古语。”
据《元史》记载:“刘国杰,字国宝,本女真人也,姓乌古伦,后入中州,改姓刘氏。帝壮之,诏加怀远大将军,赐号霸都,国杰行第二,因呼之曰刘二霸都而不名。”
“贾昔剌,燕之大兴人也。本姓贾氏,其父仕金为庖人。昔剌体貌魁硕,有志于当世。岁甲申,因近臣入见庄圣太后,遂从睿宗于和林,典司御膳,以其须黄,赐名昔剌,俾氏族与蒙古人同,甚亲幸之;又虑其汉人,不习于风土,令徙居濂州。”
“刘哈剌不花,其先江西人。倜傥好义,不事家产,有古侠士风。居有年,遂为探马赤军户。”
此处几人,或原是女真人,或是在燕赵地区居住,在蒙古统治者进入中原之初,他们最先接触到蒙古人,并开始为其服务,得到赐名的荣誉。
蒙古人进入中原是以征服者姿态出现的,其族群在政治上享有特权。而当时的汉人是被征服者,虽在文化上占有优势,但在政治上处于劣势,故“不少汉人冒用蒙名,仿袭胡俗,以谋取实际利益。”[10]据徐霆记载:“燕京市学,多教回回字及鞑人译语,才会译语,便做通事,便随鞑人行打,恣作威福,讨得撒花,讨得物事吃。”[11]元代中后期,社会上更多的汉人冒用蒙古人姓名。据《元史》卷二一成宗纪,大德八年(1304年)三月诏,“诸王、驸马所分郡邑,达鲁花赤唯用蒙古人,三年依例迁代,其汉人、女直、契丹名为蒙古者皆罢之。”
元代,在山西地区,当地亦有类似的取名现象,有学者对此进行了研究[12]。阳城人郑钧,又名郑阿兒思兰,是忽必烈即位之初汉军万户郑鼎的后人。其父郑制宜在元成宗初被授大都留守,领少府监,兼武卫亲军都指挥使。大德十年(1306年),郑制宜病死,阿兒思兰袭职[13]。皇庆元年(1312年),翼城县尉苏抄儿赤当为汉姓蒙古名字[14]。元统元年(1334年),晋城县主簿焦不花为汉姓蒙古名字[15]。至正元年(1341年),盂州判官李薛察儿为汉姓蒙古名字[16]。闻喜县簿张伯颜不花亦为汉姓蒙古名字[17]。以上人物均生活在元代后期,但可以从侧面反映出元代社会汉人受蒙古习俗影响,为在仕途上更进一步而取名蒙古名字。
《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考古报告》中对党项族人取用汉姓的情况有所描述:“这些党项族人长期与蒙古、汉族等杂居共处,在取名时有可能用汉姓,如吴哈剌那孩、梁都立别兴、李嵬令普、刘嵬立普、何逆你立嵬、杨朵立赤,等等。”[18]
在蒙元时期,有许多汉人使用蒙古名的现象,这是由多种社会因素导致的,有学者对此做了相关研究。汉人采用蒙古名的形式有三种:一是汉姓汉名全佚;二是蒙名冠汉姓;三是蒙汉名字兼备[19]。该墓墓主人所用姓名即为第二种形式。13世纪初蒙古仍为落后的游牧社会形态,直到建国之初始创文字,大多数蒙古人皆为文盲,与文化源远流长的汉人社会差距极大,所以该墓男主人为蒙古人的概率极小。
洞耳村元代壁画墓没有文字材料表明墓主名字是蒙古统治者所赐,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墓主人取名为张按答不花显然是跟随社会大潮流,为融入蒙古人的生活圈子或者在仕途获得提升而更改姓名以求得到蒙古人的认同。
该墓题记上有 “祭主长子闰童悉妇”一行落款,笔者以为“悉妇”即是媳妇的意思。张民权先生的《“媳妇”考源》记载[20]:“偶见宋拓本东坡帖作女悉妇,查字书不载此字,不知何本。苏东坡将‘息妇’写作‘女悉妇’,这有可能是据‘息’与‘悉’语音相同(或相近)而记录的。”由此可知该墓是墓主长子闰童携其媳妇共同祭祀父母并留下落款。张先生在文中考证:“今语媳妇者,大致起称于宋金之时。‘息(媳)妇’一词的出现,主要是宋金时期北方地区入声韵处于衰变过程中,由‘新妇’音转而产生的一个新语词。”根据张民权先生的考证,我们了解到“悉妇”即媳妇,这一词语在宋金时期流行于北方汉人地区,从而进一步推测墓主人应该是长期生活在北方地区并熟知当时习俗的汉人。
三
洞耳村元墓壁画中男人俱着左衽袍服,而在中国北方元代壁画墓中发现的墓主人形象多身着右衽袍服。女真人服饰尚左衽,据《大金国志》卷39记载:“其衣尚白,男子穿圆领、窄袖、左衽紧身短袍,束带,足靴。”蒙古人从1211年开始进攻金,此后宣德州成为战争多发地区,当地居民多有迁徙避难,故笔者推测墓主人可能为金代遗民,故而保持袍服左衽的传统。金人建国后,灭北宋并迁都于燕,受汉人文化影响,其服饰制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金统治者为防止女真人完全汉化,于金世宗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十二月,诏“禁女真人不得改称汉姓及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后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七月,再次重申上述禁令。这些诏令虽然不可能完全阻止女真人汉化,但在不同程度上会对金末元初的女真人在服饰上产生些许影响。
此外,就服饰而言,该墓壁画中人物衣着皆为蒙古服饰,但这并不能作为认定墓主人即为蒙古人的依据。从大的历史背景来看,蒙古人入主中原,其所代表的北方草原文化和汉文化产生强烈碰撞,蒙古统治者采取“草原本位”文化政策,同时又不禁止汉人习蒙语、穿蒙服等,这些都对汉人习俗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促使汉人对蒙古人产生认同感。
明朝灭元之后,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二月下诏,“凡蒙古服式、蒙古语言、蒙古名字一律禁止,提倡蒙汉各从其俗”(《明太祖实录》卷三十)。说明当时汉人受蒙古文化影响穿着蒙古服饰的不在少数。该墓壁画中女主人李氏河中府人身为汉人,但在画中头戴蒙古贵妇常戴帽子——姑姑冠,身穿左衽袍服,正是对当时汉人穿着蒙古服饰社会现象的直接佐证。
20世纪后期,在内蒙古和河北交界地区曾发现多座元代壁画墓,如赤峰元宝山[21]、三眼井[22]、沙子山[23]及凉城县后德胜村元墓[24],壁画题材有表现墓主生前生活的饮宴图、出猎图、归来图,装饰风格富有时代特色,反映了元代社会蒙汉文化交融的现象。画中男性主仆都身着蒙古服装,为元代的官服;无论蒙古、色目或汉人为官者,都必须穿着蒙古式服装,从而使人容易将墓主人误解为蒙古贵族。但从墓制及葬俗推断,显然是汉族官员墓[25]。陕西省蒲城洞耳村壁画墓和此类墓葬风格相似,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众多因素说明该墓男主人虽身着蒙古服饰但不一定就是蒙古人。
蒙元时期是华夏各民族相互交流、相互融合的重要阶段。在此期间,既有少数民族不断汉化的现象,也有汉人在强势的蒙古文化面前蒙古化的趋势。由是,我们在看到那些具有显著时代特色的蒙元时期墓葬时,不能因其含有蒙古文化因素就简单地断定为蒙古人墓葬。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洞耳村元代壁画墓男主人不应定为蒙古人,考虑到当时的社会背景,墓主人应该是从宣德州迁至陕西地区居住的北方汉人。
注释:
[1]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陕西蒲城洞耳村元代壁画墓》,《考古与文物》2000年第01期。
[2]萧启庆:《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台大历史学报》1992年第12期。
[3]宋代彭大雅撰,徐霆疏证,王国维笺证:《黑鞑事略》,《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三辑。
[4]参见基维百科,http://zh.wikipedia.org/wiki/%E7%B1%8D%E8%B2%AB。
[5]袁国藩:《金元之际江北之人民生活》,《大陆杂志史学丛书》第二辑第三册。
[6]萧启庆:《论元代蒙古人之汉化》,《台大历史学报》1992年第12期。
[7][11]宋代彭大雅撰,徐霆疏证,王国维笺证:《黑鞑事略》,《内蒙古史志资料选编》第三辑。
[8]杨志玖:《山东的蒙古族村落和元朝墓碑》,《历史教学》1991年第01期。
[9][10]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三十,《元汉人多作蒙古名》。
[12]瞿大风:《元朝统治下的山西地区》,博士论文,2003年。
[13]袁桷:《清容居士集》卷三十二,《大都留守郑公行状》;柳贯:《柳侍制文集》卷八,《郑阿兒思兰谥敬愍》。
[14]《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复建岱岳行祠碑》。
[15]《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四,《天井关孔庙本息记》。
[16]《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五,《盂县重修庙学记》。
[17]《山右石刻丛编》卷三十六,《闻喜县汤王庙记》。
[18]李逸友:《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考古报告之一黑城出土文书》,北京:科学出版社。
[19]那木吉拉:《元代汉人蒙古姓名考》,《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02期。
[20]张民权:《“媳妇”考源》,《中国语文通讯》1998年第09期(总第47期)。
[21]项春松:《内蒙古赤峰市元宝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83年第 04 期。
[22]项春松、王建国:《内蒙昭盟赤峰三眼井元代壁画墓》,《文物》1982年第01期。
[23]刘冰:《内蒙古赤峰市沙子山元代壁画墓》,《文物》1992年第02期。
[24]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等:《内蒙古凉城县后德胜元墓清理简报》,《文物》1994年第10期。
[25]李逸友:《论内蒙古考古文物》,《内蒙古考古文集》第一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33页。
(作者单位:侯新佳,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李根枝,荥阳市博物馆。张芳,荥阳市文物保护管理中心。)
[责任编辑 秦秀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