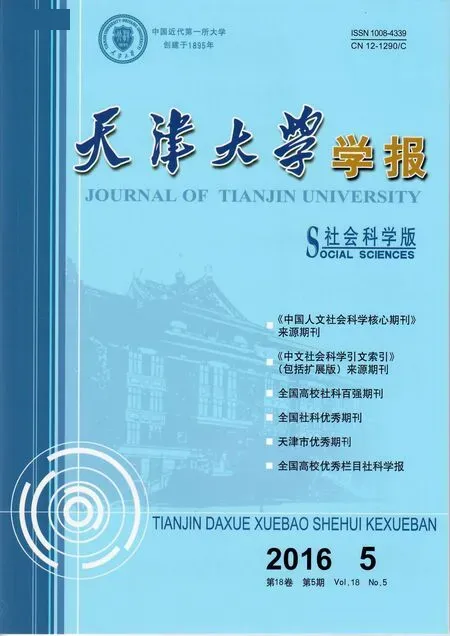社会创业研究的理论模型构建及关键问题建议
薛 杨, 张玉利
(1. 天津大学法学院, 天津300072; 2. 南开大学商学院, 天津300071)
社会创业研究的理论模型构建及关键问题建议
薛杨1, 张玉利2
(1. 天津大学法学院, 天津300072; 2. 南开大学商学院, 天津300071)
结合当前国际最新研究动态和已有研究成果,构建出基于要素视角的社会创业理论模型,并对概念范畴框架与具体研究变量进行了归纳与细分,进而针对理论框架中的社会价值创造、社会创业者、机会识别与评价、组织形式与组织身份、制度理论、社会网络等关键性问题进行了提炼与评述,指出了未来应集中面向如何强化理论驱动以及理论情境化的研究设计、提炼社会创业机会的本质属性及其构成维度、提炼制度约束条件下的资源整合机制、探索文化氛围对社会创业过程的作用机制等四个方面,进一步深化社会创业的研究。
社会创业; 要素视角模型; 制度理论; 理论情境化
社会创业是建构社会和谐、可持续发展的新兴概念,已成为公共管理、企业社会责任、非营利性组织活动必不可少的研究主题。过去十年间,面对国家能力相对弱化和公共服务不足所造成社会分化的现状,大部分民众支持的解决贫困、社会不公、财富分配不均、环境污染等诸多法律往往由于权力制衡的僵局而难以通过,促使政策制定者、环保主义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将寻找创新性、可持续性解决方案的希望寄托于社会创业活动[1],身肩使命的社会创业者成为了当前西方社会改善社会状况、解决社会问题的新途径。诸如Ashoka、Skoll Foundation、Schwab Foundation、Fast Company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基金会、中介媒体等组织,通过设奖、电影、案例研究等多种形式,对成功的社会创业者和创业故事进行全方位的打造。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创业相关学术机构、期刊杂志在世界各地相继成立,引领和带动了社会创业的发展。政府也通过政策、税收、资金等方面的调整对社会创业行为进行鼓励与支持。随着社会创业领域越来越多的从业者、政策和公共利益的出现,学术界也从最初的怀疑观望,到近十年来包括国际顶尖的主流期刊在内的社科领域,基于社会创业丰富的研究素材和跨多学科领域的学术特征投入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然而,尽管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发展,社会创业学始终未能在科学研究框架中确立自身应有的学术地位,原因至少有三点:其一,学术界和从业者至今仍然未能在社会创业实质含义上达成共识[2];其二,目前该研究领域仍未能形成统一的研究体系,缺乏清晰的概念框架和研究边界[3];其三,社会创业研究涉及多门学科、多种理论和研究方法,由于各学科所涉及的研究内容等各不相同,导致研究成果碎片化,研究方向过于分散,未能形成一套有别于其他研究领域的社会创业理论[4]。Short(2009)在对社会创业研究特点进行评估后认为,持续的概念争论不仅导致理论发展的瓶颈,还严重影响了其合法性的获取。社会创业研究领域亟需在融合与借鉴其他创业类型学术成果的基础之上,尽快形成自身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基于此,本文在系统梳理相关研究文献基础上,基于要素视角构建了社会创业的理论模型,并进一步明确了亟待研究的关键研究议题,目的在于为社会创业研究者指明研究方向与趋势,同时也有助于社会创业研究领域的收敛。
一、 要素视角的社会创业理论模型构建
学术界关于社会创业概念仍处于广泛的争论阶段。社会创业领域的文献显示,现有文献主要围绕社会创业、社会创业者和社会性企业三个界定方向进行定义。这其中,社会创业的定义侧重创业过程与行为;社会创业者的定义更为关注提出倡议的创业个体;社会性企业的定义则突出创业的有形成果。事实上,概念争论恰恰反映出所观测现象的复杂性和多样性。针对社会创业活动,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首先,如果说社会创业属于创业活动的范畴,那么它与一般创业活动(或者说商业创业活动)的本质区别是什么?这恰恰是早期研究讨论的重点问题,基本共识是与商业创业活动相比较,社会创业活动的本质不在于盈利与否,而在于驱动社会创业活动的使命具有独特性,更强调社会性使命而非商业性使命。其次,社会创业活动之间的差异并不比商业创业活动之间的差异小,那么,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勾勒出可用于一般性解释社会创业活动的过程模型?这是目前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也是难点问题。最后,如何评价社会创业活动的绩效?鉴于社会创业兼顾社会价值和商业价值的本质特征,如何评价社会创业活动的结果就成为学术研究必须予以解决的重要问题。
Dacin(2010)提出了聚焦“使命”对社会创业进行定义的新思路[5],认为“使命”产生的动机源自所处的时代背景,其最终成果正是解决社会问题而产出的社会价值,从而能够将微观的个体特征有效融入宏观的社会背景差异之中;“使命”的产生、建立、实现和巩固作为一套完整的社会实践过程,可以帮助研究者更为全面地认知并界定社会创业。如果按照“使命”的思路对这些定义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大多数研究者主要根据谁是社会创业者、社会创业活动包括哪些具体行为、他/她出于何种目的做出与众不同的行为等进行的界定。即社会创业研究主要聚焦于四个要素:社会创业者、经营范围与创业环境、社会创业资源与过程、社会创业使命。这四个方面的定义基本涵盖了学术界对社会创业定义的争议范围,同时也印证了Choi根据Gallie(1956)关于“争议概念理论”的观点,认为今后的社会创业概念研究将向“集群式定义”发展的论断[6]。因此,社会创业研究的理论研究框架应该包括:社会创业者、经营范围与创业环境、社会创业资源与过程、社会创业结果,见图1。

基于此框架,我们进一步对社会创业相关文献的进行梳理和分析,以“social entrepreneurship”、“social entrepreneur”、“social venture”、“social enterprise”为关键词在EBSCO、Web of Knowledge、ABI/INFORM和 Science Direct四大数据库搜索出自1991—2014年以来社会创业四个研究要素所涉及的变量,并进行了梳理和总结,见表1。

表1 概念范畴框架与研究变量
表1中,社会创业结果、经营范围与创业环境、社会创业者、社会创业过程四类要素包含各自变量。其中,“社会创业结果”要素包含三个层面:第一层是将社会创业看作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社会价值创造方案;第二层将社会创业视为一种跨部门的商业企业社会责任实践;第三层将社会创业视为缓解社会问题和促进社会转型的手段。 “社会创业环境”要素除了社会、政治、经济、法律等一般环境外,还包括制度环境、文化环境等促进或抑制社会创业活动的影响变量。“社会创业者”要素重点关注创业发起者,对创业团队或其他支持创业的组织内部成员的研究相对较少[7];而针对社会创业个体特征的描述,主要对比不同类型创业者之间以及社会创业者与商业创业者、社会创业者与非创业者在个性、特质、技能、行为、激励、动机、感知、形象与身份等方面的差异。“社会创业过程”要素涵盖三部分内容:社会创业组织侧重对社会性企业的跨部门合作、治理结构、资金问题以及在不同国家中合法形式的差异分析;市场导向主要针对社会弱势群体所制定的营利策略和模式;社会创新探讨的是社会创业在组织模式、创业手段等方面的创新方式。
当前文献说明,现有社会创业研究从不同学科出发,既有讨论上述概念框架中的一部分(如在社会创业环境下对社会价值创造的能力进行评估,或比较社会创业者与非创业者的特征)[8],也有讨论各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如检验社会创业者的个体特质与发现创业机会之间的关系,或社会创业者如何确定社会创业使命等)[9],同时许多研究也开始探讨这些变量之间的作用机制。基于此框架,社会创业研究开始取得一些实质性进步,特别是针对社会创业者方面的研究积累了不少学术观点,形成了社会创业者并非不同于商业创业者、社会创业者反而具备更强的商业经历具备更强的人格特质等一系列基本认识。另一方面,针对社会创业过程的研究,理论驱动型研究开始出现,已有研究借鉴制度理论、资源基础观、社会网络理论等成熟理论来解释社会创业过程中资源获取、机会识别、模式构建等重要的基础性问题,并开始从社会创业较商业创业不同的本质特点出发来开展研究设计,具有较好的发展潜力。本文将基于此框架,进一步梳理并提炼社会创业研究领域的关键议题。
二、 理论框架的关键研究问题提炼与评述
1. 社会价值创造
社会价值涉及道德行为标准、利他主义动机和社会性推广,更深层次上体现对自由、平等、宽容的价值观追求[10]。社会创业领域中的社会价值创造主要用以反映增加社会财富、缓解社会问题和提供社会需求,直接体现着社会创业者的使命。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的本质差异在于前者聚焦社会价值,后者关注经济价值。其背后则隐含着社会创业研究的关键之处,也涉及学术界长期争论的焦点:即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是否有本质区别甚至相互冲突?特别是实践层面的社会性企业往往兼具营利与非营利的混合属性,进一步加深了关于社会创业成果是否包含其经济价值产出这一问题的争论。一部分学者对此持否定态度,而相当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营利性经济行为能够帮助实现慈善活动与商业活动的相互融合,是社会创业使命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11]。根据Dacin(2011)的观点,社会创业使命不能完全否定或忽视与其密切相关的经济价值,原因在于经济价值产出往往作为社会价值创造的金融性资源,助推社会创业者实现最初目标。在社会创业研究范围内,二者虽本质属性不同,但却并非相互冲突,反而在功能上相辅相成;但前提条件要求社会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就对二者进行等级上的明确划定,即社会性企业始终要将社会价值作为发展的第一要务,而经济价值永远服务于社会价值的创造。这样的等级划分将作为社会创业的根本属性和成立基础,同样也是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的区别所在。
此外,有学者将创业学中慈善、公益行为与社会创业进行比对研究,通过对社会价值创造的角色、社会结构、目标、可持续性、经济来源、时间跨度六个维度的横向对比发现:社会创业与公益行为共同关注的是如何选择和建立运作的方式,从而具备针对社会制度和文化的再造性;而慈善一般不具有创新性和持续性且易产生对捐赠资金的依赖,因此社会创业在社会价值创造方面更具优势[12]。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社会”一词自身的概念模糊性和争议性,导致当前研究中的社会价值难以被准确测量与评估。
2. 社会创业者
社会创业者已经被证实在社会创业的启动阶段和过程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针对社会创业者个体的分析是社会创业研究的核心内容,研究主要聚焦于谁是社会创业者以及社会创业动机两个层面。针对社会创业者,学术界对其概念基本达成了共识,即针对复杂的社会问题,通过创新手段和商业模式,创建具有社会性质的组织,以推动社会进步与变革的个体[13]。社会创业者作为社会创业的发起者,与一般创业者相比具备前瞻性、创新性、风险承担和变革者的属性[14]:首先,社会创业者具有务实性和远见卓识,能够通过某项新发明、新方法、或已知技术的改进,预见未来可能实现的大规模、系统可持续性社会变革;第二,社会创业者具有足够的创业热情和创新勇气,熟练地掌握商业方法,能够跨越传统方式对产品、服务或对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进行创新;第三,社会创业者能够针对反馈不断完善、调整方法与方式,并勇于承担创新所带来的风险;第四,社会创业者偏好作为社会变革者所带来的社会成就感,具有非物质追求及利他主义的个人情怀。
针对社会创业动机,社会创业案例中相当一部分社会创业者在创业之初往往缺乏足够的经济基础和社会资源,却依然能够不计较个体利益而承担起巨大的创业压力与成本。社会创业早期研究将其动机归结于社会创业者非物质追求的个体偏好,如社会成就感、自我约束能力以及“利他主义”倾向。此后,有学者认为情感作为动机对创业行为的调节作用更加显著[15]。因此,用基于情感之一的“同情”解释社会创业起源。Miller(2010)等人提出“社会创业是基于社会需求未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所产生的‘同情’反应”,即“同情”是社会创业的动机[16]。然而,由于管理学中“同情”的概念属于“边缘化情感”,不仅与“移情”等概念难以区分,对其本身知之甚少且极易被其错误诱导[17]。同时,仅仅基于“同情”的社会创业动机,缺少对创业者特有“意识”和“能力”影响的考量,依旧无法准确表达创业动机与创业成果之间的特殊关系。社会创业动机继而被进一步拓展为聚焦社会创业个体对机会关系演变的感知。Grimes和McMullen(2013)对此做了进一步解释,社会创业过程被嵌入到一个由动机、感知和资本等构成的机会关系矩阵之中,“同情”即为其中的动机之一,并推断“同情”作为亲社会动机可以更加合理地解释社会创业者面对社会问题时的反应[18]。
3. 社会创业过程中的机会识别与评价
Mitchell等(2002)将创业识别定义为“人们基于对机会和创业的增长评估、判断及决策时所依赖的知识结构”[19],核心是利用不同方法及路径理解创业者行为和思考过程。在社会创业领域,创业者面对环境的不确定性,更多凭借的是自身本能和直觉对创业方案进行选择。例如,创业者“机敏”的特征可被视为其创业感知的方式;个体对社会创业务实性和道德合法性的感知也可以进一步促进社会创业的愿望;诸如同情等特定情感因素亦会影响感知过程,从而改变认知结构,激发社会创业行为[16]。但难点在于,社会创业背景的高度不确定性导致创业感知难以被预测和评估,而若要准确把握社会创业者评估创业机会时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信息处理能力,必须基于特定的创业背景。因此,Dacin(2011)提出,将适用于不确定背景下探索决策制定过程的“奏效理论”,应用于社会创业感知的研究之中,即创业者在高度不确定的背景和有限资源之下,利用自身的本能和直觉,预先设计出几种不同的创业路径和策略,并根据资源和环境的变化对策略进行相应调整[4]。这一思路将有助于区分社会创业与商业创业感知过程的差异,进而挖掘社会创业感知涉及相关的知识结构和信息处理能力。
4. 社会创业组织形式与组织身份
组织形式与组织身份是社会创业研究中重要的理论工具,用于解释社会创业的形成与管理,以及更为重要的社会创业道德、权力等相关问题。从概念上分析,组织形式是某一组织结构为了适应所处的制度背景而形成的典型配置[20],即该组织所表现出的结构特征;而组织身份则是针对组织固有属性的解释,以促使该组织唯一性和特殊性的形成,是基于组织特征的辨识。研究证明,通过对社会创业各种组织形式的有效区分,能够促进关于组织身份的认知,而清晰且能够被一致认同的组织身份将影响社会创业长期战略的制定和组织结构的选择。
社会创业组织形式与组织身份研究主要集中于对不同组织界限的划分,且此二者研究进展相辅相成。近三十年中,由于各组织形式之间的界限愈加模糊,多重组织形式结合的混合型组织迅速崛起,并形成了营利、非营利及混合组织形式共存的局面。其中以财务可持续性和社会目标为双重使命的混合型组织被认为是社会性企业最为理想的组织形式。同时,学者利用组织身份解释企业差异时验证了企业往往拥有多重身份,加之社会创业所涉及商业性和社会性双重导向的影响,该多重组织身份似乎特别适用于社会创业。此外,基于Albert等(1985)针对组织身份具有功利性和规范性双重特性的认定,Short等(2009)继而明确了社会创业组织表现出以创业或产品为导向的“功利性组织”和以社会或他人为导向的“规范性组织”的双重身份[21],且基于社会价值的后者对于社会创业的导向性更为明显。
5. 社会创业与制度理论
基于制度理论的创业研究在初期阶段更多关注于制度(规则)以及不同环境如何影响创业行为。社会创业变革社会的特殊性质决定其随时面临着与现行管理体制、制度等方面的诸多冲突。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是:社会创业个体如何更好地理解与管理“制度冲突”。特别是当社会创业者面对无法解决的复杂社会局面,其解决能力和解决范围都显得愈发局限之时,研究者期望通过制度层面的分析来确定根源所在,继而帮助社会创业个体更好地适应并化解冲突所带来的不利影响。Sud等(2009)挖掘出了五种抑制社会创业的制度因素,包括组织合法性压力、同质化压力、道德压力、政治压力以及结构性压力[22]。其中需要强调的是,能否获得组织合法性是社会创业取得成功的关键[23]。组织合法性是所处社会对于组织所做出的社会价值贡献的认可,同时意味着能够持续地获得各类社会资源。因此,能否吸引并持续获得社会资源是判断组织合法性的决定性因素。研究还表明,通过对组织目标和核心使命的界定进而明确组织身份,更容易实现组织的合法性[24]。然而,由于社会创业为了解决资金获取渠道有限的天然困境,往往在实践中兼有营利与非营利的混合属性,这导致了社会性企业一方面需要通过市场化手段拓宽融资渠道,满足利益相关者不同利益诉求以维持资金来源;另一方面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同时还要试图减少对于私人投资、社会捐赠等资金的依赖,以努力保证其非营利的社会属性。显然,社会创业关于营利与非营利的制度逻辑是相互冲突的,不仅造成社会创业组织运行的巨大压力,还将对社会创业组织的合法性产生负面作用,继而影响社会创业的社会价值创造。因此,在制度压力下社会创业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将社会性非营利事业与经济性营利活动在制度理论和学术认知上进行有效的融合。
随着创业学中制度理论研究的深入,有学者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影响创业行为的制度(规则)因何产生,又因何消亡?即“制度运动”问题。Mari(2009)将制度运动的原因归结为“制度缺陷”[25]。显然,社会创业相互冲突的制度逻辑属于制度缺陷的范畴。Hervieux等(2010)通过对非营利领域文献的回顾也验证了这一判断:在新制度形成过程之中,市场化行为作为有效资助社会使命的合法手段逐渐被承认,并已被各类资源视作规范社会创业者的方式。同时,公众的信任被认为是社会创业的重要资产,创业观念能否被公众认可与接受,意味着是否符合社会创业合法性,决定着社会创业的成败。然而由于社会创业的变革属性,特别是当制度(规则)变革尚未被社会广泛接受时,社会创业似乎仍旧难以获得合法性。基于此,Mair(2009)透过贫困妇女所受宗教限制与就业之间的冲突,将社会创业的合法性问题引申为如何建立广泛的社会性慈善观念,提出通过利用以“概念拼装”为形式的“修辞”手法对旧有制度逻辑进行适当扩展,以此来减少针对变革的社会阻力,增加公众的支持[25-26]。
Mair所提出的“修辞”手法是制度理论中制度创业获取合法性的重要工具。从理论观点分析,制度创业作为利用资源改造现有制度或创造新制度的行为,与社会创业在社会创新过程中所扮演角色非常类似,甚至已有学者将制度创业视为社会创业的研究背景。因此,如果运用制度创业的“修辞”手法将社会创业者塑造成为“历史英雄”的形象,或许能够成为社会创业获取合法性的有效途径[26]。可以这样说,制度创业为社会创业组织合法性提供了进一步的研究潜力与空间。然而也有学者认为,制度理论强调的是组织过程如何经过制度力量进行塑造,社会创业则更加看重个体如何利用和调动不同资源以实现社会变革。如果单纯停留在主导社会变革的英雄式个体层面,不仅无法帮助我们全面理解社会创业的动态过程,而且容易忽视外部的利益相关者、网络、组织等在跨越文化障碍和制度缺陷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因此,Montgomery等人(2012)在关注个体对社会变革引领的基础上,提出了“集体性社会创业”的理念,即在解决社会问题、去除陈旧制度、建立新制度的过程中,跨部门多角色的集体作用超过了“英雄式”的创业个体[27]。
社会运动相关理论对此加以验证,进一步说明跨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不仅能够为创业构想和实践拓展社会传播的渠道,还能有效获取组织合法性,并最终彻底实现制度化的变革与更新。同时,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创业在制度随时间推移而逐渐消亡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学者将社会运动理论与制度理论相联系,为观察所面临的阻力、变化、去除机构化和制度性退化等问题提供理论支撑。
6. 社会创业与社会网络
现有文献针对社会网络的关注主要基于创业者和创业资源之间的关系,进而理解社会创业的背景。除了创业者自身所拥有的部分资源以外,创业者还需要通过与他人或组织之间的联系,扩大诸如信息、资本、技术、人员等创业所需的社会资源。这种通过建立各社会资源之间的相互联系,整合出的有形或无形的资源网络即为创业者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存在于结构、关系和感知三维度之中[28]。从结构性维度进行分析,社会网络为社会创业者的使命搭建了可供嵌入和传播的系统。例如,每年举办的SKOLL世界论坛,面向世界各国邀请社会创业者与同行共享他们的创业经历。类似这样的信息与知识共享的网络关系不仅能够促使内部成员之间进行理念分享,其创业方面的宝贵经验也将得以跨地区进行传播与扩散,为进一步创造社会效益提供更为广泛的解决方案。从关系维度来看,社会创业者个体的社会关系是能否实现其创业使命的重要影响因素。其中,声誉作为社会创业者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为创业者和潜在投资者之间信息不对称的解决搭建了桥梁和纽带,并在企业生存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和支撑作用。感知维度涉及特定背景之下的信任和信誉,通过隐性的个人价值观和信仰在网络参与者中得以进一步共享。本地网络内的社会创业者、投资者、团体、民间组织和政府等权力主体,除了基于相似的地域背景而得以相互认可之外,还通过彼此之间的信任确立共同的社会创业目标,继而在发展本土能力、协调资源和分享信息的过程中,最大程度地提高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的生活质量。所取得的社会成果也将进一步巩固社会对于社会创业的信任,继而有利于社会合法性的获取,这是社会创业竞争中的重要优势所在。
三、 推动社会创业研究进一步深化的努力方向
1. 进一步强化理论驱动以及理论情境化的研究设计
当前社会创业研究所面临的最大挑战,莫过于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均处于特定的情境之中,其行为受到所处文化、制度等社会因素的影响。相关学者逐渐开始寻求解释“个体组织层面—环境层面”之间相互作用的变化关系,继而试图利用制度理论对社会创业进行探索,即将环境因素作为社会创业组织形成过程的重要变量加以分析。Austin等(2006)证明了政治、文化、税收、监管、人口和宏观经济状况都影响着社会创业过程[29];Weerewardena等(2006)通过社会创业多维度模型演示了动荡和变化的社会背景将严重制约社会价值的创造,从而影响社会性企业绩效和资源获取[30];Spear (2005)验证了在民族背景的差异下社会创业在解决长期失业问题中所发挥的不同作用[31]。此外,近十年跨国社会创业活动的兴起,更是对以往社会创业在单一国家成功案例的普适性提出了挑战。如面对中国民营企业的慈善捐款问题[32],学者无法直接使用西方管理学经典理论中的“制度理论”进行解释,原因是该现象背后的政治制度、政策法律、传统文化价值观等情境化特征与西方理论产生的情境化特征具有极大的差异[33]。
借鉴Bamberger从宏观(结构、环境和时间框架等因素)和微观(态度、认知和行为等因素)两个层面建构情境化理论的思路[34],未来社会创业研究一方面应注重基于本土化的基本国情、经济发展水平、地域差异性等结构性因素,以及制度变革速度、社会接受能力等时间框架性因素;另一方面应注重独特文化变量在不同文化背景之下,个体理解、接受、互动、信念和假定的差异。如针对社会创业营利与非营利交织的制度冲突,不同社会制度中的个体对于制度冲突的理解和管控方式有何不同;社会创业者在跨越边界和类别的过程中如何管理不同利益相关者的预期;制度性变革在何种社会条件下能够更加刺激社会创业和商业创业;哪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力量能够更为有效地促进社会创业等等。因此,如何在已有理论基础之上,通过情境塑造抓住制度理论与社会创业的相互关联,构建有利于解释现阶段本土化现象的社会创业理论,从而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区域的社会创业实践进行解释和指导,将对未来社会创业研究领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 提炼社会创业机会的本质属性及其构成维度
“机会”在商业领域被定义为区别于现实的未来期望且对目标实现的坚定信念[35]。在创业学研究中,机会意味着能否得到基于未来回报的有限资源:商业创业的投资人所看重的是经济性回报,导致商业创业者必须时刻关注某一产品或服务的市场规模和变化趋势;而社会创业的投资人往往基于对未来社会性回报的预期,因此社会创业者更加关注如何通过创新的方式对社会性问题进行有效的解决,并且他们始终坚信自身的变革理论和组织模式能够更好地利用投资者的资源以满足社会性需求。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社会创业的需求通常大大超出现有社会性企业所能够提供服务的数量,这也意味着社会创业相较于商业创业而言拥有更多的机会。因此,聚焦“机会识别”是未来社会创业的重要研究方向。其中,以Shane为代表的发现学派所提出的机会发现理论,将创业者视为发掘市场环境中潜在创业机会的被动者角色,而以Sarasvathy为代表的创造学派所提出的机会创造理论,将创业者视为根据市场不确定环境进行机会创造的主动参与者。前者突出了创业者较非创业者更为敏锐发觉创业机会的能力,社会创业者只需要进行发现并加以利用;后者则认为社会创业的机会并非客观存在,而是在创业者探索新的生产和服务方式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若基于机会创造理论的观点,社会创业者是如何对自身的行为结果进行反思并加以创造性地提炼?若基于机会发现理论观点,社会创业者又是如何对所发掘的机会进行准确地判断与评估?社会创业者曾经的创业经验能够为发觉新的创业机会提供哪些积极的帮助?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与探索。
3. 提炼制度约束条件下的资源整合机制
商业创业通过经济收益、物质激励方式以及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分别在投资人、员工和消费者之间创造和巩固合作关系。但由于社会创业创造社会价值的根本属性决定其在参与交换的价值形式、受众群体、时效性和评估等方面与商业创业存在较大差异[36]。例如,社会创业受限于资金获取渠道,只能更多地依靠非物质激励手段对员工和志愿者进行招募和挽留;由于社会性绩效评估的难度较大,社会创业只能凭借其对社会变革的理念、所产生社会效益的阐述,以及对社会价值创造过程的描绘,说服包括组织成员、投资者在内的利益相关者;而社会创业所提供的社会性产品和服务较为抽象,消费者在交易关系中则更加被动。“社会认同理论”表明,一旦社会群体辨别并明确承认某一个体所代表着某种特定身份,则该个体的行为结果将会改变人们对于此身份的认知和期望。社会创业实践中,媒体宣传、基金会庆祝活动等形式,对于成功的社会创业故事和创业者形象的打造,不仅提升了组织内部成员通过身份联想所获得的成就感和满足感,还能够加强社会群体关于所创造出的社会价值和社会效益的主观体验,从而在社会创业交易过程中达到自我认同和外部认同的双重效应:内部员工和志愿者的组织忠诚度更加牢固,继续投身社会性事业的热情更加强烈;投资人和消费者提升了社会创业效果的认可和满意,将为社会创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更广泛的资源和机会。同时,对社会创业成功形象的塑造还可以借鉴“品牌营销理论”的观点,宣传所讲述的创业故事不仅需要在战略上保持与其他竞争者的可辨识度,还要明确划分出细分市场以保证在目标群体中的认同效果。因此在不同背景之下,社会创业者必须通过创业故事的塑造,保证自身社会变革理念和所产生的社会影响能够被相关利益者和社会群体清晰且准确地认知并接受,理解和把握这一社会创业崛起的规律同样极为关键。
4. 探索文化氛围对社会创业过程的作用机制
社会创业背景中的“文化”作用,包括表彰仪式和创业叙述等手段对于社会意义和价值创造的传播至关重要。上文所提到的Skoll世界论坛除了为社会创业者搭建网络平台之外,更重要的作用是通过表彰仪式树立社会创业者典范,传播其在社会价值创造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试图引领大众价值观念和慈善意识,并有助于社会创业组织合法性的解决。同样,媒体通过创业故事的讲述所塑造出的社会创业英雄形象,往往能够激发其他社会创业者对于成功的想象,以及投身社会创业的热情。文化信息传播手段已在实践中被广泛用来创造有利于社会创业的社会氛围。因此,社会创业如何能够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对社会价值创造及社会变革使命的传播创造出广泛的共鸣效应,特别是如何利用社会创业的就业导向功能提升投身于社会创业的热情,继而带动社会普遍关注的就业问题将是未来值得关注的研究内容。
四、 结 语
社会创业本质上是用商业逻辑来解决社会问题并创造社会价值,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社会创业活动必然在我国社会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在过去30年里,社会创业研究发展迅猛,但并未引起我国学者的足够重视。从学术脉络上看,社会创业研究源于创业研究,但又有着鲜明的独特性,具有较强的理论发展空间。面向未来,针对社会创业过程中的机会和资源等相关问题开展研究工作,不仅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创业过程的规律,更利于了解诱发、强化和塑造社会创业活动的要素和机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1]Shaw E, Gordon J, Harvey C, et al. Exploring contemporary entrepreneurial philanthropy[J].InternationalSmallBusinessJournal, 2013, 31(5): 580-599.
[2]Mort G S, Weerawardena J, Carnegie K.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owards conceptualization[J].InternationalJournalofNonprofitandVoluntarySector, 2003, 8(1): 76-88.
[3]Nicholls A. The legigimac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flexive isomorphism in a pre-paradigmatic field[J].EntrepreneurshipTheoryandPractice, 2010, 34(3): 611-633.
[4]Dacin M T, Dacin P A, Tracey P.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 critique and future directions[J].OrganizationScience, 2011, 22(5): 1203-1213.
[5]Dacin P A, Dacin M T, Matear M.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Why we don’t need a new theory and how we move forward from here[J].AcademyofManagementPerspectives, 2010, 24(3): 37-57.
[6]Choi N, Majumdar S.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s an essentially contested concept: Opening a new avenue for systematic future research[J].JournalofBusinessVenturing, 2014, 29(3): 363-376.
[7]Light P C. Reshapi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J].StanfordSocialInnovationReview, 2006, 4(3): 47-51.
[8]Short J C, Payne G T, Ketchen D J. Research on configurations: Past accomplishments and future challenges[J].JournalofManagement, 2008, 34(1): 1053-1079.
[9]Short J C, Ketchen D J, Palmer T B. The role of sampling in strategic management research on performance: A two-study analysis[J].JournalofManagement, 2002, 28(3): 363-385.
[10] Zahra S A, Gedajlovic E, Neubaum D O, et al. A typolog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 Motives, search processes and ethical challenges[J].JournalofBusinessVenturing, 2009, 24(5): 519-532.
[11] Dees J G. Enterprising nonprofits[J].HarvardBusinessReview, 1998, 76(1): 54-56.
[12] Zoltan J A, Boardman M C, McNeely C L. The social value of productive entrepreneurship[J].SmallBusinessEconomics, 2013, 40(3): 785-796.
[13] Ziegler R. Innovations in doing and being: Capability innovation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Schumpeterian political economy and human development[J].JournalofSoicalEntrepreneurship, 2010, 1(2): 255-272.
[14] Bacq S, Janssen F. The multiple face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 review of definitional issues based on geographical and thematic criteria[J].EntrepreneurshipandRegionalDevelopment, 2011, 23(5/6): 373-403.
[15] Dees J G. The Meaning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EB/OL]. http://www.fuqua.dukc.edu/certers/case/documents/dees SE.pdf,2004-10-30.
[16] Miller T L, Grimes M G, McMullen J S, et al. Venturing for others with heart and head: How compassion encourages social entrepreneurship[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 2012, 37(4): 616-640.
[17] Arend R J. A heart-mind-opportunity nexus: Distinguishi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or entrepreneurs[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 2013, 38(2): 313-315.
[18] Grimes M G, McMullen J S, Vogus T J, et al. Studying the origin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ompassion and the role of embedded agency[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 2013, 38(3): 460-463.
[19] Mitchell R K, Busenitz L W, Lant T, et al. Entrepreneurial cognition theory: Rethinking the people side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J].EntrepreneurshipTheoryPractice, 2002, 27(2): 93-104.
[20] Greenwood R, Suddaby R. Institutional entrepreneurship in mature fields: The big five accountancy firms[J].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 2006, 49(1): 27-48.
[21] Short J C, Moss T W, Lumpkin G T. Research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Past contributions and future opportunities[J].StrategicEntrepreneurshipJournal, 2009, 3(2): 161-194.
[22] Sud M, VanSandt C V, Baugous A M.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The role of institutions[J].JournalofBusinessEthics, 2009, 85(1): 201-216.
[23] Oliver C. Strategic response to institutional processes[J].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 1991, 16(1): 145-179.
[24] Wry T, Lounsbury M, Glynn M A. Legitimating nascent collective identities: Coordinating cultural entrepreneurship[J].OrganizationScience, 2011, 22(2): 449-463.
[25] Mair J, Marti I. Entrepreneurship in and around institutional voids: A case study from Bangladesh[J].JournalofBusinessVenturing, 2009, 24(5): 419-435.
[26] Ruebottom T. The microstructures of rhetorical strategy i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Building legitimacy through heroes and villains[J].JournalofBusinessVenturing, 2013, 28(1): 98-116.
[27] Montgomery A W, Dacin P A, Dacin M T. Collective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Collaboratively shaping social good[J].JournalofBusinessEthics, 2012, 111(3): 375-388.
[28] Nahapiet J, Ghoshal S. 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J].TheAcademyofManagementReview, 1998, 23(2): 242-266.
[29] Austin J, Stevenson H, Wei-Skillern J. Social and commercial entrepreneurship: Same, different, or both?[J].EntrepreneurshipTheoryandPractice, 2006, 30(1): 1-22.
[30] Weerawardena J, Mort G S. Investigating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 multidimensional model[J].JournalofWorldBusiness, 2006, 41(1): 21-35.
[31] Spear R, Bidet E. Social enterprise for work integration in 12 European countries: A descriptive analysis[J].AnnalsofPublic&CooperativeEconomics, 2005, 76(2): 195-231.
[32] 高勇强, 陈亚静, 张云均. “红领巾”还是“绿领巾”:民营企业慈善捐赠动机研究[J]. 管理世界, 2012(8): 106-114.
[33] 秦宇, 李彬, 郭为. 对我国管理研究中情景化理论建构的思考[J]. 管理学报, 2014, 11(11): 1581-1590.
[34] Bambeiger P. Beyond contextualization: Using context theories to narrow the Micro-Macro gap in management research[J].AcademyofManagementJournal, 2008, 51(5): 839-846.
[35] Sahlman W A. Some Thoughts on Business Plans[M]. Boston: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Press, 1996.
[36] Agafonow A. Toward a positive theory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On maximizing versus satisficing value capture[J].JournalofBusinessEthics, 2014, 125(4): 709-713.
Construction on the Theoretical Model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uggestions of the Key Issues
XueYang , Zhang Yuli
(1.School of Law, Tianjin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2, China; 2.School of Busines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international research trends and the existing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onstruct a theorymodel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based on the factor perspective.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with different elemental factors is established and subdivided according to their specific variables.In order to offering th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suggestions, the key issues are also discussed, including social value creation, social entrepreneur, cognition and evaluation, image and identity, institutional theory, social networks and so on. These key issues may also predict four trend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in the future, including strengthening the study of theory drive and theory contextualization,extracting the essential attribute andcomposing dimensions of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opportunity,extracting the mechanism of resource integration under the institutional constraints,and exploring the effect mechanism of cultural atmosphere on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factor perspective model; institutional theory; theory contextualizing
2016-06-22.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资助项目(13YJCZH217);天津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资助项目(TJGL12-064).
薛杨(1983—),男,博士,讲师.
薛杨,xueyang@tju.edu.cn.
F270/DF4
A
1008-4339(2016)05-39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