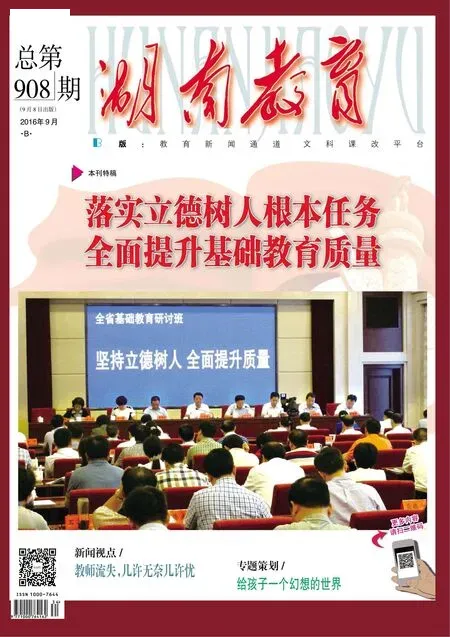语文是粒种子
乔洪涛
语文是粒种子
乔洪涛
一
语文:语者,言也;文者,纹饰也。
每一个新学期,每一届新学生,第一堂语文课,我总会从这两个字入手。我都会极其庄重地在黑板上写下这两个汉字:一横一竖,力求沉稳;一撇一捺,努力优雅;一顿一钩,臻善趋美。因为,这简单的笔画里,饱含着我对“语文”的无尽情愫,饱含着我对母语、文化、生命乃至灵魂的理解和虔诚,凝固着二十多年来我对语文教学与写作的热爱、钟情和感叹。
就像夏季阔大无垠的麦田散发的馥郁而平实的香味,就像山野秋天里沟沟壑壑峭壁的柿树上悬挂的火红“灯笼”,还像站在大海灯塔上遥望远方驰来的一片风帆,语文给我的感受,既踏实又飘逸,既素朴又惊艳,它是灯,是火,是水,是星……是春天里种下的一粒种子。
我总想把这种真实而复杂的感受传递给我的学生们,就像对写字的虔诚,就像对生活的坚韧。语文这一粒种子,几十年的孕育、萌芽、生发至葳蕤,带给我太多太多的感受,我沉浸在其中,从未生厌。它在我生命轻快的疾驰中,带给我缓慢的提醒;它在我飘飘然的肤浅中,带给我厚重的警示;它也在我犹豫、踟蹰、徘徊时给我以抉择的力量,在我孤独、茫然甚至绝望时给我绝处逢生的希望和柳暗花明的指引。
我爱语文,这不仅仅是爱一门给过我庇佑和荫翳的学科;我爱语文,这也不仅仅是我安身立命以求闻达的事业;我爱语文,也不单单是因为我享受爱情一般狂热地进行着文学写作;我爱语文,还因为,这一粒种子,与我的身体一起长大,与我的精神一起丰腴。它用语言摆渡,绽出生命相遇时互放的光芒。它的根须紧紧扎进我的心里,它的一枝一叶都关乎着我的呼吸、喜怒、思考和灵魂的表达。
二
小学的时候,每到新学期开始,最期待的就是尽快拿到《语文》课本,好一睹为快。那时候的语文课本没有现在的开本大,非常朴素。一篇一篇认真读下去,往往发新书的第一天就把语文课本都“看”完了。那心情,就像饥渴的山羊扑到新鲜的野草地上,也像饥饿的孩子突然去坐了席面对着山珍海味一般。我印象深刻的是语文课本的封面很漂亮,是彩色的。春天萌芽的柳枝,背着书包欢快上学的儿童,鲜艳的红领巾,还有飞来飞去的黑色燕子……不仅封面,课本前面有好几页都是彩色的——司马光砸缸,小猫钓鱼,美丽的梯田,神笔马良……色彩,对于孩子是一种本能的诱惑。那时候,乡村没有彩电,没有流光溢彩的画报,所以,鲜艳的语文课本对我来说都是一个斑斓的幻想。
我生长在鲁西南农村。80年代的乡村,物质尚贫乏,温饱问题都难以解决,所以,书籍很少见到。语文课本,就成了打开在我面前的一个堂皇的世界。我记得那时候还认不得许多生字,于是一个字一个字看着拼音拼着读,也能读得津津有味。有时候,就央求爸爸给我读课文。爸爸曾经读过初中,认字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他也喜欢看书,我每次发了课本,他都要把语文课本拿过去,翻着看一看。
在十几岁之前,我没有踏出过我们的村前村后。虽然,我熟悉我们村里每一家每一户的厨房、厕所在哪里,熟悉村东那一片开着荷花的池塘有多深、鱼虾有多少,熟悉村西的高土堆上野草丛里有几只田鼠、有几窝鹌鹑,熟悉村北的黄河岸边红柳生芽芦苇吐絮的具体时日,熟悉村南麦地里藏着几个坟堆伫立着几个草垛,但是我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我们乡下是一望无际的平原,我不知道梯田是什么样子,不知道大山是什么样子,也不知道大海是什么样子。这一切,都是语文课本给我初步描摹了一个新鲜的世界。
现在思考少年对语文的热爱,其本质上是对“外面”的新奇感,是“到外面的世界去”的奔走的人性欲望。这是人性中最原始、最本真的欲望,对“新”事物的追求,对一切未知的“好奇”,鼓动人去了解、去探索。
对语文的热爱,还在于语文带来了母语的启蒙,带来了汉字书写的成就感和阅读朗诵的音韵美感。一个懵懂儿童到学生的本质变化,在我们那里的人看来,最重要的指标就是认字、写字。在那样一个知识、文化贫乏的年代,别说很好地使用汉语,就是能够认识汉字、书写汉字,就已经了不起。
童稚的少年,板板正正坐在教室里,老师手拿粉笔,在讲台上示范我们如何写“一”、写“丨”……老师一边写一边讲,横要平,竖要直,就像是做人,要端端正正,不能歪鼻子斜眼。老师的话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我们觉得汉字原来还这么有意思。晨读的时候,每次端起课本,放声诵读,那优美的汉字,抑扬顿挫的声音,仿佛一种天籁。我觉得“诵读”就是一种音乐,是每一个人的“音乐”,这种起伏的旋律感和音韵美,带给生命美好的享受。我们一年级的彭老师,是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严肃男人,他教了我们几个汉字之后,就拿起用竹子做的教鞭啪啪地点着黑板上的汉字给我们领读,他微闭眼睛,抑扬顿挫,摇头晃脑,看上去很陶醉、很享受。我永远不能忘记彭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不能忘记彭老师手执教鞭的样子,那是一种生命的庄重的仪式感。多少年之后,我固执地把这种记忆复制到我的课堂上。虽然,因为性格不同,我的课堂增加了些许幽默,但语文课堂底子上的严肃和庄重依旧保留了下来。我遗憾的是没有教过小学,没有教过孩子们认字,但是上每一年级的第一堂课,我都会端端正正地写下“语文”这两个世界上最优美的汉字,用一节课的时间来和学生交流我对语文的理解,与学生一起梳理我们对语文的感情。
以汉字为桥梁,通向古今中外。语文课本上选取的那些情节曲折的故事,像一场场甘霖,浇灌在我们干涸的心田上,带给我们山野一般的起伏、河流一般的多义和丰富,带给我们生命的新奇和能量。生命需要故事。语文是故事的载体。莫言在获得诺贝尔奖的现场演讲中,演讲的题目就是《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而所有经过遴选放进《语文》课本里的故事,都是向“善”的,它通过故事的方式,表达着人性中的“善”意。
所以,语文是一粒良善的种子,它在我的心里生发,让我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拥抱阳光般的温暖。
三
十三四岁的年纪,我进入中学,已经不满足于那些“新奇”的故事了。生命的需要与生命的成长相伴随。青少年时代,身体逐渐发育,骨骼慢慢坚硬,荷尔蒙勃发,人生开始变得多愁善感,生命开始懂得忧郁、孤独,开始“为赋新词强说愁”。
文者,纹饰也。生命开始需要炫彩,需要花纹雕饰,需要招摇。女生留起了长长的辫子,男生悄悄在自己身上画上纹身。看到的河流不再是河流,而是“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看到的杨柳不再是杨柳,而是“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看到的春天也不再是春天,而是“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
有人说,当一个少女开始喜欢散文,那么,就意味着她开始怀春。这句话不无道理。小学时候,我们不喜欢读散文,我们需要故事。到了中学时代,我们开始慢慢喜欢散文,喜欢诗词。因为散文和诗词,是“美”的化身,是情绪的载体。人生不仅仅需要故事,还需要“停下来,慢慢欣赏”。咀嚼,品鉴,一个字一个字地揣摩,一个词一个词地欣赏,那些古人浓烈的情绪,那些游子漫漶的乡情,那些思妇含蓄而炽烈的爱,都渐渐显露出来。
一岁年纪一岁心。如果说,小学时候,语文是通过“让我认知”而带给我欣喜和诱惑的话,中学时代的我,则慢慢对汉语本身表现出了特别的热爱和关注。我喜欢那些抒情的散文,喜欢那些优美的词章,喜欢那些略带忧伤的古诗,喜欢那些绮丽的长短句。一种语言,此时方真正以其自身的魅力,以其精雕细刻的艺术魅力,以其传情达意的准确和柔美,征服了我。《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的柳三变的凄迷人生,“阑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的辛弃疾,“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李清照,“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这些或潦倒,或落魄的文人,携带着他们一生浸淫的“缠绵悱恻”扑面袭来,让我一时沉醉。于是,“熟读唐诗三百首”之后,我开始“偷偷”尝试着“写文章”。我满怀惶恐地调度着这些汉字,排列组合,雕章琢句,这种码字的游戏让我既惊奇又惊喜,每每欲罢不能。
这时,我有幸遇到一位“特别”的语文老师张继国老师。张老师中等身材,面瘦,眼小,留有髭须,戴红色的变色近视眼镜,在初秋里穿暗灰色风衣。右手食指微黄,明显有烟熏的痕迹。那时候我对他有些肃然起敬甚而畏惧,因为我很少在生活中见到穿风衣的男人。
后来了解到他行为独特,授课也独特,平时独来独往,不打球,不看电视,但是酗酒和抽烟,爱读诗,爱一人到野外散步,上课时腋下夹一教案,又多不用,只管娓娓道来。他喜欢朗读,讲课的声调倒也有些抑扬的韵致,但是明显读音不准,用的不是方言也绝不是普通话。有一次学习朱自清的名作《背影》,他竟然讲得自己潸然泪下,在讲台上痛哭流涕,让我们这些乳臭未干的孩童唏嘘嗟叹良久。此外,在写作上,他深深地影响了我——高一一年里所做的十几次作文中,自第一篇《喝风》开始,他一次不落地把我的作文当作范文——这极度地满足了我的虚荣心,也让我在不大的梁山四中校园里声名鹊起,并且让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读书和写作,直到现在乃至未来。如今,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记忆中的梁山四中,那学者气质的老师和热血赋诗的同学,以及那一段青葱懵懂岁月,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仔细思考一下,我想,对语文的热爱,进而变成对词章、文学的热爱,就是因为,语文是一种“美”的载体,我们在青少年时代所努力追求的,无非是一种“美”的东西。
所以,语文,那个时候在我心里种下了一粒“美”的种子,让我一生去追求美。

四
高考结束之后,填报志愿。我在所填报的六所学校里,都只填报了同一个专业——中文。
学习语文十几年,语文的情愫已经深入到血液里。大学时光,就让我专心与它相伴吧。在曲阜孔庙脚下,走进校园,我先向老夫子拜了三拜,他背后高大的图书馆巍峨挺立,看得我不禁心花怒放。我一头扎进书籍的海洋里,潜泳,如饥似渴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风尘仆仆向我走来,我在深夜里与他们对话;泛黄书页里的汉字跳跃下来,我在梦乡里与它们交流。
阅读之后,思考之后,生命需要一个出口进行表达。于是,我不断地写,不断地写。二十岁开始,写了一大批散文发表在《散文》《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刊物上,同时写出了一批小说,《狼种》《西北望蒲苇》……我应该感谢两条河流,一条是距我家一公里之遥的黄河,一条是绕村而过的运河。它们是我生活中的“语文”,在我心里种下了种子。这两条河流给我灵性,那千百年来日夜不息流淌的河水给我昭示,让我思考生命和生活。亲近泥土和河流,这也让我脚踏实地,进一步形成现实主义的小说创作追求。我努力在文字中关注人生命运,塑造丰富多彩的生命形象,这也是我写作的追求和内容。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教育的一线工作,对教育的思考和感悟较多,尤其是对转型时期的种种教育现象感受很深,身边的同事老师也各有特点,体现着小知识分子的种种优势与弱点,自己身上也存在着教育工作者的共性,于是我尝试着写了《老师,老师》《高考日》《尖子生》《叛徒》等几部中篇,陆续发表在《中国作家》《芳草》《清明》等刊物上。
写作像毒素,又像营养素,已经渗透到我们的血液和骨子里面。我觉得对一个作家来说,文学创作是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是和肉体生命、精神灵魂不可分割的,生命不息,就要写作不止,让它内化为生命的一种需要。无论是口头的表达倾诉,还是笔墨文章,你对生命的理解,都应该被记录。这是生命的尊严,也是生命的高贵之处。这是个体的,也是群体的。
因为,文学应该成为一种群体的担当,在自我的悲喜哀乐的小情愫之外,开阔出去,去承担一个群体甚至一个物种的传播责任。用作品塑造人物,更要在作品内外塑造出作家自己的“人格”,并用这种人格去引领他人,成为人类精神宝库中最炫美不朽的财富。事实证明,每一本文学巨著背后,都站着一个伟大的“人格”,人格的力量展现在作品背后,那才是作品的灵魂。托尔斯泰、雨果、巴尔扎克、鲁迅……这些大师,他们写出了经典,经典成就了他们,他们自身也成为最经典的文学形象,影响后世。
语文,在我的心里种下了一粒追求“真”的种子。我通过文字,试图拨开层层迷雾,接近世界的本质。它是我思想集中的凝结,灵魂自由的出口,也是我生命不息中对“真理”的不懈追求。
五
语文,就是一粒种子,它生根,发芽,葳蕤成长,为我的生命撑起一片茂密的绿荫。
许多年之后,我有两种与“语文”密不可分的工作——站上讲台上,开始一种叫作“语文”的文化传承事业;走下讲台,开始一种“语文”延伸了的生命“写作”。
在这“讲”与“写”的乐此不疲的工作中,我深深体验到这种事业的伟大与高贵。我珍惜这粒种子,我要把它种在千万学子的心田,种在万千读者的心田,我期盼它生根、发芽,长成参天大树,甚至长成一片繁茂的森林。

乔洪涛:1980年生,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在《中国作家》《青年文学》《文学港》《山东文学》《长城》《作品》《百花洲》《散文》《散文选刊》等文学期刊发表作品100余万字,有作品被转载和收录到多种选本。山东省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曾荣获首届“齐鲁文化之星”、首届沂蒙文艺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