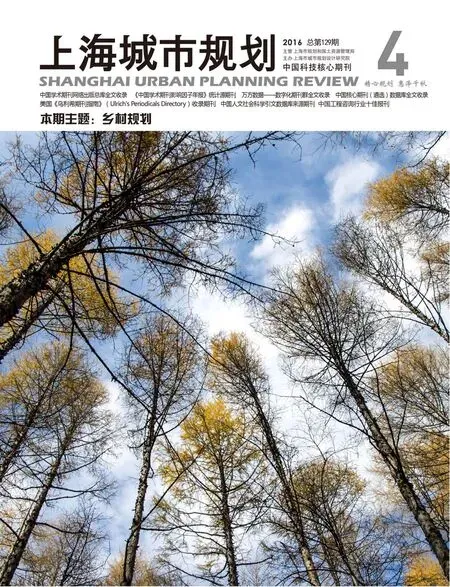吉隆坡规划: 新城区及其影响
Ross King【澳大利亚】著,纪 雁 沙永杰 译
吉隆坡规划: 新城区及其影响
Ross King【澳大利亚】著,纪雁 沙永杰 译
吉隆坡三十余年推行的多媒体超级走廊城市扩张发展战略将历史悠久的首都吉隆坡和行政新都布城、新高科技产业中心赛城以及新的吉隆坡国际机场连接起来。对这一规划的实施和影响进一步剖析,阐明这一重大举措加剧了马来西亚各种族之间的分隔,也导致政府和市民疏远,使吉隆坡老城不仅由占少数的华族和印度族裔社区主导,也成为持不同政见群体的聚集地。
吉隆坡 | 多媒体超级走廊 | 分隔 | 政府 | 公民社会
Ross King[澳大利亚]
墨尔本大学建筑和规划系教授
纪雁
Vangel Planning & Design设计总监
沙永杰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0 引言
吉隆坡始建于1857年。当时的马来穆斯林雪兰莪(Selangor)苏丹国锡矿丰富,其巴生区(Klang District)的马来首领征派华工开发巴生河(Klang River)流域的锡矿。矿工们在巴生河和鹅麦河(Gombak River)沿线的矿场工作,并在两河交汇的河口建立了驻地,命名为吉隆坡,意为泥泞的河口。矿工分帮结派,福建和广东两派经常为争夺锡矿开采和销售的控制权而爆发冲突。随着英国对马来亚的殖民统治,雪兰莪成为英属马来亚的一个州,矿场的混乱状况迫使英国政府指派华人来协助管理吉隆坡。1868年,华人叶亚来(Yap Ah Loy)成为吉隆坡的第3任甲必丹①甲必丹是荷兰语kapitein的音译,即“首领”,这是葡萄牙及荷兰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殖民地推行的侨领制度——任命前来经商、谋生或定居的华侨领袖为侨民首领,协助殖民政府处理侨民事务。,他着手平息不同派别之间的争端,并发展城镇。1880年,英国将雪兰莪州的首府从巴生迁至更具战略性中心位置的吉隆坡。
早期吉隆坡屡遭疾病、火灾、尤其是每年洪水的困扰。1881年的火灾和水灾几乎将由木头和茅草搭建的老城区破坏殆尽,英国政府决定用砖为建筑材料进行城市重建。华人利用这一城市重建契机在城郊开设了砖厂。1896年吉隆坡成为马来联邦②马来联邦(Federated Malay States)是1895至1946年英国在马来半岛的殖民政体之一,由4个接受英国保护的马来王朝组成,包括雪兰莪、森美兰、霹雳和彭亨,1895年成立,首府为吉隆坡。当时华人称之为四州府。的首府,由英国殖民政府管理。不同族裔的社区聚居在城市不同区域——马来人聚居在北部,印度人则在砖厂周边区域,华人在市区并主导城市经济。由于种族和宗教等多方面差异,各族裔之间的团结和融合非常困难(图1,图2)。
二战期间,吉隆坡于1942年1月被日军占领,1945年8月重归英国统治。1957年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a)宣告独立③1946至1948年,英国殖民政府试图把11州合并为马来亚联邦(Malayan Union)——一个在英国统领下的英国皇家殖民地,但遭到马来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马来亚联邦于1948年解散,重新组成马来亚联合邦(Federation of Malay),并恢复马来统治者的地位。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宣告独立。,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吉隆坡成为国家首都。1969年5月13日吉隆坡爆发大规模种族骚乱,血腥冲突不仅给城市造成了巨大破坏,也对马来西亚之后的发展产生深刻影响。“5·13事件”可以看作是马来西亚历史上的重要事件,各族裔之间在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差异加剧使得长期积压的种族分歧终于爆发,也进一步加深了华族和马来族之间的鸿沟。此后,马来西亚的政治基本是种族政治,在此基础上,吉隆坡规划也基本以种族为中心。

图1 1890年代的吉隆坡地图(显示了高密度的华人聚居区,松散的英国人聚居区以及马来甘榜(村落))
1 吉隆坡规划

图2 殖民时代的吉隆坡代表形象——高等法院(建于1894至1897年,其采用的英属印度建筑风格逐渐发展成所谓的马来穆斯林建筑式样)
1881年吉隆坡灾后城市重建时开始形成一些法规条例,1917年殖民政府曾颁布城镇完善法案,并于1921年建立规划管理部门。但总的来说,早期吉隆坡并无正式的城市规划。英国殖民政府和马来族裔长期以来一直担忧华人取得城市中的主导地位,因此殖民当局1900年在吉隆坡以北预留101 hm2土地作为马来族专属聚居地,即甘榜巴鲁(Kampung Bahru),1913年和1933年再次划拨土地给马来族专用,形成马来保留地。所有马来保留地都受法律保护,意图阻止华人或其他资本在城市中形成经济控制权。这些位于吉隆坡上佳地段的马来保留地本应体现较高密度的城市特征,但至今仍保持非常低密度的状态,如同城郊农村,也可以说是城市里的贫民窟。
1969年种族骚乱后,政府颁布了新经济政策(New Economic Policy),基于这一政策,从1971年至1990年实施的4个“五年经济计划”主要是为扶持经济落后但占据政治霸权的马来人,并为1984年的《吉隆坡结构规划2020草案(Draft Structure Plan KL 2020)》埋下伏笔。从这一时期开始,吉隆坡的规划和发展产生重大改变。
上世纪60年代吉隆坡继续沿巴生河谷西扩,线性地发展了新市镇序列,从八打灵再也(Petaling Jaya)、梳邦再也(Subang Jaya)、莎阿南(Shah Alam),延伸至雪兰莪州旧都巴生。随着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迁移的加速与失控,产生了严重而持续的住房危机,马来聚居区遭到冷落,而华人聚居区则人口密集,经济繁荣。同时,整个城市遭受周期性洪水灾害,交通运输极度混乱。1984年的结构规划曾试图解决这些问题,但显然失败了。
土地利用规划和交通规划之间缺乏协调加剧了吉隆坡老城的拥挤和混乱,不同管理部门和政府项目之间相互脱节,使工作收效甚微。英国殖民当局曾在吉隆坡地区修建了铁路,但马来政府选择建设高速公路作为应对城市扩张和拥堵的手段,忽视公共交通建设,直至20世纪90年代晚期才开始重视公共交通。但新的公共交通系统又是由各自独立并相互竞争的公司建设和运营,没有协调的相互竞争带来进一步的交通混乱(图3)。
马来保留地不可侵犯的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城市拥堵和洪水灾害的严重性。1990年前后,政府决定逐步将联邦政府管理机构迁出吉隆坡,建立一个新都以减轻旧城的负荷。对这一举措的正面解释是:对城市运作进行“调整”需要土地资源做支撑,迁出行政机构另建新都可以腾出政府机构在老城中占用的大量土地;而另一方面的意图是:释放出的原政府机构占用的土地应该给马来人使用,从而削弱华人在城市中心区的土地主导权,通过抑制租金和降低土地价值扶植马来族裔的资本力量。
2 吉隆坡扩张新战略
马哈蒂尔·穆罕默德(Mahathir Mohamad)于1981年7月出任马来西亚总理,并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提出马来西亚通过发展高科技和电子商务实现全面发展,在2020年成为先进国家的战略方针。在此愿景下,吉隆坡的目标是成为下一个硅谷。而吉隆坡的城市规划和发展又不得不面对内外两方面的现实问题:对内,马来人拥有政治霸权但经济落后;对外,东南亚地区日益受到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和文化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马来西亚带着加入全球秩序的渴望,又带着对这个带有新殖民特色的、缺乏个性的、跨国(或者说美国霸权)的新全球秩序的抵抗和挣扎——这是吉隆坡宏大扩张战略的潜在背景。

图3 吉隆坡老城的道路系统示意图
吉隆坡,或者说马来西亚,在地理位置上处于新加坡和曼谷两大繁忙的交通和商业中心之间,地位尴尬。为弥补这一处境的弱势,马来西亚提出了一系列交通和基础设施改善项目:巴生海港扩建;改造和提升南北铁路,使之通过吉隆坡,战略性地南北连接泰国和新加坡;建设经过吉隆坡的南北收费高速路;同时也提出了建设全球航空网络结点的设想。
与新加坡樟宜机场(Changi Airport)和曼谷廊曼机场(Don Muang Airport)相比,吉隆坡梳邦机场(Subang Airport)实力相差悬殊,因此,马来西亚急需一个新的空中门户。尽管梳邦位于自吉隆坡向西通往八打灵再也、莎阿南、巴生和巴生港(Port Klang)这条城市发展走廊的中点位置,地理位置优越,但不具备扩建潜力。新机场选址在雪邦(Sepang),距这条城市发展走廊以南约60 km,在吉隆坡市中心以南约70 km。1991年政府购买10 000 hm2土地,1994年开始进行新机场建设和开发项目,总投资预算约90亿马币(约40亿美元)。显然,新机场选址背离了此前城市顺着山谷,往西朝着巴生海港扩张的逻辑,为了确保吉隆坡及新机场能够成为东南亚新兴的枢纽,城市发展战略转向沿南北高速路和铁路布局,发展形成新的南北向城市发展带,并将这条南北发展带赋予电子经济、电子商务、电子政务的内容和功能定位,期望它成为一个资讯科技和创造的枢纽。因为所有这些城市发展内容都可以囊括在多媒体概念下,这条规划的发展带被称为多媒体超级走廊(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简称MSC)(图4)。

图4 吉隆坡城市扩展规划示意图——原巴生谷发展带和规划的多媒体超级走廊,城市战略转为形式化、高科技和南向发展
3 多媒体超级走廊
该多媒体超级走廊沿袭日本的科学城模式,以筑波(Tsukuba)和京阪奈(Keihanna)为蓝本[1],日本公司,如日本电信电话株式会社(NIPPON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RPORATION,简称NTT)深入参与其规划④1996年与NTT签署的协议中,NTT承诺在此设立一个研发中心,这也是MSC项目提出的背景之一。。相比之下,东西向的巴生谷城市发展走廊却一直依托英国和澳大利亚的规划范例。马来西亚基本没有自主的多媒体供应商,因此,由日本主导或是美国主导下的多媒体超级发展带是否会让马来西亚沦为“网络殖民地”(cyber colony)成为一个潜在问题。
多媒体超级走廊包含两个象征性的“门户”和两个新城。
超级走廊北端连接吉隆坡的门户——曾经作为吉隆坡城市中心历史风貌焦点的雪兰莪赛马会(Selangor Turf Club)马场;以及马来西亚国家石油公司(Petronas)通过1991年国际设计竞赛建设的88层高标志性建筑双子塔。双子塔既是吉隆坡的城市象征,也是超级走廊的门户,寄托着马来西亚对电子经济新时代的发展期望。
超级走廊南端是吉隆坡国际机场,是城市新经济发展带连接国际的门户。这个新机场由日本著名建筑师黑川纪章设计,被称为生态传媒(eco-media)理念和高科技手法相结合的产物[2]。
关于多媒体超级走廊功能的最初设想是打造一个全球创意创新的网络,并通过这个超级走廊上两个新城的建设来发展带动——赛博加亚新城(Cyberjaya,简称赛城)要成为电子信息技术新城[1];而马来西亚政府迁出吉隆坡后建设的新行政中心布特拉加亚(Putrajaya,简称布城)将全面采用“电子政务”(electronic government)工作模式,以创造电子信息技术行业的发展机遇。赛城规划人口24万,其中约9万居住在所谓的旗舰区,即新城的中央商务区及周边地带。负责新城开发和运营的公司MDC(政府背景的公司Multimedia Development Corporation,简称MDC)计划至2020年能有约500家IT和多媒体公司落户赛城[2],但很显然,新城开发关注的焦点停留在硬件建设上,而非新城需要的功能和内容。
作为行政中心的布城规划为一个有25万人口的园林城市⑤人口计划在后来更改为300 000人,再变为335 000人。,并计划在电子政务上大胆实验,设计为无纸化办公环境。马来西亚总理府也于1998年迁入布城[2]。布城的规划建设由总理府下属的经济规划办公室(Economic Planning Unit)主持,综合了国内竞赛的创意,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时开始建设,2005年建成。布城的功能是承载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即总理府、各部委和法院等,议会和皇宫不在其中,这是刻意强调行政和立法分开,也不突出国王作为国家的象征。
4 吉隆坡规划的实施情况
多媒体超级走廊计划的实施给马来西亚带来了直接的积极影响。2000年代早期马来西亚与基建相关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仅布城建设就贡献了近48%,约占全部国内生产总值的3%,并在金融危机期间为马来西亚经济稳定提供了保障。尽管目前布城建设成果明显,但持续发展的后续预算不足,今后进一步实施的力度很有限。布城的土地主要被政府机构和公务员住宅占据,私营企业仍主要位于吉隆坡老城,这也是今后布城发展动力缺乏的主要原因。
相比之下,作为IT科技产业平台的赛城发展很缓慢,缺乏经济动力。赛城在2007年号称已入住人口2.9万,但实际人口数量在晚上大幅下降,只剩约1万人,距离规划人口24万相去甚远。在赛城工作的人口大多居住在周边既有城镇区域,依靠通勤来这个比科技园稍大的新城。乏味的建筑,没有遮荫的大街、汽车为主的交通以及大片空置土地是赛城的主要城市面貌。
赛城也引进了一些大公司,如汇丰银行、爱立信、富士通、DHL、渣打银行和花旗银行等,这些大公司把数据处理和呼叫中心设在赛城。还有一些电子制造业厂家迁入,一些马来西亚的大学也在赛城设立校区,如多媒体大学(Multimedia University,前身为电讯大学Telecommunications Training college)、国家能源大学(Universiti Tenaga Nasional)和马来西亚博特拉大学(Universiti Putra Malaysia)等。政府和这些大学都期待能效仿斯坦福大学孵化硅谷的模式,用大学的科研力量对多媒体超级走廊的开发产生促进作用,并在赛城打造一个互联的、充满创造力和制造力的社区[2]。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赛城真正达到了这种期待的辉煌,相反,赛城的发展在对外和对内两方面都有难以超越的对手。对外,新加坡一直是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对全球领先的科技企业和科技人才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对内,赛城要面对更具活力和吸引力的吉隆坡老城的竞争。因此,最可能的结果是赛城演变为一个巨大的数据处理中心,而非真正的科技新城。
吉隆坡国际机场和其连接吉隆坡的公路与铁路建设得很好,但未能削弱新加坡和曼谷作为全球性枢纽的地位,巴生港也面临同样的境地。政府原本希望通过将行政功能搬迁集中到布城来解决吉隆坡老城的拥堵问题,但2011年对吉隆坡街道和交通情况的调查发现,老城交通拥堵以及其它与街道生活相关的问题并没有改善的迹象。政府将投资和关注点从吉隆坡老城转移到新规划的多媒体超级走廊发展带,实际上也是对老城各种亟待解决的问题无从下手的一种宏观对策。尽管如此,毫无疑问,今天的吉隆坡(老城)仍然是马来西亚经济、文化和服务业中心。
5 吉隆坡规划相关的几个重要问题
如果从道路交通、土地利用、城市公共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等常规规划要素分析,吉隆坡的多媒体超级走廊规划是合理的。但在这些物质性因素之外,对吉隆坡发展有更重要影响的问题,如: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营销、贫富差距、城镇就业不足、内乱、城市贫民窟、种族分隔和国内移民、内在殖民化、代表不同宇宙观和价值观的符号与文化资本等,更值得研究和思考。
5.1城市营销
吉隆坡城市规划一直以城市形象为中心[2]。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历届马来西亚总理都采用的做法,通过一个比一个更壮观的巨型工程体现政绩,也以此捍卫伊斯兰政权。尤其在马哈蒂尔时代,虽然城市建筑反映了英属印度建筑的传承,但越来越依附于伊斯兰意向和主题的趋势也十分明显,尤其体现在公共机构和大型企业的建筑[2-3]。但随着政府换届,这类大型项目又往往面临被忽视、改变甚至拆除的命运。多媒体超级走廊是马哈蒂尔时代最宏伟的项目,随着2003年马哈蒂尔卸任,今天也同样面临可能遭受忽视的困境。马来西亚历届总理之间的相互对立影响到执政党和国家的稳定,也对吉隆坡规划和实施带来很大影响。
如果说双子塔和吉隆坡国际机场都体现了伊斯兰和马来文化,那么布城的建设则追求理想的伊斯兰城市,相比吉隆坡老城,布城充满了形式和秩序。无论方式是否恰当,这种做法确实强化了吉隆坡的形象特点,起到了城市营销作用(图5-图7)。尽管如此,布城和赛城的综合情况依然堪忧,而吉隆坡老城和巴生谷城镇带也同样问题重重。如前所述,吉隆坡城市问题的核心是种族分隔,占据政治霸权的马来族和占据经济优势的华族,以及作为少数派的印度人之间的争端往往非常暴力和激烈,这一事实一直是吉隆坡城市规划和规划意图的潜台词。多媒体超级走廊和近期的吉隆坡规划可以看作是马来西亚政府通过在布城建立马来政权中心以脱离被华族经济主导的吉隆坡,从这个意图的角度看,规划是合理有效的。然而这样做的后果是——布城被马来穆斯林完全占有,而作为商业金融中心的吉隆坡则更进一步被华族占据。吉隆坡成为充满市民生活的城市,而布城则由警方控制出入口来实行安保,这就让人质疑规划的后果是否进一步加深了种族鸿沟。


图5 吉隆坡城市营销的新形象
马来西亚种族政治的另一方面也影响到城市规划和实施。马来西亚的印度族群主要是农民,聚居在逐步形成的传统农业区域。农业工业化的推广使这批人的权利逐渐被忽视和剥夺。随着多媒体超级走廊的建设征地和清理土地过程,他们面临被野蛮搬迁至偏远地区的命运[4]。在吉隆坡城内,贫困的印度族裔也面临同样境况,为配合吉隆坡机场高铁以及和机场相关的大型项目[5],老城原砖厂附近的印度社区正遭受大规模驱逐。
5.2城市里的贫民窟
与吉隆坡老城内的印度社区被驱逐相反,多媒体超级走廊规划范围内却充斥着马来甘榜,即马来人聚居村落或非正规居住区⑥Kahn J S. Other Malays: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the modern Malay world [M].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6: 58,文中认为对马来甘榜之所以产生的理解要从19世纪末至殖民时代后期的移民和商业的综合角度来看待。。这些原先处于城郊位置的甘榜随着马来半岛城市化进程被不断扩张的城镇包围,变成城市里的村落。英国殖民时期的法律保护这些马来甘榜永久的特殊使用权,这一法律自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一直沿用至今[2],成为城市的一个传统。

图7 布城的伊斯兰建筑主题

图6 布城二期规划总图
这些破败、低密度但受法律保护的甘榜对于吉隆坡拥挤和缺乏可开发土地的状况所具有的影响远胜于华族占有其它土地的影响。但从政治角度分析,对于由马来人垄断和主导的政权来说,指责华族比批评马来甘榜更来的容易,这也正是多媒体超级走廊开发计划形成的背景。尽管想了很多办法试图解决城市土地利用的窘境,但如果不触碰马来甘榜不合理用地的问题,吉隆坡规划很难有实质性改变。更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城市规划窘境的另一面是甘榜内低收入的马来居民大多又反对马来精英组成的政府,甘榜已成为各种反对力量的源头(图8)。

图8 受法律保护的低密度的马来甘榜(城市中心的贫民窟)
5.3公民社会的变化
在杨生关编著的书[6]中描述了包括马来和印度等吉隆坡弱势和边缘群体的状况,是过去20年边缘群体倍增的证据和写照。这种境况一方面可能与社会媒体作用越来越大有关,媒体愈来愈成为市民抗议和披露真相的一种手段;另一方面也表明市民与政府日益增强的抗拒状态,而这也是政府决定放弃吉隆坡另建新都的一个因素。很难说是因为政府主动疏远吉隆坡,或是新规划举措加剧了这种分隔和对立状态,但可以肯定,吉隆坡扩展规划战略与政府和人民在物理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裂痕有密切关系,并将有深远影响。?
5.4交通状况混乱
英国殖民当局早在1886年就修建了东西向的巴生谷铁路运输线,这条铁路至今仍提供公共交通服务。1990年代马哈蒂尔政府委托不同财团修建了另外两条铁路系统用于服务城市边缘区域;其后又修建了覆盖内城的高架单轨系统;再之后修建了吉隆坡机场快铁连接吉隆坡市中心、赛城、布城和新的国际机场。吉隆坡这5个公交系统各自使用不同技术,相互没有衔接,缺乏换乘点,更没有共同的售票系统。这也是吉隆坡规划失败的一个明显例证。负责交通的部门、战略和规划管理部门以及公路和铁路等相关机构之间没有协调,反而为各自利益进行不合理竞争。
5.5硬件与内容
吉隆坡规划发展的另一个教训是专注于城市硬件建设而忽略其承载的内容,而城市竞争最终将由城市内容和功能起决定作用。吉隆坡规划扩展区域在硬件方面的意图很强烈,也有大手笔,但内容方面相去甚远。吉隆坡老城里,在一些缺乏规划管理的区域,电影电视制作等艺术类的一些新城市功能反而自发成长,但由于担忧反政府思想的滋生和蔓延,政府对这类新功能采取了抑制而非鼓励的举措。就城市内容角度而言,将吉隆坡建成全球城市的愿景深受质疑。
吉隆坡扩展规划中的布城和赛城原计划建成新的创新创业热土,但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吸引和聚集创意人群,是一个早已国际化、拥有丰富社会和文化资源的老城区,还是新的、孤立、枯燥无味的、规划的乌托邦?全球范围内的经验证明是前者⑦关于创意中心可借鉴首尔经验:城市通过积极规划和发展来催化新的创意和创新,就不同功能建设了松岛高科技新城(New Songdo)、坡州书城(Paju Book City)、Heyri文化艺术村(Heyri Art Village)等,而作为创意中心的、位于老城的东大门(Dongdaemun)体现了硬件和内容并重,甚至超过江南(Gangnam)占据前沿地位。前卫的艺术文化依然集中在弘大(Hongdae)及相似的传统区域,而不是偏远的新区。。
References
[1]Castells M,Hall P. Techno poles of the world: the making of 21st Century industrial complexes [M]. London: Routledge,1994.
[2]King R J. Kuala Lumpur and Putrajaya: negotiating urbanspace in Malaysia [M]. Singapore: NUS Press, 2008.
[3]Lai C K. Building Merdeka: independence architecture in Kuala Lumpur, 1957-1966 [M]. Kuala Lumpur: Petronas, 2007.
[4]Bunnell T“. Multimedia utopia?A geographical critique of high-tech development in Malaysia’s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J]. A Radical Journal of Geography, 2002, 34(2): 265-95.
[5]Baxstrom R. Transforming brickfields: development and governance in a Malaysian City [M]. Singapore: NUS Press, 2010.
[6]Yeoh S G. The other Kuala Lumpur: living in the shadows of a globalizingsoutheast Asian City [M]. Abingdon: Routledge, 2014.
[7]Bunnell T. Malaysia, modernity and the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acritical geography of intelligent landscapes [M]. Abingdon: Routledge Curzon,2004.
[8]Kahn J S. Other Malays: nationalism and cosmopolitanism in the modern Malay world [M].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2006.
[9]King R J. Reading Bangkok [M]. Singapore: NUS Press, 2011.
[10]Wong S F. Walkability and community identity in the city centre of Kuala Lumpur [D]. Melbourne: The Dissertation for Doctor Degree of University of Melbourne, 2011.
Kuala Lumpur Planning: Putrajaya and its Consequences
The over-riding strategy of Kuala Lumpur planning in recent decades has been the development of a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linking the historic federal capital of Kuala Lumpur with (1) a new administrative national capital of Putrajaya, (2) a high-tech industrial center termed Cyberjaya and (3) a new Kuala Lumpur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 effect of this planning has been to heighten the racial divide in Malaysian society, also to isolate the government and its administration from civil society; a ‘second-order’ effect has been effectively to hand the historic city and its institutions to the minority,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Chinese and Indian ethnic communities, also to groups that the government would consider dissident and ‘suspect’.
Kuala Lumpur | Multimedia Super Corridor (MSC) | Separation | Government | Civil society
1673-8985(2016)04-0061-07
TU984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