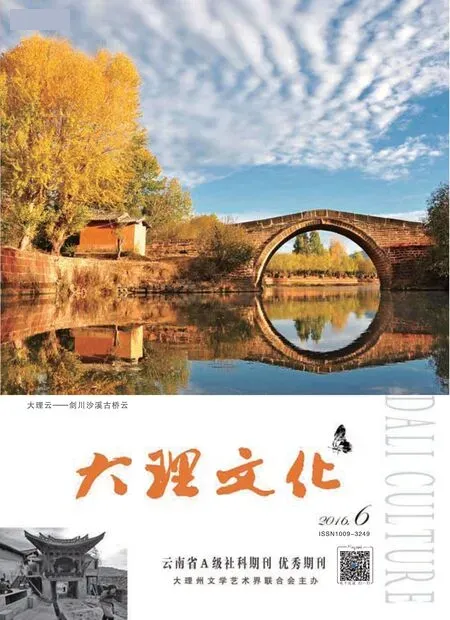沉陷记
●陈苑辉
沉陷记
●陈苑辉
没落的村小
时光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下来,在寂静与失落中等待黄昏慢慢地靠近。碎步行走于那条熟悉的村尾路,我似乎寻觅一缕旧时光的隐秘入口。外出漂泊十几年,斑鱼小学却一直维护着我的精神家园从未疏远过。它是村庄里唯一的学校,我曾在那读过六年小学,每次回故乡我都要去走一走,看一看,一个人静静地追忆年少时学习的情景。
杂草丛生的空地在夕阳瑟缩的脚步挪开之后留下了孤寂的守候。背靠着大山的教学楼放假后便闲置了,空荡荡的,但我似乎听见了隐藏于岁月深处琅琅的读书声,在青山绿树与教学楼之间回荡、悠扬。“斑鱼小学”四个字在大理石上镌刻着,镂空的字饱满、圆润,透出一股静谧之气。凝视着教学楼,仿若凝视此刻缓缓西沉的夕阳,袒露出被时间击败后徒余的没落、衰败或颓丧。举步维艰,还是苟延残喘?我的心房被悲悯与酸楚占据着,双腿像灌了铅似地沉重起来。但我必须继续往前走,去探寻一些未解的谜语。
升旗台上立着一根五米高的旗杆,它直直地指向苍茫天空,身上却爬了锈。围拢着村小的外墙约两米高,裸露出一块块红砖与细小的泥沙,墙面用石灰水写着几个像箩筐一样大的黑体字:“神州行,我看行”。墙下是一条通往小镇的大路,偶尔听见一两辆摩托车“突突突”开过来或开过去,惊起了宿于村落深处的家禽一两声漫不经心的附和,之后又归于一片寂静中,恰如飞舞的尘埃失去动源后缓缓飘落下去回到生命的静态。山与山之间组成一种互补般的交错,山脚处相连,或相隔几米、几十米,一条大路灵巧地绕过山脚,又爬上山腰,隐没。年少时,曾无数次一个人站在村小的操场凝望着这条大路,它那神秘的拐弯充满了某种未知的气息,诱惑我去设想外面的世界、城市的模样,它是不是就像望眼镜的镜片,通过它们便可看清未知的前方?对于一个小学毕业前还未走出过大山的孩子来说,他有的只是无限的向往、期待。
多年以后我在城市森林里左冲右突,失落、迷茫困扰着心房的时候,突然想起那个村小的拐弯,它多像我生命中的一道隐喻。
双脚踩在年少时留下的足迹上,仿佛踩着自己身上的某个暗疾。村小的四周,再也找不到一条关于教育的标语或宣传口号,那些曾经激荡人心、弘扬教育大计的气息似乎已荡然无存了。可是,我仍然清楚地记得教过我的小学老师——外公陈焕友、李奇浩、陈兴华、魏瑞添、李锡元……记忆最深的是读三年级。那时全班的语文成绩都不好,老师倒是非常严厉,未按时背书的学生总会被他留堂。开学初,我也是其中一员。下午放学后,已经背了课文的同学会站在窗外做鬼脸,我们完全静不下心来,断断续续地胡乱背书,眼睛却乜斜着。我们像困在笼里的小鸟,极羡慕外面的自由与乐趣。好不容易背出来了,找老师检查,而老师多半已经冲了凉、吃了饭。踩着依稀的星光回家,路旁有树枝随风摇摆,我的心也跟着摇晃起来。昏黄的灯火撩拨起我的心弦,对家的渴望愈加强烈起来,一丝丝的恐惧也爬上心头。假如双亲知道了我留堂的真实原因,他们会怎么想呢?我的兄弟姐妹又会怎么看呢?那时,我第一次深刻地理解了什么叫“耻辱”,什么叫“难堪”,它像一记强心针,让我猛然清醒过来。之后,我开始发愤背书,终于未再留堂。如今想来,倒是要感谢那位严师,是他,让我的心智快速地成长起来。
前年,最后两间土房推倒后,关于童年的读书记忆再无可以依附的实物了,童年的足迹被填上一层泥土,泥土上又长满了野草,儿时的乐园不见了踪影,我的心仿佛一下子被掏空了。站在荒草凄凄的土地上,我只能依据大概的方位来寻找村小的旧址。后来,野草竟然长进了我的记忆里,如同稻田里生长的稗子,与禾苗分享着沃土的养分、空间。
斑鱼小学,如一棵风雨中飘摇的残树,它的枝蔓,它生命的绿,在现代化进程中受到了一次次摧残与冷落。这几年,并镇,合并村小,母亲告诉我,学生在逐年减少,只剩下十几个了,且只开设了学前班和一年级,学生从二年级开始,必须到邻村去读书。前几年是断级现象,有时候学校只开设一、三、五、六年级,有时只剩下二、四年级。承担小学六年的义务教育的村小已无规模可言,学前班只是个前缀,为不足年龄的孩童特设一年的适应期和过渡期。大部分的学生随着外出谋生的父母读书,经济条件差一点的,也会在县城租个房子,把孩子接过去就近上学。我的侄子和侄女就在小镇公立学校读书,靠的是积分入学,因为手续齐全,学杂费全免了。一空闲下来,母亲和妹妹就开始拾掇外甥女的衣物。是的,她已经读完了学前班,按照正常的进程,一年级的时光已经向她敞开,且是在村小完成的。可是,她不会留在这里,不会留在我们小时候求学的这片贫瘠的土地,城市里的师资和教学质量正在召唤她。母亲又说,前几年的政策本来是要求撤并斑鱼小学的,但是村民不同意,教学楼才不至于荒废掉。
落日下的村小,它又能支撑到什么时候呢?我一遍遍追问自己,可我无法回答,也倍感乏力。这似乎是一个肃杀的季节,肆虐的风把村庄刮得如此肃杀、冷清。
令人丧气的是,在这样一所没落的村小里,老师的物品还不安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老师把摩托车停放于教学楼前竟被人偷走了,而当时他正面向学生上课。事后调查,有个同学目睹了偷车经过,可是当时他心里害怕,没敢说。丢车事件像寒风一样迅速传遍了村庄的角落,成为村民口中的一个笑柄。这个村庄里唯一的老师,家中肯定不宽裕,当失去了唯一的交通工具之后,耳边却传来村民的冷嘲热讽,也许他才体会到一种浸入骨子里的冷。夕阳已经跌落下去,一些晚霞点缀着天空,我的心,却被拧得更紧了。
从没落的村小走出来,望着依然贫穷、落后的村庄,心里满是怅然、失落。恍惚中,我记得有个故事的结尾,那个贪婪的高西木,进去时记得咒语,返回时却已忘记,他坐拥着闪烁的珠光和黄金,却未曾想到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
祠堂,见证一方血脉史
至今缭绕着袅袅烛香的祠堂,在时光的沉淀中叙说着流年的隐喻。
祠堂分为三个部分,上厅、中厅和下厅。上厅供奉着陈氏祠堂的牌位,牌位前是香炉、烛火一类,头顶有一个绳子吊起来的花灯,每年谁家生出第一个男孩,那个男孩就是“灯头”,花灯由他家请人做好,正月十三那天换上去。上灯,是村庄里最热闹的日子,别村同宗的人都会来祭祖,整个祠堂锣鼓喧天。换上新花灯后,一串一串的烟花爆竹在祠堂外集中燃放,浩大的烟雾笼罩着半个村庄,一片片纸屑铺满了地,最厚的地方可达一尺。有一年,学校还未开学,村中年轻鼓手不多,我得以滥竽充数一回。擂着鼓,跟着几个大队从村尾绕到村头,颇有一番喜庆、卖弄、炫耀的派头。最后队伍聚集在祠堂,各村队像比拼似地擂鼓,直擂得震耳欲聋。我的手掌被擂起了几个水泡,一个多星期了还疼,可是觉得特别过瘾——我终于当了一回上灯的参与者,而不是旁观者。祠堂的中厅和下厅墙壁上刻着“捐款芳名”,供查看,以示敬意。厅梁上则雕梁画凤,一幅幅传神的雕艺不知为何时所作,就像在头顶上定格起来的飞翔之物。
走一遍祠堂,昨日的时光仿佛又展现眼前,一幕幕情景记忆犹新。我的童年跟祠堂离得很近,因为它的左边是我家的老房子。逢年过节村民要到祠堂里烧香、祭拜,锣鼓的喧嚣就像注进小孩子身上的鸡血,立刻让小时候的我活力充足、经久不竭,我年年混迹其中。可是,老房子在一九九七年倒塌了,我在一篇散文里写过它的倒塌与无奈。有一年,祠堂着火了,父亲率先带领着村民去灭火。祠堂的厅梁高,熊熊的火舌舔舐着木梁,底下的村民无法扑灭。于是竖了把梯子,父亲爬上去用水桶泼水,下面的人们则组成一条传水链,一桶一桶往上递。那一刻,我觉得站在房顶上的父亲特别高大,多年来一直屹立于我的心头。大火扑灭后,又要选个良辰吉日,父亲爬上房顶去换木板、盖瓦片。祠堂,凝聚着秉性善良的父亲的汗水与心血,站在祠堂的厅堂上,心里涌出一股溢于言表的自豪。
小时候,祠堂也有过不太平的日子。几个大队为获得祠堂庇佑的风水问题发生了争执,差点演变到打架的地步。不知谁出了个馊主意,有个队的村民竟然爬上祠堂去揭瓦、撬瓦板,结果刚修缮一新的祠堂遭到破坏,地上到处是断梁碎瓦。后来,年长者从中周旋、调解,才平息了这场风波。村民又自发捐款,把祠堂再次修缮。我的外祖父是一位老先生,性情和善,从十几岁开始教书,中年以上的村民都曾是他的学生,故颇为村民敬重,每年的祠堂对联都由他执笔。于是,那一年正月十三上灯时,他写了一副这样的对联:百年成之不足,一旦毁之有余。此联意在告诫村民、警示村民,同时也发出一种无奈的感慨。这个善意的提醒,竟起了效果,揭瓦之事再未发生。上了初中以后,上学之前我来到祠堂门口会先看一看、读一读对联,似乎在期盼语言文字的启迪与神佑。而今祠堂的大门依然贴着对联,内容已是喜庆、祈愿之类了。外公于一九九六年去世,新千年我也走上了三尺讲台,这是一种冥冥中的巧合,还是一种跨越时光隧道的传承?我不得而知。
平时,村民也会利用空闲的祠堂做些私事,比如,有个木匠占用此处做过棺材。村中上了六十岁的老人或有人快死时都找他做棺材,当地的村民称其为“长生寿”。于是,当拍拍打打的声音诱惑年少的我进去后,惊诧的双眼看到了一副即将完工的长生寿!其独特的构造几乎令我魂飞魄散。首先,长生寿中间束腰,表面油上黑黑的漆油,非常光亮、肃穆;其次,长生寿两头翘起来,四块木板组成梅花形状,侧边像极了一张人脸,上面似人的额头,突突的,下面如同人的下巴,骨骼鲜明,左右两边则模仿着人耳的造型,开了盖的长生寿张大着口,迟早会抓人进去填补空腹。最令人感到可怕的是,代表人脸的两侧部分色泽红艳,像刚吃完人后嘴角留下了凝固的血。我始终与长生寿保持着一段距离。木匠只顾忙着手中活计,锤锤钉钉,他要把长生寿造得更加结实,以保证质量、效果。年少的我认为,人困在里面是无法挣脱的,也无法灵活转动身躯,生命完全处于禁锢的状态。接着我又想,死去的人被牢牢地锁在里面,没有一点自由,肯定会憋得难受的。

长生寿,于我的童年而言,是一种颇为惧怕、敬畏的东西。
踩在坚实的厅堂上,回忆起“长生寿”,我的心头又突然伤感起来。十几年来,一个个老人从村民的身边远去,一张张熟悉而蜡黄的脸庞从此不再相见,教人如何不怀念?人走了,名字却还在,常被人不经意地提起,徒生一阵唏嘘、感慨。当我再次想起死去的村民,无论此人为老者,还是青年,就像陷进了一个大坑,四周是死一般的寂静。前年春意盎然之时,独居乡下的母亲告诉我沙古表舅英年早逝,接着是……几年来,母亲用低沉的语气陆续告诉我——“你的叔祖母病死了”“立汉叔公也走了”“你权华大舅的老婆被河水淹死了”……大前年,母亲带着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低沉而喑哑的嗓音说,大舅患食道癌去世了。大舅的容颜和九十有三的外婆此刻拨弄着我的心弦。每次返乡,我必去看望外婆。风烛残年中挣扎的她,用一根棍子支撑起走路的摇摆和岁月的残忍。她张口说话,裸露出里面空荡荡的牙床,双唇朝里陷进去,似乎吞噬了人间无数的风霜和雨露。外婆经常一个人发呆,仿佛用目光触摸旧时光微弱的脉搏。
记忆中有太多逝去或依然健在的村民的模样,我无法一一数过来。而且,在我出生之前,祠堂就已经存在了若干年,须翻阅《陈氏族谱》才能大致了解先贤了。也许,建立祠堂的意义便是:不管我们后辈人身处何地,流向何方,在人生的旅途中是飞黄腾达,抑或穷途潦倒,但是,心头总有一份牵挂,连接着神圣的血脉。
外出工作十几年了,我的日子平淡如水,偶尔还会捉襟见肘。每次返回乡下,我便沉陷于一幕幕悠远的往事漩涡里,心房也会莫名地痛疼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