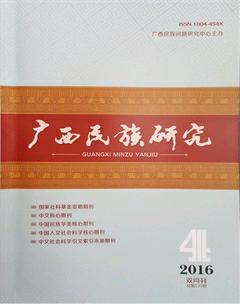五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发展规律及其影响
【摘 要】民族主义浪潮并非自古有之,而是人类群体文明发展到近代民族国家时代的产物。本文在梳理近现代发展史上各大民族主义浪潮发展轨迹的基础上,重点剖析几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发展规律,凸显新近民族主义浪潮对人类的双重影响,试图挖掘五次民族主义浪潮呈现出从惠及社会的正能量到危害社会负能量的规律。
【关键词】民族国家;民族主义;全球主义
【作 者】曹兴,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北京,100088
【中图分类号】C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 454X(2016)04 - 0055 - 010
学者关注最多的是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② 迄今为止,尚无人研究历史上到底经历过几次民族主义浪潮。此外,当前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族体 ③ 冲突,以及“ISIS”(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国际影响等一系列新近国际现象隐藏了多少民族主义元素,能否已经构成了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其在历史上居于第几次民族主义浪潮?孤立地看这些问题是毫无意义的。重要的是当前民族主义浪潮在人类民族主义发展史上占有怎样的地位?它到底还能走多远?它将会对人类社会再产生怎样的深远影响?对人类产生的影响主要是积极性的建设性的,还是消极性的破坏性的?这些问题的研究对于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正是本文关注的重要问题。对于民族主义浪潮,本文采用广义的标准,即凡是能够形成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民族主义运动都可称为民族主义浪潮。
一、旧时代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轨迹
民族主义浪潮并非自古有之,而是人类文明发展到近现代后民族国家兴起的产物,是近代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发展到以民族国家为社会单元的结果,从而替代了以往西方中世纪靠基督教和封建聚结社会的发展状况。
那么,人类发展进入近现代后,到底经历过几次民族主义浪潮?笔者认为,至少有如下四次民族主义浪潮。
(一)西欧民族国家运动是民族主义浪潮的源头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关注最多的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的东欧和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1 ]其实,这是20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但绝不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20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并不是民族主义运动的源头。
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潮源头是17-19世纪伴随着西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国家运动而产生的。西欧特殊的政治格局孕育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也孕育了民族主义政治体系。17世纪开始兴起的启蒙运动为近代欧洲民族主义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其中,法国大革命更是在“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下掀起的反基督教神权、反封建专制主义、争取公民自由和民主权利的伟大革命。在这次革命中,在反封建革命进程中把民主主义与民族主义紧密结合,人民高举全民族利益的旗帜,标志着民族主义思潮在欧洲的兴起。随后英国、德国等地都纷纷展开了资产阶级民族民主运动。19世纪30年代,比利时、波兰、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也都孕育出了本国的民族主义,建立了民族国家。[2 ]
在这场构建民族国家运动中,民族主义成为具有强大的感召力与感染力的意识形态,在欧洲民族国家创建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示范效应。[3 ]177近代民族主义运动,以破除封建神学统治、发展民族经济为目标,孕育了以人权反抗神权,主张解除天主教神学压在人民身上的奴役,解放了捆绑在欧洲各国的沉重枷锁,唤醒了人们民族认同的自觉,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划定了世俗政权的界限。在国际舞台上,奠定了以国家主权至上为政治核心的世界国际关系体系。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构建“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既有其巨大的合理性,同时隐含着天然的巨大缺陷。其合理性在于,用人权反对神权,用资本主义体系代替封建主义体系,用民族国家反对并替代基督教社会单元。其缺陷是把民族与国家混同为一体,分不清民族与国家的界限,甚至提出“一族一国”的理念。① 这种理念成为20世纪掀起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文化动能。在两次世界大战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中充分发挥了民族主义理念的合理性,只是到了冷战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才暴露了民族主义浪潮的发展缺陷。
(二)第一次世界大战掀起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
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运动浪潮率先爆发于东欧和亚洲,而后在世界其他地方迅速蔓延,特别是在十月革命影响下的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促进此次民族主义运动走向高潮。1914 年6月,奥匈帝国王室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塞尔维亚爱国者刺杀,成为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导火索。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民族主义浪潮并没有随战争的结束而降温,反而呈现出一种稳步升温的趋势。民族主义浪潮掀起了一场以反抗旧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斗争,引发了世界各地人民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革命思潮。[4 ]在这次民族主义浪潮中诞生的欧洲国家就有波兰、匈牙利、奥地利、芬兰、南斯拉夫、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等。在拉美地区激起了墨西哥、乌拉圭、秘鲁、巴西及尼加拉瓜等国的民族主义运动。[5 ]268亚洲的中国及周边地区包括印度、朝鲜、越南在内的一些国家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
与前次西欧民族主义浪潮相比,这次民族主义浪潮呈现出如下新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首先,民族主义发生地从西欧走向东欧,再走向亚非拉,民族主义发生地呈现有西欧向外扩大的态势。与前次民族主义运动相比,此次民族主义浪潮已经不局限于欧洲的地理范畴,其外延已经抵达遥远的亚非大陆甚至南美洲。
其次,这一次民族主义浪潮是前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扩大,使民族国家运动从西欧拓展到了东欧。与西欧地区的民族主义相比,东欧亚非拉民族主义并不是“原发的”,而是“衍生的”,是一种防卫性或反应性的民族主义。[6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民族主义浪潮被很多学者称为20世纪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其实,依笔者看来,那不过是前述民族国家运动的扩大和继续。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德奥同盟的失败告终,于是奥匈帝国随之解体。在原来中东欧地区长期被奥匈帝国势力蹂躏的民族掀起民族解放运动,因此诞生一大批民族国家,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匈牙利、南斯拉夫、芬兰、爱沙民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等。
再次,这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已经初具反帝反殖民的色彩,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更是动摇了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基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欧洲列强重新瓜分世界的战争。这场战争的危机促进了无产阶级革命高潮。就是在这种世界背景中,爆发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迫使俄国退出战争。
第四,无产阶级不再仅仅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大旗下的追随者,而逐渐成了各国民族主义运动的中坚力量。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激励了广大无产阶级的觉醒,在十月革命的感召下承担起了反帝反封的历史重任。中国的五四运动、朝鲜的三一运动、土耳其的凯末尔起义无疑都受到了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支持。
第五,不可否认的是,此次民族主义浪潮带有鲜明的大国强权政治的色彩,“一战”后的巴黎和会成为新旧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世界的饕餮盛宴,列强通过瓜分胜利果实平衡各国间关系,牺牲广大殖民地国家人民的利益来满足自身日益膨胀的私欲。因此,“一战”后的20年和平仅仅是短暂的休战,[7 ]224随着欧洲各国实力的消长及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不断推进,世界从“伪和平”向“真动荡”过度,新一轮国际体系的解构与建构开始了。
第六,亚非拉国家民族解放运动是承继西欧民族国家理念的延伸。西欧民族国家运动是民族主义浪潮的源头,而东欧与亚、非、拉各州国家民族解放运动则是源自西欧民族主义源头的拓展和放大。足见,这两次民族主义浪潮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是民族主义反抗帝国压迫的一种社会进步。
如果说发生在西欧的民族国家运动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运动的源头,它燃起的第一片民族主义燎原火海煅烧出来的真正首次民族主义浪潮的话,那么就不难断定发生在东欧亚非拉的民族解放运动不过是延续西欧民族国家理念的下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然而,这种延续远未结束,为此酿造出下一次民族主义浪潮。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掀开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
“一战”民族主义浪潮的战果在不断扩大。民族主义运动在沿着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着。民族国家运动导致了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次世界大战形成了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
“一战”的国际战国派生了“凡尔赛体制”,但仍未实现欧洲及其殖民地的安宁。“凡尔赛体制”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威胁,首先受到东方民族主义思潮在英法海外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挑战;其次受到意大利在欧洲、德意志大日耳曼民族复仇主义的威胁;再次受到东方日本崛起的威胁;最大的威胁是苏联的崛起,促使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围困苏联。欧洲列强和东方日本列强开始新一轮的瓜分世界,为此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如果按照人类近现代史民族主义发展轨迹看,不难断定“二战”掀开的不是“第二次”而是“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这一次民族主义浪潮呈现出如下新特点:
首先,这次民族主义浪潮是亚非拉国家对殖民主义的最后决战,后果是彻底粉碎了帝国主义国家对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殖民侵略,世界殖民体系彻底瓦解,殖民地一词成为历史概念而载入史册,[8 ]从而确立了民族独立、完整和自由的世界普世价值和历史发展潮流。世界范围的反殖民斗争将民族主义的精神传递到世界各国人民之间,自此西方列强再也无法在广大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开展殖民活动,也无法再阻挡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
其次,此次民族主义浪潮掀起了民族国家独立的高潮,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超过120个独立民族国家的可喜成就。“1944 ~ 1968 年, 亚洲和非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实现独立的国家达63个之多,其中 40 年代12个(不含中国),50年代11个,60年代40个。” [1 ]非洲的大部分国家几乎都是在此次民族主义浪潮中取得独立的,其中被称作“非洲独立年”的1960年就有多达17个国家宣布独立。亚洲的民族主义也显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建立了一系列新的国家,包括南亚的印度和巴基斯坦西亚众多阿拉伯国家,东南亚的柬埔寨、老挝和越南。仅在东亚东南亚地区诞生的新民族国家就达15个之多。而在中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运动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实现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树立了民族运动的伟大丰碑。
再次,此次民族主义浪潮也带有强烈的大民族主义的色彩,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在世界范围内飞扬跋扈,以意识形态为外衣向世界各国输出本国的外交和民族主义理念。这种带有强烈“新殖民色彩”的普世民族主义将一国的民族主义价值观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甚至不惜以武力介入的方式来变更其他国家的政权和制度,以此来实现两大国称霸世界的野心。不难断定,苏联既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大国沙文主义帝国。作为社会主义,苏联在推动和掀起组建社会主义国家运动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国际性作用。但是,其大国沙文主义帝国的霸权压制,为后来即冷战时代再次爆发民族主义浪潮埋藏了祸根。
第四,为了对抗美苏的称霸行径,世界上众多国家选择走上了联合的道路,民族国家不再选择“单打独斗”。[4 ]地区民族主义成为此次民族主义中的新表现,欧共体的成立、万隆会议的召开、77国集团的发展壮大都印证了地区民族主义的兴起。
第五,此次民族主义浪潮相比于之前的民族主义浪潮已经呈现出一种相对复杂的特点,民族主义的形式在不断扩展,范围在不断扩大,影响程度也在不断加深。本次民族主义浪潮就是强权国家的国族主义与弱小国家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民族运动间的博弈。
最后,“二战”的社会后果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摧毁了旧日的帝国殖民地体系和“凡尔赛体制”,建立了“雅尔塔体制”。“二战”后民族主义浪潮获得的最大社会后果就是一方面摧毁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殖民地体系。“正如欧洲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中迅速地获得其大部分殖民地那样,欧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同样短的时期内又失去了其大部分殖民地。”[9 ]812另一方面,导致几十个民族国家的诞生。“无论其类型如何,建立独立国家、实现民族解放的目标是其共同选择,其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方向是一致的。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民族主义浪潮的本质特点。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政治格局最显著的影响是几乎全面地摧毁了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1 ]“二战”后建立了许多社会主义民族国家,尽管“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纲领虽然五花八门,但是民族主义的要求却是一致的”[1 ]。随着美苏冷战格局的最终确立,世界各国,尤其是刚刚取得独立的亚非拉国家民族主义思潮涌动,在根除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中掀起了再一次民族主义运动浪潮。这次浪潮在二战后兴起,发展到20世纪60-80年代达到高潮。“二战”第二个社会后果就是确立了“雅尔塔体制”。1945年2月4日,美苏英三国巨头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在克里米亚举行雅尔塔会议,确立了“二战”后的国际势力体系。“这是战争结束前夕同盟国三巨头勾画欧洲重组蓝图和划分世界势力范围的会议。”[1 ]总之,“二战”后依然是帝国体制。帝国体制对各民族的压制,必然潜藏了再一次民族主义浪潮。于是迎来了“冷战”民族主义浪潮的到来。
(四)冷战掀起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
无论是“凡尔赛体制”,还是“雅尔塔体制”,其本质上都是帝国体制,都是民族主义浪潮攻克的堡垒。
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东欧剧变和两极格局的瓦解,世界范围内掀起了新的民族主义浪潮,学界称之为20世纪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实际上是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令人疑惑的是,冷战结束前后出现的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为什么会发端于苏联和东欧地区?冷战掀起的民族主义解体国家的力量为什么未能席卷或者覆盖中国,或者说为什么西方和平演变梦想在中国得以失败呢?道理很简单,民族主义是对帝国主义最好的分解器。苏东地区属于苏联帝国主义压制体制,中国的独立发展不会蒙受苏东解体的命运。还有很多其他原因,对此后文再作分析。
第三次民族主义改变了整个东欧地区的政治格局,苏联一分为十五,南斯拉夫一分为五,捷克斯洛伐克一分为二,在中亚和东欧涌现出了20多个新的民族国家。随后,巴尔干、南亚、西亚和东南亚出现的以民族分离主义为标志的民族运动此起彼伏,还诱发了诸如科索沃战争、车臣战争、阿富汗战争等地区的热战。
此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最大特点是民族分离主义达到一个极致。与以往民族主义浪潮中所表现的民族主义不同的是,此次民族分离主义大多是一种渴望“平等”的分离,而非反对殖民统治而“独立”的要求。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所引发的民族独立浪潮并非反帝反殖民运动,大多数没有发生激烈的军事对抗,多数也没有发生流血事件。实际上是在原有的民族基础之上通过谈判协商的方式而进行的分解过程。这种民族分离主义符合了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民族自决原则,也顺应了各民族人民对于取得独立自主的国际地位的意愿,是对现存国际规则和国际法的一种肯定。
人类不同时代的民族主义问题往往会重叠起来。一方面,此次新兴的民族主义浪潮的重心是东欧地区。另一方面,旧时代遗留下的民族主义问题,依然没能避开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影响,于是英国的爱尔兰人、苏格兰人要求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西班牙的巴斯克人与加泰罗尼亚人也在高举“民族自决”的旗帜下追求民族独立,加拿大魁北克人全民公决希望能脱离加拿大自治。但是,这两类民族主义问题不能同日而语。一个属于旧时代,一个属于新时代。
二、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浪潮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冷战民族主义逐渐退潮,在世界范围内直接表现为民族主义运动进入低谷期。但民族主义思潮并未偃旗息鼓,而是变换为另一种形态表现出来,即宗教民族主义。宗教民族主义是当今世界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国际现象。
有的学者初步认识到宗教民族主义的特征。高永久提出,所谓宗教民族主义是指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打上了浓厚的宗教色彩,或以宗教作为外衣来加以掩饰,或直接表现为宗教之间以及宗教内部不同派别之间的摩擦与矛盾。[10 ]10本文作者认为,所谓宗教民族主义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民族主义,表面上是宗教主义,实际上是民族主义,确切说是以宗教为表现形态偷运民族主义的一种文化理想、社会运动、政治纲领。宗教民族主义既是一种文化理想,又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同时还是一种社会运动和实践。宗教民族主义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主要是负能量的,有的把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集为一身,如“ISIS”极端组织;有的是不同宗教冲突,如“9·11”事件引发的全球性宗教冲突。
宗教民族主义带给现代人类社会的是正能量,还是负能量?恐怕不能简而论之。一方面,宗教以其特殊的感染力与感召力,在社会活动中宣传积极向上的思想,无疑会使信仰者做出有益于人民的举动。积极的宗教民族主义正是实现了宗教主义与民族主义正能量的合流,使宗教成为促进民族主义发展的助推器,达到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完美契合。世界上不乏以某一种宗教作为国教或国内大部分民众信仰某一种宗教的国家,例如老挝、印度等。这些国家往往实现了宗教主义与民族主义相辅相成,缓解了不同民族间的矛盾,也增强了国家与社会的稳定。然而,这种有益于社会的积极性的宗教民族主义并没有参与第五次民族主义浪潮。
另一方面,宗教民族主义在新世纪诱发着政治分裂、民族仇恨等社会矛盾,掀起宗教民族主义浪潮,主要包括出自伊斯兰一方挑起的“9·11”事件,出自基督教阵营的后“9·11”事件掀起的诸如推翻阿富汗塔利班、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以及威胁叙利亚政权和伊朗政权等,这些大事件成为21世纪宗教民族主义浪潮的主流。其中,隐隐约约显现出一条文明冲突的战线,那就是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形成的宗教冲突和民族冲突(后简称为“基穆冲突”)。“基穆冲突”看上去是一种宗教冲突,实际上也是民族冲突,只不过是一种特殊形态的民族冲突,确切地说是族体冲突,主要是阿拉伯人与美国人、欧洲人的族体冲突。
2001年9月11日美国世贸大厦遭到恐怖袭击轰然倒塌,世界各国都蔓延着恐惧的气息,美国在经济和政治的安全感上受到重挫。“9·11”事件后,拉开了新时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序幕,表现出与以往民族主义浪潮的不同特点。宗教民族主义是“9·11”以来民族主义思潮复苏的最主要表现。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与宗教元素形成合力,对国际世界产生巨大影响。
自“9·11”事件后,激化了基督教世界与穆斯林世界的民族宗教仇恨和冲突。美国国际政治学者福山曾评论道:“‘9·11恐怖袭击使我们看清了暴力蔓延的方式: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相结合的可能性突然意味着,原来发生在地球的遥远、混乱国度的事件与美国及其他赋予强大的国家息息相关。”[11 ]91恐怖袭击后对伊斯兰世界的敌视情绪对以美国为代表的基督教国家的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旧日里冷战民族主义浪潮的非合理性,在新的形势下显现为基督教世界对非基督教世界的“欺压”,主要对伊斯兰世界产生巨大的压迫,不仅凸显了不同民族宗教文明对基督教世界的反抗,而且激发了新时代正在崛起的民族主义浪潮的某种时代合理性,也暴露出新时代民族主义运动打上了宗教极端主义色彩,这无疑可以认定为不合理的属性。这种民族主义运动呈现为合理与非合理性同时存在、泥沙俱下的特征。
后“9·11”时代,欧美在对伊斯兰世界逐个打击、各个击破的态势中彰显出基督教文化霸权的本质,充分暴露出西方文化霸权对世界和平带来的时代危险性。“9·11”事件后,美国先后为打击本拉登基地组织而在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在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欧美还在西亚地区联合推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此外,“基穆冲突”中继续酝酿着欧美基督教世界深度打击伊朗、叙利亚两个死结。文化霸权主义是崛起中新民族主义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与历史上政治民族主义、经济民族主义表现不同的是,文化霸权主义更多采用的是从思想层面输出强国意识形态的手段。在冷战思维逐渐淡化的今天,文化霸权主义俨然成为一种新“和平演变”的工具。基督教文化与伊斯兰教文化的针锋相对已经远远超越了单纯教派层面的冲突和对抗,发展成为不同文明、不同文化之间的角力。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称之为是现代文明的冲突。① 此外,文化霸权主义在利用民族主义的极端成分排斥异族文化,抵制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文化上的侵蚀和吞并,是以一种西式的、侵略性的且带有殖民色彩文化迅速兼并其他民族的文化,从而破坏了文化生态的有序发展。
这次以宗教能量释放民族主义能量的运动不仅走向民族分裂主义,而且与极端宗教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形成合力,极大地增加了国际社会的危害性。因此,宗教民族主义运动暴露出宗教极端主义的反动元素是不可忽视的。近年来,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等地区兴起的“ISIS”更是曲解伊斯兰文明的典型,其领袖巴格达迪更是将暴力恐怖行动当作呼唤伊斯兰复兴的外衣,声称要保护人民,公开向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挑衅。其在2014年8月开始就相继发布美国人质被斩首的视频,并威胁称要杀死更多的美国人,“终有一天‘伊斯兰国的旗帜会飘扬在白宫”[12 ]。2015年初,“ISIS”更是有针对性地绑架了90名基督教徒并斩首了其中的21人,他们宣称要将对美国、对基督徒的战斗进行到底。美国扶持的伊拉克当局也毫不示弱,表示要建立起一支基督徒部队以打击“ISIS”。民族主义与宗教主义的合流已经远远超出了过往民族主义所能够延展的范畴,极端宗教势力的介入恶化了基督教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关系。“基穆冲突”规模的升级背后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复苏,更是宗教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相互交融产生了更具危险性的能量。
除此之外,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赋予了民族主义运动新的形式,也增加了对正在崛起中民族主义浪潮的研究难度。著名民族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曾说,“再精致的政治宣传也比不上大众媒体的能力,因为它可以有效地把民族象征融入每个人的生活之中”[13 ]138。特别是21世纪的今天,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已成为每个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在家,还是在工作单位或在地铁公交之上,随处可见使用各种工具上网的人。互联网的出现带给了我们生活的世界翻天覆地的变化,新技术革命让世界不断缩小,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方式也在不断增多。
不过,宗教民族主义主流之外,还有支流。在巴勒斯坦、苏丹、埃及等国也蕴含着宗教民族主义的不安定因素。其中以南北苏丹正式分离为近期最具代表性的案例。2005年南北苏丹签署了关于南北双方实现和平的协议并承认南方实行自治。2011年1月苏丹南部进行公投,超过98%的选民支持南方独立,当年7月,南苏丹正式独立并建立了“南苏丹共和国”。[14 ]从表面上看,南北苏丹分离与石油能源的开采、水资源利用、南北苏丹社会发展差异等方面紧密相关,但更深层次的则表现出南北双方在宗教信仰方面的巨大差异。苏丹南北内战是北方的阿拉伯主义与南方的非洲主义之间的对抗,[15 ]同样也是北方穆斯林与南部本土宗教信仰的对抗。这些差异早在20世纪50年代起就不断酝酿,在近期实现了总爆发。宗教民族主义使南北苏丹民族间的矛盾以宗教对抗的形式集中表现出来,两地人民以宗教为各自的舆论和思想阵地,信徒们采用极端的方式为了维护本民族、本宗教的利益而不断发生大规模冲突,最终引发了冲突与战争。值得注意的是,我们不能简单将宗教民族主义还原为“宗教”运动或“民族主义”运动。[16 ]宗教民族主义产生于特殊的地域环境、社会政治背景和民族构成,并与一定的历史背景息息相关,所以简单将宗教民族主义还原为一种世俗的民族主义显然是不合适的。
三、民族主义浪潮发展规律
民族主义浪潮的演变与发展不是没有规律可循的。揭示民族主义运动发展规律,有助于把握民族主义对人类文明的影响,对于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其实,民族主义浪潮发展轨迹与态势已经显现出一定的规律。从上述民族主义浪潮的发展轨迹中,本文作者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五次民族主义浪潮发展轨迹呈现或隐藏了从正能量的积极作用向负能量的消极作用演变的态势;其中的转折点就是冷战掀起的那次民族主义浪潮。
众所周知,多数学者已经清醒地认识到,民族主义是一把双刃剑,即民族主义对人类的影响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这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然而,民族主义双刃剑在什么时代发挥正能量,又在什么时代发挥负能量?民族主义又是如何从正能量向负能量转向的,即民族主义运动正负能量的转折点是什么?这些问题仍是学界尚未深入研究的课题。
本文作者发现,从前述五次民族主义浪潮发展轨迹看,前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即组建民族国家、两次世界大战掀起的两次民族主义浪潮,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主要起到的是正能量的积极作用。前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合理内核就是对列强乃至帝国主义盘剥世界的严厉打击或抗击。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民族主义促使古代希腊及罗马帝国的衰亡,“民族主义导致了罗马和希腊的灭亡” [17 ]46。把马克思主义这种观点进一步概括就是,民族主义是分解帝国社会单元的锐利武器。有的学者也充分认识到了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充分认识到了民族主义的破坏性和革命性。民族主义是历史上前两种帝国模式崩溃的根本动因之一。新帝国论存在众多缺陷,新帝国模式也摆脱不了未来历史的发展逻辑,即在今后的民族主义时代里,帝国模式将难于形成和维续,进而走向终结”[18 ]。帝国主义的最大不合理性是为了实现帝国核心的主导民族利益而无谓牺牲边缘性民族利益,制造民族不平等或者民族压迫,所以“冷战”激发的民族主义正是对民族不平等和民族压迫的挑战和反抗。
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的社会作用是积极的,发挥的能量是正能量,挑战和反抗的是中世纪基督教帝国。17-19世纪西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民族国家运动的积极作用主要表现为以人性反对神性、用人权反抗中世纪神权、以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反对封建专制。学界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主义,这个时期的民族主义,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统治或异族奴役的旗帜,在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统治,建立民族国家,促进民族市场的形成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19 ]
第二、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社会作用更是积极的,挑战和反抗的是西方列强帝国主义势力。因为两次世界大战激发的民族主义浪潮促使组建民族国家运动的不断扩大,使民族国家运动从西欧拓展到了东欧,再拓展到亚洲和非洲乃至全世界,具有很强的反帝反殖民的色彩,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动摇了帝国主义世界殖民体系的基础。
诚然,不可否认的是,民族主义浪潮具有巨大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民族主义并不是在任何历史发展时代都具有合理性和建设性。当民族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暴露出巨大的缺陷,激发出巨大的社会破坏性。冷战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是民族主义运动发展合理性的转折点。确切地说,冷战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是历史上民族主义浪潮从合理到不合理的转折点。或者说,冷战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是近现代民族主义浪潮由正能量向负能量发展的转折点。冷战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既发挥了完善民族国家的正能量,也激发了分裂国家等危害社会的负能量。“苏东”解体,冷战掀起的民族主义的合理性体现在对苏联帝国主义的冲击与反抗,是民族主义对帝国的分解,充分显现了民族主义浪潮的合理性。但是,冷战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的分解力似乎有些过了头,在某些方面超出了其合理范围。民族主义对帝国的分解是合理的,因此苏联解体是合理的。而东欧有些国家的分解未必全部合理。东欧国家从苏联帝国压制中解放出来是合理的。东欧地区有些国家的再分裂,有的合理,有的并不合理。如前南斯拉夫分解后的再分解,而科索沃的独立是美国强权干预的结果。这次民族分离主义的浪潮存在破坏主权国家完整和破坏社会稳定的不合理元素,为一些国家埋藏了民族分裂主义因素,包括俄罗斯的车臣民族主义,格鲁吉亚境内的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问题,中国的“东突厥斯坦”民族分裂分子、藏独分子等。这些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为了实现其分裂国家的目的不惜以极端恐怖主义手段来采取行动,公然挑衅国家的法律和国家的根本利益,已经成为影响主权国家稳定和发展的桎梏,甚至是严重危害国际社会的“毒瘤”。基于这种判断,冷战成为近现代民族主义浪潮从激发民族主义正能量向激发负能量的转折点。
值得强调的是,中国为什么能够规避冷战掀起的民族主义分解国家的浪潮?这是一种值得学界深入研究的重大问题。冷战掀起的民族主义浪潮,在本质上也是出自民族主义理念、反抗帝国主义压制的结果。这是此次民族主义浪潮的合理性所在。“苏东”解体实质上就是苏联帝国主义体系的解体。这种解体的合理性适用范围仅限于苏联体制。很显然中国不在这个体制之中。中国虽然也在社会主义体系阵营当中,而且是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但是中国率先从苏联体制的压制中解脱出来。中国本就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中国是56个各民族经历过几千年融合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宪法体制、民族政策、民族关系等等,都与苏联不同。基于上述诸多原因,西方“和平演变”的梦想、“民族解体国家”的力量,在中国面前戛然而止。
人类主体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由分立到聚合。因为人类社会的主体发展是由氏族到古代国家,再到近代国家,最后到现代国家。人类早期是氏族社会,社会主体单元只有30到100人。[20 ]118由于氏族社会是人类社会初具规模的社会,因此最初的社会群体规模都是很小的。据人类学资料显示,“一个氏族集团的成员不会很大,据一些人类学资料,一般不超过一百余人”[21 ]768。氏族时代,无数个部落、氏族林立,后来部落合并为部落联盟,再后来部落联盟提升为古代国家时代,到现代发展为不足200个国家。
冷战掀起的那次民族主义浪潮过后,约翰·纳斯比特在20世纪末预言:21世纪,人类将建立1000个国家,其根据是基于“全球性矛盾”和“苏东”解体。这种预言是极其错误的。[22 ]32-33因为大多数国家是多民族国家,经过所谓的“民族清洗”后建立的国家依然是多民族国家,不可能实现清一色的民族国家。“苏东”解体之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点,当今东欧国家依然是多民族国家,并没有实现单一民族国家的设想。因为,“一族一国”理念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在现实社会中运动中碰得头破血流,最后的社会结果还是“多民族国家”。现代主体社会发展的趋势是由分到合,而不是由合到分。因此,冷战民族主义浪潮对国家的分离并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
有学者认定,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的性质都是正能量的,即是帝国强权角逐、争霸的转换和瓦解过程中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从总体上说也都是以反抗帝国霸权为政治背景的:“20世纪人类社会的民族过程,出现过三次重大的全球性民族主义浪潮。它们分别发生于一战、二战和冷战结束前后,……如果不去涉及世界各国人民反法西斯斗争的伟大胜利和历史意义,仅就其起因和所构建的体制而言,都是帝国强权角逐、争霸的结果。这种帝国强权体制的转换和瓦解过程中兴起的民族主义运动。”[1 ]本文作者基本赞同,但并不完全赞同上述看法。如果说,前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是为了争取民族国家的独立和自由,显示的是民族主义运动史上较为合理的社会能量,那么冷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浪潮则暴露出民族主义对国家分裂的巨大危险性之负能量,极大地威胁着世界和平与发展。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全球利益与国家利益高于民族利益,因此已经开始宣告民族主义理念合理性时代已成为过去。当然,无可否认,此次民族主义浪潮依然隐含了反帝国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合理性成分。
如果说前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是合理的,而冷战掀起的第四次民族主义浪潮多半是合理的,那么第五次浪潮则应当断定是不合理的或是非理的,对人类具有巨大的破坏性和危害性。因为,第五次浪潮不是反抗帝国压制的民族主义浪潮,而是宗教参与、渗透和变形的民族主义浪潮,是一种“宗教民族主义”。
这场宗教民族主义浪潮所激发的对社会影响力主要是负能量的或消极的,集中体现为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等三种恶势力。从极端的伊斯兰分子制造“9·11”事件招致后“9·11”时代基督教世界的反击,进而造成了伊拉克危机和叙利亚危机,进而导致“ISIS”极端组织脱颖而出,都彰显了宗教民族主义的非理性、破坏性。“9·11”事件中,遇难者高达2996人,[23 ]大都是经济界金融业的世界精英。联合国发表报告称此次恐怖袭击对美经济损失达2000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生产总值的2%,① 对全球经济所造成的损害高达1万亿美元左右 ② 。后“9·11”时代,基督教世界相继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和利比亚卡扎菲政权,严重威胁了叙利亚政权,给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的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使得“ISIS”极端组织有了可乘之机。众所周知,这个宗教极端组织采用自杀式袭击、肆虐屠杀人质、大批屠杀俘虏等反人类非人道手段,挑战人性的底线,[24 ]加重了当代“基穆冲突”给人类带来的灾难。总之,“基穆冲突”及其引发的企图建立“ISIS”极端组织的行为对全世界的破坏性、危害性、非人道性是无法估量的,充分证明了这场负面的宗教民族主义对人类影响的消极性和负能量。
从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看,民族主义的出路是让位于国家主义而成为国家主义的“助理”,国家主义进一步让位于全球主义而成为全球主义的“助理”。近现代社会主体单元发展规律是从民族国家主义到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分解,再到用国家主义扬弃民族主义,最后走向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与全球主义并存的发展态势。诚然,在民族没有消亡之前,民族主义绝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它将以不同表现形态、暴露不同时代特点,不断地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正负两方面的影响。虽然随着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全球主义展现了新时代发展的方向,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已经成为“过去”或者已经不能代表人类文明的发展方向,但是民族主义元素远未消亡,反而以某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展现在新时代的特征中。庞中英曾评说,“民族主义一方面抵制全球化,一方面也在利用全球化;在全球化方面,一方面在弱化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又在促进民族主义”[25 ]。
新的民族主义浪潮是否已经到来并不重要,而怎样对待变化中的民族主义和宗教元素却是值得我们深思。本文作者深信,虽然当今时代国家主义意识形态依然是时代的主流,但是全球主义已经展示了时代发展的新方向,国家主义迟早会让位于全球主义。所以,民族主义虽然还将长期存在,但终将被国家主义、全球主义所包容。
参考文献:
[1] 郝时远.20世纪三次民族主义浪潮评析[J].世界民族,1996(3).
[2] 光仁洪,管敬绪.读《一八四八年欧洲革命史》[J].世界历史,1984(1).
[3] 周平.民族政治学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4] 曹兴,王宏岳.民族主义浪潮的发展轨及特点[N].中国民族报,2015-06-26.
[5] 唐贤兴.近现代国际关系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6] 赵立坤.20世纪民族主义浪潮试论[J].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1).
[7] 爱德华·卡尔.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M].秦亚青,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
[8] 杨恕.20世纪80、90年代全球民族主义浪潮及相关理论探讨[J].新疆社会科学,2005(5).
[9]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1500 年以后的世界[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9.
[10] 高永久,等.民族学概论[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9.
[11] 弗兰西斯·福山.国家构建——21世纪的国家治理与世界秩序[M].黄胜强,许铭原,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12] 余宇白.“伊斯兰国”为何敢挑衅美国?[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11-22.
[13]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M].李金梅,译.上海:上海世界出版集团,2006.
[14] 吴文斌.苏丹南部公投最后结果出炉 98%选民支持分裂[N/OL].(2011-02-08)[2016-07-01].http://world.people.com.cn/GB/13871838.html.
[15] 刘辉.民族主义视角下的苏丹南北内战[J].世界民族,2005(6).
[16] 钱雪梅.宗教民族主义探析[J].民族研究,2007(4).
[1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论民族问题:上册[M].北京:民族出版社,1987.
[18] 张三南,谢丽萍.论民族主义与帝国模式的终结[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9(3).
[19] 熊家学.冷战后的民族主义浪潮及其影响[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1).
[20] Christopher R. Decorse.Anthropology: a Global Perspective: Third Edition[M].Prin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n, 1998.
[21] 吕大吉.宗教学通论新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
[22] 约翰·纳斯比特.大挑战:21世纪的指南针[M].朱先鉴,等,译.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
[23] 老任.911恐怖袭击事件:美国人永远的伤痛[N/OL].(2006-09-08)[2016-07-01].http://world.people.com.cn/GB/1029/42355/4796583.html.
[24] 曹兴.ISIS:来自何处?去往何方?[N].中国民族报,2014-08-29.
[25] 庞中英,彭萍萍.关于全球化·社会主义·民族主义关系的对话[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2(4).
Abstract:Rather than existed since the ancient time, nationalism is anoutcome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till the age of modern nation-state. Based on the pectination of the trajectory ofmajor nationalist wavesin modern histor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gular pattern of development of several nationalist waves particularly and highlights the double influences of the recent nationalist waves on human beings in order to reveal the regular pattern taken on by the five waves of nationalism from the positive energy of benefiting society to the negative energy of harming the society.
Keywords:nation-state; nationalism; globalization
﹝责任编辑:黄仲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