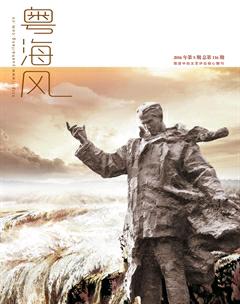书画价格与价值关系的混乱
丁涛
今年三月底,笔者曾在《扬子晚报》见到一则醒目的报道,题为《张大千超越齐白石重夺“最畅销中国艺术家”榜首》,内容是,胡润研究院,根据2015年度公开拍卖市场作品总成交额前100名中国在世和已故的“国宝”艺术家排序,发布了2016年胡润最畅销中国艺术家榜单。并据此,胡润百富董事长兼首席调研员胡润表示:“如果说钱能衡量艺术品的好坏,那这100个人可以算是中国艺术史上最具价值的艺术家了。”
且不说“中国艺术史上”与“最具价值的艺术家”是由这一年的拍卖活动而铆定的100名“国宝”,是如何荒唐和不合逻辑,仅就“钱能衡量艺术品的好坏”而言,其说辞也是显见武断和谬误的。
这里的话题涉及书画作品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实践中我们会发现,两者有时同步有时背离,通常地说,某些书画作品,价格高价值也大;也有不少作品,价格虽高,而价值却是不大的。特别在文明不彰、道德滑坡现象比比皆是的当下,书画市场被扭曲就不足为奇了。
在物质产品的生产与销售中,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了它的价值,而其价格,则是价值的货币表现。受到市场供求关系的影响,经常围绕着价值自发地上下波动,并体现了同步和协调性。一只不同厂家生产出来的普通玻璃茶杯,价值接近,价格差距也不会太大。
但是,作为精神生产的书画作品,特点就截然不同。在同样的宣纸上作同样大小的画,同样耗费一个小时(姑且亦谓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吧),成品在大画家与初学涂鸦者之间形成的价值与价格决然大相径庭,一幅可以以千万元计,一幅则分文不值!
当然,其中有一个潜在因素不能忽视,即大画家在这一个小时内完成的作品,虽然“生产成品”的具体“必要劳动时间”不长,但要达到如此高妙地一挥而就,与之几十年的素养积累和功力磨炼却是密不可分的,读者务必明鉴。
在书画中,价值与价格之间的关系与物质产品不可同日而语。特别在当下,远非正比关系所能概括和定位。看一看,按照胡润榜所列,2015年“前10名最贵的国画作品”次序吧:潘天寿《鹰石山花图》(镜心)、崔如琢《葳蕤雪意江南》(镜心)、李可染《井冈山》(镜心)、齐白石《“叶隐闻声”草虫册·册页》(十八开)、潘天寿《鹰石图》(镜片)、郎世宁《纯惠皇贵妃朝服像》(镜框)、崔如琢《山水》(四屏镜心)、潘天寿《劲松》(立轴)、无款《楷书佛经册》(三十九开),成交价从27945万元到8782万元,价格不为不高。其中崔如琢作品在“最贵”中竟然出现了两次。还有一项比较性的表格,在“前十名价格最高的在世艺术家作品”中,崔如琢的作品,拥有五个名次,占去一半指标。此表见刊于《扬子晚报》2016年3月25日,白纸黑字的赫然标题是《中国“最贵”的在世艺术家,马云上榜,崔如琢连续两年居首》。由此似乎就可以毫不含糊地认定崔如琢的中国画作品,价值超群,国内第一!笔者以为,绝非如此也。对于崔如琢作品的艺术样态及价格、价值,行内多有微词,作品与“国宝级”相去甚远,然而其作品在市场上十分值钱又是事实,如何解释呢?我以为在乱象迭出的社会大背景下,书画市场常常形成的价格与价值错位的形象,大抵出于以下几个具体因素:
一、炒作手段泛滥
不少书画家会利用各种途径不着边际地吹嘘自己的作品。有的无中生有地谎称是某某大师的入室弟子,得到指授;有的祭起骗术,以获取这个、那个大奖招摇过市,这类所谓“中国文化艺术人才协会”“中国文化信息协会”“世界艺术家精英协会”等莫须有的组织,高价售出“金奖”“银奖”,正中下怀地满足了一些人自吹自擂的需要;有的则相互联手,抬轿子、吹喇叭,在电视、报刊上频繁出现以博盛誉;有的买通亲近者撰写虚夸的祝颂文字,等等不一而足。
二、官本位的左右和影响
我们稍加留意便会发现,本来是带有群众文艺组织性质的美术家协会和书法家协会,却被浓厚地染上了官方色彩。争上一个主席或副主席、秘书长、理事等身份显著的职级,作品的价格就会随之飙升上去。副主席动辄弄上个十几名已不足为奇。其实在专业协会混上个一官半职,已无碍于专业水平,却常常与找人、找关系,甚至贿选有关。民间对近年书法家协会主席的种种非议,已足以佐证上述现象。
“官本位”意识毫不含糊地作用于书画家展览的势头,正与日俱增。君不见,展览的开幕式,报名出席的贵宾,不总是以与会者官帽大小为次序么?似乎被邀出场的官位越高,展览作品的水平就会越高一样,其实不然。正如当前不少书画家的名片上,写上不少头衔,无外乎告诉对方“我有多么了不起”,能相信吗?!可笑而已。
三、媒体有失公正的误导
电视台、报刊都一般设有专门从事介绍书画家作品的栏目,有一些比较客观、公允,帮助大众认识书画家及其作品,提高人们的眼界和鉴赏水平。但也有不少媒体,致力于创收而夸大其词的宣传,对一些并不优秀的书画家及其作品,乱称大家、大师,让人们形成了审美的错觉,而误导了不少以书画为投资对象的企业家、收藏家。更有甚者,将作品的缺陷胡吹为长处,指鹿为马,混淆视听而坑害读者。
四、优劣、美丑审美价值观判断标准的混乱
文艺的宽松政策,从改革开放实施以来,书画作品便日见繁荣发达,逐渐展示了一派多元化的热闹局面。不过问题也随之而生。围绕作品的市场化,各敲各的锣鼓,书画优劣、美丑、好坏的判定基本标准,莫衷一是,十分混乱模糊。鉴于艺术作品的好坏鉴别,远非体育项目的比赛可以锱铢必较,它只具有大体性而无确定性,只具有品位高低的倾向性而无“二三得六”的绝对性,对一件作品的评价常常会众说纷纭,甚至会得出截然相反的结果。好画能卖出好价钱并不尽然。有行内人玩笑地说,“懂画的不买画,买画的不懂画”。不少有经济实力的企业家,选择买画的敲定,往往是类如郑板桥所指出的那样是“耳食家”的行为,受制于耳听书画行情的分析,而这种“行情”,与可靠无缘,随意性太大,几无标准可循。观察2012年的一份“近现代书画行情·行情预测”用语,表述为:“陈之佛,‘迅速提升阶段;程璋,‘低价位区域徘徊;何海霞,‘价格不可限量;潘天寿,‘持续上涨;吴昌硕,‘稳步上涨;潘玉良,‘价位跳高比较大;齐白石,‘稳定上涨;任伯年,‘涨幅一般;吴湖帆,‘涨势中的正常回落……”,等等,这种统计罗列,纯由特定时段内市场之于作品的价格高低决定,内里并无价值的作用,其实质也是艺术批评标准的游离不定所致,使价格与价值 相对的一致性丢失。
关于价格与价值的问题,具体到在世书画家本人,常有自己的考量标准,如某某作品每平尺1500元,某某每平尺5000元,某某每平尺20000元,等等。作者标准的认定,往往是立足于形势比较后衡量自身作品的价值量化于价格的表现。更有在价格上具体到卖画规矩的制定,如1937年齐白石声明“送礼物者不报答,减画价者不必再来,要介绍者莫要酬谢。……”继又于1940年声明:“花卉加虫鸟每一只加十元,藤萝加蜜蜂每只加二十元,减价者亏人利己,余不乐见。”这样到明确入微的价格裁定,实是自审作品价值的价格标尺,也使我们管窥到书画市场价格与价值的另一种翔实表达方式。
针对当下书画市场价格与价值的乱象,梳理好买方、卖方、舆论宣传方、鉴定方、书画家本身方方面面的关系,使之尽量走上公平合理、繁荣发达的大道,显得尤为必要,但难度不小。一方面要提高相关各方对书画作品的审美鉴赏水平,建立包括美丑、高低、真假等判断的基本标尺;另一方面要提倡实事求是精神,避免、摈除假话、虚话的欺骗伎俩,使“货真价实”牢牢扎根于书画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