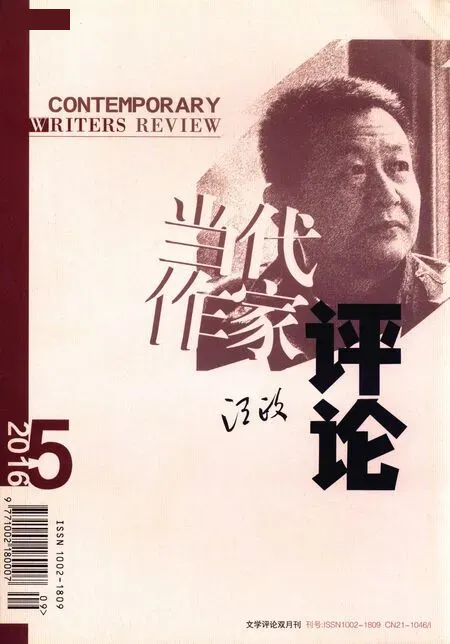沪上传奇与异邦故事
——谈朱晓琳近年来的小说创作
李松睿
作家作品评论
沪上传奇与异邦故事
——谈朱晓琳近年来的小说创作
李松睿
上海从来不缺少传奇。这座屹立在黄浦江畔的大都会自开埠之日起,就以其蓬蓬勃勃难以遏制的生命力,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一方面,遍地租界、华洋杂处的历史境遇,使得这里既是帝国主义列强入侵中国的桥头堡,也是中国人接触西洋文化的最前线;另一方面,上海长期作为远东第一大城市,它那畸形繁荣的经济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都市文化,改写了中国的文化版图,并推动着中国传统文化向现代的艰难转型。于是,各式各样的文化、思想以及价值观在这座城市相互碰撞、交锋、融合、新变,冲击着上海市民的思想,煎熬着他们的灵魂,在他们的生命历程中刻下无法磨灭的印记。从20世纪初叶开始,无数上海作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谱写着一幕幕极为动人的都市传奇。特别是以苏青、张爱玲为代表的女作家,用女性那特有的敏感与细腻,捕捉到上海市民在那个错动复杂的年代所经历的大起大落,以及这一切背后的无奈与落寞。为我们留下了不少文学史上的经典佳作。
显然,同样生活在上海的女作家朱晓琳正是在这一文学史脉络上,继续书写着有关上海的都市传奇,并显影了上海、乃至中国在当今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巨大变化。这位女作家出生在上海,在这座城市华洋杂陈、包容并蓄的文化氛围中长大。20世纪90年代初,朱晓琳远赴欧洲,在法国里昂第二大学研究法国现代文学,获文学硕士学位。回到上海后,她又在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学院任教,专门为外国留学生讲授汉语课程。这一独特的经历,使得她始终生活在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相互碰撞、交融的核心地带。这无疑影响着朱晓琳观察生活、思考世界的视角,并决定了其写作的基本主题。早在20世纪90年代,这位女作家就主要以留学生为题材进行小说创作,写出过《爱情国境线》《无国界叙事》以及《葡萄酒贵族》等作品。不过与曹桂林、周励等人的小说往往只专注于描写中国人在国外的种种遭遇不同,朱晓琳还特别关注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生活,尝试去全方位、多角度地呈现异域文化的冲击下,人性如何被无情地改写。这无疑是其创作最为特殊的地方。而朱晓琳近年来发表的几部中篇小说则延续且深化了这位作家对于当代中国最新的观察与思考,并折射出中国在新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中的位置变化。
一
纵观朱晓琳近年来的小说创作,我们基本上可以将其笔下的故事分为两类。第一类小说包括《上海探戈》(2007)、《上海屋檐下》(又名《教授娘》,2008)、《夜上海波尔卡》(2010)以及《幸福草》(2012)等作品。我们也可以将它们称作“上海传奇”,其主要内容是异乡人(既包括外国留学生,也包括进城务工人员)如何融入上海这座城市的故事,并重点呈现了他们在这一过程中所经历的内心煎熬与文化碰撞。
小说《上海探戈》主要讲述的是爱德华、西尔维娅、河村俊二以及尼姆等外国留学生在上海的种种“奇遇”。我们会发现,虽然距离新中国成立已经过去了60多年,但鲁迅先生当年所描绘的那种洋人被一批“高等华人”包围,最外面则是广大劳动者的同心圆结构,在上海仍然存在。只是因为有着白皮肤、蓝眼睛,外国人在这座城市就天然地享有特权。以主人公爱德华为例,这个来自英国的小伙子,在老家既没有显赫的背景,也没有雄厚的财力,却靠着那洋人的面孔和半通不通的汉语,在上海如鱼得水,享受着香车美女的簇拥,过着自己在英国连想都不敢想的生活。正像朱晓琳所描写的,在早高峰人潮汹涌的地铁上,人人都想抢个座位。然而一个头发都白了的老头见到20多岁的爱德华后,却非要把自己的座位让给后者。这也就难怪爱德华在享受了种种特权之后,对中国人会心生轻蔑,并感慨“在中国人眼里,我们外国人就是比他们高贵”。*②③朱晓琳:《上海探戈》,《小说界》2007年第4期。
显然,朱晓琳在小说里揭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在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特别是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在现代化程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上已经不输于任何发达国家,但在文化上却总是存在着自卑感,在金发碧眼的外国人面前直不起腰来。这无疑是积贫积弱的近代史给中国人留下的精神创伤,使得我们在经济崛起之后,始终无法建立起与此相应的文化自信。而朱晓琳的写作最为深刻的一点,是她不仅写出了上海人在与外国人交往时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精神萎靡,更写出了外国人在这一过程中的异化。小说中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场景是,爱德华请自己的妹妹和女朋友在一家餐厅吃饭,因为上菜慢了,竟不顾英国人的风度和礼貌,对餐厅老板破口大骂。长期以来被中国人“宠”坏了的爱德华,此时已经受不了一点点怠慢,把早年养成的风度和礼节忘得一干二净。以至于他的妹妹露西在事后要悄悄地提醒爱德华:“你要小心呢,以后回英国别让父母都不认识你了。”②
如果说《上海探戈》中所描绘的上海,是一个外国冒险家的乐园,让那些金发碧眼的洋人轻轻松松地被“宠爱”,赚大钱;那么小说《夜上海波尔卡》则揭示了另一类外国人在上海的特殊遭遇。这类人自幼生长在西方国家,拿着外国护照,讲着一口流利的外语,思维模式、行为方式与外国人没有一点区别,但却长着一副东方人的面孔。当他们来到上海时,这座城市会收起笑脸,突然露出其残酷的一面。应该说,这是朱晓琳一贯关心的话题。在《上海探戈》中,作家在描写西尔维娅时,就顺带写到这位瑞士姑娘自幼生长在德语家庭中,因此法语并不标准,但却在应聘法语教师时,成功地击败了一位出生在巴黎的华裔青年。因为中国学生“总觉得从洋面孔嘴里学来的外语才更正宗些”。③只是在《夜上海波尔卡》中,这一主题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开。
小说《夜上海波尔卡》的主人公廖嘉平是一位澳大利亚籍华裔青年,毕业于墨尔本音乐学院。在上海学习汉语期间,他希望靠弹钢琴的技能打工养活自己。与很多外国人感慨“只要你长着西方人的脸,在上海就不愁挣不到钱”*朱晓琳:《夜上海波尔卡》,《上海文学》2010年第7期。不同,廖嘉平这个货真价实的澳大利亚人在求职时却处处碰壁,历尽艰辛才在一家酒店谋得了在大堂弹钢琴的职位。不过很快,他就凭借自己出色的琴技和流利的英语,开始在上海富商郭其龙的家中担任家庭教师。在与郭其龙及其家人交往过程中,廖嘉平发现虽然上海人在金发碧眼的洋人面前异常友善、热情,但对自己则显得刻薄而有失尊敬。当他提出郭家的钢琴需要重新调音时,郭其龙却表示钢琴不过是个摆设,能弹出声音就行了,无需那么讲究。而郭太太和朋友打麻将时,竟不考虑廖嘉平的实际感受,硬要他在旁边弹琴助兴。她甚至还不顾对艺术家的基本礼节,经常强行打断廖嘉平的演奏。最终,廖嘉平无法忍受郭家的蔑视与侮辱,愤然辞去这份高薪工作。
有趣的是,朱晓琳虽然在小说中对上海的新富阶层颇多讽刺,但对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普通市民则寄予了深厚的感情。例如,廖嘉平的房东周先生晚年丧子,家境并不富裕,但却对廖嘉平没有丝毫排斥,给他提供了无微不至的帮助。正是在周先生的带领下,廖嘉平参加小区居民自发成立的互助组织,以自己的技能帮助邻里,渐渐在这座以排外闻名的城市里找到家的感觉。他还和周先生一起,为条件简陋的打工子弟学校开设音乐课,为孩子们送去美的享受。朱晓琳正是通过这样的描写,让读者知道上海并不仅仅是个名利场,上海人也不全是崇洋媚外之辈,这座城市同样洋溢着温情,有美好的人与事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这无疑传达了女作家对于上海的理解与感悟。
如果说朱晓琳在《上海探戈》《夜上海波尔卡》里,主要描写的是外国人在遭遇文化差异时所经历的震惊体验;那么在《上海屋檐下》和《幸福草》中,作家则调转了自己的视角,去观察乡下人来到上海后的种种境遇。显然,今天的朱晓琳已经扩展了自己的取材范围,不再仅仅关心中西方文化之间的碰撞,而是开始去思考某些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更为重要的话题:即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异与弥合。在笔者看来,这无疑是朱晓琳的思想与写作逐渐成熟的标志。
小说《上海屋檐下》讲述的是主人公黄大姐为了帮弟弟黄教授看房子,离开农村到上海暂住的故事。虽然享受着现代化的生活设施,但黄大姐在上海却并不开心,总是与这座城市格格不入。她试图与周围的邻居搭讪聊天,却不断遭遇猜忌的目光。她养了几只小鸡排遣寂寞,却因为扰民被告到了派出所和居委会,不得不忍痛把小鸡杀死。而当她因为闲得无聊,捡些空塑料瓶卖钱时,更是饱受邻居的冷眼。甚至连她亲手拉扯大的弟弟,都指责她收废品给自己丢人显眼。而与黄大姐境遇相仿的,还有小说《幸福草》的主人公曹根夫妇。他们一个在小区门前收废品,另一个则在小区里当家政工。虽然勤劳本分、认真工作,但他们却总是不被待见,还经常受到小区业主和保安的故意刁难。在这里,分属于乡村与城市的两种生活方式、价值观之间的激烈碰撞,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描写。上海在某种程度上成了黄大姐、曹根夫妇这些异乡人既爱且恨的炼狱,让他们在物质上获得满足的同时,不得不在精神上饱受煎熬。
应该说,朱晓琳在这两篇小说中的描写是非常深刻的。伴随着改革开放和户籍管理制度的松动,中国有太多人从农村来到北京、上海这样的超大型城市寻找新的机会。他们在城市里任劳任怨、辛勤工作,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由于这些进城务工人员往往只能从事重体力劳动或服务业,再加上价值观、生活习惯与城里人格格不入,使得他们总是被人歧视,甚至还常常会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进城务工人员对城市建设的巨大贡献,与在城市里感受到的歧视,在他们心中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让他们时刻感到痛苦。这无疑是当代中国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朱晓琳的小说虽然触及到了这一重大问题,但并没有深挖下去。在《上海屋檐下》中,黄大姐虽然被人歧视,但总是热心助人,不仅帮邻居买菜,找回走失的宠物,还组织小区业主联合起来反对物业公司侵占绿地,最终融入了这个上海社区。当黄大姐离开上海时,邻居们甚至还有点儿舍不得她走。而在《幸福草》里,曹根夫妇因为“在小区居民中人缘好,肯吃苦耐劳”,*朱晓琳:《幸福草》,《小说月报(原创版)》2012年第9期。被聘为小区老年餐厅的正式员工,结束了靠天吃饭的日子,可以每月领取固定工资。笔者在这里当然不是认为黄大姐、曹根夫妇的“幸运”没有丝毫现实可能性,只是作家向壁虚造的产物,但考虑到中国有数量巨大的进城务工人员挣扎在饥饿线上,这样的描写多少让人生出曲终奏雅、粉饰太平之感。
二
而近年来朱晓琳笔下的第二类作品,则包括《诺曼底彩虹》(2011)、《非洲风筝》(2011)、《白金护照》(2010)以及《伦敦眼》(2012)等四部小说。它们不再是发生在上海的都市传奇,而是去讲述上海人在异国他乡的所见所闻。与《爱情国境线》《无国界叙事》这些朱晓琳的早期作品相比,这些小说里的外国不再是一个充满希望和梦想的地方,其中上海人也不再像当年的留学生那样生活清苦、用功读书。伴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的腾飞,一部分中国人已经富了起来。当他们来到异国他乡时,心态、做派已经和当年那些清贫的留学生很不一样。正像很多境外媒体报道的,他们在国外高声说话、随地吐痰,让当地居民非常愤怒,但又挥金如土、一掷千金,极大地拉动了当地经济。可以说,正是这些让外国人既爱且恨的中国人,改写了今天的世界图景,更显影了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中的地位。而所有这一切,都在这些作品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诺曼底彩虹》讲述的是上海姑娘刘思宁高考失利后到法国留学的故事。她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家境并不宽裕。然而母亲杨清芬觉得送女儿出去留学,既能挽回因高考失利而丢的面子,又能让女儿将来找到一份好工作,于是毅然决定把家里的房子卖掉,送女儿到法国留学。不过从小就娇生惯养的刘思宁似乎无法理解这一决定对家庭的意义,也不能体会母亲身上所承受的压力。在法国学习期间,她看到同样来自上海的同学纷纷购买名牌服饰、豪华汽车,在欧洲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自己也耐不住寂寞,整天和米拉拉、健健等人混在一起,无心向学。偶尔给家里打个电话,也只是向母亲要钱。而杨清芬对此则一无所知,为了让女儿在没有压力的情况下认真读书,她甚至还隐瞒了自己已经把房子卖掉的事实。朱晓琳以平行的方式结构小说,交替讲述母亲在上海的含辛茹苦与女儿在法国的无所用心。这一对照手法的运用使得这篇小说具有较强的感染力。在读到小说的结尾处,杨清芬费尽心力凑够了路费,赶赴法国将被学校开除的女儿接回上海时,读者会忍不住感慨可怜天下父母心。
如果说《诺曼底彩虹》呈现的是一幕关于留学的悲剧,那么小说《非洲风筝》所展现的则是一出喜剧。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宗小西是上海的一名初中生。由于成绩很差,宗小西在学校里总是抬不起头来,人也变得内向忧郁没有自信。在看到孩子根本不可能考上大学后,宗小西的父母决定让他随姑姑到喀麦隆去读书。他们并不指望宗小西能在非洲学到什么知识,只是觉得在那里如果能把法语学好,将来也能找份不错的工作。然而来到喀麦隆后,宗小西这个在中国没有一点突出之处的学生,立刻成为学校里的明星。除了法语不太好,他的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渐渐地,这个原本内向羞涩的孩子开始有了自信,人也变得开朗多了。当来自欧洲的小朋友表示出对于东方人的轻蔑时,他敢于提出异议,并要求对方道歉。有些时候,他甚至还能够帮姑姑管理酒店,指挥下属。广阔的非洲草原,成了宗小西自由驰骋的新天地。在这里,朱晓琳显然是通过对比的手法,赞扬了崇尚自由的教育理念,并对扼杀青少年个性的中国教育制度提出了质疑。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涉世未深,但随着宗小西对喀麦隆的社会生活逐渐了解,他开始批评喀麦隆人大多是文盲、数学极差、没有时间观念、做事缺乏计划等问题,并在不经意间流露出某种洋洋自得的神情。似乎上海人之所以能够在喀麦隆轻轻松松赚大钱,完全是因为他们更聪明、更勤奋,而当地人则怠惰慵懒。这就使得朱晓琳笔下的上海人在面对欧美人时,总是有些卑躬屈膝,对非洲人则会抬起把他们那“高贵的头颅”。在这里,作家显然捕捉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不少中国人虽然还没有足够的自信心和金发碧眼的欧美人平起平坐,但已经开始瞧不起曾经和我们以兄弟相称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他们似乎忘记了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非洲人的怠惰并不是这片土地贫穷落后的原因,而是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制度的结果。这多少令人感到有些遗憾。
在笔者看来,或许这类作品中更值得关注的,是《白金护照》和《伦敦眼》这两篇小说。它们深刻地写出了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笼罩在发达国家头上的美丽光环如何被现实的铁壁撞得粉碎。小说《白金护照》的主人公谢如芳、苏杨夫妇,是上海一所高校的青年教师。他们利用公派出国一年的机会,在美国生了孩子,以便为下一代换取一张“白金护照”。在他们的想象中,孩子有了美国护照,就可以免费享受发达国家的医疗和社会保障。连他们自己,也能靠孩子长期在美国定居。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们在美国省吃俭用,放弃了科研,也没有任何娱乐,但仍被天文数字般的医疗费压得喘不过气来。而美国糟糕的治安,更是让谢如芳在产前遭遇抢劫,不幸早产,生下了一个患有先天性疾病的女孩。在女儿真地拥有了“白金护照”后,他们决定回国,放弃留在美国的机会。因为他们最终认识到,在美国自己永远只能是二等公民,而在中国则是社会地位较高的高校教师。只有在经济高速发展的祖国,才是让他们大展身手的舞台。
而小说《伦敦眼》则通过描写叶兆其、苏宛夫妇在去国离乡20年后重返上海的经历,展现了中国社会的活力与巨大变迁。叶兆其夫妇在出国前都是上海一家杂志的编辑。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出国热潮中,他们想尽办法来到英国,试图开启新的生活。然而文化上的差异,使得叶兆其夫妇根本不可能融入英国主流社会,只能靠开一家破旧的中餐馆勉强维生。由于他们对中国的认识还停留在20年前,所以回国前还特意买了些旧衣服准备送给亲戚朋友。可他们刚下飞机,就震惊于上海人生活的巨大改变。看着苏宛哥哥的私人轿车和复式公寓,叶兆其夫妇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而那些送给亲戚的礼物,更是让他们颜面尽失。正像朱晓琳所写的,他们出国时以为自己“逃离了沉船”,*朱晓琳:《伦敦眼》,《小说界》2012年第1期。但回国后却发现已经错过了太多机会。为了将这种今昔对比表现得更加充分,作家还颇为戏剧性地安排叶兆其的女儿在他当年的同事蔡根荣家里做护理工。20年前,蔡根荣不过是杂志社一个工人编制的发行员,可如今却已经是公司老板,甚至在英国还拥有房产。当年在英国社会底层辗转挣扎时,至少生活在发达国家成了叶兆其夫妇唯一的引以为豪的地方,但看着上海日新月异的变化,他们不由得唏嘘不已,感慨岁月的虚掷。
三
从上面对这两类小说的分析来看,朱晓琳特别善于在自己的作品中将几种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并置在一起,通过它们之间的冲突与融合构建戏剧性冲突,推动小说叙事向前发展。她近年来的小说创作,几乎全部是以这种方式写成的。考虑到作家所处理的题材,不是外国人、外地人的沪上传奇,就是上海人的异邦故事,本身就蕴涵着不同文化、价值观之间的冲突。因此,以这种方式结构小说虽略显单调,但却是非常准确、妥当的。于是,我们在朱晓琳的笔下看到,中国与西方、中国与第三世界、城市与乡村、过去与现在正发生着激烈的碰撞。几乎所有人都在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的裹挟下,来到了文化冲突的核心地带,上演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可以说,无论是爱德华的得意洋洋、还是黄大姐的饱受刁难、抑或是叶兆其的无奈悔恨,其命运遭际与个性品质并无太大关系,他们只是碰巧生在中国、来到上海,赶上了这个迅猛发展的时代。细细想来,朱晓琳的这些作品倒也真得了几分张爱玲那篇《倾城之恋》的神韵。
在这个意义上,阅读朱晓琳其实也就是阅读我们所身处的时代。今天的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高速发展后,已经崛起为一个世界强国,改写了整个世界的面貌。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阴魂不散的大背景下,中国更是充当了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如此迅猛的发展,不仅让外国人感到震惊,对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冲击其实也不亚于一场革命。简单地对比一下上海这样的现代化城市和中西部地区贫瘠的乡村,其间的落差足以让人瞠目结舌。朱晓琳笔下的黄大姐、曹根夫妇正是因为遭遇了这一落差,才饱受歧视、备感痛苦。而高速发展的中国也让那些城里人感到有些眩晕。他们开始拥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却缺乏相应的文化修养和自信,看到洋人卑躬屈漆,面对穷人则趾高气昂,走出国门后,更是挥金如土,肆意享乐。朱晓琳笔下的郭其龙、刘思宁以及米拉拉正是如此,让人不禁为他们的行为感到惋惜。而与此同时,西方人面对日新月异的中国,心中也别有一番滋味。曾几何时,西方人自视为天之骄子,生活亚非拉土地上的居民在他们眼中不过是一群土著。然而到了今天,他们在本国已经很难找到工作,只能把遥远的上海当作冒险家的乐园,其失落是可以想见的。在女作家的笔下,爱德华、西尔维娅这些金发碧眼的洋人在上海过得春风得意,但内心深处却总有几分苦涩与无奈。可以说,在朱晓琳近年来的小说创作里,对中国社会在飞速发展的过程中不同人群的心理状况进行了全方位的描绘。在笔者看来,这或许是朱晓琳小说创作最大的意义吧。
(责任编辑王宁)
李松睿,文学博士,中国艺术研究院《艺术评论》杂志社助理研究员。